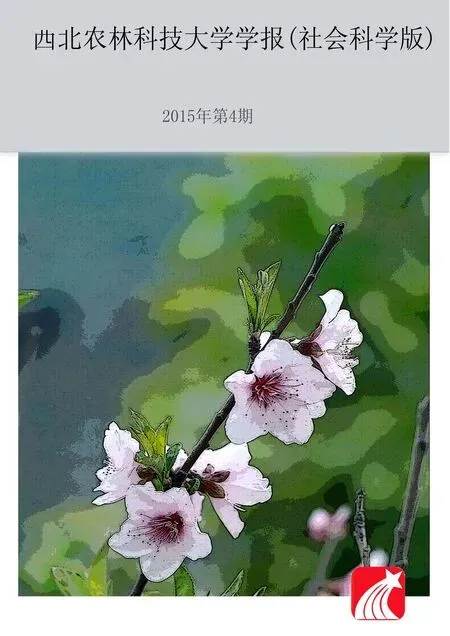城市化路径的实践与反思:从就地城镇化到激进城市化
2015-02-21曾红萍
曾 红 萍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城市化路径的实践与反思:从就地城镇化到激进城市化
曾 红 萍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苏南地区正在经历城市化路径转变,即从相对保守的就地城镇走向激进的城市化。通过对苏南A镇城市化路径分析,揭示了两种城市化路径不同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就地城镇化是村社主导的、以村庄规划为手段、以适应工业化和改善生活条件为目标的渐进的城市化;激进城市化则是地方政府主导、以“撤村并居”为手段、以土地指标和城市化率为目标的激进的城市化。政府推动的激进城市化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但因其与地方经济社会结构不相匹配,从而面临资金、政治社会稳定、社区文化再造的困境。
就地城镇化;激进城市化;城乡一体化;“撤村并居”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农村依靠村社组织进行内部资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动员,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工业化[1],农村工业化通过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和居住向社区中心集中的方式推动了农村社区的城镇化。费孝通在苏南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小城镇”建设理论成为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化路径的风向标。费孝通先生主张发展“小城镇”的目的在于解决改革开放后农村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将“小城镇”作为人口“蓄水池”吸纳农村向外的人口流动,为农村和城市两极“减负”,从而实现社会总体的稳定[2],即农村工业化带动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解决农业劳动力内卷化[3]问题,再围绕工业生产实现农村居住模式向社区中心或集镇集中的模式,从而就地实现城镇化。“小城镇”理论的核心在于“离土不离乡”“工农相辅”“就地城镇化”。由此可见,就地城镇化是苏南地区农村工业化推动下因地制宜的城市化发展路径与模式。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推动城市化向纵深方向发展。城市化的平面扩展带来了郊区土地的城市化,国家为了保障耕地红线,通过对土地用途管制的形式抑制农村过度城市化。同时,国家为了调和城市扩张和耕地保护之间的冲突,在部分省市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来缓解二者的矛盾,即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相匹配,“撤村并居”是“增减挂钩”的重要内容。在此政策背景下,苏南地区的城市化路径正在发生转变。目前,学界对苏南城市化的系统研究主要停留在小城镇阶段,而对当前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城市化路径转换问题认识不足,本文的目标之一在于通过对当前苏南地区正在经历的新型城市化路径与就地城镇化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厘清苏南地区在“增减挂钩”政策推动下的城市化实践逻辑。“撤村并居”对节约耕地、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和推动城乡一体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其是否具有限度和效度?这是本文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的客观社会现象。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农村要不要城市化,而在于如何稳定有序地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本文的核心议题在于探寻苏南地区因地制宜的城市化路径。
二、苏南A镇城市化路径实践
(一)地域社会介绍
A镇位于苏南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位于上海、无锡、苏州一小时经济圈内,地理位置优越。A镇隶属于C市,区域面积214.7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6万,下辖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7个管理区,55个行政村,49个社区居委会。该镇工业发达,高新技术产业与民营企业并存,园区工业和乡村工业并存,且乡村工业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农民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比例较高,就业的渠道主要是在乡村工业,人均纯收入8 136元。
A镇是苏南社队企业时期的先驱地,是“苏南模式”*苏南模式的基本内涵是地方政府(乡镇)和村庄集体发展工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获得极大的成功,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潘维称苏南地区发展工业是基层政权(包括村社集体)扮演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中介的一个表现,是苏南地区经济发达和社会稳定的基本原因。的组成部分。该地农村有三大特点,一是河网纵横,水运发达,为早期村社工业化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二是村庄工业化程度和非农收入比例高,早在集体时期,该地农村就开始发展工业,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村庄工业迅猛发展,呈现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图景,90年代中期企业改制,但农民“离土不离乡”的生计模式没有发生改变。第三,强集体经济与集体主义传统。村庄高度工业化充实了集体经济,与强集体经济相配套的是集体主义传统,集体主义传统以平均主义为核心,强化了村庄共同体。
(二) 1983-2009年:就地城镇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A镇乡镇和社队企业发展迅速,塑造了多个亿元村,F村就是其中之一。村社工业化推动了当地的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农民职业身份转换、村庄产业结构转变、土地用途及地域空间的转变。下面我们以A镇下面的F村为例,简要说明A镇辖区农村工业化所带来的城镇化。
第一,农民职业身份转换。F村1973年建立社队企业,以印染业为主,八九十年代社队企业蓬勃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亿元村。村庄工业化推动了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使农民就地转变为产业工人。80年代,村庄工业吸纳劳动能力有限,村社通过集体主义原则“保障一家一户有一个工人”,90年代,村庄企业吸纳了全村80%以上的劳动力,农民基本上完成了职业身份的转变。
第二,产业结构的转变。村社工业化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前,F村是典型的农业区域,以种植水稻等大田作物为主,旱涝保收,农业是村民经济的命脉。80年代,随着村庄企业的蓬勃发展,工业总产值迅速上升,在90年代初期总产值突破亿元,农业总产值下降到不足10%,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
第三,土地及地域空间的转变。首先,就业方式的改变带来了居住形态的改变。F村所在区域河网纵横,传统以农业生产为主时期,农民建房以便于耕作与运输,聚水而居形成自然村落。随着村庄工业的发展,农民工人化,在村集体的引导下农民的居住形态发生改变,从分散走向集中,形成了以村庄主干道为轴心连片的第一、二、三集中居住区,集中居住420多户,集中居住率达90%。其次,土地用途发生改变。社队企业兴起之前,F村土地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耕地,二是宅基地,而社队企业兴起之后,村庄土地用途新增工业用地,村庄土地资本化,为村庄社队企业起步提供资源基础,并成为当前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来源。
A镇所辖的农村在村社工业化的推动下,通过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转变完成了城镇化,又由于该地的城镇化并未带来大规模的人口向城市迁徙,因此,本文将之称为就地城镇化。
(三) 2009年至今:激进城市化
2009年,A镇所在的C市推行以“三置换”为核心内容的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三置换”是指农民“宅基地换商品房”、“承包地换城市社保”以及“集体资产换股权”,“宅基地换商品房”是这次城市化运动的核心。
第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与城市化运动。C市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快,每年的城市建设用地需求量上万亩,而国家每年下达的用地指标只有5 000亩,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依据国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C市出台了地方性政策“依据规划,置换规划范围内的农户自愿放弃宅基地,将农村住宅同商品房进行置换,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统一安置到集镇规划区公寓式商品房居住。农村住宅用地复垦为耕地,复垦整理后产生土地挂钩指标由所在乡镇取得”*资料来源于C市2010年12号文件。农民退出宅基地获得商品住房,从地方政府规划在集镇上的小区中获得260平方米具有完整产权的商品房,地方政府通过农村宅基地整理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第二,“撤村并居”与农村人口整体向城市转移。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运动中,C市对农村进行了功能划分,将村庄划分为整治型、控制型和置换型村庄*整治型村庄,又称保留型村庄,指具有一定规模的村庄,如之前建立的集中居住区,这部分村庄以原址整改为基础,加强村庄的综合环境整治。控制型村庄,是指在城市扩张版图之类的村庄,如城郊村,在城市化扩张过程中自动进行城市化。置换型村庄,是指在主城区和中心城区之外的、阻碍城市规划的、位于“万顷良田”范围内的、不符合村庄规模和规划要求的村庄,则通过政府主导有计划地向城镇示范小区进行整体安置。。按照规划,C市21万农户,10万户属于整治型,控制型5万多户,置换型5万多户。A镇33 000多农户,整治型7 434户,控制型19 489户,置换型6 970户。C市通过“宅基地换商品房”运动,通过“撤村并居”,推动该地区农村人口整体向城市转移。
第三,农民身份市民化。处于置换区农村的农民,通过“宅基地换商品房”集中居住到集镇小区,通过“承包地换城市社保”实现了农民身份角色的转换,转换为现代城市社会中的市民。
A镇在“城乡增减挂钩”政策背景下推动的“宅基地换商品房”运动,通过“撤村并居”使农村人口整体大量向城市转移,并通过“承包地换城市社保”实现了农民角色、身份的转换——农民市民化,农村也随之城市化。由于A镇所在区域农村城市化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因此,本文将其称之为激进城市化。
三、两种城市化实践逻辑比较
(一)主导力量:村社主导或政府主导
就地城镇化是由村社主导的。在城镇化过程中,无论是村庄规划还是资金来源、村民意愿上,都是依靠村社集体、村民组织决策,是内生型农村城镇化[4]。以F村为例,首先,从集中居住规划上来看,第一、二、三期集中小区的选址,土地调整,风貌设计都是村干部召开党员大会、群众代表大会、村民大会反复讨论、集体协商从而完成城镇化的规划、决策。其次,从资金来源上来看,主要分两部分:一是房屋由村民自建,村民按照村社统一规定的建筑风格和建筑面积,自筹经费修建,村集体用集体资金象征性的进行补贴;二是小区内道路硬化、水、电、气、绿化等公共品供给由村集体资金提供。再次,在农户向小区集中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强制农户进入小区,F村总共480户,约400户进入了小区,剩下的80户约20%的农户因经济条件困难、房屋建筑较好等原因放弃进入小区,农民的意愿充分得到尊重。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只给予政策上的引导,村社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激进城市化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主要体现在搬迁意愿、统一规则、资金筹措上。首先,激进城市化始于地方政府对农村的功能划分,地方政府将农村划分为整治型、控制型、置换型,在置换区范围内的农户没有选择的权利,必须参与“宅基地换商品房”的活动,并不考虑农户的个体情况以及未来在城市中的生活能力,“万顷良田”范围内的农户是重点置换对象,位于项目范围内的农户都要参与“宅基地换商品房”活动,而“万顷良田”里的农户大多以农业为主,经济基础较差。农民的意愿没有充分得到尊重,带有强制性。其次,在补偿标准、小区建设上都是由A镇政府统一规划和实施。农户宅基地退出按照房屋拆迁标准进行补贴,退出宅基地的农户统一获得政府提供的150平方米小区商品房,小区的建设亦由地方政府统一实施。再次,无论是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金、小区建设资金、“承包地换社保”资金均由A镇地方政府财政负担。由此可见,地方政府主导了以“宅基地换商品房”为核心的城市化运动。
(二)实施途径:村庄规划或“撤村并居”
村庄规划是推动A镇前期就地城镇化的主要途径。具体而言,村社集体通过对集中居住区的选址、房屋的占地面积、房屋的建筑风格的组织与规划,以村庄为单位,实现了农户向集中居住区的集中。村庄规划推动的集中居住,再加上工业化推动的村庄产业结构、农民就业结构的转变,实现了A镇所在地区的就地城镇化。
“撤村并居”是A镇当前激进城市化的主要途径。“增减挂钩”政策带动了农村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具体的途径是通过“撤村并居”来实现的,即借助项目资金,将原本分散在村庄各处或者是好几个村庄的农户整体搬迁到大的集镇或城市大规模聚居起来,搬迁过程不仅是地域空间的变化,即从农村到城市,同时也实现了农民体制身份的转变,即由农民转向城市居民,极大地提升了地方城市的城市化率,快速地推进了地方城市化。而“撤村并居”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三)目标:以适应工业化或获取土地指标
就地城镇化的目标在于适应工业化和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首先,就地城镇化的目的在于适应村庄工业化。村庄工业化必然带来村庄土地利用的调整,一般型农村土地分为耕地、宅基地、林地三大类,而工业化村庄会新增一类工业用地,工业化扩展占用大量土地,集中居住可以节约宅基地资源从而填补工业用地的空缺,使村庄内部的土地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属于村庄内部的规划。工业化通过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也打破了传统的居住格局,以农业为生时期,苏南农民为了耕种和运输的便利,大多在农田附近聚水而居,三三两两形成自然聚落,而村庄工业化之后,农业成为副业,农民生活围绕在工厂上班展开,集中聚居有利于农民新的生产形式。其次,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随着村庄工业的发展,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成倍增加,收入增加后农民普遍有修建楼房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期,A镇的楼房覆盖率高达60%以上。农民有建房的需求和能力,村集体通过村庄规划将建房的农民集中连片并提供道路、水、电、气等公共品,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且降低了公共品供给的成本。
激进城市化是以获取土地指标和城市化率为目标的。首先,地方政府推动“撤村并居”的首要目的在于获得土地指标,在土地指标之上的目标则是“土地财政”。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灶吃饭”,“土地涨价归公”的制度设计,使地方政府逐渐走向了依靠土地开发、利用和转让来维系地方政府的运作和发展[5]。地方政府花大量资金“撤村并居”让农民上楼,从农民退出的宅基地中获得虚拟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进而从上级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城市开发用地,试图获得更多的土地财政。其次,地方政府推动“撤村并居”是为了获得城市化率。“撤村并居”后形成大规模集聚,A镇要求2 000户作为一个集聚点,地方政府在算城市化率时,直接将“撤村并居”的点纳入进来,极大地提高了地方城市化率。城市化率的提高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有着一定的关系。中央一直将如何稳妥地推进城市化放在国家战略高度,从“小城镇”建设到“新型城镇化”政策,引导地方不断推动城市化发展,地方政府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反过来又会作为政绩得到奖励。
就地城镇化具有渐进性的特征。F村从1983-2009年,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完成了社区80%农户的集中居住,我国的城市化率从80年代的25%,到目前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6%,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3.7%[6]。可见,“小城镇”政策推动下的就地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具有渐进性的特征,而当前“增减挂钩”政策推动下的“撤村并居”则具有激进性的特点。在调查中了解到,A镇计划在短期内完成6 970户,占20.9%农户的置换,快速地将地方城市化率提高20%个百分点,显而易见,大规模“撤村并居”城市化道路具有激进性的特征。
四、激进城市化的结果与困境
(一)城乡一体化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里,A镇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农民身份转换、居住向社区集中实现了就地城镇化。从城乡关系的角度来看,就地城镇化没有打破既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在体制身份上农民仍然是农民,但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收入的增加,集中居住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从这几方面来看,就地城镇化使农村和城市之间达到了高度一体化。
2009年以来,A镇大规模“撤村并居”通过将农村居民纳入城市体系,实现了城乡完全一体化。首先,从社区管理和组织方式上来看,“撤村并居”后农户被纳入城市居民社区管理体系中,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城市化。其次,从户籍制度上来看,进了集中居住区的农户从户籍制度上转换为城市居民,打破了原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再次,进集中聚居区的农户享受与城里人相同的公共服务,主要体现在教育和社会保障这两块,进了城镇的农户小孩有就近入学的权利,且通过“承包地换社保”政策获得了社会保障。最后,农户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就地城镇化阶段,农业虽然在农户家庭生计中所占的比例很低,但其作为家庭经济的重要补充仍然是农民生产的组成部分,“撤村并居”后农民将承包地拿来换了社保,意味着农民脱离农业生产,生计方式完全倚重二、三产业。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上了楼的农户也学着城里人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社会关系按照城里人的业缘关系进行组织。“撤村并居”推动的快速城市化,是在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同等享受部分公共服务体系,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完全改变的完全城乡一体化。这种制度上的城乡完全一体化是否能够实现彻底地城市化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激进城市化的困境
无可厚非,“撤村并居”改善了农民的外部生活条件,实现了城乡完全一体化,但这种城市化的步子迈得过快,从而存在资金可持续、政治社会稳定、社区文化再造的困境。
1.资金的可持续性问题。就地城镇化中,农民和村社是主体,房屋建设资金由农户自己承担,道路、水、电公共品供给由村社集体资金承担,村庄工业的发展是农民和村社均有能力承担相应的建设资金。激进城市化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将承担“撤村并居”的一切费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拆旧费用,宅基地的退出涉及到农户房屋拆迁,房屋按照不同的结构和质量进行赔偿,大多数农户拿到的赔偿金在20~30万元;二是建新费用,参与置换的农户在中心镇免费获得260平方米具有完全产权的商品房,成本价约100万元;三是土地换社保费用,每个家庭按3口人算得要15万元,三项加起来,地方政府置换一户的成本约在150万元。按照规划,C市总共需要支出的置换金额为150万元×5万户=750亿元,A镇需要支出的置换成本为150万元×6 970户=104亿元。庞大的财政支出对于财政收入名列全国乡镇前列的A镇来说都是一笔巨资,对于苏南其他财政实力相对较弱的乡镇来说负担就更重。在调查过程中,当问及A镇领导W某项目实施的难点在哪里,其回答说“主要还是财政上的压力过大”。财政资金的可持续性是激进城市化面临的首要问题。
2.政治社会稳定问题。社区主导的就地城镇化能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能将农民的有效需求结合起来,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主体地位;二是,能够有效化解城镇化过程中的矛盾,土地的重新配置必然打破传统的利益格局,出现矛盾纷争,村社集体利用地方性规则,如村庄内部的“人情”“面子”以及运用手中所控制的集体资源将矛盾化解掉,从而完成实现大多数人利益的就地城镇化。
地方政府主要的激进城市化可能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解决村庄内部矛盾问题。“宅基地换商品房”涉及到村庄内部巨大的利益重构,这主要体现在宅基地价值和房屋拆迁上,这两块将村庄内部原本的不公平激活,村干部由于在置换过程中只扮演协调工作,工作缺乏原来的主动性,而地方政府在面临不熟悉的千家万户时也感觉到无力。二是,如何面对金融风险带来的失业问题。乡村工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且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工人工资相对低,竞争力大,可替代性强,且工作不稳定,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属于不完全产业工人,当遭遇金融危机时,这部分群体最容易下岗、失业。就地城镇化时期,这部分农民“离土不离乡”,土地是农民最后的屏障和退路。但“撤村并居”后的农民承包地换了社保,社保只包含养老保险,不包括失业保险,倘若遇上大规模的失业,农民又无土地可以维系生存,恐会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3.社区文化再造的困境。就地城镇化只是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但乡土生活方式并没发生根本的改变[7],工业化不是打破而是强化了社区共同体的乡土逻辑,社区传统得以再生产和延续。村庄工业化组织和动员就是依靠乡土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如“情面”规则、“共同体意识”等,乡土传统在反复实践中得到强化,并在集体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形成以“平均主义”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新传统,从而抑制了在村庄内部因经济分化产生的社会区隔。因此,传统乡土逻辑支撑了城市化,并在这过程中获得了再生产、传统和现代、乡土性和现代性、农村和城市之间并非割裂的二元对立关系,工业化不仅推动了城市化,也再造了农村社区的乡土性。
当前的“撤村并居”不单是聚落形态和行政组织的集中化,而是乡村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居民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的变革[8]。与城市社区不同,农村社区不单是人口在空间上的聚居,而是以血缘或地缘为基础按照“差序”原则构成的熟人社会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彼此熟悉,相互关联,按照地方性礼俗规则行事,通过历史的积淀形成一种熟人社会共同体的文化,被称作乡土文化或者是乡土性[9]。这种乡土文化渗透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构成了农民的意义世界。“撤村并居”社区再建过程中,既有的村庄边界被打破,新的社区由多个村庄重新整合而形成,农户在完成地域空间转换中如何再造社区共同体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而事实上,“撤村并居”不单是地域空间发生了转换,社区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转换,社区的组织管理仿效城市模式,农户也学着城里人,上了楼,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相互之间越来越没有关联,迈向城市的陌生人社会,社区共同体意识再造十分困难。由此引起的文化出现断层,农民该如何去调适,从而避免文化真空所带来的无所适从是“撤村并居”过程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苏南地区城市化路径为研究对象,将苏南地区前后经历的城市化道路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和激进城市化两种类型,两种城市路径在表现形式和实践逻辑两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不同的城市化路径在主导力量、实施手段、实施目的和结果上均存在巨大差异。就地城镇化是村社主导的、以村庄规划为手段、以适应工业化需求和改善居住条件为目标的渐进城镇化;激进城市化是地方政府主导的、以“撤村并居”为手段、以获取土地指标和城市化率为目的的激进城市化。激进城市化打破了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改善了农民的外部居住条件,从整体上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但其实施过程中也面临资金、可持续性、政治社会稳定和社区文化再造过程中的困境。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国家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必经之路。城市化目标无可厚非,但是城市化的路径确是值得斟酌,城市化不只是农民身份由农村人转向城市人,而是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因此,制度不是影响城市化的关键因素,而与经济收入相关的产业结构才是城市化路径选择的关键。苏南地区城市化路径由就地城镇化向激进城市化转换带来的资金、政治、文化上的困境给我们的启示是:城市化的推进必须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相匹配,不能一味地追求城市化率,而忽视了城市化的质量,应当警惕激进的过度城市化。
致谢:本文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与夏柱智博士的讨论,在此表示感谢。
[1] 董筱丹,杨帅,李行,等.村社理性:基于苏南工业化经验的比较制度经济学分析[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2(1):1-15.
[2] 费孝通.城镇化与21世纪中国农村发展[J].中国城市经济,2000(1):7-9.
[3]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315.
[4] 梁德阔.内生型农村城镇化的运行机制[J].安徽大学学报,2006(5):132-135.
[5] 孙秀林,周飞舟.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13(4):40-60.
[6]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2014-2020[EB/OL] .[2014-03-16]http://www.gov.cn/zhengce/2014-03/16/content-2640075.htm.
[7] 吕德文.撕裂中的再造——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土传统[J].民俗研究,2014(1):15-17.
[8] 马光川,林聚任.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合村并组的困境与未来[J].学习与探索,2013(10):31-36.
[9]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3-29.
From Conservative to Radical Urbanization
ZENG Hong-ping
(CollegeofHumanitiesandDevelopmentStudies,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100193,China)
South Jiangsu is experiencing the path change of urbanization,which is from conservative to radical.Based on the path of urbanization in A town of South Jiangsu,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different practical logics of these two paths of urbanization.It is found that,conservative urbanization is a gradual urbanization,which is dominated by the village itself,and village planning as the method and adapting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improving living condition as target; but the radical urbanization is led by local government,and its mainly way is “Removing villages and concentrating homesteads”,and the purpose is land indicators and urbanization rate.The radical urbanization promo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broke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achieved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However,as it does not match with the local socio-economic structure,the radical urbanization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in funding,social stabili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ulture.
conservational urbanization; radical urban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removing villages and concentrating homesteads”
2014-07-15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13YJ012)
曾红萍(1987-),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与社区变迁、农村社会学。
F302.1
A
1009-9107(2015)04-012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