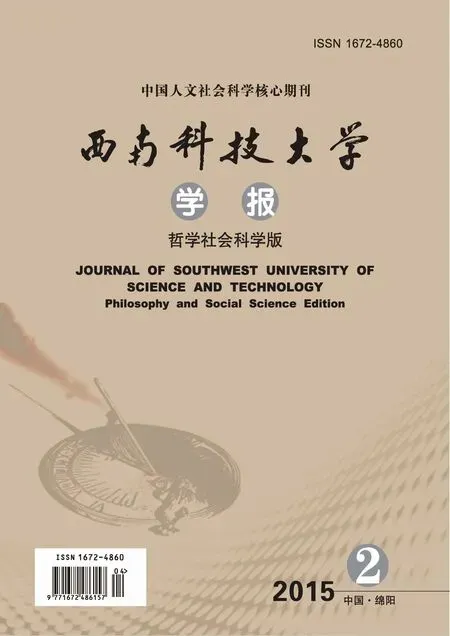《羌族释比经典》中创世神话的宗教学解读
2015-02-20陈建新刘汉文
陈建新 刘汉文
(1.西南科技大学文艺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2.阿坝师专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研究所 四川阿坝 623002)
《羌族释比经典》中创世神话的宗教学解读
陈建新1刘汉文2
(1.西南科技大学文艺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2.阿坝师专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研究所 四川阿坝 623002)
羌族神话是宗教经典。在羌族创世神话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宗教思想。在神灵观上,神与人同形同性,高度人格化,是自然的改造者而不是创造者;在神性观上,神是感性与理性并立的存在,神的意志受到情欲和道德的双重支配;在神人关系上,一方面神人相亲,神创造并关爱着人,人也敬仰着神,二者和谐相处,另一方面又截然相分,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羌族对神灵、神性和神人关系的理解,造就了羌族宗教没有天堂地狱观、没有轮回转世思想、注重生活幸福的乐观现世精神,也形成了羌族宗教缺乏精神追求、带有强烈的世俗化功利化色彩、以及浓烈的萨满教性质的特征,深刻地影响了羌族的生活方式。
羌族释比经典;创世神话;神灵观;神性观;神人关系
创世神话是古代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民对天地开创、万物生成及人类起源的幻想性的思考。《羌族释比经典》①共收录羌族创世神话五部,分别是《造天地》《造人种》《兄妹治人烟》《分万物》《取火种》。这些创世神话形成的年代,已经难以考证,但从内容上看,应当相当古老。
羌族生活于岷江上游地区,由于人口数量较少、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等原因,受周边强势的汉藏文化影响颇大。《羌族释比经典》中收录的敬神、祭祀、还愿、驱邪、解秽等唱经,有许多带有明显的汉藏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化影响的痕迹,如观音菩萨、释迦牟尼、姜子牙、二郎神都出现在唱经中。这五部羌族创世神话,总体上说,与汉藏两族的创世神话差异较大,虽然有些相似的地方,但谁影响了谁,尚待考证。因此,说这五部创世神话是很古老时代的产物,应该是有道理的。要研究原生态的羌族文化,这几部创世神话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在初民社会,神话往往与宗教同体,神话是宗教的典籍。羌族神话也不例外。与很多民族神话最终从宗教中剥离出来、实现了非宗教化不同,羌族的神话始终与宗教紧密结合,是宗教经典。《羌族释比经典》中所收录的五部创世神话,实际上是羌族的巫师——释比在祈福还愿时演唱的经文,我们可以进行神话学分析,从中看到羌族先民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风俗等民族意识方面的内容外,也可以从宗教学的角度上,分析其中包含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思想。
本文对《羌族释比经典》中所收录的创世神话进行宗教学解读,以把握羌族宗教的原生形态和本质特征,进而更深入地认识羌族宗教和羌族文化。
一、神灵观
羌族信仰多神,神的谱系复杂,各地不尽统一,有些神称呼也不一致。羌族的神大致可分为掌管自然事物的自然神,掌管人事的祖先神、劳动工艺之神,掌管地方的寨神等②。创世神话中出现的神都是自然神,主要有:男神阿布曲格、女神红满西、天神木比塔、火神蒙格西、恶煞神霍都等。
神是天地万物的开创者,是人类的创造者,是超自然的力量,这是自然宗教神灵观的主要内容。在自然宗教中,基本上不解释神何以存在的问题,因为原始的神灵观不是为了解释神的起源,而是解释人和自然的起源。从创世神话来看,羌族对神灵来源的基本解释是:神是自有本有的。《造天地》里说,天地开创之前,神就存在了:“神灵成百又上千,尊敬大小诸位神”,其中最大的两位神是男神阿布曲格和女神红满西。正是这两位神创造了自然和人类。
其实在羌族创世神话里,说自然是神创造的是不确切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天地是神创造的。在神创造天地之前,自然已经存在了——“苍宇混沌无形体,苍天大地无间隔,既无声来又无形,只有气流在流动。气流之上多尘埃,当中两个椭圆物,却是鸡蛋和鹅蛋”——宇宙混沌一团,其中有气流、有尘埃、有鸡蛋和鹅蛋。阿布曲格和红满西用鹅蛋中裂出的青石板创造了天,用鸡蛋中钻出的大鳖鱼四脚朝天顶住青石板,创造了支撑苍天的大地——而青石板和大鳖鱼都是自有的,并非神之所造。因此,羌族的神并不是绝对超自然的存在,他们与自然同在;神不是创造了自然,而是改造了自然。羌族创世神话在叙述自然与神的关系时,充满了矛盾。既然说神创造天地之前,除了神世界上只有气流、尘埃,却又说还有鸡蛋和鹅蛋,还有玉狗,在鸡和鹅被创造出来之前,这鸡蛋鹅蛋从何而来?那玉狗——它并不是神,它又是从哪里跑出来的?这说明了羌族创世神话产生的时代应该相当的早,人们的理性思维能力还潜藏在原始的直觉想象之下,在懵懂之中,羌人萌生出神与自然同在的宇宙观。
羌族神灵观的重要特点是神的人格化程度非常高。羌族的神与人形象相同,他们并不靠怪异的相貌和夸张的形体来展示超凡的能力。在创世神话中,除了写到红满西的女儿“本是一只癞蛤蟆”之外,并没有对神的长相的特别描写,——而这个“癞蛤蟆”,也为了“贪羡外表”,脱掉皮在火中烧掉了;同时,在写到神与人交往、对话的时候,平平常常,如同熟人相见,那么,我们将羌族的神理解为与人同形应当是妥当的。在《取火种》中写到,火神蒙格西和凡女阿勿巴吉生的孩子热比娃降生后,“白白胖胖像火神”,也可以反过来证明神的长相与人是相似的。
羌族的神还与人同性。所谓同性,不只是说他们与人一样,有男女性别之分,要结婚生子,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有跟人一样的思想、感情、欲念、爱憎。与其说神是高高在上的自然的和人类的主宰,不如说他们实际上是一些带有七情六欲的生灵。《取火种》写道:神之所以惩罚人,是因为神在游览神山喀尔别格山时,人在山下的闹嚷声,扫了众神的雅兴。众神向天神木比塔告黑状,说人类不安分、不恭敬。木比塔不调查、不核实,派恶煞神霍都去惩罚人类。霍都是一个心胸狭窄、整人为乐的家伙,当他看到人类居住的尼布甲格山风光美好,“凡人无忧让人恋,更比仙境要好玩”时,不由妒火中烧,施展魔法,降下冷风大雪,将春天变成了冬天。这里,我们看到了傲慢,看到了狭隘,看到了嫉妒,看到了偏听偏信,看到了喜怒无常——这些人身上的弱点,都出现在了神的身上。同样是在《取火种》中,火神蒙格西“性情温和且善良”,在尼布甲格山下美丽的凡女阿勿巴吉相遇,被她的美丽打动,他不顾人神不能互往来的天条,与阿勿巴吉一见钟情。他赠送红果让自己的爱人免受饥寒之苦,又吩咐阿勿巴吉生下了儿子后,让他到天庭来取火种,把温暖带给凡民,并且不顾天庭律令,帮助热比娃取得了火种。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柔情,看了关爱,看到了感性至上,看到了神也有跟人一样的优点。同样的叙述,在羌族史诗《羌戈大战》《木吉珠与斗安珠》《颂神禹》中,比比皆是。
神人同形同性、高度的人格化,说明了羌族宗教的自然宗教性质。羌族的神在精神上、道德上没有什么高人之处,除了长生不死,具有一些人所没有的魔法外,他们就是典型的人。因此,说羌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们的神,毫不为过。
从创世神话还可以看出,羌族宗教虽属于多神崇拜,但已经有了主神或者叫“至上神”的观念。在《造天地》里,主神是阿布曲格:“阿布曲格数最大,其次就是红满西”;但是在《兄妹治人烟》和《取火种》以及《羌族释比经典》中收录史诗和其它唱经里,主神毫无例外都是木比塔。大致是因为木比塔是羌人的保护神,是羌人“天上的父亲”③的缘故,他的地位超越了创世神阿布曲格和红满西。羌族神的谱系比较散乱,众神围绕着天神木比塔,以之为核心,他颁布天条并操执赏罚,但众神间关系并不明晰,没有构成一个秩序井然、等级森严的神的世界。这说明了在创世神话产生的和流传的时代,羌族的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基本采用头人和释比为核心的村寨自治形式,政权并未形成。神话看起来充满幻想,实则曲折地反映着社会生活。
二、神性观
神性即神的本质属性。“神以自己的意志和命令来支配和操纵自然和人间生活,乃是神性的根本。如果神灵不具有这种神性,也就不成其为神。”④有意志,操赏罚,支配万事万物,这是自然宗教所描绘的神性的共同点。但是,神对自然和人事的支配能达到什么程度,神的意志在本质上是什么,各种宗教的叙述并不一致。在创世神话中,我们发现羌族宗教在神性观上,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其一,羌族的神是有限的存在,即神对自然和人事的支配能力是有限的。
羌族的神是非超越性的。如前所述,羌族的神是生活在自然中的神,而不是创造自然的神。羌族人赋予了他们的神不灭的肉体,而没赋予他们先于自然而在的精神。他们造天会“劳累”,造地会“辛苦”,他们会“席地而坐把气歇”“喘气化成云和雾”“揩下汗水成雨水”。他们还有毛发,甚至会长虱子。从逻辑上说,由于神与自然同在,神就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因此,神拥有太多的自然属性就是自然而然的了。羌族的神不具有抽象的精神属性,他们必须借助现成的鸡蛋、鹅蛋创世,而不像基督教的上帝那样只需要一道命令。
既然神并非自然的创造者,那么他们对自然的支配能力必然有限;同时,由于羌族自然宗教和多神教的性质,每个神都有自己的职守,对超越职守的领域就变得无能为力。羌族的神是非全知全能的,不仅单独的神不能全知全能,而且诸神整体上也无法做到全知全能。
一般地说,神应该能够掌管自然、干预人事、操纵命运,无所不能,但羌族的神在这三个方面都受到了限制。在《兄妹治人烟》中,洪水突然从地底涌上来,人类灭绝了,只剩下兄妹二人得到木比塔的拯救。二人决定治下人烟,让世间重新人丁兴旺。但二人是兄妹,羞于成为夫妻,无奈中只好请天神木比塔想办法。木比塔没有安排一切,而是将二人的事交给天意决定:先叫二人各背一片磨片,分别背到两个相对的山顶上,一齐滚下来,结果两块磨片合拢在一起,又叫他们分别在两山上掷下针和线,结果飘下的针和线又穿在了一起。在这段描写中,那场从地底涌出的洪水,并非神所安排,它的消退也不是神意的结果,这是自然并非完全由神主宰的证明;同时,木比塔虽然介入了人事,但他并没有运用自己的神力让兄妹二人结合,而是交由天意决定——最高的神意志之上竟然还有天意,可见,最终支配人类命运的,并不是神意而是天意。
这样的描写在羌族史诗中也能看到。《木吉珠和斗安珠》中,木比塔的女儿木吉珠爱上了凡人斗安珠,一直拒绝神的求婚,木比塔以为她是犯了什么煞星,于是请天上的释比——地上释比的祖师爷阿巴锡拉出马:“释比快来卜个卦,喜星是否会出现”。最大的主神竟然要请求手下的释比卜卦,可见,木比塔并不是吉凶祸福的掌管者,也不是命运的控制者,他自己也受到了命运的左右。
其二,羌族的神是充满感性和情欲的存在。
羌族把自己的神分为善神和恶神(或称白神和黑神)两大类。在创世神话中,木比塔、蒙格西是善神,而霍都是恶神。有善神和恶神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羌族的宗教是二元神教。羌族所谓善神与恶神,并不是将神定义为先验的善和恶的化身,更不是将世界理解为善与恶的对抗的产物,善神与恶神间并没有善与恶、生与死、光明与黑暗、创造与破坏的斗争。如木比塔是善神,霍都是邪神,但霍都是木比塔的手下,听命于木比塔,只故意与人为难,而从不与木比塔作对。
在人为宗教中,神的品性的善、动机的善和行为结果的善是高度统一的。羌族虽然将神分为善恶两类,但神的品性的善恶,往往与他们行为的动机和后果的善恶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如,木比塔是善神,然而他的行为对于人而言,并不总是善的,在《取火种》中,他听信诸神一面之辞,派霍都去惩罚人类,在《木吉珠和斗安珠》中,他挥剑斩断了天地相接的喀尔别格山,断绝了神人之间往来的通道。这些行为,从动机上说,不是出于对人类的关爱,从结果上来看,也是灾难性的。
羌族的神品性善恶和行为后果的善恶间之所以会产生矛盾,根本原因在于,羌族同形同性、高度人格化的神灵观,使羌族的神身上包含着强烈的感性和情欲成份,这样,神的意志往往受到感性和情欲的驱使。
且看《取火种》中的三个神:木比塔听信好事多嘴神的话,认为“凡人不安分”,“不敬神山扰神林”,盛怒之下,决定降祸于人类。木比塔的行为,全然背离了其善的品性,听凭自己的感性本性。霍都是恶煞神,他的作恶也不是由于邪恶的本质所致,而是由于心胸狭窄,喜欢嫉妒的个性引起的。“凡人无忧让人恋,更比仙境要好玩”,因此“嫉妒之心如火烧”,施展魔法将人间变得天寒地冻。火神蒙格西“性情温和且善良”,见到“姣好模样赛天仙,无所遮拦裸上身”的凡间美女阿勿巴吉,不觉“动了情”,生下了儿子热比娃。温和的性情和对情人与儿子的爱,是蒙格西帮助人类取得火种的根本原因。
其三,在羌族的神身上,具有很强的伦理道德属性。
羌族将神灵分成善神和恶神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伦理意义。趋利避害,人的本性,扬善抑恶,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善神和恶神的区分,说明了羌族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赋予诸神道德品质,其目的在于用以调节现实生活中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羌族的神与很多同样处于自然崇拜阶段的民族的神不大一样,那些神往往喜怒无常,神意不可捉摸,奖惩没有标准,而羌族的主要的神、特别是木比塔,既是众神之主,也是羌人之父,他始终关心人类、爱护人类、同情人类,其品性是十分善良的,也是有理性的。就像一个凡间的父亲一样,即使一时犯下任性、失察之过,最后也会醒悟过来,恢复理性,关键时刻会站出来帮助和拯救自己的子民。神的这种属性,在《兄妹治人烟》和《取火种》中,展示得十分充分,在史诗《羌戈大战》、《木吉珠与斗安珠》、《颂神禹》中,也描写得十分详细。
神从喜怒无常,意志不可捉摸到神分善恶,带有神伦理道德本性,人类在危难时总能得到神的帮助,说明了羌族将善看成了世界的主宰力量,世界已经从无从认识、无法把握、难以捉摸的昏蒙状态,变得有规律、有秩序,反映了羌人的理性主义精神。
总之,羌族神性观的特点是,神被定义为感性与理性并立的存在,神的意志受到情欲和道德的双重支配。
三、神人关系观
神人关系是宗教中最核心的内容,因为宗教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超自然精神体——神的信仰,并且通过信仰而产生的情感力量来体验到与神的关系,从而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摆脱生存困境。在这里,人对自己与超自然精神体的关系、即神人关系的理解是最为重要的,神人关系是宗教意识的主体,所以,神灵观也好,神性观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说明神人关系。
在创世神话中,对神人关系的描绘,首先表现在神的创世活动中。神为什么创世呢?各民族对此说法不一,但无非是无目的论和有目的论两种。汉族神话持无目的论,无论是盘古开天地还是女娲造人,都是无目的的创造,或者说是自娱自乐,游戏的产物。羌族的神创世是有目的:在《造天地》里,男神阿布曲格不满意这个“没有天来没有地,既无声来也无形”的世界,于是和女神红满西商量“齐心来把天地造”。在《造人种》里,阿布曲格和红满西创造天地后,丢弃的虱子变成了禽兽鱼虾,断掉的毛发变成了草木树林,吹口仙气让一切有了生命,“天地之间有万物,万物已有样样好”。然而他们还是不满意,原来“天地还需管理者”,于是就创造了人。可见,羌族神的创世,服从于自己的目的——他们乐意看到一个和谐的世界,一个令自己满意的世界。
人是作为世界管理者被创造的,所以需要好材料,需要神付出更多的精力。阿布曲格和红满西挑选了羊角花树(即杜娟花树)造人。相对于汉族的泥土,羊角花树还真是好材料。“九沟之中摘羊角,羊角九颗削成形”,神每天对它们吹三口气,九天之后,就变成了活生生的人。正是由于是“好材料”造成的,所以人的天性是好的。许多民族都有二次创世神话:人类因为本性邪恶,罪恶累累,神决定毁灭人类,重造世界。《兄妹治人烟》就是一部二次创世神话:大水突然从地底涌出来,淹灭了大地,毁灭了人类,天神木比塔拯救了兄妹,重新创造了天地。与古犹太、古希腊的二次创世神话不同,在《兄妹治人烟》里,人类之被毁灭,并不是由于人类有什么罪恶或过失,人类是无辜的。不仅在《兄妹治人烟》中这样叙述,在《取火种》中,凡民遭受天寒地冻、缺吃少穿之灾,纯粹是木比塔听了谗言失察所致,跟人的道德无关;在《颂神禹》中,羌民遭受洪水泛滥之灾,是由于水神和火神打架,水神失败,迁怒于羌地所致,跟人的道德也没有任何关系。
在汉族神话中,神创世之后,基本对人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所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⑤,让他们自生自灭。而在羌族神话中,神创造天地和人,是为了让自己满意,这就决定了神必定始终关注着天地的秩序,关心着人类的命运和生活的幸福。一旦天地的秩序和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神就会作为拯救者出现。在《造人种》中,是木比塔救了兄妹,还为兄妹出主意想办法,重新繁殖人类,并赠送粮食种子,让人类安居乐业;在《取火种》中,火神蒙格西悲悯凡民的苦难,不惜违反天条,三次倾力相助,使热比娃将火种带回了人间。“我们的神木比塔就是我们的天菩萨,他不为难人,偏待人,我们有难,阿巴木比塔要帮忙。”⑥神是人类的保护者,这是羌族宗教对神的基本信念。
神创造并关爱着人,人也敬仰着神,可见,羌族的创世神话中所理解的神人关系是和谐的关系。但羌族人这种神人和谐的思想,并不等同于汉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从宗教意义上说即为“神人合一”,意味着在神与人之间,是一种相通和谐、并立平等的关系,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可以直达由神代表的最高真理。在神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之下,人性和神性间是可以互通的,人的身份和神的身份间是可以互换的:神话中,后羿被贬到凡间而失去神性,由神而人,嫦娥偷吃仙药而获得神性,由人而神;宗教中,道教说人人皆可成道,佛教说人人皆可成佛。而在羌族神话中,特别强调“分”的思想,这种“分”,从宗教上意义上说,就是神人相分。
《分万物》是部很独特的创世神话,它是羌人在还大愿时的唱经。“神把天地来分开,分开天地分万物,分了凡间与天界”,“皇帝分来在京城,官府分来掌大印”,“羊角花儿长沟内,迎春花儿长路边”……自然社会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天神造就,它们各有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唱经告诫人们要安于天定,不逾规矩。这种“分”的思想,也常见于敬神篇、解秽篇、祭祀还愿篇等诸多唱词中。
既然万事万物都有定数,不可逾越,那么,作为被造物的人和作为创造者的神之间的界限,更是不可逾越的。史诗《木吉珠与斗安珠》里说,本来人和神是可以相互往来的,但在木吉珠下嫁凡人斗安珠后,木比塔挥剑砍断天地相接的喀尔别格山,“从此天界与凡间,再也不能互往来”;《取火种》里也写道:“人神本可相往来,众神之主木比塔,狠心来将天条搬,断了神人来往路。”这些叙述,表面看来,描绘了人与神在空间上的相分,从深层次来说,实际上表达了人性与神性之间不可逾越,人的身份和神的身份之间不可改变的思想。在《取火种》中,还写到人之所以遭到神的惩罚,跟被诬“不安分”、“不敬神山扰神林”有关系。这让我们想到了《圣经》中通天塔的故事:不安于人的地位、图谋僭越就是最大的罪。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羌族创世神话中神人关系的特点:人是神创造的,作为被造物,人的地位理所当然应该低于神,人理所当然应该敬神拜神,服从神,人可能学来一些神所传授的法术(如成为释比),但永远不可能成为神,人与神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神人相分,构建了羌族宗教道德的基础,——人必须安于本分,不要做成神的幻想,遵守各种宗教礼仪和禁忌,才能够得到神的庇护;同时,神与人之间又是和谐相亲的,因为创造者喜欢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世界,所以,它赋予了人的好的天性,并且关爱着人类。神对人充满了爱,因此人要敬神,相应地,因为人的敬神,所以神也爱人,人的敬神与神的爱人互为因果。神人相分相亲,这就是羌族创世神话中反映出来的羌族宗教的基本精神。
结语:
羌族对神灵、神性和神人关系的理解,造就了羌族宗教的独特个性。一方面,作为创造者,神高高在上,人神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使羌人放弃了超越有限性的努力,放弃了成神成仙的冲动。羌人没有轮回转世的说法,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一生一世,是羌人坚定的信念,即使在信仰三世轮回的汉藏文化的包围之中,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羌人认为人间比天庭还要快乐,甚至连神都嫉妒人的生活。他们坚持认为,人生就是幸福,对死后的世界,并不感兴趣。人死了,灵魂就散了,没有了,不会投胎,不会转世。用释比们的话说,人死火化,灵魂就被火带走了⑥。只有凶死和夭亡的人才会阴魂不散,出来作祟,但通过法术,也能让它们安息。人只需要关注自己的现世生活,而不用关注彼岸世界和未来灵魂的处境,好好地活,平安地死。可见,乐观、现世是羌族的宗教的重要特征,与笃信人生即苦、轮回转世、天堂地狱的汉藏宗教对比鲜明。
另一方面,由于神的高度人格化,神性中情欲与道德、感性与理性的并存,神不是人的道德理想的化身,而是功利欲望的载体。羌族的神很看重人对自己的态度,对人的帮助不是无条件的,而人也很在乎神能否在现实生活中给自己以帮助和庇护。在羌族宗教生活中,处理好神人关系,成为了头等大事。人以礼仪和供品敬神、祭神、请神,而神用法术帮助人战胜邪神和恶鬼。这就决定了,羌族的神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方式不是通过精神的交流,而是通过现实的利益的交换。因此,羌族宗教总的来说,缺乏精神追求,带有强烈的世俗化、功利化色彩,以及浓烈的萨满教性质。
羌族宗教强烈的现世精神和世俗功利色彩,为宗教与生活的紧密结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敬神求神,祭祀还愿,渗透于羌族生活的各个方面,丧葬、生育、婚嫁、治病、修造、农牧、耕作、娱乐等等,都要请释比作法,以求在神的帮助下,获得平安。生活离不开宗教,宗教就是生活,构成了羌族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
注释
① 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主编:《羌族释比经典》。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年。
② 对羌族的神的分类,目前学术界并不一致。此处采用邓宏烈之说。参见邓宏烈:《羌族的宗教信仰与释比考》,《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③ 木比塔在羌语中的本义为“天上的父亲”。按羌族的说法,木比塔的小女儿木吉珠与凡人斗安珠结婚,繁衍了羌民。
④ 吕大吉:《宗教学导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
⑤ 见《老子》第十章。
⑥ 赵曦:《羌藏文化对话发展中的羌族释比文化》。 《阿坝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9第4期。
A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eation Myth inQiangShibiClassic
CHEN Jian-xin1, LIU Han-wen2
(1.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Sichuan, China; 2.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Art of Minorities of Aba Teachers College, Wenchuan 623002, Sichuan, China)
Qiang myth is also religious classic. There are a good number of religious ideas in the creation myth of Qiang. On the concept of the gods, the gods are anthropomorphic. They are highly humanized and treated as the nature reformer rather than creator. On the concept of divinity, the gods exist both emotionally and rationally. The gods’ will are dominated by both lust and morality. On the God-man relationship, the gods create and take care of man, and man also reveres the gods. They get along in harmony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ds and man are completely distinct. There is an unbridgeable gulf between the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ods, divinity and the God-man relationship forms features of the Qiang religion, which has no concept of heaven and hell, no concept of reincarnation. It just focuses on the secular spirit of optimism and happiness so that it is poor at spiritual pursuits. With a strong secular utilitarian colo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manism, this religion influences on the lifestyle of Qiang people deeply.
QiangShibiClassic; Creation myth; Concept of the gods; Concept of divinity; God-man relationship
2015-02-01
陈建新(1966-),男,四川开江人。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刘汉文(1965-),男,四川汶川人。研究方向:藏羌文化。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项目“羌族释比经典中的宗教思想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DFWH008-3。
I276.5
A
1672-4860(2015)02-008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