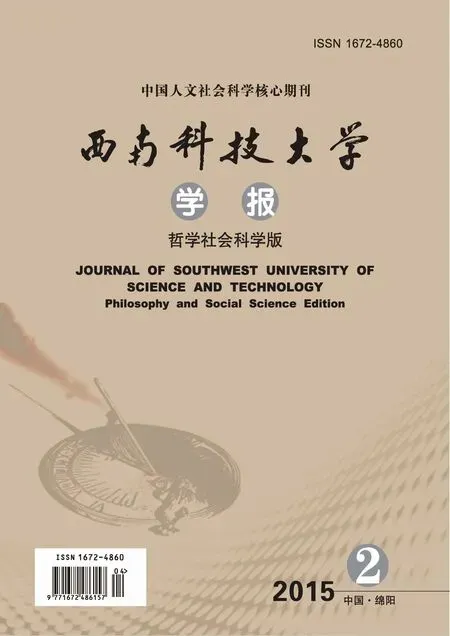《空床日记》中的聚焦分析:回归与超越
2015-02-20卿丽园
卿丽园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空床日记》中的聚焦分析:回归与超越
卿丽园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空床日记》是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晚期的代表作。从热奈特的叙事聚焦理论来看,小说的叙事聚焦呈现出以内聚焦为主,零聚焦为辅,最后呈现出内外聚焦交换使用的规律。多重聚焦叙事不仅充分展现了作者高超的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也为读者展示了一位身处生存困境的老年女性从迷失自我、自我救赎至回归与超越的成长的画面,体现了作者对陷入生存困境的老年女性的人文关怀。
《空床日记》;叙事聚焦;回归与超越;人文关怀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Margaret Drabble, 1939-)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女作家与评论家。有着“现代简·奥斯丁与当代盖斯凯尔夫人”[1]44头衔的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一直是其创作主题和动机。基于自身的经历,她书写了年轻女性步入婚恋时的迷惑、中年女性徘徊于家庭与事业间的彷徨与容颜已逝的老年女性的生存危机。这种阶梯式的女性主题书写在她的处女作《夏日鸟笼》(ASummerBird-Cage, 1963)、中期作品《中年》(TheMiddleGround, 1980)和晚期作品《空床日记》(又称《七姐妹》,TheSevenSisters, 2002)中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她灵活自如地进行着一个又一个阶段的生命书写,执着于“女性生存困境的不懈探讨”。[2]74
《空床日记》是作者年过花甲后的作品,小说以60岁的主人公坎迪达·威尔顿( Candida Wilton)为主线,书写了她面对老年生存危机,如何寻求自我、走出困境最后超越自我,获得了重生与回归的成长历程。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运用了不同叙事视角的转变,暗示了主人公不同时期的生活现状和心理变化。此外,四部分都有第三人称的日记叙述,体现了该作元小说的特征;小说中神话用典、互文指涉到处可见。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和创作立场,或与后现代的关联”。[3]136
国内外对《空床日记》的研究和关注是比较少的,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女性主题和女性叙事的视觉上。《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这部作品“真实、有趣、幽默,充满惊喜。她思索时代、女人间的友情和如何把握第二次的机会”[4]。李凤基于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探讨了女主人公的心理和社会空间[5]。程倩结合互文理论,解读了《七姐妹》(即《空床日记》)中神话指涉,评价了作者互文策略之价值[6]。有人注意到了作品中高超的叙事手法,如相菲运用了苏珊S·兰瑟的叙事理论分析了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叙事[7]。然而,却鲜有人结合热奈特的聚焦叙事理论,分析小说中主人公的回归与超越。
叙事聚焦是叙述的一个方面,是描述事件的特定角度,即以某种视角对叙述内容进行选择和限制的手段,通过聚焦,可以突出表现聚焦者的眼界和思想特征[8]59。热奈特在《新叙事话语》中提出了三分法,选用了“聚焦”(focalization)一词。他认为“聚焦就是对传统的全知叙述意义上的叙述信息进行选择和限制”[9]72。他的三分法是对三种聚焦模式的划分:零聚焦(zero focalization)、内聚焦(internal focalization)和外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基于以上状况,笔者将探讨小说的聚焦叙事规律,分析叙事聚焦与自我寻求这一主题之间的内在关系,表现出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呼吁世界应关注老年女性的生活,让她们能够老有所依,快乐地度过晚年;表达了她对身处生存困境的老年女性的同情与人文关怀。
一、内聚焦叙事:无处可逃的生存困境
《空床日记》中的第一部分是“她的日记”,坎迪达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过去与现在的生活。写日记是内心独白的一种表现方式,是典型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内聚焦型叙事是指“叙述者只说某个人知道的情况”,即叙事者=人物[10]74。由于叙述焦点与人物主观世界重合,故其叙事效果在于体现叙述内容的主观性。因此,该部分运用了内聚焦叙事手法,述说了坎迪达无处可逃的生存困境,探讨了她内心的主观世界,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叙事形式。岁数的增长带给女性身体及心理上的不适、破碎的婚姻、异化的母女情感、淡化的友谊,坎迪达陷入了老年生存困境。她用过去式时态回忆了自己作为女儿、身为人妻以及人母的生活感受,用现在时态叙述了搬至伦敦的日常生活和现状。时态的变化,使文本的叙事徘徊在过去与现实之中,主人公的处境变化及心理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日记中,坎迪达用过去时态讲述了萨福克的一切,甚至描述萨福克的客观环境时,也用了过去式,“这里曾经有一片蔚蓝的天;有绿色与黄色的草原。[11]13(there was a large sky above me in Suffolk…There were green and yellow field.)[12]19因此,主人公想逃避这个压抑的封闭空间,用过去式以示她试图忘记在萨福克的一切,让它成为过去。丈夫的出轨,女儿的冷淡加之不愿轻易与人交往的性格,使她成为”街谈巷议的对象,成了可怜可鄙的人“[11]17使她成为了一位边缘化的人物,”我现在成为了一位无依无靠、无法自保,如同被束之高阁弃而不用的‘忠诚妻子’。”[11]37面对如此窘迫的生存环境,她毅然决然地选择搬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11]37。坎迪达搬到伦敦后,虽然居住环境极其恶劣,但她却欣喜若狂。
然而,作者用现在时态讲述着伦敦的一切,“我现在陷入灰暗的伦敦天空之中,这样更好。这个困境便是我的自由。在这里将对我的肉体和灵魂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11]17(Now I live trapped beneath an enclosing grey gloomy London canopy. It is better so. In this trap is my freedom. Here I shall remake my body and soul.[13]19在此,作者以现在时讲述了主人公住在伦敦的心情:虽然客观环境不如人意,但获得了自由,有了自己的空间,而且这将是蜕变的起点,坎迪达相信未来会很美好。坎迪达因终于摆脱在萨福克的生活而自豪,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由而高兴。
虽然坎迪达用不同的时态表达了她的感情色彩,日记却并不是按着时间发展的顺序撰写的。小说以她入住伦敦第三年的生活为开端,记录了她的日常生活:每晚去健身房健身,回来后在电脑上玩单人纸牌游戏等。接着,伦敦的生活与她为人女、人母与人妻时的生活交叉着讲述。3个阶段的画面不断地在读者眼前交替转换。她不同人生阶段的想法与价值观念的变化也栩栩如生地在读者脑海里变化着。坎迪达一直在思考女性应该怎样定位自己。由于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一开始她也认为女性应该依附于男性,她的天职就是相夫教子。后来,意识到这种男性视野下的女性自我是她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男女应该平等,女性应该自我独立,正如她所反思的“我应当更加卖力地去自食其力,我靠他的钱来生活就贬低了自己,我纳闷这是否是一个男女平等主义者的想法。”[11]81在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过程中,她后悔年轻时没有像朋友朱莉亚那样独立自主,而是扮演了社会赋予的传统女性角色。尽管德拉布尔的作品都是女性题材,但是她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我没有任何一部著作是女权主义的, 因为我对于妇女必须得到公平的对待的信念是一种基本原则,因此我从未想到要把它作为主题,它不过是一个整体的局部而已”。妇女的平等地位的实现只不过是实现整个社会平等的一部分罢了,因此,与其说德拉布尔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倒不如说她是一个博爱的人道主义者。
小说以坎迪达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叙事,使叙事视角转变成了人物的双眼和意识,直接深入并生动地展示了主人公所处的困境,其逃避的愿望以及内心感情的变化。也就是说,内聚焦叙事使读者更能了解坎迪达的感情和感知,这样的技巧符合了主流上的道德描写。一位处在边缘化的坚强女性,面对无处可逃的生存困境,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自我寻求之路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引发读者对现代生活中的老年人问题的思考,传达了作者的人文主义关怀。
二、零聚焦叙事:寻求自我的朝圣之旅
零度聚焦,就是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它的特点是叙述者说出来的比任何一个人物知道的都多,即“叙述者大于人物”。热奈特认为,零度聚焦叙述就是变换聚焦,“就是在一些经典叙事中,用不确定的聚焦点或者是距离较远的聚焦点产生出全景式的描述”[14]73。由于零度聚焦以独特的位置观察,观察者就对故事世界作全景式的鸟瞰。胡亚敏把它称之为非聚焦,认为“它仿佛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控制着人类的活动”[15]25。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中,叙述者站在全知全能的上帝角度,描述了这6位老人旅途中的所见所想和内心的变化。也就是说,作者在第二部分中采用了零度聚焦,讲述了她们7姐妹寻求自我的意大利之旅。此外,文中多次的神话用典与指涉使文本徘徊在神话与现实之中,更是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众姐妹信守神话,渴求像神话人物一样摆脱现存的生存困境,并仿效他们的足迹掌握自己的命运。
起初,她们登上“萨拉姆博”飞机,象征着她们渴求像七仙女一样化身为鸽,摆脱男人的束缚和尘世的烦扰,“她已经把自己对尘世的留恋抛在身后,未来像一块梦想的画布铺展在她的面前,她全心全意地飞奔而去”[11]145。之后她们入住“狄安娜”旅馆,享受着宁静的乐土,对接下来的朝圣之旅充满期待和在旅游中寻求自我充满信心,“她已经逃脱了那种单调生活,逃脱了那种黑暗命运,感觉已经从死亡走向了重生”[11]151。旅途中,众姐妹重新阅读了《埃涅阿斯记》,沿着埃涅阿斯的足迹,参观冥府,想知道等待她们的是什么。然而不同的是,这里不再是维吉尔笔下的那样,幽暗阴森,相反这里有“蓝色的湖泊”、“绿树和芦苇”以及“生命的气息”[11]183。这些转变象征着等待姐妹们的不是死亡,而是她们走出困境后的重生。可就在她们喜出望外时,她们片刻的宁静被打破了。辛西娅的丈夫被刺伤;坎迪达的丈夫打来电话,转达女儿腿动手术的消息。可二者之间的情感反应形成鲜明的对比,辛西娅义无反顾地准备马上回去照顾丈夫,而坎迪达一直迟疑着连电话都不敢拨打。在杰罗尔德太太的强烈要求下,坎迪达心惊胆战地回了电话,跃出了走出自我的第一步。如此可见,坎迪达的内心仍很脆弱,她害怕再次受伤,害怕再次回到之前的生活。这说明老年女性走出生活困境之路并不平坦,她们害怕受伤害,解开心锁需要更多的关怀。当事情被证明并不是她所想的那样糟糕时,坎迪达独自一人买了火车票去寻找预言家西比尔,寻找命运的答案。可干缩的预言家告诉她的是:“屈服吧,这已经是极限了!”[11]198然而,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告诉我们:“这不是极限,她不能屈服。”[11]198这表明坎迪达虽然信守神话,但仍然不肯屈服命运,决心走出困境,活出自己。
该部分零聚焦叙事讲述了7姐妹的意大利之旅,对“7姐妹”的旅程进行全方位观照,表明了“她试图从自己的樊篱中逃脱出来”[11]216。此外,全知全能的“上帝形象”叙事者能灵活自如地穿梭在神话和现实生活中,拉近了读者与文本的距离,同时也凸显了德拉布尔试图通过“寄梦神话”的方式为深陷生存困境的人们寻求出路,寻找精神慰藉,稀释人类无法避免的困境。然而,残酷的现实与美丽的幻想形成鲜明的反差,挣扎中的人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要么无法接受现实的残酷而死亡,要么勇于反抗命运而重生。在《象牙门》中,德拉布尔借用《奥德修纪》中的经典意象“象牙门”象征着作品的虚幻主题,塑造了沉溺于理想世界的柯克斯在意识到堕落的西方文明之后,转向东方世界寻求理想之境,最后理想破灭,客死异乡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在《空床日记》中,坎迪达虽然寄梦神话,但仍不愿屈服命运,最后获得了重生。零度聚焦不但客观地描述了7姐妹的朝圣之旅,同时也体现了德拉布尔对传统的宏大叙事技巧的传承。
三、内外聚焦叙事的转换:意料之外的实至回归
正如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所说,“尽管上帝般的全知叙述者无所不知, 然而在透视人物的内心时一般却是有重点有选择的……”[16]123因此,在第三部分爱伦的说法中,坎迪达意外死亡,作者运用了有限的第三人称内聚焦坎迪达女儿爱伦的口吻述说了坎迪达的生活以及她身边的朋友,最令读者迷惑的是爱伦否定并纠正了她母亲之前所说的一些事情。通过爱伦的内聚焦,坎迪达的生活困境再次得到证实。但爱伦否定并纠正的一些说话实际上是坎迪达在反思自我:自己既不是一个好母亲、好妻子,也不是一个好朋友,比如“是母亲的冷淡,把父亲逼进别的女人的怀抱里,她的冷淡让我感到寒气入骨”[11]209。这也是她走出自我与寻求自我的必经阶段。作者采用了不可靠叙述者否定了前部分的第一人称内固定式视角,体现了对传统叙事方式的创新与超越。同时,德拉布尔本人站在创造者的角度和自身在场的体验,评价女性的价值和命运,流露出她个人的道德价值观。
在最后一部分尾声中,第一人称内聚焦构成了主要叙事,使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一位在困境中挣扎的“边缘人物”跃然纸上。她试图超越自我,走出困境,然而步履维艰,“我还在这儿……虽然我努力了,但我逃不脱”[11]227。她想象假装死亡,博取家人的同情或惩罚他们,却发现死后没人会在乎。在历经了多次矛盾复杂的心理变化和挣扎后,她决心改变自我,寻求出路,因为死亡只是懦弱的表现,而不是一种“姿态”[11]228。于是,她试着换位思考,试着学一门新语言,可以提供与女儿交流的机会,同时新语言也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我一直在竭力消除与女儿之间的隔阂”[11]228。最后,她勇敢地接受了女儿的婚礼邀请,成功地克服了内心的障碍,走出了困境。
内聚焦可以很好地展示人物内心世界,而外聚焦因回避了人物的主观世界使其叙事效果往往带有神秘色彩,因为外聚焦指的是“叙述者说的比人物知道的少”,即叙述者< 人物。[16]73在尾声中,穿插了两次外聚焦,叙述了改变后的全新自我,使人物具有神秘感,能够促进文本与读者的互动。第一次是讲述了她勇敢接受并参加了女儿的婚礼,“她准备接受女儿爱伦的邀请去芬兰参加婚礼。”[11]238外聚焦在此就像一个摄像机,客观地拍摄婚礼快乐的场景,实现了小说叙述的情境化。此外,玛格丽特再次用了外聚焦,讲述了坎迪达决定编织毛衣而不再是玩纸牌来打发时间,象征着她像命运3女神克洛特一样作为命运的纺线者,从此决定纺织自己的命运。内外聚焦间的转换表现了德拉布尔高超的叙事技巧,也更加客观地描述了坎迪达在多次挣扎后,成功走出困境的形象,体现了意料之外的实质回归。
结语: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作为一名关注妇女生活和心声的作家而成名。她的作品反映着与她同时代女性的命运,正如评论家罗莎琳德·迈尔斯(Rose, Ellen Cronan)说,“德拉布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她的作品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状况及妇女的处境,妇女如何力图适应战后社会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心理影响及她们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的过程。”[18]5从处女作《夏日鸟笼》到中期作品《中年》再到晚期作品《空床日记》,体现了她阶梯式的女性书写,女性各阶段的命运与生存危机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晚期作品《空床日记》中,德拉布尔打破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运用了高超的后现代主义叙事技巧讲述了以“坎迪达为主人公正步入老年危机的女性群体雕像”的自我救赎与重生的故事。该小说成功运用了热奈特的3类聚焦并成功地进行了转换,巧妙地结合了女主人公从身处困境、寻求自我到自我救赎成长心路历程,并展示了步入老年人的女性应如何解决生存危机。由于年龄增大带来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如何让老年女性幸福快乐地享受天伦之乐,需要老年人自身、家庭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努力。《空床日记》体现了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对老年群体的生存关注,表现了她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情怀。
[1] 曹琴琴. 德拉布尔创作概述及研究现状[J]. 英语广场,2013(9):44-45.
[2] [6]程倩. 寄梦神话-析德拉布尔小说《七姐妹》之互文戏仿[J]. 外国文学,2011(5): 74-81.
[3] Rubenstein, Roberta. Fragmented Bodies /Selves /Narratives: Margaret Drabble’s Postmodern Turn[J].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94(1): 136-155.
[4] 转引自未怡.论《七姐妹》中的重生主题[D].四川:四川外语学院,2011.
[5] 李凤.《七姐妹》中的心理空间与自我寻找[D]. 陕西:陕西师范大学,2007.
[7] 相菲, 徐建刚.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小说《七姐妹》的女性主义叙事解读[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0(6):22-25.
[8] 吴庆军.《尤利西斯》叙事艺术研究[M].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59.
[9][10][13][16]Gerard, Genette. Narrative Discourse Revisited[M]. Ithaca 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72,74,73,73.
[11] 德拉布尔·玛格丽特·空床日记[M]. 林之鹤,译.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8.
[12][13]Drabbel, Margaret. The Seven Sisters[M].London: Penguin Books,2002:19.
[15] 胡亚敏.叙事学[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5.
[16]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3.
[17] Rose, Ellen Cronan. Margaret Drabble: Surviving the Future[J]. Critique, 1973(15): 5.
[18] 德拉布尔,玛格丽特. 空床日记[M]. 林之鹤,译.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8.
A Study of Returning and Transcendence inTheSevenSister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Focalization
QING Li-yu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Hunan, China)
TheSevenSistersis the masterpiece of Margaret Drabble during her late writing years. Based on Gerard Genette’s narrative focalization theory, the narration of the novel is centered by internal focalization, supplemented by zero focalization and with some switch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calization. The multiple narrative focalizations not only represent Margaret Drabble’s excellent narrative strategies, but also display the readers a desperate old woman’s growth process, that is the process of self-lost, self-finding, self-regression and then to return to the reality and transcend herself successfully, which implies that Margaret shows great humanism for the aging women who are in living dilemma.
TheSevenSisters; Narrative focalization; Returning and transcendence; Humanism
2014-08-07
卿丽园(1990-),女,汉族,湖南邵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I106.4
A
1672-4860(2015)02-006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