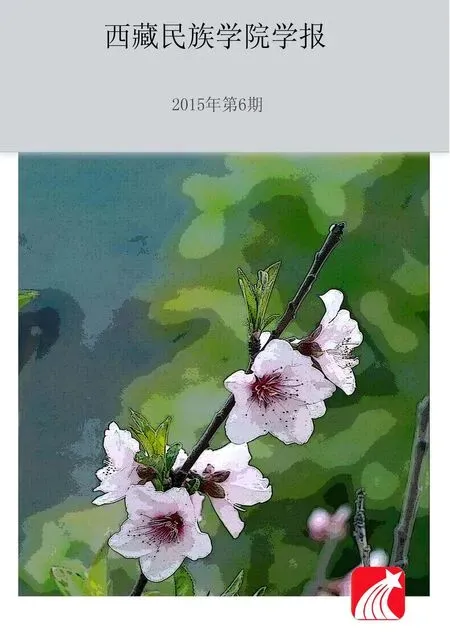涉藏汉英翻译面临的问题与翻译策略讨论
2015-02-20王鹿鸣
王鹿鸣
(陕西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3)
涉藏汉英翻译面临的问题与翻译策略讨论
王鹿鸣
(陕西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陕西咸阳712083)
涉藏汉英翻译在西藏文化对外传播、加强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是目前涉藏汉英翻译存在着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译者的专业素养不高,即不了解西藏,没有意识到涉藏汉英翻译的特殊性;另一个是翻译的主导权和话语权长期被西方控制,我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可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译者加强自己的专业素质,了解西藏文化和历史,这样才能将真实的西藏形象呈现在西方人面前。
西藏;汉英翻译;翻译策略
西藏问题是目前国内外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国外,尤其是西方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与实际的社会现实认识有时存在严重偏差,从而导致了中西方西藏研究专家沟通的障碍,甚至导致政治观点的冲突。这种认识差异除西方反华势力政治目的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部分西方人用来认识西藏的资料本身欠缺真实性和准确性,无法正确反映西藏的真实状况。
西藏材料之所以欠缺真实性,笔者认为译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去,大部分西方人是通过西方译者的译本了解西藏的,这些译文很容易受到西方译者意识形态、翻译目的和语言水平的影响,因而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反映西藏的真实情况。因此,由我们主导翻译,将西藏资料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介绍西藏的真实情况就成了一个必要任务。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译者从事涉藏汉英翻译活动,但是这类翻译活动也存在诸多问题。笔者在与一些藏族学者交流时了解到,现在从事涉藏汉英翻译的译者多为不懂藏语的、非藏学专家的英文专业毕业的翻译人员。这些译者不懂藏语,不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因此在翻译一些具有西藏特殊文化的概念时存在困难。而且现在的许多材料都是从藏文先译成汉文,然后再译成英文,而藏—汉译本本身可能存在信息丢失或误差,有时汉译英译者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必须从藏文文本中确定原文真正表达的意思。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所做的众多翻译活动都是“白忙活”,因为这些研究材料无法真正进入西方学界,从而无法在国际学术圈内产生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因而,笔者认为,涉藏汉英翻译存在其特殊性,它涉及中西话语权的不平等,因此讨论涉藏汉英翻译除了讨论“这个词在英语中对应的是哪个词”,“这个句子怎么表达才符合英语习惯”这样的具体翻译技巧外,还应该考虑更为宏观的政治和文化要素,才能建立或者夺回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准确且顺利地将西藏的真实状况介绍到国外。
要解决涉藏汉英翻译的现实问题,应该从两个层面出发,一方面要提高译文的质量,即能够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概念;另一方面要夺回我们翻译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一、涉藏汉英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专业素养
目前国内从事涉藏汉英翻译活动的译者主要是非藏族或非藏学专家的英语专业(或非专业)译者,他们通常是受相关的出版、教育或研究机构委托进行翻译活动。这些译者首先对专业术语和表达方式把握的准确度不够,尤其是涉藏文献中有大量藏语或宗教内容,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此外,涉藏文献常会涉及一些政治因素,如果译者对西藏问题不熟悉,对国家政策不熟悉,有时可能会影响到国家正常的对外交流。一般常用的术语和表达方式业内都有官方的标准译法,负责任的译者可以通过查阅藏汉、藏英辞典或咨询藏学专家确定译文的表达方式。但是有一些在业内仍存在争议的概念,译者在翻译时就不太好把握。例如,“民族”这个概念,一般译者都会翻译为“Nation”或“Nationali⁃ties”,也有些人译为“Ethnic group”。同一个汉语词汇对应着两种英文表达方式,但是这两种英文术语的内涵意义却截然不同。“Nation”或“Nationalities”是一个政治概念,与17世纪欧洲出现的“民族自决”和“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相联系,在西方语境下会让人联想到一个独立的国家,而“Ethnic group”是一个文化概念,强调“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等)甚至不同种族体质特征但保持内部认同的群体。”[1]。也就是说,我们在表述“中华民族”和“中国有56个民族”这两个概念时,虽然汉语使用的都是“民族”,但是在翻译时,前者应译为“Nation”,后者似乎应译为“Ethnic group”。而且正是汉语中的“民族”这个词具有含混性,现在不少学者提出采用“族群”(Ethnic group)来指称国内的各个少数“民族”,从而与“民族”(Nation)的概念区分开来。如果译者不了解其中的差异,遇到“民族”就译为“Nation”或“Ethnic group”,那译文必然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关于“民族”的译法早已不是一个新兴的话题,多年前国内许多民族院校名英译时已经意识到了中英语言中“民族”概念的差异性,例如中央民族大学的校名在翻译“民族”一词时就采用了音译,最后确定的官方名称是“Minzu University ofChina”。随后也有多家民族院校仿效中央民族大学的翻译方法采用了音译。当然,校名的翻译与学术文献和外宣资料的翻译不尽相同,因此不是说“民族”都译成“Minzu”就是最好。在翻译“民族”这个概念时,译者应该根据上下文语境和文本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
再如“西藏自治区”的译法现在也存在一些争议。我们一直以来采用的是“TibetAutonomous Re⁃gion”。但是,现在也有人提议将“Tibet”改为“Xi⁃zang”,即采用汉语拼音音译。因为“Tibet”一词最初是蒙古人称吐蕃为“特白忒”的译音。吐蕃并不等于现在的“西藏”,“Tibet”一词的内涵意义和所指的地理区域与“西藏”有着明显的不同[2]。目前,西藏民族大学的官方英文名称也采用的是“Xizang Minzu University”。
当然,以上两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举这两个例子是为了指出涉藏翻译中还存在着许多未统一的译法,而未统一的原因是学界对这些概念有争议。那么,如果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够严谨,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仅凭着自己的猜测望文生义,想当然地拿起原文就译,势必会导致译文的不统一和表述的含混不清。
此外,藏族人名、地名或一些特有的宗教文化概念在用汉语表述时多为藏语音译,一些不用心的译者直接用汉语拼音转译这些概念,而西方现在在表述西藏人名、地名时一般采用拉丁文转写和国际音标,也有采用两种混合体的,这样翻译出的译文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淆。笔者在进行翻译工作时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例如在《陕西中医药史话》第二十章《唐代长安与西藏的医药交流》中出现了藏族人名“哈祥马哈德丸”和“达玛郭嘎”。这两个人不像文中提到的“松赞干布(Srongbtsan Sgam⁃po)”、“那木日松赞(Gnamri Blonbsan)”和“赤德祖赞(Khrilde Gtsugbsan)”已有译文先例,因而无从参考。此外还有几部汉文音译的藏文医学著作名称,如《门杰亲木》、《敏吉村恰》和《门杰代维给布》,也是无法参考现成的译法,最后是在藏学学者的帮助下确定了译文。如果有些译者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直接将达玛郭嘎翻译成“Da Ma Guo Ga”,那么译文势必会让西方读者感觉很别扭,而且西方许多藏学学者只懂藏语不懂汉语,这种译法可能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传播西藏文化的过程中,译者显然扮演着一个纽带的作用,如果译者都读不透原文,意识不到原文背后存在的诸多文化和政治问题,那么译文质量必然会大打折扣。因此,从事涉藏汉英翻译的译者应该深入了解西藏文化,尊重西藏文化,同时要熟悉国家对西藏的政策,如果是专门从事涉藏翻译的译者甚至应该学习一些藏文和藏文拉丁文的转写,至少在翻译西藏人名和地名时能够与西方文本保持一致,没有条件学习藏文的,最好与懂藏语的专家进行合作,尽可能地提高译文表达的准确度。
二、涉藏翻译的话语权问题
(一)翻译活动在文化主体自我重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既然我们进行涉藏汉英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传播西藏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那么这种翻译活动一定是一种文化活动。大多数翻译活动都是在两种或以上文化中进行的,而文化之间通常会存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这种权力的不对等决定着翻译活动的内容和方式,而翻译活动反过来又会对两种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后殖民翻译理论家们对这种翻译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并不只关注独立后或殖民化后的前欧洲殖民地的研究,它还研究所有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3](P465),而权力关系正是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理论的重要结合点[3](P134)。后殖民翻译理论一直在试图回答两个问题:首先,国家之间权力的不对等是如何影响翻译活动的?其次,该如何通过翻译来帮助揭露、挑战和消除殖民统治残存的影响?
后殖民翻译理论家借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学说和路易斯·阿尔都塞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及“召唤”(interpellation)学说来阐述翻译在西方殖民统治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作用[3](P474)。葛兰西认为即便权威力量已经被消除,它还将继续对一个民族的自我认识、价值观和政治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尽管现在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统治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殖民国家的意识形态仍然影响着前殖民地人民。在阿尔都塞的理论设想中,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只有在统治力量的“召唤”下才能形成,而这个“召唤”的过程,就是社会成员屈从于权威的过程。将殖民地居民描述为野蛮、落后、未开化,就是从主观上建构起殖民地土著的形象,而这种落后、野蛮的主体形象又内化在被殖民者心中,强化了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从属心理,从而巩固了殖民者在当地的统治。在这个实现“霸权”和“召唤”主体性的过程中,翻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特佳斯维尼·尼南贾纳(TejaswiniNiranjana)认为弱势文化文本的翻译不仅强化了殖民者的统治,还能召唤被殖民者的主体性。她在《为翻译定位》一书中便通过麦克诺基、琼斯、密尔等人翻译和编撰印度文本的具体事例向我们阐述了处于强势文化地位的殖民者如何通过翻译活动对“东方”和被殖民者的形象进行了重构,而这种被西方构建起的被殖民者的形象又逐渐变成了“现实”[3](P134)。英国殖民者在为西方读者准备的翻译文本中将印度人描述为“逆来顺受”、“懒惰”、“狡诈”、“女人气”等等。英国殖民者通过这种“召唤”,建构起了印度的“他者”的形象,而且这个“他者”是劣等的、野蛮的,因而需要更文明、更进步的西方文明的“拯救”。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对弱势文化进行了重现,建构起了一套完整的东方主义形象,这种形象同时成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眼中的“现实”[4](P201)。也就是说,西方人在提到“东方”时,联想到的总是落后、野蛮、贫穷等低劣的形象,而东方人长期在这种强势的“西方化”认识的影响下,也开始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
根据上述西方后殖民翻译理论,翻译活动不仅是文本的转换,更是文化的影响,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按照强势文化意图的重塑。中国曾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在进行汉英翻译活动时不具有文化交流的主导,西方却在汉英翻译中长期主导着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直到今天还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涉藏翻译长期以来也受西方强势文化话语权的主导,汉语表达的权利受到忽视,一些涉藏问题的翻译标准往往不自觉地以西方话语为标准,致使我们的涉藏翻译表现出被动局面,比如前面提到的汉语“西藏”究竟是以西方“Tibet”为英译标准,还是以“Xizang”为标准更符合真实的西藏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变迁,就涉及话语权问题[2]。我们沿用西方的译法,以为“Tibet”就是西藏,正是受到了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忽视了自己的文化与历史。
(二)翻译活动在“西藏”主体性塑造中的作用
既然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前殖民地与前殖民国家之间的翻译活动,还包括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之间权力与翻译的关系,那么后殖民翻译理论也适用于研究涉藏翻译。尽管西藏未曾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但是西方国家也曾经通过一系列东方主义的翻译活动重新塑造了西藏的主体性,这也是导致当前中西方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产生偏差的一个原因。
汪晖认为,西方国家对西藏的认识是一种“东方主义的幻影”[6](P4),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眼中的西藏,是凭借其意愿,在其经验之上构筑起的一个具有主观性质的他者形象。这种他者形象又帮助西方国家构建起了自我,西藏的“东方主义幻影”也从而成为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汪晖在《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中描述了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是如何构建起西藏的东方主义形象的。根据汪晖的描述,最早将向西方描述西藏的都是一些罗马传教士,他们来到西藏是为了“寻找失落的基督徒”。卢梭、康德、黑格尔并未去过西藏,他们是通过罗马传教士对西藏文化的叙述而认识西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们的西藏观。这种被罗马传教士主观处理过的文本(主要是宗教文本)与西方学者自身的主观经验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符合西方学者内心需要的西藏形象。19-20世纪,神智论在西方开始流行,这一思潮产生于对工业化和现代化普遍怀疑的背景下。这种神秘主义与西方藏学产生了联系,它将西藏描述成“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滥饮的,与世隔绝的国度,一群仍然拥有古老的智慧的人群。[6](P23)”但这一形象与当时处于农奴制下的西藏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它不过只是20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为了满足自己逃离现代化的需要而主观构建起的一个理想世界而已。纳粹认为雅利安祖先来自于西藏,并派恩斯特·舍费尔(Ernest Schafer)三次奔赴西藏,以确定雅利安人种族的来源,目的是为自己的种族主义教义寻找科学根据。但实际上,“这与西藏无关,完全是欧洲人创造的”[6](P26)。战后西方的藏学进一步发展,但是东方主义的影响仍未消除。在经历了战争和工业化等灾难的西方人将西藏看作一个和平的、神秘的、精神性的世界。与此同时,西方学者眼中的西藏形象也通过一些大众读物,如詹姆士·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在大众中传播开来。向往西藏和信仰喇嘛教在商业包装下似乎成为了一种大众追逐时尚,而不是真的为了找寻精神皈依。
上述不同时期构建起的西藏形象尽管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是西方人为了满足自我建构的需要而树立起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立欧洲文化的优越性。而这一过程既是通过单纯的文本翻译活动,也是通过其他广义的翻译活动实现的。
这种对西藏的东方主义构建不仅使西方对西藏形成了错误的认识,还逐渐渗透到了我们自己对西藏的认识之中,成为了两种文化间的“现实”。汪晖在书中提到了云南中甸的现状,许多去中甸旅游的中国游客也都有着亲身感受。香格里拉已成为了中甸的官方名称,香格里拉不仅是西方人,甚至也是中国人向往的一个神圣的旅游之地,而香格里拉这个名称却包含着西方人对藏民族和藏文化的幻想,当地政府在不知不觉之间将香格里拉打造成了西方人想象中的模样,而我们却还以为当地的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确如此。
现在必须打破这种扭曲的主体性,否则无法纠正西方国家对西藏的认识,西藏也无法从神话中挣脱出来,寻求自身的发展,也就无法破解中西方在西藏问题认识上的矛盾,而涉藏汉英翻译在此承担着重要的作用。
三、涉藏汉英翻译策略
既然翻译活动可以重塑民族的主体性,那么它也可以被用来抵抗和消解已建立起的主体性,从而建立新的主体性。这就需要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来实现。前面提到,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翻译来帮助揭露、挑战和消除权力不平等对翻译的影响的。翻译不仅可以被用来征服一个文化,也可以被用于反抗和抵制文化霸权[4](P202)。因此,我们要采用具有抵抗意义的翻译策略来重新翻译,或重写西方通过翻译而构建其来的西藏形象。那么,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可以挑战和抵抗西方文化霸权呢?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认为翻译策略(translation strategy)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翻译文本的选择,另一方面是翻译方法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受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影响的。尽管翻译方法和技巧众多,但是基本上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大类: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和异化翻译(foreignization)[3](P146)。韦努蒂对翻译策略的划分是基于施莱尔马赫对翻译方法的描述。施莱尔马赫认为,任何一种翻译方法都不可能完全传达原文,只能尽可能地接近原文,但是译者可以在两种翻译方法之间选择。“译者要么让作者安居不动,把读者领向作者;要么让读者安居不动,把作者领向读者[7](P20)”。前一种是异化法,后一种则是归化法。异化法就是要“偏离民族中心主义,压制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标志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让读者走出国门。”;归化法是“从民族中心主义出发,使原文屈从于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将作者带回本国。”施莱尔马赫显然倾向于异化法[7](P20)。
韦努蒂指出归化翻译是用一种“透明的、流畅的、隐形的”译入语语言和风格进行翻译,目的是消除译语文本中的异域特性[3](P146)。这种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规范,消除了原文语言或风格特征,读者在阅读翻译时以为阅读的是原文,而意识不到自己阅读的是翻译。异化翻译是“选用一种被译入语文化主流价值观排斥的文本或翻译方法”[3](P147)。异化翻译要显示原文的差异性和正确展示异域文化,而要展现这种异质性就要打破译入语的话语规范。显然,韦努蒂倾向于选用异化翻译策略,因为它可以“抑制翻译的文化中心主义暴力[7](P21)”,是对“世界现状的一种战略性文化干预[7](P21)”。
那么根据韦努蒂的翻译策略观,我们的“翻译”西藏活动也要从两个两面出发,一个是文本的选择,另一个是翻译方法。
首先在文本选择方面,要挑选能够挑战西方即成“范式”的文本。当然,我们不能为了挑战而挑战,这些“范式”文本必须是不符合西藏真实情况的,需要重新改写纠正的。例如大量翻译国内优秀的、能够反映西藏现实状况的学术论文、专著或文学艺术作品。
选择合适的文本之后才涉及翻译方法的选择。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是适用于涉藏翻译的。因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抵抗西方主流的民族中心主义语言暴力、重新建构西藏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形象和呼唤新的主体性,那么在翻译时就不能再选择透明、流畅、隐形的翻译方法,而要以一种边缘化的话语抵抗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异化法挑战了英语的文化规范,突出了异域文化特征,有助于打破西方对西藏的主观认识。前文提到的民族院校校名中的“民族”采用音译“Minzu”以及“西藏”不译为Tibet而音译为Xizang都是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这两个译文都打破了原有的翻译范式,突出了自身的特殊性,也反映出我们在找回涉藏汉英翻译主导权上所做出的努力。
四、结语
涉藏汉英翻译在传播西藏文化,加深中西方相互了解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们依然面临着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方面是译者专业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是要夺回我们翻译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提高译者的专业素质要求译者
加深对西藏的了解,甚至需要懂藏文。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耐心解决。在争夺话语权方面,我们可以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选择能够真实反映西藏的文本,并采用具有“抵抗性”的翻译语言将西藏的真实现状呈现在西方人的面前。总的来说,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都要求译者懂得西藏的历史和文化,因此,涉藏汉英翻译者的肩上扛着沉重的担子,如果无法将真实的西藏形象传播出去,不仅会影响中西文化的交流,甚至会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产生负面的影响。
[1]马戎.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王鹿鸣.Tibet或Xizang,关于西藏英译的讨论[J].西藏研究,2014(5).
[3]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4]Jeremy Mo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Rouledge,2001.
[5]Mona Baker,Gabriela Saldanh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Second Edi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6]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2011.
[7]Lawrence Venuti著,张景华,白立平,蒋骁华译.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赵家红]
[校对康桂芳]
H315.9
A
1003-8388(2015)06-0131-05
2015-10-28
王鹿鸣(1986-),女,陕西咸阳人,现为陕西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