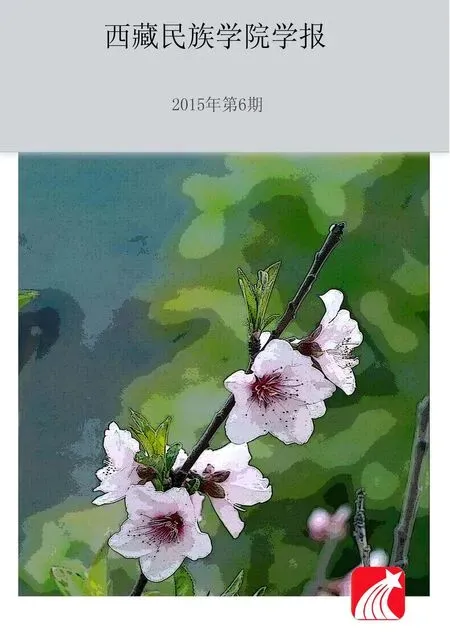西藏地方档案基本概念考论
2015-12-08侯希文
侯希文
(西藏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西藏地方档案基本概念考论
侯希文
(西藏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陕西咸阳712082)
以索解西藏地方档案管理为旨归,本研究采用考证法与历史分析法,在综论西藏与西藏地方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西藏地方档案、藏族档案、藏语档案的要义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源、梳理和辨析。
西藏地方;藏族档案;档案史;价值
近年笔者相继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西藏地方档案发展史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课题“明朝以前西藏地方档案管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倍感困惑的,就是学界对西藏地方档案的一些基本概念,诸如“西藏地方”(西藏)、“西藏地方档案”、“藏语档案”、“藏文档案”等一直语焉不详,界定模糊,存有分歧。缘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探源、梳理和辨析,以免学界因误用而产生不必要的歧义。
一、西藏与西藏地方
(一)关于“西藏”名称的由来,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西藏”一词,是藏汉两种语言结合的产物,“西”是汉语,表示西藏这块地方在祖国的西部,“藏”是藏语,就是“卫藏”(即乌斯藏),去了“卫”(乌斯)字,留下“藏”字,二字合起来就是“西藏”[1](P3)。
第二种观点,藏文“卫藏”的“卫”与满文“西方、西方的”(wargi)一词的读音相近。如“西城”的满文是“wargihecen”,意为“西边的城”;“西域”的满文是“wargiba”,意为“西面的地方”[2](P1082-1083)。另据文献记载“依议:拉藏及班禅胡土克图、西藏诸寺喇嘛等,合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清实录》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戊寅条)这段满文中两次提到“西藏”时所用的满文词组都是“wargi dzang”,其意可理解为“西面的藏”。而且“卫藏”地处中国西南。由上述我们可以推测,清朝满族君臣把“卫藏”(乌斯藏)当做“西面的藏”,称之为“wargi Dzang”。也就是说藏文“卫藏”(乌斯藏)一词先译为满文,即“西方的藏”,再从满文翻译成汉文,译为“西藏”,就此诞生汉文“西藏”一词[3]。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可信。
(二)西藏名称的渊源
“西藏”一词,最早见于《清实录》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丙申条:“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4](P34)但当时尚未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域名称,出现频次较少。1721年清军驱逐侵扰西藏的准噶尔军后,康熙帝《御制平定西藏碑文》“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一语,正式把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地区命名为“西藏”。
“西藏”历史上曾有不同的称谓,大致演变脉络为:三皇五帝的舜时期,称三危;商代一直到南北朝时期,称羌(人);唐、宋称吐蕃;元称吐蕃、乌斯藏;明朝初期称吐蕃、乌斯(思)藏,明后期称土伯特、唐古忒、图伯特;清初称图(土)伯特、伯特、唐古特(忒)、卫藏(卫指前藏,藏指后藏)、西藏等。清朝康熙始称西藏,嘉庆以后多称西藏;民国称西藏地方;建国后仍沿用,后改西藏自治区,区名至今未变。
英文“Tibet”一词,一说这是从阿拉伯文“Tib⁃bat”演变而来的,可能源于突厥人和蒙古人称藏族为“土伯特”。公元9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苏雷漫到中国(唐朝),公元851年著书《东方旅行记》,把吐蕃拼写为“Tibbat”。日本出版的《东洋史讲座》指出,阿拉伯人把西藏称为“Tibbat”,显然是受唐朝叫“吐蕃”的影响。法文版《马可·波罗游记》,称吐蕃为“Tibet”,这是目前流行的西方文字语言体系对西藏的称谓。法文译者沙里侬注释说:“‘Tibet’一名,无疑是古代阿拉伯旅行者由中国学得。”[1](P3)
在民族称谓上,“Tibet”对应“藏族”;在地域称谓上,“Tibet”多指“西藏地方”,有时泛指整个藏族地区,与“西藏地方”的含义相去甚远。法、德、俄、日等文中亦如此,这是翻译藏文与外文资料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总之,由于历史上藏语、汉语、蒙古语、满语对青藏高原各部分的地域名称和对藏族的族称都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这些历史上的名称与含义互相交叉,因此对西藏地方、藏民族的称呼及其含义仍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建立,“西藏”一词即成为西藏自治区的专称与简称,在与其他省市并列时,单字又简称为“藏”。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可以从时间、空间上分别予以简要界定。
从时间上,以1959年3月28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开始行使西藏地方政权职权为界,之前我们统称为“西藏地方”,之后称“西藏自治区”(1959年3月28日-1965年9月8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65年9月9日-至今,西藏自治区),简称为“西藏”,或一字简称“藏”。
从空间上,对西藏地方区域的理解,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特别说明如下:我们依据《西藏通史》系列丛刊总序所述,“西藏地方”就是“根据藏族历史和西藏地方历史的实际情况……在元代划分藏族地区的行政区划以前,是以西藏地区为主,包括藏族历史的主要内容,也即是包括了甘川滇藏族地区本身的历史”。从元代开始,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其所涉及区域则以当时中央政府出于行政管理、军事管理的需要而涉及的范围为准。
(三)“西藏地方”概念界定
从时间节点定位,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从此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重在强调西藏地方社会性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对西藏地方档案发展史的影响,以及西藏地方档案在社会重大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从空间维度定位,强调区域性,西藏地方档案发展史不是藏民族在其他聚居区而是以拉萨为中心“西藏地方”的“区域档案发展史”,不是纯藏文档案发展的历史,而是与“西藏地方”相关的藏文、汉文、八思巴文、蒙古文、满文等档案发展的历史。
从一般读者接受角度考量,用“西藏地方”比“吐蕃”、“乌斯藏”、“图伯特”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地方专用术语,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二、西藏地方档案
在界定“西藏地方档案”这一概念之前,我们首先讨论其上位概念“档案”,学术界曾就“档案”的定义进行过多次讨论,形成了多种学术观点,诸如“固化信息”说、“社会记忆”说、“归档保存”说、“副产品”说、“积累物”说等等。笔者采用冯惠玲、张辑哲教授的“固化信息”说:“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下文相关“档案”定义均以此为上位概念)[5](P6)。
据此,笔者认为“西藏地方档案”就是指西藏地方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其中社会组织包括西藏地方历史上的各种社会组织,诸如军事部落、吐蕃王朝、割据政权以及历代中央政府所辖下的西藏地方机构等,个人既有西藏地方历史上的各类杰出代表,如部落首领、吐蕃王朝的赞普、分裂割据时期不同政权的代表人物、苯教或藏传佛教不同派别的宗教领袖等,又有一些普通人的档案。“有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包括西藏地方从远古档案的起源到现在形成的所有的“固化信息”,诸如助记忆时代的原始记事、实物记事、西藏岩画等,藏文产生以后主要有简牍档案、金石档案、纸质档案、贝叶档案、羊胛骨档案、缣帛档案、声像档案,磁盘档案、光盘档案等。
西藏地方档案作为我国国家档案全宗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实地记录了西藏地方以藏族为主的各民族的社会活动,凝聚着他们为生存、发展、审美需要而激发出来的全部智慧和情感。这些档案集中保存在拉萨市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仅历史档案的数量就多达三百余万件(册、卷),约九十多个全宗,时间自元代至今跨七百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科技、医学、历算、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
西藏地方档案可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按档案形成的文字,可以划分为西藏地方藏文档案、西藏地方汉文档案、西藏地方蒙古文档案、西藏地方八思巴文档案、西藏地方满文档案等;按档案形成的时间,概括地讲,可划分为西藏地方历史档案(1959年3月28日以前)和西藏地方现行档案(1959年3月28日以后),后者亦可称之为西藏地方档案发展史的现代史部分。如果严格按照时段来划分,则可以细分为:西藏地方原始记事、西藏地方原始岩画、吐蕃时期西藏地方档案、分裂割据时期西藏地方档案、萨迦时期西藏地方档案、帕木竹巴政权时期西藏地方档案、甘丹颇章政权时期、新中国时期西藏地方档案;按档案形成者的不同,可以划分为西藏地方官方档案、西藏地方寺庙档案、西藏地方土司档案、西藏地方锅庄①档案等;按照档案载体的不同,可以划分为西藏地方纸质档案、西藏地方木质档案、西藏地方石刻档案、西藏地方简牍档案、西藏地方青铜档案、西藏地方贝叶档案等。按照收集方式的不同,分为西藏地方文字档案、西藏地方口述档案、西藏地方声像档案等。
三、藏族档案
藏族档案是指藏民族在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不同形式的固化信息。关于“藏民族”,石硕教授认为:藏民族是以最初的雅隆悉补野部、西藏地方诸部为核心,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扩张和征服,最终在公元11、12世纪,将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众多部落和部族融合而成的一个多元化构成的统一民族。[6]基于此,“藏族档案”应包括以各种语言文字记录和反映藏族历史的不同形式的固化信息。依据前述“在元代划分藏族地区的行政区划以前,是以西藏地区为主,包括藏族历史的主要内容,也即是包括了甘川滇藏族地区本身的历史”,那么“藏族档案”还应包括记录和反映我国境内甘、川、滇藏族聚居区历史的固化信息。这些藏族档案除保存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以外,国内诸如青海省塔尔寺、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拉卜楞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印经院,国家图书馆、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以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等机构均有保存。
四、藏语档案与藏文档案
关于藏语档案与藏文档案的联系与区别,需要特别说明:现代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综合现象,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因此藏语档案的“藏语”所指当为广义的语言概念,既包括语言的语音符号:藏语口语(狭义的语言概念),又包括语言的书写符号:藏语文字(藏文)。也就是说,藏语档案包含藏语口语档案和藏文档案,鉴于学术的严谨性、规范性准则,笔者将广义的语言概念作为“藏语档案”的上位概念。其定义可表述如下:
藏语档案是指“用藏语记载的西藏地方以往社会实践活动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不同形式的固化信息。或者说,所有以体现藏族传统文化特征的藏族语言符号或文字记载的档案都是藏语档案。而华林教授“藏文历史档案是指建国前各个历史时期以藏文形成的反映藏族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天文、历法、医药、文艺、哲学、伦理、宗教、民俗等方面内容,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文献”[7]和扎雅·洛桑普赤博士认为藏文历史档案是指“用藏文直接、真实地记载和反映生息繁衍于青藏高原独特气候和自然环境中的藏民族在漫长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形成的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和宗教文化艺术等各方面活动发展情况并具有一定保存价值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8]均强调这些档案是藏语的书写符号——藏文记载的档案,而不包括“藏语口语”记载的档案。当然我们没有否认“藏语档案中的绝大部分是藏文档案”的历史事实,正如扎雅博士所言“这些档案90%以上皆为藏文历史档案”。[8]所以用“藏语档案”,便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表述档案的外延和内涵,使其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和原貌。
西藏地方档案中的口述历史采集所产生的使用藏语叙述事件的数字录音资料,当属于藏语档案。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中存在大量的文字混合使用的情况,如机构名称使用藏文和汉字两种文字,藏文是作为政治符号出现的,但是档案主体内容使用的是汉字、满文,管理方式还是按照汉字档案或者满文档案的方式进行,因而不属于藏语档案。
综上所述,西藏地方档案基本概念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西藏地方档案基本概念关系图
由图可见,藏语档案与西藏地方档案是交叉关系,二者都是对方体系范畴里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藏语档案”是“西藏地方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西藏地方档案”按语言文字划分,可分为西藏地方藏语档案、西藏地方汉语档案、西藏地方蒙古语档案、西藏地方满语档案等。而藏语档案如果按地域划分:西藏地方藏语档案、青海地方藏语档案、云南地方藏语档案、甘肃地方藏语档案、四川地方藏语档案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西藏地方档案”与“藏语档案”有着密切的联系。“藏语档案”是按照语言标准对档案进行分类,而“西藏地方档案”是从行政区域的角度对档案进行分类,是西藏行政区域内各类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在开展各类业务活动过程中形成各种形式的档案的总称。由于语言应用实践情况的复杂性,“西藏地方档案”可能既包括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汉字的历史档案,也可能包括使用藏语和藏文的历史档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藏语档案”就是“西藏地方档案”中的一个特殊类型。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人民网”推出的藏文网页,这些网页文件也属于“藏语档案”,但是由于网站的服务器并不在西藏自治区,而不能归属为“西藏地方档案”。此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西藏编译局、西藏出版社等与民族地区有紧密联系的机构也会产生藏语档案,但是这些档案不属于“西藏地方档案”。
五、基本概念考论的价值意义
西藏地方档案基本概念的考论,一有利于学者从史论角度对历代西藏地方档案及其管理活动的整合研究,挖掘和实现西藏地方档案的当代价值,从根本上揭露和挫败境内外敌对反动势力企图分裂西藏的阴谋;二有利于探寻西藏地方档案史发展的脉络和特征,增强人们对“多元一体”中华历史文明的认同感;三有利于西藏地方档案数字化建设和信息资源的共享;四有利于学界从更高层次上把握西藏地方档案的实质而不至于迷失在这些相似概念的迷宫中,便于读者对西藏地方档案及其管理活动的源流、特质、价值、功能和内在规律的理解。
[注释]
①锅庄,是古代西藏康定地方藏汉族商品交易的场所,它兼有商行、货栈及经纪人的双重性质,锅庄主人是住该锅庄藏商的代班人,负责与汉族商人洽谈生意。
[1]徐华鑫.西藏自治区地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2]安双成.满汉大辞典[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
[3]陈庆英.汉文“西藏”一词来历简说[J].燕京学报,1999(6).
[4]顾祖成.清实录藏族史料[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
[5]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石硕.论藏民族的多元化构成及其形成时代[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4).
[7]华林.论藏文历史档案的发掘利用[J].中国藏学,2003(4).
[8]扎雅·洛桑普赤,洛龙.西藏历史档案遗产的传承及管理[J].西藏研究,2007(1).
[责任编辑索南才让]
[校对康桂芳]
G279.2
A
1003-8388(2015)06-0114-05
2015-09-25
侯希文(1964-),女,陕西蓝田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档案专题、电子文件管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藏地方档案发展史研究”(项目号:15BTQ075);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明朝以前西藏地方档案管理研究”(项目号:13YJA87001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