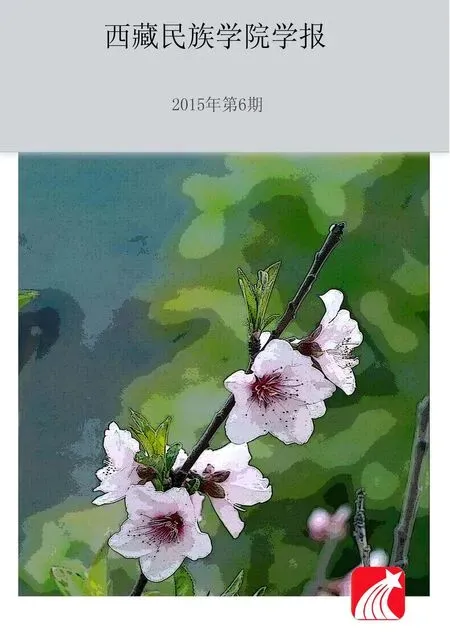论孔子至德中庸的境界
2015-02-20乔根锁赵光耀
乔根锁,赵光耀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论孔子至德中庸的境界
乔根锁,赵光耀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咸阳712082)
本文遵循孔子称中庸为最高德行这一路径,透过《中庸》对“中”、“和”的分析,探讨了“中”、“庸”作为德行的内涵,认为“中庸”是在“道”的层面下表现出来的在无声无息中敦化百姓的平常德行。
中庸;道;中;庸
“中庸”一词由孔子提出,《论语·雍也》记载:“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称中庸为最高的德行。《中庸》的义理深邃难解,历代学者对其注疏解证,今人借助新出土的文献重辩中庸思想。圣人之异于常人并非别有事物唯圣人可见,只在于认识境界上的不同,因此,笔者认为对“中庸”的理解,不在于词意上的分析和解读,而重要的是从境界上把握圣人的意思。
一、解读“中庸”的基础——把握孔子教学方式
“中庸”出自《论语·雍也》,源于孔子的感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而《论语》是主要记录孔子言行和孔子教导学生的语录集,孔子阐述“中庸”是对弟子讲习过程中出现的,因此欲研究“中庸”的内涵,就不得不先考察明了孔子教诲弟子的方式。
孔子对弟子循循善诱,教导内容因人因时而不同,如勉冉有而抑子路,对学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注重弟子的自我反省。如《论语·学而》有记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朱熹注:“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往者,其所已言者,来者,其所未言者。”[1](P53)
孔子告诉子贡更高层次上的道德境界,“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是“所已言”,也是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但是孔子也有所不言,没有说明怎样才能到这种道德修养。子贡领会了其中的意思,如《大学》中所说:“如切如磋,道学也;如琢如磨,自修也。”
我们只有理解了要不断学习、提高修养、精益求精,才能把握孔子所说“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的内容。孔子正是通过省去其中的为学路径来“引导学生发展思维能力”、“让学生通过自主批判的思考”[2],培养弟子健全人格。由此推理,作为“至德”的中庸,也是志士仁人勤而学之才能达到的最高道德修养。
二、中庸是依于“道”而称为最高的德行
孔子称中庸“为德”,又言“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可见中庸不是“道”,而是可“据”之“德”。《中庸》有解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很明确,“中”与“和”的内涵是不一致的。这里将“中”解读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这种“未发”的“中”不是“道”,而是一种依“道”“未发”之时的形态即未呈现之“德”。“和”是“中”对立面,表示为依于“道”而“发”合于时节、应于礼义的状态,是“道”的另外一种呈现即已呈现之“德”。“中”、“和”是本于“道”而呈现出来的两种“德”,这两种“德”将“道”所具有的全部“德”展现了出来。
然《中庸》全文并没有明确解说“庸”的言辞,而解说的“中”也只是“道”的一种形态,这对于被孔子称为“至德”的中庸是不完整的,应当为“庸”找出对应的内涵。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中”为“中庸”之“中”的解读,那么,也就只有“和”用来解读“中庸”之“庸”了。《中庸》紧接着有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中和”依于“道”故天地位乎其中,又以“中和”呈现为“德”故能养育万物。那么,“中”何以能表示为道“未发”之时的德,“庸”又何以能表现为“和”呢?
“中庸”本于道,是以为德。孔子唯一一次明确使用“中庸”称赞之人就是颜回,“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孔子又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与颜回共勉,这里的“行”“藏”都是依赖孔子之道的:“行”是用其“道”而为政治国,“藏”是怀其“道”而未施于民,没有将所具有的“道”呈现出来,但不能说没有立身之道。孔颖达于《中庸》首章下注疏时,表述得更清楚:“正义曰此节明中庸之德,必修道而行,谓子思欲明中庸先本于道。”[3](P1625)“中庸”不是一种修身为己的“道”,而是作为“德”的层面上来说的,是依据“道”表现出来的德行修为。
(一)“中”为道之“内”而有德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云:“中,内也,从口〡,上下通也。”又注“入部曰:内者,入也。入者,内也。然则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作内,则此字平声去声之义无不赅矣。”[4](P20)从字义上说,“中”以“内”来解,在此基础含义上可以分析“中庸”之“中”的内容。就方位及事物层面的“别于外”很容易理解,《论语》、《中庸》里面就有不少例子:“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论语·乡党》),“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论语·公冶长》),“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中庸》)等等。但是《论语》中还有一种抽象意义上的“中”,若仔细分析其含义则可以发现与“中庸”的“中”有着相似性。
《论语·子张篇》有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孔子的“仁”不是停留于言词上的学说,“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5],其本质是实践性的,“力行近乎仁”(《中庸》),似乎并不能简单地说仁在学问思辨之中。那么“仁在其中矣”又如何解释呢?朱熹注释说:“四者皆学问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为仁也。然从事于此,则心不外驰,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1](P190)从朱熹的注可以看出,学者从事学问、明于义理,使心不外驰而达于道,虽不能称为仁,但也只是尚“未及乎力行”。“中”在这里就表达了一种“未发”的形态。又如:“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因此,“中庸”的“中”可以据本意“内”来理解,表示在“道”之内——“未发”,道没有呈现具体形态而具有的德行。
若“中”表示“未发”,又如何称其德呢?“中”以其依附于“道”,故从细微之处可推究其德。颜回身居陋巷,且“屡空”(《论语·先进》),“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孔颜乐处”为后世所钦仰,德行也高于“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的子贡、“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的子路。孔子也称赞泰伯,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泰伯也没有将其德行全部呈现出来,使其恩德加诸百姓,相反其三让天下而又“泯其迹”,孔子却称他为“至德”。由此可见,一人修其“道”虽有“未发”,未能完全表达出来,但并不影响其有高尚的德行。
(二)对“执中”的矫正
历代学者都以“执中”来解“中庸”的“中”,但若将这一词各自放回语境之时并不脱离“中”的基本含义——“内”。“执中”出自《论语》: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
“允执其中”的“其”是“天之历数”的代词,而不是“中”的虚代词,否则直以“执中”告诫舜即可,何须前“天之历数在尔躬”一句话。而且在崇天、敬天的当时,天比“无过不及”更形象更直观,即使到了孔子时代,也以天赞颂圣人,子贡在面对别人诋毁孔子时,评论孔子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孔子对尧的赞词也涉及天:“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杨伯峻译注为:“尧真是了不得呀!真高大得很呀!只有天最高最大,只有尧能够学习天。”[6](P119)尧效法于天,成就了其伟大,尧再以此劝勉舜,使其言行合于天道(在天道之内)、不违背天的规律意志。朱熹在《大学章句序》里说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能“继天立极”[1](P1),而不是用如其说“无过无不及”的“中”来传承。“天”的不可超越性也使得人们对至高之“道”的理解与“天”合在一起。
(三)“庸”即平常,盛德至简如常
许慎《说文解字》录有“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7](P64下),孔颖达解《中庸》时言:“案郑玄目録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3](P1625)同音字相解,在先秦著作中很常见,儒家引用亦是不少:“政者正也”,取为政在端正之意;“义者宜也”,取义在于公正适宜。我们很清楚政不是正,正不能同等解说政;义不是宜,宜也不能完全解释义。同音互解只是偏取相近的一种意思,并不能完全通解。古文中以“用”解“庸”源自《庄子》:
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庄子·齐物论》)以“用”解“庸”,犹如以“通”解“用”,以“得”解“通”。后二者很容易为我们洞穿其意非表面简单相解,以“用”解“庸”,未能明了庸的真意。
王先谦在对上面一段话注解时指出:“庸者,寻常之理之谓也。”[8](P14)与朱熹对“中庸”的解相似。朱熹在《中庸章句》首章下注说:“庸,平常也。”认为道是“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中庸亦是“平常之理”[1](P17-18)。笔者遵从这种说法,“庸”即平常,与高明相对。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在孔子看来,道并不是高深玄远之事,都在人的日用生活之中如同“饮食之味”,“人莫不饮食者也,鲜能知其味也”(《中庸》)。又提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中庸》),平常的德行、言谈,即使隐小细微也是秉“道”所发,不可不慎、不可不勉。孔子对花言巧语深恶痛绝,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相反对“木、讷”很认可,认为这更接近于“仁”。“仁”在孔子之学中地位与“圣”相等,“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孔子曾自述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又说:“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孔子以此自我评价,可以说表达了“大道至简”。孔子弟子公西华在旁边侍奉时对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这种平常浅显的道理,要做好却是不能学得到的。
“中庸”正是有了这种“平常、不高明”的意思,所以真正有德行的人很有可能不为人所知。《中庸》有:“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君子依据“中庸”有不被别人见知的可能,圣人之所以为圣,在于知道不被别人知晓也不后悔,能坚持“中庸”不改。子路任卫大夫孔俚的宰相,子贡也任鲁、卫宰,颜渊却穷居陋巷,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即使是孔子这样有着“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论语·子张》),对于那些没有进入其门室的一般人,是不能认识到孔子的伟大,在他们眼中孔子也就是普通的贤士。
(四)盛德之“庸”才能无时不中节
“庸”理解为“平常、不高明”的话,如何为“发而皆中节”的“和”呢?“庸”的平常、不高明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常,而是一种“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孔子之道在于日用之间,如仁、义、礼、孝悌、忠信,并不涉及天道、鬼神、生死问题,但如果我们只是以日用之间来研究孔子的道就有失偏颇了。“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孔子好读周易,而周易又是法相于天地、弥论天地之道,孔子以此而后又归于日用之间,以平常之间彰显德行。孔子以“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自称,又说:“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上天赐予的盛德也是平常呈现的学之不厌、诲人不倦而矣。
《吕氏春秋》中“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9](P1012-1013)的故事说明孔子对道德典范的看法。子贡以自损财物的方式赎鲁国人,这种大公无私的行为却受到孔子的批评,“赐失之矣”,相反,欣赏子路接受溺水者所赠的牛。《荀子》记载孔子的“执满之道”更明确体现圣贤的平常。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荀子·宥坐》)[10](P379)
孔子讲述“持满之道”就是行“中庸”之德,以愚笨、退让、胆怯、谦恭来保守聪睿、功德、勇力、富有,有似《道德经》中的“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11](P19),正是这种平常之“庸”才可成就保全圣人的德行。“中庸”的“庸”是“大德敦化”时,才能无时不合于礼节,呈现为“和”。
三、中庸“至德”修行进路
“中庸”本于“道”而呈现的德行才是“德之极致,无以复加者”(《论语·泰伯》),这种德行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平常地呈现在日常之间。这种平常的德行当然是人人可行的,这是可能性上来说的,但并不是人人都在做、呈现的就是“中庸”之德。我们还要看到呈现“中庸”之德的根本在于“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不修“道”而欲求其德,是谓舍本求末也。
(一)居敬守诚,其德乃起
《中庸》提出了“诚”的概念,认为可以由“诚”到“明”的“天道”,“至诚”可以“尽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叁矣”。“诚”就是“正心”、“诚意”,在《论语》就是“敬”,是修身为礼的基础。“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节仪式都只是表达“礼”的一种形式,究其根本,“礼”在人的内心,要从内心和感情上体悟“礼”的要求,也就是“克己”、“诚意”。
(二)行“忠信”,其德乃形
孔子之学的基础就是“忠信”,有德行的人从忠信开始,一个不讲忠信的人便毫无道德可言。孔子认为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守信,一个人不讲诚信也就无法立身,犹如车子失去了行走的依据,“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是以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论语·学而》)忠信是一个人不能丢失的,即使面临生死问题也不能违背忠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所以孔子以“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教育弟子,忠信是核心,学文修行都是辅助忠信的。
(三)勤于学,其德乃长
忠信只是为人的开始,孔子成其圣、颜回成其德都在于好学。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同样,颜回也是好学者,甚至孔子认为除颜回之外弟子中再也没有好学的人了,“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雍也》)为学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了“人爵”求取俸禄,而在于修养自己的德行,“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一个不好学的人德行就有很多问题,“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四)依于礼,其德乃现
内在的德行要依附于“礼”才能彰显出来,“礼”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据。“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尽孝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仁也就是“克己复礼”。“礼”是约束自己行为的有效标准,依照于“礼”才能减少过失,提高德行修养,如孔子又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孔子推崇周礼,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我们要认识到孔子并不是绝对的认同周礼,也不是固化礼仪制度,他看到了周礼“有所损益”,同时礼也只是来约束人过分行为、克服不良弊端的仪式,更重视恭、谦、俭、让等内诚的修养。
(五)安贫乐道,其德乃丰
“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求学志道之人必然是安贫乐道的。能否安于贫困也是检验一个人是否有德行的重要标准,“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颜回“在陋巷”,真正有德行的人追求为人之道而不忧惧饮食条件。“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正是这样,“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
(六)知“天”知“命”,其德乃成
孔子观念中的“天”不是神格化的“天”,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准则,“是道德的源泉”[12]。孔子晚年好学易,易经“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特性,为孔子提供了更高层面上的参考价值,吻合于《中庸》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孔子参照于天修其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庸》)
“命”在孔子那里也不是消极意义的,相反是为人修德的基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所谓的知命,乃是“知客观限制之领域”,明确有“种种不为人之自觉所能控制之限制”[13](P100-102)。有德行的人上知“天命”不可违,下有“人命”不可逆,然后言行从事就没有困苦之时。“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孔子知“天命”的行废不在于某人的一言一行,他能坚守“道”而不遗弃,同时也不会逆天强为,并称自己不同于伯夷、叔齐、虞仲、夷逸这些人,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适宜为事,做到“无可无不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因此,有德行的人更会专心于提高自己的德行修养,不在乎死生富贵问题,这也是有别于宿命论的核心。
结语
从孔子所述的至德方面来说,“中庸”是指人的德行如天地,能恩泽万民而人民不会受到侵害,能在无声无息中敦化世人。“中庸”有其德在于有其“道”,只有修其“道”后才会有德,大“道”大德,小“道”小德,无“道”也就无德。大道不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中庸”至德也是平平常常,似乎没有高明的德行。这种看似不高明的德行是明“天地之道”后归于日用之间的“致其博而反其约”,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庸庸碌碌之意。“中庸”至德是圣人也不敢自居的德行,明了“中庸”的含义对于我们上理解圣人境界、下修自身德行都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孔京京.试论孔子教育性对话言说方式的基本特征[J].孔子研究,2007(5).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王杰.从人学的视角看孔子“仁”之学说[J].孔子研究,2001(4).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7]〔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8]〔清〕王先谦.庄子集解(诸子集成4)[M].长沙:岳麓书社,1996.
[9]〔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0]〔清〕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3)[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1]〔晋〕王弼注.老子道德经(诸子集成3)[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2]彭富春.孔子的仁爱之道[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5).
[13]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王勇]
[校对康桂芳]
G279.27
A
1003-8388(2015)06-0101-05
2015-09-15
乔根锁(1951-),男,陕西合阳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汉传佛教哲学与藏传佛教哲学、中西方文化比较。
赵光耀(1989-),男,河南安阳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