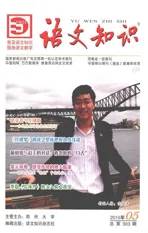阅读与写作应建立类的概念
2015-02-13湖南省常德市外国语学校夏峥嵘
☉湖南省常德市外国语学校夏峥嵘
阅读与写作应建立类的概念
☉湖南省常德市外国语学校夏峥嵘
2014年中考阅卷遇到一篇备受争议的文章,半命题作文“再见,--------”。某考生的题目是“再见,青涩”,以阅读苏轼等大家作品的感受为主,文中赞颂了苏轼等人的情怀和操守,每一个片段的末尾提到了阅读作品让我“告别青涩”,文笔不错。很多老师认为该给高分,也有老师认为文章是以评论人物为主,而本次考试要求写作记叙文,这篇文章表达方式为夹叙夹议,不属于记叙文范畴,应归属于议论文或者议论性散文。
众所周知,记叙文是以记人、叙事、写景、状物为主的文章,以写人物的经历和事物发展变化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文体。而议论文是对某个问题或某件事进行分析、评论,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文是以理服人的文章,记叙文则是以事感人的文章。
无独有偶,中考前夕,曾有个学生问备课组老师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区分说明文和议论文?当时老师感慨万千,因为问话的学生是中上层次的学生。
这说明,即使是语文素养较高的初中毕业生对文体都没有建立清晰的概念。这种后果的形成与教材编写没有体现类的概念和语文教学没有建立类的概念密切相关。
一、从类的概念看现行语文教材
当下的语文教材,很多没有体现语文的类的概念,尤其是主题单元教材。
(一)主题单元组元方式的缺失分析
1.主题组元方式指向性是道德的类的概念,忽略了语文学科独立性。
2013年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亲情”,在单元导读里,有这样两段话:“浓浓亲情,动人心弦。亲情是人间真挚而美好的感情,描写亲情的诗文往往最能打动人。本单元的这几篇课文,以不同的生活为背景,抒发了同样感人至深的亲情。”
“学习本单元,要正确流畅地朗读课文,整体把握文章的内容。要结合阅读提示和课后练习,抓住重点难点问题,深化理解;也要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体会课文所表达的丰富多样的情感。”
第一段是主题介绍,第二段是阅读要求。
整个单元共七篇文章,以亲情为主线,体裁不同。现代文共五篇文章:《散步》《秋天的怀念》是散文(叙事散文),而《金色花》《荷叶·母亲》是现代诗,《羚羊木雕》是根据张之路的小说《反悔》改编的,《咏雪》《陈太丘与友期》语体不同,是文言文。
当然,按主题分类也是类,而且这种分类方法由来已久。1920年,何仲英发表的《白话文教授问题》一文中提到:“现在我听说一个中等学校,全教授白话文,他选材的方法,是以和人生的关系为纲,以新版各杂志中关于某一问题的文章为目。他的现用分类法是:人生问题、妇女问题、文学问题、科学问题、道德问题……依着问题去寻材料。”其中的“某一问题”就是主题,只是这个类不是科学的语文的类,比如“家庭亲情”单元,比如“学习生活”,比如“自然美景”,比如“人生体验”,这应该是属于社会、人生、道德等范畴的类。这样编排的目的似乎主要是引导学生关注亲人、师友、关注自身生活,编排的理论依据倚重于语文的人文性特点,把语文教学的目标侧重在人文修养上。这其实是把语文的教学目标附属于道德修养的功利性教学目标上。这与古代的“文以载道”,以及上世纪的“语文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甚至准备把语文课改成“革命文艺课”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今天,我们建立的语文学科的科学体系,应该兼顾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特点,不应让语文仅仅重复着“文以载道”的功利目的,不仅仅是将“文”改换成“工具性”,将“道”更名为“人文性”。2011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的“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应该是在学生接触文本时自发、自然地感受到的,是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慢慢渗透的。
2.主题单元的组元方式主观性太强,科学性不足。
对于某些文章的主题的理解,我们往往也是见仁见智的,如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用主题为单元组元的方式主观性太强,有失客观。
仍然看人教版2013年新版教材的第一单元,单元的主题是亲情,《散步》《秋天的怀念》《金色花》《荷叶·母亲》均以亲情为主题,均为母子之情,似乎也稍嫌单调。
《羚羊木雕》虽说涉及与亲人的交往,其主题却不是讴歌亲情,表现的是友情与亲情冲突时的一种纠结与矛盾,是对价值观的一种呈现、反思、甚至是指责。有作者张之路的一段话为证:“送礼物的事情可以写成一篇小说,礼物就是眼前这只比较贵重的羚羊木雕。至于是不是告诉孩子要讲信用?是不是表现家长不理解孩子?以至于是不是批评家长重财轻义?说实话,在写作的时候还来不及想,要想的就是写出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以及他们的矛盾心理!争取做到每个人的行为和语言站在他的角度上似乎都是合理的。文章写得有意思了,意义可能就在其中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者的立场是站在同情孩子一方的!”作者显然不是为了赞誉亲情,更多是为了呈现一种生活矛盾,或者说对某种价值观的思考与选择。
编者也许想告诉孩子们,并不是所有的亲情都是美好、纯洁、无私的,当亲情遭遇诚信与道义问题时我们该如何取舍?我们似乎也不得而知。2011年版新课标强调“与教科书编者”的对话,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可是揣摩教科书编者的意图对于一线教师来说,似乎难于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这种交流的明确性不好把握。
《陈太丘与友期》选自《世说新语·方正》。《世说新语》全书原八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轶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这一章记述了陈元方与来客的对话,展现的是七岁的陈元方机智应对的辩才,应该是告诫人们办事要讲诚信,为人要方正,正因为如此才编入《世说新语·方正》。语文版教材同样选录了《世说新语》中的《陈太丘与友期》,却是以亲情为主题。
人教版把该故事编入“亲情”,有可能是因为元方的行为维护父亲的尊严,是否隐含了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意旨在其中:“我们应当维护亲人的尊严,这也是表达亲情、孝敬父母的一种方式”,我们仍然不得而知。但是编者对主题的理解显然偏离了《世说新语》编者的理解。
至于《咏雪》更偏离了亲情主题。文章选自《世说新语·言语》,编者也许只是为了表现人物的机智应对的文学才华。鲁迅曾指出:“《世说新语》这部书,差不多就可看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文中虽有亲人,但谈论的主题不是亲情,展现的亦非人物重情的风貌,而是言语的天赋。当然不可否认,一家人围炉话雪,是一幅温馨和谐的天伦之乐图。
可见,把这些与亲情有关的内容说成是亲情主题的话,多少有些曲解。如果要严格按照亲情主题来选文,古今中外的作品也很多,《世说新语》中“孔融让梨”的故事,《史记·吴太伯世家》讲述了“泰伯采药”的故事,现代的经典文章有朱自清的《背影》等。
3.主题组元导致主题先行的求证式阅读,也难以形成梯度。
主题单元的阅读往往在单元里就标明了主题,这样就容易导致阅读行为的主题先行,容易使阅读成为求证式阅读,限制了学生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的深度,不利于学生的个性阅读体验的形成,也不利于学生的个性思维的发展。
而且,主题单元,围绕主题选材,无法顾及选文的难度。这不是编者的态度执着认真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路径选择自然带来的难题,只要选择主题单元,自然会衍生选文难易难以把握的问题,因为有的主题文章多,有的主题文章少,在难易问题上选择的空间自然就小得多。
温儒敏在2010年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曾说:
而现有的多种新编语文教材的体例都变了,就是采用“主题单元”的框架结构,以主题来牵动整个课程计划。……用主题来划分教学单元或板块,往往顾此失彼,很少考虑难度系数和教学适用度,也难体现语文教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规律。这是迫切需要改进的。
可见,主题组元的方式需要斟酌。
(二)体裁单元选文应注重“类”的典型性
在教学上,体裁单元确实有主题单元所没有的便利性。只是在确定了编排方式后,文本还应围绕着单元选择,应体现单元的类的特色。某些教材在单元选文方面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要是过于侧重名篇名章,忽略了文本本身的典型性。
如语文版九年级下册《语文》第三单元为序和跋的单元,第10课为《读<堂吉诃德>》,记叙作者不同时期读《堂吉诃德》的不同感受,节选自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由中国大学者钱钟书翻译,是典型的名家名篇。语言凝练华丽,文笔优美,单就节选部分而言,是典型的散文笔调,有着浪漫诗人的浓郁的抒情风格。但节选部分的文字却不能体现典型的序文和跋文特点,也不能代表海涅的《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的风格。
钱钟书译的海涅的《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共一万多字,而语文版教材中节选部分才一千多字,对于整个作品来说,实在只能算是片头花絮,甚至都算不上。海涅的引言从人类历史、社会文化的角度阐述作者塞万提斯的思想,阐释《堂吉诃德》,评析其主题与创作风格特色与价值。《引言》的中译者钱钟书先生认为,这篇文章代表海涅对《堂吉诃德》的最成熟的见解和最周到的分析,不失为十九世纪西欧经典文评里关于这部小说的一篇重要文献。主体部分是严谨深刻的学术著作风格,与开头部分浓郁的抒情风格迥然不同。
虽说让学生读懂引言的主体部分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但削足适履的做法会产生非常大的消极作用,这种不具备典型性的节选显然会误导学生对原文的认识和对序文的特点的认识。
这种不注重典型性的选文方法在别的单元里也存在,如语文版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有四篇课文,《忆读书》《我的第一次文学尝试》《山中避雨》与《风筝》。按照教师用书的说法揣摩编者的意图,第一单元应是叙事性质的记叙文单元。然而,《山中避雨》选自散文集《缘缘堂随笔》,《风筝》选自散文诗集《野草》,虽以叙事为主,但均是较为典型的散文笔调。
(三)写作指导与“类”的概念
前文说到的中学生对记叙文没有明确清晰的概念,不仅与阅读教学紧密相联,更是写作教学忽略类的概念的结果。去年某省高考题考到了书信,得分率不高。今年湖南某市中考题又考到了书信,得分率同样不高。这说明什么?学生对应用文更没有类的概念。书信尚不会写,更遑论调查报告、影评、协议书、起诉书之类。
语文学科是科学,需要科学的体系,写作教学也是科学。写作教材的编写应有科学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建立应以“类”的概念为核心。要使写作教学建立类的概念,我以为当务之急是教材建设。我们没有独立的写作教材,更没有与阅读教学匹配的写作教材,我们所见到的写作指导都只是三言两语,零星地散见于阅读教学当中。
夏丐尊、叶圣陶先生编写的《国文百八课》是以写法为主线编辑的,这是语文教材编写的正途。毋庸置疑,语文应该以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为终极目的。吕叔湘先生这样说:“现在也有以作文为中心按文体组成单元的实验课本。但往往是大开大合,作文讲解和选文各自成为段落,很少是分成小题目互相配合,能够做到丝丝入扣的。这就意味着,直到现在,《国文百八课》还能对编中学语文课本的人有所启发。”
《国文百八课》的编排体系对当下的语文教材的编排应该还有参考与借鉴甚至是指导作用。
语文版教材是按照体裁为主分类的,但和其他教材一样,写作脱离阅读,教学内容十分简单,没有体现与阅读教学相关联的精细的梯度安排。
我们再看看人教版,2013年版新教材第一单元写作题为“从生活中学习写作”。在笔者看来,这主要还是说一种写作的态度,而非写作的能力培养与技法,因为这样的写作内容安排在哪一个单元里似乎都是可以的,与阅读教学的关联性不强。但是作为第一单元的写作安排,编者可能是想要让学生树立一种正确的写作态度。第二单元为“说真话抒真情”,第三单元“文从字顺”,第四单元“突出中心”,第五单元“条理清楚”……感觉上是循序渐进的,但从标题上看,仍然是写作要求与目的,仍然是缺失了“类的概念”。到底记叙文该如何写,如何把事记叙得生动,把人写得逼真,把景写得细致?议论文该如何写,如何提炼观点?让人感觉迷茫。梁启超先生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说“每学期开始,教以作文理法”是很有道理的。
如果说语文教学过于“玄妙而笼统”、科学性不足还有待斟酌的话,写作教学“玄妙而笼统”却是切中肯綮。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认为写作是不需要教的,教学时我们也一直强调灵性。诚然,艺术家不是老师教出来的,但是学生不懂得写作的规范是与老师忽略教授有密切关系的。语文教学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培养诗人与作家,首先是让更多的人熟悉和了解写作的基本规范,学会写作各种类型的文章。因此,写作教材建立类的概念实在是语文教学的当务之急。当然,有了合宜的写作教材,也并不意味着学生就会在写作中建立“类”的概念,还需要语文教师利用课堂提供类的训练。
二、体现类的概念语文教材举例
现行的语文版教材以体裁为单元组元方式,有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小说、戏剧、现代诗、书信、古诗文等各自成一个单元。当然,记叙文中又有更细的分类,比如记事的记叙文是一个单元,写人的记叙文一个单元,写景的记叙文一个单元。议论文中又把立论文放一个单元,驳论文放一个单元。戏剧也有两个单元,现代诗有两个单元,以难度递增的顺序呈螺旋式分布在各册书籍里。古诗文则每册书均有两个单元。
其实,在语文教材的编排体例上,自民国以来,很多有识之士做了卓越的开拓工作,叶圣陶和夏丐尊先生赫赫有名的《国文百八课》就是一例。其编排体系是每课一单元,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其中文话是编排的纲领,文选配合文话,文法修辞又取材于文选。我们看看其目录:
第一课
文话一文章面面观
文选一读书与求学
文选二差不多先生传
文法一字和词
【习问一】
第二课
文话二文言体和语体【一】
文选三孙策太史慈神亭之战(《三国演义》)
文选四语录八则
文法二词的种类【一】
【习问二】……
这种科学化的体系体现了一种准确的符合语文学科特点的类的概念。这是以“文法”,即以写作为主要的线索安排选文的内容,穿插语法知识,梯度明晰,坡度合理。编者叶圣陶先生说:“从来教学国文,往往只把选文讲读,不问每小时、每周的教学日标何在。本书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按程配置,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一方面仍求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最后附列习问,根据着文选,对于本课的文话、文法或修辞提举复习考验的事项。”
张志公先生曾评价过《国文百八课》,他说:“五十年代末,我们曾经对十九世纪末叶以下四十年间若干种‘国文’教科书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当时发现,在多种教科书之中,有几种是有显著的特色,比较突出的一种是《国文百八课》。”
《国文百八课》的编排体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于“切实用”。其中应用文有十多篇,有书信,有调查报告,有宣言,有仪式上的演说词,有出版物前面的凡例,有公文标点与款式。说明文有二十来篇,如《梅》《蟑螂》《动物的运动》《霜之成因》《二十三年夏季长江下游干旱之原因》《菌苗和血清》《苏打水》《导气管的制法》《机械人》《图画》《雕刻》《农民的衣食住》《科学名词跟科学观念》《说“合理的”意思》《何谓自由》《美与同情》《论语解题》等,篇数之多,内容之广,也都胜过同时的别种课本。
现在,有很多学生读不懂图表类文章,读不懂说明书,中考当中凡是综合性学习之类的考查学生得分必定会很低。虽说我们的课标总强调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但实际上,综合性学习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这也与教材对综合性学习内容的选择与安排有关,有的综合性学习的内容安排得当,比如语文版的“新闻”的综合性学习等;而以“道路”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多少有点为综合而综合,又把语文学科等同于科学教材了。
三、“类”的概念与“法”的指导
我以为我们的教材除了要体现类的概念外,还要有方法的指导。
2013年新版的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相对于原版作了些调整,编辑可谓用心良苦,目的是想正确引导语文教学。比如:减少了综合性学习的内容,增加了写作,这无疑是在深刻了解语文教学现状的基础上作出的理性的改变。
组元形式也有所改变,人教社中学语文室王本华主任解读2013年版的新教材时说:“改变单一的人文主题组元方式,每个单元由人文主题与语文能力两条线索组成,将语文教学目标落到实处。”我们来看七年级第一单元主题是家庭亲情,培养的语文能力是“朗读一(正确,流畅)”和“整体把握文章内容”,我想能力的培养是贯穿整个初中语文教学的,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每个单元有所侧重而已。正确流畅的朗读和“整体把握文章内容”的能力并非一个单元就能够培养,“朗读二(传情达意)和品味、揣摩精彩语句”的能力当然也并非一个单元就能培养。
朗读还牵涉重音和节奏的处理,没有了朗读知识作为基础的朗读能力还是空中楼阁。我们通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如一个人学习游泳,当然要下河,可是只看到汪洋大海,而不告诉他如何下水,他同样不会游泳。我们的语文教材一直没有语文知识指导,语文教材中我们只看到大量的材料的堆积,如同《教师用书》上同样只看到答案的罗列。
梁启超先生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把文章分为“记静态之文”“记动态之文”“论辩之文”。其中“记静态之文”应相当于说明文和写景的游记类文章;“记动态之文”包括“记人”和“记事”,相当于记叙文;而“论辩之文”则相当于议论文。每种文章都告诉学生如何去做,比如观察的方法等。我以为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教材。梁先生在书中明确地说:“教以作文理法。”
语文教科书里没有语文知识,阅读文章没有文章学知识,写作指导没有写作学知识,当然朗读更不可能有朗读方法……怎么说都是巨大的遗憾和缺陷。语文知识的缺乏势必导致语文教学对语文教师的依赖,这种依赖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要每一位语文教师都成为优秀教师毕竟只是理想图景,而非现实状态。
其次,语文教学应该体现“类”的概念。
教材编排有类的概念是十分重要的,是基础,但并非有了科学合宜的按语文学科的“类”的概念编排的教材,就意味着学生能够建立准确的“类”的概念。要使学生建立类的概念,还需要教师在教学中贯穿类的概念。
首先,教师在单元教学之前应有一个三年的整体规划,每一年、每一学期需要建立哪些“类”的概念框架,如何帮助学生建立这样的“类”的概念,教师要作到心中有数。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接触每一个单元时适当给学生讲授一些文体知识。比如,记叙文要让学生明白概括记叙与具体记叙的区别与作用、记叙文的六要素、记叙的顺序、记叙文的种类、叙事的角度等知识。当然这样的知识也不是学生一接触就能和盘托出,而是随着学生对记叙文的不断了解逐渐深入。接触议论文的时候自然就该给学生讲授议论文的三要素、论据的种类、论证的方式与方法,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体会议论文中的记叙与记叙文中的记叙的区别,体会议论文语言与记叙文语言的区别,记叙文与议论文结构方式的区别等。教师应该教给学生阅读某一类文章的方法,教给学生阅读的钥匙。
单元整体教学法是一种注重类的概念的教学方法。如果教材是文体单元的,在教学中应根据文体特点和文章个性实施教学。比如:语文版教材是按照体裁为主分类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小说、戏剧、现代诗、文言文等是单元编排的重要依据,而记叙文又分为记事为主、写人为主、记游为主的记叙文,难度递增。教师只需适当补充文体知识,在每篇文章的教学中贯穿文体知识的传授、培养学生阅读该类文章的能力就可以了。
对于不是按照文体单元组元的教材,可以实施这样的教学方式:某一单元侧重于某类文章的教学,让学生在阅读某篇文章时建立类的概念,在第二单元时又呼应该类文章的教学。还可以进行教材重组,实施单元整体教学。教材重组的方式也很多,远的如霍懋征的教学,近的如胡志民的“大单元”教学,在教学内容上打破教材的编排顺序,进行增、删、补。
另外,并不是说阅读教学中只要跟学生讲清楚相关文体知识就可以了,就建立了类的概念,还要注重文本本身的个体特点。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始终是阅读教学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就教什么”。
笔者曾听过一堂《苏州园林》的市级参赛课。课堂上,教师大量展示苏州园林照片,让学生形成视觉美感。然后让学生品味其中的语言,体会感悟语言之美。最后揣摩苏州园林建筑艺术之美,这是课堂的主线,其中也穿插了说明方法的介绍。这样的课堂有新意,但是学生第一次接触说明文单元,第一次接触说明文,这样选取教学内容无疑是欠考虑的。教者这样的处理不利于学生建立“类”的概念,模糊了说明文与散文文体的区别,追求新意就显得盲目。就这篇文章而言,语言确实是美的,但是文章精巧的典型的说明文结构,文章摹状貌、作比较的说明方法,使得侧重点不应该只停留在泛泛而谈的“美”(应该是华丽)上,而是应从体会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生动性的角度进行品味。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堂“华美”的课最终没有被评上一等奖。
中学语文教学建立“类”的概念,其学理依据是支架式教学理论。我们必须提供一种基本的概念框架给学生,这种框架中的概念是为发展学习者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所需要的,是培养学生语文素养必不可缺的。要建立“类”的概念,必须先从教材入手。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老师曾说:“我认为目前尚无一套体现语文规律和特点的教材。有太多的内容是非语文的内容,但是占据了学生大量的时间。”我们期待着体现语文规律的教材、体现语文类的概念的教材的出现。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语文教师确立类的概念,并在语文教学中以类的概念为指导进行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