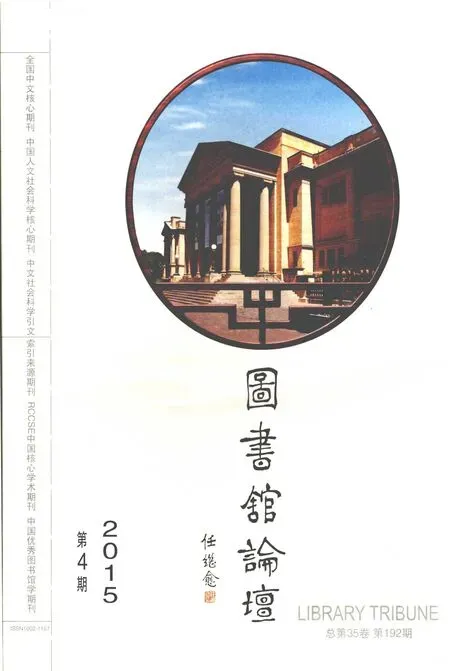基于体验的认知:图书馆文学中的学术思考*
2015-02-13段小虎王稳琴
段小虎,王稳琴
300年前牛顿通过三棱镜在阳光中看到了一个七彩世界,从而开创了现代光谱学的先河。今天图书馆文学就像是体验图书馆历史的三棱镜:在这里可以看到古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燃烧的火焰,看到人类征服空间(巴别塔)和时间(人类记忆)的雄心,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精神纵火者来往穿梭的身影……这里有纳粹集中营里的“图书漂流”,有哥伦比亚农村驴背上的图书馆,有用生命捍卫传统价值的壮举……总之,在这里,渐行渐远的历史重新走入图书馆职业生活,丰富的感性认识为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体验、新的思考。
1 已经发生的,都是序幕
据说埃及托勒密国王建造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唯一目的是收集“全世界所有人写的所有书”。此后,实现世界知识总汇也就成为无数图书馆人追求的梦想。从施莱廷格的“藏书整理”、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到谢拉的“社会认识论”、巴特勒的“社会装置说”,西方学者沿着一条崎岖的理性探索之路,为图书馆学构建了一个包括经验知识、理论知识和价值知识在内的学科知识体系[1]。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图书馆文学作品中,其实也隐藏着另一个“有待认知的感性世界”:上至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下至一般文学爱好者,都曾通过文学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提出了许多深刻的学术问题……对图书馆员而言,这些历经了“百年孤独”的文学作品不仅提供了与职业、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审美体验和情感体验,也提供了与职业、学术、生活密切联系的历史体验和认识体验,是馆员自我审视的一面镜子,拯救迷茫的一种选择。
对阿根廷最负世界声誉的文学家博尔赫斯而言,图书馆无疑是一件“拜神所赐”的作品。人类自开天辟地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通天塔之梦在图书馆里得到了某种补偿:“宇宙(别的人把它叫做图书馆)是由一个数目不明确的,也许是无限数的六面体回廊所构成……任何个人或世界的问题都可以在某个六角形里找到有说服力的答案。”[2]116-119将图书馆与通天塔(巴别塔)、宇宙、六面体回廊相联系,与其说是文学形象化表达的需要,不如说反映了这位魔幻现实主义大师致力于在图书馆空间中探索生命从“有限”到“无限”、宇宙从“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规律。当然,这注定是一段漫长且痛苦的无尽旅程。
相比博尔赫斯的巴别塔、宇宙、六面体回廊,印度诗人泰戈尔更愿意将图书馆比喻为“仙境阆苑”“人类精神的河流”“自我解放的辉煌灯塔”:“人类的声音飞越河流、山峦、海洋,抵达图书馆。这声音是从亿万年的边缘传来的呵!来吧,这里演奏着光的生辰之歌……”在泰戈尔笔下,图书馆隐藏着人类冲破羁绊、激扬个性的希望,也是孟加拉人民觉醒、解放与自由的希望所在:“一踏进图书馆,我们便站立在无数道路纵横交错的交叉点上。有的道路通向宽阔的大海,有的道路通向起伏的群山,有的道路则直通向人类的心灵深处。在这里,所有的道路都是一往无前。这狭小的书香之地,居然拘禁着人类精神的河流,拘禁着人类自我解放的辉煌灯塔。”[3]17-18
有书籍的地方,就有文明的生长。尽管在图书馆文学作品中,赞美从来都不是含蓄的、吝啬的,但这些优美文字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无数书籍或图书馆的悲凉沧桑:从古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数度灰飞烟灭到中国秦代的“焚书坑儒”;从17世纪西班牙征服者摧毁的玛雅文明到21世纪伊拉克战争毁灭的珍贵文献;从法西斯占领下的法国图书查禁到神学家宣判的禁书清单……“图书和图书馆的命运往往不决定于它的创建者所赋予的优点,而是决定于它的破坏者所强加的种种罪过和缺点”[4]106。希特勒曾经说过:“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要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它的语言,根本在学校教育。”[5]一名纳粹记者报道了1939年著名的卢布林·叶史瓦图书馆被毁灭的情境:“破坏波兰最大的塔木德学院,我们感到特别骄傲自豪。我们把大量的图书从大楼里搬出来,运到市场上放火焚烧。大火持续了20个钟头。卢布林的犹太人集合在周围放声大哭,几乎压倒了我们的声音。于是我们把军乐队叫来演奏,军队还大声欢呼,淹没了犹太人的哭声。”[4]217
在纳粹看来,烧毁欧洲成百上千犹太图书馆的火焰,能使“德国人的灵魂重新昂扬”,它“不仅代表旧时代的结束,而且照亮了新时代的到来”[4]217。
而同样的情景也曾在我国发生:1932年日军轰炸上海,目标直指商务印书馆,总厂全毁,东方图书馆几十万书籍片纸无存,焚书的纸灰在空中飘浮。一位日军司令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5]。
据说公元1世纪末里昂的一条法律规定:“每次诗歌比赛之后,所有失败者都必须用舌头把自己写的诗舔掉,不允许次等的文学作品继续存留下去。”[4]64然而到了20世纪,人们又为“谋杀图书”找到了新的办法,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内的许多美国知名图书馆就曾用显微胶片替换据说属于酸性、不易保存的报刊。但几年后一切都不存在了,因为显微胶片的寿命比纸张更短。当然,“使用显微胶片犯罪的不光是美国人,大英图书馆的报纸大部分都在第二次大战的轰炸中逃过了战争浩劫”,但最终没有逃过技术的浩劫。尽管性质不同,但还是让人联想到亚历山大图书馆馆藏被扔进公共澡堂火炉的场景……热衷于用新的传媒技术取代传统传播手段的激情有时也非常危险:198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花费250万英镑在光盘上复制著名的《末日审判书》,十几年后人们发现这份电子文献基本无法阅读,但已有1000多年寿命的《末日审判书》却保护得相对完好[4]68-69。
正如美国学者雷可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在合著的《体验哲学》一书中的观点:“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6]如果说我们的祖先是从自身所处的自然空间体验中开始认识世界的,那么今天,不断强化的信息技术体验让人们对图书馆产生了一种与历史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书籍与图书馆正在走向消亡!作为这一观念的始作俑者,技术决定论早已为博尔赫斯的“六面体回廊”和泰戈尔的“仙境阆苑”设计出一条不归之路。互联网也不失时机地向所有人许诺:“一个虚拟的空间”足以保证人类文明的传承……烧毁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火焰从未熄灭!
2 人是社会空间的创造者,但空间也塑造了人
在传统的认识中,图书馆空间是一个有着固定尺寸和建筑外壳的物理实体,一个被动的、刻板的、静止的“容器”[7]。但文学家则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激情的语言阐释了这个空间的精神意义。
“那该是怎样让人神往啊:推门进去弥漫在馆内的是浓郁的樟脑香息,沁人心脾,让人神清气爽。脚下的地板,皆以最昂贵的细木条编织成人字形的图案花纹,任是铁鞋踏上去,也是无声的猫足,无能(论)有多少人来此读书,也是空巷般的沉寂。明丽的窗子是古代宫廷式的款型,用贵重的木料嵌制成精致的窗格。玻璃的色调,犹如春水,但比春水更蓝;犹如秋空,但比秋空更多几分绿意,是夏末秋初的荷塘中犹未老去的荷叶的绿云,那是一种闲淡如小诗的情调。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静静地读几个小时的书,小口的自篇页上啜饮着知识的甘泉,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8]78这是台湾美文作家张秀亚娓娓道来的一段在北平图书馆读书时的快乐感受。事实上这种快乐感受早已深深地驻留在无数人的心中。“到了一九八八年夏末,斯潘塞公共图书馆有了显著的变化。我们的读者人数上升了。人们在馆里待的时间更长了。他们带着欢快的心情离去,又把这种欢快带到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学校和他们供职的地方……”[9]65-66
当我国学术界在2009年意大利都灵召开的国际图联卫星会议后,开始探讨“作为场所与空间的图书馆”和“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究竟是什么的时候,美国斯潘塞小镇公共图书馆馆长薇奇·麦仑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空间认识论转向”。对薇奇·麦仑而言,图书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慰藉”,并“让他们带着欢快的心情离去”,“究竟他们是来借书、租电影光盘、玩电脑游戏,还是来看望一只猫,又有什么重要的呢?”[9]166
可见,尽管书籍或图书馆有各自的命运,但空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情感体验,它在构造人的身体经验、认知方式、丰富想象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对此,法国作家古勒莫就与博尔赫斯有着超越时空的心灵沟通。晚年的博尔赫斯几近失明,但仍然在书籍和文字所构筑的世界中获得想象和智慧的力量:“对我来说,被图书馆包围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直到现在,我已经看不了书了,但只要我一挨近图书,我还会产生一种幸福的感受……”[10]208而古勒莫显然对《关于天赐的诗》感同身受:“长久以来,我都乐于相信黎塞留路的图书馆是一个理想之地,不会受到世间沧桑和偶然事件的影响,是一个安宁的避风港。能够被它接纳,我感到骄傲和幸福。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对我来说,这个图书馆就是天堂存在的证据。”[11]123
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认为,以往人们看待空间通常有两个视角:作为第一空间的物质视角和作为第二空间的精神视角,前者将空间当做物质化的“实践性空间”,是自然事件展开的场所和舞台;后者将空间看做精神意义上的“构想性空间”,是思想和观念活动的领域。但在索亚看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并没有反映出社会空间的真正活力和复杂内涵,需要构建一种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第三空间”理论,以便集中探讨人与社会生活空间的关系[12]。索亚“第三空间”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传统空间理论,特别是技术决定论者没有认识到的新问题:人是社会空间的创造者,但空间也是有生命的,它“决定着我们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以及和谁在一起”[13]。
谭其骧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在《值得怀念的三年图书馆生活》一文中,谭先生饱含深情地回忆了自己被图书馆“塑造”的过程:“我没有为北平图书馆做多少事,北平图书馆却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做学问的条件和环境,我之所以懂得一点学问的路子,在结束研究生生活后,紧接着又在图书馆里呆上这三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14]476-477据邓云乡回忆:“谭公在北图作馆员时,各部还有编纂委员,如向觉明先生达、赵斐云先生万里、谢刚主先生国桢、孙子书先生楷第,他们后来都是北大的老师。当时在图书馆,每月一百大洋工资,只是看书、写文章,另外还有贺昌群、刘节、王庸、王重民等老辈学人。古语说:未观其人,先观其友,就是这些人材济济的同事,谭公和他们朝夕相处在一起,其学术气氛之浓,友朋熏陶切磋之益,可以想见了。”[15]
在图书馆界,安德鲁·卡内基的名声丝毫不逊于商业界。1848年为逃避饥荒,13岁的卡内基随家人迁移美国。在匹茨堡中心,他发现了由安德逊上校创建、“服务于学徒工”的免费图书馆。他于1887年回忆说:“安德逊上校为我开辟了世界知识宝库,我开始喜欢读书了。”[4]90我们无法知道这位“钢铁大王”的商业成就与图书馆有哪些具体联系,但能够确定的是图书馆改变了卡内基,卡内基为世界捐赠了2500所图书馆。正如巴拉克·奥巴马所言:“当我们劝说一个孩子,任何一个孩子,去穿越门槛,那道神奇的门槛——进入图书馆,我们就永远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6]30
显然“技术决定论者所看到的图书馆空间,仅仅是一个可以被感知、被标示、被分析、被解释的物理空间,完全忽视图书馆空间所具有的精神属性以及作为场所的社会学意义”[7]。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个空间不仅是图书的栖息地,更是人类思想与观念活动的领域、一个探索未知并获得想象和智慧的场所。
3 道德的规则,并不是理性所能得出的结论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始终是书籍的“天敌”。但人类自身“破坏的欲望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人类历史的堤岸”[11]41。这不仅反映在土地战争、宗教战争、文化霸权对书籍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中破坏,也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不法者的贪婪、无知者的胜利。21世纪以来,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这种破坏性力量又以“信息社会意识”的方式侵入到“世界图书馆职业精神”领域[17]。
从体验哲学角度看,体验在建构人类概念、思维、推理或认知中起着首要的基础性作用[18]。现代馆员在不断强化的信息技术体验中,将信息技术“看成是决定社会发展、改变社会关系的自主的、独立的力量”[17],而职业生活中空间体验、情感体验、历史体验的日渐式微又产生了对职业传统的质疑,这在某种意义上导致图书馆职业生活陷入一种既疏离了自身传统又难以在社会信息服务格局中占据主导的尴尬境地。大量图书馆文学表明,体现图书馆传统职业精神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则是在历史文化传承以及无数人艰辛探索中逐渐形成的。尽管“火灾、水患、蛮族、无知者的胜利、审查和不宽容取胜都是威胁图书馆的因素”[11]28,但图书馆职业群体、正义的文化学者以及历代藏书家还是在人类一手造书、一手毁书的博弈中,坚守了自己的立场。
20世纪90年代,为了对抗美国旧金山市政当局决定从图书馆撤出几十万册长期没人借阅的书刊充当填土之用的计划,“旧金山图书馆的管理员表现出英勇的精神,他们趁夜间偷偷进入书库,把虚假的出借日期印在即将清除的书本上”[4]67。在欧洲,当纳粹分子开始掠夺毁灭犹太图书之后,肖勒姆·阿莱汉姆图书馆馆长和另一位馆员每天都从馆里偷偷带走一些书,藏在一个秘密的阁楼里,直到二战结束很久才被发现。历史学家波尔齐科夫斯基评价时写道:他做这件事“并未考虑到是否有谁需要这些书”[4]216。
著名哲学家休谟曾说:“道德的规则,因此并不是我们理性所能得出的。”[19]208这一论断在另一则故事里得到了极好的阐释:1945年5月,当捷克爆发反纳粹起义,俄国军队开进布拉格的时候,作家纳博科夫的姐姐莲娜·西科丝卡雅正在图书馆工作,她知道德国军官准备逃走,但他们借的图书尚未归还,她和一位同事决定把这些书要回来。她们穿行在俄军车辆胜利前进的街道上去挽救图书。她后来写信告诉弟弟:“我们找到了德国飞行员的住处,借书的人冷静地把书还了。可是到那时候,主要马路上已经禁止通行了,到处都是德军架起的机关枪。”[4]294肖勒姆·阿莱汉姆图书馆馆长和莲娜·西科丝卡雅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为了挽救记忆的理性选择,不如说是用生命和“行动的语言”捍卫了传统职业精神。
除图书馆职业群体之外,正义的文化学者也是书籍的忠实守护者。1702年,学者阿尔尼·马格努松得知在丹麦统治下,冰岛的穷苦居民挨饿受冻,抢劫了本国古老的图书馆,把古代书籍的羊皮纸穿在身上当冬衣,其中就有保存600多年的诗歌抄本《埃达斯》。丹麦国王腓特烈四世急忙命令马格努松航行到冰岛去挽救这批珍贵的文献。马格努松费了10年的时间才从各个偷书人身上把书页剥下来,集中在一起运回丹麦[4]113。不过,非常可惜,这套图书被仔细保存了14年之后,又在一场火灾中烧为灰烬。
面对书籍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宁波天一阁的创建者范钦就是其中的代表。数百年来范钦及其后人不仅要在火灾、水患的威胁中扩充馆藏,还必须与战乱、盗窃、掠夺斗争。他们放弃了常人基于理性的价值判断,在付出极大代价之后,终于使天一阁成为“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难怪余秋雨感叹道:“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20]112-125
美国衣阿华州潘塞斯小镇公共图书馆里发生的故事同样包含了对职业精神传承的阐释:在那个寒冷平静的早晨,被抛弃在还书箱、冻得瑟瑟发抖的小猫杜威意外地被馆长薇奇·麦仑发现,从此杜威19年的生命历程便与薇奇坚韧不屈的个人奋斗、小镇图书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史以及小镇居民痛苦与快乐、离去与归来、冷漠与友善、脆弱与坚韧、失败与成功、失望与梦想巧妙地融合在起来。她们共同“目睹了第一台电脑的光临和阅览室的增设”,目睹了“孩子们长大、离开,十年后又带着他们的孩子再次走进门来”[9]4。
当小镇底层居民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兼职或加班时,图书馆员和小猫杜威为他们的孩子带来精神上的慰藉,“把亲人之间的分离时光变成了他们相聚时共同的话题”;当有人伤心、迷茫、孤独、失望或饱受疾病折磨之时,图书馆和小猫杜威就像“在冰雪中跋涉时来到一个小木屋,屋里燃烧的柴火温暖着我们”;当有人为就业发愁的时候,图书馆员为他们准备了“就业服务资料库”,列出了所有工种,以及关于工作技巧、工作性质和技术培训的书籍……正如一位馆员的感受:“这让我有机会从另一方面看清我自身所处的环境,我从另一个角度审视着我们这座图书馆的发展,也解决了久已藏入我内心的挥之不去的疑惑和焦虑……”[21]“找到自己的位置,满足于你拥有的东西,善待每一个人,过好每一种生活,不是关于物质,而是关于爱……”[9]274书中最后的这句话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但又何尝不是信息社会对职业精神的理解。
4 如果对历史一无所知,未来也将行走于黑暗之中
书籍的历史——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每个环节、每个过程都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大到人类社会历次重大转型、东西方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小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生态的构造与差异,都在书籍载体的变化、文字的变化、内容的变化以及创作、生产、流通、阅读、交流等环节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作为人类记忆或文明传承的基本载体,书籍也随着社会的变化历经了口头传播、书面传播和数字传播三个重要阶段。
在口头传播阶段,尽管公元前3000-800年已经分别出现古埃及文字、印度河流域文字、爱琴海文字、中国文字、希腊文字等,但总体而言,那时的文字(包括图形、符号)一般只具有辅助记忆工具的功用,大量的知识依赖于大脑记忆并以口头传播的方式代代传承,著名的荷马史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口头传播(口头文化)的兴盛尽管与文字发育不成熟、识字人数不多、书写材料匮乏有关,但它也涉及到复杂的知识观念问题。以希腊为例,从公元前700年希腊字母发明到书写在希腊深入人心,期间经历了300多年漫长的过渡。一方面识字与书写在当时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而无论是国家法律、社会规范还是学术思想、文学作品,口头传播以其表达生动、受众面广、易于理解等优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另一方面,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质疑书写文化的合法性,认为书写和书面传播“破坏了对大脑的记忆训练”——“它将在他们的灵魂中植入遗忘,他们不再练习记忆,因为他们会依赖写下来的东西……”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你告诉他们很多事情,但没有教给他们任何。”[22]61
当然,当书面传播最终以实体书籍的形式体现出社会变革伟大力量之时,知识界对它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有人说它“解放了人的头脑,产生了更加原创的、抽象的思想”;有人说它“具有超越口头表达的永久性”[22]69。然而,如果就此认为书面传播从此取代了口头传播,将是一个历史性错误。因为直到今天,口头传播仍然是人类知识传播与交流的基本方式,它活跃在演讲场合、表演舞台、教室讲坛、法庭辩护以及人们日常交往之中;在许多地方,它甚至还是人们获取知识与信息的主要方式。
最近笔者对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什字乡某民族村900余位回族村民的调研表明,无论是从人口自然结构、社会结构、闲暇消费结构看,还是从居民信息来源结构、信息内容结构看,该村居民对书面传播的依赖性都极为有限。绝大多数成年人获取知识或信息的主要渠道,除了电视、聊天,就是在每日五次礼拜、每星期五的聚礼、每年两次节日会礼等宗教活动上聆听阿訇诵读并讲解《古兰经》。事实上“古兰”的意思就是诵读,早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人们就普遍认为“通过聆听朗诵来学习比个人阅读学习更有价值”,他们“希望知识通过心灵进入身体,而不是仅仅通过眼睛”[4]178。
图书馆文学作品中的很多故事同样表明,在一些较为特殊的条件下,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具有同等的地位。在纳粹建立的“家庭集中营”里,有一个31号分营关押着500多位孩子。没有人会想到,在这样严格的监视下,他们居然还有一个小小的书库,虽然“只有八本到十本书实际存在,但是还有其他书本在流通,那就是用口头转述的方法。只要没人监视,‘顾问’们便把早已熟记在心中的书背诵给孩子们听,彼此交替轮换,让不同的‘顾问’给不同的孩子们‘读书’。这种轮换被称为‘图书交流’”[4]219-220。
以口头传播的方式服务于不识字的人群,同样是阅读推广的有效手段。20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文化部成立流动图书服务机构,为了将图书送到偏僻的农村,“他们设计了庞大的绿色书袋,可以折叠成包裹放在驴背上,把图书运到山区或热带丛林,书袋展开后悬挂在木竿或树上,当地百姓可以任意选择阅读。有时图书管理人(当地的教师或长老)还会把书朗读给不识字的百姓听。村民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懂得了过去不懂的东西,还把知识转告别人’”[4]208。
尽管从历史看,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有一个从对抗走向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过程,但是今天,当数字传播作为一种新的记忆、传播和交流工具被深深地嵌入到社会转型之中时,许多人坚信它将是书面传播的终结者。不可否认,数字文献与数字传播给知识的传播、交流、利用带来了超越想象的便利,但从人类知识传播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已经在人类社会数千年的知识传播体系中,确立了牢固的基础性地位。正如书面传播的出现终结了口头传播的垄断地位一样,数字传播所终结的也仅仅是书面传播曾经的垄断地位,而不是书面传播本身。因此,从口头传播到书面传播再到数字传播的发展,是人类不断获得新的记忆、传播和交流工具的过程,其所包含的社会进步意义决不是新传播方式对原有传播方式的否定和霸权。从根本上讲,它表现为人类知识传播体系的重构与优化——即将传统的传播模式融入到新的传播体系之中,通过新旧媒体的融合与互补,丰富人类知识的传播方式、完善人类知识的传播结构。
5 结语
尽管在文学世界,图书馆文学还算不上一枝独秀,但对图书馆学术研究而言,它所带来的丰富的审美体验、情感体验、历史体验,可使人随时回想起曾经经历或感受过的生命历程,从而对未来有所预感。从学科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基于体验的认知,将图书馆学术研究引入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历史空间、社会空间之中,重新思考理性与感性、技术与人文、手段与目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其所贯穿的以体验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以及鲜明的情境性、参与性和创新性特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图书馆学科研究范式。
[1] 段小虎.图书馆学术研究中的“论域”问题[J].图书馆论坛,2013(6):26-31.
[2]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M].王永年,陈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3] 泰戈尔.泰戈尔散文选[M].白开元,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7-18.
[4] 阿尔贝托·曼古埃尔.昨夜的书斋[M].杨传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 余源培.关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思考[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4(3):19-24,29.
[6] 王寅.体验哲学:一种新的哲学理论[J].哲学动态,2003(7):24-30.
[7] 段小虎,张梅,熊伟.重构图书馆空间的认知体系[J].图书与情报,2013(5):35-38.
[8] 张秀亚.张秀亚作品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9] 薇奇·麦仑,布赖特·维特.小猫杜威[M].马爱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0]李华伟.现代化图书馆管理[M].台北:三民书局,1996.
[11]让·马里·古勒莫.图书馆之恋[M].孙圣英,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2]黄继刚.爱德华·索雅和空间文化理论研究的新视野[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24-28.
[13]陆扬.分析索亚“第三空间”理论[J].天津社会科学,2005(2):32-37.
[14]谭其骧.值得怀念的三年图书馆生活[M]//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76-477.
[15]邓云乡.水流云在书话[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16]塔季扬娜·埃斯克特兰德.图书馆名言集[M].李恺,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17]于良芝.未完成的现代性: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J].图书馆杂志,2005(4):3-7,20.
[18]王寅.体验哲学探源[J].外国语文,2010(12):45-50.
[19]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M].邓正来,译.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
[20]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112-125.
[21]郭光旭.一只猫和图书馆——小猫杜威读后感[EB/OL].[2014-01-30].http://wenku.baidu.com/view/82e4ff fc04a1b0717f d5dd0e.html.
[22]戴维·芬克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M].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