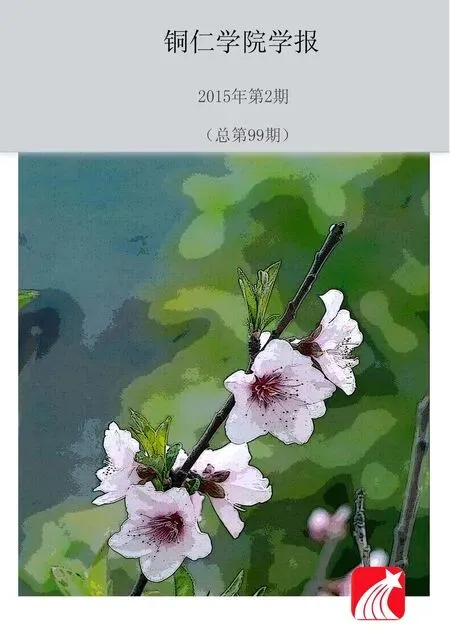瓦雷里与中国
2015-02-13曹文刚
曹文刚
(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
瓦雷里与中国
曹文刚
(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
瓦雷里与中国两个文学青年梁宗岱、盛成的相逢、对话、交流是双方在各自徘徊状态下的历史汇合:是西方对东方的召唤、选择,东方对西方的寻找、应和的时代回声。他们互为朋友和向导,在平等、友好、亲善的氛围中互为媒介互相引导,出于对中法文化交流的热情达到了共鸣,在心灵上达到了共识。瓦雷里通过盛成创作的《我的母亲》与现代中国对话。他以他的中国弟子为媒介,对中国文化作了广泛深刻的观照和思考。他批判欧洲中心论和欧洲由来已久的对中国的误解、轻视、偏见,认为西方人和中国人必须亲近共处、共生互补,不同的民族应亲近共处,为此要进行“心印而神会”的交流。
瓦雷里; 梁宗岱; 盛成; 诗哲; 中国文化
一、瓦雷里和他的中国弟子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大师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1871~1945)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诗人,在诗歌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同样有不凡的建树。20世纪20年代,诗哲瓦雷里与中国两个文学青年梁宗岱、盛成的相逢是历史的遇合,他们之间的对话、交流堪称中法文化和文学关系史上的佳话。在与梁宗岱、盛成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青年相遇时,瓦雷里已是西方文化名人,法国诗坛领袖,声名显赫。这位从年轻时就致力于“自我求证”的“内倾诗人”,在漫长的“纯我”的“精神操练”历程中,也难以超越20世纪20年代愈演愈烈的“东方的召唤”,他对中国人,这个生存在“天外的版舆”的族类,还是一无所知,他亟需了解中国,思考这个民族。正是在他面临这样一种精神困惑和文化选择的时刻,两个陌生的中国文学青年来到了他的面前,他们以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的思想风貌和精神追求引起了这位诗哲的注意,成为他关照中国、回应“东方的召唤”的重要的“媒介”。
1925年,梁宗岱这个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诗人来到了欧洲文化中心法国,开始在刊物上发表法文诗。1926年与瓦雷里相识,梁宗岱与这位哲学诗人成为莫逆之交。瓦雷里对梁宗岱翻译的王维、陶潜等人的诗歌大加赞赏。梁宗岱是瓦雷里所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通过他,瓦雷里真切地感到中国人是或曾经是最富于文学天性的民族。盛成是为了寻找救国之道,在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后来到西方的。其间,盛成在创作纪实小说《我的母亲》,他得知瓦雷里蒙受丧母之苦,便写信安慰:“你没有母亲的时候,你才来想爱你的母亲。你没有母亲的时候,你才了解你的母亲的慈爱……亲丧是万国的亲丧,心苦是人类的心苦。因此我以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来安慰翰林学士,因此我前来怜惜一个苦人。”[1]281瓦雷里接信后回了盛成一封信,不料这封信成了盛成人生的转机。靠着大诗人瓦雷里的推荐,盛成的《我的母亲》在巴黎出版,获得了巨大成功。
瓦雷里和他的中国弟子相逢,好像显得有些“偶然”,但绝不是命运的“巧合”,或“偶遇”,而是人性的汇通,是相遇的双方在各自“徘徊”状态下的历史“汇合”:是西方对东方的召唤、选择,东方对西方的寻找、应和的时代回声。历史与时代为西方导师和东方弟子的相逢创造了机遇,也为他们的交流、交往营造了适宜的氛围,这是一个平等、友好、亲善的氛围。这种平等氛围是由交往双方对异质文明的尊重和赞赏而确立起来的,是由导师对弟子的欣赏、弟子对导师的崇敬而建立的。瓦雷里留给弟子的印象是:“为人极温雅纯朴,和善可亲,谈话亦谆谆有度,娓娓动听”。[2]17
在梁宗岱之前,中国文学界对瓦雷里这位诗学王国的哲人的介绍可以说是一鳞半爪,而在他之后,瓦雷里在中国成为很多人谈论的对象,虽然对其的理解远远不及梁。在他之前,瓦雷里集诗人、哲人于一身的身份,令许多人对他的作品退避三舍。梁宗岱的出现让中国读者眼前为之一亮,他对瓦雷里《水仙辞》的翻译,以直译为主,不仅是一行一行地译,而且是一字一字地译,极力模仿原作的节奏用韵,再现了这部作品超逸高远的情、境、意。“哲学诗”是西方象征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滥情和矫情的反对,经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而由瓦雷里最终形成的。已有的哲学诗往往流于“无味的教训”,许多人担心理智混入艺术而怀疑象征主义哲学诗的价值,梁宗岱说:“梵乐希(瓦雷里)却不然。他象达文希之于绘画一般,在思想或概念未练成秾丽的色彩或影像之前,是用了极端的忍耐去守候,极敏捷的手腕去捕住那微妙而悠忽之顷的——在这灵幻的刹那顷,浑浊的池水给月光底银指点成溶溶的流晶:无情的哲学化作缱绻的诗魂”。[2]17-18
作为瓦雷里的朋友和向导,梁宗岱第一个将《水仙辞》原汁原味译介到中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他还写了有关瓦雷里的评传,这是中国较早的完整介绍瓦雷里的文章,他是在中国学者中第一个系统而深刻地研究象征主义特别是瓦雷里的玄学诗。同样,作为梁宗岱的朋友和向导,瓦雷里向法国读者首次推荐了梁译“陶潜诗选”,在梁处于徘徊观望和疑虑中的时候,瓦雷里及时给予梁以指导。他们互为媒介、互相引导,对中法文化交流的热情达到了共鸣,在心灵上达到了共识。梁宗岱和瓦雷里之间的密切交往,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梁宗岱把瓦雷里看作是法国象征主义的传人,他认为瓦雷里的诗歌创作已经达到了一个至高的境地。在梁宗岱的眼中,瓦雷里的诗歌如《海滨墓园》、《年轻的命运女神》应该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标准,代表了诗歌的最高境界。瓦雷里成为梁宗岱艺术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梁宗岱对瓦雷里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他高度认可瓦雷里有关主、客观关系的看法,他评述道:“我们对于心灵的认识愈透彻,愈能穷物理之变化,探造化之微;对于事物与现象的认识愈真切,愈深入,心灵也愈开朗,愈活跃,愈丰富,愈自由。”
[3]155瓦雷里的哲学思想对梁宗岱的文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梁的文学批评集《诗与真》的命名就出于这样的思想:“真是诗底唯一深固的始基,诗是真底最高与最终的实现。”[3]5在这里,艺术世界中“诗”与“真”的关系相当于哲学世界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梁宗岱以瓦雷里的诗学理论为参照,构建了自己的有关象征主义、纯诗以及诗歌形式等诗歌理论体系。
二、瓦雷里对中国文化的观照
瓦雷里与中国弟子的交流、对话,为各自了解、认识对方的文化提供了契机,他们成了对话双方互看、互识的对象,担当了无可取代的“异文化使者”。他们互为“媒介”,他们所承担的“文化使者”身份具备着一种双向性的态势:对瓦雷里而言,梁宗岱、盛成是中国文化的使者,对中国弟子而言,瓦雷里是法国文化使者。瓦雷里通过梁宗岱译介的《陶潜诗选》和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携手、交流,通过盛成创作的《我的母亲》与现代中国“母亲”对话,通过这部小说,他认识了中国人的勤劳、博爱、智慧与忍辱负重。他看到的是充满智慧、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中国,从而引出了这位诗哲对中国文化的观照和思考。
通过陶潜的译诗,瓦雷里认识到古代中国人的勇气、朴素、耐性、纯洁与渊博。他发现了中国田园诗人陶潜极端精巧、蕴藉的艺术风格和智性追求,将之与西方古典诗人维吉尔和拉·封丹进行比较,对陶诗的艺术美极为赞赏,在他看来,陶诗的朴素体现了中国智慧的魅力。瓦雷里一生所悉心探讨的“对称”,并非只有欧洲人才予以重视,也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追求。中国文明处处都表现出“对称”的特点,中国先哲时时都注重“对称”的追求,人们熟悉的就有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墨子的“爱人之身如己之身,爱人之家如己之家,爱人之国如己之国”,等等。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对称”例证更是俯拾皆是。瓦雷里在探讨“对称”问题时,也提到了《道德经》中“有无相生,长短相成”的这种“对称”形式。[4]120-121由此可见,“对称”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位置,在中国民族智慧中焕发出同样光彩。瓦雷里用自己的“精神求证”和科学探索证明了人类的精神智慧是相通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世纪的西方诗人瓦雷里能在中世纪中国诗人陶渊明的诗歌中找到共鸣。
紧接着,瓦雷里与盛成相遇,由其为媒介,与现代中国进行了思想和情感的交流,由此对中国文化作更广泛深刻的思考。瓦雷里为《我的母亲》作了一篇长序。他在序中指出加强西方与东方文化的交流是紧迫的大事,以公正态度质疑欧洲中心论和欧洲由来已久的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与埃及、犹太、希腊、罗马文化不同的,是独立的文化系统,但与西方共生共存。中国民族的文化个性复杂而矛盾,文化蕴涵丰富,变化快追求新的西方文化和长期稳定不变的中国文化各有各的长处,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彼此应该取长补短、相互尊重、平衡发展。中国人既有四大发明,何不利用来为自己带来实际的利益呢?既有很高的科学水平,为什么不能进步呢?他承袭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疑问,追问得更具体,思考得更深远。他以历史的目光回顾了“前进”的西方与“守旧”的中国的交往历程,进行深刻反思,指出,是“求快”“求变”的西方人敲开“不变”的中国大门,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觉醒将会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东西方将取得何种新的平衡?人类应怎样应对?瓦雷里没有停留在一般西方人“亚洲妖魔”或“黄色巨兽”的心存恐惧的层面,而是将自己的思考推向深入:相异的民族是应该相近的,西方人和中国人应该亲近共处、共生互补,他的思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不同的民族应如何亲近共处呢?瓦雷里接着往下追问。他认为要做到“心印而神会”的交流。他批评欧洲人只对中国的物品感兴趣,却轻视、蔑视中国人的精神、性情,中国民族的生活、生命,因为比物品、艺术杰作更宝贵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他的这个认识显然超过了他的前辈和同代人,达到了一种历史的深度。应该怎样看待西方的“进步”与东方的“传统”,及与此相关的东西方文明交流问题,是他终生求证的课题。诗人的思考富含历史的厚重感和现实感。在当今世界,天下仍不太平,动荡、战争、冲突时有发生,人类亲近共处的准则时时遭到践踏,诗人思考的分量便愈发凸显出来,诗人的忧虑和危机感并非多余。
[1] 盛成.瓦乃理[M]//盛成文集·纪实文学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2] 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3] 梁宗岱.诗与真[M]//梁宗岱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4] 梁佩贞.漫谈比较文学[M]//杨周翰,乐黛云,编.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Poet P. Valary and China
CAO Wenga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
Valary's meet,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wo Chinese literary young men is the historical confluence when they were all at the wandering state. It is the echo of times when the West summons and chooses to the East and the East seeks and responds to the West. Being friends to each other, they mutually acted as guide and medium in a equal, friendly and amiable atmosphere. They have reached consensus in spirit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ir enthusiasm to China-France communication of culture have achieved resonance. Valary talked to modern China through Shengcheng's work My Mother. With his disciples as media, Valary mad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culture. He criticized Europe-centralism and Europe's misunderstanding, despise and prejudice to China with the thought that the western people and the Chinese people must be close to each other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order to reach this purpose, people of different nations should live harmoniously and make smooth communication based o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Valary, Liang Zongdai, Sheng Cheng, Poem and Philosophy, Chinese Culture
I206.6
A
1673-9639 (2015) 02-0074-03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白俊骞)(英文编辑 韦琴红)
2014-09-09
本文系安徽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陈独秀翻译研究”(SK2013B452)研究成果。
曹文刚(1971-),男,安徽六安人,汉族,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