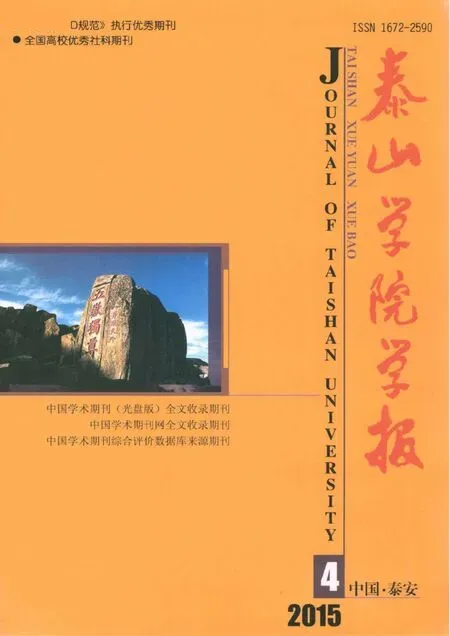论吕碧城的女性解放探索实践之路
2015-02-12宁宇
宁 宇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泰安 271021)
论吕碧城的女性解放探索实践之路
宁 宇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泰安 271021)
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与实践是女性解放真正得以实现的动力和前提,在这一过程中,吕碧城的女性解放实践之路值得关注。她连续发表文章,积极倡导女权和女学,具有明确的女性自主意识,并以自身的积极参与为中国女性探索了一条解放之路。同时,吕碧城的经历也说明中国的女性解放之路任重而道远。
吕碧城;女性解放
“1898年戊戌变法的革新之气对女界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国妇女民族意识、平等意识、自立意识及性别意识初步觉醒的起点。”[1]晚清男性学者出于保国、变革等需要呼吁女性解放虽在客观上促动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但并未真正从女性自身的诉求出发以贯彻和实践这些思想。如果女性自身在思想上不能回应这些意识,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现实中不能以行动加以实践,那么,女性解放只能是空谈和理想。女性自身的参与、实践是女性解放的动力,也是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重要条件和标志。在这一过程中,吕碧城以其观念和自身实践为中国女性探索了一条解放之路。
吕碧城(1883-1943),字遁天,号明因,后改作圣因,安徽旌德人。自幼受到了其时少有的良好教育。1904年成为《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从此,吕碧城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同年9月,袁世凯指令开办天津公立女学堂,吕碧城任总教习。两年后,在此基础上,创建北洋女师范学堂,这是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吕碧城任总教习(校长)。中年以后致力于“戒杀护生运动”,长年茹素吃斋,心中充满了禅意。1943年在香港孤独辞世。
一、思想观念的解放
在《大公报》期间,利用这个平台,吕碧城连续发表文章和诗词兴女权、倡导女子解放和宣传女子教育,显示出她对女性解放的认识和思考,引起了强烈反响,并结识了大批当时的妇女运动领袖人物。
吕碧城接受严复等人的影响,以西方“天赋人权”为武器,从国家利益和民族角度出发,提出兴女学、废缠足、女子团结等女权主张,产生深远的影响。吕碧城大力呼吁男女平等,并身体力行。在吕碧城加入《大公报》后写的一首词《满江红》[2]中,我们能感觉到她接触新思想、新事物之后的欣喜与激动,词中对罗兰夫人、贞德高唱女权的先觉者充满羡慕,似乎找到了争取自身和妇女解放的“曙光”,即来自西方的榜样力量。该词的下阙表达了在此之前她所承受的束缚——幽闭、羁绊,故而有井底之蛙的感叹。
在《敬告中国女同胞》中,吕碧城呼吁破除旧例,辟“好古遵圣、因循守旧”之积习,要用发展的眼光,以变通、进化、改革的意识追求女子的自立。“此吾率土同胞所当打破迷团,力图自立,拔出黑暗而登于光明。上以雪既往众女子之奇冤,下以造未来众女子之幸福,使之男女平等,无偏无颇。”[3]
从个人之权利而言,吕碧城在“天赋人权”的影响下,提出个人“完全自由之身”本应享有天所赋之权利,而中国几千年的现实却造成了“男子得享人类之权利,女子则否,只为男子之附庸,抑之、制之,为玩弄之具、为奴隶之用。”[2](P137)因此,她提倡要先树立个人独立之权,使其人“对于家不失为完全之个人,对于国不失为完全之国民”[3](P20)。
在争取女子独立的过程中,吕碧城也揭示了中国妇女所面临的现状。女子被剥夺了自主权,不能自由活动,足不出户,不许读书。中国女子甚至连奴隶都不如,奴隶一身尚可己有,而女子只有“仰面求人给衣食,幽闭深闺如囚犯而已。囚犯犹有开赦之日,此则老死无释放之期”。在此惨淡昏黑之地狱,最让人痛心的是女子自身不以为苦,相安而足,“哀莫大于心死,吾二万万同胞,诚可谓身未亡而心已死之人也。”
吕碧城提出,“顾世事非个人独立所能成者,是则合群之道宜急讲矣。”[3](P31)从合四百兆人为一大群的观念中,可以看出,她所提出的“合群”超越了同时代人所提出的结妇女团体之观念,希望激发女子个人之权利,进而与男子共同在竞争之世界发挥自己应有的才能。这是从爱国的层面提倡女权,而非“顽谬之鄙夫”所言“欲放荡驰跅”,也不是“欲其势力胜过男子”,其目的是使国人“合力以争于列强,合力以保全我四百兆之种族,合力以保全我二万里之疆土。使四百兆人无一非完全之人。”[2](P135)这样的认识也避免了将女性解放运动引向过激的倾向。
吕碧城还指出在传统顽固势力依然强大的中国提倡“男女平等”实为首创,虽然有舆论的宣传,但在实践上若不能坚持,众志成城,必会被顽固势力授以口实,进而对这一新生事物压制阻挠,希望人人尽一份自己的责任,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竭力为之;今日不成,明日为之;明日不成,后日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呼吁大家行动起来,“时不可失,海内同志,诸君子,其共勉之哉!”[3](P13)
在词的写作上,吕碧城有自己明确的创作意识,实质上体现其女性自有本色的观念,与上述的女权观念并无二致:
海通以来,女学尚矣,又以各种专科及蟹行文字瘏其精力兼谋经济独立,何暇专心著述,为名山事业哉?其结习难忘,余勇可嘉者,亦仅发为诗词歌咏而已。兹就词章论,世多訾女子之作大抵裁红刻绿,写怨言情,千篇一律,不脱闺人口吻者。予以为抒写性情本应各如其分,唯须推陈出新,不袭科臼,尤贵格律隽雅,情性真切即为佳作。诗中之温李、词中之周柳,皆以柔艳擅长,男子且然,况于女子写其本色,亦复何妨?若言语必系苍生,思想不离廓庙,出于男子,且病矫揉,讵转于闺人,为得体乎?女人爱美而富情感,性秉坤灵,亦何羡乎阳德?若深自讳匿,是自卑抑而耻辱女性也。古今中外不乏弃笄而弁以男装自豪者,使此辈而为诗词,必不能写性情之真,可断言矣。[2](P196)
在这段话中,透露了几种信息:一,尽管女学有一定的发展,妇女也获得了一定的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在妇女解放实践中,妇女既要借学习专科技能以获得经济独立进而自身独立的能力,若还要应付来自家庭婚姻的种种问题,势必没有时间和闲暇从事创作。二,世人对女子创作多有成见,吕碧城认为女性以本色便能赢得创作的一席天地,“抒写性情本应各如其分”,推陈出新,格律隽雅,情形真切就是佳作,并非一定要抑制女性自身的特性。三,古今中外有喜欢女扮男装者,以此心态来创作诗词,会失掉性情之真。她拒绝性格和心灵的“换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决定了她和秋瑾等时代女性不但在行为方式、创作方面,而且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秋瑾变卖家产以促进女权运动,而吕碧城的倡导女权有其内心意愿的展现,也有出于维持生计的因素。
有论者说吕碧城是一种被迫的女性独立、进而需要经济独立,决定了她没有成为一个彻底的女性主义者[4],有一定的道理。更重要的是在其思想观念上,她所说的平等自由,是指女性具有“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的权利,而“非欲其势力胜过男子。”[2](P135)“其志固在与全球争也,非与同族同室之男子争也”,[2](P136)从国家层面指出女性权利与男性权利同样重要,提出“女子为国民之母,对国家有传种改良之义务”[3](P28),这是维新人士观念的继承,但她将女性放在一个和男性共同合成完整之人的层面上加以论证,认为争取女性权利的平等有益于社会国家。
女权运动的兴起,恰恰证明了社会上男女观念的不平等,吕碧城认为办女学开女智、兴女权才是国家自强之道的根本。
二、吕碧城对女性解放的探索与实践
“兴女学”思潮的讨论在男性学者那里主要表现为贤妻良母主义、女国民和男女平等等内容,而女性自身更多地将女性受教育权推进到塑造女性健全人格等方面,进而探讨女性如何受到教育等问题,完成了由“女性性别”教育到“人”的教育观念的转变。
吕碧城不仅积极倡导女学,还身体力行地加以实践。在1904年天津公立女学堂的发展中,吕碧城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自己担任国文教习,并发表多篇言论以作舆论宣传,如《教育为立国之本》、《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保姆讲习所演说稿》、《论某幼稚园公文》、《女界近况杂谈》等,宣扬兴办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把兴女学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以此冲击沿袭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在筹办过程中极大地坚持了自己的主张和观念,显示出强烈的个性。对于教育,吕碧城基于实践层面得出清晰的认识,“教育者,贵能矫正其偏诐之性情,而发扬其固有之美德,复授以各种学术”,[3](P24)确切中肯,现代教育中,“育人”也是归宿和目的。而女子教育尤其需要提倡,因为几千年的旧习俗导致女子受到种种束缚,从国家、自身的角度指出兴女学是必要的,可以开启女子的智慧。
关于女子教育,尽管她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新式教育,但却提出了完善的教育思想。她在《大公报》发表了《论中国当以遍兴蒙学女学为先务》,“故有贤女而后有贤母,有贤母而后有贤子,古之魁儒俊彦受赐于母教。”认为应该从儿学蒙学就抓起,而不是先设立中学、大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兴办学校的问题所在。
在《兴女学议》中,她首先揭示中国女界之现状:“其思想之锢蔽,器量之狭隘,才力之短绌,行为之贪鄙”,笔端犀利。康同薇也认识到封建社会那些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女子,或以文词自娱其乐,或以才藻自矜,带有特有的守旧性,学无所用。而吕碧城则全面剖析传统女性自身的弱点,这是数千年政教风俗所致,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先铲除种种劣点。
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因为有实际的办学经验和实践,吕碧城指出,“就事体论,则管理者校长之责也,教授者教师之职也,然而教授之兴管理,固互相联络不可须臾离者,则教师之与校长,固同兼训练管理之职矣。”[3](P20-21)校长和教师只有共同协调,承担管理教育之职,才能更好地促进学校的发展。确为的见。
在学校的规章制度方面,吕碧城提出应循序渐进地让学生接受法律意识和规范,尤其是培养社会公德心,使学生具有遵纪守法意识。考虑到实际情况,应循序渐进,讲法者要从自身做起,以榜样的力量加以正确引导,从而形成遵守法律之风气。从这些细致的规定和考虑上,我们看到了女子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
在教师的选聘上,吕碧城提出“品性纯正”是根本,这一条件在今天选聘教师时依然值得遵守。她还指出在目前中国的现状,姑且用女教师,但符合条件的人数很少,如果风气已开之处,还是用男教师为宜。而在学生资格上,她认为“以身体健全,年龄少小为合格”。
吕碧城还重视学生德育、智育和体育的全面发展,使学生提高自身的修养,以树立自立自养的观念。在这里,吕碧城将兴女学与女权结合起来,注重培养学生的经济自立观念和能力。发扬女学生的自身优点美德,培养国家思想。她充分肯定我国女子具有“挺然独立之资”,“受数千年足不出户之束缚,一日开禁则以孑然弱质游学于数万里之外者,踵相接,非富于独立之性曷能臻此?”在这里,有对秋瑾等留学生的肯定。
在学校课程设置上涉及蒙学、普通、专门等三个方面,包括算数、历史、国文、美术等课程,对各科特点都有具体的要求。对教学环境、饮食、宿舍也有具体细致的要求,体现了作为女性在教学管理实践层面的细心和周到。在《兴女学议》的结论中,她提出了自己的教育设想,在兴女学的基础上,设立师范,以解决师资缺乏的问题,从而最终能达到女子教育的真正普及,在实践层面部分实现了这一构想。
吕碧城的女子教育思想超越了维新派富国强兵、保国保种的套路,也不同于革命派借兴办女性来实现政治变革的企图,真正站在人权、女权的角度,把塑造新女性、完善女性人格作为最终目的,对于实现女性真正解放,具有积极意义。尽管这个思想没有完全付诸实践,但摆脱了长期以来束缚女子教育发展的政治框架,摆脱了将女性解放工具化的倾向。
对于女学的发展和走向,吕碧城有自己的认识,她认为女学的发展须规范。从现实来看,“官府兴学之宗旨与国民教育主义相反对”[3](P14),在女学中也确为事实,吕碧城主张设立一机关,以起稽查、监督之作用。她还提出将报纸和女学结合起来,吕碧城以她自身对报纸等媒体的参与和了解,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个新生事物的兴起如女学,势必要通过媒体让广大民众知悉其中的详情,并借以消弭反对者的声音。她提出“今宜创一女学丛报,月出二册,专讲女学……学堂之优劣,学课之高下,学制之变更,亦潜心探访。随时登录,褒之贬之。”这是她鉴于以往女界之杂志不是专门讲女学,建议女学与女学丛报二者应互相促进,互为依存。当然,这只是吕碧城的设想,因为经济和其他的因素,并不能如维新派家眷等真正付诸实践,但依然表现出其识见。她还提出设立女学调查会,因为女学初创之际,缺乏实践经验,调查会可以起到互通有无,互相联络之作用,促进女学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吕碧城还有创办女子教育会的设想,该会以“联络同研究女子教育期于女学之发达”为宗旨,分研究部、调查部、编译部和建设部,是在上述女报、调查会的基础上研讨有关女子教育思想,只是未能变成现实。
吕碧城还有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宏愿,“(程白葭)谓曾向当局建议在奉天办一大学,招考中外大学文科毕业而有国学根柢之人,优给膏火,教授有系统之国学并予备低级之学科待东西洋人来学,毕业后介绍至各国大学为汉学讲师,俾发扬东方文明,导全世界人类入于礼让之域”,“此议实获我心。盖东化西渐已有动机,各国大学多添设汉学讲科”。[2](P195)在西学东渐之风盛行之时,吕提出“东化西渐”,可见志向宏伟。在她的许多文章中,也谈到怎样建立一个强国的想法。她认为在这竞争的世界,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强国就必须四万万人合力,因此不能忽视二万万女子的力量。解放妇女,男女平权是国之强盛的唯一办法。她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世人,济世救民。
吕碧城不仅发表了不少文章从理论层面对女权和教育等问题进行探讨,更重要的是以自身的实践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
在20岁之前,吕碧城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方式和知识,但吕碧城的生平经历中有许多因素导致她产生女性意识,如家中无子,自然在幼年的成长过程中缺少“男尊女卑”观念的亲身感受,这一点和父母的开明教育密切相关。亲族在其父亲去世后争夺遗产,甚至绑架母亲,而吕碧城给父亲的学生、朋友求援,显示了善于开动脑筋和社会打交道的潜在能力。幼年“众叛亲离,骨肉齮龁,伦常惨变,而时世环境尤多拂逆”[5]的曲折经历,就因父亲没有儿子,即使女儿再优秀也无继承权,族侄比她更理直气壮地享有继承权,使她萌生女性独立意识,并倍加珍惜自身获得的独立。与舅舅的决裂一方面显示其个体意识强烈,非一般女性能比,另一方面也让她走上独立自主之路,也坚定了她认为女性须在经济上独立的意识。出游欧美是基于优裕的经济条件,而她的商业才能也非常突出。
吕氏四姐妹都从事女子教育,其中三人任女子师范校长。吕湘任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吕美荪任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吕碧城任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四妹吕坤秀任厦门女子师范学校教师。这样的经历本应该在姐妹中形成共同探讨交流的气氛,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吕碧城并没有和她们往来的文字记录。或许姐妹之间也有竞争,互比高低。在王忠和的《吕碧城传》中,说到了吕碧城在《大公报》期间,大姐和吕美荪也曾到天津,得到英敛之的赞赏,英敛之还编印《吕氏三姊妹集》,姐妹筹办北洋公学,但关系逐渐交恶。在《予之宗教观》中,吕碧城有言:“予于家庭锱铢未取,父母遗产且完全奉让(予无兄弟,诸姐已嫁,予应承受遗产),可告无罪于亲属矣。”[5]其中透露了一些消息,“予应承受遗产”自然是吕碧城接受新观念之后产生的思想,而宣称“锱铢未取”,之前必有一番试图承受遗产的努力,或许导致姐妹交恶,众叛亲离。在王忠和的《吕碧城传》中也有较为细致的分析。在塘沽舅舅家寄人篱下六年,她大姐嫁给舅舅之子严象贤,也住在塘沽,姐妹间应有照应,但在吕碧城以后的文字记录中无只言片语提及,也值得猜疑[6]。其实,更多的应该是源于吕碧城强烈的个性,在多篇研究吕碧城的文章中,以“特立独行”来形容她,她的老师严复也说:“碧城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
同时,吕碧城的经历中也有一些因素影响了她以后的生活。汪家和她解除婚约,让她看到世态人心,也为她以后的情感生活留下阴影。以她的个性,在受到如此打击之后,未必没有心里的想法。严复说:“吾常劝其不必用功,早觅佳对,渠意深不谓然,大有立志不嫁以终其身之意,诚可叹也”。世上男子,只有梁启超、汪精卫等能入她的眼,可惜都已婚或年龄偏大偏小。在《大公报》期间,亲眼目睹了周围众多妇女的婚姻不幸,也会加深她对婚姻的恐惧。她在以后的生活中始终谨慎、忧虑地对待感情,蹉跎中失掉或者是自己放掉了机会,逐渐坚定独身的念头,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有人曾分析吕碧城的择偶标准为当时的名人或才华,在重视才华方面其实和秋瑾有共同之处:“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7]。若吕、秋二人确能如愿,可能人生际遇会如吴芝瑛那样,同样精彩而会少些凄苦。
1904年吕碧城想到天津探访女学,被舅舅骂,“予忿甚,决与脱离”,第二天只身离开舅舅家,在去往天津的火车上,有幸熟识了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到天津后,暂住其家中。她后来也反思,当时“年幼气盛,铤而走险”[7](P480)。我们从文字中能想见当年她离开舅舅家的决绝,而她在离开之前当和母亲有过交待或保证,在《横滨梦影录》中有证:她在1922年春天与一位“仪止楚楚”的日本少年邂逅,“彼出其名刺授予,加注地址,谆以别后通讯为请。”“予等兴辞,诸美妇中唯一年长者与少年握手为礼,余皆避之。予仅颔首,亦即迅步趋廊外。少年则急引手穿槛花(时槛上遍置盆花),招予曰:‘此别未必重逢,请一握为幸。’余从之。”但渡海后,她将名刺投到海中。其后两年忽然梦到“与家族聚处如旧时,篝灯闲话,其乐融融”,大概心中也是思念家人的罢。“忽一僮款扉投以名刺,视之,则横滨所邂逅者。方诧愕间,僮复扛一巨簏入,曰:‘此某君所遣也,请验收。’”因为之前曾交谈过吕碧城肄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美术,所寄来的竹箱里装满了美术用品。“吾母顿严霜幕面,怫然曰:‘不肖儿!予纵汝游学,竟滥交若此友及木屐儿耶!’予欲辩而格格莫致一词。家人环视,虽不明加指斥,但或努其唇,或嗤以鼻,鄙夷之情有甚于语言者。吾母检点各物,一一掷之于地,一物一詈而不或爽。予惶愧无以自明。”至此我们就能理解吕碧城的放弃和拒绝,作为一位要强的妇女,吕碧城在离开舅舅家时也应该有所表示的,这段透露了她对婚姻审慎态度的隐衷。母亲在孤儿寡女无所依托的情况下,也应该在顶着巨大的压力下支持她们姐妹的自立、游学,吕碧城的二姐吕美荪在一首诗《送崐秀四妹由天津南归》中,提到“慈亲有训勉自立,委身女学奔风尘。负米各走千里外,生女庶不羞乡邻。”说出了母亲长远的眼光和所忍受的压力,她们姐妹也确实很有志气,各有所成。吕碧城在心中会时时以自己的保证或承诺来要求自己,但内心的欲望无法压抑,终究会有所显现的。
在《游庐琐记》中,曾邂逅一位名叫“威尔思”的德国人,两人是有共同的话题的,一路以英语交谈,他还将一束花相赠。几天后,吕碧城与前来拜访的威尔思在门前相遇,两人同赏落日。后来威尔思再邀吕碧城一同出游,却被她谢绝。“向晚,天气沉霾,亦犹予意之不适。未进晚膳,颓然就寝。”可见,吕碧城的拒绝也是压抑了自己的内心欲望的。在游三叠泉时,就佛堂假寐,她做了一梦:“一西人面白皙微有短髯,因兵败国破愤而自戕,由巨石跃下,头颅直抵于地,有声砰然即委身不动,盖已晕矣。须臾勉自起立,予视其颅凹陷,盖骨已内碎而皮肤未破,予知其已无生理,钦其为殉国烈士也,乘其一息尚存之际,遽前与握手为礼。其人精神立焕,且久立不仆。予讶之,因问曰:‘汝将何如者?’意盖谓生乎死乎。其人答曰:‘我为汝忍死须臾。’言甫竟,血从颅顶泛出,鲜如渥丹。”梦境以突兀的方式泄露了吕碧城的内心世界,她的怅惘、欲望也因此得以宣泄。
不仅对婚姻世事非常审慎,在日常生活中,吕碧城也是在生平无多依靠的经历中学会了保护自己,在《建尼瓦湖之荡舟》中,写她向往能坐一瓜皮小艇,优游于湖光山色之中,一日午后沿堤散步,一少年邀请她,便登舟而去。后来又说:“然予此行极为谬妄,愿读吾此记者切勿效尤。盖予为孤客,不唯人地生疏,且不谙方言,不善摇桨,乃随陌路之人舍陆登舟以去,不啻以生命付彼掌握,其不遇险者侥幸耳。”[2](P171)
吕碧城虽然洋装打扮,但骨子里依然还是传统的。有人评价吕碧城反对白话文,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为现代文学遗憾。现在看来,处于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她在一些方面的坚持未必没有道理,人们是无法完全割断历史的,“五四”的激进所造成的古今文化的断裂值得人们思考。
事实上,当妇女自身意识开始觉醒,并在行动上有所实践之时,思想进步的男性学者赞许男女平等,要求不缠足、有知识,更大意义上想让配偶跟上自己的思想发展,能够更深层地理解自己,但男性的择偶标准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并不希望与特立独行的妇女共走一生。所以,男性尽管敬重、钦佩吕碧城,甚至愿意和她交往,寻找红颜知己的感觉,但并不意味着她的婚姻有可能,“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焉。”[7](P480)由此可见,社会思想的解放带给婚姻家庭的影响是缓慢的,大多数呼吁并参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女子在其时找不到合适的出路。
吕碧城是女权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率先走上社会独立谋生的先驱者”[8]。她不仅热衷于公众活动,还针对当时中国女子的现状提出解决办法,动用一切宣传手段倡导女权,对女子进行思想启蒙;积极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女子受教育的程度,提供其自强自立的基础,并争取以靓丽的形象在国外展示中国女性的魅力,“执着于女性特征而立足于社会、成就于社会”[9],从而以思想观念的先进和前瞻性为当时的女子设计了一条争取自身解放、追求独立的人生道路。
与秋瑾相比,吕碧城对妇女解放运动显得温和、从容,也更理性,上面所论到她所坚持的男女平等已有明显表现。1904年5月,秋瑾与吕碧城曾有交往。秋瑾劝吕碧城同去日本,投身革命运动,但吕更倾向于以改良的方式变革现实。她没有接受秋瑾的提议,而是答应用“文字之役”,与秋瑾遥相呼应。1907年春,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其发刊词中有出于吕碧城之手的。同年秋瑾在绍兴就义。吕碧城与秋瑾的交往引起官方注意,险些被抓。自此,吕碧城收敛许多,严复说她“自秋瑾被害后,亦为惊弓之鸟矣。”
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因为有女性自身的参与,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发展。而吕碧城的经历也说明妇女解放运动的艰难曲折以及行进中女子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1]常彬.从婉约闺阁到鉴侠革命:秋瑾诗文与早期女性自觉[J].河北学刊,2006(6):132-136.
[2]刘纳.吕碧城[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49.
[3]戴建兵.吕碧城文选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9.
[4]胡凤,等.中国近代新女性构建中的悖论——以吕碧城为个案研究[J].大连大学学报,2007(2):77-80.
[5]李保民.吕碧城诗文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81.
[6]王忠和.吕碧城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17-18.
[7]秋瑾.秋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6.
[8]王慧敏.一枝彤管挟风霜,独立裙钗百兆中——试论南社作家吕碧城女性独立意识的意义[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88-92.
[9]李奇志.吕碧城其人其文的“英雌”精神追求[J].湖北社会科学,2008(11):111-113.
(责任编辑 闵 军)
On Lv Bi-cheng's Female Liberating Practice
Ning Y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Taishan University, Taian 271021, China)
Female 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e was the dynamic and premise of female liberation. Lv Bi-cheng continued proposing that focus should be paid to woman's development of liberation, actively proposing female rights and studies, and setting an example of herself to took participation for Chinese female probing lib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Lv's experience explained that the road of Chinese female liberation was difficult and had a long way to go.
LV Bi-cheng;Female liberation
2015-05-22
宁 宇(1975-),女,河北邢台人,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
D440
A
1672-2590(2015)04-009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