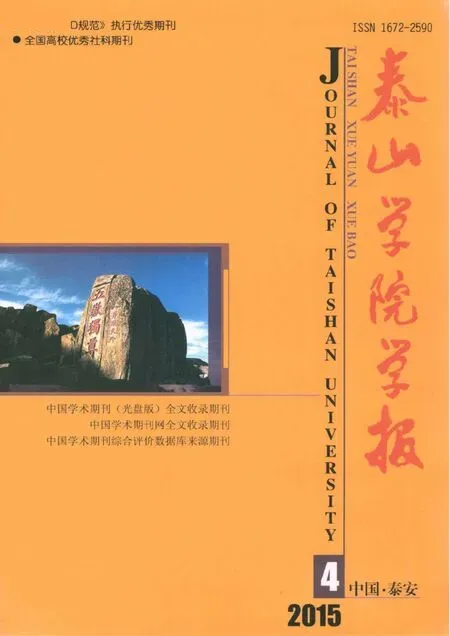乡献证史论风流
——《金代泰山文士研究》述评
2015-02-12李志刚
李 志 刚
(泰山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乡献证史论风流
——《金代泰山文士研究》述评
李 志 刚
(泰山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史学研究若要别开生面、创造新的学术增长点,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的运用必不可少。学者周郢曾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陈寅恪“诗文证史”基础上提出“乡献证史”,即是该领域有益的尝试。以方志、谱牒、金石刻辞、档案文书、乡邦诗文等地方性文献为“立足境”,介入重大论题研究热点与学术前沿,解决学术界存留的疑点与难点,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甚至有学者认为,“地方性材料的记载,起到的并不仅仅是拾遗补缺的作用,有时候甚至会动摇既有的历史记忆,让历史画面面目全非。”[1](P6)“乡献证史”与传统局限于一州一府一县的方志研究相比,所用材料虽有相似之处,但因眼界的拓展与最终期待解决的问题有异,实属重大进步。一是为“大文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地方性史料,在史料拓展方面功不可没;二是为传统大文史研究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就这点来看,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尓兹名著《地方性知识》及国内方兴未艾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念、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最近泰山学院聂立申副教授出版了《金代泰山文士研究》一书,该书以历代文献,尤其是泰山文献及地方碑志为根基,介入金代人物史研究的大话题中,以“金代泰山文士”群体为研究对象,既有群体共相论述,又有个案专题阐发,不仅是地方文史研究的楷模,更是“乡献证史论风流”的重大体现。
聂立申先生耕耘于泰山名士研究已有十余年,2012年就以党怀英为个案,出版专著《金代名士党怀英研究》。《金代泰山文士研究》是作者在党怀英个案研究基础上补充深化,进而扩大到整个金代泰山文士群体研究的最新成果。
这部著作共分为十章。第一章主要说明本项研究的缘由、现状、史料与研究方法等基础性问题,作者带着终金一代,泰山及周边地区为什么能够涌现众多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影响重大文士的问题意识,展开讨论。可以说,这一问题贯穿于整部著作,后设章节均为解决此问题而展开。研究形式上,为兼顾科学严谨与可读性,作者定位于纯学术与科学普及的中间状态。这在学术专著汗牛充栋,而读者乏人,科学普及粗制滥造,圈钱捞钱的恶劣出版环境下,不失为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集中在金代泰山文士的溯源,作者根据文士的出仕途径差异,把泰山文士分成被动入金型、主动入金型和自育自主型;根据出生籍贯或活动轨迹区域,又分为三类:即崛起于泰山本地的本地型文士、生于泰山周边区域而闻名于金的周边型文士、因任职隐居游历于泰安的活动型文士。从类型学的角度,分析文士群体的特色,正是作者对“系统性”追求的体现。
作者从时间角度论述金代泰山文士的发展变迁脉络,从空间角度论述泰山文士的地域特色。时间维度上,金代泰山文士的发展经过奠基期、崛起期、中间期、低谷期。作者并没有单就文人论文人,而是把文人作为一个集团,纳入金代的世运及政治、军事、文化盛衰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时代的盛衰直接影响塑造文人的气质,例如作者论道:处于奠基期的泰山文士,因宋末金初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曲折坎坷的人生遭际,多半具有心怀故土、怀念宗邦的凄苦之风;到了金世宗时期,金朝步入稳定的盛世,泰山文士则逐渐脱离凄苦之风,代之以追求闲情逸致的“乾坤清气。”(第56页)诸如此例的论述,显示出文士政治态度的认可、总体性格的塑造,甚至审美情趣的选择,无不与世运盛衰相配。作者在这一章中也特别标举出“金代泰山文士集团”五个地域性特点及形成的原因。作者通过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论述泰山文士的形成及其演变,一廓以往的迷雾,清晰地展示出泰山文士群体的总体面貌及演变规律。金代作为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虽在初期因军事斗争,宋人南迁,造成人才的短期流失,但当社会逐渐稳定后,泰山的地域人文景观形成,拥有共同特色的文士人才也大量涌现。政治意识形态干扰减弱,是否也显示出某些人才生成的规律?这是作者的论述给予我们的启示。
第四、五、六章作者进一步讨论泰山文士日常生活、社会交流以及价值取向。特别是在第六章中,作者通过长时段的思考,认为金代泰山文士性格的形成远距离的影响来自于宋初三先生与泰山书院,突出了文化教育对泰山文士出现的影响。
清代学者阮元曾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2](P1)“十万读书声”造就的人才,形成特色地域文化景观与风俗习惯,必须要从更远更长的“东鲁遗风”中才能找到根据与源头。
第七章、第八章是党怀英、赵沨的个案研究,研究风格与《金代名士党怀英研究》一脉相承。但是从编排上来看,或与第九章“金代泰山文士的特点与儒家风格”、第十章“金代泰山文士的历史地位”互换位置,会更好。最后两章的综合研究与前六章的风格更为接近。若前八章综合论述泰山文士,最后两章个案研究,体系井然,开合得当。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见,所谓编排究属小道,无关宏旨。
中国有“知人论世”的历史传统,《孟子·万章下》就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赵岐注:“读其书,犹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论其世以别之也。”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对照西方史学传统认为西方历史学重视事件,而中国史学重视人。[4](P316)可见,对人的重视,以及通过研究人而论其时运人心是中国史学的悠久传统。《金代泰山文士研究》基于金代泰山地区一个个文士的个案研究,再把零散的文士综合成一个文士群体,进而通过对文士群体的生活状态、文化追求、政治认同、思想情感、历史渊源等的整体研究,观照金代二百多年的世运盛衰。在“知其人而论其世”的道路上,埋头前进。正因如此,本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为乡邦论史,作者带有饱满的激情。在本书的前言与后记及正文中,作者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生活在泰山脚下,为乡邦论史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如《后记》中说:“也许是生活在全国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泰安;也许是工作在名为泰山学院的高校的缘故,像命中注定似的,我对泰山文化始终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特殊热爱和探索欲望。”历史研究近代以来努力追求客观,最忌作者情感的过度渗入,但历史学家并非无情感之人,在不影响真相的前提下,作者情感的适度参与,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如陈寅恪用《柳如是别传》煌煌大著不颂武装颂红妆,常常“感泣不能自已”。本书虽杂有乡邦情感,但未达到影响客观真相的程度;正因此种自豪感、责任感的参与,使作者在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尚能通过一二史料排列,铺延成文。
第二,材料的收集已达到竭泽而渔的程度。中国历史材料丰富程度虽举世无双,但分布极度不均匀。印刷术发明前,现存材料非常有限,致有学者发出唐前无书可读,或书已读尽之叹;宋后印刷技术的运用,典籍汗牛充栋,但又因正统意识、华夏中心等观念的影响,有关辽、金、夏、元的史料常有“文献不足证”之感。作为一个存在一百多年的王朝,金留下的典籍屈指可数,这造成了金史研究的天然困难。然该书对碑文、石刻、诗歌材料的挖掘与利用,以与正史、文集、地志常规材料的互为印证方面的比较研究,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在有限的材料中爬罗剔抉,辑出丰富的史料,也作了大量的统计。翻看本书一个重要的印象就是表格图示众多。如《金代泰山文士概况表》把110个文士的姓名、生卒年、简介、籍贯、职官非常直观明了的方式展示在读者面前。
第三,考证精细、详略得当。考据之学必依据于材料的精实与丰富,但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通过逻辑推演,往往更是精彩丰呈。如关于赵沨生年的考据,作者先据赵沨《元日》出现“劳生已强半,更欲沾清流”推断出两个结论:一是“劳生已强半”说明赵沨已过50岁;二是“更欲沾清流”说明赵沨尚未进入翰林院的清流工作,又根据《金史·赵沨传》得知赵沨在金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年)才经党怀英等人进入翰林,后作者综合断定《元日》诗必写于入翰林前的大定二十六年或二十七年,结合“已强半”,推断出赵沨生于天会十四年或十五年。
仅一项证据是不够的,作者再根据赵沨撰写的《王榆山先生墓表》“赵沨自念与先生为友三十年,其志向相同,忍以不文为辞哉?”通过确定的王榆山卒日与“为友三十年”再倒推,得出赵沨生于天会十四年的说法是正确的,且与《元日》诗相符,最后作者还利用党怀英撰写《醇德王先生墓表》中相关信息进一步确定天会十四年的说法,整个逻辑推演思路非常明晰。当然最后结果是否一定是天会十四年,也存在其他可能性,这并非因作者的思维或逻辑有误,而是因古人的数字记载方式往往比较笼统模糊。所谓“强半”“三十年”,我们很难能确指“五十”或“三十”,当然在未有更新更好史料出现之前,赵沨生于天会十四年左右,不失为最好的一种说法。
第四,议论有节、振聋发聩。作者把泰山文士的价值观分为救世经世型、存身求生型、守志宏道型。并认为金朝统治时期,大量泰山文人加入金朝政坛,并成为官僚队伍的主体,拥有较为强大的政治权力,逐渐演变为官僚地主,从而形成了士人——官僚——地主的循环圈。此后通过家学、官学培养自己的子弟读书入仕,保持和扩大在朝廷的政治、经济权益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第122页)此番议论在宏观角度上,较为深刻地揭示金代文士的演变规律,生动地指出所谓的文士集团的自我塑造,自我繁衍的能力,以及这背后的思想政治经济原因。
本书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大量的思想文化问题,提出了许多精彩的分析和结论,但也有少数地方不免令人心生疑窦,或虽精彩但不“解渴”,有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另本书内容的编排方面某些地方有重复之嫌,如第二章“金代泰山文士溯源”第一节讨论泰山文士的界定、范围构成,与第二节“泰山文士溯源与概况”中的“泰山文士溯源”,在内容上稍显重复拖延。当然这里有作者行文追求详实为先的定位有关,我们在这里仅是责贤求全而已。
通过作者的议论,我们能够看到金代泰山文士集团的基本价值取向,但也有问题书中未有详加讨论,但属题中之义。泰山文士的救世经世型、存身求生型、守志宏道型,是否存在时间上的变异?金代初期,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中竭力辩解父亲仕于金朝的事实,可以看出金初泰山文士有以忠于宋为荣,仕于金为耻的价值判断;但同样是汉族士人,金朝末年的路铎、周驰,均不肯降元而均赴井而尽。忠诚与背叛,光荣与梦想,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泰山文士在一百多年中,之于宋、金、元的忠诚与背叛的曲折心路历程,甚为可叹。这种曲折的心路历程,是如何实现的,令人深思。因为在清初与清末,历史似乎有所重复,张煌言、钱肃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反清复明,梁济、王国维、郑孝胥的忠清,均是以生命为筹码的大付出。揭示金代汉族士人的心路变化,或许可为后世历史的认识提供假借。是此以期望于作者能有更新更好的论著出现,解人以“饥渴”,释疑论道。
十余年的师生交往,我始终坚信先生在此领域研究的执着与追求,亦充分相信作者会在文献收集、历史议论、文章布局以及研究方法、视野等方面,做出更大的成绩。
[1]陈金华,孙英刚.神圣空间:中国宗教中的空间因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2]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3]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4]汪中.释三九[A].新编汪中文集[M].扬州:广陵书社,2005.
(责任编辑 梅焕钧)
2015-06-17
李志刚(1983-),男,湖北崇阳人,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史学博士。
G236
A
1672-2590(2015)04-014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