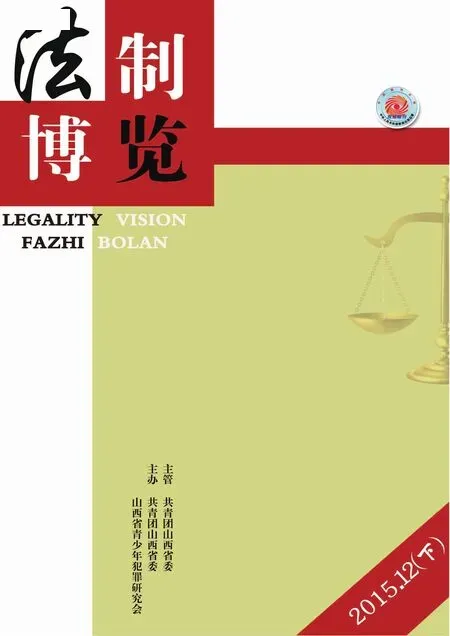电影与法律:以影片《偷自行车的人》为例
2015-02-07朱小兵
朱小兵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1
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拍摄,以二战结束后的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罗马为背景,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之作。故事的主人公里奇,和大多数人一样,一直处于失业的状态。等了两年后,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张贴海报的工作,但前提是他必须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影片通过里奇买车,丢车,找车,偷车的过程,深刻的反应了劫难之后的民生凋敝和社会现实,反映了小人物的命运遭遇,是一部社会伦理剧。
一、里奇代表的底层人物的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指介于感性和理性阶段之间的一种特有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既包括人们对法律的零散的、偶然的、感性的认识;也包括一些系统的、必然的、理性的认识。法律意识的内容包括法律认知,法律态度,法律价值,法律思维等。
里奇具有朴素的法律意识。他知道偷盗这样的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所以他期望自己既没有被偷,更不想去偷别人。他期望自己的车没有真丢,说不准在哪里就找回来了。所以,在他的车找不到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巫婆”,——里奇的妻子玛丽亚非常的信任她。在拮据的时候还给她50美元算卦,并且天真的以为离奇的工作真的是她带来的——并且带着儿子到了那,而“巫婆”只说了句“要是眼前找不到就永远也找不到了”。影片中,我们看到找“巫婆”的人很多,屋外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不光是里奇父子,很多人都在那里排队等“巫婆”给自己看看“命相”,这就反应了战争后包括罗马等城市中人民在精神上的空虚和价值观的迷茫,人们不得不借助这样的“巫婆”来消除心中的恐怖,惊慌,和无助。
接着里奇就去警察局报案。但警察是没有心情帮一个海报张贴工去寻找他丢失的自行车的。里奇又去找自己的朋友,但朋友们在装模作样的找了一阵后也都撒手不管了。执着的里奇带着布鲁诺在偌大的罗马城不知疲倦的寻找,结果找到自己的车了,可是因为偷车的人也是一个穷鬼,找到贼也无法要回自己的车。在穷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之后,他动了恶念。他内心里也追求真善美,拒绝道德的瑕疵。所以偷车前,他先让儿子离开。他抵触盗窃,但是现实令他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车对他来说,意味着工作,意味着生存,他不能没有这辆车。
影片通过里奇失业,得到工作,丢车,找车,偷车的诸多情结,深刻的反应了当时的那个时代的凋敝民生,也让我们感受到小人物的悲惨和心酸。是社会环境使人的生活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很多时候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就像里奇,他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应当被谴责和惩罚的人。法律意识不可能脱离生活现实凭空形成,它需要物质的保证。导致影片中里奇陷入窘迫和崩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实实在在的贫穷。贫穷是一座大山,压在穷人的肩膀上。贫穷制约并决定了法律意识。特别是像里奇这样的底层人物,不得不为生存耗尽一生,并不断被命运牵制。影片揭露了这样一个社会悖论:逃离贫穷却被现实拖入更深的贫穷。
二、电影与法律的分歧
电影与法律的分歧,主要体现为情与理的冲突。为了生存而生存,影片真实的展现了背负生存重担的小人物生活中的“无可奈何”。电影的天平是倒在对底层人物的情感关怀这边,倾向的是不合法行为中的合情合理的情感选择。作为观众的我们,在心里上也是接受并同情里奇的。可以设想,在本片中偷盗自行车只是违法,即使因为剧情需要假设里奇犯罪,或许我们还是可以同情他的,因为“即使罪不可赦,也情有可原”。正如阿图尔·考夫曼所言“宽容特别是要给予那些生存受威胁的人:穷人,饥饿者,游民,被蔑视者,简单的说:即那些贫苦度日的人,身体上的贫困或心灵上的贫困…对于这些生活在阴影底下的人们,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只要他们仍然贫困度日,人类尊严,自由,文化,宽容对他们是毫无人性上的机会,而且对于饥饿及口渴的人而言,上帝只能显示出面包和水的形式。”
电影与法律涉及多方面的博弈,诸如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性,说理与强制,实质公正与形式公正等。电影是非理性的,法律是理性的。电影是对理性的背离,处于理性的彼岸,不赞同理性。法律则是由理性发展起来的经验和由经验检测的理性。它们之间的区别大而明显:法律规范的是行为,是对互异甚至对立的各种利益做出优先安排或是平衡,电影涉及的是观念,而且很有可能是对既定秩序中的利益格局表达出观念性的反叛;法律依赖于权力,电影诉诸美感和影响力。法律基于理性而补救理性,电影则是非理性的感觉与想象。法律以事实为依据,追求中立,而电影常常是偏颇甚至激越的。
本片中,里奇如果最后被送到警察局,受到“公正”的法律制裁,作为观众,我们的内心是不安的,甚至心生凄凉,因为我们知道里奇并不是一个坏人。虽然,法律试图扮演“大写的真理,”主张在“理性化”的法律条文面前,依靠其理性和强制性,总得到一种“公正的”“唯一合理的”判决。然而问题随之而来,既然法律是通过穿梭于法律规则和具体事件之间的互动过程渐进发展起来的,就难免会遭遇形形色色个案中的特殊正义问题。如果说普遍正义是基于制度的语境,目的在于形成让人信服的一般性规则,那么,特殊正义则是基于现实的语境,就事论事的具体情景具体分析。电影偏重的就是特殊正义,而依据法律的直接后果是,法律判决经常演绎一种“正”高于“善”的局面,所谓的内容明确逻辑一致的法律法规,因为缺乏应有的灵活,僵化甚至停滞,令人难以接受。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很多电影中,法律常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因此,用标榜理性的法律坐标去评价电影人物是没有意义的,电影和法律之间甚至存在尖锐的对峙和冲突。
三、电影与法律的内在通联
然而,电影与法律还是有着一些内在的通联性。无论是电影还是法律,都需要从日常空间中剥离出一个独特的表达空间。法官的法律判定与事实判定是相异的,存在着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的权衡;同样的,艺术家是在一个暂时脱离日常生活的空间进行的艺术表达,因此,电影世界中的善恶是非也不能等同于现实生活。并且,法律正是通过规则的约束以构建人类的共同生活,从而在不完美的凡俗世界保证最基本的善——一种将恶最小化的善。电影虽然强调个体的差异和审美,但是电影也有着自己的社会化功能。正如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提到的,“艺术不是无谓的游戏,而是有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职能,人们致力于艺术活动最初只是自己直接的审美价值,而它们所以在历史上被保存下来并发展下去,却主要因为具有间接的社会价值…艺术不但是一种愉快的消遣品,而且是人生的最高尚和最真实的目的之完成”。对应于人的理性和非理性两重需要,电影和法律分别以两种方式呈现,但是它们如影随形,联手反应了人的复合性需要。
电影主要是在视觉方面进行文化传播,塑造可触可感的人物的影像。正因为具有强烈的形象性和可感性,使得电影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然而,电影也是文学,哲学,美学,法律等多种内容的承载体。电影不仅因为有趣,因为它的娱乐功能,而且因为对于情感,人生,人性,社会等方面的探讨,因为对于各种困境和矛盾充满哲学意味的沉思与拷问,从而使我们有所感,有所悟,感受到一些深微的东西,从而体现思想情操和表现思想内涵。从而给予我们启发,引发我们无限的思绪。作为一种大众艺术,电影的成功离不开高科技的视觉体验,然而电影的本质在于叙事,在吸引眼球的同时,震撼我们的心灵,传达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情怀,传达对于真善美的守望。比如,电影大师西恩·潘,他的诸多影片,不仅对人物性格塑造得当,还有对于罪与罚这一命题的关照,对恶善的终极回答。
法律主要是在世俗生活的行为方面发挥作用。讲究理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然而,把现实层面中的价值问题转化为法律层面中的技术问题,既是法治的妙笔也是法治的败笔,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完美的法律,肯定是善法;完美的法治,是善法之治,即既符合客观真实的要求,又符合合法性的要求;既不允许为照顾事实真相而牺牲合法性,也不允许为现实合法性而牺牲事实真相。法律作为一项社会规范,虽然早就与道德规范分离,有着自身的逻辑和价值判断,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强调法律评价独立于道德评价,强调法律真实优先于事实真实。但是,法律至少包含着最低的社会道德要求,看护着文明和正义的大门,正如霍姆斯提到的,“法律最大的正当性,就在于它与人类的根本天性是相互贴合的”。
电影和法律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坐标框架和评价模式,但是两者内在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电影在满足我们审美的同时,贯穿了对于人生价值的寻求和靠近,通过一幕幕感人至深的人间悲喜剧,展现对于美好的追寻。法所追求的首要和最直接的价值——公平正义,也是由人们比较普遍和持久的是非善恶观念衍生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法律在古罗马被视为艺术对待,法被认为是一种关联着善与公平的艺术。也正因为如此,柏拉图认为,立法的最大目的是和平和善意,立法者制定每项法律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善。近现代法学家也一直关注法的形成与适用的最好方式,如德沃金主张的,“好法官要基于良心的违法,在某些特定案件中拒绝将先定规则适用当前案件,弃置之,如此,方能有真正的善。”
[1][德]考夫曼著,刘幸义等译.法律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杨力.法律思维与法学经典阅读:以哈特法律的概念为样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3][古希腊]柏拉图著,张智仁,何勤华译.法律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