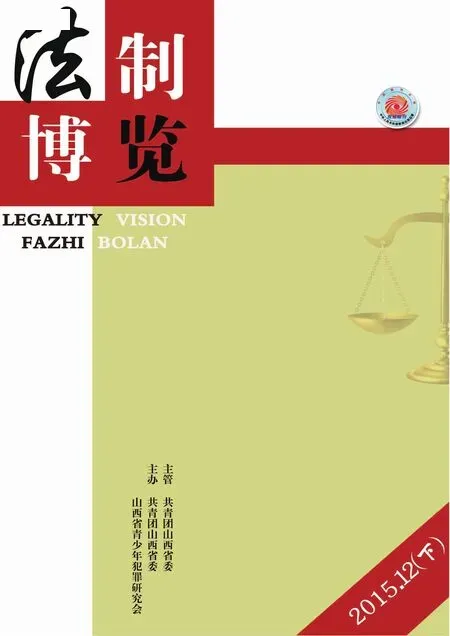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解决路径研究
2015-02-07高林娜
高林娜
河南大学法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解决路径研究
高林娜
河南大学法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2014年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分为6类:(1)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2)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3)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纠纷;(4)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同纠纷(5)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合同纠纷(6)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它将本质上是合同纠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列为了物权纠纷。关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的解决大多数学者只是在制度外探讨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的仲裁、调解、和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运用,对于从制度内深入讨论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解决的路径,学界对此的探讨是不充分的。笔者将将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关系角度入手,讨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进而深入探讨我国未来对于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债权的物权化;救济途径
中图分类号:D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36-0086-02
作者简介:高林娜(1994-),女,河南鹤壁人,河南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2013级本科生。

一、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物权性质
我国物权法规定土地经营权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1],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的用益物权应属于物权的范围,那么其取得方式必然也要符合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一物一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民事主体基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取得,基于民事行为的取得又可分为创设取得和移转取得。不论是创设取得还是移转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都离不开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对于土地承包权合同的性质有“行政合同说”、“民事合同说”、“经济合同说”,在上述观点中,经济合同并非主流观点,争议集中在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2]笔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属于民事合同,理由如下:
(一)从合同的主体上看,行政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必定是行政主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双方无论是在发包的一级市场还是在土地流转的二级市场,合同双方的当事人均为平等的民事主体。
(二)从合同的目的来看,行政合同的签订主要是为了政府职能的实现,从而完成其作为行政主体的任务。由此来看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并不是行政合同。
(三)从行政合同的履行、变更、解除上看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在行政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不平等,而土地承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故而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是民法调整范围内的合同,而非行政合同。
在此,笔者更深入探讨在民法制度的框架内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笔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应当是受合同法调整的,但在其保护上应该被物权化。综合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应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设立或取得,而且纵未登记也具有物权的对抗效力;地方人民政府发放证书、登记造册,只是为了“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取得和发生物权效力的要件。[3]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是同源的,受物权法保护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充要条件。这是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与普通民事合同的重要区别。
债权的物权化对于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什么是“债权的物权化”学界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有学者认为债权的物权化是指对债的相对性的突破。[4]还有学者将“债权物权化”归纳为债权通过制度的设计被赋予了原先本不具备的性质或效力,这些性质或效力体现出物权的特点,包括排他性、优先效力、对抗效力。[5]在此笔者颇为赞成第二种观点对于“债权物权化”的界定。债权物权化制度设计的本质是为了增强债权的效力,赋予债权以物权的某种效力,使之能够有效地被保护。而物权法将受其保护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规定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充要条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二、现今法律对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的规制
土地承包经营分为家庭方式的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家庭方式的承包与其他方式的承包在其流转权限上的法律规定是不同的。民事案由中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分为6类。这其中既包括了家庭方式的承包也包括了其他方式的承包。民事案由规定将以上的土地在二级市场的流转所发生的合同纠纷规定为合同纠纷,将农村土地在一级市场的分配所引起的合同纠纷确认为物权纠纷。笔者将从纠纷发生的性质入手,来分析我国现今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解决的立法现状。
我国立法上对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的案由规定从根本上反映出了目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力度,其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
三、对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解决制度的思考与重构
(一)土地承包合同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
1.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
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经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取得。这与不动产物权取得方式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不同。对于怎么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学界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学者提出农地使用权设立合同,应采取书面形式,当事人双方应当到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6]王利明教授则认为应区分家庭方式的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家庭方式的承包。家庭方式的承包因其特色不需要登记增加登记机关的压力,而其他方式的承包不涉及成员权,且承包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自主约定,因此其他方式的承包应该设置登记制度。在此笔者不能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理由如下:
从目前我国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规范来看,我国《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都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登记只是对抗要件,未经登记仍可以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其行使权利的方式受限。
从是否涉及成员权的立法精神来看,其他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所享有的权利虽然不是直接基于其自身的成员权取得的,但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将农村的非耕种土地进行承包给本集体组织以外的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政府批准。其他方式的承包经营权是基于成员权的行使间接取得的,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没有成员权而否定其依据土地承包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违背我国相关法律的。
从取得方式来看,其他方式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内容由双方自主协商确定,这较家庭方式的承包其限制较少。但我国《物权法》规定对于农村集体内部的“四荒”土地,允许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现行的法律对农村的土地利用方式采取了区别对待的规则,经过集体经济组织民主程序决定后,可由集体组织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社会组织承包此类土地。采取这类承包的方式一般有招标、拍卖、公开协商。农村非耕地的承包采取招标、拍卖的方式不仅要遵守《招投标法》、《拍卖法》有关规定,而且要结合土地承包经营的特点,充分保障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权,承包的方法、程序、过程和结果应当公开,特别是对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开。法律对于其他方式承包经营权的取得程序要比家庭方式的承包严格许多,若在对其增设登记等程序会使得其取得方式过于复杂,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2.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适用物权法区分原则的思考
有学者认为将土地承包合同与土地上的权利分开是不可取的,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并不是一旦法律规定,承包经营权人就自然取得了对土地享有的物权,在法律规定承包经营权以后,农民还需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合同,才能产生物权,[7]对此笔者不能赞同。笔者认为:
我国物权法规定了区分原则,用来区分物权的变动的结果与可能产生物权变动的债权行为,说明了因债权设立物权的效力产生物权边变动结果的物权的效力是不同的,是两个法律关系。[8]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中承认区分原则不仅有利于协调民法中物权变动制度、物权与债权的关系等各项制度而且有利于在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纠纷。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因而它也具有合同的一般性质。合同是典型的债权,债权具有相对性,非有法定情形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这也就意味着合同法允许在一个标的上设立数个相同的债。物权是典型的绝对权,具有对世性,因而长久以来,物权一直惯行着“一物一权”的原则。笔者认为将两者之间的关系量化,其两者之间的关应是映射关系而非函数关系。
基于上文的论述,实践中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形式以合同为主。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该如何保护自己权利?是基于合同法产生的权利还是基于物权法产生的权利?有学者认为农村土地的经营形式,只有“承包经营”可以作为用益物权得到物权法上的保护,而农村实际存在的经营形式则看不到赖以得到物权法保护的依据。[9]对此,笔者颇为赞同,但是对于立法上想要给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救济尚有距离。
笔者认为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救济应该完全的物权化,只要有合法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无论是那两方之间发生纠纷都应该采取物权的救济方式。原因如下:
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是一种稳定的物权。农业本就是投资多,时间长,收益慢的产业,如果将农村的土地流动性增强势必会导致投机资本进入农村土地,不利于我国目前农村土地的利用。
保护农民的集体利益。我国目前农村的现状很难保证农民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权利。乡村组织以行政命令的办法和“村规民约”的形式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并成为新阶段侵犯农民权益的主要形式。[10]确立农村集体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实质上是增强了农民手中的权利。首先,物权受侵犯所产生的物上请求权,如排除妨害请求权等。此类救济性物权的行使不以权利人有过错为阻碍。其次,物权性的救济赋予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于村委会行使发包权也是一种限制。村委会作为发包方可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重复发包的现象,那么若以债权来约束双方的行为显然不合适。若是物权性质的保护,则面对此情况对于发包人来讲就是无权处分,对于承包方而言就享有追认权。物权更有利于保护农村集体的利益,也更加有利于提高农村的土地利用效率。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生存的根本,截止至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乡村人口居住比例仍有50.32%[11]。因此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加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对于稳定我国土地制度的根基具有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1]物权法127条.
[2]张伟.农村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规制论[D].中国地质大学,2011.
[3]江平.民法总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4]郑在义,龚端.合同相对性原则外制度在合同法中的地位[J].国家检察院学报,2004(6).
[5]程晓丽.论债权的物权化[D].华东政法大学,2008.5.
[6]2014年民事案由规定.
[7]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233条.
[8]王利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保障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9]江平,民法总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10]渠涛.民法理论与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1]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