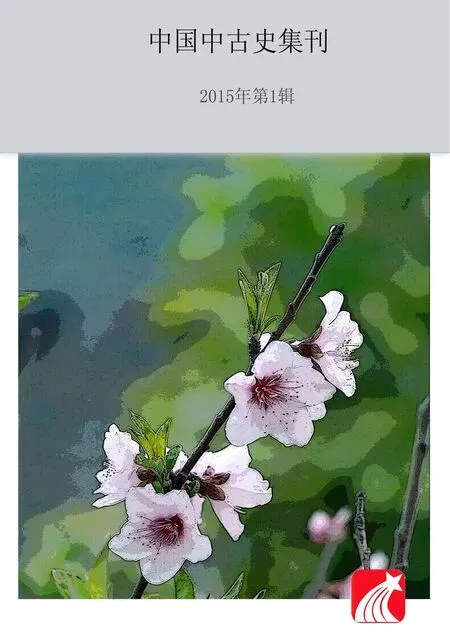庆山还是阇崛山*
——重释《宝雨经》与武周政权之关系
2015-01-30孙英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孙英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孙英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中国本土的阴阳灾异思想在中古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君主提供了新的政治理论和解释系统,两种思想体系发生激烈冲突与融合。这是中古时代思想、知识和政治世界的一大面相。然而关于外来之佛教与本土知识和思想体系的冲突与融合,学界之前更多关注的是佛道关系、佛教与儒家伦理的互动等等,而阴阳五行、谶纬、术数和佛教的关系,却遭到了很大程度的忽视。
学界已经注意到武则天在利用佛教做政治宣传的同时,也大量使用了中国传统的谶纬祥瑞思想。即便是最具佛教代表性的《大云经疏》,也充斥着祥瑞之说、谶纬之言。[1]相关的研究参见〔日〕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岩波书店1927年版,第686—747页;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大云经疏〉初步研究》,《文献》2002年第4期;金滢坤、刘永海:《敦煌本〈大云经疏〉新论》,《文史》2009年第4辑,第31—46页。和《大云经疏》一样,对武周政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宝雨经》,也明显窜入了中国本土的阴阳灾异观念,并运用佛教新知识对其进行了改造。这部分内容在之前萧梁时期译出的同本佛经《宝云经》和《大乘宝云经》中是没有的。菩提流志窜入这部分内容,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是利用佛教提供的新理论将中国传统阴阳灾异学说视为不祥之兆的现象解释为祥瑞,为武则天的统治寻找合理性依据。本文目的就是以武周政权利用佛教化解山涌灾异说作为一个切面,研究中古时代外来佛教与本土知识、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一、女身为帝和杀害父母说:《宝雨经》对武周政权的意义
武周政权与佛教关系密切,已为学界所广泛认同,如陈寅恪《武曌与佛教》从家世信仰和政治需要两方面说明了武则天信仰佛教的必然性。[1]陈寅恪:《武曌与佛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5年第5本第2分册,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155页。长寿二年(693),在武则天的支持之下,达摩流支(武则天改其名为菩提流志[2]《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卷183《薛怀义传》。,Bodhiruci)等译成《佛说宝雨经》(以下简称《宝雨经》)十卷。《宝雨经》的译出并非偶然,它是武后革唐为周的政治运动中的重要一环。然而过去学界比较关注武则天利用《大云经疏》进行政治宣传,而对《宝雨经》的意义揭示不够。主要的原因在于《旧唐书》明确提到了武则天利用《大云经疏》:“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1]Antonin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Napoli: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Seminario di Studi Asiatici, 1976,pp.125-136.2005年,富安敦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不过对《宝雨经》的研究,基本并未更改或增加更多的内容,参看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5. 在两书中,富安敦都在俞正燮《癸巳存稿》以来研究论著的基础上,指出《宝雨经》译文中的窜入和附加部分。而两唐书对《宝雨经》都未提及。
但实际上,《宝雨经》的翻译,对武周政权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富安敦(Antonino Forte)在《七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一书中,已经指出两者同等重要,共同构成了武周政权的佛教理论基础。[2]《大正藏》第10册,第1页上。富安敦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武后御撰《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新的八十卷《华严经》于圣历二年(699)10月译完,武则天在御撰序言中大谈佛教赋予自己的符命:“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宝雨》之文后及。加以积善余庆,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殊祯绝瑞,既日至而月书;贝牒灵文,亦时臻而岁洽。逾海越漠,献琛之礼备焉;架险航深,重译之辞罄矣。”
在这段自述中,武则天把《大云经疏》、《宝雨经》都视为预示自己符命的谶文,《大云》在前,《宝雨》后出,而“河清海晏”、“殊祯绝瑞”则是标明自己的统治受到肯定的征祥。然而在《宝雨经》译出之前,武则天在宣扬自己符命的时候,仅仅提到《大云经疏》,并不会提到《宝雨经》,比如天授二年(691)三月,她在《释教在道法之上制》中说:“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历数表于当今,本愿标于曩劫。《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敷化,弘五戒以训人。爰开革命之阶,方启惟新之运。”[1]《唐大诏令集》卷113,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87页。
可以推测,《宝雨经》译出之后,被纳入既有的宣传体系,完善了《大云经疏》的不足,从这之后,《宝雨经》和《大云经疏》在武周政权的政治宣传中往往被一并提及。
实际上,把《宝雨经》和《大云经疏》相提并论,视为武周政权上符天(佛)命的理论基础,是当时的一种共识,并不局限于武则天本人。比如当时有名的大臣李峤在《宣州大云寺碑》歌颂武则天云:“藏象秘箓,祯符郁乎《大云》;发迹乘时,灵应开于《宝雨》。”[2]《全唐文》卷284《李峤·宣州大云寺碑》。贾膺福的《大云寺碑》说得更加清楚:“自隆周鼎革,品汇光亨,天瑞地符,风扬月至。在璇机而齐七政,御金轮以正万邦。(阙六字)千圣。菩萨成道,已居亿劫之前;如来应身,俯授一生之记;《大云》发其遐庆,《宝雨》兆其殊祯。”[3]《全唐文》卷259《贾膺福·大云寺碑》。
李峤和贾膺福把《大云经疏》和《宝雨经》并列的做法,跟武则天自己所谓“《大云》之偈先彰”,“《宝雨》之文后及”的精神是一样的,都是把《宝雨经》视为跟《大云经疏》同等重要的文献—这其实是带有谶书色彩的佛典。
虽然没有像《大云经疏》一样获得在全国建寺的待遇,但是作为武则天受命符谶之书,菩提流志等新译《宝雨经》也同样颁行到地方。这一点荣师新江已有详细的揭示。[4]荣新江:《胡人对武周政权之态度—吐鲁番出土〈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校考》,《民大史学》1996年第1期,转引自《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1—214页。陈寅恪在《武曌与佛教》中已指出,敦煌残本的《大云经疏》,即当时颁行天下以为受命符谶之原本。而颁行到地方的《宝雨经》写本,根据荣师新江的研究,共有六件,可分为三组:
(1)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敦煌所获S. 2278号,为《佛说宝雨经》卷第九,有长寿二年(693)译场列位及证圣元年(695)四月八日检校勘授记。其题记云:“大周长寿二年岁次癸巳九月丁亥朔三日己丑佛授记寺译,大白马寺大德沙门怀义监译,南印度沙门达摩流支宣释梵本。”又,北京图书馆藏李26、李31为卷一残卷,S.7418为卷三残卷。这些应是颁到沙州的写本残卷。
(2)德国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吐鲁番与乌鲁木齐间一遗址出土的MIK Ⅲ-113号,为《佛说宝雨经》卷第二,有长寿二年译场列位。这应是颁行到西州的写本残卷。
(3)日本东大寺圣语藏所藏日本传世写经,也有《佛说宝雨经》卷第二,也有长寿二年译场列位。这应当抄自原颁行到唐朝某地的写经。
三组写经均用武周新字[1]一般来说,写有武周新字的碑铭都是新字颁行的天授元年(690)至神龙元年(705)之间刻成的。而个别较此年限为晚的敦煌文书仍用武周新字,但大都不是通用的“年”、“月”、“日”、“天”等字。有关研究很多,此处不赘,比如可参见王三庆:《敦煌写卷中武后新字之调查研究》,《汉学研究》1986年第2期。综合判断,这些《宝雨经》写本,应该是在其译出的长寿二年(693)之后迅速颁行到沙州、西州等地的。在内地诸州的颁行情况应该大致类似。,写经格式基本一致,译场列位大体相同,都属于译场译完后送到秘书省的“进奏本”。这些具有强烈官方意识形态的写本,很快就被送到唐朝地方各州,可见武周政权对它们的重视程度。吐鲁番出土的《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在所拟抄写的佛典目录最后,列入了《宝雨经》,说明此经对当地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官方,甚至渗透到胡人部族及地方大族,他们主动地抄写《宝雨经》,不但是个人信仰的原因,更带有强烈的政治投机色彩。[2]同上书,第214页。
过去学者多强调《大云经疏》为其以女身统治天下进行政治宣传[1]比如王国维:《大云经疏跋》,载罗福苌编:《沙州文录补》,1924年,叶5b-6b,收入王重民编《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69—270页;又陈寅恪:《武曌与佛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1935年,第137—147页,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37—155页。,但是实际上《大云经疏》所涉及女身当王的内容不过寥寥数语,含糊说净光天女当王阎浮提,实不足以单独作为武则天篡唐称帝的有力根据。《大云经》早译出,即《大方等无想经》。昙无谶《大方等无想经》云:“有一天女,名曰净光……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2]《大正藏》第12册,第1097页上—1098页上。但是,第一它并未提到武则天的名字,第二也没有提到何处为王,只是说该天女将来会作转轮王。薛怀义等撰《大云经疏》时,将经中“净光天女”解释为“今神皇王南阎浮提一天下”。根据这些注疏,垂拱四年五月,武则天加尊号“圣母神皇”。但是,这不是佛经里的内容,而是薛怀义等人的解释,可以说是于经无征,有点牵强。[3]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宝雨经》最大的贡献,第一在于它明确说明此女将在南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为帝;第二,它并非注疏,而是佛经,从而解决了武周政权于经无征的问题。因为《宝雨经》的译出,武则天称帝得到了佛经经文的证实。可以说,《宝雨经》才是武则天为女主的直接理论来源。有的学者比如郭朋就指出,《宝雨经》有关武则天女身为中国主的内容,比《大云经》要清楚得多:在“佛灭”后两千年的时候,有一位“故现女身”的“菩萨”,要在印度东北方的中国“为自在主”[4]郭朋:《中国佛教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诚为确论。
除了《宝雨经》支持武则天以女身当皇帝这一观点之外,汤用彤提出新说,认为菩提流志等人在新译《宝雨经》时增加了“菩萨杀害父母”的语句,从而为武则天杀害李唐宗室提供了理论依据,武则天引《宝雨经》以自饰。[1]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44页。此说颇令人费解。《宝雨经》并无“菩萨杀害父母”之文,而是菩萨为了让信众心生信服,现出神通,在信徒面前幻化出父母,菩萨杀害的,是其幻化出来的父母。[2]《大正藏》第16册,第293页中。与此同时,《宝雨经》谈到最多的还是孝顺父母的内容,比如当谈及为了菩萨不生边地时,《宝雨经》说,边地之人“顽嚚愚憃,犹如哑羊,如是等类于善恶言义不能了知,不孝父母,不敬沙门、婆罗门”[3]同上书,第312页下—313页上。。可见,《宝雨经》并不反对,甚至是歌颂孝顺父母的。所谓菩萨杀害父母只不过是其教诲有罪众生的手段,防止他们自怨自艾,放弃获得救赎的希望。
菩提流志译《宝雨经》之前,已经存在两种译本,一种是梁扶南三藏曼陀罗仙译《宝云经》8卷,另外一种是梁扶南三藏曼陀罗仙共僧伽婆罗译《大乘宝云经》(俱在《大正藏》第16册)。对比三种译本,《宝云经》和《大乘宝云经》中都没有所谓支那女主之说,可知菩提流志译本中关于日月光天子现女身为国王的说法是其窜入的。
关于“杀害父母”的内容,出现在《佛说宝雨经》的卷第三:“若此有情未能悔过,是时菩萨欲令彼人心生信伏,为现神通,广说彼人思惟之事。……菩萨又复于彼人前化作父母,说如是言:‘汝可观之,我即是汝同伴丈夫,汝莫悔过此所造业,毕竟不堕捺洛迦中,亦不退失利益安乐!’如是说已,即便杀害所现父母。菩萨于彼有情之前示现神变,彼人思惟:‘有智之者,尚杀父母不失神通,况我无智而造此业,堕捺洛迦,退于利乐!’尔时菩萨为彼有情演说妙法,令其恶业渐得轻微,犹如蚊翼。是名菩萨除遣恶作方便善巧。”[1]《佛说宝雨经》卷3,《大正藏》第16册,第293页中—下。
但是实际上,这段内容不是菩提流志编造的,更不是窜入的。在梁扶南三藏曼陀罗仙译《宝云经》的对应部分,也就是《宝云经》卷第二,有同样的内容:“ 云何名菩萨善除疑悔?若见众生作五逆罪及余诸恶,菩萨即语众生言:‘汝今何为愁苦如是?’彼人答言:‘我作五逆罪,愁忧悔恨。舍此身已,当久受苦恼,长夜衰损,无有义利。’菩萨为现神变,适其心念。令彼信服,便生信敬爱乐。菩萨又复化作父母而加逆害,彼作是念:‘菩萨神足威力无量,犹害父母,况我愚痴而能不作?’”[2]《宝云经》卷2,《大正藏》第16册,第217页中—下。
梁扶南三藏曼陀罗仙共僧伽婆罗译《大乘宝云经》相应部分(卷第二)也有同样的内容:“善男子,云何菩萨善解断除疑悔方便?菩萨摩诃萨见是众生作五逆罪,及余不善种种罪业。……是时菩萨于其人前,而作变化,化作父母,而作是言:‘仁者见不,我之父母亦被杀害。’杀父母已,复作神通而现是人,令其欢喜,‘如是之人,有大神通,尚杀父母,何况于我?’是时菩萨为是众生而说法要,令其罪业展转轻微,薄如蝇翼。如是菩萨断除疑悔,善巧方便。”[3]《大乘宝云经》卷2,《大正藏》第16册,第251页上。
对比三种译本,可知菩提流志新译《宝雨经》关于菩萨“杀害父母”的内容并非是菩提流志等人窜入的,更不是捏造的,在原本中就有同样的内容。从内容可以判断,这段内容是在说犯下杀害父母等罪业的人,因为担心陷入无尽报应而对前途绝望,菩萨为劝导此类有情,幻化出父母进行杀害,达到说服他们打起精神,遵从佛法的目的。从逻辑上推断,《宝雨经》十卷,最能达到政治目的的当属卷一,在卷三中增加政治内容,将混杂于繁杂的佛经教义中,恐会损害政治本意。武则天以《宝雨经》菩萨“杀害父母”为自己屠杀李唐宗室辩护的观点,恐有度解释的嫌疑。从逻辑上说,武则天杀害的是李唐宗室,而非自己的父母;而且屠杀李唐宗室早在垂拱年已经基本完成,何必在数年之后再为此费劲寻找依据?就逻辑而言这中间还有一定距离。
从上述分析来看,武则天凭借《宝雨经》为自己女身称帝寻找到了确切的佛经依据,这一说法确可成立。而所谓《宝雨经》为武则天屠杀李唐宗室提供依据一说,仍颇可存疑。这些是已揭示出来的内容。实际上,《宝雨经》中明确跟武则天的政治宣传有关的内容,还有被前辈学者所忽略的部分。
二、山涌和五色云:重读《宝雨经》窜入部分
《宝雨经》虽然往往被归为疑伪经[1]牧田谛亮《疑经研究》将疑伪经按照编撰意图分为六种,其中第一种即为迎合统治者统治意图而造,而武则天时期的《大云经》和《宝雨经》被归为此类。参见〔日〕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版。,但实际上菩提流志等窜入的部分比例不大,主要集中于卷第一。窜入最为明显的部分,也就是卷一中关于武则天以女身在南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为自在主的部分:“ 天子!以是缘故,我涅盘后,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位居阿鞞跋致,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治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令修十善;能于我法广大住持,建立塔寺;又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供养沙门;于一切时常修梵行,名曰月净光天子。然一切女人身有五障。何等为五?一者、不得作转轮圣王;二者、帝释;三者、大梵天王;四者、阿鞞跋致菩萨;五者、如来。天子!然汝于五位之中当得二位,所谓阿鞞跋致及轮王位。天子!此为最初瑞相。汝于是时受王位已,彼国土中,有山涌出,五色云现。当彼之时,于此伽耶山北亦有山现。天子!汝复有无量百千异瑞,我今略说,而彼国土安隐丰乐,人民炽盛,甚可爱乐,汝应正念施诸无畏。天子!汝于彼时住寿无量,后当往诣睹史多天宫,供养、承事慈氏菩萨,乃至慈氏成佛之时,复当与汝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1]《佛说宝雨经》卷第一,《大正藏》第16冊,第284页中—下。笔者重新标点。原标点多有错误,尤其是画线部分,原作“汝于是时受王位已,彼国土中,有山涌出五色云现”。
对比前代的《宝云经》和《大乘宝云经》,可知这部分内容全部是菩提流志等人窜入的。其实这部分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讲武则天以女身为帝。菩提流志等人甚至捏造了新说法化解了佛教传统理论的女人“五碍说”—也就是女身不能作转轮圣王、帝释、梵王、魔王和佛(三界法王)。《宝雨经》把魔王换成了阿鞞跋致菩萨(Avaivart)。阿鞞跋致菩萨汉译为“不退转”,是菩萨阶位之名。经一大阿僧祇劫之修行,才能得到此位。菩提流志等人借佛典之名指出,虽然女人身有五障,但是武则天可以得到转轮王和阿鞞跋致菩萨两种位阶,只是不能为佛、帝释和大梵天王。这一点非常重要—武则天侧重宣传的是自己的转轮王角色,而非弥勒。学界以前往往说武则天以自己为弥勒佛下生为主要理论依据,恐为不妥。当另文辨析,此处不赘。
第二个内容,是为前辈学者所忽视的。包括富安敦在内,都对此毫无揭示。这一部分内容从上述引文的画线部分起,主要论说武则天受命称帝的符瑞—尤其是画线部分,是确有所指,并非泛泛而谈。《宝雨经》窜入部分强调,当武则天称帝之后,将有“无量百千异瑞”,但是《宝雨经》说,对这些祥瑞,“我今略说”,然而,在此句之前,《宝雨经》却列出了两个重要的祥瑞,即画线部分:“汝于是时受王位已,彼国土中,有山涌出,五色云现。”之前这一内容往往被读成“彼国土中,有山涌出五色云现”,似乎是山中涌出五色云。实际上并非如此,“有山涌出”和“五色云现”是两个祥瑞,而且应该是在武则天登基之后,国土中出现的。这部分内容带有强烈的中国本土祥瑞思想的色彩,但这仅仅是泛泛而谈的政治修辞吗?事实上恐非如此,所谓武则天受命之后,国土中“有山涌出,五色云现”是特指的,是有具体的事实做基础的。
先看五色云。五色云即景云,又称庆云。唐政府将祥瑞分为大、上、中、小四类,合计名物有一百四十八种,对于祥瑞的处理,《唐六典》记载:“凡祥瑞应见,皆辨其物名。……若大瑞,随即表奏,文武百僚诣阙奉贺。其他并年终员外郎具表以闻,有司告庙,百僚诣阙奉贺。其鸟兽之类有生获者,各随其性而放之原野。其有不可获者,若木连理之类,所在案验非虚,具图画上。”[1]《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4—115页。有关唐代祥瑞名物的简单辨析,参见牛来颖:《唐代祥瑞名物辨异》,《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
庆云属于大瑞,是最为重要的祥瑞之一。所以需要文武百官诣阙奉贺。关于景云的政治和思想意涵,笔者已有专文论述[2]参见孙英刚:《音乐史与思想史:〈景云河清歌〉的政治文化史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0年第26辑。,此处不赘。概括而言,景云是所谓太平之应,所以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预示着统治良好,获得了上天的肯定。不过奇怪的,两唐书等文献都没有记载武则天时代发生庆云。这是否说明《宝雨经》所说武则天称帝,则五色云现仅仅是政治修辞呢?事实并非如此,武则天之后李唐复辟,关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自然会有所曲笔,庆云之瑞也就不录。但是检《全唐文》就可发现,庆云或者景云确实在武则天时代出现了,而且在当时被大书特书,大肆宣扬。陈子昂为武则天歌功颂德的《大周受命颂》云:“ 又有庆云,休光半天,倾都毕见,群臣咸睹。……庆天应之如响,惊象物其犹神,咸曰:‘大哉!非至德孰能睹此?’昔唐虞之瑞逖听矣,今则见也。天物来,圣人革,时哉!”[1]《全唐文》卷209《陈子昂·大周受命颂》。
陈子昂记载的这次庆云出现在洛阳,“倾都毕见,群臣咸睹”,看见的人都认为这是武则天至德所感应,陈子昂更将其与武周革命联系在一起—“天物来,圣人革”。庆云出现后,百官给武则天的贺表是李峤所写,他在表中写道:“臣某等言:伏见今月十一日诛反逆王慈征等,乃有庆云见于申未之间。萧索满空,氛氲蔽日,五彩毕备,万人同仰。……谨拜表称贺以闻。”[2]《全唐文》卷243《李峤·为百寮贺庆云见表》。在另外一份贺表中,李峤引用《瑞应图》云:“天子德孝,则庆云出。”又云:“天下太平,庆云见。”[3]《全唐文》卷243《李峤·为百寮贺日抱戴庆云见表》。
作为大瑞,庆云出现,除了在京百官上表祝贺之外,地方各州也上表庆贺。崔融《为泾州李刺史贺庆云现表》就是泾州刺史上奏给武则天祝贺庆云出现的:“臣某言:伏奉诏书,上御武殿,有庆云映日,见于辰巳之间,肃奉休征,不胜抃跃。中贺:臣闻诸《瑞应图》曰:‘天下太平,则庆云见。大子大孝,则庆云见。’……谨遣某官奉表称庆以闻。”[4]《全唐文》卷218《崔融·为径州李刺史贺庆云现表》。
从上述证据来看,武则天时代发生了不止一次庆云出现,每一次出现都有百官上表祝贺,消息下发各州,进行全国性的政治宣传。这正是《宝雨经》所谓“汝于是时受王位已,彼国土中,有山涌出,五色云现”的部分写照。中宗复辟之后,其皇后韦氏也有政治野心,模仿武则天,制造了五色云:“(景龙二年二月)皇后自言衣箱中裙上有五色云起,令画工图之,以示百僚,乃大赦天下。……乙酉,帝以后服有庆云之瑞,大赦天下。内外五品已上母妻各加邑号一等,无妻者听授女;天下妇人八十已上,版授乡、县、郡等君。”[1]《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
以上是五色云部分,那么,武则天受命,则“有山涌出”是什么意思呢?这部分内容更加复杂,涉及中国本土的阴阳灾异思想和外来的佛教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山涌多与地震相联系,这是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从垂拱二年(686)开始,长安至洛阳的地震带进入了活跃期。这一年,在长安和洛阳之间的某个地方发生了地震,以至于在临潼新丰县露台乡出现山涌,高二百尺。余震则在此后两年反复,所以垂拱三年、四年,长安和洛阳都有不同程度的轻微地震。[2]诸史料都将这次山涌系于垂拱二年,只有《旧唐书·俞文俊传》记为载初元年(690)。根据崔融《为泾州李使君贺庆山表》,其称武则天仍然为“皇太后”,可知此时武则天仍未登基,也可证这次山涌发生在垂拱二年。关于地震与革命之关系,笔者已有专文讨论,此处不赘。[3]参见孙英刚:《佛教对阴阳灾异说的化解:以地震与武周革命为中心》,《史林》待刊。对于这次新丰山涌,《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则天时,新丰县东南露台乡,因大风雨雹震,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三顷,池中有龙凤之形、禾麦之异。则天以为休征,名为庆山。荆州人俞文俊诣阙上书曰:‘臣闻天气不和而寒暑隔,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山变为灾。陛下以为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诚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恐灾祸至。’则天怒,流于岭南。”[1]《旧唐书》卷37《五行志》“山崩”条;《旧唐书》卷187《忠义上》。
临潼地处临潼一长安断裂带上,地震风险较高。而且当地又以温泉著称,唐代著名的华清池就位于这里,可谓地下水资源丰富。地壳变动往往伴随地下流体变化。所以在这次山涌发生之后,由于地下水涌出,在小山周围形成了巨大的水池。而且由于温度和其他生长环境的变化,植物也可能出现反常的现象,所以有“禾麦之异”的出现。
然而荆州人俞文俊对新丰山涌的解释,依据的是传统的阴阳灾异学说,他把新丰出现的山涌解释为女主当政的反映。山涌预示着“女主居阳位”,是当时一种普遍的观念。纬书一般也将地震和山川改易解释为君主权威遭到挑战。比如《春秋文曜钩》云:“女主盛,臣制命,则地动坼,畔震起,山崩沦。”[2]《纬书集成》,第813页。《春秋潜潭巴》说的更为简明直接:“地震,下谋上。”[3]同上书,第832页。存于日本尊经阁文库的唐萨守真《天地瑞祥志》第十七“山条”云:“ 厥妖山崩,谓阴乘阳,弱胜强。又《汉书·元后传》曰,昔沙麓崩,晋史卜之曰,阴为阳雄,土火相乘,后六百卌五年宜有圣女兴乎?”又记云:“山嘿然自移,天下有兵,社稷亡。”[4]《天地瑞祥志》卷第十七。
萨守真《天地瑞祥志》编纂于麟德三年(666),当时武则天还未攫取最高权力。它明确指出,山川改易是“阴乘阳,弱胜强”,并把山川变易视为当年汉朝元后以女身掌权的征兆。新丰山涌后三年,也就是永昌元年(689),长安附近的华州再一次发生了剧烈的山川变动,《新唐书》是这样记载的:“永昌中,华州赤水南岸大山,昼日忽风昏,有声隐隐如雷,顷之渐移东数百步,拥赤水,压张村民三十余家,山高二百余丈,水深三十丈,坡上草木宛然。《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禄去公室,赏罚不由君,佞人执政,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1]《新唐书》卷35《五行二》“土·山摧”条。
这次山川改易被解释为“佞人执政,政在女主”。这样的论断虽然是倒放电影式的回溯,但是从《天地瑞祥志》等文献的记载来看,这种观念确实为大众特别是精英所广泛认同。
武则天对这样的解释非常忌惮。如果她在阴阳灾异说的框架内承认地震、山涌是自己上台的征兆,那么无疑供认了自己是以下犯上,这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承干出震、革唐立周的神圣性和合法性。这也是为什么武则天强烈反对把新丰山涌解释为阴胜阳,下犯上,并将提出这种见解的俞文俊流放岭南并最后杀死的主要原因。那么,她该如何化解这样的理论困境和舆论压力呢?
三、庆山说:从新丰庆山到万年庆山
对于686年的新丰山涌,武则天最初选择了将其祥瑞化—依据《瑞应图》所谓“庆山”说,代替被广泛接受的“山变为灾”说。武则天将新丰涌出之山,称为庆山。围绕着新丰庆山,她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宣传,下令改新丰县为庆山县,“赦囚,给复一年,赐酺三日”[2]《新唐书》卷4《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而且把这个喜讯下发各州,于是“四方毕贺”。[3]《旧唐书》卷187《忠义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崔融为泾州刺史撰写了的贺庆山表:“臣某等言:某日奉某月诏书,新丰县有庆山出,曲赦县囚徒,改新丰为庆山县,赐天下酺三日。凡在含生,孰不庆幸?中贺,微臣详窥海记,博访山经,方丈蓬莱,人迹所罕到;层城元圃,道家之妄说。……当雍州之福地,在汉都之新邑,圣渚潜开,神峰欻见。政平而涌,自荡于云日;德茂而生,非乘于风雨。游龙蜿蜿,疑呈八卦之图;鸣凤嗈嗈,似发五音之奏。仙蚕曳茧,美稼抽芒。……”[1]《全唐文》卷218《崔融·为泾州李使君贺庆山表》。
这时正是武则天推崇佛教压制道教的时期,所以崔融还在奏章中攻击道教关于层城元圃的说法是“妄说”。这篇贺表极尽曲意附会之能事,把“庆山”涌出解释为“圣渚潜开”、“政平而涌”、“德茂而生”的反映。这篇贺表基本上是依据《瑞应图》的观点进行阐发,不脱传统的祥瑞灾异思想的范畴。
学界往往忽略了“庆山”本来就是重要的祥瑞,其背后有自身的知识逻辑和思想背景,不是武则天随意取的名字。[2]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大云经疏〉初步研究》,以及金滢坤、刘永海《敦煌本〈大云经疏〉新论》等研究,均未揭示庆山自身的思想意涵,曹丽萍《敦煌文献中的唐五代祥瑞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反倒对庆山有所讨论,可以参看。而且,庆山跟庆云一样,是“大瑞”的一种。如果发生,需要文武百僚诣阙奉贺。这就是崔融贺表写作的背景。
庆山为祥瑞,当时是较为普遍的观念,比如萨守真《天地瑞祥志》的“山条”云:“《瑞应图》曰:‘庆山者,王志德茂则生也。’”[3]《天地瑞祥志》第十七。
作为大瑞,庆山是君主“德茂”的感应,不再是“阴乘阳”、下犯上的反映。武则天之所以强调这次新丰山涌是庆山,就是要避开通常所谓的地震山移是臣犯君反映的政治风险,转而强调庆山涌出是她统治良好的反映,是上天对她的肯定。
利用庆山作为符命的征祥,还见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敦煌文献《李明振再修功德记碑》记:“庆丰山踊,呈瑞色于朱轩;陈霸动容,叹高梁[于]壮室。……遐耀天威,呈祥塞表,因凿乐石,共纪太平。”[1]P. 4640《李明振再修功德记碑》,《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2册,第252—253页。
此时并非张氏族子张承奉掌握归义军政权,而是张议潮十四女李氏及其子,我们不能不揣测当时李氏是有意模仿武则天,将庆山涌出解释为李氏接管张氏政权乃天所授意。从这一内容也可推知,敦煌对内地的政治操作颇为熟悉,并能举一反三,用于自身合法性的塑造。其实就在武周时期,敦煌出现了大量跟武周革命有关的祥瑞,基本为沙州地方官员和家族曲意附会、进行政治投机的产物。《沙州都督府图经》详细收录了这些祥瑞。此图经写本有P. 2005、P.2695、P. 5034三号,尤其以P. 2005(即卷三)保存最为完整。[2]李正宇校注者较好,参见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144页。其详细记载了作为武周政权征兆的种种祥瑞,包括“白龙”、“黄龙”、“五色鸟”等,基本是为了赞颂女主临朝,武周革命的曲意附会之神异现象。[3]相关论述,参见余欣:《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
新丰出现“庆山”之后不久,到了载初元年(690),西京万年县又出现了山涌。这一年,武则天正式废掉睿宗称帝,改唐为周。也就是在其称帝后不久,西京留守武攸望(也正是武氏家族的重要成员)上表,称所部万年县霸陵乡有庆山涌出,这显然是沿袭686年新丰山涌的做法:“臣于六月二十五日得所部万年县令郑国忠状,称去六月十四日,县界霸陵乡有庆山见,醴泉出。臣谨差户曹参军孙履直对山中百姓检问得状:其山平地涌拔,周回数里,列置三峰,齐高百仞。山见之日,天青无云:异雷雨之迁徙,非崖岸之骞震。欻尔隆崇,巍然蓊郁,阡陌如旧,草树不移。验益地之详图,知太乙之灵化。山南又有醴泉三道,引注三池,分流接润,连山对浦,各深丈余,广数百步。味色甘洁,特异常泉,比仙浆于轩后,均愈疾于汉代。臣按孙氏《瑞应图》曰:‘庆山者,德茂则生。’臣又按《白武通》曰:‘醴泉者,义泉也。可以养老,常出京师。’《礼斗威仪》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醴泉涌。’《潜潭巴》曰:‘君臣和德,道度协中,则醴泉出。’臣窃以五行推之,六月土王,神在未母之象也。土为宫,君之义也;水为智,土为信,水伏于土,臣之道也;水相于金,子之佐也。今土以月王而高,水从土制而静,天意若曰:母王君尊,良臣善相,仁化致重,德茂时平之应也。臣又以山为镇国,水实利人,县有万年之名,山得三仙之类:此盖金舆景福,宝祚昌图,邦固不移之基,君永无疆之寿。自永昌之后,迄于兹辰,地宝屡升,神山再耸,未若连岩结庆,并泌疏甘,群瑞同区,二美齐举,高视古今,曾无拟议。信可以纪元立号,荐庙登郊,彰贲亿龄,愉衍万宇。臣辱司京尹,忝寄留台,牧西夏之疲人,荷东蕃之余宠,游泳鸿露,震悚明神。禧祉有归,光启兹部,喜睹殊观,实百恒流,踊跃一隅,驰诚双阙。伏请宣付史馆,颁示朝廷。无任凫藻之至,谨遣某官绘图奉进。”[1]《全唐文》卷222《张说·为留守奏庆山醴泉表》。
这篇上表出自张说的手笔,他引用了《瑞应图》、《白武通》、《礼斗威仪》、《春秋潜潭巴》等谶纬祥瑞之书,并以五行之说解释附会,认为这次万年县庆山涌出,是继新丰庆山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征祥,“自永昌之后,迄于兹辰,地宝屡升,神山再耸”。在祥瑞思想里,庆山往往和醴泉连在一起,庆山涌,醴泉出,被认为是上天对君主统治的高度肯定。
围绕着万年县庆山,西京留守连续上表,均出自张说之手,为武则天上台寻找理论依据。张说《为留守奏瑞禾杏表》云:“臣今月三日得所部万年县令郑国忠状,言县界内霸陵乡新出庆山南之醴泉,北岸有瑞杏三树,再叶重花;嘉禾三本,同茎合穗。臣谨差司兵参军郑味元检覆皆实。臣谨按孙柔之《瑞应图》曰:‘嘉禾者,五谷之长也,王者德茂则生。昔炎帝教洽人心而嘉禾秀,周公理合天道而嘉禾丰。’”[1]《全唐文》卷222《张说·为留守奏瑞禾杏表》。
这次,在庆山醴泉北岸,出现了瑞杏重花,嘉禾合穗的祥瑞。接着,西京官员又在庆山醴泉之瑞,“于山陵东柏城内得嘉禾一本”,“下则异亩合茎,上又同连双穗”。于是张说又奉命撰写《为留守奏嘉禾表》呈给武则天。[2]《全唐文》卷222《张说·为留守奏嘉禾表》。
这还不够,应该就是在此之后不久,张说受命撰写《为留守奏羊乳獐表》,在讨论完植物祥瑞后,转向动物,务必使武则天的茂德,泽被众生。他在上表中说:“臣今日得所部万年县令郑国忠状,送新出庆山下羖牝羊乳獐麑一头。……况复晨饮醴浦,夕下灵山,翳仙杏之奇花,拾嘉禾之余穗:羊祯甚玉,獐庆如银。晦朔未移,祥符累集,福应之盛,前古未闻。”[3]《全唐文》卷222《张说·为留守奏羊乳獐表》。
万年县庆山醴泉,似乎在神都洛阳的朝廷引起了很多讨论和争议。西京方面的不断上表,呈送图样、名物,更新信息。然而,通过将地震山涌的灾异解释为祥瑞的做法,存在技术性的难题—界定庆山和普通地震山涌的标准,只有《瑞应图》的比对。但最为大众所接受的说法,依然是“山变为灾”的观念。
四、佛教的加入:从庆山到祇阇崛山
关于万年县山涌的解释,随着佛教的加入,被赋予了新的意涵。因为史料的缺憾,难以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就在不厌其烦地发出“庆山”的最新信息后不久,西京方面改变了说法,在庆山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认定为佛教的祇阇崛山。张说《为留守作贺崛山表》云:“臣闻山川变见,如来有得道之祥;国土远移,至人任不思之力。伏惟皇帝陛下宏惠福深,勤人愿满,莲花授记,应上圣之降生;贝叶开图,握大雄之宝命。司户参军孙履直伏承臣奏所部万年县新出庆山醴泉,乃有天竺真僧于春首献状,若以梵音所记,此是祇阇山。恒河沙佛,必经林下;虚空众圣,常处岩间。隐见外方,涌秀中土,岑泉可识,体类宛然,感应十号之尊,示见千轮之主。”[1]《全唐文》卷222《张说·为留守作贺崛山表》。
根据此表可知,有一位所谓天竺真僧献状,指认此山为祇阇山。庆山是中国传统祥瑞思想里面的瑞山,根据这位天竺僧人,按照梵音,就是佛教里的“祇阇崛山”。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之前强调阴阳感应的庆山说,转而论述“感应十号之尊,示见千轮之主”的祇阇崛山,将祇阇崛山在中土的出现,归结为“如来有得道之祥”,“上圣之降生”,也即武则天以佛教转轮王身份君临天下。
不光是万年县的庆山被解释成了佛教的祇阇山,连之前的新丰庆山,也跟佛教产生了关联。根据《佛祖历代通载》,证圣二年(696),在新丰庆山出现了佛迹,所以武则天“敕建寺宇”。[1]《佛祖历代通载》卷12,《大正藏》第49册,第584页中。
祇阇崛山(Gdhrakūa)是佛教的圣山,又名伊沙堀,揭梨驮罗鸠胝,姞栗陀罗矩咤。在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之东北,释尊说法之地。《一切经音义》注“鹫峰山”云:“西国灵山名也,古曰祇阇崛山,是存梵语,讹也。此山多鹫鸟,因以为名也。”[2]《一切经音义》卷29,《大正藏》第54册,第499页中。祇阇崛山与佛祖联系在一起,被视为灵山,唐蓝谷沙门惠详云:“ 祇阇崛山,唐言鹫头,亦云鹫峰。接北之阳,孤标特起。既栖鹫鸟,又类高台。空翠相映,浓淡分色。如来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广说妙法,即说此经之处也。故经云:‘常在灵鹫山。’”[3]《弘赞法华传》卷1,《大正藏》第51册,第12页中。
正如惠详所说,佛经常常提到祇阇崛山,将其描述为圣人住处,比如鸠摩罗什奉诏译《大智度初品中》论道:“是山于五山中最高大,多好林水,圣人住处。”[4]《大智度初品中》卷3《住王舍城释论第五》,《大正藏》第25册,第76页下。又云:“佛多在祇阇崛山中,不在余处。”“祇阇崛山,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住处。”[5]同上,第78页中。“祇阇崛山清净鲜洁,受三世佛及诸菩萨,更无如是处,是故多住祇阇崛山。”[6]同上,第79页中。
正因为祇阇崛山对佛教意义重大,所以崇佛的君主往往视此山为佛教圣地。后魏太祖道正(武)皇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就造祇阇崛山图一所,“加以绩饰,莫不严具”[7]《弘赞法华传》卷1,第13页中。拓拔珪谥号为道武皇帝,惠详“道正”之说不详来源。。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命李义表、王玄策送婆罗门客回国,同年十二月到达摩伽陀国,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抵达王舍城,王玄策等人登上祇阇崛山,于是勒石为铭,其辞有云:“大唐出震,膺图龙飞。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迈轩羲。高悬玉镜,垂拱无为。”[1]《法苑珠林》卷29,《大正藏》第53册,第504页上—中。
在佛祖讲法处勒石纪念,言辞却用“出震”、“龙飞”、“光宅”等带有中国本土天人感应思想的字眼,这一历史场面背后的思想内容之丰富,自不待言。[2]关于王玄策出使的研究,参见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东方学报》1994年第66册;又《〈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
对祇阇崛山描述得最为详细的,当属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译《大方广三戒经》,在这部佛典中,昙无谶详细描述了作为佛教圣地的祇阇崛山的种种祥瑞之象:“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祇阇崛山,而是山王高峻广博,持众杂谷,犹如大地生杂种华。……多种杂类,所谓:师子、虎犳、象马、骐驎、熊罴、獐鹿……羖羝、猕猴,是等众兽,止住其中;有无量众鸟,所谓:孔雀、鹦鹉、鸲鹆……是诸众生以佛力故,不为贪欲、瞋、痴所恼,不相茹食,共相亲爱如母如子。是时山王中,稠林郁茂,枝条无折,多众杂树:天木树、毕利叉树、马耳树、毕钵罗树、紧柷加树、呵梨勒树、呵摩勒树、毘酰勒树……蒲桃、桃杏、梨柰……是等诸树无不备有。……是山王中所住众生,及诸草木充润光泽,犹如华鬘以水洒之,光色鲜净遂倍增胜。……是山王中多诸池流,清冷水满,生诸莲华,青黄赤白红紫等色,大如车轮。若取华时,香气普熏满一由旬。”[3]《大方广三戒经》卷上,《大正藏》第11册,第687页上—中。
若依此描述对比在万年县出现的庆山,确实有些类似的特征,比如醴泉滋润草木,树木出现“再叶重花”,发现“同茎合穗”的嘉禾,甚至北岸出现不合时节的瑞杏,这都与昙无谶描述的祇阇崛山有貌似的地方。更能佐证此山为祇阇崛山的,是之前张说《为留守奏羊乳獐表》中提到的庆山下母羊给獐麑喂乳,獐麑对母羊依恋,乃至“狎扰因依,动息随恋,如从所产”。这不正是昙无谶所讲的,在祇阇崛山中,“诸众生以佛力故,不为贪欲、瞋、痴所恼,不相茹食,共相亲爱如母如子”吗?这些似是而非的情节为佛教徒按照佛教教义重新阐释这次因地震而引发的山涌提供了现实的素材。
以前学界认为,敦煌莫高窟第321窟主室南壁的通壁经变,是服务于武周革命的《宝雨经变》。[1]史苇湘:《敦煌莫高窟〈宝雨经变〉》,《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83页。但是后来王惠民从该画榜书上认出20多个字的题记,否定了这一说法,认为是《十轮经变》。[2]王惠民:《敦煌莫高窟若干经变画辨识》,《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若从图像上来说,如果是《宝雨经变》,势必不能忽略菩提流志等人窜入的重要内容—“有山涌出”—祇阇崛山。表现祇阇崛山比较生动的,比如第420窟(隋)窟顶北披的灵鹫山,一座山就是一只鸟的头(鹫头);又比如第431窟(初唐)北壁《观无量寿经变》,也描述佛在灵鹫山说法。不过在321窟主室南壁的通壁经变中确实未看到描述庆云和圣山涌出的情景,或许从侧面也证明这并非真正的《宝雨经变》?
实际上,庆山并不容易造成,必须有碰巧的地震引发山涌,所以在整个中古时期,利用庆山来进行政治宣传相当罕见。对于同样一个自然现象,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解释,即便他们秉持的都是一样的理论,但是解释的结果却完全不同。比如杜光庭,一样是将新丰山涌解释为庆山,但是他认为这是李唐中兴之兆,因为李唐是土德,土地和山石变化是李唐的征兆,而非武则天的瑞祥:“文明元年,天后欲王诸武,太上乃现于虢州阌乡龙台乡方兴里皇天原,遣邬元崇令传言于天后云:‘国家祚水而享太平,不宜有所僭也。’天后遂寝,乃舍阌乡行宫为奉仙观。后庆山涌出于新丰县界,高三百尺,上有五色云气,下有神池数顷,中有白鹤鸾凤,四面复有麒麟狮子。天后令置庆山县,其诸祥瑞,具载《天后实录》,以表国家土德中兴之兆也。”[1]《全唐文》卷933《杜光庭·历代崇道记》。
在阴阳五行的复杂和顽固面前,武则天其实是非常被动的,她可以选取阴阳灾异理论里面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进行解释,但是却无法忽视相反的解释依然存在。在原有的理论之外,寻找新的解释,成为她的自然选择。推翻之前力主的庆山说,转而采用佛教所说的祇阇崛山,这一方面论证自己佛教转轮王的身份,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本土阴阳灾异说搀混不清的被动局面。
五、余论:《宝雨经》与阴阳谶纬之关联
从上述分析可知,《宝雨经》卷1窜入的,不仅有关于武则天以女身为帝的内容,而且把当时已经发生的、作为武周革命祥瑞的山涌(不管是阴阳灾异说的“庆山”还是佛教圣山“祇阇崛山”)和庆云也塞了进去。这两部分内容是相互关联的,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佐证和支持—“汝于是时受王位已,彼国土中,有山涌出,五色云现。……复有无量百千异瑞,我今略说。”山涌和庆云是为当时大众所热议和熟知的现象,武则天为此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宣传,居然在佛典《宝雨经》中出现,势必形成强烈的印象,即武则天的上台是于佛典有征的,不但有文字的记载,而且在现实中也已经得到验证。这与《大云经疏》相比,更加具体和明确,因而完善了武则天利用佛教宣传自己符命的理论系统。
作为主导翻译《宝雨经》的菩提流志,能够将带有强烈祥瑞色彩的内容恰当地融入佛典,并且利用佛典化解本土阴阳灾异说,是跟他本人的知识背景有密切联系的。赞宁《宋高僧传》描述菩提流志的学识云:“历数、咒术、阴阳、谶纬靡不该通。”[1]《宋高僧传》卷3《唐洛京长寿寺菩提流志传》,《大正藏》第50册,第719页下—720页下。睿宗《大宝积经序》也说他熟习“历数、咒术及阴阳等”[2]《全唐文》卷19《睿宗·大宝积经序》。。菩提流志本人出身婆罗门,熟悉历数、咒术、阴阳、谶纬,这就难怪他能够在所翻译的《宝雨经》中融合外来的佛教意识和本土的阴阳谶纬观念,进而服务于武周革命的政治宣传。这可视为是丝绸之路传入佛教文化又一次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抗和融合。
除了菩提流志外,来自印度和其他异域的梵僧、胡僧乃至俗人都在武周革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万年县出现山涌后,献状、指认涌出之山为祇阇崛山的“天竺真僧”,菩提流志在佛授记寺翻译《宝雨经》时同宣梵本的中印度王使沙门梵摩同[3]智升:《续古今译经图记》,《大正藏》第55册,第368、371页。,显然和菩提流志具有类似的种族和信仰背景。正如荣师新江所论,胡人在武周革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荣新江:《胡人对武周政权之态度—吐鲁番出土〈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校考》,第204—221页。菩提流志等来自天竺的僧俗也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本文为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人文学科整体推进重大项目“中古中国的知识、信仰与制度的整合研究”、2012年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2CZS020)和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2YJC77005)“纬学思想与隋唐时期的政治合法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