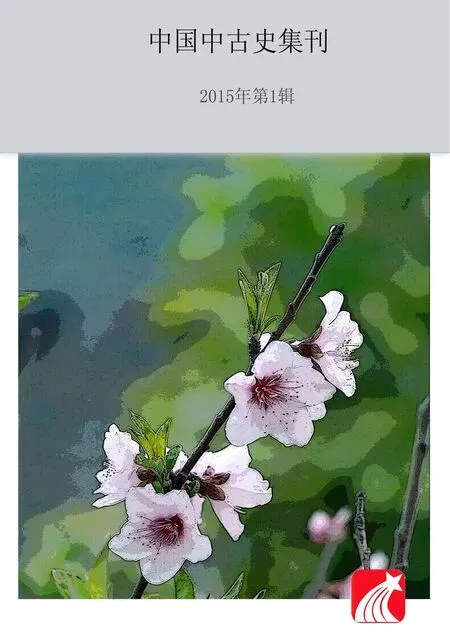汉唐间本草学史研究
——以神农家为主线
2015-01-30深圳大学历史系
肖 荣(深圳大学历史系)
汉唐间本草学史研究
——以神农家为主线
肖 荣(深圳大学历史系)
一、前言
提及古代本草学的发展史,自然会联想到《神农本草经》、陶弘景(456—536)、《新修本草》、陈藏器(约687—757)、《证类本草》、李时珍(1518—1593)等名家名著,一般也会认为是他们的层层积累,才逐步构建出现今完善的药物知识体系。从名家名著之知识积累来概括本草历史并无错误,只是过于简单。如本文即将集中进行研讨的汉唐八百余年间的本草学史,就具有一定的故事性。早期《神农本草经》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但本草学术的前景何去何从,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典型的一例,如享有大名的《吴普本草》参考“神农”的同时一再引述“黄帝”、“岐伯”、“扁鹊”、“雷公”、“桐君”等神人之说,主张本草世界应当长期多元并存。到后来,学术发展往神农家一边倾倒,陶弘景为之集注,唐代医官又再次加以修订,神农家走向中心,成为本草学问的代言人。究竟是何等机缘让后代医家为神农家倾付心力?其发展过程又是如何呢?参考现有的研究成果,冈西为人将陶弘景校定本草至《证类本草》之成书称为古代本草学术的隆盛期,认为此时诸医家关注药物起源、真伪优劣鉴别,内容上前后层层相因;[1]〔日〕冈西为人著,魏小明译:《中国本草的历史展望》,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0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4—136页。冈西为人撰述时间较早,贡献非凡,然今日阅读之,许多观点需加辨正。如他认为汉唐本草家注重起源与真伪辨别,金元以后则以药理学说为核心课题,原因在于金元本草家大多是临床家,对药物的关注集中药理治疗的层面,至于应用之外的博览涉猎,并非所长,中古医家出身道家或官吏,不以医术为业,知识点固多在药理之外。按自古至今之业医者,不管出身如何,必然要深悟洞悉药物之体性疗效,才不至于贻误生命,中古时期医家著作本草或层叠征引、辨析药物真伪,不如金元以后医家之直抵本质,然于药物性味实用的探索,并未见丝毫怠慢。中古时期医家与金元医家的差异,不过是论述的方式而已。廖育群指出陶弘景采用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无实”八性质及上、中、下三品两种不同方法并行分类,是源于他的仙道追求和作为医学家不同知识取向之间的调和;[2]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52页。廖育群文中虽没有就仙道追求或医家的知识取向展开详细分析,然而他的见解能切中要点。王家葵、张瑞贤则以《神农本草经》的文本为中心,梳理陶弘景和唐宋医家的承袭与增补[3]王家葵、张瑞贤:《神农本草经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192页。。此外,尚志均、傅维康等也充分评介诸本草著作的文献概况及学术成就。[4]尚志均于中古本草著作之辑复用功颇勤,在此基础上评介各著作的概况,所撰述的多篇论文,最后被结集成专书公开发行,见尚志钧编撰,尚元藕整理:《本草人生—尚志钧本草文献研究文集》,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72页。傅维康主编的《中药学史》(巴蜀书社1993年版)出版的时间相对较早,书中的第三、四章简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重要本草著作及学术成就。学者们角度各异的研究,已为本文全面梳理此时期本草学发展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本文试图结合学术背景,将多方面的信息整合为一,整理出本草学问显隐起伏的前进过程。
二、汉代的学术传统
如上文说到,魏晋时期《神农本草经》权威地位稍显薄弱,本草学多家丛处,指向不明。造成这一局面的,与汉以来的学术传统直接相关。按本草学起源于早期民众的不懈探索,犹如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最终造就《本草经》的传说所告示的,知识地不断积累,最终将形成本草药物学专书。因史料缺失,已经无法探明第一部本草专书究竟成于何时,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先秦时期,本草药物知识已有相当的积累。[1]研讨先秦时期的药物学知识时,学者们会提及《诗经》、《山海经》、《离骚》中记录的动植物信息,并指出它们与本草药物学之间有密切联系。对此笔者并没有任何异议。作为后来走入独立学科的本草学,必然历经由浅至深的累积过程。历史进入汉代后,本草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史记·仓公传》记载,阳庆传授仓公医术,用《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等典籍[2]这批典籍也就是《内经》编撰时所采纳的原始资料。详细可参见张灿玾主编:《黄帝内经文献研究》,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103页。肖荣:《〈内经〉是如何编成的?》,邢斌主编:《中医思想者》第1辑,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年版,第97—137页。,还包括一部未曾命名的“药论书”,同样的,仓公传授冯信医术时也是“论药法,定五味”[3]《史记》卷105《仓公传》。司马迁撰述本传时,基本依据仓公自述的“诊籍”,因改动较少,史料价值极高。。不同于其他医学典籍,药物书籍没有专称,内容如何,也已泯灭难以考知,一眼之下,又不免会让人产生药物学术水平低下、本草专书已早被历史淘汰的印象。为此,必须从当时医学界师徒知识传授的方式说起。
《史记·仓公传》载仓公的第一位老师公孙光曾对他说:“吾方尽矣,不为爱公所,吾身已衰,无所复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与公,毋以教人。”仓公听后回答说:“得见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传人。”意即淳于意,为仓公本名。他们师徒间的对话中都强调一点:避免将医药知识随便传与他人。仓公后来拜师于阳庆,《仓公传》说“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1]《史记》卷105《仓公传》。关于中国古代的禁方现象,可参见李建民:《中国古代“禁方”考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7年第68本第1分册。,禁方意也是不妄传予他人。类似的事例又见《后汉书·郭玉传》。郭玉的老师程高追寻涪翁多年才得到传授,而郭玉从小拜师,才顺利学到医术。[2]《后汉书》卷82下《郭玉传》。当然,本文绝不会因为几个例子而推断,两汉时医师师徒间都以极为严密的方式进行知识传授,但这毕竟能说明那个时代的许多医家,特别是学术成就较高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爱惜自身的学问,将学之不易的本事传授给有心人。这样传授方式一旦形成风气,必然影响到医药专书的传播局面。像刚才提到的《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等书籍,内容涉及一般的生理、病理、辨治的基本法则,理论色彩较强,颇能自成系统,普通读者不必受任何专业训练,细细读之也能从中了解医理的妙处,因此流传甚广,不受医界内部传授的限制。退一步说,医家即使想将其列入小范围的禁方之内,估计也力不能及。明显一例,莫如20世纪70年代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大量关于生理经络、脉法灸法的帛书,墓主却无任何迹象是著名医家。[3]马王堆三号的墓主,有学者认为是第二代轪侯利豨,也认为是利豨兄弟。详细可参见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傅举有:《关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墓主问题》,《考古》1983年第2期;陈松长:《马王堆三号墓主的再认识》,《文物》2003年第8期。至于药物书籍则不必然:第一,著作的行文古板,内容单调乏味,近似工具书,如从博物学的标准衡量,趣味性又远不如《山海经》之类书籍;第二,书中关于药物性味治法的叙述说明不易通懂,须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才能落实于运用,一般学人颇难企及;第三,全书架构简单,无法形成首尾相应的理论体系,难以满足读者的求知愿望。诸多天然条件减弱了本草学向外界散布的能力,加上医界内部以极为谨慎的态度进行知识传授,本草学著作容易变成医学界内部的学习数据,在从业人士的小范围内流传。与之相应的,本草学的著作形成专书的进度相对落后,相关的资料,极有可能附着于医理药方文献流传于世。如今日尚可见的张仲景《金匮要略》附有的“禽兽鱼虫禁忌并治”、“果实菜谷禁忌并治”之类章节,大概是原先本草部分的遗存,而《汉书·艺文志》之所以未曾著入任何本草典籍,原因应当是该类典籍“隐藏”在各家经典的“外经”之中。
本草学知识专业色彩浓厚导致普及程度相对有限,丝毫不影响学科内部学术水平地提升,因为其作为治疗疾病最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持,任何时代的医家都会为之倾付心力。早在先秦时期,《五十二病方》已呈现出医家颇具系统化的运用能力,入汉之后,学术水平有更大幅度的飞越。首先,在医家群体内部,先秦以来的知识积累持续发酵增长,药物运用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先秦,如同为出土文献之居延、武威汉代医简,远比《五十二病方》高明。而且另一个与医家即有交集、又略有不同的群体—方士,也活跃本草学的领域。
按所谓方士,即有方之士,他们往往各持一方技能,游说宫廷或王公大夫,说神仙修之可得、长生不死并非不可企及之类的鬼话。他们的方术形形色色,包括入海求仙、秘法候神、服食、炼丹、房中等,实际却都是仰食富贵人士、权充生计的途径。本草药物之学作为服食、炼丹的基本知识,也颇能触动富贵人士的长生登仙欲望,因此有人以之作为技能,打入富贵人士的门府。但本草药物学内容分散,于众多药物的用法难以一一深度展开,诸多条件使得自身吸引力难比丹药、房中等其他类型的技能。或许是缘于这样原因,王公贵族们对此兴趣相对较小,这类人才浮出历史水面的不多,而且还容易与侍医一类专门从事医疗事务的人士混为一谈。如《汉书·郊祀志下》记载,汉成帝在(前33—前7)继位的第二年就全面清理祠祀制度,其中就有让“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归家的举措[1]《汉书》卷25《郊祀志下》。,在当时,他们明确是被视为方士之流。他们主张药物有仙、俗之分,人们如果能适当服用其中的仙药,能延寿长生,甚至还可能实时升仙。同时,他们因熟谙众多矿物和动植物的品性、产地及用法等,能满足人们博物学问方面的探寻,又会被列为方士之内个性相对独立的一撮人。如前举的成帝罢方士与本草待诏归家,汉平帝元始五年(5)征天下能人,方术也与本草二类技能分开。[2]《汉书》卷12《平帝纪》。原文云“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应征到达京城的,达数千人之多。
总的来说,汉代时深切掌握本草药物学知识的,除一般医者之外,还有一批人数不多、水平精湛的本草专业方术人士。两者有很大的交集,但性质不一:前者主体思想在治病救人,后者则长生不死。他们共出一源,现实之中异质而同存。
然而,学术向前发展毕竟有着优胜劣汰的竞争,医者、方士不同取向的学术之所以能多元并存,恐怕要取决于两者各自的优势。医者的药物知识经从业者师徒世代地打磨,性味主治的认识必以深入精确,也必然能配合医理病理系统,作为日常医疗的实用,所以正统地位根深蒂固。相比之下,方士的本草学问也本于前代积累的药物性理知识,只是被有意地引向神仙长生之说以迎合王公大夫求仙、博物方面的口味,因而学理本身带着医学、方术、博物三重性格。或者正是由于方士的本草学的直接目的不在医疗,知识体系不受医者世代传承所带来的主观性影响,又有方术、博物等学问的加盟,知识体系相对开放,故能在医者与正统神仙方术的两个强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进而自立门户。如《汉书》说楼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1]《汉书》卷92《楼护传》。如《传》中言,楼护家世代为医,小的时候曾跟随父亲出入贵戚之家,可见医者、方士学问取向虽异,而现实中学习及掌握者或能多者兼通。,方士的本草学俨然有与医经、方术三足鼎立之势。
两股各有优势的本草药物学术力量在长时间的发展进程中,最终都孵化出相应的著述。诚如前文所讲,医者的本草药物学主要在师门内部传承,内容相对少为人知,如汉末大医家张仲景自述《伤寒杂病论》依据的文献时,只是含糊说是《药录》[2]现今《伤寒论》的标点本多数将张仲景自序的这一段标点为“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事实上这样的标点存在诸多不通之处:首先,任何汉魏目录著述未曾见《胎胪药录》一书;其次,“胎胪”与“药录”前者指妇儿、后者为药典,无必然联系;再次,“胎胪”专书见《太平御览》卷722引《张仲景方序》、“药录”专书可印证《隋书·经籍志》。故而正确的标点应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对此,学者已多辨析,较早的如19世纪日本著名汉医大家森立之。可参见〔日〕森立之著,郭秀梅、冈田研吉、加藤久幸校点,崔仲平审订:《伤寒论考注》,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作者、内容、渊源无从考起,依然属于师徒内部世代相传的文献资料。其能考知,大概就是前文引述《吴普本草》时提及的“黄帝”、“岐伯”、“扁鹊”等,此时医药从业者内部可能尚未有本草药物专书流传。而方士本草学自开始即融合神仙、博物诸说,同时又照应游说王公大夫的用途,无论学术体系内部,还是向外传播的动力,都超过了医学从业者的药物学。方士们长时间的学问积累,汇聚成一部极具分量的专书—《神农本草经》。
该书条文的主体部分采自医学著作[3]近来医史学者喜欢称《神农本草经》非一人一代的产物,是先秦以来经验累积而成。论断虽无误,而前提却值得怀疑。任何医药典籍,必然都是先秦以来逐次形成,《神农本草经》无法例外。问题在于,前秦时期尚未见本草的称谓,被我们称为《神农本草经》这部书,乃汉代以本草学术为业的方术之士根据传之久远的医药学知识编纂而成的,之前并不存在该书雏形,更不存在历代文本上的层层积累。,之后又融入相应的神仙及博物文字,首尾完整,体系严密,历经各时代的层层传抄,至今大体面貌仍能被辨认。如书的文本所示,编撰者有意将诸药物分成上、中、下三大类:上者应天,服之轻身益气;中者应人,服之遏病补虚;下者应地,服之除寒热邪气,基本宗旨是在阐明服食求仙的可行性。由于知识理论与医者药物学同源,书中对本草性味主治的叙述十分详明。以熟知的人参为例,条文云:“味甘,微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一名人衔,一名鬼盖。生上党山谷。”[1]尚志钧校注:《神农本草经校注》卷2 《上品药》,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45页。
其中味甘微寒,主补五脏之类,乃医者组方治病的理论依据;久服轻身延年,乃神仙家之言;别名、生上党山谷则可归入博物学的范畴。对于神仙家而言,博采诸家之长,精准阐述各本草药物之药理乃取信于人的第一步,有了这一步,凌驾于世俗日常医疗之上的仙俗分类及服用成仙的提法也就能顺理成章。加上条文中性味、主治地叙述不必受某一师门所持成见的限制,视野开阔,取材广泛,故相对精确,可与其他医学经典向配合,共同运用于实践医疗;同时医药、神仙加上别名、产地等信息,又足以响应人们的探求各类自然物体的需求。《神农本草经》的知识面确实能有效照应到神仙、医药、博物三家,且独立一格,学术成就自不待言。
回到本草药物学术的内部,《神农本草经》成书后,想必会让医疗从业者惊讶不已,因为一部力求表述求仙思想的药物著作却精准、全面地阐述各种药物的品性用途,以至于可以直接指导实际医疗。同时代的医者们是否参考之、运用之、甚至诋毁之,因限于史料缺略,这些可能产生的反应,几乎无从考知。可提供一丝线索的,大概要属该《经》的第1卷《序录》。《序录》中除了开篇几个上、中、下药分类的条文外,基本都在述说药物的配制、品性、剂量、产地等医者着重关注的方面,与正文各条文一再强调的服用长生不死的主旨颇不相符合,或有可能较早医家综合总结《神农本草经》思想内容、进而求取运用的产物。
无论事实如何,《神农本草经》作为本草药物知识的时代总结专书,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如何有效的接受及运用,正考验着后来的医药从业者。
三、新时代的学术局面
陶弘景注《神农本草经》说“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1]陶弘景编,尚志钧、尚元胜辑校:《本草经集注(辑校本)》卷1《序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神农本草经》之最终成书,大概就是东汉时期。[2]历代都有学者对《神农本草经》的成书时间发表看法,相对集中的是认为成书两汉时期,其实古早以前陶弘景言之已明。而且,后代所谓的《神农本草经》缺乏其他版本比对,不过特指陶弘景见到的东汉时人编订的这部典籍。随着时代的变迁,《神农本草经》影响力越发集中在医学领域。其原因大概是汉末道教兴起,传统神仙方术被吸纳到道教的庞大体系之下,作为跨越医药、方术的本草学,只能作为相对实用的服食、炼丹方术的理论前提,重要地位较为有限,事实也证明,魏晋之后,已再没有人单以本草技能而进入宫廷者;在博物学方面,本草学本只是涉及可为入药的物类,数量有限,叙述的内容以性味医疗为主,专业性较强,且枯燥乏味,难在博物学科上占据主流。原本在汉代方技门类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本草学,在魏晋时代已失去生存发展的空间,脆弱的独立性不复存在。
只是方士们在本草上的有力探索,并不会随着学问的独立性淡去而丧失意义,他们关于药物性味主治等方面的总结,丝毫不比医学从业者逊色。在此学术背景下,《神农本草经》只有回归到医学理论界内部发挥功用。
而此时医学理论界内部,也出现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局:其一,秦汉以来多线指向的医学文献,在黄老学强大凝合力的统合之下,形成了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经典—《黄帝内经》;[1]肖荣:《〈内经〉是如何编成的?》,邢斌主编:《中医思想者》第1辑,第97—137页。其二,经汉末张仲景的改造,医理辨证与原本复杂方剂运用亲密无缝地结合起来,可为医学学者共同依仿的对象,原本师门之内小范围的所谓禁方传承,显然已缺乏现实意义。历史悠久的医学理论在《黄帝内经》及张仲景方的推动下,疾速往大一统局面的方向发展。如众所周知,《黄帝内经》属于基本医理、张仲景方为方剂运用,二者如要最大范围产生作用,尚须一套药具有普遍指导能力的药物体系的支撑。同时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不囿某一师门之成见,多方采撷,流传较为广泛,多种优势使得它超越诸多师门流派内部的药物本草典籍,一跃成为与《黄帝内经》、张仲景方相互配合以成新局的天然选择。如陶弘景自序《神农本草经集注》说:“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华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须。”[2]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辑校本)》卷1《序录》,第3页。
《神农本草经》被后世医家追溯为本草学历史上传承久远的正统著述,成书时代相近的《桐君采药录》、《药对》等不过被视为补充作用的旁支,强烈的对比正说明现实中的《神农本草经》已经与《黄帝内经》、张仲景方一同走进医学学术的核心地带。它们三者犹如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共同组成具有稳固结构的岐黄学理体系,各自之间又相辅相成,在营构汉魏大一统走势的同时,也造就出自身的学术经典地位。
仔细分析又可发现,它们三者因文本来源及学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在自身医理、医方、药理小范围的领域内产生的影响也稍显不同。《黄帝内经》整合的对象是先秦以来指向各师门传承的不同医理文本,因以黄老学虚无同一超越精神为指导,诸家文本融汇其中,后来医家之学习,必然绕不开它的基本学理叙述及高超掌控能力,故为万世不易的“医家之宗”。张仲景则以《黄帝内经》基本理论的核心,将前人行之有效的医药组方引向岐黄学术的认知体系之下,而且诸采用之方组合严密、理法可依,经得起历代医者的层层验证,乃岐黄学术史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医圣”雅号也当之无愧。相比之下,本草药物品类繁多,名号、产地、乡间经验、医家实践等条件都影响着本草药物性味主治阐释的深度及广度,《神农本草经》能博采众家之长,毕竟收录有限,药理阐述,难以一时深入涉及,因此,自成书后,虽可作为诸家本草药物的杰出代表作而与《黄帝内经》、张仲景方并列为经典,却无法享有《黄帝内经》和张仲景方一般的历史光环。在时间稍晚的医家看来,“神农”似乎只是作为本草诸家中的最为显眼的一家,而不是凌驾诸家之上的经典著述。如吴普着本草专书时,既以《神农本草经》为主要参考,同时又列出“黄帝”、“岐伯”、“扁鹊”、“雷公”、“桐君”,甚至还有同时代“李譡之”等著作。这里可随机举《吴普本草》的条文说明之:“桔梗:《神农》、《医和》:苦,无毒。《扁鹊》、《黄帝》:咸。《岐伯》、《雷公》:甘,无毒。《季(李之误)氏》:大寒。叶如荠苨,茎如笔管,紫赤。二月生。”[1]吴普著,尚志钧辑校:《吴普本草》,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8页。
吴普提到的《黄帝》、《岐伯》、《扁鹊》、《雷公》未必都是出自某种本草学专书,《汉书·艺文志》云:“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2]《汉书》卷30《艺文志》。《黄帝》、《扁鹊》诸等,或是各自典籍中的本草学部分。但不管表述形式如何,黄帝、岐伯、扁鹊各派也都是医道正统,他们的解说各异,同一药物之下,药性就可能有苦、酸、甘诸说。繁复不一之多家叙述吞没了《神农本草经》作为经典著作本来应当享有的重磅声音,如果一定要给此时的学术局面下一简要概述的话,那么现今用于形容国际局势的“一超多强”就再合适不过,“一超”指的是神农家,“多强”则是黄帝、岐伯、扁鹊诸家。
《神农本草经》之所以无法永久保持本草学界的经典地位,恐怕还缘于它神仙长生的主导思想。作为一部方士整编而成的著作,神仙长生之说本无可厚非,只是当影响力转向医学内部时,就显得不合时宜。《黄帝内经》早已明确指出“拘于神鬼者,不可与言至德”,张仲景所用之方也基本没有涉及神仙伏鬼之术。《神农本草经》满文长生不死,必然难以取信于深具岐黄学术学养的医者。当然,深谙岐黄之道的医家们不会因为神仙长生说就摒弃《神农本草经》,如吴普所著本草专著就没有提及神仙说,但它要获得医学界的一致认可,还是必须遵照岐黄学理的路数。
至此,我们也颇能预测到,在未来的学术发展进程中,《神农本草经》如要继续保住自身的经典地位,必然要有所改进。改进的路向大体有二:其一,在原先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可行的形式,将诸家学术及新进的经验再次吸纳进来,整编成新一代的《神农本草经》;其二,抛弃原先文本中的神仙长生空乏论说,文本叙述尽量往医学本位的方向看齐。第一个路向是主线,直接决定改进是否成功,第二个路向相对次要,是改进是否成功的辅助说明。可以想象,如果缺乏有效的改进,晚后具有总结性的本草学专书甚有可能会超越其上,成为时代的新经典。
四、陶弘景集注《神农本草经》
可惜的是,后进的高水平本草学专书并没有浮出水面。由魏到晋、再由晋入南朝,本草药物学领域不时有新作问世[1]如《隋书·经籍志》收录,《吴普本草》、《李譡之本草经》、《秦承祖本草》、《王季璞本草经》、《宋大将军参军徐叔响本草病源合药要钞》、《徐叔响等四家体疗杂病本草要钞》、《云麾将军徐滔新集药录》等,因标出作者名称,可知就是魏晋至刘宋时人的著作。只是,这些著作早已亡佚,著者、著述的确切情况,全然不可考见。至于《隋志》,还有新、旧《唐志》著录的那些未曾标明著者的本草著作,更无从确定真实成书时代。然而根据这些线索,我们还是可以推知魏晋刘宋间本草学著述数量不在少数。,但似乎都是匆匆过客,未曾留下深刻足迹,以《神农本草经》为领头的多家并存学术局面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缓缓前进。真正将本草药物学推向新高度的,是要到南朝齐梁时,历史主角是陶弘景。
陶弘景一生勤奋用功,建树多端,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为道教教义,一为医药学理。[2]陶弘景之学业及在道教学、医药学的成就,前辈学者已有充分地探讨。如〔日〕石井昌子:《道教学的研究:以陶弘景为中心》,东京国书刊行会1981年版;〔日〕麦谷邦夫:《陶弘景的医药学与道教》,吉川忠夫编:《六朝道教的研究》,春秋社1998年版,第313—330页;王家葵:《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2003年版; 程乐松:《即神即心:真人之诰与陶弘景的信仰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皆可为参考。在医药学术的领域,他秉承家学,潜心修习,实践水平高超,所纂述的《补阙肘后百一方》、《本草经集注》都具有极为顽强的学术生命力。[1]时至今日,这两部的整体样貌还能被保存下来,甚至还能为现代医疗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意见,而与它们同时的医著基本亡佚殆尽。《补阙肘后百一方》之贡献在于医方一类,与本文主题无直接关系,姑且不论,本文重点要讨论的是《神农本草经》之成书在本草学史上的伟大意义。
此时的陶弘景已归隐山林。他说自己在茅山上吐纳修炼之暇兼修医术,对于本草学问,是“览本草药性,以为得圣人之心”[2]《本草经集注(辑校本)》卷1《序录》,第1页。,所以有意要撰述之。所谓“得圣人之心”,直观的理解是明晰学问之内核,对学科学理有高屋建瓴的见识。其实只要了解陶弘景所接承的学术现状,即可知道他这样说的另一层含义。当时传承已久的本草经典《神农本草经》“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卅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多少”[3]同上书,第3页。,几无可以信任的版本流传于世。造成这种状况的,大概是医家们为了各自学理说明或医疗实践之用的任意裁割。医家们的做法本无可厚非,采纳百家之长以为己用,乃是岐黄学术千古不易之王道,只是当关注点转向本草领域,一部原本为集大成的经典之作却被弄得真本丧失,只剩下多方裁割之后的断壁残垣,不免让人感叹现实的学术界正统学问已经沦丧,水平集体下降。在此背景下,陶弘景道出“得圣人之心”,大概也在于表明自己重振神农学说,引导本草学往秩序化方向发展的学术责任感。
要重振神农学术,他首先还是要正视《神农本草经》的沉落局面。试想如果文本永久停留于汉魏阶段,缺乏义理上必要的自我更新,《神农本草经》叙述本草药物的广度、深度如何能满足晚后社会复杂的医疗活动?现实中,魏晋以来许多医家对《神农本草经》缺乏应有的热情,他们或曾大篇幅参考《神农本草经》的经典文本,但不会下意识去整理拓展该文本,使之成为医疗活动的必备手册。或根据前代文本及自己的观察研究,独立撰成本草专著;或剪裁《神农本草经》等经典文本,以表达自己的医理思想;还有相当一部分医家延续汉魏学术风格,在经典医理、医方指导下研讨本草药理,著作上则是将本草药物的使用附在医理、药方之后。[1]典型的一例,如《小品方》十二卷的尾端专门留有“述用本草药性”一卷,见陈延之撰,高文铸辑校注释:《小品方·目录》,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小品方》此版本乃依据《小品方》残本及中古多部大型方书的引文辑佚而成,目录部分为残本所有,故相对完整。“述用本草药性”位列十二卷的第十一卷,第十二卷为“灸法要穴”,之后有文字云“右二卷,连要方合十二卷,是一部,为一帙”。可见在原书中,本草与灸法既与医方连为一体,也独立成帙,形式与汉魏医家著述一致。这几种学术表述形式表面上都取材于《神农本草经》,实际上却貌合神离。陶弘景的一段叙述,无意间道出《神农本草经》的尴尬地位:“自晋世以来,有张苗、宫泰、刘德、史脱、靳邵、赵泉、李子豫等,一代良医。其贵胜阮德如、张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稚川、蔡谟、殷渊源诸名人等,并亦研精药术。宋有凡此诸人,各有所撰用方,观其旨趣,莫非本草者。或时用别药,亦修其性度,非相逾越。《范汪方》百余卷,及葛洪《肘后》,其中有细碎单行经用者,所谓出于阿卷是。或田舍试验之法,殊域异识之术。”[2]《本草经集注(辑校本)》卷1《序录》,第24—25页。
在陶弘景的语境下,“药术”、“本草”都是指代《神农本草经》。根据他的细致考察,魏晋以来诸多名医遣用药物的方法,都与《神农本草经》的学术旨趣相吻合,也就是说,众多医家之遣用药物各有法则,理论精神约同《神农本草经》,但细节层面略多差别。医家这是扬弃《神农本草经》诸多不合时宜的理论述说,求取经典与实践相切合。而且陶弘景也提到,医家使用的不少药物《神农本草经》未曾收录。《神农本草经》文本的深度和广度,已经与现实的医疗实践脱节,如再不有效地改进,经典地位岌岌可危,本草学世界也将彻底失去领军式的著作。
陶弘景志向远大。他之用功于本草学,着力点是推举垂垂老矣的《神农本草经》。为了让自己的努力得到重视,他必须强化或者说是神化《神农本草经》的正统地位。他说自己坚信本草学术是始于远古时期的神农氏,由于当时尚未有文字,本草知识是借口耳相传流传下来,至文字产生伊始,《神农本草经》就著录成书,与《素问》一样,都属最早一代的经典文籍。自成书之后,《神农本草经》又经历代医家删补修饰,实用方面意义重大:“春秋以前及和、缓之书蔑闻,道经略载扁鹊数法,其用药犹是本草家意。至汉淳于意及华佗等方,今之所存者,亦皆修药性。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1]《本草经集注(辑校本)》卷1《序录》,第24—25页。
如前文已引的文本,陶弘景基本确信现行流传的《神农本草经》是“仲景、元化等所记”,与神农尝百草古老传说相配合的古朴面目相去已远,但为了提点该经的重大意义,不得不追溯传承之前传承已久的本草学问,说医和、医缓、扁鹊、仓公、张仲景都自觉依据本草学体系处方医疗。按先秦时期医家的医疗实践所依据的本草学理论,与后来成书的《神农本草经》同属一源,自可视为一家之说。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神农本草经》只是后世成书的诸多本草学著作之一(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无法等同前秦以来指向多端的本草学问。陶弘景含糊其辞,有意绕开本草学界多家并存的现实,将本草学与《神农本草经》混为一谈。根据他的思想逻辑,《神农本草经》得自远古,乃本草药物学界之根本所在,只因为历代各自传抄,导致错漏百出,版本众多,重新进行整理势在必行。
《神农本草经》面临的现实困境还远不只是错漏和版本众多,最要害之处是怎样将后进的本草知识收录其中,以求挽救作为日常医疗本草药物理论依据的学术影响力。陶弘景认准《神农本草经》作为整合乱局的主线,推导该经伟大的正统地位,自然不能将这一层干系直接挑明,但他十分清楚,眼前最急切的任务就是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极大地改变旧本《神农本草经》的落后面目。因而他在指出目前传本存在众多错误之后,立即说道:“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卅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 世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并此序录,合为三卷。虽未足追踵前良,盖亦一家撰制。吾去世之后,可贻诸知音尔。”[1]《本草经集注(辑校本)》卷1《序录》,第3页。
态度非常明朗,即分成两个途径进行整理:其一,进“名医副品”三百六十五种,使本草数量翻了一番;其二,详细注明实用、产地及仙道用法等本草药物条目的必要信息。所谓“名医副品”,现代学者存在争议,有的认为是之前独立成书的《名医别录》,有的认为是陶弘景集注《神农本草经》之后,将引述的诸名家的文本集合而成的[2]持前一种观点的,如廖育群:《岐黄医道》,第148—150页;持后一种观点的,有尚志钧,见陶弘景集,尚志钧辑校:《名医别录·后记》,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319页。,从行文的基本文义讲,即是指那些历代名家施用却不见于《神农本草经》的药物品类。陶弘景将总数等同于原先的条目引录进来,原经格局已被打破,加上综合前代医家以及自身的见解作为注释,原先的文本所占比例大大减少,论述内容所涉及的层面相应更为多元,面目为之一新。可任举一例说明之:“水银味辛,寒,有毒。主治疥瘙,痂疡,白秃,杀皮肤中虫虱,堕胎,除热。以敷男子阴,阴消无气。杀金、银、铜、锡毒,熔化还复为丹。久服神仙,不死。一名汞。生涪陵平土,出于丹砂。畏磁石。今水银有生熟。此云生涪陵平土者,是出朱砂腹中,亦别出沙地,皆青白色,最胜。出于丹砂者,是今烧粗末朱砂所得,色小白浊,不及生者。甚能消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还复为丹,事出《仙经》。酒和日曝,服之长生。烧时飞着釜上灰,名汞粉,世呼为水银灰,最能去虱。”[1]《本草经集注(辑校本)》卷2《序录》,第130页。
由于格式限制,上引的文字连成一片,难分彼此,其实在陶弘景的原著里,“味辛,寒”等文字用红色笔写成,属《神农本草经》原文;“有毒”、“以敷男子阴,阴消无气”等是墨书,乃《名医别录》;“畏磁石”以下是小字,为陶弘景注释之文。红字部分只是关于该种药物性、味、主治、产地的简要介绍,只有墨字、小注加入后,性味异说、是否有毒、主治别用、古今产地、现今出产、恶畏关系、现实使用、仙道用法,甚至具体医案等随之而至,经中的内容才充实许多。当然,那些由陶弘景加入《神农本草经》的条文,红字部分不存在,就连性味主治之说,也都是由墨字写出。而当彼此相对独立的各个条文汇聚成全书后,明显可以看出,陶弘景的整理使得《神农本草经》之文本篇幅以及具体论述的广度和深度,都已远超之前。
陶弘景称自己的整理工作为“集注”,但实际之举措远非“集注”二字可以概括清楚,因为所谓“集注”,是不会大面积将他家学说引在经文之中,更不会特意将原先不属于该《经》的条文罗列进来,并入经文的核心内容。他所开展的工作更像是以《神农本草经》为原则指导,重新整合当前本草学术的诸家之说,是依托于《神农本草经》之上的再创作,路径类同《神农本草经》原先之成书。事实上,陶弘景在序文里“虽未足追踵前良,盖亦一家撰制”一句,早已清楚表明自己的撰述足以成就一家之言,而不是仅仅作为原先经典的注释本传世。
按当时的学术界,神农家已日益走向没落,多家杂驳的无序局面呼之欲出,陶弘景本着承前启后的学术责任感,扛起神农的旗号,无疑为古老的神农本草家注入一支效力卓著的强心针。虽然我们十分清楚神农家只是他的重整本草学术的标杆,并非学理叙述的标准模板,但他客观上的努力,使得神农家以新鲜姿态再次展现于本草界,学术生命得到长足延续。
陶弘景原本可以隐去神农家的名号,自立一家之言,博取本草学大师地位。他之所以如此青睐神农家之言,一方面,是托神农之号著书立说,更容易获得认可,另一方面,恐怕是与他虔诚的道教信仰有关。他中年挂朝服于建康城门,归隐山林,大多数著作是之后写出。《神农本草经》也不例外,是他“在茅山严岭之上”,修习道法之余的产品。[1]《本草经集注(辑校本)》卷1《序录》,第1页。由于抱着强烈的修仙得道的宗教情感,他十分爱重《神农本草经》原先具有浓厚方术色彩的上、中、下药分类方法,说:“今案上品药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势力和浓,不为仓卒之效,然而岁月将服,必获大益,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天道仁育,故云应天。……中品药性,治病之辞渐深,轻身之说稍薄,于服之者,祛患当速,而延龄为缓,人怀性情,故云应人。……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恒服,疾愈则止,地体收煞,故云应地。”[1]《本草经集注(辑校本)》卷1《序录》,第7—8页。
长生、延龄、救病之分等,陶弘景语气坚定,绝无放松的可能,《神农本草经》与他的求仙思想相通。但从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试图进一步从服用效果的层面去提取该分法的药理依据,如他肯定上品之仙药能轻身益气,不老延年,又说此类药物能“遣疾”,愈病之后,生命且能延伸;中品治病的性质逐渐加深,长生益年的效用减薄;下品毒气猛烈,专用于攻击病症所用,不能长期久服。在具体条文的注释里,也以叙述药物的药用为主,没有把仙道中的用途当作重点。陶弘景著书立说似乎游离于神仙与世俗的本草药物学问之间。他选择《神农本草经》,确实能有效照顾到这一点,因为言之凿凿、仙俗上下分等、点到即止的神仙说以及治病求效的世俗用法在这里巧妙地混合为一。
平心而论,汉代时本草学独立一家,学术性格与方士求仙同类,魏晋之后,影响转向医学,因而贯穿其中的神仙方术因素理应要被逐渐清除出去。然而作为南朝学术代表的陶弘景还是重蹈神仙之说,使本草学之方术性格不减弱反而被强化。
五、唐代新修
站在后来者的高度,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评判陶弘景的一些不足,但一定不能否认在客观历史环境之下,陶弘景重新整合本草学问的意义及水平。事实证明,《神农本草经集注》成书后颇受医家重视,有多个版本流传于世。[1]如《隋书·经籍志》记载,置于陶弘景名下的,即有《陶隐居本草》、《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太清草木集要》。在紧接的历史发展中,本草学发展动向如何,由于史料缺乏,我们知之甚少,但有理由相信,以《神农本草经集注》阐述药物之广度与深度,一定能打动诸医家,陶弘景的整理工作,也必定能得到大面积的认可。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唐代前期官方准备重新整合本草学术时,毫无疑问地选择《神农本草经集注》作为主体文本。
唐代新修本草经是发生高宗显庆年间,此时社会历史已有翻天覆地的改变:长时段的南北割据已经结束,国家再次走向统一。强烈的社会政治转变也深刻影响着医药学术的发展。其最为关键的,莫过于新时代学术重心地迁移。在之前南北分裂的年代,南方医药学术的发展远远超过北方,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医药著作,基本上都受南方地域性因素的严重约束,进入统一时代后,北方一跃成为全国医药学术的重心,前代医药著作许多叙述已多不合时宜之处。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下,流传了一百余年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也暴露出诸多缺陷。如唐代人说:“昔陶弘景以《神农经》合杂家《别录》注 之,江南偏方,不周晓药石,往往纰缪。”[2]《新唐书》卷104《于志宁传》。
说这句的是于志宁,背景是回答高宗皇帝关于是否有必要重修《神农本草经》的疑问。[3]以“纰缪”的描述《神农本草经集注》,也见于《旧唐书·吕才传》,其云“时右监门长史苏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谬”。参见《旧唐书》卷79《吕才传》。他点出的“江南偏方,不周晓药石”,正是陶弘景编撰时所无法避免。陶弘景所处的时代南北药物流通不畅,他自己也曾清楚说到“自江东以来,小小杂药,多出近道”[4]《本草经集注(辑校本)》卷1《序录》,第32页。,北方药物确实接触较少,认识面度也相对有限,而且他以一己之力来阐述种类如此众多的药物,发生错漏的概率更大。[1]唐代孔志约为《新修本草》作序,说陶弘景“时钟鼎峙,闻见阙于殊方;事非佥议,诠释拘于独学”,判断可谓公允。原文见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新修本草(辑复本第二版)·序》,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基于陶注《神农本草经》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唐代前期的医官立意进行修订。这次修订不同于以前时代医家之“私修”,而是依托于国家官方机构集体创作。[2]可参见范家伟:《〈新修本草〉与唐代本草学》,《大医精诚:唐代国家、信仰与医学》,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73—112页。孔志约序《新修本草》有简要概述:“朝议郎行右监门府长史骑都尉臣苏敬,摭陶氏之乖违,辨俗用之纰紊。遂表请修定,深副圣怀。乃诏太尉扬州都督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无忌、太中大夫行尚药奉御臣许孝崇等二十二人,与苏敬详撰。……于是上禀神规,下询众议;普颁天下,营求药物。……《本经》虽阙,有验必书;《别录》虽存,无稽必正。考其同异,择其去取。铅翰昭章,定群言之得失;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撰本草并图经、目录等,凡成五十四卷。”[3]《新修本草(辑复本第二版)·序》,第1—2页。
朝廷重臣牵头、国家最高医疗机构参与、各地政府奉诏提供药物信息,种种优越条件都暗示后来的读者,这次修订活动将在学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事实果真如此?可看看医官们的具体修撰。
医官们的修订工作总的说来可以分成三个大方面:其一,绘图;其二,注释;其三,新附条目。本草药物著作附上图案,使诸药物形象生动,易于辨认,而所谓注释,即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文本之中加入小字按语,作为辨正、深化或增补原文之用,其分布遍及陶弘景原先的《序录》及书中的大多数条文。可随机举一例说明之:
半夏味辛,平、生微寒、熟温,有毒。主伤寒寒热,心下坚……五月、八月采根,曝干。
射干为之使,恶皂荚,畏雄黄、生姜、干姜、秦皮、龟甲,反乌头。槐里属扶风,今第一白者为佳,不厌陈久,用之皆汤洗十许过,令滑尽,不尔戟人咽喉。方中有半夏,必须生姜者,亦以制其毒故也。
谨案:半夏所在皆有,生泽中者,名羊眼半夏,圆白为胜。然江南者,大乃径寸,南人特重之。顷来互相用,功状殊异,问南人说:苗,乃是由跋。陶注云:虎掌极似半夏,注由跋,乃说鸢尾,于此注中,似说由跋。三事混淆,陶竟不识。[1]《新修本草(辑复本第二版)》卷10,第151—152页。
第一段乃《神农本草经》及《名医别录》内容,第二段是陶弘景集注,第三段就是唐医官的新注。在文中,唐医官指出陶弘景根本就不知道由跋、鸢尾与半夏之间的合理区分,导致注释时指鹿为马,错漏百出。他们还注出半夏的生长地,说形貌圆白者为胜。加上附有的该药物的图案,半夏形貌清晰明了,比陶弘景旧本可靠不少。推至全书,《新修本草》的文本确比《神农本草经集注》更上一层楼。当然,《新修本草》中除了陶弘景原本收录的730种药物外,还多增入120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附条目。新附条目内容表述与其他条文保持一致。随举一例:“白药味辛,温,无毒。主金疮,生肌,出原州,剪草,凉,无毒。疗恶疮、疥癣、风瘙。根名白药。
三月苗生,叶似苦苣。四月抽赤茎,花白,根皮黄。八月叶落,九月枝折,采根,晒干。新附。”[2]《新修本草(辑复本第二版)》卷9,第138页。
前面叙述药物性味主治、毒性产地等,后面则就药物形貌质量产地等信息的进一步辨析,结构基本延承自陶弘景。有这些新鲜条文加盟,《新修本草》面度更广,更显示出学术方面的优胜性。
如再仔细归纳,《新修本草》可表彰之处还有不少,那么医官们获取进展的重点所在何处呢?只要细细思考即可得知,他们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来自技术性的层面,即包括绘图、辨正药物形貌、指出出产地、增加某些实用方法等,至于本草药物之施用原则、诸类常用药物之性味毒性主治的基本状况等,则难有突破性的见解。其缘由,或是《神农本草经集注》时,用药原则及诸常用药物之性质效用已有充分之覆盖,学术高度难被超越,作为承接伟著之后的《新修本草》,只有在横向的广度及精确程度上求取突破。如书内容说展现出来的面目,药物种类从原先的730种增至850种,旧本的诸多错误得以辨析,实用治疗方法的信息略多增加,《新修本草》在全面涵盖《神农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拓宽了本草学之视野,使得本草学之叙述清晰可靠。因而无论形式还是实际运用,它都是《神农本草经集注》的升级版,面目功能扩大而且完善,是全面超越《神农本草经集注》的时代新作。而且可喜的一点是,在升级过程中,参加编修的医官们有意识去摆脱神仙道法思想的羁縻,叙述药物性质效用时就事论事,绝少掺杂神仙之说,导引本草学术向医学学科本位回归。当然,也不能过度拔高《新修本草》的意义,毕竟作为时代升级版,它的学术主旨、思想要素与旧作相去不远。
《新修本草》成书之后,凭借着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全国的范围内传播开来,一直以来“一超多强”的本草学界最终迈进了《新修本草》“单一集权”的时代。而作为已经全面被超越的旧版本,《神农本草经集注》随之淡出历史舞台,逐步走向亡佚。
至此,由方士创立、陶弘景全力推举、唐医官修订推广的神农家学术终于成为本草药物学问的核心所在,汉唐间的本草学历史画上完美的句号。
六、结论
时处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谈及传统药物学,多数会把《神农本草经》列在崇高的位置,认为它是本草学术不祧之祖,地位一直居高不下。如上文对本草学早期历史的梳理叙述,是多个看似偶然的机缘将神农家推到本草学问的中心:如果没有汉代方士的关注和编修,《神农本草经》不会独立成为专书;如果没有医学走向一统的潮流,医界可能不会重视具有统合意义的神农家言;如果没有陶弘景的再次整理,《神农本草经》可能沉沦入土;如果没有唐医官的整编和推广,《神农本草经》影响面可能不会如此广泛。汉唐时期本草学有着显隐起伏的丰富经历。这不免也将我们引向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关系的老话题上:医药学术对于本草统一局面的内在需求以及后来者对前代学术的超越属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神农家的出现及一步步走向学术中心则是纯属偶然。
用必然性及偶然性来解读汉唐间本草学,恐怕又略过玄虚,如上文所梳理当中过程的若干重大关节,即汉代方士、陶弘景、唐代医官以不同的方法目的整合神农家学说且产生不同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而且这些重大关节的前因后果,如带有浓厚方术色彩的《神农本草经》被推到汉魏学术中心之后逐渐式微、陶弘景既延续神仙又以医药学术为本位、唐代医官批评严厉而实际改造有限,等等,也和其他领域的历史过程一样具有规律性与故事性,颇值得从辨析源流的角度来进行细致梳理。
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关于医学学术史叙述,多数是本着经验
理论总结的目的,落实点是历史上医家、医著的医法可为今日医疗借鉴之用,相对忽略考辨医家、医者之间学理传承的渊源流变。其实,从历史源流来研讨医药理论的发生、发展,又何尝不能为深入解读、运用经典医籍所传承之经验理论提供帮助?如本文审视汉唐本草学之源流,可让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医家是立足现实,从深度及广度求取学术上的突破,也至少让我们明确要用批判继承的眼光来参阅各类本草名籍。医药学术史的叙述方式一定不会局限于总结经验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