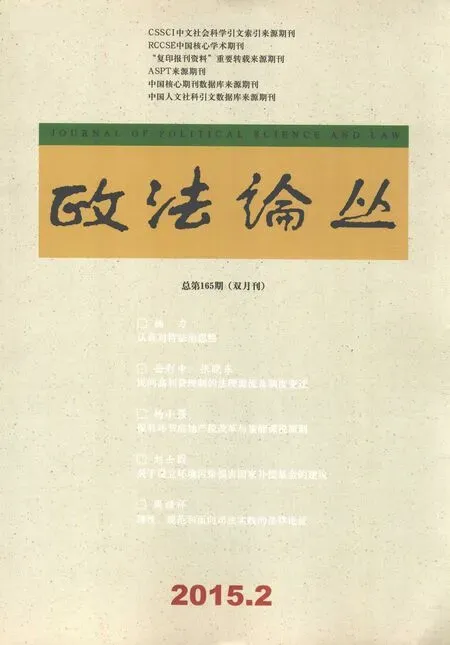疏离与回归:女性继承权的制度建构*
2015-01-30王歌雅
王歌雅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疏离与回归:女性继承权的制度建构*
王歌雅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女性继承权的制度建构,经历了性别平等逐步消解性别歧视的社会发展进程。原初社会女性神圣及诸子均分德性的道义判断,使女性继承权的初始享有占得先机。而男尊女卑、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与深化,使女性继承权遭遇排挤与遮蔽,引发女性继承权与性别平等的继承权以及崇男抑女的男性继承权的道德疏离与制度疏离。只有重塑人格平等、意思自治、弱势关怀、社会本位的价值基础,才能建构社会性别平等的继承权制度体系,并在继承观念的矫正与继承立法的干预下,实现女性继承权的回归与保障。
女性继承权 制度建构 性别平等 立法干预 观念矫正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女性继承权经过了由疏离到回归、由与男性继承权的差别对待到与男性继承权平等保护的历程。这一历程体现着继承权保护的演进轨迹:从身份到人格,再由人格到身份。而其价值特质在于伦理的塑造与教化,即“人类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是:无论多么恶劣的人类生活环境,都不可能泯灭人们对属于人的实践生活的德或德性的景仰;无论它多么稀少,当它展示在人的生活当中时,它都得到普遍称赞。”[1]
一、疏离的女性继承权
在尘封的历史中,女性继承权与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相始终,与宗法制度相表里。在男尊女卑观念制约下,女性继承权与男性继承权发生疏离,与男女两性平等的继承权发生疏离。该疏离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被认为合乎伦理且符合德性。甚至“人们通过践行去获得的理解与体悟通常能够达到一个基本层次或水准。它构成一个基于人的德或德性的基本解释。”[1]
(一)德性追求导致疏离
在中外继承立法史上,女性继承权似乎从未被彻底剥夺;在特定历史时期,女性甚至享有独立的继承权。只是随着时代更替,尤其是在男权至上、男尊女卑性别观念的建构下,女性继承权才开始发生了与主流德性追求——维护男性继承权的道德疏离与制度疏离。于是,女性继承权渐次被遮蔽、被排挤、被边缘。
在西方,女性继承权的享有最初源于性别神圣习俗——女性神圣。古代西亚地区伊斯王国的《李必特·伊斯达法典》有关继承的规定,并非封建时代的宗祧继承,而是财产继承。由于“早期的西亚,女人是属于神和神庙的,因此苏美尔的女性,几乎和每一座神庙都有关联。如果是女神庙,那她们是神的管家;如果是男神庙,那她们是神的妾媵。成为神的眷属,是苏美尔女孩和整个家族一种无上的荣耀。所以法律承继这一习俗,特别规定保护神妻的法律地位,强调神妻也可为继承人。”[2]P15其第22条规定:“倘父犹存,则其女——不论其为恩图、纳第图或卡第什图——可以居父之家,亦如一继承人。”然而,当女性属于神或神庙的性别神圣光环退却之后,女性继承权开始发生了疏离。在约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穆拉比法典》中,女性继承权的享有,已演化为针对赡养与改嫁的权衡,且以女性不改嫁作为德性判断标准。其第172条规定:“倘其夫未给她以霜妇之赡养费,则应归还其嫁妆,并应就其夫之家产中给以等于一继承人之一份”。“倘此妇欲去,则她应将其夫所给孀妇赡养费留给其子女,而取其父家之嫁妆,并可以嫁与其所喜爱之丈夫。”[3]P80约公元前十五世纪的《赫梯法典》第27条、46条规定,“女子可以继承自己父家的财产和地产,以作为她的嫁妆。其丈夫可以继承她的嫁妆,但她死在自己父家除外。”[2]P30赋予女性尤其是女儿以继承权,成为给予嫁资、维持生计的德性考虑。
在我国,由于周代之时即已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故女性继承权的享有,最初是源于诸子均分的德性考虑,以体现父慈子孝及对子辈个体权利的平等保护。如“汉代财产继承制度较之西周有明显进步……尤其是对庶子、女儿继承权的法律规定,反映了私有制下对个体权利的重视。”[4]P73随着时代推移,女性继承权的享有也逐步附着了尽孝、传宗、守节等德性要求。“开成元年(836年)七月五日敕节文:‘自今后,如百姓及诸色人死绝无男,有女已出嫁者,令女合得资产。其间如有心怀觊望,孝道不全,与夫合谋有所侵夺者,委所在长吏严加纠察,如有此色,不在给与之限’。”[5]P332即,出嫁女在娘家无男性继承人时可承继遗产。而尽孝道又不侵夺遗产,是应当提倡的德性。《大明令·户令》载:“凡妇女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立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女性对亡夫遗产的“继承”,以女性守节及为夫家继嗣为德性前提。故女性继承权并非真正的遗产继承权,而是遗产管理权。女性是前位继承人,继嗣之人是后位继承人。
(二)身份继承引发疏离
在中外古代的继承法中,身份继承制也引发了女性继承权的疏离。而嫡长子继承、无子继承、寡妻妾继承、户绝财产的继承,成为身份继承的核心。与之相对应,女性继承权则因其自身身份不同——生母之妻妾的身份、出嫁与否的身份、改嫁与否的身份、有子与否的身份而有所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女性继承权的享有,以父无子且以生母为父之妻的身份为前提。其继承法所规定的继承主要包括:儿子继承、无子继承、其他亲属的继承和遗嘱继承。除儿子继承排斥女性外,其他继承均赋予女性以继承权。在无子继承时,女性继承权的享有在于维护家族利益的传承。即“女继承人”可以“继承”父亲的遗产,但“女继承人”实为前位继承人。“她附属于家庭财产,这笔财产将随她带给其丈夫,并传给他们的孩子。这样,女继承人父亲的家庭才能延续。”[2]P76“女继承人”须符合相应规范与身份要求:“其一,女继承人的父亲没有合法的儿子继承他的财产和地位;如果他有几个女儿,则每个女儿都得到其财产的相等份额。其二,女继承人的父亲未在遗嘱中处分财产,或为她的女儿做出安排。其三,女继承人必须是合法出生的,比如妾的女儿就不能成为女继承人。”[2]P76
在古罗马继承法中,女性继承权的享有,则以其未出嫁为身份前提。《十二表法》规定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的目的,在于指定继承人并将延续死者的法律人格,但“罗马法律说已嫁之女不得继承”。[6]P54宗亲是法定继承的基础,但在大法官法出现后,血亲继承取代了宗亲继承,且女性继承权受到限制。即女性继承权的享有,以婚姻身份加以识别——已嫁女性不能承受遗产,未嫁女性虽承受遗产但不能任意支配。女性继承权仍属前位继承权。即“她若有继承权,她只是临时的继承人,几乎只有享用之权。若无她的弟兄或她的族人的允许,亦不能赠送或变卖;且其兄弟或族人既生前为她的管理人,死后亦即她的继承者”。[6]P55“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公元1世纪到2世纪),如果其父亲没有留有遗嘱,女儿和儿子享有同等的继承权。”[7]P134查士丁尼一世时,法定继承以血亲为基础,并遵循男女平等原则,进而使女性成为四个法定继承顺序中的继承人之一。
欧洲中世纪,女性继承权弱化于男性继承权。具体表现有:在日耳曼人的继承法中,“其一度盛行的继承顺序为:子女、孙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在同一顺序中,男性优于女性。通常,女子得到的遗产仅为男子的一半。”[2]P169而在继承的客体上,也存在基于性别的身份限制——男性血亲继承武器等战争用具;女性血亲继承家庭用具。至于家庭占有的份地,在日耳曼王国初期,仅由儿子继承。直至6世纪下半期,伴随土地的私有化,如果死者没有儿子,则由其女儿或兄弟姐妹继承。[2]P170在地方习惯法中,女性的继承地位并未得以改善。至12世纪,女性继承权的享有也只是在无子或无男性同辈亲属的情形下才得以实现。“中世纪英格兰的继承制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长子继承制; 二是妇女继承权完全依赖男性,女性不享有独立的继承权。”[8]P113“这一状况直至20世纪中期以后,英国部分学者才开始对这种男女不平等的继承权加以反思与批驳。”[8]P119-121
在我国,嫡长子继承制构成了继承制度的身份规制,导致男女两性继承权的疏离。女性继承权的疏离,其本质为女性继承权遭遇排挤:首先,女性无继承权可言。我国西周时期的继承制度,包括政治地位的继承、祭祀权的继承和家族共财管理权的继承。《仪礼·丧服》载:“有适子者无适孙。”有关爵位的继承,依遵“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祭祀继承即宗祧继承,嫡长子掌握祭祀权。《礼记·曲礼》载:“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家族共财管理权由家长行使,女儿无继承权。但“为了贵族的体面和联络感情,大多给予一定数量的嫁妆,这同样是出于父或兄的赐予,而不是女儿的权利。”[4]P26故女性继承权成为给予嫁妆的别称。其次,女性继承权基于婚姻身份的存在而被遮蔽。如秦代“在丧夫寡妇能否继承已故丈夫遗产的问题上却无任何规定。”[4]P43相反,丈夫可以继承妻子的遗产。第三,女性继承权的客体主要表现为动产或嫁资。即基于身份继承以及家族财产传承考虑,男女两性在继承的客体及数量上存在差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依法律和民间习惯,“男性继承人继承不动产及最重要的动产——奴婢,而女性继承人仅能继承一般动产而已。”[4]P110唐《户令》规定:“诸应分田宅者,及财务,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故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第四,女性继承权的享有以丧夫且无子为前提。唐《户令》载:“寡妻妾无男者,承夫分。”即寡妻妾若要继承丈夫应分的家产,尚须无子。第五,女性继承权尤其是女儿继承权的享有以户绝财产为限。唐《丧葬令》规定:“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宅店、资财、并令(本服)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大清律例·户律》规定:“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所有亲女承受。无女者,听地方官详明上司,酌拨充公。”在中国传统的继承法中,基于家族本位、男尊女卑的立法传统,女性继承权处于虚位状态。“女性只是在夫亡无子的情况下才能‘凭族长择立昭穆相当之人为嗣’;而财产继承,各代法律也只承认诸子均分制,女儿能承受的只是‘户绝财产’。可见,在以宗法父权制为核心的承继体系中,无论是身份继承还是财产继承均是以男性为主,女性处于被排斥的地位。”[9]P130-131
尽管国度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但古代各国的继承法对女性继承权附着的德性要求与身份限制却大致相似或相同。这种相似或相同,主要源于性别排挤文化,即无论是嫡长子继承,抑或死者人格的继承;无论是身份继承,抑或是财产继承,均以性别尊卑作为确定继承权的基础——女性继承权的缺失及劣后于男性继承权。具体表现:女性对丈夫遗产的继承权,实为用益权或管理权,即前位继承权;女性对家父遗产的继承权,以户绝遗产为客体,实为受限的继承权。这种以男性为中心、以身份为基础的传统财产继承制度,不仅剥夺了女性的继承权益,戕害了女性的人格独立,而且加剧了男女两性身份上与人格上的不平等。只有对男女两性不平等的继承制度予以彻底改革,才能彰显男女平等的价值追求与伦理关怀。
二、回归的女性继承权
女性继承权的享有经历了由疏离到回归的历程。这一历程,体现出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也体现出性别文化的演进与更替。在中外历史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进程中,“个人主义”逐步取代“家族主义”;“平等观念”逐步消解“身份观念”。女性继承地位日渐崛起,女性继承权日渐独立,女性继承权日渐达至与男性继承权的平等。正如英国历史法学派的奠基人梅因所述:“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10]P9
(一)回归的价值基础
西方18世纪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冲击着人格有别的社会现实,也使自由、平等、博爱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继受。“实际上,自由、平等、博爱既是近代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所普遍提倡的政治口号和立法原则,也是他们伦理道德范畴的政治哲学基础。所谓自由,不但是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且是被广泛理解为公民的各种政治经济的和伦理道德意义上的自由;所谓平等,不是基督教教义中所说的原罪平等,而是人人在法律面前和伦理关系上的平等;博爱,就是所谓爱同类,以至于泛爱众生。”[11]P86“天赋人权理论”成为人人平等与尊严自由的思想基础,并成为人格平等的精神内涵。正如卢梭所述:“一切立法体系的最终目的,可以归纳为两大目标:自由与平等。”[12]P62
大陆法系国家在“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理论”牵引下,民事立法发生了本质改变,并将人格平等、两性平等的观念与道义纳入民事立法,为女性继承权的回归奠定了观念基础与原则指导。
第一,人格平等呼唤回归。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该规定确立了人格平等原则,并推动了法国民法在亲属法和继承法领域逐步清除了主体资格不平等的有关规定。例如,1891年3月9日的法律扩大了生存配偶和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1970年6月4日的法律规定了夫妻地位平等;1972年1月3日的法律维护了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使非婚生子女、养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2]P267上述立法有助于继承权在配偶、子女之间的平等实现。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第11条规定:人都有权利能力;在法律范围内,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能力与义务能力。以此确定人格平等的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修改的《日本民法典》第1条规定:“对于本法,应以个人尊严及两性实质的平等为主旨而予以解释。”该规定为废除家制、户主权而代之以亲权和夫权奠定了基础。
第二,意思自治助推回归。18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使意思自治在导源于罗马法之后,逐步发展为私法原则。1804年《法国民法典》率先确立这一原则。依据意思自治这一“最高指导原则”,继承法衍生出遗嘱自由原则,即民事主体在法定范围内享有遗嘱自由权,该原则为女性遗嘱自由权的享有提供了原则指导。
英美法系国家伴随着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价值转向,其民事法律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并将个人主义和弱势关怀的理念纳入继承立法,从而使女性继承权的回归获得了法律保障。
第一,弱势关怀牵引回归。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关注弱势群体利益,促进社会平等与和谐,构成了英美契约法的主流价值取向,引发了“从契约到身份”的社会运动。由于英国实行的遗嘱自由范围广泛且没有特留份制度的制约,于是催生了女性维护继承权的遗产继承契约模式。即配偶之间通过生前订立契约,在契约中约定遗产由另一方尤其是妻子继承的份额或子女继承的份额,以维护女性继承权。[2]P395美国从19世纪开始着手进行已婚妇女的权利改善运动,多数州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法》。如1839年《密西西比州已婚妇女财产法》规定了配偶之间实行分别财产制,赋予妻子对自己的财产以所有权,从而使已婚妇女的法律地位基本实现了与丈夫的平等。
第二,社会本位昭示回归。近代英美法系国家基于个人本位原则,笃信所有权神圣观念,将所有权视为个人意志的体现,所有权成为排除他人限制的独断的支配权。基于所有权的充分表达与自由行使,遗嘱自由成为财产所有人处分财产的有效手段。20世纪后,基于社会本位昭示,为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英美法系国家提出了财产“合理利用”原则,并在继承领域提出了遗嘱限制原则。即对完全遗嘱自由进行限制,以维护他人利益和社会群体利益。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有助于女性继承权的维护,也为女性继承权的回归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近代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西方近代伦理学说开始传入中国。尤其在洋务运动之后,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伦理观,强调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主张以人文本,肯定人的价值。[4]P115试图运用西方近代伦理学说分析中国近代的社会道德现象,思考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问题,提出了更新国民道德的近代伦理观和救亡图存的法治观,积淀了女性继承权回归的价值观:
第一,伦理启蒙倡导回归。在伦理启蒙运动中,基于人道主义、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进化论和功利主义伦理观的传播,逐步形成了维新派的伦理思想:批判君权神授和三纲,倡导男女平等和各自独立。[13]P198-204指出,“中国要救亡图存、兴国智民,就须解放妇女,使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13]P204并使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法律地位。其中蕴含的男女继承地位平等观念,为女性继承权的回归提供了思想前提。
第二 ,伦理变革力主回归。中国近代救亡图存运动,使女性解放运动成为伦理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解放运动的思想内涵,以批判封建三纲、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从一而终为主线。女性解放运动的价值主旨,是倡导男女平等、人格独立与女性解放。男女平等乃天赋人权,只有确立男女平等观念,才能让女性拥有独立人格。[2]P243男女两性人格独立,不仅表现为女性具有与男性平等的参政权、受教育权、劳动权和财产权,而且也表现为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婚姻家庭自主权和继承权。[2]P244女性解放运动推动了传统伦理的变革,为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继承权提供了思想支持,也为女性继承权的回归提供了伦理保障。在西学东渐、伦理变革进程中,我国清末民初的继承立法发生转型,女性继承权也开始由疏离转向回归。透过《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继承立法与司法改革,可梳理女性继承权的回归路经与制度选择:
首先,女性继承权的初始保护体现出人格平等的价值追求。在民国初年,受近代西方国家民法权利本位、人格平等理念以及女权运动的影响,女性继承权得到了相应的关注,女儿和寡妻的继承权也显现出相应的变化。女儿继承权的变化是通过如下路径实现的:第一,在室女通过“嫁奁”的方式获得父亲的财产;第二,亲女为亲所喜悦者,可酌分相应财产;第三,父母亡故时,虽有同宗可立之人,但其放弃继承权时,所有遗产由女儿承受,即女儿继承权的变化,是以女性承受相应财产为特征的,承受财产并非“继承”。至于寡妻的“承夫分”权,相当于财产代管权,该代管权的行使,须遵循丈夫的遗愿或尊亲属的许可,且只有于生活必须时,才可对代管财产有一定的处分权。上述女性“继承”权益的变化,体现出家族成员的伦理关怀,也体现出性别关怀的曦微。
其次,女性继承权的确立体现出性别平等的伦理追求。早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通过了《妇女问题决议案》。明确了“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规定女子有财产继承权”、“反对司法机关对于男女不平等的判决”等精神。规定女性有继承权,“可谓于吾国法制史上放一异彩矣”,[14]开创了中华民国女性在法律上与男性同等待遇的新纪元。然而,男女两性继承权的形式平等并不等于实质平等。在司法实践中,女性继承权的保护呈现出局限性——“最高院按照妇女运动决议案规定明确承认女子有财产继承权,但强调仅限于未嫁女”。[4]P179其理由是:“女已出嫁,无异于男已出继,自不能有此项权利”(《民国十七年解字第34号解释例》)。[15]P47可见,女性婚姻身份的变化成为女性享有继承权的掣肘。女性继承权的保障,并未建立在男女两性人格平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身份差异的基础上。身份差异制约物质财富差异,制约女性的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与人格尊严、人格自由。
(二)回归的制度展现
女性继承权的回归,伴随伦理观念和性别观念的变革而逐步实现。尤其是继承立法价值基础的变化,催生了继承制度改革,也为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继承权提供了德性基础和制度保障。因为,“任何人都具有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的可能性:任何正常的、能够通过生活理解人类生活事务的人都不曾被天然地剥夺德性地生活的自然条件,都能够选择德性地而不是邪恶地生活,正如他也能够选择邪恶地生活一样。”[1]基于人格独立与性别平等,赋予女性以独立、平等的继承权,既是德性生活的要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女性继承权的平等保护,通过民法典继承编的改革而逐步完成,即通过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制度的渐次改革,实现女性继承权的独立与平等保护。女性继承权的独立与平等保护,意味着继承立法逐步剔除了封建因素——废除男女不平等的长子继承制,实行男女平等的均分继承制;取消身份继承制,实行财产继承制;并在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的制度设计上,表现出男女平等与子女平等的特点。《法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遗产,按下列规定的顺序及规则,归属于死者的子女及其直系血亲、直系尊血亲,旁系血亲及其尚生存的配偶。”其第745条规定:“子女或其直系卑血亲,不分性别及长幼,亦不论其是否出于同一婚姻,得继承其父母、祖父母或其他直系尊血亲的遗产。如继承人均为第一亲等卑血亲并以自己名义继承时,应按人数继承相等的份额;如继承人全部或部分为代位继承时,应按房数继承。”该规定确立了配偶之间、子女之间(包括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平等且同一继承顺序均等的遗产继承权。《德国民法典》第1931条规定了配偶的法定继承权;1969年修正的《德国民法典》第1934a条规定了非婚生子女的遗产补偿请求权,即非婚生子女可取得与婚生子女相等的遗产份额。《日本民法典》第887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为继承人”;第890条规定:“被继承人的配偶恒为继承人。于此情形,有前三条规定的继承人时,配偶与这些人为同顺位继承人。”《瑞士民法典》也确立了配偶、子女同等的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的权利。上述规定提升了已婚女性及女儿的继承地位,为女性继承权的回归提供了制度保障。
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女性继承权的平等保护,是通过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的适用来加以实现的。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废除长子继承制。早在十二世纪末,英国针对不动产确立了长子继承制,即基于武功而获得的土地应由长子继承,而自由租地和军役租地的财产,则由长子和亲系优先继承。直至1925年,英国财产法废除了长子继承制,为女性继承权的享有创造了条件[2]P396-379;二是废除限嗣继承制。美国在独立前,适用英国的限嗣继承制——直系子孙继承制。进入十八世纪后,美国各州先后废除或改良限嗣继承制。例如,弗吉尼亚州于1776年废除限嗣继承制,纽约州于1786年废除限嗣继承制,实行同一顺序继承人平分遗产的继承规则,且不以性别为限,为女性继承权的享有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推进遗嘱继承制。基于遗嘱自由原则,英美法系国家赋予遗嘱人以自由权,使其通过遗嘱处分自己的遗产。倘无遗嘱,适用法定继承,即遗产由死者最近的亲属——配偶、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继承。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交互配合,为女性继承权的实现构筑了制度体系,有助于实现继承权的性别平等。
20世纪初期,伴随我国由近代向现代的转换,传统继承法也发生了制度改革与体系转型。即我国继承法之近代化,以法律移植为主要手段,以继承制度的抉择为进路,以人格平等的初现与家族主义的势微为特征。伴随继承法之近代化,女性继承权也由疏离转向回归。清末编撰的《大清民律草案》虽未施行,但却从立法上确立了法定继承女性劣位的制度雏形。即在继承时,如无嗣子继承和代位继承人时,“亲女”属第五顺序的承受遗产之人(《大清民律草案》第1468条)。其承受遗产的顺序劣后于被承受人的配偶、直系尊属、亲兄弟、家长之后,显现出男性继承权优于女性的特质。女性代位继承权的享有,则以“从一而终”为要件,即“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得承其夫应继之分,为继承人”(《大清民律草案》)第1467条)。《大清民律草案》继承编立法的原则和内容虽相对保守且立法技术不够成熟,但却奠定了女性成为法定继承人的制度基础,成为中国传统继承法制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为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继承立法提供了有益借鉴。[16]P49与《大清民律草案》继承编相比,《民国民律草案》继承编则赋予女性以相应的遗产权利:一是酌给遗产继承权。“亲女”虽为第五顺序遗产继承人,但可酌请分与遗产,即“所继人之亲女,无论已嫁与否,于继承开始时,得请求酌给遗产归其继承”(《民国民律草案》第1340条);二是遗嘱设立权。“民国初年,基于性别观念的更新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民国民律草案》第1128条赋予女性以遗嘱设立的自由权,即‘妻不经夫允许,得自立遗嘱’。女性是否具有设立遗嘱的权利,是女性是否具有独立人格的标志之一,这与古代法相比,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体现出女性法律地位的提高。”[17]P158《民国民律草案》继承编虽未颁行,但却体现出崇尚家族主义、男权主义的立法精神。而《亲属编》中对女性遗嘱设立权的赋予,显现出男女两性人格平等的价值诉求,具有进步意义。《中华民国民法》继承编的制度改革,则体现出“改造意义”的立法精神,即“法律纵不能制造社会,而改良习惯,指示方向,确有效力。”[16]P58凭借改良习惯、指示方向的立法目的,《继承编》对体现宗法观念的继承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与改革:首先,废除宗祧继承制度。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亲属继承法先决各点审查意见书》指出:“宗祧重在祭祀,故立后者惟限于男子,而女子无立后之权,为人后者亦限于男子,而女子亦无为后之权,重男轻女,于此可见,显与现代潮流不能相容……故认为宗祧继承,无庸规定”。[18]P788废除宗祧继承,为传统继承法的变革增添了人格平等气息,昭示了男女平等精神;其次,赋予女性以继承权。基于改造主义的立法原则,女性在继承人范围中的地位得到确认。即“遗产继承人,除配偶外,依左(下)列顺序定义:一、直系血亲卑亲属。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中华民国民法》第1138条)。上述继承顺序贯彻亲等近者优先继承的原则,排除了以性别差异而定继承顺序的尊卑观念,有助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财产权益的保障。而中国继承制度之改革,对女性解放至关重要。《中华民国民法》继承编除继承传统法文化因素外,还对宗法制度、尊卑等级观念进行了有效荡涤,从而使我国继承法的制度改革体现出人格独立、男女平等的精神,实现了由家族本位向个人本位的立法转变,完成了女性继承权由疏离向回归的制度转换。
三、建构的女性继承权
女性继承权由疏离转向回归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人格独立、性别平等成为女性继承权得以回归的价值基础与原则保障。在女性继承权日益获得与男性继承权平等的社会进程中,如何切实地保障女性继承权的实现,既是立法问题,也是司法问题。而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纳入继承立法与继承司法,是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保障。尤其是在性别歧视的风俗习惯还未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背景下,建构性别平等的继承制度是女性继承权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
(一)继承观念的矫正
“近现代以来,性别平等已经在法律文本中得以解决,但性别歧视的观念以及性别等级的模式却依然顽固地存在,而这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19]P33尽管“法律常常以中立自居,但却包含了性别歧视的内容,并且也正是中立的标准才使得社会性别的结果在法律上得以正当化。”[19]P34因为,“法律,从实在法的角度论,倾向于反映现存的权力结构,因此,法律更多的是男权力量的宣言。因为,‘在每一个我们所知道的社会,这些义务都是由男性建构的。’”[19]P34于是,在尘封的中外继承立法中,女性继承权处于被颠覆、被疏离、被歧视的状态。超越性别歧视,建构性别平等的继承立法与继承司法,是女性继承权得以实现的制度保障。
女性继承权乃基本人权,是女性权利谱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平等与非歧视原则在继承领域中的反映与落实。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指出:“男女及大小国家权利平等。”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规定:“人人生而平等,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其第2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197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被誉为“国际妇女权利法案”,是妇女人权国际保护的重要法律文件及里程碑。[20]P65在该公约中,“对妇女的歧视”,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20]P66即“任何基于性别的待遇差别,其特征是:有意或无意地使妇女处于不利地位,使整个社会不能在家庭和公共领域都承认妇女的权利;以及使妇女不能行使她们应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20]P66为矫正社会性别歧视,救济女性权益,世界“各国纷纷立法或修法,确立两性平等之地位。如1957年德国《男女平权法》,1965年《法国民法典》修正,英国1969年《家庭改革法》和《离婚法》,美国1970年州法全国统一委员会的《统一结婚和离婚法》。”[2]P508上述立法和修法,为女性继承权益的维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国也在20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简称《继承法》)。《继承法》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部继承立法,既担当着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功能,也承载着我国当代继承法的变革追求:继承权男女平等①。继承权男女平等作为《继承法》开宗明义规定的处理继承关系的基本原则,集中表现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的确定男女平等;同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男女平等;代位继承、转继承的适用男女平等;继承权的丧失男女平等;遗嘱继承权男女平等。继承权男女平等,成为我国女性继承权由疏离转向彻底回归的重要立法标志,也是女性继承权得以实现的制度保障。
“社会性别的产生源于社会的建构,这是持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的学者一致的观点。”[19]P33“社会性别不平等首先表现为基于性别而实行的社会角色的不合理区分,也就是说在社会角色、 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的性别歧视。”[20]P151为此,世界各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在反对社会性别歧视、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时,都非常重视在社会生活诸领域摒弃歧视立法与歧视政策,推进法律领域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为女性继承权的平等享有与司法保障进行赋权与制度建构。
(二)继承立法的干预
女性继承权由疏离转向回归,是社会文化建构与转化的结果。其中,性别歧视文化建构了性别歧视的继承习惯,也建构了性别歧视的继承立法。即“在法律建立之初,女性没有参与到法律建设中去,因而在法律文本中没有留下女性的声音,女性也就不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而男性因为是法律最初的建设者而自始至终地作为法律的主体,于是,女性被置换成了法律的客体,并作为男性监护的对象而存在。”[19]P61故矫正性别歧视的继承观念,将逐步改变社会中人男尊女卑的继承意识,进而树立性别平等的继承观念。而性别平等的继承观念,将矫正重男轻女的继承习惯或继承习惯法,建构社会性别平等的继承立法与继承制度。
近现代以来,尽管性别平等已成为继承立法中的应有之义,但性别歧视的继承思维、继承观念、继承习惯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继承的观念差异、城乡差异、主体差异。而矫正性别歧视的继承文化与继承习惯是继承立法与继承司法的重要内核,也是实现继承权性别平等的重要路径。因为,“平等,当然首先是规范的平等,或权利的平等”。“实现男女平等就包括规范与事实的双重任务,要交融地使用规范平等与事实上的女性‘特权’手段,建构男女真正平等的社会结构。”[19]P5
大陆法系国家在建构继承立法之时,已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从而为继承权男女平等提供了法律文本。在法定继承中,无论是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顺序与继承份额的界定,还是代位继承与转继承的规定,均贯彻了男女平等原则。如《德国民法典》第1925、1926、1928条的第2款分别规定:如果继承开始时父母仍生存,由父母单独和等额继承;如果继承开始时祖父母仍生存,由祖父母单独和等额继承;如果继承开始时,曾祖父母已经去世,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中与被继承人亲等最近的亲属继承;若有数人同为最近亲等亲属,则等额继承。《瑞士民法典》第457-459条分别规定:子女平均继承;父母平均继承;被继承人父系及母系的祖父母均生存的,按其亲系平均继承。《越南民法典》第679条规定:“同一顺序的继承人享有同等份额的遗产。”在遗嘱继承中,无论是遗嘱能力、遗嘱处分方式及遗嘱自由限制的规定,还是负担的履行、替补继承人等规定,均体现了男女平等原则。《法国民法典》第902条规定:任何人均得以生前赠与或遗嘱处分财产,……但法律宣告无能力的人除外。《瑞士民法典》第468条规定:“被继承人须成年后始得缔结继承契约。”《日本民法典》第964条规定:“遗嘱人可以以概括或特定的名义,处分其财产的全部或一部分,但不得违反关于特留份的规定。”《意大利民法典》第536条规定:“特留份继承人是那些由法律规定为他们的利益保留一部分遗产或者其他权利的人。他们是:配偶、婚生子女、私生子女以及直系尊亲属。”《德国民法典》第2096条规定:“被继承人可以就一个继承人在继承开始之前或之后继承资格消失的情形,指定由他人作为继承人。”上述规定,平等适用于男女两性,体现了继承权男女平等的立法精神。
英美法系国家虽以判例为主,但继承权男女平等理念却已深入人心且渗透于司法实践的诸环节。在有限的英美继承立法中,性别平等理念与男女继承权平等观念相始终。如英国1952年的《无遗嘱遗产法》第5条规定:“本法的附则之二是使在本法生效后配偶一方无遗嘱死亡的生存配偶取得婚姻住所。”[21]P351969年的《美国统一继承法典》(《美国统一遗嘱检验法》)第2-102条规定:生存配偶的无遗嘱依法如下:(1)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生存的直系卑亲属和父母,则生存的配偶取得全部遗产;(2)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生存的直系卑亲属,但父母一方或双方生存,则生存配偶除继承5万美元的遗产外,还可继承剩余遗产的1/2……。[22]P97其第2-401条规定:被继承人死亡时,其生存配偶有权取得价值5000美元的宅园特留份。如果没有生存配偶,则被继承人的未成年子女和未独立生活的子女可以一起取得价值5000美元的宅园特留份。[22]P112上述规定表明,无论在法定继承领域,还是在遗嘱继承领域,均体现了性别平等的理念,有助于人格尊严与财产权益的充分维护。“司法实践中的里德诉里德案(Reed v. Reed),是美国有关平等保护条款的案件,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判定遗产管理人的确定不得因性别而存在歧视,男女享有平等的被指定为遗产管理人的权利。”②最高法院审议该案件并发表了一致通过的判决,认为爱达荷州法典相关法条赋予男性的此项特权是专制且违宪的。最高法院在该案中,首次判决确立了基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所产生的“禁止基于性别的不平等待遇”。[23]在最高法院判决生效前,爱达荷州修改了该法条,新法于1972年7月1日生效。
2012年,在《继承法》实施27年之际,社会各界围绕继承法的修正展开了广泛探讨。在《继承法》修正进程中,关注女性继承权的实现成为修法的主要目的之一。
首先,继续贯彻男女平等的继承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简称《建议稿》)③第2条明确规定了继承权男女平等原则,其目的“在于为继承行为立法”,[24]在于为继承行为提供性别平等指引——无论在法定继承中,还是在遗嘱继承中,继承人的遗产继承权男女平等。例如,在增加规定的夫妻共同遗嘱、替补继承人、替补受遗赠人以及后位继承的制度规范中,遵循并深嵌了男女平等原则。④
其次,肯定丧偶儿媳与丧偶女婿的继承权。即“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无论是否再婚,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⑤这一规定超越了传统继承法中的身份差异,体现出丧偶儿媳与丧偶女婿的人格平等与性别平等。
再次,特留份的制度设计融合了男女平等原则。将特留份权利主体界定为“被继承人的配偶、晚辈直系血亲、父母。特留份主体的限定,吻合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社会结构,顺应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22]P99同时,有助于性别平等精神的弘扬。
最后,归扣制度的增补将顺应民俗风尚与性别平等追求。即“继承开始前,晚辈继承人因结婚、分家、营业、教育、生育等事项,接受被继承人生前赠与的财产,依据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思表示或者风俗习惯,属于提前处分遗产的,应当按照赠与时的价值归入遗产计算价额。赠与的价额在遗产分割时应当从该继承人的应继承数额中扣除。但超过应继承数额的部分不必返还。”⑥这一规定,既体现为在尊重被继承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以不归入为一般原则、以归入为例外的立法精神,也表现为归扣制度的性别平等与人文关怀,有助于填补现行《继承法》的立法空白。
四、结语
总之,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基于社会结构的男权性和女性权益应服从男性利益的屈从性,“女性在历史的语境中,在社会文化地位上,一直处于社会低层的状态,是被社会权力中心拒绝的‘边缘人’,没有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表达自身意愿的权力。”[25]当社会变革逐步消除不公平的性别歧视现象时,当性别平等即“反对歧视女性”的观念已经“从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批判理论,并形成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时,[25]女性继承权的保护与实现才能变成现实。即男女平等以及男女继承权平等,必须超越以性别身份为分析范畴和立法基点的局限与障碍。只有将男女两性建构在人格平等的道德范畴和立法基点之上,才能使男女两性的继承权由形式平等达至实质平等。而女性继承权的平等保护,不仅折射出女性的身份地位、生存状态、资源配置,而且反映出女性的人格尊严与性别价值。对女性继承权的充分保护,是体现女性价值和保护女性利益——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道德保证与制度保障。为此,继承权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应予坚守。
注释:
① 参见《继承法》第9条。
② 404 U.S. 71 (1971). 萨莉与塞西尔·里德(Sally and Cecil Reed),是已婚的分居伴侣,因对他们已故儿子的遗产由谁作为遗产管理人而发生纠纷。两人分别向爱达荷州埃达县( Ada County, Idaho)的遗嘱检验法院(Probate Court )提起诉讼,请求指定自己为遗产管理人。爱达荷州法典规定,在遗产管理人的确定过程中,“男性优先于女性”。因此,埃达县法院指定塞西尔为遗产管理人。萨莉为此提出上诉直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其在最高法院的代理律师认为,爱达荷州法典相关法律属于歧视条款,违反了基于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产生的禁止性别歧视原则。
③ 《建议稿》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黑龙江大学民商法学研究中心联合研究完成。参见杨立新、杨震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④ 参见《建议稿》第37、38、39条。
⑤ 参见《建议稿》第58条。
⑥ 参见《建议稿》第9条。
[1] 廖申白.德性伦理学:内在的观点与外在的观点——份临时提纲[J].道德与文明,2010,6.
[2] 何勤华,魏琼.西方民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编委会.汉穆拉比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 梁凤荣.中国传统民法理念与规范[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
[5] 孔庆明,胡留元等编著.中国民法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6] [法]古郎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M].李玄伯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7] David Johnston, Roman Law in Contex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 3.3; Frier and McGinn, A Casebook on Roman Family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ter IV; Yan Thomas, "The Division of the Sexes in Roman Law", in A History of Women from Ancient Goddesses to Christian Sain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8] Eileen Spring,Law Land and Family: Aristocratic Inheritance in England, 1300-1800,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3.
[9] 徐静莉.民初女性权利变化研究——以大理院婚姻、继承司法判例为中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0] [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1] 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3] 王歌雅.中国婚姻伦理嬗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4] 郁嶷.女子继承权问题[J].法律评论,287.
[15] 郭卫.最高法院解释例全文[M].上海:上海法学编译社,1946.
[16] 朱勇主编.中国民法近代化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17] 王歌雅.中国近代的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8]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9] 周安平.性别与法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0] 陈明霞,黄列主编.性别与法律研究该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1] 蒋月等.英国婚姻家庭制定法选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2] 张玉敏.中国继承法立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3] Reed v. Reed-Significance, Notable Trials and Court Cases-1963 to 1972.
[24] 王歌雅.论继承法的修正[J].中国法学,2013,6.
[25] 罗蔚.当代伦理学的新发展:女性伦理学评介[J].伦理学,2005,8.
(责任编辑:唐艳秋)
Separation and Return:System Construction of Women’s Right of Inheritance
WangGe-ya
(Law Schoo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e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The system of women’s right of inheritance has been constructed as the concept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substituted with gender equality in the society gradually. Women had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due to the female godhead and moral judgment to distribute equally among the offspring in the primitive society. However, women’s right of inheritance was excluded and veiled while it was believed that man was suprior to woman and the system that the oldest son had the right to inheritate was set up and developed, which caused the moral and institutional seperation among the women’s right of inheritance , right of inheritance of gender equality and men’s right of inheritance to respect men and constrain the women.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right of inheritance with the gender equlity and realize the return and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 of inheritance by the correction of inheritance concept and intervention of inheritance legislation, we have to rebuild the value basis of personality equlity, autonomy of will, care for disadvantaged group and social standard.
women’s right of inherit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gender equility; legislation intervention; concept correction
1002—6274(2015)02—067—10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排挤与女性婚姻家庭权益的法律保障”(11BFX072)的阶段性成果。
王歌雅(1963-),女,山东莱州人,法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人身权法、性别与法律制度等。
DF52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