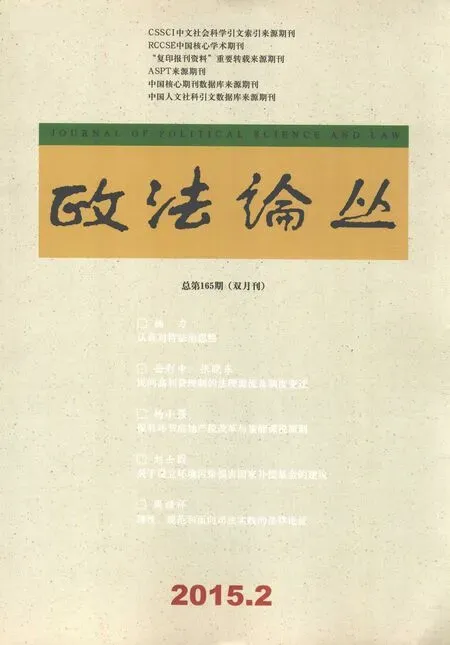论矿害责任承担规则与责任方式*
2015-01-30胡卫
胡 卫
(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438)
论矿害责任承担规则与责任方式*
胡 卫
(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438)
矿害责任在我国并未得到应有重视,其规制规则简单粗疏,不能为受害人提供有效救济,制度供给不能满足司法需求。应以危险责任法理为基础,以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中心明晰矿害责任的法律构造;对矿害责任承担规则予以具体化,以满足不同情形下矿害责任的司法规制;并应对矿害责任承担方式进行梳理,活用多种责任方式为受害人提供周延的救济。
矿害责任 责任规则 责任方式
矿害责任指为矿物的钻探、采掘以及与此相关的选矿、冶炼和其他事业中,因挖掘土地、矿井积水或排水、碎石或矿渣堆积以及排放废气等给他人造成的损害。[1]P125日本、韩国、德国、瑞典、荷兰等国矿业法有矿害责任的专门规定。我国矿产资源法第32条、煤炭法第11条和第27条、水污染防治法第38条、水法第31条等规定,可对应国外矿害责任,在实践中发挥着矿害责任的规制功能。但由于立法技术限制和立法者认知原因,并没有将自然法学所倡导的“法”规则完全变为“法律”[2]P112,以至于上列规定对矿害责任的规范甚为粗疏,未完整规定矿害责任构成要件、责任承担规则及责任承担方式等,难为矿害受害人提供周延救济。由于矿害责任制度供给严重不足,造成法官适用法律和裁判案件困难,宜从制度上和司法上予以缓和。
一、矿害责任构成以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中心
(一)矿害责任构造不清晰致司法适用困难
关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理论上素有过错、损害事实、因果关系的“三要件说”与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的“四要件说”的争论。在过错责任原则下,三要件说主张过错吸收违法性,四要件说则采纳违法性独立于过错。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7条未特别强调违法性,但理论上始终存在违法性否认说[3]P301与违法性肯定说[4]P159的争论。采矿实施者对开采矿产资源和开发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补偿义务与恢复义务是“污染者付费、破坏者担责、收益者负担”原则的体现。[5]因矿害责任规制规则简单粗疏,在是否需要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认定两方面存在较大分歧:
第一,矿害责任究竟适用过错归责还是无过错归责并不明确。司法实践中,矿害责任是否要求主观上的过错有不同观点,而矿产资源法等并未提供归责原则的确定依据。一些法院认为应以过错为归责事由。如“沈怀彬与临沂市西高都煤矿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①中,对被告地下开采行为导致原告房屋开裂等损害,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过错责任加以认定,显系以过错归责,忽略了矿害责任危险责任的特性;在“三门峡市槐扒黄河供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②案中,由于义马煤业集团曹窑煤矿有限公司对隧洞下部煤炭的开采行为直接导致了山体裂缝、隧洞变形、沉降等损害结果的发生,义煤集团本身存在过错,尽管其子公司已破产,义煤集团仍应承担过错责任。另一些法院则认为矿害责任以无过错为归责依据。如“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西庄村委会与山东省长岛县海运公司损害赔偿纠纷”③案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采矿导致西庄村受到海水严重侵蚀的认定上,并未要求被告存在主观上过错,适用的是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聂胜等149户村民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五矿、六矿及中平能化医疗集团总医院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④,五矿、六矿生产废水与总医院的生活废水共同造成了辛庄村地下水污染,使149户村民生活饮用水受到污染,法院适用无过错责任判决三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而多数采矿损害案件中,采矿企业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等因素,往往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⑤
第二,矿害责任因果关系认定困难。矿害责任若系因采矿过程中排放废水、废气、堆放废渣或废石等,引发重金属环境污染或其他污染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权益损害的,可归入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并可援引第66条因果关系证明规则,由受害人就污染行为和损害结果承担举证责任,采矿企业就免责事由或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但当矿害责任以破坏生态的形式造成损害时,因果关系认定就存在困难,司法实践的处理思路不尽一致:一是由受害人对采矿行为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如“张山河与张跃进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⑥中,法院以张山河所举证明材料不能证实其房屋损害确系张跃进与他人在经营煤矿中越界开采所致,所诉请的经济损失也缺少事实根据,且请求法院保护其权利的期间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二是将采矿损害解释为特殊环境侵权行为,适用因果关系举证倒置规则由采矿企业对采矿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如“贵州省桐梓县木瓜镇龙塘村老房子32户村民与綦江县赶水矿产有限公司损害赔偿纠纷案”⑦中,法院通过将水资源解释为环境组成部分,被告因采矿导致水资源断流属于特殊环境侵权,进而适用因果关系的举证倒置规则,在被告不能举证证明无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承担败诉责任。三是通过技术鉴定确定采矿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多数情况下,当事人会申请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采矿是否造成房屋、建筑物、构造物等损害的原因进行鉴定,并以鉴定结论作为定案的依据。⑧但鉴定易混淆因果关系认定举证责任分配。
(二)基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矿害责任构成
侵权责任法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协调法益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以保护行为自由为己任。人们期待侵权行为法和损害赔偿法能有助于保障个人的基本生存,并以此建立相应的社会化国家机制。在这种期待中,我们才能探察到侵权和损失赔偿法律制度发展至今的决定性动力。[6]P5-7但法律所强调的重点已从承担过错责任转移到补偿损失。责任客观化、危险责任的扩展就是这种趋势的典型特征。危险责任制度的设立就主要是考虑到,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同时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危险,并由此产生损害。即使对此尽最大努力加以防范,这种损害仍然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在允许从事高危行业的同时,应建立与之相应的损失补偿机制——“部分解决社会不幸事件的方案的现代形式”。[6]P258危险责任是德国法上的概念,创设该制度的原因主要是人们认识到新的设施、技术、物质或材料是未知和无法预见的风险的源泉,因此允许使用的同时,有必要设立一个严格责任来平衡由此产生的损害。
矿业活动是典型的危险行为,易造成大气、土壤、水体污染和生态破坏。[7]P58-61矿产资源开发中重金属环境污染尤为严重,其污染路径有三:一是开采过程改变了矿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和存在形式,无论是露天开采还是坑道开采,在此过程中都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重金属污染。二是选矿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石和尾矿,是导致重金属环境污染的重要路径。选矿过程中主要产生尾矿。尾矿通常呈泥浆状,存放于尾矿库,这是重金属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选矿废水和尾矿沉淀后废液经简单处理后循环使用或用于农田灌溉,部分废水废液经尾矿坝泄水孔直接外排至周边水体、土壤,进行形成重金属污染。尾矿库中的重金属污染物可以通过扬尘,对周围土壤和水体产生影响,进而直接或间接危害人体健康。洗选矿过程中添加大量络合剂或整合剂等药剂,络合铜、锌、汞、铅、锰、镉等有害重金属,形成复合污染,改变重金属的迁移过程,加大重金属迁移距离。三是冶炼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含重金属污染物的废渣、废气和废水,排入大气、土壤、水体或海洋环境中造成污染,并呈交叉污染、复合污染的态势。矿区的环境污染和尾矿治理一直是我国突出的环保难点,已发生多起尾矿溃坝、渗漏及冶炼过程过程中的重金属污染事故,给周边民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因此对金属矿山矿害责任的规制不容忽视。
鉴于矿业活动的危险性,各国矿业法对矿害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日本,矿害早已成为严重社会性问题,如造成严重大气污染的别子铜矿山烟害事件、日立矿山烟害事件,在水质污染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足尾铜矿山矿毒案,以及居于四大公害案件之首富山痛痛病镉污染事件。日本《矿业法》第109条据此将矿害作了无过失责任的规定。[8]P23意大利最高法院用“谁受益,谁承担负担”原则对矿害严格(绝对的)责任比例进行了具体化。[9]P566这种严格责任来源于对矿山企业等行为责任寻求“对允许从事危险行为的一种合理的平衡”[6]P256-259,系基于分配正义的基本法理:1.矿业权人或实际采矿经营者制造了危险源,损害应由造成损害的人承担责任。2.矿业活动所产生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仅能由矿业权人或实际采矿经营者控制,其具有控制这些危险的条件和技术。3.矿业权人或实际采矿经营者的危险活动为其创造价值,由获得利益者负担因此危险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责任,系正义的要求,亦即“利益归属之处亦是损失归属之地”。4.因危险责任而生的损害赔偿,得经由商品服务的价格机能及保险制度予以分散。⑨上述理由虽代表不同学说,但没有必要将其视为不兼容,公害的场合(如矿害责任),企业因生产经营活动获得利益的同时造成他人损害,同样也是因为危险行为在自己支配范围内,就该背负无过错责任。[10]P10新近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则认为,矿害责任等采纳无过错责任的真正原因,在于权利人行使权利应对他人负有保证不侵害的义务。[11]即享有法律上的利益者,必对他人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等“法益”负有一定保证义务,违反即担责。
基于矿害责任作为危险责任的法理,其法律构造建立于无过错责任原则基础之上,析言之:
第一,矿害责任坚持无过错归责原则。但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划分并非绝对,在适用无过错责任的领域,现代侵权法上是一个过错、无过错责任的交错适用领域。[11]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在体系上存在关联,针对某一事实两种规范同时发挥作用,即“过失责任与无过失责任的竞合”[1]P8。以环境污染责任发展过程为例,责任适用不断发生演变,对那些生产者超标排放、违法排放,认定其过错不再困难,判例或立法也逐渐优先适用过错责任,只有那些认定过错困难的污染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因此,在规定无过错责任类型时,应注意同时规定或允许优先适用过错责任。⑩亦有观点认为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两者没有适用上的先后关系,应从受害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允许受害人自由选择适用。[12]我们认为,面对采矿行为所致水污染、土壤污染、尾矿溃坝等重金属污染事故频发的现实,企业和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容忽视。如一味强调无过错归责,忽视过错在无过错责任中优先性,难以遏制重金属环境污染在我国的发展态势。承认矿害责任中过错与无过错交错、并优先适用过错责任,具有重要意义:1.体现对矿害责任者的惩罚性。过错蕴含了行为的可责难性、可归咎性。对存在明显违法、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矿害责任制造者,不适用过错则难以体现对其过失的惩戒,优先适用过错则突出对恶意侵权行为制裁功能。2.最大限度维护受害者利益。在域外司法中,实行严格责任的产品责任、有毒物侵权等领域,若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或漠视他人权利者,可科以惩罚性赔偿责任。优先适用过错,可使受害者同时获得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使矿害责任赔偿额“量”有别于纯粹的无过错情形。3.对潜在加害者有激励作用,利于促进环境保护。在矿害责任中区分过错与无过错,使责任有所差别,以激励采矿经营者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或破坏环境,发挥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制约功能。
第二,矿害责任不要求加害行为存在违法性。若将矿害责任以普通侵权责任论,则受害者必须证明加害者行为存在违法性,如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需对加害者的违法性进行证明,这与其认为采矿损害属于过错责任的观点一脉相承。但将矿害责任界定为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若司法上仍要求构成矿害责任必须以矿业权人存在违法违规为前提,则很难谓真正的无过错责任,受害者居于弱势地位,难以证明加害者何时何处何事存在违规,其与加害者之间不具有地位上的互换性,将导致受害者救济上存在客观障碍。从我国矿产资源法第32条、煤炭法第27条、水法第31条、草原法第50条、森林法第44条、土地管理法第36、42条等规定看,其既无对采矿企业的主观过错的规定,亦无对行为违法性的要求。结合环境保护法第64条规定解释,该条承继环境保护法修订前第41条规定,没有像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那样强调要求环境侵权以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为前提。从矿害责任主要以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方式实现的角度解释,无疑可推导出矿害责任无须要求矿业企业存在违法性为责任构成条件,亦与各国将矿害责任规定为无过错责任的通例相符。
第三,矿害责任由加害者承担不存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对“环境”的界定虽反映出了“环境”的一般立法特征,但是该定义对于“环境”的内在价值和特性反映不够,没有体现出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性和环境的整体性。[13]这种宽泛定义下,主要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种方式所表现的矿害责任,完全可归入环境侵权。环境保护法第64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依然未解决矿害责任中以破坏生态方式侵权的因果关系认定问题,在侵权责任法中也找不到破坏生态侵权责任的对应位置。然而生态破坏侵权与环境污染侵权机理相同,在性质与致害过程上高度相似,统归于“环境侵权”至为恰当。作为晚近出现的生态破坏侵权行为,同样拥有污染行为所具有的间接性、持续性、广泛性、复杂性、严重性等特征,且与污染行为可以相互作用,同样具备污染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举证责任倒置、诉讼时效延长等特殊规则的科技基础、社会基础和法理基础,因而,应当将其提升到与污染侵权同等的地位,适用相同的规则,构建统一的环境侵权体系。[14]按照“相同案件应得到相同处理”的平等原则,为不造成法律体系的割裂和受害人救济的欠缺,基于对受害人特别保护的理念,生态破坏侵权责任统一适用环境污染责任因果关系举证证明规则,由加害者承担不存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不仅弥补了侵权责任法欠缺生态破坏侵权的立法缺憾,也实现了环境保护法第64条的立法意旨。
二、矿害责任承担规则的具体化解析
(一)矿害责任承担规则粗疏
矿业活动是利益复杂交错的生产经营活动,存在诸多利益相关者,明确责任主体范围及责任分担规则是矿害责任不可或缺的规制内容。依矿产资源法第32条、煤炭法第27条、水法第31条第2款等规定,矿害责任主体为“矿山企业”、“采矿者”、“采矿单位”,且未明确矿害责任的分担规则,不能适应矿害案件规制的需求,表现在:1.采矿权人与实际采矿者分离时产生的矿害责任由谁承担不明确。这种分离可以是基于采矿权人的合法授权分离,如采矿权出租、托管等情形;也可以是基于采矿权人非法授权分离,如非法承包及变相转让矿业权等形式。2.受让人是否对受让前的矿害责任负责并不明确。从矿业管理实践看,受让人基本上对其受让前发生的矿害责任承担了责任,其是否享有对转让人的追偿权则依转让协议约定确定。3.矿害责任加害人为数人时,责任分担规则不明确。司法实践中有依原因力比例对外承担按份责任的处理,亦有原因力比例难以确定时由数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做法。4.矿业权消灭时矿害责任承担主体不明。矿害责任具有环境侵权的潜伏性、累积性、持续性、复杂性等特点,损害后果可能在矿业权终止后一定时间才发生,此时如何确定矿害责任主体法律亦无明确规定。实践中,有以诉讼时效超过为由驳回原告诉请的;有的尽管子公司破产,但母公司对子公司造成的矿害责任有过错时,由母公司承担过错责任,处理方式有明显差异。
(二)矿害责任承担规则的具体化
为化解矿害责任承担规则粗疏带来的司法适用困难,有效规制矿害责任,有必要将其具体化:
第一,明确矿害责任承担者的界定原则。依行为者负担责任的法理,除非有特殊的责任转承或替代责任等特殊情形外,应当由矿害责任制造者或危险控制者承担责任。因而矿害责任的承担者主要是矿业权人。以荷兰民法典第6:177条、日本矿业法第109条第1款、韩国矿业法第91条第1款、德国矿山法第20条、波兰地质与采矿法第93条等规定为例,确定矿害责任承担者时形成三项规则:“损害发生时规则”,即损害发生时的矿业权人应对所发生的矿害承担责任;“最后所有者规则”,即矿害责任发生于矿井废弃、矿业权被吊销或矿业权期限届满后,则由最后的矿业权人应承担责任;“特殊时效规则”,基于矿害责任具有潜伏性、累积性、渐进性、缓释性等特点考虑,其诉讼时效较普通侵权责任长。如荷兰民法上矿害责任时效为矿井废弃之日起5年,日本矿业法规定为侵害之日起3年但最长自损害发生之日起不超过20年。针对我国立法表述不清晰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借鉴国际先进立法予以明晰:因矿业企业以矿业权为根本要素,建议统一以矿业权人界定矿害责任主体,比现行法上简单以“矿业企业”、“采矿者”、“采矿单位”指代更为科学,亦不产生歧义;以“损害发生时规则”和“最后所有者规则”作为一般规则确定矿害责任主体,既符合矿业权行使的规律,亦便于识别和追责,符合责任自负的法理;基于矿害责任与环境侵权的亲缘性,宜与环境保护法第66条相衔接,诉讼时效定为3年为妥。如损害系持续性的,则诉讼时效应从持续性损害停止之时计算。
第二,加害者为数个主体时矿害责任的分担规则。立法政策上为保护受害者利益,强化了制造危险者或因危险获利者的责任。我国矿产资源法未对数个责任者并存时矿害责任分担进行规定,但可为侵权责任法第8~12条及第67条环境污染责任分担规则所覆盖。依体系化解释,数个责任主体并存时的责任承担规则可细化为:1.数个主体共同过错致矿害责任发生时,应依侵权责任法第8条共同侵权规则由多个责任主体承担连带责任。2.数个主体行为均可能导致矿害发生危及他人人身或财产安全,其中一个或者数个主体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依侵权责任法第10条共同危险行为规则承担责任。若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3.数个主体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4.数个主体分别实施侵权行为导致矿害发生,在无意思联络的情况下形成共同侵权,应依据侵权责任法第67条根据原因力比例来确定责任分担。在此意义上,侵权责任法第67条是第12条的具体化。侵权责任法第67条将之前普遍适用的连带责任修改为按份责任原则,根据侵权行为的原因力即“污染参与度”承担按份责任。但若依第67条无法查明矿害责任比例时如何确定分担规则,可根据第12条后段得出答案:即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矿业权人与实际采矿经营者分离时责任规则。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宜分如下情况对待:一是矿业权出租时应由矿业权人和承租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矿业权出租目的是进行采矿经营而非通常意义上的使用,加之矿业权为期限物权,出于管理需要将出租视为转让进行管理。但这并非真正权利转让,此时若发生矿害事故,矿业权人仍为法律意义上的矿害责任人,自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矿业权出租亦须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具有一定的公示效果,且承租人进行采矿经营获得利益、制造危险,参照日本、法国、韩国等规定,明定承租人亦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利于受害者的救济。二是矿业权托管经营期间矿害责任由委托人承担。托管经营本质上是具有管理经验和水平的受托人向矿业权人提供劳务服务的行为,其间形成的是委托关系。目前政策层面上只认可全面托管方式。就全面托管而言,矿业权人将矿产资源的开采经营等全面委托给受托人,以托管协议方式约定矿业权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包括发生矿害事故时的责任分担。这种托管经营从法律关系上讲仅约束委托者和受托者,对受害者不具有约束力。从保护善意第三人角度,应当由委托者即矿业权人承担矿害责任后,再按其内部按约定与受托人分担责任。三是矿业权承包经营期间矿害责任应由发包人和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15条、《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38条等规定禁止以承包方式变相转让矿业权,但难免存在违法承包或变相承包方式,此时矿业权人与实际采矿经营者之间处于分离状态,在“河南新密市杨岗煤矿与梁丙辰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认定由发包人先行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后,再按其内部约定向承包人追偿的实践并不具有普遍性,其默认了矿业权承包行为的合法性,其处理结论值得商榷。相反,因非法承包不予保护,在非法承包经营期间导致矿害事故发生,应认定发包人和承包人均有过错构成共同侵权,应依侵权责任法第8条共同侵权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矿业权发生转移时矿害责任承担规则。矿害责任的承担者应当是矿业权人自无异议。但当矿业权发生变动时,对矿业权变动前后发生的损害在原矿业权人和新矿业权人之间如何分担并不明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办法》第12条规定,矿业权转让,则矿业权人的权利义务也随之转移。若矿害责任发生在矿业权转让之后,责任由受让人承担乃属自然;但矿害责任发生在矿业权转让之前时,由于矿害责任并非当然等同于民法上的“义务”,则原矿业权人是否承担矿害责任尚无明确依据。对此有两种不同立法例:一种是损害发生时的矿业权人与受让人对矿害责任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日本矿业法采此例。另一种是损害发生时的矿业权人承担矿害责任,发生后受让矿业权成为采矿经营者不对此等损害承担责任。如果此等损害是在采矿作业期满后出现的,则由最后的采矿经营者承担。该立法例的代表是荷兰民法典。从我国实践情况看,部分法院创设的“债务随资产转移原则”有其合理性,但为保护受害者获得足够赔偿,则发生损害后再转移矿业权的,损害发生时的原矿业权人亦是行为责任人,应与受让人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方才有效避免实践中当事人借助转让矿业权逃避责任情形的出现。
三、多元化责任方式在矿害责任中的活用
(一)矿害责任承担方式有待明确
矿产资源法第32条规定了“赔偿”和“采取必要补救措施”两种责任方式;水法第31条规定的责任方式包括“采取补救措施”和“给予必要的补偿”;煤炭法第27条复垦以将土地“恢复到可利用状态”和“给予补偿”;土地管理法第42条规定“复垦”;草原法第67、68条主要规定了赔偿损失。可见,在我国法律中因采矿行为导致的损害责任方式主要归结为赔偿损失、恢复原状和采取补救措施等三种。赔偿损失适用最为广泛,部分法律涉及的“补偿”宜解释为赔偿更妥当;“复垦”或“恢复到可以利用状态”实际上是恢复原状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其他“补救措施”可视为矿害责任的特殊责任形式,属于民法通则第134条和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侵权责任“主要”承担方式之外的责任形式。但该类规定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对预防性责任方式排除适用并不妥当。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侵权责任法第15、21条规定,当采矿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时,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侵权责任。但实践中,法院很少支持受害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预防性责任方式的诉讼请求。如“铁厂沟镇人民政府等22个单位、米泉市铁厂沟村杨生虎等214户村民与新疆乌鲁木齐矿务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矿务局露天煤矿是自治区的重点建设项目,各行各业均应支持其建设,保证其正常进行。但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承担不得损害他人权益的义务,不得滥用权利。由于矿务局露天煤矿长期使用爆破施工方式,其爆破振动的累积效应导致邻近单位、企业和村民的房屋不同程度的损坏的客观事实存在,矿务局理应承担损害的赔偿责任。对原告等提出的停止侵害等预防性责任方式予以驳回,代之以赔偿损失解决。
第二,恢复原状在矿害责任救济中的作用未得以发挥。矿业活动是典型的危险行为,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地质灾害等问题,危及他人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立法中多强调以赔偿损失或补偿方式对受害者进行弥补,司法实践中也多以经济赔偿方式解决纠纷。但这并未解决持续性矿害责任所带来后遗症的解决。如湖南石门鹤山村因开采雄黄矿导致土壤、水体遭受砷、硫等严重污染,当地民众因此遭受砷中毒、皮肤癌等严重疾病,其根源在于既无有效的经济赔偿机制,也无有效的环境恢复措施,导致矿害污染所致的损害持续至今仍未消除,损害状态还在继续。如今,在很多矿区存在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和生态破坏,未得以有效修复,持续地影响着当地人的生命健康和生态安全,亟待恢复原状责任方式发挥生态复原功能。但囿于成本和可行性考虑,恢复原状责任方式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其对维持利益的救济功能难以发挥。
第三,必要“补救措施”的内涵与外延均不明确。矿产资源法第32条和水法第31条规定,在因采矿等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水枯竭或地面塌陷等损害时,采矿单位应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这种补救措施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责任承担方式,或可理解为替代性责任方式。如“贵州省桐梓县木瓜镇龙塘村老房子32户村民与綦江县赶水矿产有限公司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在恢复原状已无可能的情形下,应该采取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状况相符合的必要的补救措施。考虑到整体搬迁、修建三级提水站、铺建供水管道成本明显太大,且结合渴望工程的实际供水情况,二审法院决定采取每户修建小水窖的责任形式。但实践中,究竟何谓其他补救措施并不明确,应依个案情况而定。
(二)责任承担方式适用的改进建议
依大陆法传统,责任承担方式是被以“提取公因式”的方式置于债法总则或侵权责任法总则中规定,前者如德国民法典第249条、奥地利民法典1323条、台湾地区“民法”第213条等,后者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侵权责任法第15条等规定。修订前的环境保护法及污染防治单行法中,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承担方式包括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两种责任方式,矿产资源法、水法、煤炭法等规定了矿害责任承担方式包括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责任承担方式的改进对确保矿害受害人得到合理救济,促进生态正义和生态公平具有重要意义。[15]
第一,活用预防性责任方式。尽管矿产资源法等并未规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预防性责任方式适用于矿害责任,但从体系解释和逻辑上看,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规定的预防性责任方式可适用于矿害责任。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预防性责任方式在矿害责任中的适用,涉及多方面的利益衡量,“并且排除技术亦必须加以斟酌”。在制度设计上不宜采取在“禁止采矿”及“受害人完全忍受”之间二择一的途径,致使此类诉讼救济的途径成为一种“零和游戏”,而应允许中间排除或部分排除的可能性。[16]P128在民事责任领域,“以软性协商或民主式参与的做法,也逐渐成型,用以取代过度法律抗争式的赛局,避免全输全赢的零和局面。”[17]P140因此,预防性责任方式的内容并非简单的全部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或消除危险这种单一的方式。而是根据不同的具体环境损害情形采用具有预防性功能的责任方式的变形形式,包括部分停止侵害、中间排除妨害、替代赔偿或补偿等方式。原因是“停止行为不仅对事业活动是一个大打击,宽泛地认可停止行为请求的话并不是没有使得有用的社会事业活动被迫停止或废弃的危险。”[8]P31
第二,规范赔偿损失责任方式。赔偿损失是最常用的责任方式,矿害责任将其作为基本责任方式自为恰当,应当将涉及矿害法律中的“赔偿”、“补偿”等规范表述为“赔偿损失”,以免歧义。矿害赔偿包括对造成他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赔偿,亦包括对环境损害本身的赔偿。赔偿损失是对受害人价值利益的赔偿,代表了抽象、宏观的角度,看到的损害是受害人财产总额的减少,所以只能保障受害人的金钱价值利益。[18]对微观的、具体的角度观察矿害责任所致的水体污染、耕地土壤碱化、硬结、地陷、地表水断流等损害,属完整利益的侵害,金钱赔偿并不能全部弥补,不能解决当代人长远利益和后代人环境利益的维持问题,故单独适用赔偿损失责任方式是有缺陷的,可与恢复原状等其他责任方式并用。为保证受害人得到充分赔偿,日本《矿业法》第117、118条和《煤矿矿害赔偿等临时措施法》第4、5条还规定了矿害赔偿准备金制度,由矿业权人按规定标准提存,矿害受害人对矿害赔偿准备金享有比其他债权人优先获得赔偿的权利。矿害赔偿准备金不同于我国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其使用具有专属性,在矿业权人破产时或矿井闭坑后仍可使用该笔资金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第三,强化恢复原状的救济功能。在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恢复原状是首选责任承担方式。恢复原状强调经济合理性,当恢复原状的费用或成本过高时,应当采用经济合理的责任方式。基于生态损害特殊性,诸多国家立法或司法中对生态损害中适用恢复原状责任方式上实行法律保留。如日本尽管采纳金钱赔偿主义,但在四大公害发生后,环保法及司法判例中强调了环境再生的理念。我国矿产资源法矿害责任的恢复原状以复垦、种树等方式表达,司法实践中已有运用的案例。《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不仅肯定了恢复原状在环境司法中的积极运用,并“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在环境恢复性司法理念得到广泛认同的今天,恢复原状作为对完整利益救济的最佳责任方式,可对矿害责任造成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中发挥积极修复作用。法院应在充分考虑可行性和经济性的基础上,优先适用恢复原状以维持受害者长远利益和环境整体利益。
第四,发挥必要“补救措施”在个案中的救济功能。采取必要“补救措施”作为矿害责任的责任承担方式,有别于停止侵害等预防性责任方式,也与恢复原状等责任方式有异,是侵权责任法第15条开放式的列举之外的责任形式。虽对何谓“采取补救措施”无统一解释,但其意旨是应采取合理的措施使侵权所造成的损害得以矫正与弥补,须结合个案情况加以认定。以解决采矿行为致饮用水源、地表水断流为例,可采用措施包括:整体搬迁、修建三级提水站、铺建供水管道、修建蓄水小水窖等,但在选择补救措施时,要坚持“必要性”和“可行性”。如在采矿致居民房屋损害的案件中,有赔偿损失、修缮房屋、加固处理、整体搬迁等多种可选措施,后三种即为“补救措施”,但在选择何者为妥时要充分考虑经济性、可行性和安全性等因素。
注释:
①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临民一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
②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三民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
③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7年第4期,第103页。
④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平民终字第118号。
⑤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豫法民再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
⑥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豫法民终字第407号民事判决书。
⑦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黔高民一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
⑧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1997)晋法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平民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
⑨ 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页。
⑩ 参见刘士国:《侵权责任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0页。
[1] [日]田山辉明.日本侵权行为法[M].顾祝轩、丁相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 刘士国.科学自然法观与民法解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3]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 杨立新.侵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
[5] 曹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考察[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1.
[6] [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M].齐晓琨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 林家彬等.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8] [日]原田尚彦.环境法[M].于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9] [奥]伯恩哈德﹒A﹒科赫、赫尔默特﹒考茨欧.侵权法的统一:严格责任[M].管洪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10] [日]吉村良一.日本侵权行为法[M].张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1] 刘士国.论无过错责任[J].法学研究,1994,5.
[12] 王利明.论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适用[J].中国法学,2010,6.
[13] 李执萍.环境基本法中“环境”的定义考究[J].政法论丛,2014,3.
[14] 张宝.生态破坏致人损害的责任认定[J].绿色视野,2010,10.
[15] 蔡守秋.论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几个问题[J].政法论丛,2013,4.
[16] 叶俊荣.公害纠纷处理之检讨与建议[M].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1990.
[17] 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18] 李承亮.侵权责任法视野中的生态损害[J].现代法学,2010,1.
(责任编辑:黄春燕)
Rules and Ways of Liability on Mining Damage
HuWei
(Law School of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8)
Liability of mining damage in our country did not receive due attention. The regulation rules are very simple and they can’t provide effective relief for victims. The tension formed between the system supply and demands of justice. The legal liability of danger should be taken as the foundation of it, and its legal structur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no fault liability.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judicial regul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t liability mining damage, the rules of liability of mining damage should be refined. And we should clarify the ways to assume liabilities, and provide complete relief for the victim.
liability of mining damage;rules of liability;ways of liability
1002—6274(2015)02—119—08
本文系刘士国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金属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236)的阶段性成果;作者主持的贵州大学重点学科特色学科重大项目《交往行为理论与民法解释范式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GDZT20120009)的阶段性成果。
胡 卫(1978-),男,贵州毕节人,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法总论与民法解释学。
DF468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