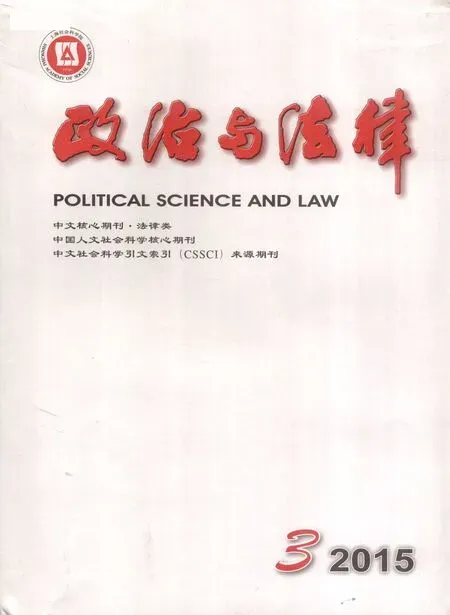债权让与性质斟酌及其类型化尝试
2015-01-30谢潇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谢潇(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债权让与性质斟酌及其类型化尝试
谢潇
(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债权让与的法律性质是一个债法(或者说合同法)中的经典问题,学界对此颇多争议。比较法上的关于债权让与性质的讨论由于理论路径与历史嬗变的不同,呈现出较大差异。事实上,债权让与因债权充当支付手段抑或交易标的而呈现出不同性质,民法理论中的准物权行为说、债权合同说与事实行为说均难以对债权让与的性质作出圆满而统一的解释,故而应以类型化的方法将债权让与区分为标的型债权让与和支付型债权让与,并配置不同的法效解释规则,乃至引入新的法律条款,方能明晰债权让与的法律性质,适应关于债权让与的实务需求。
债权让与;类型化;标的型债权让与;支付型债权让与
我妻荣先生曾在其煌煌巨著《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中指出,“人类在仅依物权形成财产关系、仅以物权作为物权财产客体的时代,可以说只能生活在过去和现在。但是,承认了债权制度,就可以使将来的给付预约,变为现在的给付对价价值”。①[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诚哉斯言,债权制度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商业的发展,而且取得优越地位的债权甚至成为了“法律生活的目的”,②同上注,我妻荣书,第7页。日益活跃在流通领域,债权交易成为了常态。然而,同灵活多变的债权交易现实相比,以我国《合同法》第80条至第83条为代表的债权让与制度却显得十分简陋。学术界对债权让与的法律性质虽多有探讨,但一方面仍众说纷纭,未有通说,另一方面则大多借鉴外国立法例与学说对债权让与的法律性质进行简单的统一界定,而少有关于债权让与法律性质的严格而细致的分析。性质界定的混乱必然导致制度建构无从入手,以致现实问题处理之无章可循。因此,透过法制史、比较法与实例研习,引入类型化思维,从解释论与立法论的角度探究债权让与性质统一论之弊与债权让与类型化的新规则,将颇具实益。③本文所指的债权让与系指非证券化债权让与。就证券化的债权而言,债权的让与呈现出商事交易的特点,具有迅捷性、公示性、排他性的特点,因而在理论上将此类债权的让与视为类似物的交易,由证券法和物权法进行规制是较为妥当的,同时在立法上,我国《物权法》有关权利质权的规定也暗含了这种趋势。
一、法制史与比较法上的观察
可以肯定的是,大陆法系的债权让与起源于罗马法,不过,“罗马法关于让与债权之理论,不甚发达,循序渐进,方式亦多,直至帝政时代,始成完备之制度,组为现代法例之典型”。①陈朝璧:《罗马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早期罗马法对债权让与持否定态度,其缘故在于,经典罗马法定义中,债为“法锁”,其在概念起源上意为以非物理的法律方式将当事人置于枷锁之中,②See Reinhard Zimmermann, The law of Obligations: 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 Juta & Co, Ltd, 1990, p.5.罗马法之债是具有人身属性的法律关系,是不可转让的。③See J. T. Abdy, Bryan Walker, The commentaries of Gaius and Rules of Ulpian,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of Press, 1885,87-88.在早期罗马法中,若要实现债权事实上的移转,则通常须通过债的更新,即旧债的消灭与新债的生成,来迂回实现债权移转之目的。④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认为:“如果我想把某人欠我的东西给你,我绝不能采用哪些据以向他人转让有形物的方式,而必须让你在我的准许下同他人达成要式口约;这样将使得他人摆脱与我的债务关系并且开始向你负债,这被称为债的更新。”参见[古罗马]盖尤斯:《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版,第63-64页。早期罗马债法反对债权让与的原因在于当时债的概念中人身属性色彩浓厚,履行债务的方式中包含对债务人人身的强制。⑤如罗马《十二表法》中第三表就规定,倘若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且无人为其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则债权人有权把债务人切成肉块。参见徐国栋、阿尔多·贝特鲁奇:《〈十二表法〉新译本》,纪蔚民译,《河北法学》2005年第11期。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债务奴隶制被废除,债权逐渐成为一项纯粹的财产权,从而排除了债权让与在经济、社会领域的障碍。在后期罗马法中,债权让与乃是通过将债权让与之受让人视为债权人的代理人而予以部分实现的,债权让与之受让人自裁判官处可获得一项对债务人的债务清偿请求权,从而事实上获得了债权人之地位。⑥See Rudolph Sohm, The Institutes: a Textbooks of the History and System of Roman Private Law, translated by James Crawford Ledli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07, p.425-428.而随着近代继受罗马法的大陆法系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勃兴,出现了“债权财产化”的现象,债权(尤其是金钱债权)成为了完全而独立的纯粹财产权,具有高度流通性。⑦我妻栄=有泉亨=清水誠=田山輝明『我妻·有泉コンメタール民法―総則·物権·債権―』,日本评论社2010年,第845页。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陆法系的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民法普遍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债权让与制度。⑧陈静娴:《合同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大陆法系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债权让与概念因其所属法系支系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的差异。如在我国台湾地区,债权让与通常被定义为“系指不变更债之同一性,由债权人与受让人合意,将其债权移转于受让人之准物权契约。”⑨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日本法学界通说则认为,债权让与指不改变债权内容而将它移转于他人的合同。⑩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05页。日本学者北川善太郎给出了较为完整的定义,其认为债权让与乃是在保持债权同一性的前提下以移转该债权为目的的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诺成、不要式的合同,属于具有债权处分性质的准物权行为。⑪同上注,韩世远书,第405页。德国民法中的债权让与也具有相似的性质。⑫同上注,韩世远书,第405页。而在法国民法中,债权让与制度相对来说并不发达,在法国,合同转让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引起立法者的重视。法国民法典将债权让与规定于第六编“买卖”下的第八章“债权与其他无形权利的转让”中,但是并没有像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那样相对应地规定债务承担;并且,在法国民法中,债权让与也并不是一个在学术界形成了共识的法学概念,法国民法学者通常讨论的是“合同转让”。⑬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388页。总体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均承认债权让与合同的有效性,并且各大陆法系国家的债权让与在概念上也没有太大差异。①但是因大陆法系分为德国法系和法国法系,又因德国法系奉行物权行为理论,在处理债权让与性质的问题上,大陆法系的两大分支仍有分歧。
英美法系国家对债权让与的承认则经历了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早期英国普通法判例认为债权乃是特定人对特定人的权利,债权让与一方面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②有英美法学者认为“在一个对违约的债权人施以严厉制裁、信用仅发生微弱作用的社会中”,一项债务对债权人来说具有“人身性质”的规则是合理的。参见[美]E·艾伦·范思沃斯:《美国合同法》,葛云松、丁春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9页。另一方面则可能增加讼争,加重法官的工作负担。③如科克法官(Lord Coke)就指出,允许让与合同权利“将导致争议和诉讼的数量激增”。参见[美]E·艾伦·范思沃斯:《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0页。不过和罗马法有关债权让与制度发展的历史相似的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债权让与成为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诚如Macleod所言,“如果有人问我们——是谁完成了对人类财富最为影响深远的发现?我们认为,在深思熟虑之后,我们可能会较有把握地回答——是首次发现债权是一种可流通商品的那个人”。④转引自前注③,E·艾伦·范思沃斯书,第699页;并参见杨桢:《英美契约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9页。经济的发展使现金交易行为的重要性下降,债权的财产属性、长期存在性、收益性使债权让与成为商业常态。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的普通法院仍旧墨守成规,拒绝对债权让与给予充分救济。⑤不过普通法院也并非没有任何让步,比如让与人进行让与的目的在于清偿其对受让人所负债务时,普通法院仍旧会例外地给予救济。参见前注③,E·艾伦·范思沃斯书,第700页。17世纪,英国的商人们转而寻求衡平法院的帮助。大法官法庭不像普通法院那样敌视债权让与,相反,它认为债权受让人为取得债权付出了代价,因此理应获得保护。衡平法院在保护债权受让人方面具有突破性的举措是赋予了债权受让人独立的请求权,而非仅仅将其视为让与人的代理人,这使得债权让与纠纷主要集中于衡平法院。普通法院见此情势,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开始对债权受让人进行较为充分的保护。不过在普通法中,从判决的表面措辞来看,债权受让人仍须遵循诉讼的相关形式要求,以让与人的名义起诉。可以说,债权让与制度在英国的生成“主要归功于衡平法与普通法之间的竞争”。⑥同前注③,E·艾伦·范思沃斯书,第700-701页。
英美法系对债权让与并没有进行概念问题的讨论,这大抵与英美法系更为重视实际操作,疏于概念的逻辑梳理的缘故有关。但就美国法而言,《合同法第二次重述》第317条给债权让与下了一个定义:“债权让与系让与人作出的转让该权利的意思表示(manifestation),正是基于这一意思表示,让与人的权利才得以转让。”⑦Se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American Law Institute's Restatement of the Law of Contracts with Annotations to the Washington Decisions, 9 Wash. L. Rev. 87 (1934).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迥异于大陆法系通常理念的债权让与性质:第一,债权让与本身并不是一个双方意思表示,其只是债权让与人的单方意思表示;第二,债权让与也不是一种履行行为,其只是债权让与人表示将作出债权移转行为的允诺;第三,债权让与作为一种允诺,是债权受让人最终取得债权的效力依据。倘若仅从这一定义出发,则会发现,美国法上的债权让与,似乎更像是一种单方行为,即债权人声明其债权让与他人,则他人即因债权人的声明而获得债权,换言之,债权让与仅依债权人单方意志即可实现。不过英美法学者大多认为债权让与是一项普通的涉及债权安排(Assignment)的合同,⑧See Neil Andrews, Contract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26-227.并且被让与的债权只能是让与人因合同而自第三方处获得的利益,⑨See Paul Richards, Law of Contract, Person Education, 2007, p.523.即纯获利益的债权(尤其是无负担的金钱债权)。
二、实例研习:不同法域的思维模式比较
经由法制史与比较法的简要考察,可知大陆法系(主要是德国法系)与英美法系在债权让与法律性质的选择上相异,然而这种差异是否具有实益呢?兹以较为典型的债权让与和其原因行为关系问题与双重债权让与问题为例进行探讨。
(一)实例一
设甲为债权人,乙为债务人。后甲与丙订立买卖合同,购买一台电视机。丙很快将电视机交付给甲,但是甲并没有向丙给付价金。后甲与丙订立债权让与协议,约定甲将债权让与给丙,作为价金之替代物。债权转让协议生效后,甲及时通知了乙,乙也及时向丙清偿了债务。之后不久,甲发现丙卖给自己电视机时隐瞒了该电视机存有重大瑕疵的事实,遂以欺诈为由,诉至法院,撤销了甲与丙之间的买卖合同。此时甲与丙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效力如何?
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对此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是,甲与丙订立的买卖合同因撤销而归于无效,债权让与协议作为准物权行为,具有无因性,该买卖合同的无效并不影响债权让与协议的有效性,但是丙因甲之缘故而从乙处获得金钱,此时丙获得金钱的法律上的原因已经丧失,因此甲可以依不当得利法请求丙返还乙支付给丙的金钱。
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建基于将债权让与定性为准物权行为的准物权行为说。准物权行为说认为债权让与和其原因(如赠与、买卖)是区分的,①川井鍵、鐮田薰:《現代青林講義·債権総論》,青林書院1999年版,第177页。例如甲和乙约定,乙将其自行车出卖给甲,甲将其对丙的债权让与给丙。在该种约定中,甲和乙首先基于合意成立了一个买卖合同,同时又基于履行合同的目的达成了一个债权让与合意,该合意便是债权让与合同,而甲与乙之间的买卖合同便是该债权让与合同的原因。针对“债权让与合同的效力是否受原因效力的影响”这一问题,大陆法系存在有因说与无因说两大学说。②林良平、石田喜久夫、高木多喜男:《現代法律学全集8債権総論(改訂版)》,青林書院1987年版,第173页。采无因说的学者认为,债权让与合同乃是典型的处分行为,或称准物权行为,其所涉及的债权移转效果何时发生的问题与物权变动、物权行为理论问题十分类似,因此以物权行为理论类推适用于债权让与,使债权让与无因化乃是十分自然的事,③同上注,林良平、石田喜久夫、高木多喜男书,第173页。这也与债权摆脱人身属性,渐次拥有财产属性的近代化趋势相吻合。④同前注⑨,川井鍵、鐮田薰书,第173页。采有因说的学者则认为债权让与和物权契约不同,因为债权让与合同通常为原因(例如买卖合同、赠与合同)所包涵,两者的区分没有物权变动原因与物权契约那么明显,而更为重要的在于,债权让与的意思表示欠缺外部公示,债权让与不以在原因之外另行订立合同为必要,因此采无因说既在逻辑上没有充分理由,又于实务上难以操作,采有因说则较为妥当。⑤石川利夫、尾中普子:《債権法講義概說》,評論社昭和58年5月10日初版發行,288頁。从大陆法系各国立法例来看,采无因说者有之,如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采有因说者有之,如瑞士与日本。债权让与无因性问题在这些国家均与其物权行为理论有一定联系,各国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债权让与无因性的立法。
英美法系的观点则简单得多,在英美法上,只要债权让与协议本身没有瑕疵,其便是有效的。不过在上述设例中,因甲与丙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甲需要向丙返还电视机,而丙取得债权并接受乙清偿相对于甲来说便是一种无偿取得了。在美国合同法中,无偿的债权让与因丧失对价而具有可撤销性。⑥同前注③,E·艾伦·范思沃斯书,第718页。此时,甲可以向法院主张撤销该债权让与,并主张丙向其返还不当得利(unjust enrichment)。
大陆法系(主要是德国法系)与英美法系对该问题的处理在结果上似乎是一致的,都是促成不当得利的返还,不过具有差异的地方在于是否维持债权让与本身的效力。大陆法系(主要是德国法系)认为债权让与的效力如同物权行为一样,具有独立性与无因性(至少是相对无因性),因此债权让与效力应当予以维持以保护交易安全。不过一般的债权让与在大多数情况下欠缺公示外观(证券化的债权可能因具有纸质载体、电子载体和登记而具有公示方法),因此径直将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理论类推于债权让与略显牵强。英美法系则将债权让与视为一种允诺,将债权让与合同视为允诺的组合,认为基础合同的消灭将导致嗣后的债权让与成为没有对价的合同,因此债权出让人自然有权以此为由撤销合同,并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英美法系的处理方式比较符合债权作为相对权的特点,逻辑也更为简单,并且取得了和大陆法系一致的法律效果。
(二)实例二
设甲为债权人,乙为债务人。后甲与丙、丁先后订立了债权让与合同,两份债权让与合同效力如何?若甲先后通知乙其与丙、与丁订立债权让与合同事实,则乙应当向谁作出清偿?若甲先行向乙通知其与丁之间订立了债权让与合同,乙则向丁为清偿,此时债权让与合同效力如何?
我国台湾地区的处理方法是,首先,债权让与为准物权之处分行为,因此债权一经让与即有效成立。在本设例中的“双重债权让与”情形中,第一次债权让与合同应为有效。至于第二次债权让与,按照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46条的规定,应当因合同标的自始给付不能而无效。①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页。但是倘若甲先行向乙通知其与丁之间订立债权让与合同的事实,并且乙已经向丁进行了清偿,则发生“表见让与”之效力,即基于甲向乙作出的通知,赋予乙对丁所为之清偿以法律效力。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中,可以进行债权让与通知的人既可以是受让人也可以是让与人。不过,在发生“表见让与”效力的情形,则必须由让与人作出债权让与通知,否则不生“表见让与”效力。
“表见让与”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界存在争论:如果债务人明知让与合同不存在或无效,是否也发生表见让与之效力呢?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意见各殊。孙森焱教授认为“债权人让与债权之通知,牵涉受让人之利益,债务人既受债权人之通知,惟有向受让人履行债务,至于让与契约是否有效,为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利害关系之认定问题,不宜因债务人对让与事实之存否有所认识而负担危险”;②参见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1997年8月修订10版,第707页;转引自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1页。而邱聪智教授则认为“惟此见解(笔者注——指孙森焱教授的观点),与法律不保护恶意之原则有背,是否妥当,不无商榷”。③参见邱聪智:《民法债编通则》,1997年修订6版,第464页;转引自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2页。可以说,孙森焱教授的着眼点在于风险负担的分配与债权让与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的分离;邱聪智教授则更加注重民法之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不过公平正义之理念因个案而异,不宜作为一般性规则。在“表见让与”中,债务人善意与否是一个较为模糊的问题,并且法律不应在此课以债务人过重的义务,因为就算债务人知道债权让与无效的事实,但是债务人依债权人的通知行事,在法律上也并无多大的可责难性。债务人的恶意不应当成为阻却“表见让与”成立的事由。
德国自2002年债法现代化法改革后,在民法典中删除了契约自始客观不能给付则契约无效的条款,转而认为自始客观不能给付的契约本身是有效的,④杜景林、卢谌:《德国债法改革——〈德国民法典〉最新进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页。但是该契约无法产生给付请求权,而是次生出损害赔偿请求权以维护相关权利人的利益。若依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的规定,则甲与丙、甲与丁之间的合同均为有效,只是在甲和丙订立债权让与合同之后,因债权已被处分,所以甲和丁再行订立的债权让与合同成为了自始客观不能给付的合同(事实上变成了无权处分),乙因甲的通知而对丁作出清偿则可类推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定,由丁善意取得债权(前提是丁是善意的),丙则可以向甲主张损害赔偿。如果丁为恶意,无法善意取得债权,那么丁可以依合同本身向甲主张违约损害赔偿。这种处理方法可谓逻辑井然,不过略显繁琐。
英美法系的处理方法则更为灵活。以美国法为例,甲所订立的两个债权让与合同都是有效的。不过债权让与合同本身并不直接导致债权的归属。当发生甲先后与丙、丁订立债权让与合同的情形时,则构成美国合同法上的竞争性债权主张问题。竞争性债权主张问题在美国合同法上有三种解决方法。第一种规则称为纽约规则(New York rule)。根据纽约规则,应由第一受让人取得债权,这符合发生在前的权利优于发生在后的权利之基本法律原则。不过纽约规则刚性有余而灵活度不足,该规则认为即使第二受让人已经受领了债务人的给付,第一受让人仍享有优先权,可以向第二受让人主张返还。支持这一规则的理由比较混乱。有的法院以“相同的衡平法权利,则成立在先的优先”为根据来解释第一受让人的优先权;有的法院还认为经过第一次债权让与,债权人已经失去了债权,因此他手上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转让了。①同前注③,E·艾伦·范思沃斯书,第733页。后一种说辞倒是和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思路是一致的,只是缺少一种精致的概念逻辑将其整合起来。第二种规则称为英格兰规则(English Rule)。根据英格兰规则,原则上第一受让人享有优先权,除非第二受让人已经先于第一受让人向债务人进行了债权让与的通知。②See Dearle v. Hall, 38 Eng. Rep. 475,492(Ch. 1828).适用该规则的法院解释说,这一规则能够鼓励受让人尽快通知债务人。第三种规则称为马萨诸塞规则或者四个马夫规则(Massachusetts rule or four horseman rule)。马赛诸塞规则仍旧在原则上承认第一受让人的优先权,但是对该优先权设置了许多阻却事由:其一,第二受让人受领了债务人支付的款项,或者以其他方式实现了债权;其二,第二受让人对债务人获得了一项胜诉判决;其三,以更新(novation)的方式与债务人订立了新合同或者占有了象征性的书面文件。该规则突破了英美法原先对衡平法权利的绝对保护,可以说体现了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③See the Article 173, Article 326 of American Law Institute's Restatement of the Law of Contracts with Annotations to the Washington Decisions;转引自前注19○,E·艾伦·范思沃斯书,第734页。由此,本设例若依美国法,则会因适用规则的不同而产生不同效果:在纽约规则下,丙取得债权。丙可以向丁主张返还债权。而在英格兰规则下,可以认为甲对乙的通知同丁对乙的通知具有同等效力,则应由丁优先取得债权。在“马赛诸塞规则”下,因为丁已经受领了乙支付的款项,因此丁取得债权。由此也可以看出,债权让与在美国法上基本被作为合同对待,只是在合同履行的问题上会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英美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合同”这一术语持较为开放与宽泛的态度,如Treitel便将合同定义为“能够产生债并为法律所承认的协议”,④See Treitel, The Law of Contract, Sweet & Maxwell, 2011, p.1.而美国合同法更是将合同视为“一个允诺或者一组允诺,对它的违反将导致法律提供救济或者对它的履行法律视为之义务”,⑤See A. W. Brian Simpson, A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of Contract: The Rise of the Action of Assumpsit,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5, p. 6.这一定义甚至把大陆法系通常视为单独行为的法律行为也纳入了合同的范畴。英美合同法上合同外延的宽广性与其没有德国法系式的抽象法律行为概念有关,尽管其地域性的解决方式使得债权让与的处理规则不能统一,但是英美法系将债权让与视为普通合同予以处理的方法,的确比大陆法系更为简洁和便利。
(三)实例应对的思维模式比较
在双重债权让与问题的处理上,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两大法系的特点:大陆法系坚持认为一经债权让与,债权已经为相对人所有,原债权人再行让与债权事实上构成了无权处分,围绕无权处分的问题又进而富有逻辑性地推导出表见让与的问题,却最终陷于交易伦理与交易安全的战场。英美法系的处理方式则较少逻辑色彩,更多地关注实务的解决,其首先认为债权经两次让与并没有真正归于任何一个受让人手中(纽约规则除外),所谓的双重债权让与问题实质上就是受让人相互竞争主张债权的问题。故而在英美法上,债权让与并不涉及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系)会面临的债权无权处分问题,债权让与的真正实现,依赖于债权人的权利主张行为,债权让与本身在英美法上并无德国法意义上的即时处分性格,只是单纯的允诺而已。同时,大陆法系选择了“原因——结果”模式探讨债权让与诸问题,并且纠缠于债权让与有因或无因的问题,而英美法系通常不考虑债权让与的有因无因性问题,只是将其纳入合同法领域,作为一项普通合同对待,在债权让与原因合同无效时,径行以债权让与合同丧失对价为由,而令债权让与人可撤销债权让与合同并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与大陆法系相比,这一路径更为简洁。
不过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讲,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债权让与法律性质的界定均具有浓厚的历史沿革意味,可以称之为文化影响下的自然选择。例如英国普通法中甚至至今保留着让债权受让人以原债权人名义起诉的程式要求。日本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比较法’就像魔女诱惑性的歌声,常常会以学习外国法、将其本土化作为诱人的口号”,①[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对于我国这样典型的继受法国家而言,比较法的材料只能作为债权让与性质问题的一种学理参考,而不能简单模仿。
三、统一论斟酌与类型化尝试
(一)债权让与性质统一论斟酌:对既有学说的评述
我国学界对债权让与法律性质的学说解释主要有两种,即准物权行为说和债权合同说,②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债法总则编、合同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这两种学说基本为大陆法系思维与英美法系思维在我国学理上的分别展现。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依循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传统,将债权让与的法律性质定性为准物权行为,③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并参见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72页。并且如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那样对债权让与的有因性与无因性进行了讨论,④我国《合同法》对债权让与的有因性与无因性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学说上亦分歧严重,大致有相对的无因行为说和有因行为说两大类主张。相对的无因行为说认为债权让与原则上为无因行为,原因的有效与否并不影响债权让与的效力,债权让与的原因无效时,债权人可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受让人返还因受让取得的利益,并认为债权让与不是绝对的,可以由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排除,即当事人可以约定使债权让与合同与原因行为相关联,原因行为无效,其让与行为亦无效。有因行为说则认为债权让与的效力受原因影响,原因无效时债权让与也无效,不过例外地承认票据行为等债权让与行为的无因性,以满足商事交易的要求。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11页。但是并没有脱离德国法的窠臼。不过德国民法学说之所以将债权让与定性为准物权行为,并非渊源于对债权让与性质的深层次学理探究,而是将物权行为理论与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二元区分理论径行类推于债权让与的结果,这只是一种学术路径依赖的表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思考的产物。对于我国的立法及法学理论而言,在没有对继受物权行为理论达成无争议共识的情况下援用准物权行为说解释债权让与的法律性质,则更加欠缺解释力与说服力。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从英美法国家处理债权让与的理论与实务出发,总结出了债权合同说。债权合同说认为,债权让与本质上是一个无名合同,在法律适用上主要参照我国《合同法》的总则、买卖合同和赠与合同部分。主张债权合同说的学者认为债权让与通常与所谓的原因行为(或称基础行为)是融为一体的,因此应对债权让与及其原因行为做整体把握与判断,①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页;余延满:《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页;翟云岭:《合同法总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6页。并且提出了我国现行立法例选择了债权合同说的坚实理由,即“第一,我国民法学界几乎一致否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从维护民法财产权变动体系的一致性的角度出发,自然不能将债权让与视为一种准物权合同。第二,就法理而言,将债权让与视为一般的债权合同更为合理,符合债权的特性。第三,根据我国法律,债权让与原则上是一种无名合同”。②参见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债法总则编、合同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以上两种学说,既有因袭传统的,也有服膺现行法的,却欠缺对债权让与真正意义上的严格分析。诚如卡尔·拉伦茨所言:“法律专家通常严格区分‘基于现行法’以及,‘由将来适当的法律’出发所作的陈述……并非所有法律政策上恰当的结论,均可在现行法的范围内,借方法上确实可靠的解释或法的续造来实现。”③[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4页。因此径行从立法论出发探究债权让与的法律性质则可以成为一条更加妥当的路径。
就准物权行为说而言,债权让与能够被定性为准物权行为的理念支撑有二:其一,债权让与是处分债权的行为,其乃是一个处分行为;其二,债权是一种物或者可以被拟制为物,具有可流通性,因此通过物权行为理论来解释债权让与是可行的。这两大理念支撑有两大隐性条件:其一,该法域存在物权行为,其二,被让与的债权具有确定的物之属性或拟制物属性。不过我国目前并不具备这两大条件,其缘故在于,在制度建构方面,我国《物权法》十分明晰地否定了物权行为理论,④我国《物权法》第15条确立了物权区分原则,即将物权变动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在效力上予以区分,物权变动与否并不影响物权变动原因行为的效力,但是我国《物权法》并未在物权变动领域增设物权行为的规定。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物权法》所采纳的是源起于奥地利民法典的“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不过也有少数学者(如孙宪忠和李永军)认为我国法已经承认了物权行为。⑤ 另外一种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甲和乙订立了买卖合同,约定甲以80万元购买乙之商品,后双方对买卖合同进行微调,甲以其对丙的100万元债权作为80万元的代替物交付给乙,以作为对买卖合同之履行。此时债权让与具有代物清偿之性质。这使得准物权行为说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将债权让与解释为准物权行为缺乏立法上的支撑。同时,就债权性质而言,债权本身不具有物之属性,虽然债权同物权同属财产权,但是债权严格来说只是物的信用替代品,其仍然具有平等性、相容性等特性,几乎不具有排他性,用准物权行为来解释债权让与显得颇为牵强。此外,与物的买卖不同,一般债权的让与通常并不需要交付与登记,债权让与并不具有公示性的一般要求,债权也没有被拟制为物的法理基础(证券化的债权则具有被拟制为物的可能性),所以准物权行为说并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与债权性质,不足采纳。
相较于准物权行为说而言,债权合同说显然更为契合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同时也注意到了债权让与中以债权为标的物出卖这一情形与买卖合同的相似性,故而包含更多的合理性因素。不过进一步探究会发现,债权合同说也有不尽周延之处。债权合同说在解释单纯的债权让与中具有优势,例如甲对乙有一个100万的债权,后甲将之以50万的价格让与给丙。在该债权让与中,债权让与就是一个类似于买卖合同的无名合同,用合同说解释能较为圆满地解决债权让与的性质问题。但是假设甲与乙先行订立了一份买卖合同,在此之后甲又与乙约定甲以100万元的债权交换乙的商品,以该债权充当价款。⑤在这里,甲将100万债权让与给乙的行为究竟是一个合同还是一个单纯的履行行为呢?如果是一个合同,它是否受作为原因行为的互易合同之效力的影响呢?债权合同说并没有对这种情形给出较为圆满的答案。
除了以上两种较为流行的学说以外,也有学者为了解决前述学说的困境,提出了“事实行为说”。该学说将债权让与和债权让与合同进行了进一步区分,从而认为债权让与本质上是一个事实行为,并以英美法文献为例证,认为债权让与本质上是债权的转让行为,而不是一个合同(一项允诺)。①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4页。不过细究起来,该学说有将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缺陷。在债权让与中,一旦双方达成就债权的让与合意,则债权已经随合意的达成而发生转移;只是在债权出让人未通知债务人时,这种让与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罢了。因此,在债权让与中并不存在一般合同所具有的合同履行问题,事实上并无债权让与和债权让与合同的区分,债权让与本身就是一个以权利的即时移转为内容的合同。而就英美法系部分学者将债权让与和合同进行区分的问题而言,其缘由在于英美法上的典型合同受对价(consideration)理论支配,而债权让与有时是以赠与的方式实现的,故严格以英美法理论来看待债权让与的话,则会认为债权让与不一定是一个具有对价的合同。不过我国语境下的合同并不要求对价,因此英美法语境中的债权让与在我国理论的映射下其实就是一项合同。诚如范思沃斯所言,“由于合同权利也属于一种财产,因此调整这种权利转让的很多法律规则,类似于财产法上调整土地和动产移转的规则”,②同前注③,E·艾伦·范思沃斯书,第695-696页。值得注意的是,持“事实行为说”的学者引用的正是范思沃斯的语句,以支持“事实行为说”,即“需要牢记的是,债权让与是债权的转让行为,而不是一个合同(一项允诺)”。参见前注19○,E·艾伦·范思沃斯书,第695-696页。英美法上的债权让与在其理论体系中类似于与英美法中与合同既相似又不同的契据,本质上是一种协议,③在美国财产法上,要转让不动产,只有合同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合同以外制作具有双方合意内容的书面契据(deeds)予以交付。有学者甚至认为契据制作与交付行为就是英美法上的物权行为。参见吴一鸣:《契据交付:英美法中的“物权行为”——历史的巧合还是生活的必然?》,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秋季卷,第335-351页。但以我国理论而观之,这种契据其实就是一种合同。因此可以说英美法上的债权让与其实仍旧是一种合同。故可以说,债权让与“事实行为说”既不符合法理,亦无比较法上的依据。
职是之故,统一论下的准物权行为说、债权合同说与事实行为说均无法较为妥当地解决债权让与的性质界定问题;类型化方法则是一种可期待的替代性思维框架。
(二)法效果的妥当性安置:债权让与类型化探微
1.类型化方法与类型化基准的择取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提出了本体论的一项重要原理,即“当若干事物虽然有一个共通的名称,但与这个名称相应的定义却各不相同时,则这些事物乃是同名而异义的东西”。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页。换言之,在语言学意义上,某一概念所涵盖的外延可能包含了内涵方面各各不同的事物,也正因为此,倘若某一事物无法用统一化概念予以充分定义的话,则很大程度并非语言的问题,而系事物本质所致。⑤德国法学家考夫曼认为,对于类型理论而言,法学家们发现事物的本质是划定法律上各种事物类型的基础。参见[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87页以下。对于法律体系中既有的概念而言,倘若在统一论之下概念无法推导出统一的法效结论,则不应强行将法效结论统一化,而应对形式上统一而实质上包含殊异性因素的法律概念进行类型化的方法论处理,从而以妥协的方式祛除学说理论的目的性偏好,完成不同情形的法效妥当性安置。
仔细分析债权让与,亦可发现在债权让与中也存在“同名异义”的修辞现象。这一修辞现象的出现并非人们刻意而为之,而系法律发展的历史积淀所致。前已述及,在罗马法(尤其是古典罗马法)上,债为法锁,乃债之关系双方的特别结合关系,与第三人无涉,故债权在诞生之初仅仅只是一项工具性权利,其本无交易价值,罗马法也不允许债权流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诚如我妻荣所判断的那样,债权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这一经济地位使得债权(尤其是应收账款)获得了交易价值,成为了可供交易的制度物。在债权获得交易价值之后,最容易发生的债权让与现象为买卖债权。由于债权通常具有债务履行期,且与债务人的资力联系紧密,很多债权人为获取现金或者规避风险而愿意将债权出售,由此,最初的债权让与实质上就是以债权为标的之买卖合同。嗣后,随着金融业与信用体系的发达,债权逐渐在清偿债务方面发挥出了类似货币的功能,即在实务上,以有价值的债权(通常在经济与会计事务中称之为应收账款)清偿在买卖合同、承揽合同中的价款债务。而在这一类型的债权让与中,债权所充当的便不是交易标的物,而是类似货币的支付手段,并且在这一类型的债权让与中,债权让与明显存在一个与之有联系的在先合同——而这一在先合同在以债权为出售标的的债权让与中并不存在。基于此,依据债权在债权让与中所充当的角色的不同,可以大致将债权让与类型化为以下两类:其一,将债权作为一种可买卖、赠与的标的,直接以债权让与的方式获得相对人的价金;其二,将债权作为类似于货币的支付工具或者代偿工具,以清偿债务。就第一种类型而言,债权乃是以合同标的之身份登场的,因此这时的债权让与本身就是一种类似于买卖合同或者赠与合同的无名合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第二种类型而言,因债权乃是充当了类似于货币的支付工具的功能,所以债权让与呈现出与原因行为(如互易合同)相分离的态势,此时的债权让与实质是一种支付行为,而该支付行为又属于交付行为的一种——这又回到了类似物权行为理论讨论的老路上去了:要不要承认该交付行为是一种独立的合同;或者认定该交付行为只是一种单纯的合同履行行为?①事实上,有学者注意到了债权让与的交付行为性质而提出了“事实行为说”,即债权让与合同与债权让与是两个不同的行为,前者是旨在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之债权行为,后者则是债权自其主体处移转到受让人之手的过程。在不承认物权行为制度及理论的背景下,债权让与乃是一种事实行为。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事实上这和是否承认物权行为一样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物权行为理论下,债权让与是一项独立的法律行为,并且是抽象的无因处分行为,其效力与物权行为一致,故常称之为准物权行为。不过鉴于我国并未完全继受物权行为理论,②我国通说认为我国《物权法》并未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如崔建远教授认为,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我国《物权法》只是区分了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而没有区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故我国《物权法》并未采纳物权行为理论;陈华彬教授则在批评物权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现行《物权法》没有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并且断言“我国《物权法》及将来的民法典等民事立法不采此项理论和制度,毫无疑问,乃为完全正确的抉择”。参见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参见陈华彬:《民法物权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151页。不宜将这种以债权作为标的为支付的行为认定为准物权行为,同时也不应将其视为一项单纯的事实行为,因为在债权让与中,确实包含了当事人的意志。德国法式的“原因——结果”区分的法权模型包含着对债权让与正当性的原因思考,尽管在法理上具有非凡的魅力,但在未继受物权行为理论的条件下,却显得有些另类。而英美法式的将债权让与视为在先合同之关联合同的做法却具有借鉴意义,即不用去讨论债权让与的有因性与无因性的问题,只需要关注债权让与作为一项合同,其是否对其他合同具有目的上的从属关系。仔细分析,将债权作为类似于货币的支付工具或者代偿工具的债权让与,毫无疑问,这一类债权让与是为在先的合同的价款债务清偿服务的,故应当将在先的合同认定为主合同,而将债权让与认定为该主合同的从合同,倘若作为债权让与目的之主合同消灭,目的既失,债权让与合同自应一同消灭,而债权让与合同消灭之后,则依不当得利法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损益关系。因此,倘若以“主合同——从合同”的法权模型替代“原因——结果”的思维模式,既能克服“准物权行为说”所带来的不必要的学理繁琐,也能涵射“债权合同说”所忽略的债权让与和其目的合同常常出现分离之情形,更具法理上的解释力。
2.债权让与类型化尝试
论述至此,可知债权让与的法律性质是一个难以整理出统一学说的问题,故对债权让与性质作统一解释难以周延,而应依类型化方法对债权让与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为不同类型的债权让与设置相应的法效规范。根据前述的类型化分析,债权让与可分为以下两类。
(1)标的型债权让与:作为可供交易之物的债权让与
倘若债权是被用作出让之标的,则债权让与宜解释为系一项无名合同,因为此时的债权让与本质上与买卖合同或者赠与合同无异,只不过标的物并非有体物,而是可供交易或者赠与的债权。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作为可供交易之物的债权本身天然涉及第三人(债务人),即使债权受让人与债权出让人和债务人并无关联,债权出让人与债务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也会影响标的债权的可交易资格。当被交易的债权所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有瑕疵而归于消灭时,应当解释为被交易债权丧失标的物资格而灭失。
在法效设置原则方面,由于标的型债权让与和买卖合同和赠与合同的较大相似程度,故原则上有对价的标的型债权让与应以买卖合同为法权原型,类推适用买卖合同的规定;无对价的标的型债权让与则应当以赠与合同为法权原型,类推适用赠与合同的规定。
(2)支付型债权让与:类似货币的作为支付手段的债权让与
倘若被让与的债权是作为类似货币的支付工具或者代偿工具而存在于买卖合同、雇佣合同、互易合同、租赁合同等合同或者类似的无名合同中,则须进一步为类型化分析。
第一种类型是径行在合同中约定以债权为对价的替代价款的支付型债权让与。这一类型的支付型债权让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合同。例如,甲与乙约定,甲承租乙的店铺经商,甲以对丙的债权作为租金让与给乙,此即包含债权让与因素的类似租赁合同的无名混合合同。在这一无名混合合同中,债权让与只是一项不具有独立意义的意思表示,一旦无名混合合同生效,债权即发生让与效力。故这一类支付型债权让与并不需要单独设立规则,其也并非一项独立的合同,只是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的意思表示,在法律适用上依无名混合合同的原理,参照《合同法》总则以及无名混合合同最接近的法权模型适用法律即可,而不必单设规则。
第二种类型是当事人先行订立了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合同,嗣后又达成了债权让与协议,即依一定债权作价支付价款或者租金的支付型债权让与。这类债权让与的特殊性在于,严格来说,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同,盖因其并未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反而一旦生效受让人即取得债权,原债权人即丧失债权,故本质上此时之债权让与乃是披着合同外衣的合同履行行为。合同履行行为的性质在学理上存在较大的争议,①在此问题上我国学理存在巨大争议,即合同履行行为究竟应当解释为事实行为还是包括物权行为在内的处分行为。通说认为我国并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故合同履行行为通常并不能被解释为一项独立的物权行为,其性质上系属事实行为。但基于交易便捷与嗣后的充分救济之考量,如前所述,可以参考英美法的经验,将嗣后的支付型债权让与认定为与其基础性目的合同之间具有效力关联性的从合同,如此一来,则一方面不必将嗣后的支付型债权让与定性为准物权行为,从而避免学理上的争论,另一方面亦可使作为支付手段的债权让与和其基础性目的合同构成效力牵连关系,当作为主合同的基础性目的合同因效力瑕疵而最终归于无效时,作为从合同的债权让与则一并无效,原债权让与人得向对债权名义占有人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从而矫正原债权让与人与债权名义占有人之间的不当利益损益状态。
3. 具体法效的妥当性安置
(1)债权让与类型化的解释论
尽管在学理上我国学者大多并未注意到债权让与的不同类型,不过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债权让与的确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表现张力。如在“北京汇成万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诉北京市新锐市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让与合同纠纷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原先存在的是供应原材料的买卖合同关系,但被告后拖欠货款,且无现金支付能力,故原告与被告嗣后另行订立了一份债权让与合同,约定被告将其对第三人的债权让与给原告,以作为对货款给付的替代;②参见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09)昌民初字第5149号民事判决书。在“徐柱增诉杨刚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原告与被告有借款合同关系在先,但嗣后被告没有财力全部偿还本息,故将自己的债权让与原告,以替代剩余本息。①参见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2014)遵民初字第3218号民事判决书这两个案例中,债权让与是作为对基础合同的履行手段而存在的。而在“尤某黉诉周某强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②参见甘肃省通渭县人民法院(2013)通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史中华诉沈根跃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③参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4)湖吴康商初字第516号民事判决书。、“九江祜佳旅游用品有限公司诉上海易在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④参见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4)奉民二(商)初字第1386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则均是以低价从原债权人手中买得债权后再向债务人主张债务的过程中发生了纠纷,在原告与原债权人之间的债权让与中,债权只是充当了交易的标的。前述案例说明标的型债权让与和支付型债权让与在我国司法实践上确实存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法律未经修正前,于解释论而言,应当如何对债权让与为类型化解释?
对于有对价的标的型债权让与而言,其系以债权为标的而进行的类似买卖的活动,故而根据《合同法》第124条的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法官应当首先将标的型债权让与定位为最接近买卖合同的一项无名合同,在规则的适用上,《合同法》第130条中规定的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给买受人的义务应当转化为债权出让人将债权转移给债权受让人的义务;买受人支付价款的义务则直接对应于债权受让人支付价款的义务。不过,在进一步解释的过程中,买卖合同中的一些特殊规范应当不予考虑。根据《合同法》第80条的规定,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生效以债权人通知债务人为必要,因此只有债权出让人通知债务人之后,债权受让人才能实际取得对债务人的请求权。换言之,债权让与中的“交付”系以通知的方式完成,如此一来,买卖合同中关于货物交付的规则、风险转移的规则、货物受领的规则、验货规则、质量异议期规则等均无适用余地,因为债权本质上是一项制度拟制物,其尽管具有金钱价值,但却没有一般商品的有体性特征。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标的型债权让与中,债权出让人不可能负担物上瑕疵担保责任,但其却可能受《合同法》第150条规定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条款的约束,债权出让人须保证其所让与的债权系真实债权且无其他当事人对该债权享有请求权(如连带债权),否则债权受让人有权向债权出让人主张违反瑕疵担保义务的违约责任。对于无对价的标的型债权让与而言,法官首先应当将其解释为最接近赠与合同的无名合同,根据《合同法》第185条至第195条的规定决定无对价的标的型债权让与的法律适用。具体来说,债权人赠与债权与债权受让人的债权让与合意一旦达成,便应当解释为债权人将债权赠与给了受让人,并且受让人不仅表示了接受,而且实际也获得了债权本身。因此,尽管此时的债权让与十分接近于典型的赠与合同,但与有体物赠与合同不同的是,其不存在赠与合同与被赠与物权利转让相分离的情形,故而《合同法》第186条的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不能适用于无对价的标的型债权让与。此外,还须特别指出的是,《合同法》第189条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条文可类推适用于无对价的标的型债权让与,具体来说,倘若因赠与人的过错致使被赠与的债权价值受到极大贬损,如债权赠与人未能及时履行被让与债权所对应的对第三人的债务而使被让与债权受到抗辩甚至无效,则债权赠与人应当对债权受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对于径行在合同中约定以债权为对价的替代价款的支付型债权让与而言,裁判者首先应当以这项支付型债权让与为中心检索与之最接近的法权模型框架。例如,甲与乙约定,甲承租乙的门面房开店,并以自己对丙的债权作为租赁对价让渡给乙。对于这一设例,裁判者应当将整个合同解释为一项类似租赁合同的无名合同,从而定位规范的适用区间,即《合同法》总则与该法第212条至第236条。然后,具体到该无名合同中的支付型债权让与而言,其应当被解释为构成该无名合同的一项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使甲的债权因无名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转移至乙名下,不过在甲通知丙以前,这项债权让与对丙并不发生效力。不过在解释上,应当承认债权受让人对债权出让人享有债务人通知请求权,这是因为倘若无此请求权,则一旦债权人不为通知,债权受让人所受让之债权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就当事人先行订立了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合同,嗣后又达成债权让与协议的支付型债权让与而言,在解释论上,首先,应当将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基础合同与债权让与协议予以区分,即债权让与协议在性质上是一项合同,而不能被解释为基础合同的一部分,因为两个合同的合意发生时间、合意的基础并不完全同一。其次,对于基础合同与债权让与协议之间的关系而言,由于债权让与协议的目的在于基础合同之履行,故可以认为债权让与协议尽管是一项自成一体的合同,但对基础合同具有附合性与从属性,一旦基础合同因其瑕疵而归为无效,那么丧失目的之债权让与协议自应一并无效。换言之,债权让与协议应当被解释为基础合同的从合同,其为基础合同的履行服务,并随基础合同的消亡而消亡。①有学者认为债权让与具有无因性,即合同权利一旦转移,即与其移转的原因相分离,不受原因的影响。即使原因无效,也不影响移转的效力。让与人只能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返还。参见李永军:《合同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61页。但实际上,这只是将债权让与定性为准物权行为之后的思维惯性使然。事实上,由于债权不同于有体物,即使不维持所谓债权让与的效力,在债权让与原因无效时,令债权让与一并无效,所能适用的规则也是不当得利规则,故而债权让与无因性的探讨并无实益。最后,在不涉及与基础合同关系的法律问题时,债权让与协议本身也应当被解释为一项普通无名合同,只是与标的型债权让与不同,债权并未充当交易标的,在这种债权让与中并不涉及债权本身价款的意思表示,债权仅仅被作为如货币一般的支付手段而被让渡给了受让人,因此这一债权让与协议反而应当主要类推适用合同法总则条款与赠与合同条款。
在解释论上还须予以提示的问题是债权让与嗣后的处理规则问题。与买卖合同不同的是,债权让与不仅存在通知债务人才可对债务人生效的特别规则,更为特殊的是,债权让与之后,债权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仍旧为债权,但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后,债权受让人通常会兑现债权,债权由此会转化为金钱与其他有价值的财产,如不动产、动产、有价证券甚至另一个债权。有鉴于此,倘若债权让与嗣后无效,则基于公平原则与善意原则,应作出如下解释。第一,倘若债权尚未届至债务履行期,债权尚未兑现的话,则原债权让与人只须请求债权名义占有人返还债权凭证并通知债务人即可。第二,如果债权已经兑现,则分为三种情形予以处理。其一,倘若债权让与合同或者债权让与的基础性目的合同因债权让与人的过错而消灭,则原债权让与人只能请求债权受让人返还债权实际兑现的金额。这项规则的缘由在于,债权在兑现过程中,实际兑现的金额通常等于或者小于债权理论金额,为了保护债权受让人的善意与体现对债权让与人过错的否定性评价,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平原则,债权受让人仅负担返还现存利益的义务即可。其二,倘若债权让与合同或者债权让与的基础性目的合同因债权受让人的过错而消灭,则原债权让与人有权请求债权受让人返还债权的理论金额。这项规则的设置理由与第一项规则相似,即为了保护债权让与人的期待性利益与其善意的心理状态,并体现出对债权受让人过错的否定,债权受让人须返还债权理应被兑现的金额,而非实际兑现金额。其三,倘若双方均有过错,则根据双方过错程度由法官裁量债权受让人应当返还的金额。至于涉及违约或者其他事由的,则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处理。此外,倘若债权兑现所转化的不是金钱,而是不动产、动产等其他有价值的财产,由于债权转化物系他种法律关系的标的,原则上不应涉及债权转化物的返还问题,但债权转化物的价值可以作为债权兑现金额的酌定性因素。
(2)债权让与类型化的立法建议
尽管以《合同法》第124条为基础解释规范,结合法理推导,能够完成对债权让与的类型化解释,但如果以立法的形式将前述的解释内容明晰地予以规定,则一方面能够提高参与债权让与的各民事主体的可预期性,另一方面也能增强法官裁判的确定性与准确性。因此,综上所述,基于对债权让与性质与法效的类型化分析,我国《合同法》宜增设如下条款。
第一,增设第83条之一前一句:“债权人以获取金钱或者其他对价为目的让与债权的,可以根据债权的性质参照适用第九章的规定;债权人以赠与或者使相对人纯获利益为目的让与债权的,可以根据债权的性质参照适用第十一章的规定。”增加这一条款可以明晰标的型债权让与的一般规则,同时,“根据债权的性质”这一用语也赋予了法官较为灵活的自由裁量空间,使法官能够在民法规范体系中寻找最适合的规范基础。
第二,增设第83条之二前一句:“债权人订立合同后,以履行合同、清偿债务为目的让与债权的,主合同因不成立、无效、被撤销、解除等原因消灭的,债权让与无效。”这一条款的规范意旨在于明晰支付型债权让与和基础合同之间的主从合同关系。将支付型债权让与定位为效力与基础合同有牵连关系的从合同,有助于消弭债权让与性质之争,并实现支付型债权让与法效果的妥当安置。
第三,增设第83条之三后一句:“被让与债权已经兑现的,债权受让人应当向债权让与人返还被让与债权实际被兑付的金钱。债权让与或者债权让与的主合同因债权受让人过错而消灭的,债权受让人应当向债权让与人返还被让与债权应当被兑付的金钱。双方都有过错的,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应返还的金额。”这一条款着力解决债权让与嗣后无效之后如何处理的问题。通常,债权让与之后,债权不太可能仍然以债权的形态长久存续,其必然转化为一定的金钱或者其他实物。不过出于方便与公平的考虑,应以金钱作为债权被兑付之后的一般替代返还物。在具体的返还规则方面,将过错作为影响金钱返还额度的重要因素,符合民法的公平正义与私法自治之理念。
(责任编辑:陈历幸)
DF522
A
1005-9512(2015)03-0117-14
谢潇,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