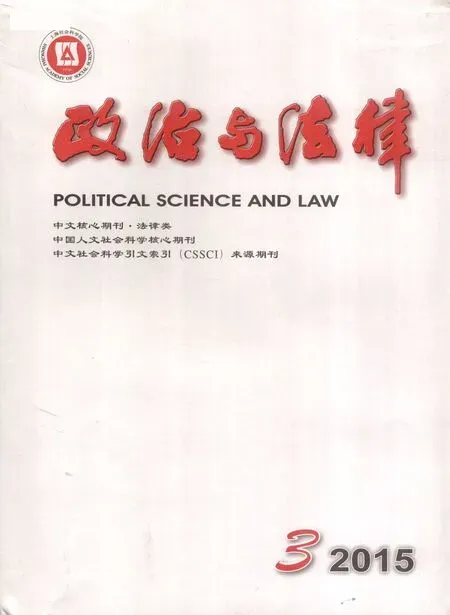论债务人的能力限度利益制度*
——从罗马法到中国法
2015-01-30李飞华侨大学法学院福建泉州362021
李飞(华侨大学法学院,福建泉州362021)
论债务人的能力限度利益制度*
——从罗马法到中国法
李飞
(华侨大学法学院,福建泉州362021)
我国《合同法》第195条规定了赠与人的债务减免权。此规定突破了债的全面履行原则,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中债务人的能力限度利益制度。该制度对具有特殊身份和处于特殊债的关系中的债务人予以特别照顾,在保留其必要生活费用的前提下来确认当下的债务履行额度。除《智利民法典》和《阿根廷民法典》外,该制度在现代民法中为具有相似功能的其他制度所取代:在侵权法中采纳损害赔偿额的缩减制度为现代侵权法发展的趋势,但在合同法中,出于确保法律适用的安定性和可预见性的考虑,类似规则的适用被局限于赠与合同。有必要基于给予“亲密关系”中的债务人比“陌生关系”中的债务人更高程度的保护以及人性关怀之理由,将该制度引入我国法。
赠与;债务人能力限度利益;债之履行;损害赔偿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据此,赠与人取得在一定条件下不再履行所承诺的赠与债务的权利。对于赠与人的这种权利的性质,在我国学者之间存在“法定解除权”①即认为《合同法》第195条规定的赠与人“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是指赠与人有权解除合同,但这种解除权的行使不发生溯及力,赠与人无权要求返还已经履行的赠与。参见王利明、房绍坤、王轶:《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和“穷困抗辩权”②即认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赠与人可以拒绝履行未履行部分的赠与义务,并且其拒绝的表示可使受赠人的权利永久地消灭。参见易军:《撤销权、抗辩权抑或解除权——探析〈合同法〉第195条所定权利的性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两种认识。且不论此等权利的性质为何,就结果而言,赠与人行使该权利的结果,将使赠与人根据有效的赠与合同③赠与合同的诺成性与实践性之争随着《合同法》的出台逐渐平息,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几成共识。参见陈小君、易军:《论我国合同法上赠与合同的性质》,《法商研究》2001年第1期。所承受的债务被缩减,而不必继续履行余下的债务。
《合同法》赋予赠与人的这种特权突破了合同的全面履行原则,根据该原则,债务人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债务。“履行”固然是消灭债的重要事由,但并非所有的履行都能达到消灭债的效果,具有此等效果的履行必须是全面的履行,具体表现为履行的主体、内容、时间、地点等多个方面,尤其以债的内容的全面实现为要。债务人按照债的具体内容,以债的关系确定的标的所为的全面履行,才发生债的清偿效果。④参见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264页。
由于债的渊源的多样性,全面履行在不同发生根据的债的关系中表现为不同的样态,其最为显著者为合同之债的全面履行原则和违约与侵权损害的完全赔偿原则。《民法通则》第88条第1款(“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部履行自己的义务”)和《合同法》第60条第1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确立了合同的全面履行原则。《民法通则》第112条第1款(“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和《合同法》第113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则确立了违约损害的完全赔偿原则;而根据侵权法的一般理论,侵权损害赔偿同样以完全赔偿(填补损害、完全赔偿)为基本原则,要求侵权人填补被侵权人所受的损失,使其回复至如同侵权未发生时的状态。⑤参见徐银波:《论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缓和》,《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
无论是合同的全面履行原则还是损害的完全赔偿原则,如果恪守这些原则而忽视个案的特殊性,有时难免导致不公的结果,因此,为解决非常态下的债务履行问题,立法上往往设立各种机制来缓和这些原则的适用,如债的分期履行规则(《民法通则》第108条)、侵权法中的过失相抵规则(《侵权责任法》第26条)、合同法中的部分履行规则(《合同法》第72条)等。然而此等规则并没有从根本上减轻债务人的责任,其仍可被认为是债的全面履行原则的另类表达。与这些规则相比,《合同法》第195条赋予赠与人的在法定条件下“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债务减免权,似乎是一个异类,它完全打破了债的全面履行原则。立法者之所以如此厚待赠与人,是因为“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双方地位严重违反均衡正义。因此,法律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优遇赠与人,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利益趋于平衡”。⑥同前注②,易军文。
立法者对赠与人的独特优遇,使人不禁产生如下疑问:除赠与人外,在其他债的关系中,是否存在类似赠与人的、因其所处的特殊债的关系或考虑到他与债权人的特殊关系等因素而需要给予相似的债务减免权的债务人?对赠与人的特殊优遇,除赋予其债务减免权外,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制度设置?除合同之债外,在侵权之债中,是否有适用此等债务减免的可能?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为肯定,那么民法是否因此承担了本不应由它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此等功能在多大程度上与民法相兼容?带着这些疑问,本文拟从历史和比较法的角度,考察赠与人的债务减免权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揭示一种逐渐被淡忘的债务人保护制度,以期为立法者设计债权人利益与债务人利益的平衡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罗马法中的能力限度利益
(一)能力限度利益的引出:债的全面履行原则及其缓和
债的全面履行作为合同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为现代各国民法所遵循。现代法中的这一原则来自罗马法,罗马法中关于债的全面履行的规则主要体现于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的一个片段I.3,29pr.,“此外,所有的债,因清偿了应清偿之物而消灭”,①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页。译文有改动。此外,本文所引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片段,皆参考了该译本,所引优士丁尼《学说汇纂》,除特别说明外,皆系笔者根据如下版本译出:The Digest of Justinian (Latin text edited by Theodor Mommsen with the aid of Paul Krueger,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Alan Wats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5).这一片段对应于盖尤斯《法学阶梯》3,168:“此外,债主要因清偿了应清偿之物而消灭。”这两个片段宣告了债的履行的基本原则,其中“清偿应清偿之物”绝不能单单理解为必须清偿,而且含有必须准确、全面清偿之意,②Cfr. Antonio Guarino, Studia sulla “Taxio in id quod facere potest”, Exceptum ex 〈Studia et Documenta Historiae et Iuris〉, Fasc.I-1941, p.8.因而,通常情况下,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的部分清偿而不构成受领迟延。③Cfr. Mario Talamanca, Istituzioni di Diritto Romano, Milano, 1990, p.639.
然而,严格坚持全面履行原则并不总能带来预期的公正结果,④薛军教授通过《学说汇纂》的一个片段D.12,1,21论证了罗马法中债的全面履行原则并认识到禁止部分履行的弊端,紧接着阐述了20世纪以来各国对该原则的变通。但为他所忽视的是,后古典时期的罗马法中已经出现他所论述的20世纪以来的对债权人拒绝部分履行的限制。参见薛军:《部分履行的法律问题研究——〈合同法〉第72条的法解释论》,《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于是从古典时期开始,裁判官在某些诉讼中做出变通,强迫债权人接受部分履行,尤里安的《学说汇纂》对此有如下记载:“D. 12,1,21:有些人认为,不能强迫那些要求给付10个金币的人先接受5个金币,以后再请求给付其剩余的部分;亦不能强迫要求归还自己全部土地之人,在诉讼中只接受部分土地的返还。然而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裁判官似乎都基于人道(humanius)的原因而迫使原告接受向他履行的部分给付,因为减少争讼也是裁判官的职责。”⑤参见[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契约之债与准契约之债》,丁玫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页。译文有改动。“人道”是优士丁尼法律改革最主要的指针之一,他这么做,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人道”是基督教所大力宣扬的教义之一,身为被基督教会奉为“大帝”的三大皇帝之一的虔诚的基督徒,优士丁尼在关于《学说汇纂》之批准的Tanta敕令和关于《法学阶梯》之颁布的Imperatoriam敕令的开头,莫不“以朕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义”,而他下令编订的被后世法学家称为《市民法大全》者所汇集的也莫不是适合基督教国家的罗马法。⑥参见[日]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XV罗马世界的终曲》,郑维欣译,三民书局2008年版,第317页、第321页。因而,优士丁尼以“人道”之名行变革法律之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体现了由于基督教的影响而出现于后古典时期的罗马法中对债的全面履行原则之变通的还有不少其他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两项:减免债务简约(pactum quo minus solvatur)与债务人的能力限度利益(beneficium competentiae)。前者是在死者的遗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的情况下,其继承人与其所有债权人之间达成的缩减各自债权的协议,该协议需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如果未能达成一致,则由裁判官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做出裁判,但裁判官首先要考量的是债权额而不是债权人数,这是马可·奥勒留皇帝的一个敕令所规定的(D.2,14,7,19; D.2,14,8)。后者是考虑到债务人的特殊身份或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基于公平的考虑而赋予特殊债的关系中的诚信债务人的一种利益或照顾,即在为债务人保留一定的必要生活费用的前提下,估定其能够承担的最高责任额,从而将其责任限于其资产范围之内。⑦参见[意]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个人主义与罗马私法》,薛军译,载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二)能力限度利益的制度配置
能力限度利益是罗马法中一些列规则的概称,其最初的表达为damnare in id quod facere potest、damnare in quantum facere potest等形式,意为“在其能力范围之内判罚”,而为我们所熟知且通用的表达能力限度利益的beneficium competentiae一词乃16世纪德国法学家所创。①See Adolf Berger,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Roman Law 372-372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Independence Square, Reprinted 1991);同前注⑧,Guarino文,第15页;Matteo Marrone, Istituzioni di Diritto Romano, Palumbo, 2006, p.517, n.301.
能力限度利益从属于限额估定(taxatio),限额估定是程式诉讼中的一种判罚方式,出现在程式的判决要旨(condemnatio)中。罗马民事诉讼法的发展经历了从法律诉讼到程式诉讼再到非常诉讼的演变,其中程式诉讼分为法律审和事实审两个阶段,前者由裁判官负责,在其初步审查后做出程式书状交由负责后者的承审员进行审判。裁判官所做程式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承审员的任命,其次包括请求原因、原告请求、分配裁判和判决要旨。除上述四项主要的程式内容外,有些程式诉讼中还有一些附带程式。
在判决要旨中,其程式是授权承审员宣布判罚或开释,而所有包含判决要旨的程式都涉及钱款估价,即承审员的判决通常体现为一定的钱款,这笔钱款的数额在有些程式诉讼中是确定的,有些是不确定的(Gai.4,48-49)。对于钱款额不确定的判决要旨,有两种表达形式。一种是确定某个限额(taxatio),比如:承审员,判罚N.内基丢斯向A.阿杰流斯给付不超过一万塞斯特斯,如果事实不成立,则予以开释(Gai.4,43)。另一种对判罚的数额没有规定限度,其程式例如:承审员,物价值多少,就判罚N.内基丢斯向A.阿杰流斯支付多少钱款,如果事实不成立,则予以开释(Gai.4,51)。但在所有数额不确定的判决要旨中,裁判官为限制承审员的权力,通常都会指出判罚的最高数额,这在特有产之诉和转化物之诉中尤为明显。②同前注⑨,Talamanca书,第312页;Giovanni Pugliese, Istituzioni di Diritto Romano (Terza edizione), Torino, 1991, p.293.对最高限额进行估定的一种典型方式就是当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存在某种特殊关系时赋予作为被告的债务人以能力限度利益,即要求承审员在为债务人保留必要的生活费用的前提下,在其资产限度内做出判罚,从而避免可能对债务人进行的人身性执行、财产拍卖(bonorum venditio)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廉耻。
赋予债务人能力限度利益是否就意味着债权人只能获得部分履行,债务人能力限度之外的债权部分因此就消灭了呢?如果债务人以后经济状况改善,是否要继续履行余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优士丁尼之前的罗马法和优士丁尼法中有所不同。在前者,债务人在享受能力限度利益的情况下,余债成为自然之债,即便债务人此后经济状况好转,亦无须再继续履行。这是证讼(litis contestatio)的效力使然。③Cfr. Ottorino Clerici, Sul Beneficium Competentiae in Diritto Romano, Napoli, 1982, pp.76-77.证讼原是法律诉讼中一个承上启下的程序,表现为双方当事人在法律审结束时邀请数名见证人在场对有关争议加以确认和说明。该程序的作用在于对诉讼标的加以确定并将争议提交承审员裁决,从而启动事实审。随着证讼的完成,争议所涉及的债的标的不再取决于原来的债,而开始取决于证讼。④参见黄风编著:《罗马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证讼因而具有消灭原债的效力(Gai.3,180)。证讼后来也保留在程式诉讼中。
在优士丁尼法中,证讼不再具有消灭原债的效力。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享有能力限度利益的债务人在其此后经济能力好转的情况下仍要继续履行余债?优士丁尼《学说汇纂》和《法典》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在D.15,1,47,2、D.17,2,63,1和C.5,13,1,7中,优士丁尼明确要求负有返还嫁资义务的丈夫和对其他合伙人负有债务的合伙人,在被授予能力限度利益时必须提供“余额保证”(cautio de residuo),即必须保证在其此后获得清偿能力时继续履行余债。因此可以认为,在优士丁尼法中,在法律没有要求且当事人没有约定提供此等保证的情形,余债消灭。但不可否认,通常情况下债权人都会要求债务人提供此等保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能力限度利益并不意味着对债务人的最终执行和债权人的剩余债权的终局丧失,在债务人提供余额保证的情况下,能力限度利益只是意味着基于债务人的经济状况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而暂时减少对其判罚的履行额,但并不减缩债务本身,因而当债务人的经济状况好转时,必须就减少判罚的余额继续清偿。①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三)能力限度利益的制度建构
1.能力限度利益的适用目的
能力限度利益是产生于古典初期的一项法律制度,其具体产生时间难以确定。通说认为,能力限度利益最初只是适用于赠与人的一项照顾制度,由安东尼努斯·皮尤斯(Antoninus Pius)的一项敕令所引入(D.50,17,28:“被奉为神的皮尤斯皇帝的批复如下:因赠与而被起诉之人,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进行判罚”)。此后,其适用在个案中逐渐扩大。在产生之初,如上文所述,该制度的本旨在于通过将对债务人的判罚限于其能力范围,从而避免人身执行、财产拍卖及由此带来破廉耻,但后来,其要义逐渐发生变化,演化为限制对债务人的判罚:为贫穷的债务人做出必要生活费的扣除以使其不致受穷(deductio ne debitor egeat)。至于这种转变发生的时间,主流的观点是,在古典时期即有对贫穷债务人生活费的保留,但仅适用于赠与人(D.42,1,19,1:“……我认为不能夺走赠与人的全部财产,而应当为他们留下一部分而不致使他们受穷”),而优士丁尼将其一般化,适用于享有能力限度的任何债务人。②Cfr. P. P. Zanzucchi, Sul C.D. Beneficium Competentiae, Bullettino Dell’Istituto di Diritto Romano, 1916 (29), pp.63-65.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上文所述的能力限度利益最初的本旨与财产委付制度完全重合。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学者对上述能力限度利益的初衷产生质疑的原因,笔者对此深有同感。在罗马法史上,对不履行债务的债务人的执行手段有一个从人身执行到财产执行的转变,其标志是公元前326年《佩特流斯法》(Lex Poetelia)的颁布。但直到共和末期引入财产拍卖制度,才使债的执行程序真正具有了财产形式:以强制执行的方式拍卖债务人的财产来清偿其债务,从而避免对债务人的人身性执行,但所带来的后果是使债务人破廉耻。财产性执行的进一步发展是凯撒或奥古斯都时期颁布的《关于财产委付的尤流斯法》(Lex Iuria de Boni Cedendis),它确立了财产委付制度,允许非因其过错而陷入破产境地的债务人将其财产委付于债权人来避免强制性的人身执行、财产拍卖以及破廉耻。③同前注①,彼德罗·彭梵得书,第216页。既然已存在这么一项制度,公元2世纪中叶的皮尤斯皇帝就不太可能再引入具有同样主旨的能力限度利益,后者必然有其别于前者的特殊功能。
实际上,能力限度利益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它的适用被严格控制在有限的几类具有特殊关系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比如父母对其子女、恩主对其解放自由人、合伙人之间、夫妻之间等),或者适用于特定类型的债务人(比如赠与人、军人等),而且避免人身执行以及引致破廉耻的财产拍卖只是享有能力限度利益的一种后果,这种后果本身并不具有必然性,如果债务人拒不执行在其能力限度内的判决,债权人同样有权诉诸人身执行和财产拍卖。④同前注②,Zanzucchi文,第64页。另一方面,保留在优士丁尼《学说汇纂》中的晚于皮尤斯皇帝几十年的保罗的一个片段(D.50,17,173pr.)告诉我们,当时的状况已经是,在对享受能力限度利益的债务人进行判罚时应当为其做出一定的维持生活的扣除。⑤D.50,17,173pr.:在对那些享有能力限度利益之人做出判罚时,不能夺走他们的全部财产,而应当为他们留下一部分而不致使他们受穷。因此可以推知,能力限度利益在其产生之初即在于为贫穷的债务人扣除一定生活费用,并不存在通说认为的制度转型,该制度在后来的发展只是扩大了其适用范围而不再限于赠与人,认为直到优士丁尼时期才将必要生活费进行扣除的观点(即认为D.50,17,173pr.系优士丁尼的添加)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这样一来,即使存在财产委付制度,债务人根据能力限度利益还可以享有其他利益——保留必要的资产而“免于极端的崩溃,并且给予他在逆境过后重新开始的机会”,①同前注②,马尔蒂诺文,第70页;同前注②,Zanzucchi文,第94页。这或许才是该制度的宗旨所在。
2.能力限度利益的适用范围
能力限度利益并非所有债务人均得享有,有权在裁判中享有此等利益的对象被严格限制,在优士丁尼法中,其适用范围包括如下几种案型。
(1)赠与人
由于赠与的无偿性,赠与人通常受到法律的特别眷顾,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赋予赠与人能力限度利益是能力限度利益制度产生的初衷,D.23,3,33、D.42,1,41,2和D.39,5,12都将赠与人的能力限度利益指向皮尤斯皇帝的一项敕令(D.50,17,28),其内容已在上文揭示,D.39,5,33pr.同样明确了赠与人仅在其能力限度内对受赠人承担给付责任。此外,应当为赠与人做出保留在D.42,1,30中得到强调:“如果通过赠与的方式允诺了钱款,并且赠与的数额可能耗尽赠与人的所有财产,以致他一无所有,那么只能在他能力限度内提起诉讼,从而为赠与人留下一笔生活费用。”为赠与人的保留开创了此后一般性地为所有享受能力限度利益的债务人进行保留的范式。
对于享受能力限度利益的债务人来说,在优士丁尼法中,生活费的扣除已经成为常态,但在考量债务人的能力限度时,对债务人的其他债务的扣除却并非如此,而只有在赠与人的情形方得如此,这也是赠与人区别于其他享受能力限度的债务人的特别之处。对此,D.24,3,54很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点:“在确定丈夫的支付能力时不扣除任何债务,对于合伙人、恩主和父亲,同样如此。但如果某人因赠与而被起诉,其支付能力的确定应扣除所有的债务。”
(2)合伙人
就合伙而言,其成员间的亲密关系受到重视,“甚至合伙人之间要求享有一定程度的兄弟权”,②同前注①,彼德罗·彭梵得书,第291页。因此在合伙人之诉中,受到其他合伙人起诉的合伙人享有能力限度利益就容易理解了。这种能力限度利益不仅授予全物合伙的合伙人(D.42,1,16),而且也授予个物合伙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合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兄弟般的关系”(D.17,2,63pr.)。
合伙人之诉中的能力限度利益与其他情形中的能力限度利益一样,具有严格的属人性(D. 24,3,13),因此合伙人的担保人并不享有,但该担保人作为合伙人的代理人的情形除外,这也适用于所有在能力限度内承担责任之人的代理人(D.17,2,63,1)。合伙人的家父或主人、继承人同样不享有授予合伙人的能力限度利益(D.17,2,63,2)。在确定享有能力限度利益的合伙人的财产范围时,不得扣除其债务,除非证明该债务产生于与合伙有关的事务(D.17,2,63,3)。
(3)财产委付人
自《关于财产委付的尤流斯法》“开创了一项为现代破产法所遵循的”财产委付制度,③M.W. Frederiksen, Caesar, Cicero and the Problem of Debt, 1966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6, 141.破产债务人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于其财产范围之内。但资不抵债的债务人将其财产委付于债权人后,并不导致其剩余债务的消灭(C.7,71,1),当债务人取得新的财产后,仍需继续清偿,否则,债权人得对其提起诉讼或请求将其新得财产予以拍卖,但债权人仅得在其能力范围之内提起诉讼,即财产委付人就其未清偿的债务部分,在新取得的财产范围内享受能力限度利益(D.42,3,4pr.),“因为对被剥夺了其全部财产之人,如果仍就全额做出判决,不人道”(I.4,6,40);④See also Louis Edward Levinthal, The Early History of Bankruptcy Law, 66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and American Law Register 5/6, 238 (1918).如果债务人新得的财产数量微薄,则债权人不得请求进行拍卖,因为一个人不能被剥夺其日常生活所需(D.42,3,6)。
(4)军人
缘于罗马的军事立国思想,必须在法律上保护和优待军人。“有利于军人”顺理成章地成为贯穿罗马法的众多原则之一。就能力限度利益而言,实际的情况是,在古典时期的罗马法中已经允许领取薪俸的军人享有此等利益,但军人并未因此获得如同赠与人一样的在计算其财产限度时对债务的扣除权。①同前注②,Zanzucchi文,第95页。换句话说,他与赠与人以外的其他享有能力限度的债务人一样,所享利益仅为在其财产限度内受到判罚以及伴随的对生活费的扣除(D.42,1,18= D.42,1,6pr.)。
(5)直系尊亲属及恩主
一般认为,直系尊亲属被其直系卑亲属(成为自权人后)和恩主被其解放自由人起诉时可以享受能力限度利益,②同前注④,Pugliese书,第293页;同前注①,彼德罗·彭梵得书,第119页、第244页。其论据主要有如下三个片段。I.4,6,38:“但如果某人对其尊亲或恩主起诉,……原告得不到超过其相对人之所能的判决。”在优士丁尼《学说汇纂》中与此对应的片段只有D.42,1,30的后半段和D.42,1,17。前者所谈论的范围限于父母子女之间:“在父母子女之间,同样应遵守该规则。”这里的“该规则”需要结合D.42,1,30的前半段来理解:“如果通过赠与的方式允诺了钱款,并且赠与的数额可能耗尽赠与人的所有财产,以致他一无所有,那么只能在他能力限度内提起诉讼,从而为赠与人留下一笔生活费用。”前后联系起来分析,不难看出,该片段所讨论的语境是赠与,因而所谓的父母子女之间的能力限度利益只是在赠与的情况下适用,此外也看不出它只是单向规定父母对子女享有能力限度利益而不是反之亦然。至于紧接着规定了合伙人的能力限度利益的D.42,1,17,其辞曰:“男女恩主、其子女和父母同样如此。”也就是说,他们同样享有能力限度利益。这一缺乏论证的对恩主的能力限度利益的宣示性规定着实令人生疑,需详述之。
能力限度利益,归根结底就是为债务人保留一定的生活所需,不致其因清偿债务而在经济上陷于生存困境。然而直系卑亲属对直系尊亲属、解放自由人对其恩主本来就负有抚养义务,③参见徐国栋:《罗马私法要论》,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118页。这似乎使得后者对前者的能力限度利益不再必要,这也成为某些学者否认后者的能力限度利益的依据。④同前注②,Zanzucchi文,第98-99页。但笔者认为并非如此,试想一下《智利民法典》第1627条的规定,或许我们就会豁然开朗:“不得同时主张抚养费和能力限度利益。债务人应选择其一。”可以说,《智利民法典》的这条规定准确地把握住了能力限度利益的命门。
(6)被解放、被剥夺继承权或放弃继承权的家子
对于此等家子享有的能力限度利益,为片段D.14,5,2pr.所明示:“裁判官规定:‘如果处于他人权力下的某人达成一项交易,此后他在对其享有权力之人死亡时被解放或被剥夺继承权或放弃继承权。在进行适当的调查后,我将在他的能力范围内的授予相对人诉权,不论该交易是他自发订立的还是经对其享有权力之人的同意而订立的,也不论交易所得是归入他的特有产还是归入对其享有权力之人的遗产。’”但此等家子的能力限度利益仅在合同之诉中存在,对于私犯之债则不适用(D. 14,5,4,2; D.42,1,49)。此外,纵然家子在其被解放或剥夺继承权之前已被判处承担全额责任,但在胜诉的债权人此后提起的已决案之诉中仍得享有能力限度利益(D.14,5,5pr.)。
(7)与嫁资的偿付与返还有关之人的能力限度利益
就优士丁尼罗马法中有关能力限度利益的规定,与嫁资的偿付与返还有关者最多,所涉对象也最为复杂。
①丈夫与妻子的能力限度利益
I.4,6,37:“同样,如果妇女提起嫁资之诉,已决定:丈夫应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换言之,在其财产允许的范围内受到判处。”优士丁尼在其一项向君士坦丁堡和所有行省发布的另外一项敕令中做了同样的说明(C.5,13,1,7)。这些规定宣示了丈夫就嫁资的返还享有能力限度利益。虽然笔者所列举的上述片段均出自优士丁尼之手,但丈夫的能力限度利益其实早在古典法中就已存在。
如前所述,能力限度利益具有严格的属人性,因此在丈夫死后,其继承人无从享有这种利益(D. 24,3,12),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皇帝的一项敕令重申了上述规则(C.5,18,8)。但在拉贝奥看来,丈夫的继承人为妻子所生者除外,此等继承人享有能力限度利益(D.24,3,18pr.)。与适用能力限度利益的所有其他情形相同,这种人身性并不排除代理人享有与本人相同的能力限度利益(D.17,2,63,1),丈夫的代理人在丈夫生前亦如此(D.42,1,23)。还要说明的是,丈夫在返还嫁资时的能力限度利益为丈夫所享有的特权,不得以相反的约定排除之,因为约定不以丈夫的能力范围为限而是就嫁资全额进行返还“准确地说是违反良俗的,因为很明显,它违背了妻子对其丈夫应有的尊重”(D. 24,3,14,1)。
丈夫相对妻子所享有的能力限度利益不独限于嫁资返还的情形,安东尼奴斯·皮尤斯皇帝的一项敕令将丈夫的能力限度利益扩展到妻子就其他交易而起诉丈夫的情形,优士丁尼法中索性规定反之亦然,即丈夫对妻子提起诉讼时,妻子享有与丈夫相同的能力限度利益(D.42,1,20)。但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婚姻效力之一的配偶相互享有的能力限度利益,仅在嫁资返还及合同之诉中有其适用。①同前注③,Marrone书,第222页。
②公公与岳父的能力限度利益
上述第一种情形中丈夫的嫁资返还义务的前提是丈夫取得嫁资,如果丈夫是家子,且嫁资被交给家父,对妻子来说,嫁资之诉的被告则是公公(D.24,3,22,12)。在这种情况下,公公就嫁资的返还享有能力限度利益(D.24,3,15,2),因为公公处于父亲的位置(D.24,3,16)。
如果岳父做出嫁资允诺但未履行,其女婿为此提起诉讼的,岳父是否享有能力利益存在争议。②A. Arthur Schiller, Jurists’Law, 58 Columbia Law Review 8, 1233 (1958).保罗于《普劳提评注》第6卷指出:“……如果岳父因嫁资允诺被起诉,是否也享有能力利益?看起来这确实是公平的,但正如内拉蒂写到,我们的规则事实上并非如此。”(D.42,1,21)拉贝奥认为,在婚姻存续期间,岳父就嫁资允诺享有能力限度利益,如果婚姻破裂,则视情况而定(D.23,3,84)。彭波尼则明确主张只有在婚姻存续期间,岳父就嫁资允诺才享有能力限度利益(D.42,1,22pr.)。内拉蒂与普罗库鲁斯的意见更为宽和,只是指出岳父就嫁资允诺享有能力限度利益,并不考虑婚姻是否解除(D. 24,3,17pr.)。
③家外人的能力限度利益
在优士丁尼罗马法中,做出嫁资允诺的家外人也得以就嫁资的偿付享有能力限度利益。家外人的嫁资允诺被看作是一种赠与,因赠与人享有能力限度利益,此等家外人亦被赋予能力限度利益(D. 23,3,33)。然而保罗却持有相反的观点,在他看来,做出嫁资允诺的家外人应当就嫁资允诺的全部数额承担责任,而不考虑其能力限度如何(D.23,3,84)。乌尔比安的观点更为合理,正如其给出的理由,家外人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赠与人的地位。
(四)小结:能力限度利益制度的本质和机理
上文对能力限度利益适用案型的分析表明,各种能力限度利益之间并无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它们具有不同的内在构因,能力限度利益制度是在法律实践中由裁判官或者由皇帝的敕令逐渐累积起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制度,如果说各种能力限度利益之间存在某种共性的话,这种共性只能在其适用结果中找到,即为享有此等利益的债务人的生计考虑而将其承担的责任额暂时限制在其能力范围之内,从而为其保留一定的生活费用,并因此使其免遭人身性的执行、财产拍卖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廉耻的严重后果。除此之外,很难说它们之间还有其他统一的有机特征。①同前注⑧,Guarino文,第21-22页。
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试图挖掘其制度基础的努力。笔者在上文曾经点出,能力限度利益作为部分履行的一个类型,构成债的全面履行原则的一项例外。表面上看确实如此,债务人享有此等利益的后果导致债权人必须接受债权人的部分履行。②同前注③,Marrone书,第51页;Antonio Guarino, Diritto Privato Romano, Napoli, 2001, p.805.但这并非该制度设计的动因,实际上,它是为缓和早期罗马法对债务人的严苛规定,作为一种仁慈,为贫穷的债务人保留一定生活费用所配置的法律手段。③See Patrick Mac Chombaich De Colquhoun, A Summary of the Roman Civil Law Vol. 3, 169 (Gaunt, Inc. 2000).即便以“人道”之名对罗马法大肆变革的优士丁尼也无意于对债的全面履行原则进行改革,而只是在个别情形表现出某种慷慨。以能力限度利益为代表的对债务人的慷慨并没有冲击到债的全面履行原则,④事实上,自该原则确立以来,其主导地位从未曾被动摇。首先,虽然D.12,1,21提到裁判官基于人道的原因会强迫债权人接受部分履行,但从该片段所处的位置看,它并没有出现在“关于清偿和责任免除的”D.46,3 中,而是被规定在D.12,1“关于被借贷的物,如果确实被提出要求,关于要求返还之诉”,因而其中对部分履行的规定并不具有一般性,其措辞“上述两种情况”也表明了其适用的有限性。其次,就缓和了该原则的减免债务简约而言,仅在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有其适用,其实质乃权利人对权利的放弃。再其次,就能力限度利益而言,虽然其适用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债的完全履行原则,但其适用范围有着严格的限制。而是基于某些债的关系中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或者针对某些债务人的特殊身份而赋予债务人的一项特权,这项特权的对立面与其说是债的全面履行原则,毋宁说是债权人的平等地位(par condicio creditorum),因为债务人一旦被赋予能力限度利益,则预示着与该债务人处于某种特殊关系的债权人与其他债权人相比的不平等地位。⑤同前注⑧,Guarino文,第12、25页。
法律之所以在某些债的关系中违反债权人的平等地位原则,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能力限度利益具体分析。概而言之,可以将其区别为两类。一类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存在某种特殊关系的情形,这种特殊关系可以被称为“亲密关系”,上文所分析的案型(2)、(5)、(7)属此。合伙人之间有兄弟般的关系、直系尊血亲和恩主对直系卑血亲和被解放人有抚养请求关系,嫁资偿付与返还中的特殊关系乃是婚姻关系,这些特殊关系的存在使得处于这种关系中的债权人的地位受到削弱。另一类是某些债务人本身具有特殊性的情形,上文分所分析的案型(1)、(3)、(4)、(6)属此。赠与人因其行为的无偿性、财产委付人因其先前向债权人做出的财产委付、军人因其在罗马社会结构中的独特地位、被解放的家子及被剥夺继承权和放弃继承权的家子则因其先前地位的不独立性而获得法律的眷顾,得享能力限度利益。⑥丁玫教授在合同赔偿制度的框架下谈论能力限度利益,似乎不妥,能力限度利益涉及的乃是一般意义上的债的履行,并不限于赔偿问题。参见丁玫:《罗马法合同赔偿制度》,《政法论坛》2001年第5期。但这些不同类型的能力限度利益却有着相同的适用前提,享有此等利益的债务人必须是诚信债务人,⑦同前注⑤,Clerici书,第82页。其本质则在于上文一再强调的,对经济能力有限以致完全履行债务可能导致存在生计问题的债务人赋予一项特别照顾,而这项制度的起点,是人道与公平的理念,所谓“法乃善良与公正的艺术”(D.1,1,1pr.),优士丁尼将法学家杰尔苏(Celsus)的这句格言置于其《学说汇纂》的起首,统率着法律的一切规定。
三、现代民法中的能力限度利益及其借鉴
(一)能力限度利益制度的现代继受:以智利民法典与阿根廷民法典为代表
罗马法中基于人道和公平理念所创设的能力限度利益及其各种案型,除诸如军人和家子的能力限度利益等少数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而逸出现代民法的内容外,被智利《民法典》和阿根廷《民法典》全盘继受。
《智利共和国民法典》在“债的清偿”的语境下,其第1625条首先对能力限度利益进行了界定:“依其社会地位和境况,并在其财产状况改善时负补足义务的前提下,为使其负担的清偿义务不超出其所能,在保留其俭朴生活的必需品的范围内赋予特定债务人的利益,为能力限度利益。”第1626条则规定了能力限度利益的适用范围:“对下列人员,债权人有义务赋予能力限度利益:1、其直系卑血亲或直系尊血亲,没有对债权人实施任何构成剥夺特留份的侵害行为的;2、其配偶,没有因其过失离婚的;3、其兄弟姐妹,未对债权人实施与直系卑血亲或直系尊血亲之特留份继受权剥夺情由有同等严重程度的有过失侵害行为的;4、同等情形下的合伙人,但仅限于产生于合伙合同的相互诉权;5、赠与人,但仅限于要求其履行承诺的赠与之时;6、已委弃财产,但被继续请求以嗣后取得的财产补足清偿委弃前存在的债务的诚信债务人,但只有为其利益委弃财产的债权人有义务赋予此等利益”。第1627条进一步规定:“不得同时主张抚养费和能力限度利益。债务人应选择其一”。《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第799条和第800条完全继受了《智利共和国民法典》第1625条和第1626条的规定,未有任何改动。①分别参见徐国栋主编,徐涤宇译:《智利共和国民法典》,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322-323页;徐涤宇译注:《最新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198页。
可以说,智利《民法典》与阿根廷《民法典》对能力限度利益的规定与罗马法一脉相承,除了剔除有关嫁资的偿付与返还、恩主、军人等因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环境消失而不复存在的规定外,基本反映了古典后期罗马法中能力限度利益的样态。它们与罗马法中的能力限度利益制度的不同在于:其一,负担授予能力限度利益的义务人不同,在罗马法中为裁判官,在这两部民法典中为债权人;其二,从这两部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其明显的制度宗旨是,给予“亲密关系”中的债务人比“陌生关系”中的债务人更高程度的保护,而在罗马法中,能力限度利益制度的各种案型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共同的制度基础。
除智利《民法典》和阿根廷《民法典》外,罗马法中的能力限度利益制度所涵摄的情形在现代法中为具有类似功能的其他制度设置所代替。②需要注意的是,beneficium competentiae作为一个经常被误解的概念仍然被保存下来并经常被用于对诸如破产、借贷等法律问题的分析。例如,有学者将能力限度利益适用于破产者的情形,将之误认为是对破产者债务的免除。See Garrard Glenn, Property Exempt from Creditors' Rights of Realization, 26 Virginia Law Review 2, 130 (1939); Walton H. Hamilton, In Re the Small Debtor, 42 The Yale Law Journal 5, 481 (1933). 再比如,随着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蔓延,冰岛、希腊等国家由于债务问题而面临“国家破产”的悲剧,于是“国家破产”是否如个人破产一样享有能力限度利益的问题浮出水面,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预见性地提出国家也应享有能力限度利益的论点。See M. Schmitthoff,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Loan, 19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4, Third Series, 183 (1937).尤其是现代民法中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权(我国《合同法》第195条)与确定损害赔偿额时的减缩规则,对此做出了最好的回应,两者分别代表了合同法和侵权法中现代版的能力限度利益。
不可不察的是,罗马法中的能力限度利益的适用范围主要限于合同之诉,甚至有些情形明确排除它在私犯之债中的适用。③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能力限度利益仅适用于合同之债,而绝对排斥私犯之债。同前注16○,Clerici书,第82页。与之相反,现代版的能力限度利益,除智利《民法典》与阿根廷《民法典》外,主要体现于侵权法中损害赔偿额的缩减制度,而它在合同法中的适用,仅残存于赠与合同。
(二)我国立法者的态度及司法者的回应之一:以合同法为线索
就我国现行法而言,《合同法》第195条确立了赠与人的债务减免权,而损害赔偿额的缩减制度并未得到明确地规定。但我国法中并非没有体现债务人能力限度利益的规定,实际上,《民法通则》第108条的规定就包含了此等意义:“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该规定与能力限度利益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适用的结果是授予债务人分期履行的权利,既然是分期履行,所分的履行期限应是确定的;而后者适用的结果是,首先,为债务人保留一定的必要生活费用;其次,并不确定余债的履行期限,而是视债务人财产状况的好转情况而定,其对债务人的保护力度显然大于前者。然而,即便是《民法通则》有了此等规定,但其并未在《合同法》中得到任何回应,而且还被有些学者诟病为法官对当事人的债的履行的干预,应为《合同法》第72条所吸收。①同前注⑩,薛军文。
不但我国立法中缺乏类似智利《民法典》和阿根廷《民法典》中对“亲密关系”中的债务人的特殊保护规则,司法者在这方面也没有走得更远。对照上述两部民法典所规定的前4类与债权人具有“亲密关系”的债务人保护方面,②对第5类享有能力限度利益者,我国《合同法》第195条已经规定了贫穷抗辩权,而对第6类享有能力限度利益者,由于我国法中没有财产委弃制度作为支撑,在此不予讨论。即可看出我国司法者的态度如何。
其一,司玉山诉司爱卿民间借贷纠纷案(2011夏民初字第913号):原告与被告系父子关系,被告曾向原告借款2万元,并约定了还款期限。后因经济困难,被告先期偿还了利息2千元,本金及余息在期限届满后经原告多次催告尚未偿还,原告诉至法院,请求被告偿还本金及余息。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双方应按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被告在收到原告借款后未按约定履行全部还款义务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继续履行全部借款本息的违约责任”,从而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其二,胡清华诉杨杏荣债权纠纷案(2011宁民初字第190号):原告与被告原系夫妻关系,双方协议离婚时,被告承诺自愿向原告给付10万元并当即给付5万元,对余款5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欠条,约定一年内还请。被告因经济困难在期限届满后没有偿付余款。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偿付余款。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被告应主动清偿到期债务。被告长期拖欠有损原告的合法权益”。据此,法院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还原告欠款的本金及利息。
其三,曹克刚与黄更祥、曹克强民间借贷纠纷案(2011雁民一初字第493号):原告与被告曹克强系兄妹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因购房及做生意需要资金,多次向原告借款,本息累计达137万。双方对该事实没有异议,但被告目前经济困难,请原告给予时间或用固定资产抵债。最终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被告虽系亲属关系,但二被告向原告借款多年,未能偿还借款,有违诚信原则”,遂判决被告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全部137万欠款。
其四,谢某某诉张某某等合伙协议纠纷案(2011郴北民一初字第701号):原告与被告合伙经营挖机。某日,原告与被告协商,两被告一致同意原告退出合伙,并达成协议,约定由被告在某日之前向原告支付退股本金及运费共3万元,并出具了欠条。被告在约定的期限内偿还了原告1.4万元,余款1.6万元经多次催告尚未偿还。原告遂起诉被告偿还欠款并支付利息。双方对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但被告称因经济困难暂时无力偿还。法院认为“欠款到期后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还款,应承担继续履行、支付逾期利息的违约责任”,从而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上述四个案例中,司法者一致选择了“债务必须全面履行”作为判决的依据,而不考虑债务人“经济困难”的现实状况,即便此等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存在某种“亲密关系”。
(三)我国立法者的态度及司法者的回应之二:以侵权法为线索
如前所述,损害赔偿额的缩减制度未明确规定于我国法中,我国《侵权责任法》所贯彻的依然是对损害的完全赔偿原则。实际上,2012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0条曾拟规定:“免费搭乘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被搭乘方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适当减轻其责任”。该条文完全体现了司法机关针对某些特殊案件缓和适用完全赔偿原则的意图。然而遗憾的是,2012年12月公布的该司法解释的最终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删除了这一条文。不可否认,从侵权责任法所承载的基本功能来看,在一般情况下,完全赔偿原则有其合理性,它要求侵权人对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进行填补,使其回复到如同侵权行为未发生时的状态。然而,在特殊个案中,如果不加变通地严格适用该原则,则很有可能导致不公正的结果。
以陆某某等诉高某某其他合同纠纷案(2013崇民一(民)初字第3135号)为例:原告陆某某、袁某某分别系袁某之配偶、女儿。某日,被告与袁某发生交通事故,致袁某当场死亡。经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某日,原告与被告经交警大队调解,双方确认被告赔偿原告21万元,被告当场支付19万,同时被告出具一份欠条,言明余款2万元于5年内还清。到期后,被告未按约付款,故涉讼。被告对案件事实无异议,但因经济困难无力还款而要求减免欠款。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对被告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赔偿款2万元。
当然,实践中也不乏司法机关主动缓和适用完全赔偿原则的情形。以一则未成年人失火侵权案为例:①对该案例的报道参见韩泽祥:《任丘两女童玩火致木材市场“火烧连营”》,《燕赵都市报》2011年12月2日第06版。任丘两个7岁女孩冯某和康某,在某旧木材市场戏耍玩火引燃市场内堆放的木材,由于火势凶猛,着火面积达万余平方米,致使13户村民堆放在市场内的木材化为灰烬。事后,13户受损的村民向任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两女孩的监护人赔偿损失共计185万元。法官经过八次调解,原被告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由被告赔偿13名原告财产损失27万元。
在该案中,如果严格适用完全赔偿原则,一方面将因被告的经济能力欠缺而使判决得不到执行,另一方面也将导致因为孩童的一次冒失之举而葬送两个家庭的安定生活的结果。法院在调解过程中一再强调的也是:原告家庭经济困难,已陷入极端的困苦之中。因此,笔者有理由质疑完全赔偿原则在个案中的合理性。针对此等个案,司法机关纵然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来避免和缓和适用完全赔偿原则所可能带来的弊端,但这只能算是“权宜之计”,而且不能指望这种“权宜之计”在所有个案中都能得到实现,比如前文提及的陆某某等诉高某某其他合同纠纷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从立法上解决完全赔偿原则的僵化问题才是治本之举。
如果说合同之债中债务人的能力限度利益制度以及类似制度配置的阙如可以理解,因为它毕竟只为少数国家的立法所接受,那么,在损害赔偿之债中,在侵权法被赋予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发展趋势下,我国立法者仍然恪守侵权损害的完全赔偿原则,则极易导致个案的不公。面对完全赔偿原则适用于个案所面临的问题,我国已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在个别情形下可例外酌减侵权人的责任,②参见杨立新:《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5页。但他们并未在为债务人之生计考虑的“损害赔偿额的缩减制度”的语境下一般性地讨论该制度,更不知债务人的能力限度利益制度为何物。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在侵权人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损害赔偿额的缩减制度为多数国家的立法例所采,远者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18条、已经纳入《瑞士民法典》第五编的《瑞士债法典》第44条第2款、《荷兰民法典》第六编第109条、《西班牙民法典》第1103条、《葡萄牙民法典》第949条、东欧各国之民法典、北欧各国之损害赔偿责任法,近者如《欧洲侵权法原则》第10:401条,等等。①对各国法中侵权损害赔偿额的缩减制度的详细分析,参见林易典:《论法院酌减损害赔偿金额之规范:欧陆各国民法中之酌减条款与我国民法第二百十八条之比较研究》,《台大法学论丛》第36卷第3期,第305页以下。上述立法尽管措辞各异,但其内容和制度宗旨基本相同,其文字表述可以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18条为例:“损害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者,如其赔偿致赔偿义务人之生计有重大影响时,法院得减轻其赔偿金额”。
与罗马法中的能力限度利益制度相比,现代侵权法中的相应制度的最大突破在于:一是将其适用案型从少数几类特殊的债务人扩展于所有债务人;二是豁免了债务人此后在其经济能力好转时继续履行余债的义务;三是基于人性关怀之理由,突破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亲密关系”的限制,将损害赔偿额的缩减制度扩大适用于所有的损害赔偿关系。这些突破充分体现了现代民法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未采纳损害赔偿的缩减制度的国家,比如德国和奥地利,当下也已经展开关于引入此等规则之立法改革的讨论,而在同样没有在立法中采纳此等规则的法国,于法院实务上,虽没有公开地以衡平为由酌减损害赔偿额,但仍有进行酌减之实。②同上注,林易典文,第四部分。
那么,除了赠与合同外,能力限度利益何以在合同法中消弭了呢?欧洲侵权法小组的一些成员在对第10:401条表达异议的同时提出了同样的疑问,究其原因,乃类似能力限度利益的规定对法律的安定性带来了巨大挑战,顾及被害人的保护倒是次要的原因了。③欧洲侵权法小组编著:《欧洲侵权法原则·文本与评注》,于敏、谢鸿飞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页;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390页。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仍有不少立法者和学者对侵权法中损害赔偿的缩减制度抱持疑虑,且合同法中的能力限度利益除少数立法例外也不被接受的根本所在。法律安定性和可预见性的需要迫使立法者放弃能力限度利益,但对正义的诉求又使能力限度利益以其他方式变相留存于现代民法的某些领域。
(四)小结:我国引入能力限度利益制度的必要性
不可否认,赋予民法以社会保障功能并不会因此就使民法承受太多负荷,侵权法中损害赔偿额的缩减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良好运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而给予“亲密关系”中的债务人比“陌生关系”中的债务人更高程度的保护,虽然可能会招致对债权人不平等保护的非议,但具有相同机理的赠与人的债务减免权的平稳运行,完全可以打消这种忧虑。因此,是否有必要以部分牺牲法的安定性为代价,而在具有“亲密关系”的合同之债的关系人之间,以及基于人性关怀的考虑而在损害赔偿之债的关系人之间引入能力限度利益,已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研究者所要考虑的应当是,在我国未来的立法或修法中,如何进行更好的制度设计,从而将该制度可能具有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而在立法者做出回应之前,笔者寄希望于司法者在面对此等个案时能依照公平正义的理念对案件做出酌情处理。
(责任编辑:陈历幸)
DF522
A
1005-9512(2015)03-0137-13
李飞,华侨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本文系华侨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4SKBS3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