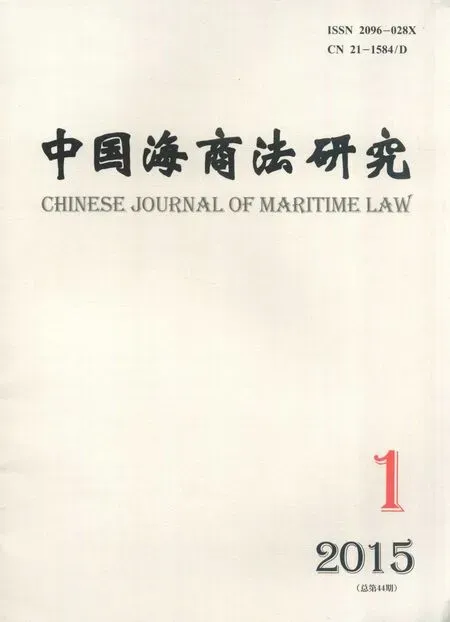从“华天龙”号案看王室豁免原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
2015-01-30杨晓楠唐艺卿
杨晓楠,唐艺卿
(1.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2.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北京 100875)
从“华天龙”号案看王室豁免原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
杨晓楠1,唐艺卿2
(1.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辽宁大连116026;2.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北京100875)
摘要:王室豁免原则是英国普通法中的一个古老原则。香港回归前,英国政府在香港法院享有司法豁免权。“华天龙”号案中,香港法院第一次检视了回归后这一原则在香港特区的适用问题,在判决中裁定中国政府代替了英国政府继续在香港享有司法豁免权。这一判决引发了法律界的激烈争论。从王室豁免在普通法中的历史沿革出发,通过与主权豁免原则的对比,分析王室豁免在香港特区的适用以及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王室豁免;“华天龙”号;主权豁免
一、“华天龙”号案情及其判决
2008年4月21日,马来西亚Intraline Resources SDN BHD公司以“华天龙”号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离岸钻油工程服务为由申请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将其扣押。“华天龙”号称“亚洲第一吊”,是中国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所有的大型打捞船,被扣押时正在香港进行救捞工作。[1]114被告广州救捞局提出以提供保释金的方式申请释放“华天龙”号,2008年香港高等法院审理了关于保释金数额的争议,一审判定保释金为6 500万美元,二审判决将其提高到约1亿2 241万美元。由于保释金额极高,原被告持续对此提出诉求,被告在2009年10月21日以主权豁免和王室豁免原则为由对香港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
2010年4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石仲廉(William Stone)法官在一审判决中驳回了被告对管辖权异议的申请,认定香港法院对此案享有司法管辖权①参见Intraline Resources SDN BHD v. The Owners of the Ship or Vessel “Hua Tian Long”,[2010] 3 HKLRD 611。。在判决中,石仲廉法官认为,王室豁免原则在香港回归后依然是香港法的一部分。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替了殖民地时期的英国政府继续在香港享有王室豁免权,广州打捞局作为交通运输部下属的一个实体,也享有王室豁免权。但由于被告在诉讼一开始已经意识到有该项权利却一直参与诉讼,故法院认为被告在此案中已放弃此项权利,因而香港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
被告享有王室豁免权这一观点随即引发了一些香港学者的强烈抨击。[2]1尽管被告对此判决提出上诉,但与讼双方均同意不对被告是否享有王室豁免权这一问题提出争辩。根据普通法精神,法院作为消极裁判人不应处理假设性问题或主动引起争议,但上诉法庭因受学界影响,罕见地在2010年11月23日的庭审中要求双方对此问题进行辩论,并特将案件押后审理以期双方再度考虑。[3]但最后双方并未对王室豁免原则形成实质争议并在上诉中和解,所以上诉法院最终未能处理这一问题,因而“华天龙”号案的一审判决成为香港特区法院唯一一件处理王室豁免原则的判例。这一原则的适用可能会对未来香港乃至内地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该判决引发了各界对于这一古老原则的重新思考。
二、王室豁免原则的起源及在英国普通法中的适用
王室豁免(crown immunity)又称“官方豁免”,是一项普通法原则,指王室及其成员或代理人可以免于在法庭被起诉或执行。这一原则产生于英国封建时期,早在1268年布莱克顿(Bracton)时期就有“国王不能在他自己的法庭以其名义被起诉”的原则。[4]2王室豁免原则在理论上源于一则古老的谚语,“国王不会犯错”(The king can do no wrong),这经常被认为是封建制度下有限司法管辖权和王室(主权者)特权的体现。
(一)对王室豁免原则的两种普遍误解
然而,对王室豁免原则长期存在着两种出于字面理解的误读。
第一,“国王不会犯错”这一法谚一味地神化了封建王权的至上性。实际上,这一理解偏离了这一原则的本意。英国学者指出,这一谚语应被解释为“国王必须不能、不被允许、也不能够犯错;如果他的行为违背了法律,就不再是法律上的行为,而是错误”。[5]也就是说,国王的行为和其他人的行为在客观上并没有差异,只是如果国王做了错事,就丧失了其行为的合法性基础,不再是上帝旨意的体现。这里的错误自然包括了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
第二,王室豁免原则会产生王室和政府在法律之上的效果,使得当事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无计可施,从而严重影响了政府行为的问责性。[6]实际上,即便适用王室豁免原则,也不意味着当事人无法获得救济,只是当国王犯错时救济方式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在英国封建制度下法院作为国王意志的产物和国王的代表,在逻辑上缺乏管辖其主人的合理性,而且“每个人不应该作其自身的法官”也是英国法的基本原则之一。[7]518因此,国王的身份并没有致使其行为在法律上与其他人的行为有本质差异。
(二)王室豁免原则下获得救济的方式
王室豁免原则赋予了国王和政府官员在法院中一定的特权,并且这种特权的行使不限于侵权案件。侵权案件是最重要的豁免案件类型,但这一原则的适用也包括了其他类型的诉讼。而且,王室豁免不仅适用于诉讼程序,也适用于申请法院令状(order)执行的程序,因为司法权在这一过程中也同样受到主权者的限制。
但即便这样,权利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依然可以获得有效的救济,只不过对国王和政府官员的诉讼方式有所不同。
第一,根据王室豁免原则,国王不能在法院直接被起诉。如要起诉国王,应以权利请愿(petition of right)的方式征得国王的同意。权利请愿是在爱德华一世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制度,通常用来要求归还落入国王手中的个人财产或不动产或者补偿其损失,以及要求赔偿因国王的违约而造成的损失。但是,很多诉讼繁琐而冗长,因此关于国王不动产的诉讼通常通过权利声明(Monstrans de droit)②在普通法中,当属于臣民的财产被王室占有且档案记载表明王室已对该财产享有权利时,臣民为取得其财产可在衡平法院或财税法院提出其权利声明,根据档案中所载事实或陈述新的事实来表明其对财产的权利。的方式得以解决。[8]1860年《权利请愿法》简化了权利请愿的程序,规定权利请愿可以由普通法院审理,这在1947年《王室法律程序条例》颁布之前是普通主体对抗国王的主要合同救济方式,但不涉及侵权领域。梅特兰认为,需要以这样的方式获得国王的同意是因为国王签署一个普通的令状(writ)来实施对其自身的处罚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此需要一个请愿(petition)而不是令状。[7]518总之,王室豁免原则并不意味着国王在法律之上。因为国王被认为是正义和衡平的源泉,所以通常不会拒绝对受损权利的救济申请,因此权利请愿通常不会被没有任何缘由地拒绝,国王也需要做出赔偿。
第二,如果起诉国王的下属或政府官员的话,那么不是必须获得国王的同意。亨利三世时期,财政署作为行政司法机构可处理私人对治安官和低级治安官的案件,但当时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地方层面,因此诉讼也限于低级官员。[4]9地方官员可以因刑事罪名被起诉,也可以因普通法被起诉。但如果政府官员是以国王的名义做出一定行为,那么,司法官在裁定之前则需国王确认与诉行为不是国王的意思,否则诉讼不能进行。尽管国王在很长一段时间保留了干涉诉讼的权力,詹姆斯一世的法律甚至要求如果原告起诉官员败诉应赔偿双倍损失,因为对官员提起诉讼会影响行政的有效性。[4]10但这不意味着不能对国王的官员提起诉讼或缺乏救济,只不过行政机关不愿将审查行政行为的权力赋予普通法院,因此特别规定了特权法院来处理此类案件。光荣革命之后,这些特权逐渐被取消,普通法院也可以处理起诉官员的案件,但在侵权案件中仍有限制,如1865年的Featherv.TheQueen案①参见Feather v. the Queen,(1865) 6 B&S 257。中,法院认为国王不能侵权,因此对其仆人以国王名义进行的侵权提起的权利请愿不予许可。
第三,当然,无论对于国王还是政府官员,更有效地消除司法豁免权的方式是通过立法赋予法院管辖权。1947年的《王室法律程序条例》是英国法中对这一原则最重要的立法变革,该法规定了在法律生效后任何人都可以对国王提起诉讼,而且国王和其代理人也需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该法同时规定,法院可以要求国王公开相关文件或信息。但是,该法律对国王的船舶作出了特殊的规定,关于国王所有的船舶的责任引照英国《商船法》的程序规定。
综上所述,在古老的英国普通法中,王室豁免原则适用于国王、国王的代理人和官员的行为,而且这一原则并不区分该行为的内容。也就是说,王室豁免不限于国家职能行为,对国王及其官员的合同和商业行为也同样适用。在对国王的起诉中,得到国王的同意通常是必要条件,而权利请愿一般会得到有效的救济;而对国王的官员行为的诉讼,则经常不需要国王的同意。这种形式可能更多地取决于诉讼便利性和可能性,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国王或者官员在法律之上。而且在英国法律改革之后,王室豁免原则很难在实际中起到阻止或者干涉当事人获得有效救济的作用了,因为这在强调法治和司法独立的英国是很难说得通的。总之,即便在没有立法废止之前,王室豁免原则在英国普通法中也顶多是一个抽象的、仅具有程序法意义的概念,而并没有对被侵害人的救济构成决定性的实质影响,唯一的问题可能在于在侵权诉讼中对司法权的限制。
三、王室豁免原则与主权豁免原则的比较
主权豁免原则(sovereign immunity),也称国家豁免(state immunity),这是一个与王室豁免原则密切联系、甚至时常容易混淆的概念,因为二者都涉及到国家或者国家的官员在法院中是否免于管辖或执行的问题,具有相当大的相似性。在“华天龙”号案中,被告在抗辩时也一并提出了王室豁免原则和主权豁免原则适用的主张。实际上,早期在英国法院国王正是因为其主权者身份而获得豁免的,即便在学术文献中王室豁免也常被称为主权豁免,美国法院1812年的Mowerv.Leicester案②参见Mower v. Inhabitants of Leicester (1812),9 Mass. 247。判决中王室豁免原则就使用了主权豁免的概念。但是在今天,主权豁免原则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法上的重要制度,与王室豁免原则也应有着清晰的区分。
首先,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王室豁免是源于普通法的原则,给予的是本国主权者的豁免权,因此可以称为国内主权豁免。即便在王室不存在的情况下,主权者不能进行自我限制,维持行政的独立和裁量权,防止机构间不当干涉,这些也可以成为王室豁免原则延续适用的理论基础。而主权豁免则是指在一国法院内对其他国家主权者提供的豁免原则,即未经主权国家同意,国家不得在外国法院被起诉或者执行,其目的是避免国家假借司法管辖权干涉他国内政,可以称为外国主权豁免。主权豁免原则通常基于国际礼让、互相尊重、维护主权等理论基础,而且一般通过立法方式进行规定,如英国1978年的《主权豁免法》、美国1976年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新加坡1979年的《国家豁免法》、巴基斯坦1981年的《国家豁免法令》、南非1981年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澳大利亚1985年的《外国国家豁免法》等。此外,还有与此相关的国际条约规定了国家间的司法豁免关系,如1972年的《欧洲国家豁免公约》和2004年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华天龙”号案所扣押的船舶属于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在香港回归后属于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所以主权豁免原则并不适用于这个案件,该判决也持这一观点。
其次,王室豁免作为一项普通法原则,其适用的对象与主权豁免原则不同。如上所述,因为王室豁免基于国内主权至上,因此适用这一原则的时候一般不会直接审查该行为的性质,而是通过对行为主体的判断来决定是否适用王室豁免原则及采取什么样的救济方式。也就是说,王室豁免原则的适用并不限于国家行为,行为主体以谁的名义、行使什么职能、是否受成文法排除才是决定其豁免程度的主要要素。相比之下,主权豁免原则考虑所涉行为的实质内容,分为绝对豁免和相对豁免(或称有限豁免)两种情况。英国对主权豁免制度曾经采取绝对豁免原则,即外国主权者的所有行为都不能在法院被起诉。但在1978年改为采取有限豁免原则,[9]89即国家只能因国家行为获得豁免而不能在商业行为中要求豁免,而决定该行为是否是商业行为则应考虑该行为的内在性质而不是该行为的目的。美国的《外国主权豁免法》、[10]15《欧洲国家豁免公约》和《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也都采取了有限豁免原则。这是因为外国法院对主权国家的豁免通常基于主权礼让,但不希望因豁免导致国际商业运作受到影响,也不想因此影响法院行使正常的司法权。在刚果金案中,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陈述了我国在主权豁免原则问题上的立场,认为我国一贯主张对外国国家及政府行为及其相关财产实行绝对豁免原则,并说明这一原则立场延伸适用于香港①参见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nd others v. 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2011) 14 HKCFAR 95。。香港终审法院在刚果金案的判决中认为,在1997年回归之前,香港适用的是英国普通法上的有限豁免原则,而不是国际法原则,至于回归后是否应适用、如何适用这一豁免原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第158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最终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绝对豁免原则也应适用于香港,香港法院对外国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均无管辖权②同上,另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9]89-92
再者,由于主权豁免通常通过立法规定,因此可以获得豁免的主体比较清楚而且有限,主要包括国家本身、元首、政府部门等。大部分国家为了保证商业贸易的有效性,给予国有企业的豁免权是很有限的,一些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子公司都没有豁免权。对于控股公司的豁免权问题,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采取“结构主义”而不是“职能主义”,即不以行为性质作为豁免标准。[11]相比之下,王室豁免原则的适用主体则以法院的解释原则为前提,这一概念本身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王室豁免原则适用的主体不尽相同,什么样的法人团体属于政府的一部分进而享有豁免权是一个普通法解释的问题,通常采用的学说包括“控制说”和“功能说”,采取不同的学说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最后,豁免权排除的前提不同。在主权豁免原则下,如果国家明确表示放弃主权,或者在合约中表明受制于法院管辖则丧失了豁免权。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在被告提出证据证明其享有主权豁免的情况下,原告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放弃豁免或无豁免权,法院才能享有管辖权。[10]16而王室豁免权则通常不会因事先声明而丧失,在一些情况下需要在事后得到国王的同意,而且即便国王在审判时同意了法院的管辖,也不意味着其在执行程序中丧失豁免权。但是如上所述,即便在1947年之前,王室豁免权也并不排除当事人以其他方式获得救济;而对于主权豁免原则而言,当事人往往会因为诉讼一方获得豁免权而丧失有效救济的途径。
四、王室豁免原则在香港的适用
随着英国大肆的海外扩张,王室豁免制度伴随着普通法的拓展适用在殖民地得以沿用和发展,也延伸适用至香港。通过这一原则,英国政府在殖民地法院享有豁免权,这样可以保护英国政府作为殖民地主权者的地位。不过,在一些废除君主制度的前殖民地(如美国),因王室已经不再存在,豁免的主体则由国王和王室代理人转变为州或国家的主权者及其雇员。而在其他的殖民地,这一制度随着普通法的保留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王室及其在本地的代理人仍享有王室豁免的特权。
“华天龙”号案件判决是香港回归后香港法院对王室豁免原则首次检视的结果,该判决将王室豁免原则在香港的适用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1997年7月1日之前的适用
回归前,香港法院并没有实际处理王室豁免的判决,所以,并不知道殖民地法院对王室豁免原则采取什么样的解释原则。在“华天龙”号案件判决中石仲廉法官认为,香港在回归前存在着两套可以享有王室豁免权的机构:一个是英国王室及英国政府,另一个是香港本地的官方政府,前者是王室豁免自然应适用的主体,而后者则是殖民者在香港的代理。对于香港本地的官方政府,根据1873年香港的《民事诉讼法》,如果要起诉本地政府需要获得总督的同意并在诉讼中以律政司司长(Attorney General)为被告。此后1957年的《官方法律程序条例》是英国《王室法律程序条例》的翻版,规定可以起诉香港本地政府。《官方法律程序条例》第25条还特别说明,该条例并没有授权法院扣留、扣押或者出售属于女王或政府的船舶,或就该船舶给予任何人留置权。有学者认为,该条例在回归后的版本1997年的《官方法律程序条例》同一条款足以排除法院在“华天龙”号案中的管辖权,而无需引入王室豁免原则。[1]118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这两部香港法律中都使用了“王室”(crown)一词,但其中文翻译为“官方”而非“王室”,而且从法律的规定来看,这里的王室仅包括了香港本地政府而不包括英国王室,“华天龙”号案的法官和被告律师都认同这一点。可见,在回归之前,立法并没有赋予香港法院审理英国王室和政府案件的管辖权,因而英国王室和政府在殖民地是享有普遍的司法豁免权的。
(二)1997年7月1日之后的适用
尽管《基本法》的目的之一是维持香港法律的延续性,但回归本身给香港带来的变化不是文字上的替代,而是一种宪政制度彻底的变更。回归后,中国政府代替英国政府成为香港的主权者,之前英国王室和政府在香港享有的法律上的特权和权力应如何适用,这对于香港法院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
“华天龙”号案中,石仲廉法官对王室豁免原则的推理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第一,1957年的《官方法律程序条例》并没有从立法上排除英国王室和政府的豁免权,因此,王室豁免原则作为一项普通法原则在回归后仍得以适用,唯一改变的是中国中央政府代替了英国王室和政府享有在香港这一地区法院的豁免权。
第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国政府享有王室豁免权,这一豁免权应延伸适用至哪些部门?被告是否属于豁免权延伸适用的范围?对于这一问题,石仲廉法官分析了王室豁免原则适用的两种学说,一个是由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提出的“功能说”,即是否享有豁免权应取决于该公司或者该行为是否属于国家行为行使的一种①参见Bradken Consolidated v. Broken Hill Proprietary Co Ltd (1979) 53 ALJR 452。;另一更有影响的学说是“控制说”,即该实体是否在国家控制之下。石仲廉法官认同“控制说”的观点,认为核心问题在于该公司能否以其自己的名义行使独立的权力。
第三,石仲廉法官认为,中央政府享有王室豁免权,交通运输部作为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因而享有豁免权,而证据显示广州打捞局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而是交通运输部的下属机构,受交通运输部控制(控制其运作和财政),因而可以享有司法豁免。
第四,尽管被告享有豁免权,但因被告一直参与诉讼,则被认为已放弃豁免权,因此香港法院仍可对此案享有管辖权。
学者对该判决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石仲廉法官正确确认了中国政府作为主权者在回归后享有的豁免权,“确认了中国政府机构官方豁免权的法律渊源是普通法”,“确认官方豁免权适用对象的认定标准是控制说”,“确认官方豁免权可以通过诉讼行为予以放弃”。[12]
反对者则认为这一判决会降低香港法院的司法地位,因为其他采取有限豁免原则的国家法院可以审理针对中国政府下属机构和企业的商业行为提起的诉讼,甚至国内法院因为缺乏王室豁免这类原则也可以享有对政府和国有实体的管辖权。再者,国内制度的复杂性使得实际适用“控制说”时会遇到一些困难。[2]1相反,他们认为《基本法》第22条的设计已经说明“中央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一切机构及其人员均须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这一条款排除了王室豁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
对于判决的争论,笔者认为,《基本法》第22条的设计并没有排除王室豁免原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延续适用,这一条文也没有明确授予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管辖权。相反,《基本法》第19条规定了对香港法院的管辖权限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对管辖权的限制;香港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只要王室豁免原则是回归前香港法律的一部分,就应在回归后成为原有法律对法院管辖权的限制。而回归前《官方法律程序条例》并没有排除英国王室及政府在香港法院的豁免权,因此这一豁免权在回归后仍应存在,并由新的主权者享有。至于这一制度的封建残余性或不合理性、不平等性,只是说明了普通法原则本身的合理性问题,并不应影响其有效性。对于这一点,笔者认同石仲廉法官和董立坤教授的观点。
但是,对于石仲廉法官适用的“控制说”来确定某一实体是否属于王室豁免权的享有者问题,笔者更倾向于反对者的意见。“控制说”对于财务和运作比较公开明确的机构而言是一种较为适当的标准,但对于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外国公司很难获知其运作的规律,香港法院获得的材料也往往由被告方提供,这样难免影响原告方在商业贸易中的判断。若因此丧失救济机会,则有失公允。
五、“华天龙”号案判决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虽然“华天龙”号案件的判决由高等法院原诉法庭作出,从普通法判例等级来看,上诉法院和终审法院未来的判决均可优于或推翻这一判决,但这一判决现今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关于王室豁免原则的唯一判例,已成为香港法律的一部分。尽管中国政府及其下属机构在香港享有的王室豁免权可以通过参与诉讼来放弃,但判决仍可能给香港和内地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一原则会对香港法院的管辖权造成很大限制。在香港从事公务和商业行为的中国内地企事业单位数量众多,如上所述,用“控制说”来判断这些企事业单位的性质对一般民事主体和法院都是较为困难的事情。若采取王室豁免原则,无论这一实体进行的是国家行为还是商业行为,其对诉讼或者执行都可享有豁免权,而且该实体可选择通过参与诉讼放弃豁免权。如果该实体通过参与或申请豁免的方式选择对其有利的诉讼,而放弃对其不利的执行,香港法院无法管辖,那么,众多国有企事业单位可能在法律上享有不当的特权。
其次,更重要的是,上文对英国普通法制度下的王室豁免原则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一原则并没有剥夺权利受侵害人的救济权,而国内法律中缺乏权利请愿制度、国家诉讼程序法等可参照英国限制豁免权的立法,那么,如果被告申请豁免,原告无法获得任何救济。
再次,如果按照王室豁免原则的适用,法院获得管辖权通常要根据事后的追认,而不是事先的协议,而且即便事后追认诉讼程序的管辖权,也不当然放弃在执行程序中的豁免权,那么国有企事业单位在法律程序上可选择规避法院管辖的空间就更大了。
上述几点貌似均给中央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带来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诉讼上的优势或特权,实际情况则不然。王室豁免原则在香港特区的适用并不会给中央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带来额外的利益,而且从长远来看是弊大于利的。因为如果该中央政府机构或事业单位执行的是国家行为,那么根据《基本法》第19条和刚果金案的先例已经可以获得在香港法院的豁免权,根本无需担心香港法院作为一个地区性法院对主权行为的干涉。香港特区法院也在多年审判实践中已经在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变得日益成熟,[13]因此在刚果金案中主动提出根据《基本法》第158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所以,也极少会出现以司法判决影响中央主权行使的情况。如果案件所涉的是普通商业行为或者是国家控制的国有企业,那么这种诉讼上的不平等性和特权性可能会给未来的商业伙伴造成极大的影响,尽管在这一案件中的广州打捞局是直接隶属于交通运输部的单位,但“控制说”这一原则可能会因辩方律师的解释而适用至其他国有企业,这种对贸易伙伴的潜在影响会大大影响我国国有企业在香港的竞争力,影响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商业地位,转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
总而言之,尽管王室豁免原则无论从合理性上看还是实际经济效益上看,均不是一个维护我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合法权益的有力原则,但笔者认为其合法性不能因此受到质疑。在现有的普通法原则下,唯有通过明确的立法排除,才能够减少这一原则适用产生的不当影响。而根据《基本法》第17条的规定,这样的立法极可能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在咨询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后,决定立法会提请备案的法律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赵亮.2010年香港海商法判例综述[J].中国海商法年刊,2011(6).
ZHAO Liang.The overview of the maritime case law in Hong Kong[J].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aw,2011(6).(in Chinese)
[2]CHEUNG E,GU Wei-xia,ZHANG Xian-chu.Crown immunity without the crown[J].Hong Kong Lawyer,2011(11).
[3]官方豁免权惹法界哗然上诉庭罕有主动要求审[N].明报,2010-11-24(8).
Crown immunity brought out the debates,the court of appeal surprisingly required the issue actively[N].Ming Pao,2010-11-24(8).(in Chinese)
[4]LOUIS L.Suits against governments and officers: sovereign immunity[J].Harvard Law Review,1963(1).
[5]EHRLICH L.No. XII:proceedings against the crown(1216-1377)[M].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42.
[6]ERWIN C.Against sovereign immunity[J].Stanford Law Review,2001(5):1214.
[7]POLLOCK F,MAITLAND F.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M].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8.
[8]元照英美法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928.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Anglo-American law[M].Beijing:Law Press,2003:928.(in Chinese)
[9]董立坤,张淑钿.香港特区法院对涉及国家豁免行为的案件无管辖权[J].政法论坛,2012(6).
DONG Li-kun,ZHANG Shu-dian.The HKSAR courts do not share the jurisdiction over the cases of sovereign immunities[J].Tribune of Politics Science and Law,2012(6).(in Chinese)
[10]宋锡祥,高大力.从“天宇案”透视国家主权豁免问题[J].东方法学,2010(1).
SONG Xi-xiang,GAO Da-li.On the sovereign immunity:a case analysis of Tian Yu[J].Oriental Law,2010(1).(in Chinese)
[11]肖永平,张帆.美国国家豁免法的新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805-806.
XIAO Yong-ping,ZHANG Fan.U.S.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law:developments & impacts[J].Wuhan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2007(11):805-806.(in Chinese)
[12]董立坤,张淑钿.论中国政府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豁免权——以华天轮案为例[J].政治与法律,2011(5):11.
DONG Li-kun,ZHANG Shu-dian.On the immunities of Chinese government in HKSAR[J].Politics Science and Law,2011(5):11.(in Chinese)
[13]YANG Xiao-nan.Two interpreters of the basic law:the CFA and NPCSC[C]//Hong Kong’s Court of Final Appeal: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in China’s Hong Ko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69-93.

The doctrine of crown immunity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 case analysis of Hua Tian Long
YANG Xiao-nan1,TANG Yi-qing2
(1.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2.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Crown immunity is an antique in the British common law. Before the transition in 1997, Hong Kong courts did not enjoy the jurisdiction ove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under this doctrine. After the transition, the court examined its application in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Hua Tian Long case, holding that it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replaced the colonial governor to enjoy the crown immunity in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judgment was then hotly criticized by some Hong Kong scholars.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his doctrine, and analyzes its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nd also its influences in the futur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imilar doctrine of sovereign immunity.
Key words:crown immunity;Hua Tian Long;sovereign immunity
作者简介:杨晓楠(1979-),女,辽宁大连人,法学博士,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E-mail:chapelly.yang@gmail.com;唐艺卿(1992-),女,湖北赤壁人,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E-mail:tangyiqing123mao@sina.com。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与邻国海洋权益争端问题的国际法理研究”(12JZD04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骨干项目“‘一国两制’下香港行政长官普选制度研究”(313201511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技创新团队项目“海洋强国战略的海法保障”(3132014313)
收稿日期:2014-06-30
中图分类号:DF96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15)01-009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