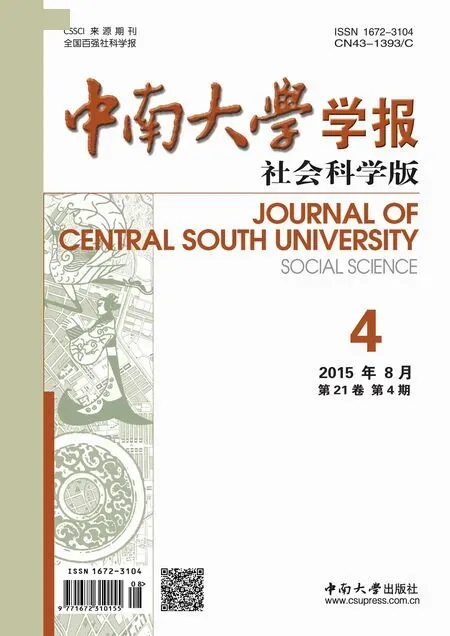嘉庆朝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
2015-01-21常冰霞冯永明
常冰霞,冯永明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
嘉庆朝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
常冰霞,冯永明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
为了打破和珅专擅引发的皇帝失聪、官场疲玩,嘉庆帝在处置和珅后便开启广开言路这一政治信息渠道,试图达到掌控政治信息、调控帝国动态的目的。为了确保信息渠道的机密,皇帝采取了禁抄附稿、道员密奏、条陈封口等诸多措施。洪亮吉的露章条奏以及委托永瑆、朱珪、刘权之代为呈奏,最终触犯了嘉庆帝对信息机密的强调而遭受惩处。于广开言路背景下分析洪亮吉上书事件,可以发现皇帝在此事上前后迥异的态度,并非是对妄言渎奏的总爆发,而是对洪亮吉“言事违例”以及“居心殊不可问”的惩罚。
广开言路;信息控制;洪亮吉上书事件;言事违例
新掌权之嘉庆帝及其朝廷所推行的各项革新举措,在清帝国以及由其衍生的“中国”之历史中产生了长远影响。[1]尤其是“最具革新精神”[2]的广开言路举措,不仅开创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的“言路大开”[3](11314)局面,而且凭借言官的“指责朝政”而于时局“补益良多”。[4]即便是偶遇“无知妄渎”之事,亦不过将原折掷还而“免其议处”,其原因皆在于“降旨求言”。[5](155)然而,洪亮吉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并委托成亲王、朱珪、刘权之代为呈递却触怒龙颜。对于洪亮吉因上书而谪戍伊犁,学界或从政治革新视角①出发将矛头指向嘉庆,认为此举不仅表明其在用人行政方面的赏罚不明,更是其未始终坚持改革方针或半途而废的体现;或于广开言路下就上书事件进行批判性反思②,认为是嘉庆在广开言路上的全面后退,而赦免洪亮吉的目的则是为了扭转言路不通;抑或从法律③及皇权视角④探索洪亮吉获罪的本质原因,指出“既属不幸,亦为万幸”[6](5559)之洪亮吉获罪的根源,在于其上书内容及方式对皇帝的“冒犯”。无论是从政治革新、广开言路,还是从皇权与法律角度的分析,学界多侧重于对嘉庆帝的批判,而较少从嘉庆继位后的革新举措这一框架中前后贯通地分析事件的深层次含义。因此,在中外学界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分析嘉庆及其官僚体系的“贡献”[1]时,沿循诛杀和珅、广开言路的分析框架对该事件进行纵向考察,不仅可以阐释皇帝如此处理的政治动机,而且还可深入分析其背后后暗含的信息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洪亮吉上书始末
洪亮吉,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喜论当世事,嘉庆三年因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乞归。和珅伏诛后,洪亮吉为朱珪起用,于嘉庆四年四月派充实录馆纂修官。八月二十日,洪亮吉以“春初束装匆遽,在都车马衣履未具”为由乞假获准。是时“川陕余匪未靖,湖北、安徽尚率兵防堵”,皇帝时发谕旨筹饷调兵。对于时局之艰,洪亮吉“晨夕过虑,感叹焦劳,中宵不寐”[7](183)。鉴于“曾蒙恩遇,不当知而不言”,于二十四日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极陈时政,分别委托成亲王、吏部尚书朱珪、左都御史刘权之代为呈递。然而,其上书却令嘉庆帝龙颜大怒,于二十五日谕令“军机大臣即传该员,将书内情节令其按款指实、逐条登答”。因所供“言语闪烁,不实不尽”,嘉庆帝再发谕旨,将洪亮吉革职并“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5](302−303)被押入刑部南所狱后,因“司事者不测上意”而“严加桎梏”。[8]二十六日,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将洪亮吉照大不敬律定拟斩立决。二十七日,嘉庆帝谕令洪亮吉从宽免死,发往伊犁交与将军保宁严行管束。同日传谕保宁:
俟洪亮吉解到后严加管束、随时察看,如能改过自新、安静守法,俟三五年后据实具奏,侯朕降旨。倘或故态复萌,使酒尚气,甚或妄肆议评、诋訾国是,又复形诸笔墨,保宁即一面锁拿,一面据实严参具奏,毋得稍为讳饰。[5](307−310)
从嘉庆帝所发谕旨来看,如果洪亮吉依然妄肆议评,则照律治罪;若能改过自新,则可于三五年之后宽减其罪。不过与皇帝设想不同,洪亮吉却因一场祈雨而提前赦免。自嘉庆五年入春以来,雨泽较少,立夏以后仍未降雨。为了缓解旱情,嘉庆帝降旨将各省军、流以下案件减等,派遣官员致祭风神,并亲至社稷坛斋心步祷,却始终不见效果。经过反复思量,嘉庆认为“惟有渥沛恩施,庶可仰祈昊贶”。于润四月初二谕令刑部详细查明从前所办重案中久禁囹圄犯官及各员子孙释放回籍后,仍不准当差应试之人,以及发遣新疆等处永远不准释回的官常人犯,“酌量加恩,以期敬迓庥和,速敷霑泽。”[9](195)初三日,皇帝谕令洪亮吉释放回籍,仍行知江苏巡抚岳起留心查看,不准出境。[9](196)富有戏剧性的是,就在谕旨颁发当日便彤云密布,子时“甘霖大沛,连宵达昼”,京师“近郊入土三寸有余,保定一带亦皆渗透”。[7](190)对于诏下而雨降,嘉庆帝制诗纪事:“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于呼吸,益可感畏。”[3](11315)时人亦称,“诏赦直言获罪洪亮吉归,是日大雨,天人之感应捷矣。”[10]不管是嘉庆所言之天鉴可畏,还是陈康祺所述之“天人感应”,其背后暗含的仍是对皇帝仁政的赞誉与褒扬⑤,但徐珂却直言皇帝在洪亮吉上书事件中的处置失当,“赦下之次日,朱文正公珪入见,仁宗手洪书示朱,朱跽捧以观,则见御笔署其首四字,曰:‘座右良箴。’朱顿首泣曰:‘臣所鬱结于中,久而不敢言者,至今日而皇上乃自行之,臣负皇上多矣,尚何言!’伏地久之始起。”[11]无论是慑于皇权的“久而不敢言”,还是皇帝自行改之导致的“负皇上多矣”,无不彰显群臣对嘉庆帝问罪洪亮吉的不满以及赦免后的激奋。
细细思辨洪亮吉上书事件的整个过程,我们便会发现从其上书至谪戍新疆,案件短短三天时间便告完竣;从罹罪到颁发赦免谕旨仅及百日,堪称自辟新疆以来汉员赐还之最。[12]三天定罪反映的是皇权的雷霆万钧,百日而还则映射皇恩浩荡,如此明显的差异难道因缘于祈雨?此外,军机处会同刑部严审后以“罪在不赦”“丧心病狂,无复人理”[5](307)照大不敬律定拟斩立决,皇帝亦认为“肆意妄言、有心诽谤”实属“罪由自取”[5](309)。但在赦免谕旨中却做了截然相反的评论,不仅称洪亮吉所言“实无违碍之句”,而且所论“实足启沃朕心”。[9](196)诚然,洪亮吉所奏“全都属于国家大政,所举事例,也大多有实据,既有对内外诸臣的弹劝,亦有对君王的规谏,实不失为切中时弊的肺腑之言”[13]。但又该如何解释嘉庆前后迥异的态度?若将时空延展,沿循广开言路进行前后贯通的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事件背后的真正意蕴。
二、集思广益?信息控制!——嘉庆帝广开言路
道格拉斯·诺思曾经用“代理人”指称各个帝国的官僚政治。作为统治者代理人的各级官吏虽然会在帝王统摄下履行职责,但那些“代理人”的自身利益很少与统治者利益完全一致。[14]帝王要想介入官僚机器并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必须全面而可靠地掌握信息。[15]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君主能否通过官吏来实现其国家产权效用最大化,主要取决于官僚制度能否有效测度官吏的相关信息。”[16]所以,要实现对作为“代理人”的官僚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的监控,统治者便需要一个政令下传和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系统,在传递政令的同时将各级行政体系的情况反映到皇帝手中,以便做出准确且快捷的应对。清承明制,将科道作为官僚体系的监察系统,试图借此实现对包括各级行政体系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监控。然而,具有风闻奏事之权的科道官员,却常常成为党同伐异、参劾政敌的工具,使统治者难以获取真实的政治信息。康熙帝对风闻奏事之权禁止或开启的踌躇,不仅反映出统治者将科道视作政治信息渠道的意愿,更揭示了统治者在科道提供信息与风闻奏事之间的矛盾心理。随着康熙后期政治斗争的加剧,皇帝在重申科道风闻奏事的同时,开始使用密折这一信息收集渠道。后者的出现“可以证明当时包括科道制度在内的政治信息渠道无法满足皇帝的需求,皇帝需要一种更广泛、安全、准确的政治信息渠道,以便让他能够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主动地位”[17]。
密奏制度自其创立之初便是统治者掌控帝国动态、调控朝廷官场的犀利武器,是“中央决策的主要信息资源”;而军机处则“使皇帝对于信息加工处理的效率明显提高”,有利于权力的时空扩展。[18]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密奏制度与完善皇帝独裁之军机处[19]的结合,实质上是使“一切政务完全由皇帝独揽”[20],而非另外“再增加一个可能与君权抗衡的力量”[21]。虽然密折确实弥补了科道言官因介入党争而使信息壅蔽的弊病,但随着制度化色彩越来越重,其在信息提供方面的功能亦逐步削弱。尤其是为了防止密奏中的参劾,和珅不仅令各地在呈递奏折时须“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6](2693),同时又利用军机大臣掌管军务、吏部、刑部事务以及户部题奏事件的机会任意延搁、擅自驳奏。和珅对各地信息的筛选上奏,无疑削弱了皇帝对信息的掌控。尽管和珅的专擅蒙蔽使下情不能上达,但廷臣若“能及早参奏,必蒙圣断立置重典”。而今却“无一人奏及”,足见内外诸臣因畏惧和珅而“钳口结舌”。[5](16−17)在嘉庆帝看来,倘若群臣能参奏和珅,必然不会导致“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22]的情形。虽然表面上控诉的是廷臣对和珅的畏惧,但背后暗含的却是与“钳口结舌”相对应的皇帝对帝国动态的无所洞识。换言之,真正令嘉庆苦恼的并非被其称为致使数十年腐败与弊政的“元恶”⑥,而是因其专擅所引起的官场负面效应,即通过“传知各省抄送折稿”[5](34)等方式致使皇帝对信息掌控的不足。是以,无论是由和珅专擅所导致的下情不能上达,还是因其庇护所带来的地方官场的沆瀣一气,均是嘉庆帝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嘉庆四年正月初五日,皇帝遵皇祖、皇考“颁旨求言”之例,循“兼听则明、偏听则蔽”之训,谕令“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使“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以符“集思广益至意”!无论如何言述,始终难掩其降旨求言、广开言路的真实目的,即借一切事宜的“封章密奏”达到“周知天下之务”,并借此考察官员是否“尽公”以及“兴利除弊”。[5](11)质而言之,是借助广开言路这一政治信息渠道打破群臣“钳口结舌”的官场颓态。如果说广开言路的谕旨所传递的是一种试探信号,那么皇帝随后颁发的上谕则是快刀斩乱麻地将和珅剥离出去从而把密奏这一重要信息来源握于手中,并使军机处再次恢复至其创设之初的功用⑦。初八日谕令各部院衙门文武大臣及直省督抚藩臬、凡有奏事之责者及军营带兵大臣等:“嗣后陈奏事件俱应直达朕前,俱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将所奏之事豫先告知军机大臣。即如各部院衙门奏章呈递后,朕可即行召见,面为商酌,各交该衙门办理,不关军机大臣指示也。何得豫行宣露,致启通同扶饰之弊耶!将此通谕知之,各宜凛遵。”[5](13)斜体为皇帝御笔添改之处,虽寥寥数语却彰显诸多信息。“俱应”与“豫先”不仅表明密奏失去其应有之效,更折射出皇帝对此状况的愤怒、不满以及军机大臣权力的膨胀;“不关军机大臣指示”一语在重申密奏机密的同时,更是直接将因和珅擅权而旁落至军机处的权限再度收于皇帝手中;而“各宜凛遵”则反映嘉庆对密奏这一信息渠道的重视和改变“通同扶饰之弊”的决心。
正月十二日,嘉庆帝再下谕旨,借哈当阿折内另有副封一事敲打群臣,谕令“嗣后严行禁止,毋许再用副封,致干重咎”[5](17)。虽然嘉庆帝以“尚未接奉谕旨”为由免予追究,但借此警告的意味却颇浓。如果说先前两次谕旨所传递的是谆戒与警示,那么在将和珅定罪后就抄送折稿一事所颁谕旨则明显带有最后通牒的含义:“今和珅业经伏法,所有随带文书当永远停止。倘经此番饬禁之后尚有仍蹈前辙者,必当重治其罪,决不姑贷。”[5](34)从最初的“各宜凛遵”到随后的“致干重咎”,再至“重治其罪、决不姑贷”,反映的是嘉庆彻底杜绝另有副封的决心以及对信息来源渠道的重视。透过广开言路的面纱向下发掘,我们便可发现嘉庆一直在强调或支持的是信息的重要以及皇帝对此类信息的掌控与独享。正如嘉庆四年六月十二日所发上谕所言:“治天下之道莫要于去壅蔽,自古帝王达聪明目、兼听并观,是以庶绩咸熙、下情无不上达。朕自亲政以来首下求言之诏,虚己咨询、冀裨国是……设非诸臣应诏直陈,则贪劣之员岂能即时败露。”[5](207)此语一语中的,不仅陈述了信息对于帝王治理天下的重要以及降旨求言的实际效果,更暗示了嘉庆借广开言路之名、行掌控信息资源之实的真实目的。
三、嘉庆帝对政治信息渠道的重视与掌控
嘉庆帝广开言路的真实目的,正在于借助密奏这一信息渠道将和珅专擅导致的皇权失聪以及官场疲玩大加整饬。对于和珅专擅导致的皇帝失聪,嘉庆帝尚能于剪除和珅、掌控信息渠道后通过官缺的调补来打乱和珅构建的利益网,那么对于地方官场媚上欺下、怠玩因循的黑暗与腐败,除了于督抚等重要职位使用得心应手之人外并不能彻底打破地方的官僚体系网络,只能使用奏折来掌控地方官员动态以及全国局势。因此,无论是私密之奏折,还是公开之条陈,均是皇帝掌控信息并据此作出补救或指示的依据。是以,皇帝对信息渠道的掌控严密便不言而喻。
嘉庆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湖北布政使张长庚递到请安折一件,于“请安”字下添写“叩慰睿怀”四字,嘉庆帝对此大为恼火,不仅在于未见此款式,更在于张长庚于湖北多事之秋并未就川陕义军“是否相距已远、民情是否一律宁贴”提及一字。嘉庆帝广开言路、禁止副封的最终目的在于掌控各处信息,从而加强对帝国的控制,但地方大员却并不遵办,以致嘉庆得出“地方大吏于民情漠不关怀”的结论。[5](67)如果张长庚的奏折只是令嘉庆指摘地方官员不关心民情的话,那么湖北按察使祖之望的奏折则令嘉庆帝对奏折之机密性提出质疑。二十九日,祖之望的请安折呈递圣前,嘉庆帝竟然发现其所采用的样式与张长庚的奏折完全一样,亦是于“请安”字样下添缮“叩慰睿怀”四字。在皇帝看来,“若非同城彼此酌定,安能如此画一?”是以,嘉庆帝据此认为祖之望与张长庚两人的奏折实际上是“商同缮写”。[5](68)凡具有陈奏密奏之权者,可以参劾上司、同僚属员,甚至辖境以外之人。[23]为了确保信息的精确,皇帝往往会“另有访问打听”[24]。但商同缮写却使密奏失去了官员互相监督、彼此制衡之效。正如嘉庆帝所言,“设遇举劾所属官吏应行密奏之处,亦皆似此通同一气,其弊将不可胜言。”[5](68)藩、臬两司有“奉事之责”,自当随时将吏治、民瘼据实入告,但湖北两司却“视同膜外,匿不上闻”。为了确保密奏应有之效,甚或为了遏制商同缮写现象的出现,嘉庆于三月初十日颁发谕旨,给予道员密奏之权:“嗣后除知府以下等官仍不准奏事外,其各省道员均著照藩、臬两司之例,准其密摺封奏,以副兼听并观、集思广益至意。”[5](81−82)嘉庆帝此举不仅是借助道台制约督、抚、两司,更是借助其熟知本省政务民情的功用拓展更广阔的信息来源渠道。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巡漕给事中刘坤由五百里递到折报,嘉庆帝以为必系紧要事务,不料所奏竟系旗丁控告于采芹等勒扣造船帮费一案,以“实属不晓事体”为由交部议处。[5](71−72)由于担心降一级调用,会导致其他“不晓事体之员,遇有要务,转或拘泥,不敢由驿驰递”,而将其施恩改为降二级留任。尽管此时刘坤再次递到呈奏寻常事件的五百里奏折,但皇帝因甫经议处而未再加饬谕。不过,当刘坤于三月二十一日第三次呈奏照例办理漕运情形的五百里驰递奏折,并用六百里文书向兵部查讯前次驿递奏折事宜后,嘉庆帝不胜其怒,不仅将其降一级调用、不准抵销,而且撤销其巡视南漕事务。[5](99)从皇帝谕旨来看,刘坤获罪并非仅仅是至再至三的徒劳驿站,要不然亦不会为了防止官员拘泥而施恩减罚。其获罪更多地因缘于“全不晓事”,是对其完全无视奏折担当之重责以及不能体会皇帝看重密折之深意的惩处。因此,如果说嘉庆帝看重的是关系民生或吏治的重大事件而非循例办案之小事的话,还不若说其看重的是提供政治信息的密折这一渠道。
正是因为对密奏的看重,皇帝才会借诸多时机加强对信息传递机密的防范。嘉庆四年六月初一日,皇帝因湖南从九品谭学庠条奏事宜一摺封套并未黏口一事训诫群臣。在其看来,封章陈奏事件应如户部堂官般将“原封进呈”以直达御前,若先经拆阅,难免会出现“私行压搁不为呈递”或素相交好“代为隐匿”之事。 为了防止“和珅之续”局面的出现,嘉庆帝传谕各部院衙门,若呈控事件“系本人喊禀及露章投递者,自不妨先行阅看;傥系本人自行缄封,即应将原封呈览,不许私自拆阅……以杜壅蔽而昭慎密”。[25]密折正是因其机密而成为皇帝驾驭群臣的利器,虽然如今广开言路、明目达聪,但密折之本质与犀利并不会改变。嘉庆对不许私自拆阅的重视以及与转奏之人无涉的强调,不仅彰显其将广开言路下的条陈当做有效的信息来源、驭下工具,而且表明其对信息的掌控和机密的重视,即便是亲王触犯其底线亦难免责罚。六月十七日,成亲王淳颖以“别处并无引见”为由,将宗人府所递引见官员奏折撤出。嘉庆帝对此大为恼火,直斥责淳颖此举是欲“首先尝试复和珅之故”。嘉庆以和珅喻成亲王,不仅仅将矛头指向其本人,更在于皇帝对撤销奏折之潜在影响的关注。在其看来,若任由已经呈递的章疏“公然擅彻”的陋习相沿,“设遇有封口奉章或参劾大臣章疏,亦可任其徇私托人代为彻下”,必会导致“下情不得上达”。即便成亲王声称是因“天气暑热”而为皇帝“节劳”,但其行为本身却有阻挡嘉庆了解帝国动态之嫌。是以,嘉庆借此谕令内外衙门,“陈奏事件一经接受,皆应直达朕前、听朕批示,毋得捺搁擅彻。傥有仍蹈前辙者,一经察出,必当从重治罪,决不宽贷。”[26](575−576)
无论是给予道员密奏之权,还是对不得私自拆阅及擅撤奏章的重视,均反映出嘉庆对信息渠道的重视与维护。其对刘坤的惩罚以及对成亲王的训示,更像是对其妨碍皇帝掌控信息行为的警示。即便是以监生身份妄谈国政、指陈利弊且欲变乱旧章的周砎,妄参司员之恒杰,甚或以副都统干预查抄和珅之事并欲审讯使女、寻掘金银之萨彬图,请普赏八旗、以资市易货物之富森布,亦只是罢斥而已。其本质原因正在于,对此“尤出情理之外”的“无知渎奏”治罪,是“自蔽耳目、杜言路”,以致“小民之疾苦何由得知,臣工之贤愚从何考察!”[5](212)
四、以沽直名?皇权祭品!——洪亮吉上书事件再分析
广开言路之本质,在于将信息渠道掌控于手并借此体察民情、驾驭百官、调控帝国。是以皇帝对于此有威胁之事严厉惩处,同时又审慎地维护信息之机密。从广开言路、禁抄附稿到道员密奏、条陈封口,再到不许私自拆阅、毋得捺搁擅撤,相继实施此措施的目的正在于确保信息的机密。从各宜凛遵、致干重咎到重治其罪、绝不姑贷的严厉措辞,自兼听并观、集思广益至杜壅蔽而昭慎密的循循善诱,则反映皇帝对信息渠道的重视和期望。但反观洪亮吉上书一事,不仅露章陈奏,而且还一式三份分别委托成亲王、朱珪、刘权之代投。尽管其条奏言辞恳切,所言之事切中时弊,却始终与嘉庆帝所强调的信息机密大相径庭。是以,嘉庆对洪亮吉上书事件中相关人员的斥责与定罪亦绕此展开。
依照先前所发上谕,嘉庆帝准允代呈者可以先行阅看露章陈奏,但阅后应将原封进呈,而不得捺搁擅撤。对于洪亮吉请求代为呈递的奏章,虽然朱珪、刘权之有权拆阅,但阅后应“即时进呈”,而二人却在“奉旨查询”后“始行交出”。嘉庆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朱珪、刘权之上请罪折,以未将洪亮吉投递原书进呈为由自请交部严加议处。尽管皇帝以“朱珪平日人品端正”,“刘权之节次陈奏之事尚能切实敷陈”为由,将严加议处改为“交都察院、吏部议处”,但二人的做法却完全无视皇帝的煌煌圣谕以及对信息机密的强调。[5](304)是以,与其说降三级留任[26](637)的处罚指向二人对洪亮吉的“意存回护”,还不若说是对二人触犯信息机密的惩处与警示。
八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洪亮吉后呈奏,除却对其所言逐条批斥外,还对洪亮吉的上奏方式严加谴责。在成亲王等人看来,作为翰林的洪亮吉即便想陈奏时事,亦当于“圣主广开言路之时”自具封章并“转交该管衙门代进”。而洪亮吉却将“关涉皇上起居政治”的“毫无影响之谈妄写书札”并各处投递,其“居心更不可问”。洪亮吉“无礼于君者,罪在不赦。况敢肆其诽谤,实属丧心病狂、无复人理”[5](306−307)。 如果说成亲王等人的呈奏尚有揣测上意之嫌,那么八月二十七日的上谕则代表了皇帝对洪亮吉上书一事的明确态度。广开言路之目的,便是希望内外臣工“各抒所见、指陈利弊”。即便洪亮吉“所陈系毫无影响之事”,亦“可随时披阅,藉以为始勤终怠之儆”。所以,若“洪亮吉以此等语言手疏陈奏,即荒诞有甚于此者”,皇帝亦不会“加之罪责,更当加以自省,引为良规”。[5](308−309)质而言之,如果洪亮吉以封章陈奏,即便内容再荒诞不经,亦不会令皇帝动怒,反而以此作为警戒。
相较将不经之言“留以备览”彰显的宽容,上谕对其上书方式则严厉斥责。在嘉庆看来,如果身系编修且曾在上书房行走的洪亮吉条奏事件,“原可自具封章”直达御前,或“交掌院及伊素识之大臣代奏”。但洪亮吉却“以无稽之言向各处投札,是诚何心”?其于同日向伊犁将军保宁所发寄信谕旨中再次重申各处投递的别有用心:“条陈不于该管衙门处封求代进,乃率意书写,各处呈送,居心殊不可问。”[5](309−310)出于改变“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现状的考虑,皇帝于嘉庆五年闰四月初三日所颁谕旨中称洪亮吉所论“实无违碍之句,仍有爱君之诚”,但对其上书方式却仍存不满。认为洪亮吉就欲言之事“不自具折陈奏,转向成亲王及尚书朱珪、刘权之私宅呈送,原属违例妄为”,难逃“违例奔竞取巧营求之咎”,在释放回籍的同时仍令江苏巡抚留心查看,不准出
境。[9](196)
无论是用“不值与之辩论”暗示洪亮吉的指摘确无其事,还是用“欲拼伊一身,触怒朕前”映射洪亮吉“以沽直名”,甚或以“引为良规,藉以修省”彰显虚心纳谏之风,无不凸显皇帝盛怒的原因不在于所奏内容,而在于将无稽之言“各处呈送”的别有用心。尤其是惩处洪亮吉时所言的“居心殊不可问”,以及释放谕旨时所称的“违例妄为”和“违例奔竞取巧营求之咎”,均表明皇帝一直强调的始终是洪亮吉言事违例以及各处投递的别有用心。皇帝对洪亮吉的惩处与释放,则表明其“试图向官员们示范应如何上言”[27]以及对信息控制机密及排他的重视。
五、余论
“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28],皇帝与官僚体系之间掌控信息多的一方,便在行政过程中占据较有利地位。嘉庆帝激活广开言路这一政治信息渠道,其真实目的便是凭借掌控的信息实现对帝国动态的洞悉,因而必然会对信息来源渠道以及信息的机密多加重视。嘉庆于处罚洪亮吉次日对作为“启示”和“补救”[29]工具的京控制度作出重大调整⑧,便是其进一步“明目达聪”“下情上达”的信息控制手段。随着京控“补救”功效的日渐明显,皇帝便对广开言路的方式再次作出限制,于十一月初五日谕令“不应奏事之人,不得妄行封奏”,否则按例治罪。[5](438−439)
纵观嘉庆四年三月下旨求言到八月的洪亮吉上书事件,我们便会发现皇帝一直将广开言路所要达致的“下情上达”为目标。从诛杀和珅到禁止抄送折稿,自进言封口至赋予道员密奏之权,甚或开禁京控以及对不应奏事之人的限制,无不彰显嘉庆对信息渠道的维护和控制,亦无不表露其对信息的重视与专享。因此,皇帝对妄言渎奏的包容有加、对洪亮吉上书内容的迥异评价以及上书违例的不断强调,均是“守成型君主”嘉庆“消除妨碍封建政权正常运行的一些弊政”[30]的手段或方式。
注释:
① 参见:关文发的“评嘉庆帝”,《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张玉芬的“嘉庆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4期;魏克威的“嘉庆时期的内政改革和失败”,《长春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魏克威的“论嘉庆为政之失”,《长春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② 参见:关文发的《嘉庆帝》,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51页;陈金陵的《洪亮吉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5年版,第209—220页;关文发的“试评嘉庆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陈辽的“‘世界第一’的中国之主——论嘉庆帝”,《南通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③ 参见:周轩的“〈大清律例〉与清代新疆流人”,《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
④ 参见:Susan Mann Jones’ Hung Liang-chi (1746—1809): The Perception and Articulation of Political Problems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Ph. 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2:162, 165,170;A·W·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4−337页;张国骥的“论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制度性腐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3期;刘源的“戍发伊犁白日还——洪亮吉上书案”,《紫禁城》2011年第4期;崔岷的《洗冤与治吏——嘉庆皇帝与山东京控》,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3页。
⑤ 将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的言论,经董仲舒等人阐发后日益为统治者所重视。及至清朝,帝王更是将清狱恤刑视作感召休祥的“第一要务”。此方面的著述可见卫周安的《清代中期法律文化中的政治和超自然现象》,高道蕴等的《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康沛竹的《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赵晓华的“清代的因灾恤刑制度”,《学术研究》2006年第10期。
⑥ 嘉庆帝曾慨言:“和珅任事日久,专擅蒙蔽,以致下情不能上达。若不立除元恶,无以肃清庶政、整饬官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四册,第33页;罗威廉的“引言:乾嘉变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 William T. Rowe. 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in Qing History),《帝制晚期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2011年32卷第2期。
⑦ 关于军机处在清朝行政体制中的作用以及嘉庆对军机处的整顿,参见刘绍春的“嘉庆整顿军机处维护双轨辅政体制”,《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高翔的“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⑧ 嘉庆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皇帝谕令:“嗣后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遇有各省呈控之案俱不准驳斥,其案情较重者自应即行具奏,即有应咨回本省审办之案,亦应于一月或两月视控案之多寡汇奏一次,并将各案情节于折内分晰注明,候朕披阅。倘有案情较重不即具奏,仅咨回本省办理者,经朕看出,必将各堂官交部严加议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朝上谕档》,第四册,第310−311页。
[1] William T. Rowe. 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in Qing History [J]. Late Imperial China, 2011, 32(2): 74−88.
[2] 张玉芬. 嘉庆述评[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86(4): 64−71.
[3]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4] 昭梿. 啸亭杂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350.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嘉庆朝上谕档·第四册[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6] 清史列传[M]. 王钟翰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7] 林逸. 清洪北江先生亮吉年谱[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1.
[8] 洪亮吉. 洪亮吉集·第四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1082.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嘉庆朝上谕档·第五册[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0] 陈康祺. 朗潜纪闻二笔[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494.
[11] 徐珂. 清稗类钞[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501.
[12] 陈金陵. 洪亮吉评传[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260.
[13] 关文发. 试评嘉庆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1): 110−117.
[14] 道格拉斯·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陈郁,罗华平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34.
[15] 王成兰. 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J]. 清史研究, 2002(2): 58−67.
[16] 屈永华. 中国传统官僚制度的效率之争——从《荒政》和《叫魂》说起[J]. 政法论坛, 2010, 28(5): 115−123.
[17] 刘文鹏. 清代科道“风闻奏事”权力的弱化及其政治影响[J].中州学刊, 2011(4): 180−187.
[18] 张世明, 冯永明.“包世臣正义”的成本: 晚清发审局的法律经济学考察[J]. 清史研究, 2009(4): 1−34.
[19] 高翔. 也论军机处、内阁和专制皇权——对传统说法之质疑,兼析奏折制之源起[J]. 清史研究, 1996(2): 20−29.
[20] 李鹏年. 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1989: 16.
[21] 刘子杨. 清代的军机处[J]. 历史档案, 1981(2): 99−104.
[22] 吴晗.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4881.
[23] 胡鸿廷. 清代官制研究[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9: 25.
[2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摺汇编·第五册[M].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363−364.
[25] 昆冈.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76: 17091.
[26] 嘉庆朝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7] 崔岷. 洗冤与治吏——嘉庆皇帝与山东京控[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 21.
[28] 孔飞力. 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 陈兼, 刘昶译.上海: 三联书店, 2012: 157.
[29] 欧中坦. 千方百计上京城: 清朝的京控[C]// 高道蕴. 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477.
[30] 朱诚如. 嘉庆亲政后中央权力的重组[C]// 朱诚如, 王天有.明清论丛·第三辑.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2: 266.
Encouraging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throne of Hong Liangji in Jiaqing Dynasty
CHANG Bingxia, FENG Yongming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Management College, Th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010051, China)
In order to break the deafness of the emperor and the sluggishness of the officials which resulted from Heshen’s autocracy, the Emperor Jiaqing encouraged the free airing of views after executing Heshen. The purpose of this measure was to control information and regulate imperial trends through this political information channel.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nfidentiality and exclusiveness of this channel, Jiaqing took measures such as the forbidden copy of the memorial to the throne, secret memorial of circuit intendant, sealed memorial and so on. Therefore, when Hong Liangji gave the unsealed memorials to Yongxing, Zhugui, Liu Quanzhi and asked them to transmit the information to Jiaqing on his behalf, he eventually violated the principle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suffered punishment. By analyzing the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control, we can find that the Emperor’s different attitudes result not from the general outbreak of false statements, but the punishment to Hong Liangji for his “violation of memorial to the throne.”
encouraging freedom of speech; information control; the throne of Hong Liangji; the violation of memorial to the throne
K249.305
A
1672-3104(2015)04−0225−07
[编辑: 颜关明]
2014−06−30;
2015−06−20
常冰霞(1981−),女,山东聊城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清代法制史,清代政治史;冯永明(1983−),男,山东青州人,历史学博士,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清代法制史,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