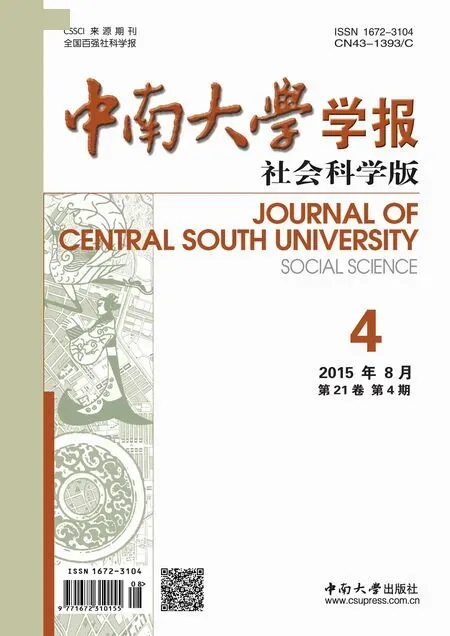狂欢与规训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余秀华诗歌现象”
2015-01-21陈守湖
陈守湖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狂欢与规训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余秀华诗歌现象”
陈守湖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在微信朋友圈中意外走红的余秀华诗歌,告别了自足自为的私性书写,进入到众声喧哗的大众文化场域。在这个杂合着消费法则、话语权力、身份符码的场域里,上演了一场网络社群的诗学狂欢,进而获得了主流媒体和出版机构的关注。从自为到共谋,从沉默到喧嚣,从抵抗到融合,余秀华诗歌的民间立场和草根书写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与规训。
民间诗人;大众文化;狂欢;规训
2014年末,生活于湖北钟祥乡村的普通农妇余秀华,因诗歌在微信朋友圈意外走红,进而演化为一起大众文化事件。从自媒体到他媒体,从新兴媒体到传统媒体,加之网络社群的群情共举,使得余秀华诗歌的传播成了一种充满仪式感的行动。于乡村寂寞书写想象中的爱情、艰难中的企望、荒芜中的温度,把生命痛感凝结为诗意,把寻常岁月流动为歌吟的女诗人,就这样走到了大众文化的中心地带。一个不幸承受脑瘫疾患的女诗人,在大众传媒的共谋下迅速成为“媒体红人”。从惊慌失措,到坦然接受、从容应对,余秀华及其诗歌被融入并收编在大众传媒的符号矩阵之中,成就了独特的文化消费现象。在众多命名与标榜的背后,“农妇诗人”“脑瘫诗人”“中国狄金森”“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等标签,无疑是传媒话语在零乱的诗性符码中着力涂抹的可视性的新奇图景,它唤起了更多受众的群观,亦成功地引来了主流媒体、文化精英、权威出版社的关注。于是,“民间的”“草根的”“通俗的”,也拥有了向主流的、精英的、高雅的贴近的可能性。最终,两本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月光落在左手上》的策划、预售、出版与热销①,为这次大众文化的群体性狂欢总结收官。然而,在这起大众文化事件的背后,“余秀华”与“余秀华诗歌”渐行渐远,基于诗意抒写的自我告白,进入到众声喧哗的大众文化场域。在这个杂合着消费法则、话语权力、身份符码的场域里,上演了一场网络社群的诗学狂欢。“余秀华诗歌”成了不折不扣的大众文化现象。和西方视野中“大众文化”所承载的抵抗话语意蕴略有不同的是,中国语境中的“大众文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基于文化享乐的消费旨趣。在传媒全面介入日常生活的当代中国,传媒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使传媒文化的市场意识和商品属性日趋彰显。“激发受众的消费欲望便成为传媒改造和发展现代文化的动因。”[1]由此,大众文化体现出强烈的“传媒拜物教”色彩。“它以其自身的逻辑设定商品(记号、符号)生产的扩张与延伸,为大众提供快感的满足、欲望的佐餐,使商品具备了一种审美的符号。”[2]在“传媒拜物教”的逻辑主导下,余秀华诗歌自然而然地被抽象为彻底的“形象”和“符号”,并诉诸于大众文化的永恒属性——商品和消费。将余秀华诗歌现象置于大众文化视域之下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从自为到共谋,从沉默到喧嚣,从抵抗到融合,在大众传媒的生产链条上,余秀华诗歌实际上已被重构为能指漂移、符码狂欢、意义规训的大众文化景观。
一、从自为到共谋——能指的漂移
余秀华诗歌走红是一次偶然,但她写诗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她已经默默写了十六年。除了极少数的诗歌投机者,写诗从来都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即使屡屡有诗人制造诗歌的“身体事件”,也不能抹去诗人群体的总体寂寞。“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这既是调侃,也是实情。
诗人回到世俗生活,是“艺术自律”神话消失的结果。西方语境中的审美现代性,基础就是建立在自律艺术之上的。启蒙现代性为世俗生活实现了合法化论证,摧毁了宗教神权和贵族血统论,张扬了理性之光。而理性之光在照亮人类文明的同时,亦使人类生存面临渐趋异化、意义荒芜的危险。正是在这种困境之中,艺术地位被空前抬升。在市民社会中不再依附于贵族豢养而实现独立的艺术,在审美救世的乌托邦建构中走到了云端。它和世俗生活格格不入。在审美无功利论一统江湖的审美主义看来,正是工具理性和世俗生活遮蔽了意义。艺术不是来亲近日常生活的,它是来拯救深陷其中的芸芸众生的。“几个趣味相投的艺术家、爱好者和辩护人自称一个小圈子,遵循彼此熟悉的行业术语”[3]。在审美救世的神话中,自律艺术在自己的天地里为所欲为,最终这种造反精神终结了艺术自己。当然,“终结的不是艺术本身,终结的只是艺术史的叙事模式”[4]。艺术自律终结之后的典型文化症候,就是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在审美救世的宏大叙事中自我赋权的自律艺术,由此被大众文化拆解而分崩离析。诗歌与诗人地位的跌落,正是审美从精英主义走向大众文化的必然。
中国尽管没有和西方对应的现代性进程,但近现代以来的文明融合,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现代性在中国体现出复杂的构成。一方面,既有社会现代性的高歌猛进,另一方面,亦有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同时还有着与西方工业社会同质的大众文化。文化上亦体现为前现代(一部分地区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文化模式)、现代、后现代相混合的“中国特色”。这种混合现代性体现到中国当代艺术中,就是自律性艺术与日常生活艺术的并行不悖。
新诗这种舶来的文学样式本来就是中国现代性工程的一部分。以1916年胡适发表在《新青年》那首《两只蝴蝶》算起,中国新诗走过了启蒙话语、革命他律、审美自足等起起落落的百年“诗史”。在大众文化势不可挡的当下中国,诗歌与诗人以何种形象存在?显然,总体上还是以审美自足的形象出现的。写诗在功利的文化氛围中,往往被视为“无用”的技艺。诗歌仿佛成了自我指涉的话语。彻底的边缘化反倒使诗歌精神弥足珍贵。告别了宏大叙事,亦无关世俗功能,诗歌变得更加纯粹了。“许多诗人没有中断对梦想的追寻,没有熄灭自己对生活的热情,仍旧相信伟大的生活将继续滋养诗人的灵魂。”[5](19)网络诗歌的红火,尽管褒贬不一,但其美学意义是值得标举的。其中蕴藏的自由意识、审美想象、文化民主亦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余秀华正是这个为“诗”而“诗”的群体中的一员。据媒体报道,她的第一首诗写在1998年。[6]与不少网络诗人“反诗歌”的标新立异相比,余秀华的绝大多数诗歌是着力于提炼生命体验的。这是一种纯诗的美学追求,而不是一种身体游戏。“他听不清楚一个脑瘫人口齿不清的表白/那么多人经过春天,那么多花在打开/他猜不出我在说什么/但是,每个春天我都会唱歌/歌声在风里摇曳的样子,忧伤又甜蜜”(《每个春天,我都会歌唱》)[7](82),这样的诗句里,有坚毅的人生态度表达,有温暖的情感梦想追求,打动在现实生活中忙碌打拼而无心观照自我心灵的读者,是自然而然的。
余秀华诗歌的走红,是对传统媒介与精英写作群体的反讽。尽管余秀华的几首诗歌也曾在贵为中国诗歌第一刊的《诗刊》发表,但并没有引来专业诗评家与诗歌爱好者的广泛关注。而当她的诗歌出现在诗刊社微信公众号后,余秀华诗歌的影响获得了核爆般的提升。阅读量短短几天达到了5万。而另一家诗歌微信公众号“读首诗再睡觉”,推送了余秀华诗歌《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阅读量超过了7万。微信朋友圈、微博、网站、博客,网络媒体开始疯转余秀华的诗。也正是在网络等新兴媒介的推动下,余秀华和她的诗歌渐渐成为一种现象。诗刊社联合凤凰读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余秀华等5名草根诗人举办了“日常生活、惊心动魄”的诗歌朗诵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官方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亦专程到湖北钟祥采访了余秀华。并于2014年12月22发表了报道《诗里诗外余秀华》。2015年1月13日,诗人、学者沈睿的评论《什么是诗歌?余秀华:这让我彻夜不眠的诗人》(后被某网友在转发时改为《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再度引发转发热。在网络疯转、“余”热不散的情形下,湖南文艺出版社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与余秀华签订出版合同,推出了创造诗集销售神话的《摇摇晃晃的人间》与《月光落在左手上》。②
从一个人的寂寞书写到媒体、粉丝、专家、出版商的共同参与,看起来余秀华诗歌的意义得到了多维呈现,但“余秀华诗歌”与“余秀华诗歌”指向的对象之间的意义映射,却在“能指的漂移”中愈加模糊。基于余秀华及其私性书写的诗歌文本,越来越偏离诗歌本身而成为意义繁复的大众文化景观,使“能指”与“所指”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空洞。这一切的发生,均来自大众传媒的魅惑:“媒介技术推动着多元化的符号能指的制造。它使符号能指与其直接意指的所指之间的联系被粉碎。”[8]对余秀华诗歌现象的关注,我们更多地看到现象的生成与复制,却绝少看到诗学意义上的深度探究。大多数诗评家保持沉默,即有能指漂移不定的因素在其中。而这恰恰是余秀华诗歌现象中最不该缺席的能指。青年诗人、学者杨庆祥就指出,余秀华诗歌的美学价值在于“真”,她的诗歌是对依赖景观与符号建构起来的流行美学的挑战。而各方共谋之后的“余秀华诗歌”已经开始变形。“那份真——独自面对命运并和命运死磕到底的真,还会在诗歌中蓄积起来并成为一种有力量的写作吗?所有的人都没有耐心来进行足够的等待,而真正的诗歌和真正的命运恰好需要这种忍耐。”[9]
二、从沉默到喧嚣——符码的狂欢
诗歌是寂寞的写作,诗人是寂寞的歌者。诗歌的真正魅力不在于广场狂欢,诗人世界也不是喧闹的市场。这并不是说诗人要与现实生活相隔离,而是诗歌写作的确需要耐得住寂寞。余秀华说:“于我而言,只有在写诗歌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10]这是自足自为的创作境界。当余秀华的诗通过微信进入到网络这个虚拟世界,她与她的诗歌,就像从内河游到大海的鱼,面对的是网络海洋的纵情喧嚣。而这种喧嚣来自于因趣味而聚合的网络社群的共同参与。正是网络社群的存在,使余秀华诗歌的大众文化色彩不断加码。
Web2.0时代的到来使互联网发生了巨变。 “它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制者集中控制主导的互联网体系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由广大用户群体智慧和力量主导的互联网体系。”[11]在电脑科学家西巴·帕克特看来,社群创建是互联网的重要价值所在。而且这种价值是随着互联网人数的增长而呈指数级上升的。[12]传统的网络社群是一种松散结构。自媒体使网络交往日趋圈子化。而正是网络社群的圈子化,让虚拟社群具有了一定的实体意义。人类学意义上的社群,是基于排他性而构建起来的。实体的社群,往往由血缘、地缘、语言、文化等要素来设定“边界”。同样,网络虚拟意义上的社群,亦有自己的“边界”。这个“边界”由共同趣味来设定。共同趣味使网民分化为无计其数的社群。它以交流方式上的民主性解构了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科层化”。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缘关系由此确立。“在这种网缘关系中,双方以获取信息和情感交流为目的,以心理认同和兴趣一致为粘合剂。”[13]余秀华诗歌之所以能迅速在网络传播,就在于存在着以诗歌为“粘合剂”的网络社群。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我们的媒介是我们的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内容。”[14]网络社群诗学狂欢不仅仅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且在深层结构上重置了传统审美意义和形态。这种质性的改变与媒介关系密切。要想在互联网信息的海洋里脱颖而出,就必须强化带有普泛性的大众身份,而且表达出网络社群的共同趣味,才有可能获得更大范围的关注。为了提升信息的魅惑度,“简化”与“塑型”就成为关键工序。对于“余秀华诗歌”予以标签化的符码处理,亦势在必然。
“中国的狄金森”③出自于学者沈睿。她在评论余秀华诗歌时说:“我觉得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她的诗歌是语言的流星雨,灿烂得让你目瞪口呆,感情的深度打中你,让你的心疼痛。”[15]“中国的狄金森”这一称号出来后,有人认为余秀华的诗和狄金森并不怎么像。也有人说余秀华诗写得是不错,但也别急着扣上“中国狄金森”的帽子。[16]媒体采访余秀华时,她说她根本就不知道艾米莉·狄金森。[17]但在这场弥漫网络的大众文化狂欢中,余秀华像不像狄金森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余秀华从此有了这样一个洋标签。这无疑具有很强的大众文化传播效应。在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的腰封上,赫然印着“余秀华,她是一位纯粹的诗人,被誉为‘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而在此后的诗集销售推广中,这个标签对媒体极具眼球效应。[18]
诗刊社微信公众号2014年11月10日以《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者的诗》为题推送余秀华诗歌,显然有悖良善伦理。尽管这条微信让一些人反感,但“脑瘫患者”和“诗人”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强烈冲突,还是让这一符号化的推送获得了成功。余秀华的诗歌无疑有自己的特点,她也有诗人的才华和秉赋,但并不能否认这个标签所带来的“附加值”。诗人欧阳斌直言余秀华的诗有模仿海子的痕迹,“只是大家把她的脑瘫因素考虑进去之后,有点神化了。其实在国内能写到她这个水平的诗人,是有很多的。”[19]诗人左右亦认为,余秀华和她的诗歌之所以被《诗刊》发现、推介并被媒体热炒,“身体的特殊”是一个重要因素。[20]
还有一个更为体现网络时代大众文化传播特点的标签就是——《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首诗在余秀华的诗歌里,其实算是较为平常的一首。较之《我养的狗,叫小巫》《我爱你》《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世界》要逊色得多。但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党”式的标签,却带动了余秀华诗歌的走红。时至今日,许多网友最熟知的余秀华诗歌依然是《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 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21],赤裸欲望,不加遮掩,狂放甚至略显粗鄙的诗句,以及这首诗中杂合的“肉体”“流民”“花朵”“春天”“故乡”等纷纭的意象,显然是对张扬身体伦理、挑战权威话语、沉溺泛政治想象的大众传媒文化的响应。正如诗人韩东所言:“媒体关注的诗歌从来不是因为诗歌本身,而是从其他兴奋点上捕捉的。”[20]
电子媒介构筑起来的赛博空间和现实若即若离。“它的非官方、非权力和反贵族化充分显示着民间的姿态和立场;无所拘囿的自由和颠覆理性权威、蔑视等级秩序、追逐感性欲望,又使得这一空间成为一个众声喧嚣的狂欢节广场。”[22]但这种基于媒介技术而实现的话语狂欢,在带来大众文化民主性的同时,也有着致命的硬伤——文化的媒介化。媒介化的一个显性的后果就是意义被符码拆卸与重装。在这个符码重构的世界里,“流动的是媒介化的信息,并不是主体的直接在场”[23](247)。具体到“余秀华诗歌”这一大众文化现象,传播甚至成为了网络社群的“共同仪式”。读不读余秀华的诗,余秀华的诗写得好不好,都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在于一种非理性的对网络热点的追逐,并通过转发这样的仪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依靠共同文化气质的粘合,网络社群在余秀华诗歌的文本内外实现了审美共感,维系了余秀华诗歌在大众文化场域中生产、传播、消费的链条。从而赋予了余秀华诗歌溢出文本的复杂意蕴。一方面,在欲望伦理和消费主义充斥的大众文化时代,诗歌之于心灵的安顿价值得以彰显。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诗歌传统的国度,就中国人的文化心灵塑造而言,诗歌往往有着类似宗教的作用,“它所强调的是,世界除了我们所看见的那些,它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关乎理想、意义,关乎人的秘密和精神出路”[5](3)。余秀华诗歌之所以受到追捧,与“诗学基因”的激活以及“诗学氛围”的复苏不无关联;另一方面,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生产和传播机制,使诗歌价值快速流布的同时亦不断消解。因为,“大众文化是一种表意的、模糊的、非语境化的、反映情感体验的文化形式。它不是作者中心主义的表现,并不反映作者的主体性”[24]。在这个意义上,众声喧哗的诗学狂欢,在播撒余秀华诗歌精神意旨的同时,亦使其迅速凝结为大众文化符号并向消费价值转化。
三、从抵抗到融合——意义的规训
余秀华诗歌写作的真正意义在于她的诗歌中对于沉重肉身、人生命运和宏大叙事的抵抗。身患残疾,偏居乡野,生存境况也不理想,但因为内心诗意的丰盈,使余秀华诗歌显示出独特的抵抗诗学价值。读她的诗,我们能体会到身体残疾的余秀华强大的内心力量。她以诗性追求抗击着命运困境。就像她在开博客之后的感言中所说的:“我的博客我的地盘,以后我写自己的真心。这就是小人物的自由,像一只小屁虫,想横着趴就横着趴,想竖着就竖着。也可以像一棵狗尾巴草,向左歪可以,向右歪也可以。”[25]正是小人物与大时代之间的巨大隔膜,使余秀华诗歌的存在有大意义。
她抵抗残疾的身体——“当我注意到我身体的时候,它已经老了,无力回天了/许多部位交换着疼:胃,胳膊,腿,手指//我怀疑我在这个世界作恶多端/对开过的花朵恶语相向。我怀疑我钟情于黑夜/轻视了清晨//还好,一些疼痛是可以省略的:被遗弃,被孤独/被长久的荒凉收留//这些,我羞于启齿:我真对他们/爱得不够”(《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7](101)。
她抵抗不堪的婚姻——“他喝醉了酒,他说在北京有一个女人/比我好看。没有活路的时候,他们就去跳舞/他喜欢跳舞的女人/喜欢看她们的屁股摇来摇去/他说,她们会叫床,声音好听。不像我一声不吭/还总是蒙着脸//我一声不吭地吃饭/喊“小巫,小巫”把一些肉块丢给它/它摇着尾巴,快乐地叫着//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我养的狗,叫小巫》)[7](4−5)。
她抵抗荒芜的爱情——“只有我这个不争气的女人,把人间的好都安放在你身上/还想去偷去抢//仿佛世间的美只配你享用/玫瑰不够,果园不够,流水和云不够/春天是不够的/你猜我在偷窥的路上会不会失足//哦,天哪,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不要说出来/哦,如果我真的失踪了/你要常翻翻自己的身体:多出的一块疤痕/会不会无关紧要地疼”(《美好之事》)[7](198−199)。
加缪曾说:“我们作品的高贵处,永远是根植在两项十分难于遵守的誓约中:对于我们明知之事绝不说谎,并且奋力去抵抗压迫。”[26]抵抗在余秀华诗歌中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姿态。正是这种抵抗平庸的力量,使得她的诗歌以小人物的平民化情调与苦涩的生活本色超越了精英主义的宏大论调。与此同时,她的诗歌浸满汗渍、泪水与体味,鲜明地区别于其他的书写者,因为“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27]。这种生活的痛感,显然只有在“抵抗”的姿态中才能感受得到。换一个对于生活世界百依百顺的诗人来写那个小小的横店村,很有可能就是“炊烟”“稻子”“母亲”“大地”等大而无当的意象中弥漫的所谓乡愁了。余秀华诗歌的抵抗诗学价值,来自于她本人的身体和人生困境,但更重要的是她自己对诗歌的独特理解。在余秀华的世界里,诗歌“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7](223)。
进入公众视野并被大众文化裹挟的余秀华,其写诗心境和在寂寞中的“抵抗写作”显然迥异。哪怕余秀华依然想坚持初衷,实际上已经回不到她那个“横店村”了。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训功能。余秀华自足自为的诗歌写作,与经历了大众文化产品流程再造之后的诗歌写作,注定不可能是一回事。大众文化所追求的商品化、媒介化、符码化,对于纳入其中的文化产品来说,都有着潜移默化的意义规训作用。如果说余秀华诗歌在创作场域中体现为赋魅,那么在大众文化这个消费场域中则是祛魅。藏身于诗歌背后的余秀华走到了大众文化生产机制中,朗诵自己的诗歌,奔忙于读者座谈会,在书店签售,一轮又一轮地接受媒体采访……她自己也成为这个链条中的一环,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在无数次地被贴上标签“营销”之后,余秀华和她的诗歌已经告别当初那个饱满着肉身欲望、充斥着命运抗争、驳杂着世象人心的“情境性”的场域,成为了“脱域”的抽象化、概念化、符号化的大众文化产品。而且完全可以想见,只要诗集还要再版,这样的概念还会不断强化。余秀华诗歌的意义被重置与拆解是自然而然的。大众文化的强大规训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野蛮生长的博客写作进入到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甄别和评价意味的出版制度中来,无疑要经受另外意义上的规训。在诗集出版前,余秀华写了2 000多首诗。什么样的诗进入到公开出版的诗集中来?显然不是率性而为的,而是有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考量的。这包括文化经济和文化政治两个层面。在大众文化时代,诗歌成为消费宠儿的概率极小。意外地成为大众文化事件的余秀华诗歌,如何最大程度地制造影响,为大众文化产品生产的各方带来利润(不一定是经济意义上的),是一个首要考虑的原则。消费余秀华也就成为必然。选择哪些诗出版,显然不是余秀华个人所能完全自主的,而是基于市场考虑的各方共谋。即使出版社给了余秀华亲自选诗的权利,市场接受的法则依然会起作用。毕竟,诗集出版之后不是作为纪念品放在家中自娱,而是要进入市场接受读者挑剔的。更何况,出版社早就在舆论上吊足了余秀华诗歌追逐者的胃口。早早地在当当、亚马逊等网站开展诗集预订了。出版本来就是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训化色彩的文化制度。两本诗集出版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首余秀华的“名作”并未入选。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将沈睿的评论改名为《余秀华:让我疼痛的诗歌》作为代序,其中亦删去了沈文中曾经引述并评论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不管是出版方还是余秀华作出不入选的决定,文化政治的意识形态思虑都是必然的。在诗集出版和营销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规训机制无疑会对余秀华今后的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对于出版方来说,依然希望余秀华诗歌获得大众文化市场的持续接纳。对于余秀华来说,今后能再出诗集并且能受到读者关注也是再自然不过的愿望。自足写作的余秀华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已经消失。
“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视为一个不断地从整合状态向分化状态的转变,那么,出现了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23](357)“余秀华诗歌现象”呈现的正是这样的复杂文化景观——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主导文化一炉而冶。一方面,自律艺术依然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否则,诗歌就没有可能成为文化热点。余秀华诗歌意义的公众认同,其实和它具有的对技术化、工业化、世俗化所带来的现代性隐忧的批判价值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高扬消费主义和欲望伦理的大众文化漫溢于当下中国。这使得余秀华诗歌被迅速地整合为大众文化商品,并不遗余力地予以营销。此外,主导文化在大众文化的意义链条中始终保持着潜在的均和与监控功能。这种复杂的文化生成机制,在造就大众文化狂欢的同时,亦伴生着特殊的规训机制,对于意义的重构或消解也就在所难免。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典型症候。
注释:
① 据《西安晚报》2015年2月4日报道:《摇摇晃晃的人间》首印15 000册发往全国,一天即被抢光。出版方称后续至少还要加印10 000册才能保证诗集的供应;据《楚天金报》2015年4月5日报道:《月光落在左手上》两个月内销量超过10万册,是在世的诗人中卖得最好的。
② 参见诗刊社微信公众号(shikan1957)、湖南文艺出版社微信公众号(hnwy201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微信公众号(lixiangguo2013)相关内容。
③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是19世纪美国女诗人,其诗歌生前认同度并不高。进入20世纪后,狄金森在20世纪初的英美诗坛受到了广泛关注。现代派诗人将狄金森视为现代派诗歌的先驱,意象派诗人更将她尊为意象派诗歌鼻祖。参见周建新:《21世纪中国艾米莉·狄金森热的背后》,《当代文坛》2013年第4期,第115页。
[1] 蒋建国. 消费主义时代的大众传媒和物欲症传播[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1): 103.
[2] 范玉刚. “大众”概念的流动性与大众文化语义的悖论性[J].人文杂志, 2011(1): 112.
[3] 伊凡·休伊特. 修补裂痕: 音乐的现代性危机及后现代状况[M]. 孙红杰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8.
[4] 吴剑峰. 试论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当代艺术转向[J]. 浙江社会科学, 2014(11): 128.
[5] 谢有顺. 文学的常道[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6] 程远州, 王锦涛. 诗里诗外余秀华[N]. 人民日报, 2014-12-22(14)。
[7] 余秀华. 月光落在左手上[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8] 隋岩, 姜楠. “能指狂欢”的三种途径——论能指的丰富性在意义传播中的作用[J]. 编辑之友, 2014(3): 58.
[9] 杨庆祥. 余秀华: 独自面对命运[N]. 北京青年报, 2015-1-20(B01).
[10] 余秀华. 摇摇晃晃的人间[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 2.
[11] 黄晓斌, 周珍妮. web2.0环境下群体智慧的实现问题[J]. 图书情报知识, 2011(6): 113.
[12] 胡泳. 网络社群的崛起[J]. 南风窗, 2009(22): 38.
[13] 张文宏. 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影响[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1(4): 70.
[14]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 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09.
[15] 沈睿. 余秀华: 让我疼痛的诗歌(代序)[C]// 余秀华. 月光落在左手上.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v.
[16] 徐萧. “中国狄金森”?余秀华不缺这帽子[N]. 东方早报, 2015-1-17(A16).
[17] 杨超, 高一点. 余秀华: 我的灵感是天上掉下来的[N].华商晨报, 2015-1-25(A07).
[18] 王烨. “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余秀华深圳“任性”签售[N].南方都市报, 2015-3-23(A07).
[19] 裘晋奕. 脑瘫+农妇+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 贴了这些标签的女诗人余秀华红了[N]. 重庆晨报, 2015-1-25(10).
[20] 叶长文. 众诗人评说余秀华诗歌蹿红事件: 请抛开“脑瘫”来谈论她的诗[N]. 晶报, 2015-1-20(B07).
[21] 余秀华. 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EB/OL]. http://blog.sina. com.cn/s/blog_5fb7c5b80102vf0z.html, 2015-1-13/2015-4-13.
[22] 马大康. 虚拟网络空间的话语狂欢[J]. 浙江社会科学, 2005(4): 149.
[23] 周宪. 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4] 郑祥福. 从认识论视域解读大众文化[J]. 浙江社会科学, 2003(3): 143.
[25] 余秀华. 我的博客[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 61667c450100eu8f.html, 2009-8-11/2015-4-15.
[26] 堵军.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暨演讲文库(第13册)[M].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4: 4210.
[27] 刘年. 多谢了, 多谢余秀华[C]// 余秀华: 摇摇晃晃的人间.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 178.
Revelry and discipline: the phenomenon about YuXiuhua’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ss culture
CHEN Shouhu
(College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YuXiuhua’s poetry, which has become unexpectedly popular through WeChat, symbolizes an end to the self-sufficient private writing as well as an entry into the field of mass culture, which is full of various sounds, consumption law, discourse power and identity code. At the same time, network community has directed carnival poetry which gains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publishers. In some sense, Yu Xiuhua’s poetry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from writing for herself to writing for others, from silence to hubbub and from resistance to fusion, in which the folk standpoint and grass-root writing of her poetry have been obscured and disciplined.
folk poet; mass culture; revelry; discipline
G122
A
1672-3104(2015)04−0203−06
[编辑: 胡兴华]
2015−04−09;
2015−06−25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审美文化产品的评价理论研究”(12AZD010)
陈守湖(1972−),男,贵州天柱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大众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