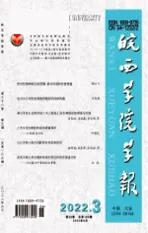地方文献关于清代民国皖西茶叶运销的书写
2015-01-01马育良郭文君
马育良,郭文君
(1.皖西学院,安徽 六安237012;2.河南省农机鉴定站,河南 郑州450008)
清代与民国时期的中国茶叶贸易,与清代以前的中国茶叶贸易有很大不同。此前的元明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虽已处于渐起状态,为清代大规模海外茶叶市场的开拓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一般来说,清代以前,中国“天朝”自居,中国茶主要通过官方渠道输出域外,是中国主动作为。从清初开始,中国茶叶贸易应时易变,逐渐转为域外主动引进中国茶叶,商贸性质日显,中外茶贸规模及所占外贸份额、茶贸份额日巨,从而逐步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
就此而言,清代与民国时期的中国茶叶贸易,又是紧密相连、不容易分割的。
当然,包括皖西茶叶运销在内,清代与民国时期的中国茶贸之路,是波澜起伏而又崎岖坎坷的,这尤其表现在海外运销售方面。
一
2011年版《安徽通史》清代卷(下)称:进入晚清民国后,“六安、霍山一带所产的绿茶,唯一贸易路线是:主要由淠河运至正阳关,下淮河,遇洪泽湖入运河以至镇江。……淠河水运在夏季涨水时百担之船可直通镇江。霍山茶的上品运到苏州,转往营口、东三省;中等的销往国外;其次的则北运至亳州及周家口,再销往华北;较差的茶在附近销售,有的运到口外、蒙古等地。三为鲁庄,采运至山东。同光年间苏庄、口庄茶商极多,营业甚盛。”[1](P697-698)可以认为,这一论述概括了清代民国时期皖西茶叶运销的大体情况,虽然其中具体的运输路线还可以作进一步商榷。
证诸地方史志、碑刻、档案、诗文等历史文献,清代民国时期皖西茶叶运销的史实大略记载如下。
(1)清顺治《霍山县志》卷二《茶考》:每岁采造春茶时,“男妇错杂,歌声满谷,日夜力作不休。校尉、寺僧、富商大贾,骑纵布野,倾橐以值。百货骈集,列市开肆,妖冶招摇,亦山中胜事。”
(2)清嘉庆二十年(1816)《霍山县志》:“土人不辨茶味,唯燕、赵、豫、楚需此日用。每隔岁,经千里挟资裹粮,投牙预质。”
(3)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霍山县志》卷二《地理志下》“物产”:“货之属茶为第一,茶山环境皆有,大抵山高多雾,所产必佳,以其得天地清淑之气,悬岩石罅偶得数株,不待人工培植,尤清馨绝伦,故南乡之雾迷尖、挂龙尖二山左右所产为一邑最,采制既精,价亦倍于各乡。茶商就地收买,倩女工捡提分配花色,装以大篓,运至苏州。苏商薰以珠兰、茉莉,转由内洋至营口,分售东三省一带。近亦有与徽产出外洋者。次则东北乡与西南近城一带,多北运至亳州及周家口,半薰茉莉,转售京都、山西、山东。而西乡自土地岭以西,迤逦而南,茶叶厚,微苦,枝杆粗大,采焙不精,皆青齐茶商于大化坪、五溪河收买,运消(销)山东一路。诸佛庵以北数保,则由土人运潮枝至州境之流波 ,西商收买,自行焙制,运消(销)山西、口外、蒙古等处。极西之九五保,所出极微,味制俱逊,多为鄂人收买。至前志所载诸名目花色:如银针、雀舌,则茶始萌芽者;梅花片、兰花头、松罗春则茶初放叶者;统名之为小茶,价既数倍,采以维艰,故惟近城及柳林河、诸佛庵数处有之,运销京都为多。气候则东南稍暖,谷雨前即可采摘,故有雨前、毛尖之名。西山谷雨后,始能开山,间数日采摘一次,须二旬始毕。故有头道、二道、三道、四道之分。最后,并宿叶而撷薙之,曰翻柯老茶,为民间常用。春茶既毕,五六月复生新苗,谓之子茶。其干扁而味微涩,价亦半减。然爱惜株柯者,恒蓄不采取,次春茶必茂盛。又一种名苦丁茶,虽名为茶,实则木本,枝叶似茶而大,有二种:一叶小上有刺;一叶大而圆,皆天然自生深山岩石间,无子种,与茶同时采制,味苦,其性极凉,可入药,近年茶商多喜购买,山民渐事觅植,极难长成。”[2](P182-186)
(4)清光绪三十一年《霍山县志》卷二《地理志下》“物产”:“《吴志》:土人不辨茶味,唯燕、齐、豫、楚需此日用。每隔岁,经千里挟资而来,投行预质。牙狯负诸贾子母,每刻削茶户以偿之:银则熔改低色,秤则任意轻重,价则随日低昂,且多取样茶。茶户莫能与较。虽迭经告诫,申详各宪,严饬乡保稽查,茶户稍沾实惠,然弊端犹未能尽除也。按茶之为利虽厚,工则最勤苦:日采摘,夜炒焙,恒兼旬不得安枕。人力不足,又须厚雇客工,茶值稍昂,犹可相偿。军兴后,厘捐日益,浮费繁多。商人成本既重,则转而抑减民值。近日行户渐增,竟有汇缘茶商,预计价值把持行市者。黠贩收买,则又搀老叶加水潮,茶商得以借口,故茶价愈趋愈下。光绪以来,每觔(斤)银不过钱余,贱时才七八分,以是民用益绌。近徽郡仿外洋以机器烘焙,制精工省,颇获其利。本邑绅商如能集股设公司,精其制造,则利权操之于我,诸弊不禁自除矣。西人亦云:霍茶香味较胜徽产。”[2](P188-189)
(5)清同治十一年《六安州志》卷之四《风俗》:“商所货、粟、米、竹、木、茶、耳、药草诸物,盐荚则来自淮阳,徽人掌之,土居无与贩者。”[3](P67-68)
(6)清同治十一年《六安州志》卷五十四《艺文·霍山》载陈燕兰《霍山竹枝词(并序)》:“(序)霍为六分邑,僻处万山中。地瘠民贫,近县百里皆产茶。每岁谷雨前采制,贡之内府。山田少宜谷,民惟赖茶以生。自春徂夏,商贾辐辏。……近城百里尽茶山,估客腰缠到此间。新谷新丝权子母,露芽摘尽泪潸潸。”[3](P431)
(7)周始编著《皖志述略》(上):“淠河上游诸水,纵横奔流于县境(按:霍山县)。……淠水长五百里,北流入淮,可以通航,运输土产。‘故埠联帆’,霍山十景之一,有诗咏之:山城转运倚长河,燕晋齐梁岁几过。遥望风旌东北转,住船半拟住家多。”①
(8)1993年版《霍山县志》:“‘苏庄’以苏州籍茶商为主,‘口庄’以周家口籍茶商为主,清同治、光绪时在本县占有重要地位。民国期间,多利用津浦铁路运销山东。故鲁庄日趋繁盛。每逢茶季,山东茶客云集皖西茶区,常达200余人以上,省内邻县和鄂东黄安等处的茶商及小贩性质的‘杂庄’也纷纷来县贩茶。”民国三十年《安徽概览》记述:霍山“运往济南、天津的茶叶,从淠、颍两河和津浦路运输便捷,需费较少。抗战期间,交通断阻,只能由产地用排筏和船运到原墙集,再用牛马车或人力挑运到亳州和商邱,时久费大”[4](P221)。
(9)霍山《茶叶山歌》:“头茶碧绿二茶香,采茶人家昼夜忙。好茶提针长街卖,粗茶留着自家尝。”“霍山有座挂龙尖,中外驰名好茶山。当年黄芽曾进贡,一路推销到济南。”(霍山县项志培采录)[5](P122-123)
(10)清雍正三年(1725)苏埠徽州会馆碑铭:“苏家埠是姜、茶、麻、竹木、瓜果之第,白浒圩、韩摆渡、苏家埠、八里滩等保素为产麻之区,行青岛、营口,通日、俄诸国。”[6](P153)
(11)晚清民初浣月道人《六安竹枝词》:“一山独立号天峰,峰下人家晚更浓。隔岸街衢通楚豫,盛家书馆接重重。”明确提到独山淠河对岸有条通往湖北、河南的古道。晚清民初,流波江伯良与人合作在汉口汉正街682号开设抱云轩茶庄,后易名毓华茶庄。其营销线路或与这条古道有关。《六安竹枝词》又咏道:“流波 上石泉清,雀舌新芽最擅名。江氏祠前风乍过,茶香暗逐粉香生。”道人自注:“治西一百四十里产茶最佳,江氏聚族于此。”[7](P20,53)
(12)民国二十四年(1935)《安徽政务月刊》附《六立霍茶麻销售情况》记载:“六立霍为安徽产茶区域,人人皆知,其所产之茶,多销售东三省及直鲁豫江浙等省。”[5](P167)
(13)1997年版《六安地区志》根据历史资料统计:“民国期间全区茶叶产量,民国8年1 622吨,民国19年4 112吨占全省总产39.2%,其中外销鲁豫2 425.7吨占59%。抗日战争期间,民国27年3 285吨、民国28年4 326吨、民国29年……总产4 477.6吨,其中六安1 722.7吨、立煌1 209吨、霍山1 078.2吨、舒城467.7吨。民国33年总产4 673.4吨,其中春茶占60.4%,子茶占35.5%,老茶占3.1%,片茶占0.9%,茶末0.1%,外销3 738.5吨占总产量80%,其中销山东济南2 525吨,河南周家口、商城605吨,湖北黄安108.5吨,天津500吨。”[8](P115)
(14)周始编著《皖志述略》(上):“《六安州志》:本州商旅贩运之货,有粟米、竹木与茶等,以茶为最著名。”“瓜片,主要运销北方,早先有山东、张家口等地茶商前来贩茶,转销外乡。”[9](P303-304)
(15)1993年版《六安县志》:“据清同治《六安州志》记载,明崇祯年间,六安东关为闹市,闹(按:疑应为‘行’)旅云集,多从北关由淠河运货。民国年间,航行在淠河排筏及山河帮、河南帮、淮河帮的大小船只往返如梭,桅杆林立,多达千艘。山区的竹木、茶麻、药材、扫把等山货,均通过此河运至六安县城、正阳关、淮南、蚌埠等中转运销省内外,返回则装载食盐、煤炭、日杂百货等物资。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政府迁至立煌(现金寨县)后,淠河水运盛极。”②
(16)1992年版《金寨县志》:“西淠河航道。位于本县中部山脉的东侧,流经苏家埠、六安至正阳关入淮河。1958年以前,流波、麻埠等地的大宗茶麻、竹木及其制品,依靠毛排经此航道运往六安、阜阳等地销售,返回时运进食盐、布匹等生活用品,转销县境各地。”[10](P264)
(17)浣月道人《六安竹枝词》:淠水遥通颍水前,櫂歌声歇夕阳天。布帆无恙频来往,半是茶船半米船[7](P62)。
(18)寿春贤达李贻训先生在《正阳关之恋》一文中,如此眷怀自己的故乡:“我的童年时期,正是抗日战争前夕。那时的正阳关,是长淮航运枢纽,皖西的茶麻竹木等特产,都由此运往蚌埠,再由铁路运往各地。每天都有客货轮开往蚌埠,拂晓开船和夜晚到船,码头上人声鼎沸,灯火辉煌。”
(19)1944年,黄同仇(时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主持编纂《安徽概览》,《概览》所附“皖西各县茶叶运输表”③清楚表明,民国时期西、东淠河沿岸所产茶叶多经苏埠水运外销。实际上舒城西乡所产茶叶也多转毛坦厂,陆运到青山,再转入淠河茶麻古道,经东淠河水运到苏埠,远销各地。
(20)1996年版《寿县志》:“淠河航道。淠河南自六安马头集入县境至正阳南清河口入淮,流经县境46公里,建国前为皖西通淮主要航道。出口茶麻、竹木、药材、桐油、生漆等;进口食盐、糖、百杂货等物资多经该航道运出运入,年运量约在6~10万吨之多。”[11](P259)
关于皖西茶叶产区市场及集散市场的分布及其运作,《安徽通史》清代卷下根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安徽省志》第2卷的相关材料,作了如下描述:“六安茶山内有7处市场。苏家埠设有市场,供六安城乡之需要。独山镇,两河口之西北,20里内有茶行76家,在七大市场中居第二位。麻埠有茶行90家之多。霍山,每年产茶五千石上下,其中管家渡周边所产数量最多。每逢茶季,北京、山东的茶商,都亲自到山内市场办茶,故各市场都设有茶栈,北京茶客辄作大宗采购,每客所办,辄在一万石上下。另有青山,每年产额约有万斤(100石)。”“清代六安茶商可分为茶行与茶铺两种,茶行之地位在山户与客商之间,是买卖的中介,‘以赚取行用钱为业’(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安徽省志》第2卷),有时也自行买茶卖与客商。三店铺设有大规模制茶厂,有三四十家茶行。茶铺,从茶行买茶,而贩卖于直接消费者或批发给小商家,其规模远不及茶行。六安茶行本店都设于苏家埠,而另在麻埠及霍山办茶业。主要大字号有:甘德和、德丰源、辛裕和、鼎盛、和丰、万和兴、匡恒生、吉盈丰、兴盛祥等。茶铺都设在六安城内经营,主要进行零售批发生意,著名大字号有:程德大、恒有德、宝源丰、汇源、宝兴,前两者是太平帮,后三者则是徽州帮。六安茶铺以太平商人及徽州商人最占优势,茶商之间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只是各帮有自己的会馆,以此来加强联络。在皖西的霍山县,每逢采茶季节,人们夜以继日地加工茶叶,人力不足,就厚资雇用客工。”[1](P699-700)
茶叶生产者(茶农为主,茶工身份难以确定)与茶叶营销者(茶贩、茶商)构成了市场主体,二者间的关系一般是:“先由茶号收买毛茶再精制加工,或由茶贩向茶农收买再转手卖给茶号。茶农、茶贩出售毛茶给茶号时,须经茶行介绍方可成交。茶行先看货定价,再交给茶号复评、复秤,茶号简单精制包装后运往销区,转售给销区茶庄批发或零售。茶行得佣金,茶农受多出(处?)佣金茶行加重盘剥的双重剥削。”[4](P221)
二
寻觅清代民国皖西茶叶运销的踪迹,往往牵扯着这一时期更为深广的中国与国际茶业史背景。
清代民国时期,皖西茶早期即可北上达青岛,经海路至营口,进入东北,进而“通日、俄诸国”。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传统水道淠河、史河入淮颍,北上亳州或河南周家口,“半薰茉莉,转售京都、山西、山东”等华北地区;津浦路通车后,皖西茶多由淠淮改经蚌埠行于山东,进入北方。亦可“运销山西、口外、蒙古等地”。关于皖西茶运销河南及山东的变化情况,陶德臣分析道:“周家口就是一个中转站,成为茶商采购六安茶的主要据点,因而成为‘齐、鲁、燕、赵、汴、宋、山、陕以及口外、蒙古等地’如此广阔地区的集散中心。入民国后,办六安茶的苏庄、口庄不复存在,鲁庄独占市销。茶由颍水西上而往周家口者,改为循淮河而东,直趋蚌埠,由津浦路运山东,或由以前的由淠水运淮河改为用簰筏由中梅河出三河,过巢湖经芜湖至浦口,转津浦路而北上。‘本区茶叶,向为唯一重要销场之山东市面’,如济南、泰安等地,实为重要集散中心。”“考虑到山东、河南承销茶叶有限,周转市场的作用主要是把茶输送到更远的市场。”④西进可达武汉。东运者一般经运河达镇江、苏州或其他南方城市,或经巢湖-裕溪口进入长江,转海路远销。但经苏州者,据陆允昌编《苏州洋关史料》称:“复在本地拣选焙制,窨以本地之桂花与闽省运来之珠兰花、茉莉花,熏妥后运往北方,全备华人购饮。”[12](P305)可见皖西茶运苏州者也以北上“转由内洋至营口,分售东三省一带”为主。从外部信息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皖西茶曾在北京、天津市场占有不小份额。据《中外经济周刊》第179号所载《北京茶叶之需给状况》文,光绪二十六七年(1900~1901)前,“北京销行之茶,概为六安货。”20年代,六安年产茶300万斤左右,“其销路,以山东为最多,北京、天津等次之。”[12](P337)北京茶商还曾在霍山设主要茶庄。抗战期间,皖西茶尚有输往西安者。皖西茶有无境外销售情况?证诸清雍正三年(1725)苏埠徽州会馆碑铭:苏家埠茶、麻等“行青岛、营口,通日、俄诸国”;以及光绪三十一年《霍山县志》明言霍山茶“近亦有与徽产出外洋者”,恐未可轻易作否定结论。而上引陶德臣“考虑到山东、河南承销茶叶有限,周转市场的作用主要是把茶输送到更远的市场”之语,笔者以为亦可启发我们作进一步思考。
但如果将皖西茶的运销置入清代民国时期整个中国茶的外贸格局中考察,我们还必须考虑2个因素,其一是中俄茶贸在整个清代民国时期中国茶外贸中所占的比重,对此应有客观的评估。清代民国期间,中国茶的国际贸易大势是——明末清初,至少到18世纪初,荷兰是西方国家中最大的中国茶叶贩运国。此后到19世纪末,伦敦则一直是中国茶的全球最大消费与转卖市场。此间,中国大部分输出的茶叶运往伦敦,约占总额的百分之六十。“自十七世纪末叶起,英国向中国购茶数量渐增(为供本国消费及转售于他国),掌握此利润丰富之贸易垂200年之久。1886年达到贸易之最高峰,此时中国之输出总量约300 000 000磅。此后英国商人之目光转注于印度及锡兰茶叶,乃渐放弃中国市场而让与其竞争者之俄国商人。”[13](P55)而中国茶出口于1886年发生盛衰转折的关键正在于此。二是皖西茶如有参与对俄贸易的机会,也主要是绿茶,而绿茶在整个中俄茶贸中的地位和影响如何,也需要有客观理性的分析。很重要的一点是,俄国茶商约从1850年开始,大力引购的是中国红茶、工夫茶,不久又改购中国久已与蒙古贸易之砖茶。俄商甚至先后在汉口、福州设厂专制砖茶,改良中国压制砖茶工艺,改用蒸汽压力机、水压机。
《安徽通史》清代卷(下)根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安徽省志》中的相关资料,编制成《晚清安徽茶叶对外输出路线表》[1](P693),也显示了一些问题,参见表1。

表1 晚清安徽茶叶对外输出路线表 单位:石
路线表显示六安茶对外输出方向仅东北地区,数额仅40 000石,这显然与清代六安地方志书的书写有些差异,这或许同该表仅反映了某一年度(《安徽通史》未标明年份)六安茶的外输情况有关。
在中俄陆路茶贸中,晋商居功厥伟。上引清光绪《霍山县志》卷二《地理志下》中现身的“西商”,同活跃于武夷茶市中的“西客”一样,皆为晋商。清人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七称:“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俄国商队进行的茶叶贩运,吸引大批晋商深入福建武夷茶区,从事茶贸,在衷干《茶市杂咏》中有这样的书写:“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返,络绎不绝。”[14]清代皖西,除了光绪年间流波、霍山茶区有“西商”的活动外,在苏家埠这样的茶叶集散贸易中心,也活跃过晋商的身影。
就茶叶营销而言,苏家埠在皖西茶国内外营销中占有过突出地位。清初,苏家埠在明末战乱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康熙到嘉庆时期的150年间,苏家埠商贾云集,茶麻竹木运销省内外,绩麻织布遍及镇乡。码头云集的各种船筏盛时近千,正常时也有三五百只,水上运输约占本地货物总吞吐量的百分之八十。镇内建有“陕西会馆”“山西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徽州会馆”“旌德会馆”等。晚清,刘铭传家族也在镇上开设当铺。民国年间,西、北大街及沿河一带,船行、茶麻行、粮饼行、车轿行、搬运行、旅馆饭店、茶楼酒肆栉比鳞次。苏家埠因有“小南京”之称。
清代晋商在苏家埠有一定影响,“山西会馆”及合盛号等商号,即为晋商所建,并且获得过州府的特别关注。一通乾隆二十三年(1758)上党合盛号所立刻碑,即由时任六安知州的晋人李若松亲撰碑铭,盛赞合盛号“自开创以来,同财共本,无分宾主,议守先人成规罔逾越,屈指将百载。店愈多而人亦广,不竞多寡,不较劳逸,克勤克俭,能耐能忍,协力同心,均分义利”[6](P491-492)。晋商以关羽为信仰对象,讲求信义,与清初统治者的道德蕲向存在某种一致性。李若松所撰碑铭所彰显之晋商价值观的核心——以义制利,义利结合,至今恐仍不乏启示价值。
清咸丰元年(1851)中俄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后,两国陆路贸易,添设伊犁、塔城两地,连同恰克图共开3处通商。由此,对俄贸易的山西茶商,又有西路、北路之分。西路茶商称“西商”,北路茶商称“北商”。西商主要经营安徽建德等地的朱兰茶,转贩后“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此项朱兰茶,“惟西洋人日所必需,非俄人之所用,伊亦不买。”⑤而北商仍走携武夷茶或白毫茶——经张家口、恰克图线——贩售俄人的旧路。同治三年(1864)后,天山南北持续动荡,西路茶商程化鹏等不得已“改由北路出恰克图一线销售”[14],西商自此改道。从光绪年间“西商”在流波从霍山诸佛庵以北茶区进茶,然后“焙制运销山西、口外、蒙古等地”情形看,当时流波、霍山一带的“西商”,乃改道张家口、恰克图后,仍从安徽购茶的山西茶商。
三
从历史上看,皖西茶在明清时有过一些辉煌,但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皖西茶业由渐衰进入困境。就市场而言,譬如北京,前引《北京茶叶之需给状况》文曾言光绪二十六七年(1900~1901)前,“北京销行之茶,概为六安货。”据《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所载左润华《话说北京茶馆》一文介绍,今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北京茶馆图”,其中一幅内容有“茶馆门墙上挂着写有‘雨前’‘毛尖’‘六安’字样的招牌”[12](P378),也颇能显示皖西茶在京都的影响。但据前引《北京茶叶之需给状况》文,到20世纪初,“嗣后以风气变迁,六安茶销数逐渐减少。”到20年代,“其势力已一落千丈。”就价格而言,1929年,陈序鹏在载于《安徽建设》1929年第8期之《皖北茶业状况调查》中指出:“南茶售价八九十元、百元不等,北茶仅售价二三十元,几及南茶三分之一,同一品质,因制法销路之不同,价格遂相悬如此。”[1](P702)
这当然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除了论者所持茶商榨取、税卡重多外,我们认为,首先应是国际方面,英国殖民地印度、锡兰及日本在科学种植、机器制作、规模经营等方面都逐渐超越了中国传统茶业,以1886年为界,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占有的优势地位开始逐渐丧失,出口量持续下落。这使中国茶、安徽茶都步入了艰难。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日益萎缩的情势下,原本外销的优质茶转而向内,必然挤占了本属基本内销的皖西茶的市场空间。但这种影响的过程比较缓慢,这从皖西茶在北京等市场的遭遇可以想见。据《北京茶叶之需给状况》,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市场上,“绿茶销数最多,约占百分之九十九,红茶不过百分之一而已。”茶源状况为:“红茶来自汉口最多,福州次之,绿茶以徽州及浙江货为最多,福州货次之,六安货(安徽霍山产)最少。”而在皖西茶的重要销地山东,情况也发生了变化,皖西茶从晚清民初的都市市场退向了乡村,据《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7期刊载张本国之《皖西各县之茶叶》称:“目前山东泰安济南各大市场中之戏园、浴堂、茶馆、酒肆等处,所用待客之茶,皆为‘龙井’‘大方’,均无更用‘六霍茶’者。所谓‘六霍茶’之销场,现已由城市全被排挤到穷乡僻壤,为一般劳动者之解渴品矣。至于名城大埠,殆已无‘六霍茶’之立足地。”[12](P384)在京、鲁城市市场上,取代皖西茶的基本上是原为外商青睐的名茶。皖西茶在东北的遭遇,属于另一类,日本茶人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侵略战争形成的强势,采取多种手段,“驱逐中国茶”(日本国立茶业改良场报告语),“九一八”后,终于使得安徽茶“东北销路顿告断绝”[12](P374-375)。
其次,皖西茶叶制作方法存在缺陷、瑕疵,这是导致皖西茶在国内一些重要市场失去地位的主要原因。仅从成品茶品质方面考察,皖西茶与南方茶比较,本就长期不占优势,虽然“西人亦云:霍茶香味较胜徽产”,但明人屠隆、许次纾对此说得很明白,屠氏在《茶笺》中评六安茶道:“六安茶:品亦精,入药最效。但不善炒,不能发香而味苦,茶之本质实佳。”许氏《茶疏》称:“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大江以北,则称六安。然六安乃其郡名,其实产霍山县之大蜀山也。茶生最多,名品亦振。河南、山陕人皆用之。南方谓其能消垢腻,去积滞,亦共宝爱。顾彼山中不善制造,就于食铛大薪炒焙,未及出釜,业已焦枯,讵堪用哉。兼以竹造巨笱,乘热便贮,虽有绿枝紫笋,辄就萎黄,仅供下食,奚堪品斗。”许氏言及霍山茶南北人皆喜,喜为皖西茶人引以为耀,但最后部分文字却鲜有人及,或以为此部分文字所述与黄大茶制法大体相同,在许氏看来,其制作工艺确实乏善可陈。许次纾(1549~1604),字然明,号南华,明钱塘人。清历鹗在《东城杂记》中称他“好品泉,又好客”,其所著《茶疏》一卷,“深得茗柯至理,与陆羽《茶经》相表里。许次纾嗜茶之品鉴,并得吴兴姚绍宪指授,故深得茶理。”到晚请民初,与南方茶系的皖南徽茶比较,当时的皖西茶在制作工艺方面仍无大的改进。如茶园种植方法不当,往往竭泽而渔,使茶叶质量逐渐衰退;制作环节存在很多弊端,如炒干与烘焙各在茶户、茶号进行,制作方法简单,制作工具简陋;商品茶、或者说至少黄大茶仍用篾篓装扎(贡茶袋装),这不利于茶叶色、香、味的保护。对此,地方士绅也十分清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霍山县志》所载《吴志》之语——“近徽郡仿外洋以机器烘焙,制精工省,颇获其利。本邑绅商如能集股设公司,精其制造,则利权操之于我,诸弊不禁自除矣。”就说明了这点。
所以在1910年,时任安徽巡抚朱家宝便特别提出:“六安、霍山等州县向为产茶之区,惜该处乡民未经研究制茶种植新法,不足以挽利权。”[1](P699)随后,六安州采取了一些改良办法,在麻埠茶厘“设立讲习所,并改制红绿茶标本,以资研究,而兴利源”⑥,“采取种焙等法,招生研究,以便改良,而关利源。至所需经费,即于每年茶市时抽收茶捐引厘为经费。”⑦后终因世事变迁,实际效果有限。到1939年,“皖西茶叶指导所为改良制茶技术,提高茶叶品质,曾在立煌县麻埠、流波、毛坪、霍山县城关、诸佛庵、大化坪、漫水河、六安县毛坦厂、落地岗、东西溪、舒城县晓天、乌沙等地创办茶厂,主要品种为瓜片、毛峰、兰花、黄、绿大茶、茶末等,抗战胜利后停办。”[8](P271)
皖西茶失去北京市场、鲁省城市市场,与其茶质不高有直接关系。即使在东北茶市的遭遇,也不能说同此无关,日本茶人对东北茶叶市场,虽早怀野心,但其尚知针对东北茶市采取一些改良措施,据《经济评论》第3卷第4号(1936年4月)所载余焕《中国茶叶之衰落及其原因之探讨》一文内容,知“日本国立茶业改良场报告”曾要求“精密考察该‘国’(按:满洲国)的饮茶习性,能够供给适合满蒙人嗜好的茶叶”;并“累遣专家实地调查,并从事各种宣传”;“雇佣中国技师,制炼东北人所嗜之茶叶。”[12](P374)
再次,有学者认为皖西茶“均系内销,运达地点不远,经过时日无多”[1](P702),这不准确,事实是皖西茶在清代往往是销往各地后或由其他茶商转手销往俄、欧、日等地,有的是晋商、徽商直接到皖西产地采购作若干处理后远销境外。但皖西茶营销方面也确实存在一个重要问题——本土人受传统本末意识影响较深,使茶叶生产不仅多分散经营,而且多视其为副业,不愿加大投入。同时长期的农耕生活使人们安土重迁,不大习惯到国际市场上博弈。如同治《六安州志》卷四《舆地志七》“风俗”载:商货之事,“徽人掌之,土居无与贩者。”上引光绪《霍山县志》卷二“物产”材料中,似乎更受后人关注的是“苏商”“西商”的活动身影。
第四,淠河等河道淤塞、交通不便。如光绪《霍山县志》卷二《地理志》“水利”:“河道未淤以前,贸易甚盛,舟楫往来由城北可上达梁家滩。今载运仅恃竹簲,亦且时时浅搁。山中竹木结筏而下者,非遇大水不能出。商务之衰实由于此。兴水利即可以疏通运道也。”[2](P161)当然,随着皖西山区各地交通状况的改进,皖西茶外销交通困难的情况到民国后也有所改变。
可见,20世纪上半叶,皖西茶曾经历了一个低谷时期。此间,“六安瓜片”制作工艺获显著进步,并声誉鹊起,驰名海内。然而,在民国时期,这一点似乎未能扭转皖西茶的颓势。就皖西茶产量而言,“瓜片”所占比重过小,从本文“一(13)”引述民国三十三年(1944)茶叶产量上可以看到:当年六安全区(统计对象为六安、立煌、霍山、舒城县)总产4 673.4吨,其中片茶仅占0.9%。
以上仅就一般而言,其实历史材料也往往呈现相互矛盾的陈述。从前文“一(13)”所引材料可以看出,以民国八年(1919)、十九年(1930)、二十七年(1938)、二十八年(1939)、二十九年(1940)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皖西茶业资料(统计对象为六安、立煌、霍山、舒城县)进行历年比较,无论产量,还是外销量占比,都呈现增加的势态,从销往地区看,占据要位的仍是山东、河南和天津,只是基本上走向了低端市场。这种情况到50年代初仍无改变,《中国茶讯》1950年11月号所刊王明渊《皖西茶叶调查报告》称,皖西茶“主要市场在华北”,“片茶销长江南岸、淮河一带,蓝花茶销京津,大茶销山东河北农村。”[12](P377)但 除 “兰 花茶”外,在东北、北京似乎完全失去了市场。所以说,国际市场变化对于皖西茶运销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也还需要作理性、具体的评估。
194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编印之《茶叶产销》报告指出:中国人口众多,“饮茶成风,故每年本国茶叶消费量至为可观,约占产量百分之九十,其余则供外销。”[12](P377)关于旧时国内茶叶年消费量,有多种数字统计,互相间差距很大,笔者认为这个“百分之九十”的比例可能相应客观一些。如果认同这点,笔者以为中国茶虽在国际市场遭遇困局,但鉴于国内需求占比的绝对优势,其对于皖西茶形成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
其实,通观清代民国皖西茶的运销情况,虽然我们不认同旧时皖西茶只限于国内销售的观点,但传统上皖西茶主要运销于国内,特别是东北、山东、河南(信阳除外)等地,也是不争的事实。关于此点,张本国先生《皖西各县之茶叶》一文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前,皖西茶叶“最大销场,厥推东北各省,向之苏庄采办到苏,更加熏花精制,由海道运销关东、辽、沈、吉、黑等处。”笔者基本接受这一看法,但要说明的是,笔者怀疑这条材料直接来自上引光绪三十一年(1905)《霍山县志》卷二《地理志下》“物产”那段记述,它是否适宜于说明“九一八”前皖西茶的情况?况且引语也节略不全。一般认为,入民国后,苏庄已不在皖西茶叶市场上出现。但不管怎样,皖西茶曾有过主要运销于东北等国内市场的历史,这是否会给今日的皖西茶叶营销一些启示呢?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皖西茶要首先改良自身。
注释:
① 周始编著《皖志述略》,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编印,第307页。引诗也见同治《六安州志》卷五十四“艺文”。
② 六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六安县志》,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235页。部分内容参考清同治十一年《六安州志》卷五下《舆地志八》。
③ 表据黄同仇《安徽概览》,安徽档案馆1986年重印,1944:117编。见马育良《淠河“茶马古道”再探》,《皖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5页。
④ 陶德臣《中国传统市场研究——以茶叶为考察中心》,长虹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370页。在该书第383-384页,陶德臣对皖西茶在山东市场的运销,有更详细的书写。
⑤ 清宝鋆等编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五六卷。参见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6期,第125页。
⑥1910年8月27日《申报》,第1张后幅第4版。转引自《安徽通史》清代卷(下),第699页。
⑦1910年12月22日《申报》,第1张后幅第4版。转引自《安徽通史》清代卷(下),第699页。
[1]汤奇学,施立业,周晓光.安徽通史(清代卷下)[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
[2](清)秦德章修.霍山县志(清光绪三十一年刊)[M].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3](清)吴康霖.六安州志(清同治十一年刊)[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4]霍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霍山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3.
[5]六安市政协文史委,六安市农业委员会.六安茶[M].合肥:黄山书社,2014.
[6]《苏家埠镇志》编委会.苏家埠镇志[M].苏家埠:安徽省六安县《苏家埠镇志》编委会编印,1988.
[7]孙德艾.风雅皋陶地[M].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
[8]六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六安地区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7.
[9]周始.皖志述略(上)[M].合肥: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1983.
[10]金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金寨县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1]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寿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6.
[12]陶德臣.中国传统市场研究——以茶叶为考察中心[M].北京:长虹出版公司,2013.
[13]威廉·乌克思.茶叶全书(下册)[M].中国茶叶研究社,译.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
[14]蔡鸿生.“商队茶”考释[J].历史研究,1982(6):1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