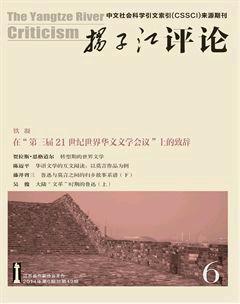华语文学的互文阅读:以莫言作品为例
2014-12-31瑞典陈迈平
[瑞典]陈迈平
华语文学的互文阅读:以莫言作品为例
[瑞典]陈迈平
互文阅读是当代文学批评者熟知的一种方法。依据这种方法,文学文本的意义并不孤立存在该文本之内,而是产生于阅读过程中,是当读者在阅读该文本时有意无意地把该文本放置在自己曾经阅读过的记忆文本的互文网络结构中时产生的,它必然关联到其他的文本,构成互文关联。换言之,阅读是在其上下文中去进行,才能分析和批评,才能达到对文本的更深入更有效的理解。
互文阅读可以是一种语言文学之内的阅读,其互文网络结构和互文关联不涉及外语文学,但在跨文化的语境中,互文阅读有了更加丰富和复杂的互文网络结构,不仅在横向上跨越多种语言文学,而且在纵向上也可能变成多种语言的历史文本的互文阅读。即既有原文上下文,又有译文上下文。我愿意称之为“并置上下文”。当代比较文学基本上就是以这类复杂的互文阅读网络为基础的。
除了个别掌握不同语言的专家能做“并置上下文”的互文阅读之外,大多数译文读者只能通过翻译才能阅读其他语言的文学文本。语言障碍使得他们不可能充分了解原文的上下文和文化背景。这是因为,原文的互文网络结构和互文关联,通常并不能因为译本而同时带入到译本的语境。这就是有的哲学家认为翻译不可能的理由。大多数译文读者有不同于原文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因此在阅读译本时,其实只是在自身语言的阅读记忆文本的互文网路结构和互文关联中阅读。换言之,其上下文不是原文的上下文,而是译文的上下文,所以译文的互文阅读往往是所谓的“重置其上下文”。
“重置其上下文”,实际是与原文上下文脱节,因此也往往是一种“误读”,也可能就是“错置上下文”。这类情况下的互文阅读也可能产生译文阅读的正面效果,因此又使得翻译有可能成立而有效。尤其是在译文“信、达、雅”的情况下,甚至能够达到“并置上下文”,即既能一定程度地在译文中带入原文的上下文,帮助译文读者了解原文的互文关联,又能在译文自身语言的上下文里激发读者对自身语言文本的互文。但是,在不少情况下,这种的互文阅读也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使得译文完全让读者不知所云。即使优秀的原文,翻译并无大错的译文,因此也难以被其他语言的读者接受。
上面介绍和讨论的互文阅读,包括上下文的“并置”、“重置”或“错置”,基本上就是在世界文学的语境里华语文学面对的状况。华语文学已经不仅是在中文上下文里的互文阅读,更多是在跨语言的语境中的互文阅读。我们当然需要对华语文学的翻译更加重视,需要更多的“并置上下文”的优秀范例,但也难以避免译文的“重置上下文”和“错置上下文”。上下文的“重置”或“错置”甚至可能是一种常态,不论其效应正面或者负面。当华语文学创作还存在着某一种“影响世界的焦虑”时,还可能导致作家自己主动“重置”或者“错置”上下文,即华语作家不为华语读者写作而为译文读者而创作,脱离我们华语文学应有的原文语境和互文关联。
莫言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个在世界文学语境里取得成就的华语作家,他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跨文化语境中互文阅读“并置上下文”的成功范例。例如,2012年12月10日的颁奖典礼上,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派尔·韦斯特拜里耶介绍莫言的时候指出说,在莫言的作品里,“我们从未遇见毛的中国的那种标准形象的理想公民”。显然,韦斯特拜里耶是联系毛时代的中文文本,与莫言文本做互文阅读。同时,韦斯特拜里耶也赞扬莫言,说他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比大多数作家都更滑稽热闹也更加令人惊骇的”作家。这说明韦斯特拜里耶也将莫言文本放置在世界文学传统中,和其他传统文本互读。他激活自己对世界文化传统中其他语言文本的记忆,建立的是莫言文本和这些文学传统文本的关系。瑞典学院的网站,也提到莫言和福克纳的创作的关联,即在莫言文本和福克纳文本之间建立一种互文关联。
据我所知,不少瑞典读者在阅读莫言时,把他和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的小说文本比较,特别是和《约斯塔·贝尔灵的传说》比较,认为很有近似之处。两者都围绕自己的独创的家乡风景展开传奇的故事。这些读者往往对韦斯特拜里耶所说的“毛的中国的那种标准形象的理想公民”则全然不知,也不可能进行这样的互文阅读。
瑞典读者在莫言和拉格洛夫文本之间建立的互文阅读能给人非常有意思的启示。这种互文关系,对于一个中文原文的读者来说,几乎不存在,不太可能会联想到,因为他们大都没有读过拉格洛夫的作品(虽然早有过中文翻译),据我所知连莫言本人也没有读过《约斯塔·贝尔灵的传说》,所以瑞典读者对莫言的互文阅读是一种典型的“重置其上下文”,而且也未尝不可。
但由此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中文原文读者和外文译文读者,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互文阅读,因为他们的文化和文学背景是不一样的,文本记忆是不同的。各有各的上下文。中文读者可能意想不到瑞典读者会有这样的互文阅读,而瑞典读者在其互文阅读中也可能想不到中文读者可能的互文阅读。只有瑞典学院的文学专家会注意到原文的上下文。瑞典学院给莫言授奖词说到他的创作把“民间传说、历史和当代融为一体”,自然也考虑到了他的文本和中国民间文化的文本及中国历史及当代社会文本的关系,这个特点在莫言作品译文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我相信,大部分瑞典瑞典没有读过另一类中文原文的互文文本,而这对理解莫言作品也是非常重要的文本。对于中文原文的读者,莫言作品原文的互文阅读,当然还有译文读者不可能阅读出的重要意义。这是大部分西方的译文读者不可能进行的互文阅读,因为他们没有原文所在的那类互文性文本的阅读经验和记忆,不可能将他们读的莫言作品的译本和其他中文文本做互文关联和对比,置于一个中文互文网络的背景中。中文读者在阅读莫言的同时,则可以激活自己的文化记忆和文学记忆,和莫言的文本形成关联,在阅读中产生意义,形成自己的理解。
以《生死疲劳》为例。我所读到的瑞典文的书评,都没有把这部作品和中国现当代的农村小说进行互文阅读。其实,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一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文学的重要主题。《生死疲劳》正是从描写中国当代农村的土地问题和农民形象切入的史诗性作品,对当代中国历史浓缩作画。其中涉及的土地革命(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在当代中国小说中都有典型的文本可以参考并作互文阅读。例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柳青的《创业史》乃至浩然的《艳阳天》等等。
我认为,只有把《生死疲劳》放入到这种中文当代文学史和社会史的上下文中去进行互文阅读,才能看到莫言对历史的更独特更深刻的认识,所塑造的文学形象也具有了不凡的意义。具体地说,我们可以比较《生死疲劳》地主西门闹的形象和《暴风骤雨》中恶霸地主韩老六的形象,或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恶霸地主钱文贵的形象,或者《创业史》里的富裕中农郭士富的形象,《艳阳天》里的地主马小辫的形象,就能看到莫言笔下的西门闹超越了以往机械简单的通过阶级分析定性的地主形象。
再以《红高粱家族》为例,这部小说,应该和中国现当代的抗战小说进行互文阅读才能理解其不同一般的意义。熟悉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人,自然都读过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描写抗日战争的当代中文小说,如《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等。这些小说强调抗日战争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其英雄主角都是共产党员。这些浪漫主义的革命故事并不基于现实,而更多是宣传。而《红高粱家族》是根据作者家乡的一个真实历史事件,其中抗日的英雄都是农民或土匪。
在中文语境里,对莫言作品的互文阅读因此有了重写历史的作用,甚至有了颠覆性的作用,即现阅读的文本可以对读者既有的记忆文本进行质疑和挑战,以该文本的有效性来颠覆其他文本的有效性。莫言的作品,大都有这样历史重写的作用,也有颠覆既有历史话语的重要意义。这种意义,在译本的互文阅读中却往往是看不见的。如何帮助译文的读者理解原文的这样的意义,对华语文学在跨文化语境中的阅读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华语文学的创作、阅读和翻译,应该逐渐走出上下文“重置”甚至“错置”的困境,而争取“并置”的最好前景。
※笔名万之,著名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