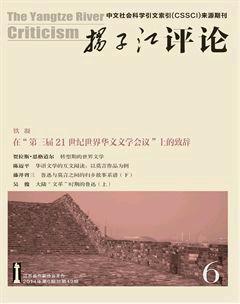新时期初大陆武侠电影的探索及其边界──以《海囚》、《武林志》与《武当》三部影片为例
2014-12-31宫浩宇
宫浩宇
新时期初大陆武侠电影的探索及其边界──以《海囚》、《武林志》与《武当》三部影片为例
宫浩宇
1981年,也就是在新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神秘的大佛》问世的一年之后,大陆上映了一部武侠电影《海囚》(李文化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两年之后的1983年,银幕上又出现了两部颇具影响力的武侠电影——《武林志》(张华勋执导,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和《武当》(孙沙执导、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在大陆武侠电影谱系中,这三部影片并无拓荒之功,更非巅峰之作,笔者为何还要将之拿出来讨论?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当时广受欢迎,也不在于这三部影片比《神秘的大佛》得到了更多来自评论界的赞赏;最重要的原因是,考察这三部影片所呈现出的文本特征及其细微变化,有助于我们以新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武侠电影传统在新时期的“重生”之旅,以及在“重生”之后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这不仅是关于武侠电影,同时也是有关中国娱乐电影乃至整个中国电影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命题。重读这三部影片,重在借助对影片文本及其语境的立体式阅读,叩问以下几个问题:由《神秘的大佛》所引发的舆论风波在尘埃尚未落定之际给创作者留下怎样的精神余震、电影创作者在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下做出了怎样的一种自我保护式的修正,以及在这样的语境下,大陆武侠电影何去何从。笔者期望能以此对新时期中国电影所处的特定的历史境遇,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
一、“文武并重”:废墟中的重建
《海囚》、《武林志》与《武当》是在《神秘的大佛》公映之后问世的。殷鉴不远,《神秘的大佛》的坎坷遭遇,①足以引起创作者的警觉与反思——较之先行者,这三部影片呈现出了诸多新的面貌。
最明显的一点是,这三部影片在“武”与“侠”这两个武侠电影最核心的元素上做得更加符合类型规范。武侠电影之所以被称为武侠电影,一个根本的判断标准就在于要有量足质优的“武”;否则,就是名不副实,就是糊弄观众。而所谓“武”,当然是指武打动作,在这个方面,虽然《神秘的大佛》已经有了可喜的尝试,但也留下了一些明显的缺憾:一个是武戏太少——只有两场;另一个就是武打动作尚显虚假造作,更谈不上有什么美感;再一个就是许多武戏是和剧情脱节的,为打而打的痕迹很明显。作为初次尝试,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任其如此,大陆武侠电影终将行之不远。
值得庆幸的是,这三部影片的主创都清楚地察觉到了这一弊端,并着手加以改善,力求为武戏充电,使之既不失充沛、精彩,又能与文戏水乳交融。对此,张华勋有很好的阐释:“我吸取《神秘的大佛》的经验,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文武并重’的要求。因为光文戏好,缺乏功夫,就将失去《武林志》的特色,失去武术题材影片的特点,如果只有功夫,而文戏不好,就很难表现好人物。于是我们确定了选择演员的三点基本要求:凡是角色要表现装(武)功的都选武术行家;演员的气质必须符合角色的要求;最后一点才是演员的形象。”②修正的结果是:一方面影片的武戏在数量上得到了明显的增加,而且大多能合情合理地融入到情节的进程之中;另一方面,人物的武打动作也比《神秘的大佛》看起来要更有章法,而非大呼小叫的乱打一气。显然,这与三位导演在影片中启用了众多专业武术运动员有着密切的关系。③一般来说,没有武术基础的演员,也不是说就不可以通过临阵磨枪的“培训”、凭借移花接木的电影特技(吊威亚、跳弹床、镜头分切等)来制造以假乱真的银幕效果。然而,就当时的条件来看,绝大多数大陆导演对这些技术是不熟悉的,甚至都闻所未闻,何谈使用?再者说即便在武侠电影创作的大本营香港,若要在影片中展现出真正绝妙精伦的动作来,终究也还得依赖起码的基本功,而这偏偏又是难以速成的。这就是为何大凡取得成就的武打明星,大多是“练家子”的道理了;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张华勋在拍摄《神秘的大佛》时,尽管很想在武戏上大做文章,但最终出来的效果还是难脱虚假了。追求高水准的“武戏”,除了要求演员动作优美,打得有板有眼外,也离不开对打斗场面的精心组织和对某项绝技或独门秘器的刻意渲染。应该说,这两部影片在这一点上也取得了重要突破。《海囚》中出现了“双打”与“群打”(这一点突破了诸如《保密局的枪声》、《神秘的大佛》、《戴手铐的旅客》等同一时期设置了“武戏”的影片只有“单打”的局限)、《武林志》中出现了“八卦掌”、《武当》中出现了的“九宫神行掌”以及暗器等等,皆为明证。这表明此时大陆电影创作者已深得武侠电影之三味了。
在这三部武侠电影中,主创不仅充实了“武”的内容、优化了“武”的品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引入“侠”的精神,并对之做出符合现代意识的诠释与强调。何者谓之“侠”?从传统意义上来看,一个人若要被称之为“侠”,不仅要身怀绝技,还要敢于“以武犯禁”;更要有“武德”,懂得如何使自己的暴力行为与惩恶扬善的义举正相关,而不是一味的好勇斗狠、争名夺利。要做到上述几点,“侠”平时要力求“立节操,以显其名”、“忧人之忧”,平日里尽可不拘小节,甚至放浪形骸,但是大是大非上则不能含糊:必须做到“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一个人再有高超武艺,只要达不到上述几点要求,就绝对称不上是“侠”;顶多只能算是武林高手。
以此观之,《武林志》中的东方旭无疑是一位“侠”。尽管他身怀过人的武艺——这一点,导演在影片开场时通过设置了一个让他若无其事地踩碎石板的情节暗示给了观众。但随着剧情推进,我们看到,东方旭面对欺辱,并没有滥用武功,而是处处克制、忍让,不与性情鲁莽却同样富有正义感的何大海一般计较。直到影片最后,他一举击败了俄国大力士达达洛夫,方始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东方旭的这种隐忍不发的性格,是与其外在的、良好的“武德”互为表里的,它们共同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非到迫不得已,绝不出手伤人。这种信念所包含的核心价值观,可以用“后发制人”一词来概括。导演孙沙更是直接了当地承认,他拍摄《武当》“想要留给观众印象的,就是‘我们向来是后发制人’这句话”④。事实上,他也确实让片中人物时时把这句话挂在嘴上。应该说,“后发制人”是为中国武侠电影所一贯弘扬的一种价值观。众所周知,武侠电影离不开表现暴力,可暴力又的确不是一个好东西,它从来都是为有良知的人所憎恶的,也就自然成为银幕表现的禁忌。问题在于,越是被划为禁忌的东西,往往越是有无穷的“魅力”,创作者就越是想尝试,观众也越是欲罢不能。武侠电影常常遭人诟病,与此不无关系。在表达权受到宪法保护、对影视作品实施严格的分级制的社会中,电影作品表现暴力从法理上说是没有禁区的;但像武侠电影这种面对主流市场的类型电影,创作者一般还是要有所为,亦有所不为的——暴力可以有,但必须拿捏分寸、点到为止,不然就会因与普通观众的伦理道德相抵触而遭到有形的与无形的限制,从而被隔绝在大众之外,走向边缘化。因此之故,武侠电影创作者一般都会在表现暴力之同时,对暴力进行“修饰”,一个常见的策略,就是一边强调正面人物的道德优势,一边再用同样的笔墨去强调反面人物的道德劣势,“特别注意首先表现非正义者的挑衅与侵略行为,从而为正义者使用暴力进行反抗确立充分的道德依据。”⑤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传达出一种“后发制人”的价值观,以消解暴力的残酷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像《武当》那样在主人公决斗之时总是将“后发制人”一词直接道出,不免有些生硬直白,但两部影片能够对这一价值观自觉的遵从和强调,却是值得肯定的,它意味着此时的大陆电影创作者对武侠电影的认识与理解,已不再像《神秘的大佛》那样以猎奇的心态对暴力做直观化处理,或是肆无忌惮地展示杀敌的快意与戾气,而是以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认同为前提,穿透“武”的表层形态,有意识地触及支配侠士所言所行的深层行为准则——对暴力的自省、对行使暴力的正当性之恪守。正是在这些地方,《武林志》和《武当》刷新了大陆武侠电影的类型观念和文化内涵,也得以不仅同《神秘的大佛》,也同《海囚》区别开来。
二、“拍出社会主义的新型武术片来”:乍暖还寒中的无奈之举
谈论新时期的大陆武侠电影,不能不提到香港电影的影响。由于政治原因,1949年之后,武侠电影在大陆销声匿迹,但它在香港却香火不断,而且渐入佳境,香港也由此成为武侠电影这一在中国最重要的电影类型的一个重生之地。进入新时期,受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大陆电影人“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得不去拍摄以往被人们所鄙视的娱乐电影,其中当然少不了武侠电影了。创作这种电影,没几个人有经验,那就只好去学习。向谁学呢?最理想的学习对象无疑就是香港电影了。事实上,在《神秘的大佛》问世之际,香港武侠电影虽然还未曾在大陆公映,却早已以“内参片”的形式成为了包括张华勋在内的许多大陆电影创作者参考和借鉴的范例。⑥只是由于观念上的束缚,加上《神秘的大佛》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娱乐化倾向因被一些评论人诟病为过于港台化而遭致激烈的口诛笔伐,大陆武侠电影与香港武侠电影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就是创作者们讳莫如深的事情了。香港武侠电影的影响在当时还只能以匿名的状态存在。⑦
这种状况在《少林寺》横空出世之后,获得了一些改变。1982年,《少林寺》在中国大陆公映,旋即掀起巨大的观影热潮。这让初沐市场经济春风的大陆电影人不禁产生垂涎之感。尤为重要的是,不同于《神秘的大佛》,这一次,《少林寺》不仅为普通观众狂热追捧,更博得舆论界几乎一面倒的赞誉,可谓叫座又叫好。如此一来,《少林寺》在当时给予大陆电影工作者的,就不仅仅是成功的诱惑,还有借鉴时的一点理直气壮的心态。陈荒煤鼓励同行积极摄制武侠电影时所说的一番话,便很能代表这种心态:“为什么今年这么多厂不搞武术片呢?大家可以看看《少林小子》,在国际上很轰动,为什么我们有钱不赚呢?”⑧显而易见,在越来越多的评论者那里,香港武侠电影已不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值得效仿的榜样。就是在这种寒冰初融的舆论氛围下,李文化、张华勋与孙沙才敢将自己从《少林寺》或其它香港武侠电影中习来的手法,更多地运用到各自的新作品中去。诸如对武术运动员的启用、对“后发制人”的价值观之传达,以及对习武练功场面的详尽刻画等等,均可从《少林寺》中找到相对应处。可以这样说,不向香港武侠电影偷师学艺,《海囚》、《武林志》以及《武当》能成功完成“升级换代”,而非重蹈《神秘的大佛》之覆辙,是不可想象的。
但大陆电影创作者对香港武侠电影的借鉴,不是全盘照搬的,也没有条件、没有胆量这样做,甚至于在公开的舆论平台上,他们还要极力撇清自己与香港武侠电影的关系:“我们要拍武术题材的影片,绝不能走海外的路子”,而是要按照厂领导的指示,“拍出社会主义的新型武术片来”。⑨彼处的武侠片、功夫片,在此地只能被称为武术片、武术题材影片,而且还要被冠上一些限定词——“社会主义的”、“新型的”云云,实在是耐人寻味。看来,大陆武侠电影创作者只能去选择那些容易被批评者所接纳的内容,否则就会被无端地扣上各种帽子。为生存计,不能不借鉴,同样是为生存计,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借鉴,大陆武侠电影创作者只好“一停二看三通过”了。
具体来讲,大陆电影创作者对香港武侠电影的借鉴,是通过重新组织武侠电影的一些经典桥段来完成的,目的是使这些元素旧貌换新颜,以符合彼时的“特殊国情”。这一点,借助对两部影片共有的一个情节即“擂台比武”的分析便可清楚看出。“擂台比武”在中国武侠电影中堪称是一个“经典场景”,⑩《武林志》和《武当》中均出现了“擂台比武”的情节,并不奇怪。值得注意的是,与香港武侠电影相比,“擂台比武”这一“经典场景”,在这两部影片中被赋予了新的所指。“擂台比武”必然分出胜负,而胜负则联系着个人的成败得失、进退荣辱,这是传统中国武侠电影并不回避的主题。然而,在这两部影片中,情况略有不同:如果说“擂台比武”在片中还具有决定成败得失的功能的话、还能让人感受到强烈的荣辱感的话,那么,这成与败、荣与辱也不再为个人所专有,而是同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其想表达的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入侵者的传统斗争精神”“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凛然气概。”⑪于是,擂台之上的“演出”也就超越了单纯的、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升格为一场关乎民族尊严、国家命运的对决,“在不同武术技击方式(中国的八卦掌和西方权术)的交锋中,包含着奴役与抗争、侵略与反抗”⑫,其中少了一些江湖气,却多了不少民族大义。李文化拍摄的《海囚》也将中国勇士同洋人一决高下设置为重头戏,“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对帝国主义的斗争”⑬,只不过“斗争”的场景不是擂台,而是甲板。然而,无论擂台也好,甲板也罢,弥漫其间的都是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样的情节,再次频繁地现身于银幕之上,还要到新世纪CEPA的签订引发合拍武侠大片再度勃兴之后,《霍元甲》、《叶问1》、《叶问2》、《精武英雄》等均属此类。尤其是票房大卖的《叶问2》,在人物关系的设置、矛盾冲突的构建与高潮段落的铺排等许多方面,都与《武林志》甚为相似!二者这种遥相呼应的“历史联系”,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的借鉴,抑或相似的时代思潮使然?问题的答案,还有待另文探寻。
民族仇恨覆盖了个人情仇的表达、国家荣辱被置于江湖恩怨之上,此种原则一旦被确立,就意味着个人成功必须要与高于个人成功的某项宏大的事业紧密结合起来,才是有价值的,才是值得去做的;否则,就是个人主义的,是没有太大价值的,也就是不值得去做的。不难看出,这是从“十七年”电影、“文革”电影延续下来的一个经典主题,而这一主题之所以在新时期仍然“在场”,是因为它得到了创作者的集体认同,至少是集体遵从。张华勋在谈到自己如何创作《武林志》时说过一段话,很能揭橥这种心态:“影片中如果不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历史事实,不提沙俄大力士的名,没有警察厅同绿宝石洋行的狼狈勾结,共同欺压民众百姓,也就失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特点,这场关系着民族尊严的打擂比武也就会失去其思想意义,仅仅变成一般的角逐较量而已。这当然是不可取的。”⑭显然,这已经不全然是在学习香港武侠电影了——当时主流的香港武侠电影,比如成龙、洪金宝、楚原、徐克的影片,大多只是演绎个人的恩怨情仇(用大陆的标准来衡量,就是“一般的角逐较量而已”)而不会牵涉太明显的国族话题;毋宁说是在悄悄地向土生土长的现实主义回归。纵观中国电影史,现实主义有着深厚的传统。一般认为,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国防电影”,到抗战胜利后的“进步电影”,再到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都在不同程度上诠释着现实主义、践行着现实主义,尽管其中不乏误读、曲解和滥用。步入新时期,尽管中国电影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但作为一种指导创作实践的经验法则、一种主导批评实践的理论话语,现实主义依然保持着难以撼动的正统地位,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批评家,抑或一般观众,在把握一部电影作品时,常常“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追随新中国电影之余绪,从现实主义的理论库中寻找合适的话语资源。换言之,现实主义已经内化于电影创作者的世界观、审美观和创作意识中,构成一种潜在的、对创作者来说极具约束力的自我评价体系。即便在没有任何的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一个创作者也很可能会依据“熟悉的”现实主义原则来组织、规范自己的创作行为,更何况这种外在压力在当时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不小。如此一来,在旨在讲述“成人的童话”的武侠世界中注入一些现实主义因素,也就成了创作者在乍暖还寒的政治环境下必然会去选择的一种绝妙的生存策略,目的是通过“把一个体现国家意志的爱国主义主题与一个关注大众心理的伦理主义的道德主题‘镶嵌’在一起”⑮,为影片保驾护航,规避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明乎此,李文化、张华勋以及孙沙的“回归”,就不难理解了。
从影片上映后的舆论反映来看,创作者们的这种选择大体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三部影片在上映之后除了延续卖座鼎盛的势头之外,在舆论上也收获了远多于《神秘的大佛》的好评。比如,有的影评肯定了《海囚》“是一部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较好的影片。”⑯也有论者指出《武林志》“在表现民族武功的壮美的同时,也在追求一种朴实美”“使东方旭、郜莲芝等人物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深厚的社会根源。”⑰还有人认为“这部影片体现了我国电影工作者的一个重要的努力,即尝试着把武打片上升为一种严肃的现实主义的电影艺术”⑱。诚然,我们或许并不能简单地将影片的商业成功与上述“爱国主义思想”、“坚实的阶级基础”或“严肃的现实主义”云云划等号,但在阴晴不定、忽左忽右的政治语境下,创作者对被官方和主流评论家所认可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回归,的确是为作品找到了一个征服舆论的有效方式,从而成功地穿越政治迷雾,不至于像《神秘的大佛》、《少林寺弟子》、《客从何来》、《幽谷恋歌》等影片那样,成为众矢之的,更避免了遭受影片《瞬间》、《太阳和人》那样的厄运。美国学者安敏成观察到“每一个重要的解冻时期(包括1956年间的‘百花运动’和后文革时期)的文学都被当作是对解放前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良性复归而受到热烈称赞”⑲。显然,新时期大陆武侠电影“复活”的经历,多多少少印证了这一论断。
问题在于,现实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影片的主题显得厚重、严肃,也能让影片的形式变得呆板、无趣,对以娱乐大众为主旨的武侠电影来说,尤其如此。诚然,现实主义因在中国“具有了一种最安全最少异己性的外观”⑳而令创作者趋之若鹜,但由于主流舆论所认可的现实主义原则与类型电影的创作规范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又未能也无法在当时得到有效的化解,所以这两部武侠影片尽管依然卖座(部分原因是当时优质的娱乐电影还很匮乏),却少了许多生机活力,显得“老成之态甚足,缺乏动作片应有的英气和潇洒”㉑,以致影片的类型特征变得有些模糊,与其说是武侠电影,不如说更像是历史片,或者其它某个比武侠电影名声更好的类型。李陀在当时就敏锐地指出:“我们在看《武林志》这部影片的时候,有一种在看历史故事片的感觉,而不是武打片或功夫片的感觉,这绝不是偶然的。”㉒为什么“绝不是偶然的”?听听创作者的“现身说法”也许就明白了。李文化把《海囚》定位为是一部“人物多、场景多、场面大的历史题材影片”。㉓张华勋的说法是:“就《武林志》的内容和故事来看,我们应该十分明确,它不是什么武打片、功夫片。而是一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悲壮而严肃的正剧。”㉔孙沙则强调:“在样式上,《武当》可称为民族武术片(也是一部体育片)”“不可以把影片搞小气了,影片要具有一种明确的历史感”。㉕看来,影评人的直觉不是捕风捉影——连创作者本人都不愿意“看见”自己的作品与武侠电影(更不用说香港武侠电影)扯上瓜葛。在实践层面上拍摄武侠电影,在理论层面上却又偷梁换柱、闪烁其词,极力回避它,新时期初的大陆武侠电影创作者正是在这样一种纠结的状态下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结语
和“破冰之作”《神秘的大佛》不同,《海囚》、《武林志》以及《武当》既有票房,又有口碑,可谓名利双收。这应归功于大陆电影创作者通过对香港武侠电影的借鉴,在“武”与“侠”两个方面优化了作品的艺术品质;更得益于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归为评论界所赞赏的现实主义风格。乍暖还寒中,几经波折后,大陆武侠电影终于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不再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这不意味着它们已经奔驰在康庄大道上了,因为这种“合法性”的获得,是以让武侠电影的写实性而不是假定性愈来愈得到强化为代价的,是以让武侠电影愈来愈皈依“国家”而不是“江湖”为代价的,是以让武侠电影愈来愈“有意义”而不是“有意思”为代价的,一句话,是以磨平武侠电影的“特殊性”,使之愈来愈远离武侠电影而不是相反为代价的。其结果就是:强加的“生活依据”、陈旧僵化的历史主题以及基于想象而不是史实的民族主义情绪等现实主义元素,逐渐挤占了对诸如光怪陆离、天马行空、快意恩仇等浪漫主义元素的书写空间。与其说这是在开创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新型武术片”,不如说是在“去武侠电影化”。《海囚》、《武林志》以及《武当》给大陆武侠电影踏出了一条新路、活路,随之又无奈地将之引到了歧途甚至绝境,使得它与主流的武侠电影传统渐行渐远。至此,包括武侠电影在内的中国娱乐电影,实际上已经走到了探索的边界,再一步,是万丈深渊,抑或一片坦途,在当时是没人能够清楚预见的。
【注释】
①关于《神秘的大佛》的创作过程及舆论反映的研究,可详见宫浩宇:《〈神秘的大佛〉:一种探索片的诞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②⑨⑪⑭张华勋:《我对开拓武术题材的新认识——〈武林志〉导演工作汇报》,《电影导演的探索(第四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305—306、295、297—298页。
③比如,导演孙沙曾介绍说:“影片《武当》集中了全国九省(市)22名武术教练员、运动员担任片中各类角色,他们都是国家一流武术人才,有的曾多次荣获金牌,多次出国访问”。详见孙沙:《一次探索——简忆〈武当〉的导演创作》,《电影导演的探索(第四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页。④孙沙:《一次探索——简忆〈武当〉的导演创作》,《电影导演的探索(第四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页。
⑤⑫⑮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版,第8、116、122页。
⑥参见张华勋:《我拍〈神秘的大佛〉的前前后后》,《电影艺术》,2004年第1期。
⑦李文化曾在文章中提到一个细节:“《海囚》中武打场面较多,……我们在处理这些群众场面的设计中,原来想搞点“一招一式”类似香港那类武打式的东西,……”这说明李文化在当时是看过香港武侠电影的。详见李文化:《谈影片〈海囚〉的导演处理》,《电影导演的探索(第二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页。
⑧陈荒煤:《一个新的严峻的历史考验——从1983年展望未来》,《电影通讯》,1984年第6期。
⑩详见贾磊磊:《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经典场景”》,《电影艺术》,2004年第1、3期。
⑬㉓李文化:《谈影片〈海囚〉的导演处理》,《电影导演的探索(第二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347页。
⑯刘乃叔:《〈海囚〉尚有败笔》,《中国大众影评长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⑰王志超:《功夫片絮语》,《电影艺术》,1985年第1期。
⑱李陀:《武打片的新进展——〈武林志〉》观后》,《电影艺术》,1983年第11期。
⑲[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⑳戴锦华:《斜塔:重读第四代》,《电影艺术》,1989年第4期。
㉑王海洲:《中国电影:观念与轨迹》,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㉒李陀:《武打片的新进展——〈武林志〉观后》,《电影艺术》,1983年第11期。
㉔张华勋:《〈武林志〉导演阐述》,《电影通讯》,1983年7期。
㉕孙沙:《一次探索——简忆〈武当〉的导演创作》,《电影导演的探索(第四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315、316页。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