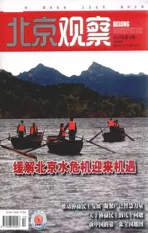徐世昌是否曾密赴彰德
2014-12-13徐定茂
文 徐定茂
作者 系第九、十、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专职监察员
在近代史研究领域里,多年来由于一些虚构历史的存在而遮蔽了事物本来面目。而徐世昌《韬养斋日记》的刊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还原历史的真相。
北京出版社近日出版发行了先祖徐世昌的《韬养斋日记》,同时一并推出《徐世昌与韬养斋日记》系列丛书。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吴世民指出:“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徐世昌有时是直接参与者,有时是推动者或阻拦者。徐世昌日记始终对亲历耳闻的诸多事件均详加记录,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内容,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对今天的文史工作和首都文史的研究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可以说,在近代史研究领域里,多年来由于一些虚构历史的存在而遮蔽了事物本来面目。而徐世昌《韬养斋日记》的刊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还原历史的真相。
举例来说,早先社会上始终有一种说法,即武昌起义后徐世昌曾赴彰德秘密会晤袁世凯。袁进而向清廷提出索权的六项条件,为其最终夺取“革命胜利果实”打下基础。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华书局,1994年版)讲:“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急忙派陆军大臣 昌率领北洋军队赶往武昌镇压革命。北洋军队是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不听从 昌的调度,清政府束手无策。10月14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统帅北洋军队南下镇压革命。袁世凯野心勃勃,想乘机向清廷索取更大的权力,借口‘足疾未愈’,留在彰德不肯出山。27日,清政府不得不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袁世凯仍不满意,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予他军事全权,保证供应充足军饷等条件……”
应该承认,武昌起义的确为袁的复出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见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 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
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讲,“袁世凯的计划是要让清朝廷更多地受到革命火焰的煎熬,以致不得不向他交出更多的权力。朝廷在10月20日(农历八月二十九日)派出袁世凯的老朋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到彰德敦促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提出了六个条件,这就是: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汉起事人员;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全权;六、保证饷糈的充分供给”。
然而从徐世昌日记的记述中看,这个情节不过是向壁虚构得来的。
首先,徐世昌微服出京赴彰德游说袁世凯一说至今没有第一手材料可以来证明此事,此说最早出自何人也很难确定。如今能够查到比较早的是李剑农先生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里说的,“徐世昌见他不出,便微服出京亲往劝驾。及清廷再三催促,袁便以徐世昌和奕 为介,提出六个重要条件来,非清廷悉行允诺,决不出山”。
在辛亥前后任《滇报》的编辑邓之成先生说,“诏令下达后,袁迄未来京拜命赴任。庆王疑虑,派徐世昌去彰德约袁同来北京。徐到后,知袁欲乘清廷之危借机要挟,意在取得内阁总理大权。徐未加劝阻,亦未同其来京”。(《我知道的北洋三雄》,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说的最逼真的还数陶菊隐先生。陶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里讲,“奕 明明知道是袁的授意叫他出面来保荐,现在目的达到了,为什么又要装腔作势地不肯受命呢?因此他叫徐世昌于10月20日(八月二十九日)秘密到彰德去摸袁的底子。徐到彰德与袁进行了一度密谈,就很快地跑回北京来,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回报奕 说:‘真是不成话,他还提出了一些就职的条件……’奕 问他提出哪些条件时,他又支支吾吾地不肯说出来。直到盘问得紧,才吞吞吐吐地说出六个条件……这是袁、徐串通一气地演出来的一幕双簧戏”。
过后,陶先生好像忘了早先是怎样讲述密访彰德的日期。他又在《袁世凯演义》(中华书局,1979年版)里面说:“10月20日,徐世昌从彰德跑回来,气急败坏地回报奕 说:‘咱们甭再找他(袁世凯)了,难道少了他这出戏就唱不下去不成?’直至奕
问道:‘哪些条件?’徐才把六个条件摊出来……”
这里面,李、陶及邓讲述相同的地方仅限于提出了徐世昌曾密访彰德会晤袁世凯的说法。不同的是李和陶先后提出了“六项条件”之说,邓之成先生之说仅为当徐了解了袁的真实想法后“未加劝阻”,随后便悄然回京了。
有区别的地方在于李剑农先生说徐世昌是自己主动去的彰德,但没有指明时间。邓之成和陶菊隐则提出此行是庆王奕 指派的。邓的文字里也没有注明时间,陶却提出了两套时间程序,一是“10月20日秘密赴彰德”、一是“10月20日从彰德跑回来”。
李剑农出生于光绪六年,在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学习时加入同盟会,后东渡入早稻田大学。武昌事发后回国,在汉口《民国时报》任新闻编辑;邓之成疑为邓之诚之误,光绪十三年出生,武昌义举时为昆明第一中学的教员,兼领报社工作;而陶菊隐是1898年出生的,辛亥年不过是十余岁的中学生。民国二年时中学没毕业便到长沙《女权日报》当编辑,后也一直从事新闻工作。
由此可知,李、邓、陶当时均在从事新闻工作,在没有第一手材料证明的情况下而由新闻报界人士写出的信息在可信度方面就不免要大打折扣了。尤其是辛亥年间李剑农身在日本,邓之成(诚)在中学任教,而陶菊隐还在中学里读书。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中学生是从什么渠道得知如此重大而机密的事情?而在日本生活的人员去讲述彰德的故事,真实的成分又会占几成呢?
可惜的是,在此后多年中,徐世昌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之说几乎成为了一种共识。
后来又有袁静雪先生在《我的父亲袁世凯》(《八十一天皇帝梦》,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里说,“听说他的老朋友,当时的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也来劝他出山。那时候三姨太太的住房紧靠着一个院子里的厢房。我父亲就在这厢房里办公和会客,这两排房屋虽然不是一个院子,但后窗却是紧对着的。我们在夜里三四点钟一觉醒来,总是望见那边厢房里的电灯还亮着,还仿佛听见那边有说话的声音”。
袁静雪,原名袁叔祯。三姨太金氏所生,与袁克文为一母同胞的兄妹。文中“三姨太太的住房”即是袁静雪母亲的房屋,所以此文可信程度较高。只是袁静雪也只是“听说”徐世昌来了,并未见到。同时袁文里也没有“提出了六项条件”一说。
时至今日,又有王学斌先生在《利国无能但利身——读徐世昌“韬养斋日记”》(《书屋》,2011年02期)一文中讲:“近日笔者有幸读到徐世昌未刊的《韬养斋日记》,阅罢这长达一百五十余万字的私人记录,方使我深感……武昌首义爆发后,举国响应,清廷顿时方寸大乱。徐与袁心中早有默契,听闻风声有变,立即活跃起来。他联合奕 、那桐,四处散播‘收拾残局,非袁不可’的论调。载沣出于无奈,只得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让他主持大局。孰知袁世凯奉诏后,却故意徘徊观望,以‘步履维艰’为借口迟迟不上任。这可急坏了徐世昌,他赶忙微服出京,赴彰德劝袁出山(一说是朝廷命徐世昌到彰德请袁复出)。此事在其日记中只字未提,可见极为隐秘……”
王学斌先生的文字与前面几篇的不同点,在于王的依据是“近日笔者有幸读到徐世昌未刊的《韬养斋日记》”。徐世昌是当事人之一,北京市政协委员朱良提出,“日记当属于当事人在当时的第一手记载。作为日记,作者并不准备写给外人看,也就没必要写虚假的东西。日记中史料的真实性基本不用怀疑”。(《韬养斋日记出版过程中我经历的几件事》,载《徐世昌与韬养斋日记·辛亥篇》,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应该说,徐世昌日记里的记述是第一手材料,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然而所见王文,洋洋数言,除了重复一些陈旧的说法外并未从日记中获得任何线索。尤其是“此事在其日记中只字未提”的说法不免令人疑惑。既然日记里“只字未提”,王学斌先生又是如何从“有幸读到徐世昌未刊的《韬养斋日记》”里得知徐世昌“赶忙微服出京”的呢?
日记是这样记述的:
辛亥 八月 二十日 未明起,入直。巳正三刻散。拜客一家。回家。午后杏荪、琴相来谈公事。同琴轩谒庆邸会议公所。久谈。归。约铁路南北段总办谈公事并请宴。闻武昌为叛兵所扰,瑞总督乘兵轮到汉口。
廿一日 未明起,入直。午初三刻散。回家,小憩。留姜翰青、李季皋晚饭,久谈始去。
廿二日 未明起,入直。午正散。回家。李季皋在此,留饭。
廿三日 未明起,诣寿皇殿外外随侍皇上。行礼,入直。未初三刻散。回家。本日奉旨,派拟考试孝廉、方正题目。今日奉上谕,袁世凯补授湖广总督、岑春煊补授四川总督。
廿四日 未明起,入直。午正散。回家。留梧生饭。
廿五日 未明起,入直。午正二刻散。午后到内阁会议。归。李季皋来,留晚饭。
廿六日 未明起,入直。午正二刻散。到内阁公所。
廿七日 未明起,入直。午正散。回家。
廿八日 未明起,入直。召见三次。午正一刻散。回家。
廿九日 未明起,入直。午正一刻散,回家。到内阁公所。
三十日 未明起,入直。午正三刻散。回家。
九月 朔日 未明起,入直。午初三刻散。同琴轩到西城宝宅早饭,同到资政院行开院礼。未刻归。
初二日 未明起,入直。午初二刻散。回家。
初三日 未明起,入直。午正三刻散。回家。
初四日 未明起,入直。未初二刻散。回家。
初五日 未明起,入直。未正散。回家。
初六日 未明起,入直。未初二刻散。回家。夜,涛、朗两贝勒至琴轩宅,约往。谈公事,夜深始归。
初七日 未明起,入直。未初一刻散。回家。夜,涛贝勒、李季皋来谈公事,夜深始去。
初八日 未明起,入直。未初一刻散。回家。
初九日 未明起,入直。未初一刻散。回家。今日蒙恩赏,重阳糕。
初十日 未明起,入直。未初一刻散。回家。小憩。到庆王府会晤各社会人员。
十一日 未明起,入直。未初二刻散。回家。到资政院,上灯后始归。本日同庆王同具折,辞内阁协理大臣职。奉旨俯如所请。蒙恩著充弼德院顾问大臣。
十二日 未明起,入直。同庆邸、那相具折谢恩。本人召见二次。未初刻散。回家。小憩。
十三日 未明起,入直。午正三刻散。回家。
十四日 未明起,入直。午正一刻散。到摄政王府,谢送礼。
十五日 未明起,入直。未初刻散。答拜客数家。回家。
十六日 未明起,入直。未初刻散。回家。
十七日 未明起,入直。未正散。回家。
十八日 未明起,入直。午正一刻散。回家。
十九日 未明起,入直。午正三刻散。回家。
二十日 未明起,入直。午正二刻散。回家。
廿一日 未明起,入直。午正散。回家。会客不断,至申刻。摄政王命同琴相到北海大他坦晋谒。本人蒙恩授为军谘大臣。辞,不获请。
廿二日 未明起,入直。谢恩。午正一刻散。到军谘府到任办公。
廿三日 未明起,入直。召见三次。午正二刻散。回家。慰廷到京,访谈良久。夜归,看公事。
日记表明,在廿三日袁世凯(慰廷)到京之前,徐从未离开过京城。在这段时间内除“召见”外,先后与载沣、奕、载涛、毓朗、那桐(琴轩)、徐坊(梧生)、李经迈(季皋)、姜桂题(翰青)、盛宣怀(杏荪)等有过交往,而八月廿九日(10月20日)那天“到内阁公所”。若真是“极为隐秘”从而“在日记中只字未提”的话,王学斌先生就应该给出一个必须在日记里造假的理由。其实当时就连袁世凯都没有“极为隐秘”的想法,他的态度很明确。袁讲,徐世昌的确给他发过电报,建议“勉弟以释前嫌,明大义,速行应召出山,仔肩大任,础国家于磐石之安,登斯民于衽习之上……”袁则回曰,“弟归田日久,自量能力不足以统辅全军,自知德鲜不足以削平内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不智,何苦以垂老之身而作此误国、误民、误身之事而受万人之嘲骂耶”。同时还请徐世昌“善为我辞,请朝廷收回成命,另简贤能。”(《尺素江湖·袁世凯家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
袁世凯说的也不无道理。在“武昌为叛兵所扰”的情况下仅一个“湖广总督”恐怕难以有所作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不智……”因此要求“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全权、保证饷糈的充分供给”,否则“请朝廷收回成命,另简贤能”也是很正常的。这里面根本没有“这可急坏了徐世昌,他赶忙微服出京,赴彰德劝袁出山”的必要。
就连皇族权贵们也并不是不了解这些内幕。载涛在《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里讲,“至于外间传说,徐世昌曾秘密赴彰德,往来磋商条件。据我想,袁、徐两人早有默契,似不必再作形式上之会见。且当时亦未听说徐有赴彰德之事”。(《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由此我们不免要质疑王学斌先生“有幸读到徐世昌未刊的《韬养斋日记》”的可能性了。若说王其实并未见到日记的话,除上述外还有两个佐证。一为日记既然“未刊”,王学斌先生又是何时、何地,在什么情况下“有幸读到”的?二为王学斌先生还在文中讲:“1894年9月底,徐赴湖北出差。按日程安排,徐本不必经过武汉,但为了结识湖广总督张之洞,他还是找个由头不请自来……”我早先写过《徐世昌在小站期间的武汉之行》(载《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一文,里面记述了丁酉年八月廿五日至十月廿九日的全部日记。其中也曾记述:
丁酉 七月 廿一日 杨叔峤同年自京赴鄂,过此,来久谈。本约同行,刻余营中有事,中秋后方能南行也。
杨叔峤就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日记表明,七月间杨锐便曾约徐世昌一同“赴鄂”,只不过徐“营中有事”才推到“中秋后方能南行”。如果王先生真的见到过日记原文,就应该读到“张孝达(张之洞,字孝达)制军世丈屡约,未果赴,至是往,晤谈甚欢,留榻节署……”(《徐世昌年谱》,贺培新辑,载《近代史资料》第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的全过程,里面根本不不存在“本不必经过武汉”从而““不请自来”的一丝可能,此种提提法与其在“此事在其日记中只字字未提”的下面编造了“急坏了徐徐世昌赶忙微服出京,赴彰德劝袁袁出山”的故事一样,杜撰的可能能性 较大。
综上所述,日记证明,徐世昌昌可能是积极谋划并主张袁世凯复复出之人,但徐世昌从未秘赴彰德德,袁世凯和徐世昌也没有密谋并并提出出山的任何前提条件。这一一点关系到袁世凯究竟是否真正愿愿意出山以及是否提出了如“召开开国会、解除党禁”等重大政见问问题 ,还是需要搞清楚的。
在《徐世昌与韬养斋日记》书书里,附有戊戌、辛亥两年日记的影印材料,敬请各位方家由此抉以功过之辨。
应该说,日记的刊出,起到了“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