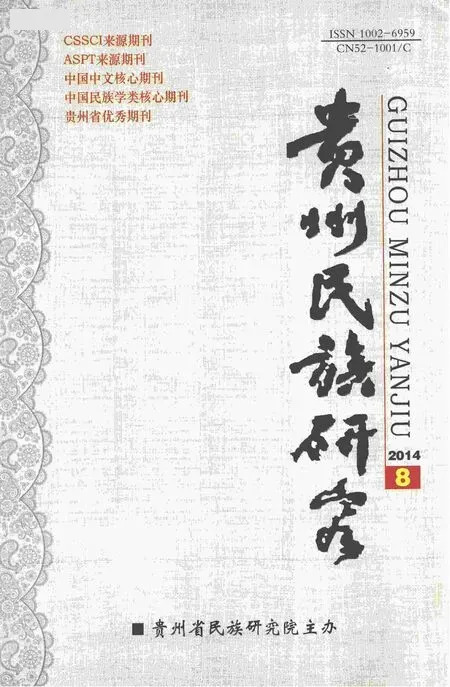权力、空间与知识:少数民族教育的异质性研究
2014-12-03李朝军
李朝军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濮阳 457000)
一、少数民族教育的异质性表征
(一)少数民族教育的权力异质性
教育中的“权力”并不等同于政治经济领域的行政权,而是指施教者的教育表达形式对自身以及后继人的影响能力,即影响知识传达与实践的权力。就少数民族教育而言,教育中的“权力”施加建立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演进的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之上,拥有区别于主流教育的异质性特征。首先,少数民族教育信息的发出具有鲜明的排他性,例如藏族教育明显受到了近代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史的影响,出于对西方传教士的宗教敌对情绪与《拉萨条约》的屈辱经验,藏区英语教育呈现出不容忽视的文化选择现象,主要表现为在英语教课书中剔除英美文化背景,造成严重的英藏对译障碍。“民族历史矛盾与族群偏见给予施教者隐性而合法的权力,压缩、抛弃、篡改知识信息”[1],其后果是致使全球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文化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其次,少数民族教育用以“创造知识系统与信仰体系的基础工具是语言”[2],而语言的言说者将自身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离开来。罗兰·巴特认为,语言是民族教育的“强权”标志,致力于传播、推广、提倡本民族能够理解的生活方式。例如少数民族村社活动中的宗教语言环境,通过讲述、吟诵、讲演、家庭继承等途径对少数民族学生人格特质施加显而易见的影响,维吾尔族人一出生就经历宗教受洗仪式;哈尼族的主要节庆“扎勒特”、“苦扎扎”、“阿玛拖”均源自宗教信仰;藏区学生见面会一边低呼“阿嘎勒勒”,一边诚挚地做出祈祷动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鲜明宗教色彩造成少数民族教育与现代主流教育文化的脱节,语言是“权力”的同盟者,少数民族语言的“场域逻辑”与教育话语权共生,在维持民族认同的共性基础外,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思想,决定着受教育者的命运。
(二)少数民族教育的空间异质性
西方教育的空间理论指出,“国家权力运行的最佳场所是学校空间”[3],原因在于国家权力的运行注定要从宏观理论走向微观体现,从硬性管理走向软性调控,学校是国家决策以教育的形式下放、传播,并以简单温和的手段实施人力资源规训的微观空间。对此,我国民族教育学亦提出了“教育空间”的概念,就少数民族相对封闭的文化空间而言,国家权力依靠少数民族学校的空间控制发挥作用,具有较之主流社会的异质性特征。首先,“学校空间安排是将学生的社会活动场景固定化”[4],使其成为学生的日常惯例。例如校舍、教室、走廊等物理空间;教师的身体姿态、教学腔调、行为偏好等人身空间;历史人物、标语图像、名言警句张贴等精神空间,它们共同产生了以下两个结果,一是纪律性培养,二是意识形态的濡化,即使在偏远地区,国家权力也会无声遁入,但少数民族学校不仅拥有国家意识的表征,还拥有活跃的“民族性”渗透,其中最重要的途径是少数民族学校特有的伦理渗透。例如侗族体育教育的“抢花炮”训练,作为侗族传统运动的体育技能教学,男生与女生不能同场;男生同场教学中的低年级学生不能与高年级学生竞赛,并非出于比赛的公平性考虑,而是体现侗族村寨的社会伦理结构,可见“少数民族学校是从建构社会权威、整合社会秩序的角度来发挥教育空间的最大力量”[5]。又例如少数民族教育对学校作息时间、教学节奏的安排,少数民族学生的家庭劳力与劳作时间没有明显的区隔在学校教育规划之外,学生随时会因为割草、放牲口、看护弟妹等家务工作而机动性地调整上学时间,意味着建立在少数民族教育主体与少数民族文化行为之上的学校规训系统没有真正融入制度化的国家教育结构,少数民族尚未确认自身归属于“国家”中的文化人身份。
(三)少数民族教育的知识异质性
少数民族教育的知识异质性源自“知识的教育不能遮蔽知识产生时的地方性”[6],即教育领域的“知识境遇化”观念,具体的知识在具体的地方性情境中产生,少数民族教育的知识因素“受到少数民族特定教育情境的确认、理解以及保护”[7],其较之主流社会的异质性特征表现如下:第一,少数民族教育中的“知识”与地方性生活联系紧密,外界对少数民族知识的审视必须融入少数民族地方生活空间,否者很容易混淆“生活”与“知识”的界限。例如藏族人对“茶”的认知体系,藏区的喝茶叫‘呷通’,意为“吃饭”,藏人的牛羊肉饮食结构需要茶碱来维持人体酸碱平衡,因此藏族没有“茶饮料”这一说法,藏族生物营养学是将“咖啡碱”、“鞣酸”、“茶碱”等物质划入人体必备营养元素,和现代营养学的归类存在明显差异。第二,少数民族教育中的知识因素拥有大量的民族传统生产技能,随着社会经济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变迁,知识利用的途径与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少数民族生产知识传承却未能跟上社会发展速度,中国主流教育领域虽然也有相似情况,但少数民族教育中的知识流变却出现了明显的扭曲与消隐问题。例如一些少数民族教育从传承社会主流文化出发,在课程编制中以“普遍性”、“中立性”为标准取缔了一些必要存在的“地方性知识”,将有价值的少数民族“经验”排斥在课程之外。例如现代林木生产技术,为了抑制水土流失,提倡绝对的山地植被覆盖率,但诸如苗族喀斯特山区的疏林灌草地带却有必要保留山地斜坡的无植被空间,为苗族游耕提供生存条件。可见,少数民族对所处社会生态与自然环境有着独立的理解体系,其中蕴含着宝贵的民族传统智慧,地方性知识文化格局并不适用“一刀切”。
二、少数民族教育的异质性思考
(一)少数民族教育的隐性破坏力
少数民族教育的权力异质性指向意识形态的排斥以及少数民族“场域逻辑”中的话语权现象,它们证明了教育领域存在无法被忽视的“民族情志力量”。无论是来自社会历史矛盾、族群偏见,还是受到语言环境的禁锢,少数民族教育都显示出与教育目标不相关的、不服从社会期许的隐性破坏力。民族教育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帕森斯认为:“少数民族教育是国家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其存续条件是不能具备泛滥的民族主义情绪”[8],并设置了两个衡量标准来判断民族教育中的“情志力量”是否越界。第一,少数民族教育的意识形态交流是否通过对立、冲突、抵抗等形式出现,并划分社群边界,它意味着少数民族教育受到“去文化”的隐性权力影响。藏族英语教科书剔除英美文化背景,过滤信息承接者与不同信息编码的接触,跨文化交际形同虚设便是属于此类。第二,少数民族教育是否通过潜在的“代表类别的语法范畴”引导固定的知识界定与理解,使得话语干扰教育中的智力因素。少数民族语言强权便属于此类,“其作为创造知识系统与信仰体系的基础工具将自身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离开来”[9],特别是宗教语言在少数民族教育领域的无限延伸导致少数民族教育与现代主流文化的对接不畅。那么如何规避少数民族“情志力量”的越界呢?对此人类学给出的答案是:发生在教育中的“文化簇”具备永恒的不变性,少数民族对地域文化边界的驻守与生俱来,“除非文化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发生改变”[10]。教育发起者的民族身份发生改变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身份地位的对外扩展却能够实现,即依靠少数民族自我发展能力以及文化地位的提升,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得以构建,便会自然具备民族自信,能够理性看待与包容自身传统与外来冲突,教育的“权力”边界便不攻自破。
(二)空间惯性与人力资本边缘化
少数民族教育的空间异质性指向学校教育对少数民族学生“社会化”场所的设计,少数民族学生接受教育的过程受到学校空间的能量惯例,具体表现如下:一是道义与思想惯例,例如少数民族学生区别于社会主流文化的民族价值观出自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灌输;二是智力与思维惯例,例如少数民族学生基于宗教信仰的智力倾向来自学校对少数民族社会习俗结构的继承。三是常态生活与课程惯例,例如少数民族学生处于民族文化课程熏陶、师生关系、教学方式中的身份强化环境。以上少数民族教育的空间惯例既是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对国家权力的服从,亦是少数民族学校对民族价值观、文化道德、等级观念的驯顺,代表着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结构性制约,过度的结构性制约将导致人力资本的边缘化。对此,美国人力资源学家刘易斯亨利指出,没有任何人能对这种结构性制约进行抵制,但提供人力资本的“双边化”却是可能的。人力资本的双边化是指“本土化模式”与“主流化模式”的并行教育,即确立少数民族教育设计的不同目标维度,学校教育既为少数民族当地建设服务,亦为面向第二、三产业的人力资源转移服务,意味着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层次性改造,例如促使课程设置的多样性对应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少数民族丰富的社群活动已足够应付学生的民族文化习得,不需要在必修课程中安排大量的文化内容,技术类、贸易类知识涉猎更有利于打破少数民族学生的乡土认知壁垒。又例如乡镇学校合作、市镇学校合作等地方性教育资源的整合,可基于族际交往实现现代化教育成果的共享,开发学生差异性的空间认知行为。
(三)地方性知识的复原与改造
少数民族教育的知识异质性指向地方性知识的境遇化,一是少数民族教育中的“知识”与地方性生活联系紧密,其相对独立的理解体系很容易混淆“生活”与“知识”的界限;二是少数民族教育中的知识因素拥有大量的民族传统生产技能,相关知识利用未能跟上社会发展速度,表现为地方性知识流变的扭曲与消隐问题。尽管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少数民族教育中的知识流变是为了主动适应社会环境,但我们却必须弄清楚知识适应的基本原则。首先,根据斯图尔德文化内在结构理论,“社会发展变化速度比生态环境演化的速度快”[11],改造地方性知识需要优先考虑生态适应性,而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结构本身便蕴含着突出的生态适应性,特别是对于自然地理环境中世代承袭的知识经验必须得到足够重视,不能轻易更改。例如隋唐五代时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灾害,便是由于古代中央王朝大力推行与当地生态资源利用方式相背离的种植技术,导致环境恶化的结果。对此少数民族教育应通过复原那些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不可替代的、具有高度稳定性与连续性的地方性知识,保护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智慧。其次,复原地方性知识与改造地方性知识应该是同步发生的,斯图尔德文化内在结构理论将知识流变比喻成一个夹心蛋糕,认为“任何知识的流变都是特殊进化与一般进化的复合体”[12],特殊进化是地方性知识的保护性进化,一般进化则是社会需求对地方性知识的适应性改造。例如藏族教育与现代营养学针对“茶碱”类物质的差异性划分,在科学发展的理性框架下辩证地对待教育分歧,应同时做到反映“生活逻辑”与“学科逻辑”两个基础面,完整地向学生呈现地方性知识与学科知识的不同分类。可见,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复原是复原知识的地域性价值,而改造知识则是通过跟进学科发展,满足地方性知识的社会适应性,两者缺一不可。
[1](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金小红.权力分析的特点与文化分析的缺失一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一点思考[J].南京社会科学,2010,(07).
[3]高 蜂.空间的社会意义:一种社会学的理论探索[J].江海学刊,2013,(02).
[4]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5]黄金结.从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问题[J].当代教育科学,2011,(04).
[6]姚 霖.回归位育:学校教育中的本土知识传承之思[J].民族教育研究,2012,(04).
[7]王 鉴,安富海.知识的普适性与境域性:课程的视角[J].教育研究,2010,(08).
[8]麦克·F·D.知识与控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9]马志颖.课程是一种特殊的文化[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8).
[10]杨红英.论异质性人力资本[J].思想战线,2010,(03).
[11]王锡宏.少数民族教育双重性理论与实践探索[J].贵州民族研究,2009,(12).
[12]王 鉴.论我国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及其政策支持[J].学术探索,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