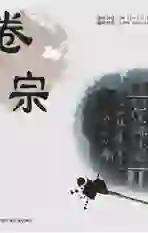苹果:从“时尚神坛”走向“大众流行”
2014-11-19温彩云刘思佳白楠
温彩云 刘思佳 白楠
摘 要:作为移动互联终端的领导品牌苹果,如今正在经历着从时尚消费品走向大众流行商品的过渡阶段。本文从符号传播学的视角,对苹果通过建立完整的时尚体系引发全球范围的影响这一现象进行深入解读,以期破解苹果作为一个时尚符号从“先锋”到“顺从”的神话密钥。(本文原刊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8月)
关键词:苹果;时尚;流行;符号;大众文化
基金项目:本论文得到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B88)、吉林省教育厅规划课题(JLSJY2012G105 )、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青年基金团队项目(12QN043)的资助。
手机市场向来战无常胜。据华尔街研究公司Canaccord Genuity对美国无线运营商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今年5月份美国智能手机市场三星销量首次超过苹果iPhone成为销量之王,这对三星来讲是一个阶段性胜利。回想iPhone5上市首周3日,其500万的销售额便超过4S整整一百万,可之后一直处于依靠降价促进销量的状况。据《广州日报》报道,仅2013年1月份iPhone5的价格就下降了20%,业内人士认为这是苹果创新不足而被迫采取的策略转变。自苹果新总裁库克上任以后,其先后推出的廉价版产品也显示着苹果通过调整价格策略开始走大众普及路线。[1]作为消费者,在做出选择苹果还是三星的决策过程中,究竟什么因素在发挥着关键作用?笔者认为,是时尚的机制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时尚作为一个自中世纪开始就出现的现象,同当今时代内容相互碰撞,从而使苹果成为偶然之于必然的时尚产物。
1 苹果“时尚神坛”的建构
“时尚”作为一个新事物,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与政府的“止奢”法令在禁止非贵族的民众奢侈性攀比的过程中由开始的奏效走向了最后的瓦解,由此这些法令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它们强化了服装和贵重物品作为重要社会标识物的地位。随着19世纪社会大生产的迅速扩张,工人阶级开始走进时尚的领地。从那时开始,时尚逐渐开始了民主化进程,而有关时尚问题的研究也日渐走进人们的视野。[2](P33-34)一般而言,有关时尚的传播路径问题,大致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对于这两种观点,都有众多的支持者和研究者。时尚发展至今,同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使得时尚在当下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而苹果作为这场科技时尚革命的引导者,其时尚体系已相对完备。那么,苹果的时尚体系究竟是如何进行建构的呢?
首先,苹果作为电子科技产品的范畴,它首先表现为科技领域的一场革命,科技自身的特点——电子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电子产品频繁的更新换代——使得它在以科技作为依托的背景下具备了与时尚进行结合的先决条件。在对时尚本质的描述中,新颖和变化经常被提起。康德认为:“新颖性使得时尚具有吸引力。”[3](P21)他认为并非美,而是新才真正同时尚具有关联。罗兰·巴特也赞同这种观点,“每一个新的时尚就是一份对继承的拒绝书,就是对先前时尚压迫的一种颠覆。”[4](P19)因此,“新时尚中蕴含着解放的力量,它将个人从旧有力量中解放出来”[5](P19),而正是由于时尚对“新”的不断追求,使得时尚难免呈现一种非理性状态,“它会为了变化而变化”[6](P19)。从本质上讲,变化即新颖形式之一。可见,新颖性是时尚的基本特点,现代科技产品在新颖性上与时尚的本质不谋而合,因而成为这个时代被时尚幸运选中并借以寄生的崭新的载体。而苹果品牌之所以能将科技的先锋性同文化的先锋性如此完美的融于时尚之中,则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一则由BBC制作的传记式影片《史蒂夫·乔布斯:亿万富翁嬉皮士》很好的诠释了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的乔布斯对于苹果成功的关键性作用。影片从乔布斯青年时期经历的加州反主流文化运动对他日后的深远影响这一层面揭示了一个事实:作为深刻影响到苹果创始人的那种嬉皮士精神与计算机革命千载难逢的相遇最终造就了作为引领科技时尚的苹果品牌的诞生。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掀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主要指当时的青年群体对主流政治、文化、道德习俗采取的反叛和背离态度,他们无视传统和权威,提倡以“新颖”的生活方式同主流文化相对抗,充满抵抗现状和改变世界的先锋性色彩。其时计算机革命刚刚兴起,以IBM公司为主导的个人计算机领域蓬勃发展,IBM公司以严格的模式化管理和用人制度而著称,这恰恰给苹果以一改现存的个人计算机领域传统刻板的世界观的机会。正是乔布斯对计算机革命和嬉皮士运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主流和反主流文化的热爱,才使苹果能够同时拥有科技和文化先锋性的双重基因。[7]
其次,苹果时尚的源起并非单纯的某一类群体所能概括的,其更多地体现为几种力量综合在一起的爆发合力。苹果对以往科技产品的超越可谓遥遥领先,这使它具有当之无愧的革命性的一面,因此,苹果从科技和文化两个角度对品牌进行符号编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包揽技术性精英、社会上层人士以及年轻族群在内的一切和时尚传播有关的发起者们。这三类人群并不是绝然分离的,他们之间既有独立也有交叉,因此,可以将之理解成一个包含了这三类人群主要特征的更广义上的社会群体。由于这一时尚体系归根结底需要建立在商业趋利的法则之上,而时尚运作的最终目的也不过是尽可能多的吸引人群,创造利润,所以,苹果按照不同标准划分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消费人群。当然,苹果最先锁定的这三类目标人群无疑具有某种相似点,笔者认为先锋性特点是他们的共同核心要素。
技术性精英隶属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主要从事或热衷与科学技术领域有关的一切活动。这一消费群体无疑和苹果具有最直接的利益关系,他们的生活方式、信息接收状况甚至价值观取向等都能够同苹果形成协同一致性,因而它们具有创造并追求技术先锋性的要求和特征。而另一类苹果的目标人群——社会上层人士,更多的表现出以财力为基础和展示对象的、在技术和理念的层面上具有一定需求的炫耀性消费动机和行为,他们试图展示的是社会资本的先锋性。对于这种需求,苹果主要通过领跑手机市场的价格区隔策略来实现品牌的高端品质和独特性。有关时尚自上而下传播模式的理论认为,社会上地位较高的阶层为了同社会较低阶层拉开距离进而实现某种创新,而社会等级较低的人们为了缩短这种差距,则不断模仿和攀爬,这就是有名的“滴流理论”(trickle-down)。正如史文德森所描绘的那样:“时尚创造于社会顶层,然后如水般渗透、滴流到各个社会阶层。”[8]我国学者王一川曾在《大众文化导论》一书中提出了时尚生成的条件,他认为,时尚首先“必须经过位居社会较高层次的少数群体对个性化的认同;同时,在大众中存在模仿的欲望和条件。当这两个因素同时具备时,时尚就会生成;而其中任何一方缺席,时尚就无法形成”。[9]这种将时尚看做自上而下的社会过程的理论以早期的凡勃伦和西美尔的理论最为代表性,他们皆认为时尚具有阶级属性,阶级区分应被当做时尚的重要基础和结果。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继续发展了他们的理论,认为应将社会区分置于时尚过程之先,消费是为了显示与一个阶级的从属关系,消费只是差别和差异策略的游戏。苹果正是利用这种自上而下的时尚传播模式实现了将科技和社会地位的先锋性特征建构为时尚符号,为更多的人群追逐和模仿提供了条件。
作为以年龄属性为特征的群体,年轻族群具备思想观念和行为上的先锋性。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70.1%的苹果产品消费者年龄在17至35周岁,偏年轻化是苹果消费群体的显著特征。作为出生并成长于后工业时代(部分地区为工业和后工业交叠出现,如中国)或者消费社会中的一群人,他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理念具有十分显著的后现代化色彩,对传统上所谓的中心和权威感的反抗和解构构成他们观念和行为中的重要部分,他们倾向于通过对象征符号的利用和展示来表达一种社会意见,或者个人实现,以此来标识自我作为个体的独特性和作为某一群体成员所能达成的融合性力量。他们的身份并不根据社会分层标准来界定,而是根据年龄。它更能说明“时尚更多的成为一种个性化选择,而不是对某个特定中心指示的服从”。正如史文德森在《时尚的哲学》一书中所认为的,在即时性文化之中,“时尚的传播模式更多的是基于年龄而不是基于收入和财产,时尚总是从年轻的消费者中兴起,然后逐渐扩散到年长者中”。[10]苹果在1986年和1997年分别制作的《1986》和《非同凡想》两则广告颇为一致的表达了“苹果能够改变世界”这一一以贯之的品牌理念,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是它作为一种先锋性的观念的输出和时尚体系精神支柱的构建性力量无疑代替了众多的年轻族群羸弱的抗争式表达,成为他们众多符号表达式和展示列队里强有力的一支。他们无非是想像布尔迪厄所定义的“个性”那般,“一个人在对品质的对象进行支配的能力中被确定的品质”[11](P120),也就是说,离开被赋予了品质的符号对象,消费者将无从进行“自我教养”,西美尔将之抽象的称为“客体性精神”,他认为“自我是在与世界上的客体进行互动而形成的”[12](P118-119),符号性消费为主体同客体的互动提供了机会,消费对象要融入自我就需要付出更多的符号努力。因而,年轻族群试图通过苹果建立的时尚符号来建立和完善自我的个性就不足为奇了。
2 苹果“时尚神坛”的解构
所谓“时尚”,或许我国学者王一川的解读更能体现其作为一个过程的完整性,“‘时是此时,‘尚是共同崇尚。时尚仅仅表示此一时段的流行风尚,并不意味着永恒。因此时尚具有即时性和当下性特征。”[13](P181)由此可见,时尚是会终结的。如果说从本质上来讲求新和求变是维系时尚生命力的基因,那么当这种新颖和变化的速度一旦无法满足人们内心的渴望和要求的时候,某种时尚也就接近枯竭,代之以另一种时尚的崛起。西美尔曾用“社会融合”和“标明差异”来揭示时尚自身所蕴含着的两个对立的要素,也就是说,时尚既可以满足一个人追求独特自我的个人主义倾向,又同时满足了他寻求群体归属和融合的顺从主义倾向,因而时尚是对模仿和区分的渴望。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和巴伦·伊舍伍德形象地将这两种功能比喻为“桥梁”和“栅栏”。[14](P114)当时尚一旦无法满足人们对模仿和区分的渴望,即他们不能从已有的时尚符号中获取群体归属和自我实现的价值的时候,他们就会放弃对它的利用,那么时尚便终结了。
有关时尚终结的形式,笔者认为可以从时尚内部的瓦解和时尚外部的扩散两个方面来考虑。时尚内部的瓦解是指时尚内在机制受到自身或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不再有效运行,其新颖性和变化性的改变程度放缓甚至停止,最终导致时尚的终止;时尚外部的扩散主要指时尚超越了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而扩散到更加广泛的其他社会群体中间去,使之逐渐变得大众化和流行化。有时,时尚的终结可能会是这两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苹果“时尚神坛”的解构就是这种情况。
首先,从苹果时尚的内在生成机制来看,其科技先锋性开始瓦解。iPhone5相较于四代而言,技术创新方面并没有超出以往的那些范围:机身厚度、重量、处理器等,最大的突破恐怕就是屏幕尺寸由原来的3.5寸发展到4寸,而这个尺寸相较于其他品牌的手机而言也不算新鲜。尽管对于移动互联设备来讲,每一毫米的“瘦身”都是对技术苛刻的考验,但它所达到的效果却未必能够满足时尚的要求。在苹果第四代达到巅峰以后,人们对苹果的期望值也被抬升到一定高度,如果后续的改变低于消费者对其新颖性和变化性的预期,那么,苹果作为时尚运行系统的速度就会减慢,同时更容易被在这两个方面超越或能够弥补苹果不足的品牌所替代。同时,这种科技先锋性的瓦解更多的体现在其受到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为人们的思想观念灌输了更多的有关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内涵。当下,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消费性符号,其传播媒介也日益变得信息化和符号化。在这种背景下,苹果作为移动互联终端已经远远超越了通讯设备的功能,而成为大众文化和流行物的传播媒介,即手机作为一种新媒体已经越来越多地具有信息化和娱乐化的功能。当这种集移动媒体和大众文化内容于一身的产品掌握在人们手中的时候,人们追求的是一种娱乐的、平面而无深度的、大众文化本质所要求的媚俗的、追求感性愉悦的日常审美理想。享乐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抵抗和消解的努力,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已经从劳动“异化”的悲哀走向符号“异化”这一端时,他们便以一种毫无反抗的顺从的方式对一切符号加以接受和利用,并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重新解读。因而,人们对失去外部刺激的时尚符号的原本敏锐的感受就会钝化成对技术创新带来的人性化、便利性的坐享其成以及对大众娱乐内容的追逐。由此,技术的先锋性退居其次,大众文化的强大包容力通过将先锋性归并到消费体系之中完成了对先锋性的符号化任务,从而使先锋性迷失在异彩纷呈的其他符号之中。
其次,从苹果时尚向外扩散的角度来看,苹果的小众消费时尚变为大众消费流行,其主要消费群体的个性被消解。苹果引领的是一场有关移动互联设备科技创新的革命,随着技术的更新,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品牌也逐渐认清了时尚的走向,纷纷投身到时尚的追逐战中。甚至连一些低端产品都已经在效仿苹果,它们的技术不甚成熟,仅仅从外观上进行抄袭。正是这些模仿和试图追赶、超越苹果的众多品牌的“加盟”,使原本只属于小众消费和审美的时尚空间日益变成一个大众流行的消费场所。苹果作为一个时尚符号并不能总是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它可以被人们根据自身的适度性原则而替换掉,转而去寻找至少在某一方面更具新颖性的时尚符号。因此,从时尚到流行,不仅是消费人群范围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时尚作为社会区分的功能在萎缩,先锋者和社会上层人士将试图通过对新的符号的使用而使自身摆脱“乌合之众”。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时尚的扩散并不仅仅表现在数量上的增多,它更以一种观念和态度上的流行性演变来解构苹果时尚。而这种观念和态度上的流行性演变,我们可以描述为经过改造后被消解了先锋性的“个性化”。根据费斯克为“个性”下的定义,“个性是社会事物、语言、性别经验、家庭、教育等等的建构,商品被用来承载已被建构的个人差异感”[15],我们认为,如果前半句是真实的个性,那么后半句就是商品经济下个性的符号化表达,它是一种虚假的“客体性精神”的体现。时尚源起的“新”的观念在苹果这里表现为对中心式、权威感的不妥协,以“改变世界”的信念在科技领域进行革命性的反主流文化实践。它将先锋性融入到产品和符号之中,不仅作为支撑起苹果时尚体系的灵魂和支柱,同时起着为时尚固守个人区分和社会分化的作用。但是随着这种模仿的欲望越发强烈,规模越发广泛,“个性化”实际上也具有了普遍性,人人都追求个性,个性却千篇一律。这时的个性已经彻底沦为对“个性化”时尚符号的追逐,其原来所具有的文化批判属性的先锋内涵已不复存在,“个性化”成为一种人为制造的虚假的商品,用以满足人们模仿的欲望。当“个性化”可以通过追逐和模仿来实现,它就会变得极其不稳定。正如社会学家哈维·弗格森所言:“商品能够成为一种符号,仅仅是因为它已经丧失了内在固有的价值,它的象征能力取决于其内在的无意义。”[16](P127)史文德森也认为,时尚符号并不能帮助人们实现个人认同的构建,因为“这个认同就会像符号价值一样短暂而飘忽。”[17](P127)所以,当对苹果时尚符号的追逐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现象,大众便会为了追逐而追逐,顺从于有关“个性化”的各种符号版本,这时的“个性化”实际上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流行物和符号样本。
如上所述,苹果借助电子科技的先锋性和后工业时代技术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时尚神坛”随着时尚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的变化而逐步消解,但这并不意味着苹果从此无法与时尚结缘,而是说它引领了一场科技的时尚从高端走向普遍的社会化过程。苹果时尚符号从标准的时尚范式逐步走向大众流行,彰显了时尚自身的发展过程和规律。由于时尚本身所具有的时距性和小众性特征,苹果时尚体系的解构终究成为必然。(本文原刊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8月)
参考文献
[1]199IT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中心: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1728.html
[2][3][4][5][6][8][11][12][14][16][17][德]拉斯·史文德森,《时尚的哲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P33-34
[7]史蒂夫·乔布斯:亿万富翁嬉皮士: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3MzAyNTM2.html
[9][13]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9,P180
[15]周宪,从视觉文化观点看时尚,学术研究[J],2005.4
[16]刘力,解码时尚教皇乔布斯,城市·环境·设计[J],2011,12
作者简介
温彩云(1977-),汉族,女,博士研究生,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消费文化,影视传播。
刘思佳 (1988-),汉族,男,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2012级广告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广告文化学。
白楠 (1990-),汉族,女,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2012级广告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广告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