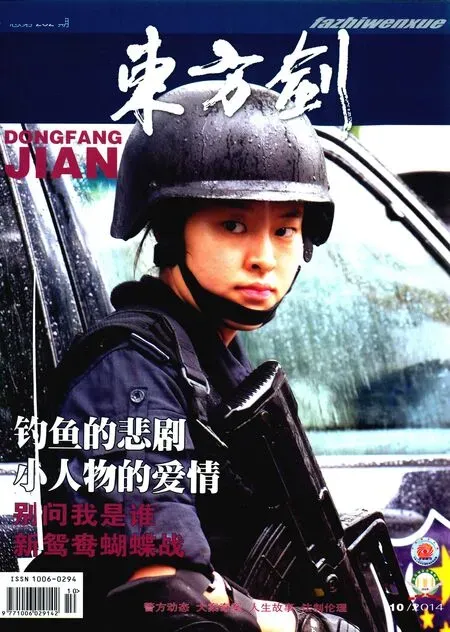沙尘暴带来了什么
2014-11-14李雅民
◆ 李雅民
沙尘暴带来了什么
◆ 李雅民
十月,北方又到沙尘暴频繁造访的季节。大中城市PM2.5严重超标,已威胁到人们的健康,每年沙尘暴到来,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对由人类活动制造出来的PM2.5,各地政府开始采取系列的防治措施。对自然形成的沙尘暴,防治的呼声亦逐年增高,而且认为那是人类对自然破坏的结果,认为通过投资改善环境,最终能够控制住沙尘暴。
沙尘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来自哪里?它是否一无是处?是否能被控制住?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理应正视一下这个年年不请自到、而且令人烦恶至极的家伙。
A:不许说它半个“好”
沙尘暴应是气象部门关注的一种天气现象,但气象部门却不愿再谈有关沙尘暴的问题,数年前发生在纸媒与网媒上一场有关沙尘暴的争论,仍在影响着这里的人们。
据介绍,2007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针对沙尘暴问题发表过一种与众不同的见解。当时他是对一位采访记者说,沙尘暴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所谓制止沙尘暴,实际是违反科学规律的。沙尘暴给人类造成损失的同时,也有其正面效应。说到底,没有沙尘暴就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中华民族。接着他又历数沙尘暴的“正面效应”,如沙尘暴为中国创造了黄土高原;为太平洋浮游生物送去大量营养物质,使得海洋生物种群繁衍不息,等等。这下不得了,因为在民众意识里,沙尘暴问题早已被妖魔化,被视为人类破坏大自然造成的一种恶果,认为必须要战胜之,秦大河讲“不可战胜”,当然不行。何况在我国还有很多部门、很多人为战胜沙尘暴奋斗了数十年,突然间一位国家级专家站出来替沙尘暴“说话”,讲“所谓制止沙尘暴实际是违反科学规律”,这些人当然接受不了,立刻站出来激烈反驳秦大河的观点。
如今回顾并分析那场争论,发现当时尽管秦大河在其言论中强调了我们不能忽略沙尘暴给人类造成的巨大损失,但目前完全消灭它是不现实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治理它,尽量缩小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媒体上还是很快就出现了一批诸如《给沙尘暴翻案凸显空洞理性》、《讴歌沙尘暴,人哭沙在笑》和《学者们不必对沙尘暴大献殷勤》等持批驳观点的文章。如有文章说:“在沙尘暴危害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屡屡经专家学者之口爆出的‘沙尘暴有益论’无疑非常不合时宜”。另有文章说:“每到沙尘暴频繁肆虐的季节,各种各样的舆论总要铺天盖地地袭来。秦大河在这个时候为沙尘暴‘翻案’,赋予沙尘暴崇高的‘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真可谓恰到好处——显然是给那些动辄抱怨政府过度开发、治理沙尘暴不力者,提前打了‘预防针’。”还有文章说:“众所周知,沙尘暴进入公众视野也就近10年的事情,而且华北东北的沙尘暴越来越频繁。甚至今年2月底新疆一列客车在吐鲁番境内遭遇特大沙尘暴,发生11节车厢被大风刮翻的惨剧。如此等等,显然不合沙尘暴数百万年来一直存在的逻辑曲线……给沙尘暴翻案的时空解读,只是将我们引入了形而上的理论境界,是对自然界存在即合理的一家之言。”
除此之外,网上舆论争吵得更是激烈,有人说:“制止沙尘暴不是违反科学规律,只能说是人类力不从心。我认为荒漠不是地球的本来面目,如果考证应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有人甚至说:“把沙尘暴说成是‘科学规律’似有‘伪科学’的嫌疑。”
尽管秦大河是中科院院士,其言论仍被很多人质疑,甚至是攻击。中科院生态专家王如松教授当时发表了一点类似的观点,不想也是引火烧身。那是在华北电力大学举行的一个“绿色大讲堂”上,王如松仅说了“抛开对人的作用性,沙尘暴可以净化环境,还给海洋带去丰富的营养元素”,并说了“沙尘暴的产生不全是由于人为因素”,事后经媒体一报,网上针对这一新闻的议论几乎全是讽刺和挖苦。许多网民指责王如松是在为沙尘暴洗刷“罪名”,从而就是在为人为破坏自然环境洗刷“罪名”。有人甚至撰文扣“帽子”说:“专家们的论调背离起码的立场和常识,其危害并不比沙尘暴小,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宣扬‘沙尘暴贡献论’的专家们,担当了沙尘暴帮凶的角色,因为这会误导公众,使我们在麻痹大意之中,再次错失治理沙尘暴的良机。”
过后,在央视的一个访谈节目里,一位嘉宾发言时也谈到了“沙尘暴有消解酸雨和改善温室效应等作用”,节目一播同样遭致众人反对。一位环保方面的老专家甚至表示要去找中央电视台领导说理,质问为什么要播出如此“荒谬”的言论?
人们憎恶沙尘暴,到了容不得说它半个“好”字的程度。而且直至今日,很多人仍是这样的认识和态度。那么,秦大河等人的说法到底是对不对?记者采访诸多科研机构,了解到一些有关沙尘暴的科学知识。
B:沙尘暴的起源和历史
专家、学者的观点并非不可质疑,问题是质疑之前,需要先以科学的态度查清大自然最真实的面目,也就是说,弄清事实真相,譬如沙尘暴是否自古就有?沙尘暴是否能消除酸雨?是否能给海洋带去福音?等等。
如今一提沙尘暴,许多人立刻联想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的确,人类对大地过度的索取,如砍伐了森林、犁翻了草地、使地表出现了沙化。但在几千、几万年以前,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微乎其微,为何地球各处已经出现了一片片浩瀚无际的沙漠?这就不能不从地球的变迁和气候的形成来研究这个问题。
科学考察已探明,在过去大约1000万年的时间里,印度次大陆一直向亚洲方向挤压,使得青藏地区在不断的造山运动中隆起,最终形成了“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在这一漫长的挤压过程中,逐渐升高的喜马拉雅山不仅隔断了从印度洋北上的湿暖气流,而且大约在800万年前开始导致了亚洲季风的出现。在亚洲季风的作用下,加之失去了来自印度洋湿暖气流的滋润,亚洲内陆日益干旱,历经漫长岁月,青藏高原北部地区的地貌逐渐演化为塔克拉玛干等众多的中亚沙漠,中国西北地区也因常年干燥变成了北半球温带、暖温带中的干旱荒漠区。
生活中有这种常识,烧得很旺的火炉,轻轻一捅,炉灰立刻飞满室内。那是因为靠近炉火的空气被烤热,热空气迅速上升,把炉灰推向屋顶。同样,在春天干燥的季节里,沙漠表面、特别是高海拔地区的沙漠表面,在太阳辐射下温度上升,像火炉一样烤热了地表的空气,热空气急剧上升,形成了垂直的气流。这种气流能把沙漠中的数以吨计的沙尘卷向高空,最高能到距离地表数公里之高度,然后再在亚洲季风的作用下,以沙尘暴的形式,向东方大规模长途输送,最远能被输送到亚洲远东的各个国家,甚至是太平洋中央的夏威夷。
地质和气象学家们对沙尘暴形成与发展的这一推演是否准确?有个最好的例证,那就是中国的黄土高原。过去,人们始终奇怪:在中国,以兰州为中心、面积达38万平方公里的地上,为何能有一片厚达数十到数百米之间的黄土层?巨大的黄土层绝非本地岩层自然风化的结果,那么它是来自哪里?早在19世纪,西方地质学家们来中国考察时,就已注意到中国黄土高原这一奇特的地质现象。庞培利、利西霍芬、奥勃鲁契夫和安特生等地质学家们,曾经常年研究这片黄土,当他们经历一场场的沙尘暴,并沿着沙尘暴来袭方向追溯源头后,认为中国黄土高原的形成原因是,风力搬运并沉积于草原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地质科学家们,发现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其颗粒的粒径,从西北到东南,以逐渐减小的态势分布,由此也增强了黄土是被强风从西或西北方向吹来的推定。此外,中国的地质科学家们还测定出黄土高原的形成起于260万年前。长期从事黄土高原和全球变化研究的地质学家安芷生,把从西部某地黄土高原底部的粉尘取上来进行测定,发现其“年龄”已有800万年。这说明强劲的亚洲季风,千万年来一直在向地球的东方输送着黄色的沙尘。
由此可见,早在260多万年之前、甚至是更早的时期,沙尘暴就已存在于中国所在的这片土地上。而它的产生,是源于地球自身的变化,比如地球板块的运动、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和沙漠与亚洲季风的存在,等等。试问谁能逆转地球板块运动的方向?谁能推平喜马拉雅山脉?而若解决不了沙源和风源的存在,彻底消灭沙尘暴的问题显然就是一种梦语。因此,秦大河等科学家们说得没错——沙尘暴不可能被消灭。
C:沙尘暴是否一无是处
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发展到最后都有一分为二的结果,此乃自然辩证法的法则。地理学研究表明:地壳的隆起让地球某些地域逐渐漠化成沙漠,而起自沙漠的沙尘暴,又在地球其他地区创造出一片片肥沃的土地。
例如,浩瀚的太平洋中有无数因火山爆发制造的岛屿,比如日本列岛,包括远在太平洋中央部位的夏威夷群岛,推算其岛龄,发现它们年轻得难以风化出那么多的土壤,但其岛上又是令人难以置信地生机盎然,科学家们自然要问,它们的土壤来自哪里?检验其土壤的构成,发现竟是来自大陆的沙尘暴,而其中不少就是来自中国的沙尘暴,都得到过中国沙尘暴的好处。另外,诸如火山灰铸就的新西兰,能在那么短的地质时间里演化成可供人类居住的家园,也是得益于乘着南半球的西风、从澳大利亚刮去的沙尘暴。
科学家们查明,分布于世界的几大黄土地带,无一不是沙尘暴造化的结果。那些黄土地带,后来无一不是人类的“面包筐”,种植着养育亿万人口的玉米和小麦。如中国的黄土高原,中国五分之一的耕地集中在那里,养活着中国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此外,还有被黄河从黄土高原上冲刷下来的泥沙铺就的华北平原,更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福地。
除此之外,科学家们发现尽管沙尘暴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麻烦、甚至是灾难,但它少至也在做着三大好事,比如增补养分给土壤,比如滋养海洋生物和缓解空中的“酸雨”。
众所周知,植物生长消耗地力,尤其是在人类集中耕种的田地里,尽管人类的施肥术可弥补地力的缺失,但化肥成分单一,远非自然沙尘养分丰富。动物世界里常见这种场景,海洋许多鱼类排卵,必须要千里迢迢赶到靠近河口的海域,有的还要沿河逆流而上,拼死冲到上游浅滩,不惜遍体鳞伤、甚至是累死。鱼类之所以如此,就为让鱼苗在生命最为弱小的时期吃到足够的浮游生物——河流里、特别上游浅滩处营养物质充裕,浮游生物数量远比海洋里丰富。海洋,特别是像太平洋和大西洋那样的大洋,靠河流补充矿物质营养,规模十分有限,铺天盖地的沙尘暴却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缺憾。沙尘暴飘出大陆之后,其中数以吨计的铁、磷等矿物质,少量着陆于岛屿,滋养上面的植物,其余绝大部分降落海洋,大面积地营养了海里的浮游生物,浮游生物大量繁衍,促进食物链上鱼虾种群的发展,亿万年来,海洋里的生物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
十年前,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对全球变化中“全球铁联系”的研究上取得科研成果,其论文被刊发在美国《科学》杂志上。那是由11个国家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们联合进行的一项科学研究,中国以安芷生为首的科学家们,以自己的研究描述由含铁粉尘联系的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与反馈机制,表明我国内陆频发的沙尘暴现象,虽然对邻近区域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但以全球角度看,由陆地释放的粉尘粒子及其携带的铁元素,通过大气环流沉降于海洋,促进了北太平洋的渔业生产;同时还吸收、降低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为减轻由温室气体引起的全球增暖效应做出了贡献。
2000年至2005年间,中国科学院与日本文部科学省曾合作过一项题为《风送沙尘的形成、输送机制及其气候效应研究》的重大科研项目,工作时,中方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石广玉,曾多次与日方科学家们开玩笑说,不要总是抱怨中国的黄沙给你们带去了多少“危害”,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们还应感谢我们才是。我们忍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将最富营养物的内蒙古浑善达克等地表层土壤的沙尘输送给了日本海和太平洋。如果没有这种输送,海洋浮游生物和鱼类生长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你们不要奢望再吃什么“美味刺身”了。
此外在人们眼里,沙尘暴无疑是恶化空气环境的一大元凶,孰不知正是这个“元凶”,一定程度上也在做着净化空气的好事。人类聚集区域内,因煤炭燃烧、汽车运行而排出的大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高空中与水蒸汽结合,形成含有硫酸和硝酸的“酸雨”。“酸雨”污染湖泊、河流、水库和土壤,影响农林牧渔业,腐蚀建筑、文物以及金属材料制品,有百害而无一利。有意思的是,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人们不明白中国北方地区为何少有“酸雨”?还以为“酸雨”是南方独有的产物。后来科学家们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王自发博士研究发现,我国北方地区工业发达、车辆众多,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并不少于南方地区,较少发生“酸雨”事件,是因为北方地区大气中常有沙尘出现,沙尘微粒中含有较多的Ca2+、Mg2+等碱性离子成分,可以把中国北方地区、包括韩国和日本等地的“酸雨”(pH值4.7)中和成普通雨水(pH值5.6)。
如此看来,沙尘暴对人类社会还确实存在着一些好处。问题是今日人们最关心的是“可吸入性颗粒物影响人体健康”、“大气能见度降低影响交通和日常生活”等“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最需要的是晴朗的天空和洁净的空气,而不再需要沙尘暴去创造什么新的绿洲,更不关心太平洋上渔业丰收与否。所以沙尘暴的功绩在许多人看来不值一提,有人提了,而且是把它提高到“没有沙尘暴就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中华民族”的高度,自然会遭到非议和攻击。
D:应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和对待自然
其实,秦大河、王如松等专家学者,说沙尘暴“不可能被消灭”,本意是提醒人们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沙尘暴这一和风、雨、雷、电以及台风和海啸一样的自然现象,不要把沙尘暴过于人为地妖魔化,进而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再次做出有违科学规律的事情。
科学研究已表明,那些源自地球超级大漠的沙尘暴,人类无论如何努力,也休想阻挡住它们,更甭提“消灭”。而一些源自局部干燥地区、规模小型化的沙尘暴,人类通过退耕还林或还草、以及合理的植树造林等措施,多少有可能降低一些它的危害。
不得不承认,过去在“战天斗地”和“人定胜天”等思想指导下,人们无意中干过一些破坏环境的蠢事。例如在西北地区开荒,愣要把生态脆弱的草原开垦成粮仓,结果薄薄的一层土壤被拖拉机的铁犁掀开,西北风一吹,尘土升天,草原很快被沙化。
问题是如今人们认识到过去所犯的错误,想通过努力纠正自己的错误,恢复环境原貌,但在行动中由于缺乏对自然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同时还有“战天斗地”、“人定胜天”观念,结果再次做出了不合科学规律的决策。
《中国地理》杂志总编辑李栓科是一位地理学家,曾经研究过人类应该如何面对沙尘暴的问题。不久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植树造林是防沙治沙的一大战略措施,但要以科学的态度去实施。有些地方不管当地环境是否适宜植树,机械地套用这一措施,结果树苗年年种,年年死,浪费了大量钱财,环境丝毫没变,而他还在那里坚信什么“人定胜天”。有些地方栽下的树苗倒是活了,甚至成林了,成为“人定胜天”的一大例证,但实际上,从长远角度看,那些树木一是最终还要枯死;二是进一步加剧了那一地区的干燥程度。因为种植树木需要用水,而那一地区年降雨量仅够存活某些生命力极其顽强的野草,满足不了树木生长的需求,怎么办?打深水井,用地下水灌溉。在干旱地区种树是件非常费水的事,浇在地上的水,很快被蒸发;树木从地下汲取的水分,也很快通过庞大的树冠挥发出去,有科学家形象地把它比喻为沙化土地上的“抽水机”。而地下水是不可再生的资源,用完就完了,等到用完之后你还用什么?所以说那些树木还是得死。将来树木一死,地下水资源也没了,那地方岂不是更为干燥,恐怕连野草也活不成了。
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介绍过他们所做的一场治沙实验。2000年,蒋高明带着一支队伍赶到内蒙古浑善达克的腹地正蓝旗时,那里的牧场全部沙化,几乎看不到一根草。他们围起4万亩沙地,开始用传统的方式,设计了一层层的防护林带,还搞飞播,撒山杏、沙棘和沙柳等种子,花了五六十万元,但都失败了。两年后,不想却在圈儿外的一个沙窝子里发现了一种草,那草不是人工种植的,却长到143厘米高。这使蒋高明等人深感意外,意识到只要是禁牧,自然生态就能恢复,自然力比人的力量大。后来,中科院的科学家们把这一发现运用到其他地区的实验中去,结果在其他4个地方的实验中,也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封起来的地方,生态恢复竟比花钱治理的好。随后在几年的时间里,蒋高明和他的同事们在浑善达克腹地中所做的事情,就是将那片严重退化的草场封育起来,什么也不干,那片草场反倒长出了一米多高的青草。
最后,简单而有效的生态恢复实验,让中科院植物所的科学家们理出这样一种理念:即在生态恢复上,撤下“人定胜天”旗帜,释放并利用自然力,是最科学的出路。
然而,这一理念假如能被上升为纲领性的决策的话,那么是否还搞规模庞大、投资巨大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就得重新予以考虑了。可是谁敢怀疑和动摇无数人已经奋斗了多年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呢?秦大河在“两会”针对沙尘暴的发言,就被某些人怀疑是妄图动摇这一“工程”,结果被群起而攻之。
科学家应该是敢于直言的,因此社会舆论应该允许像秦大河、王如松等专家、学者发表以前人们从未听过的理论和观点,而不应盲目地予以否定和攻击。
据了解,目前已有科研机构开始重新审视“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可行性。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科学家们得以与世界同行广泛交流,考察后中国科学家发现,世界上类似于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有前苏联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阿尔及利亚的“绿色坝项目”和美国号称人类有史以来世界级造林工程的“罗斯福工程”等,那些国家的政府也曾做出过通过大量投资植树造林恢复环境的战略决策,但最后除了“罗斯福工程”后来调整策略——放弃人工造林,改为护土、还草和人退——取得成功外,其余全都收效不大,甚至加速了生态退化。所以,科学家们回过头来再看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曾经提出的,把三北干燥地区不到5%的森林覆盖率通过人的努力提升到15%,觉得那是一个“童话”。
我们历来强调要尊重科学。面对沙尘暴,我们似乎确实到了应该重新认识和对待它的时候了。
发稿编辑/姬鸿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