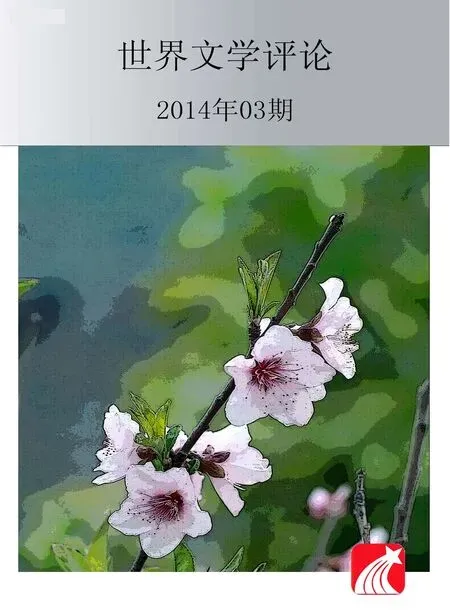传承与坚守:中国艺术精神的脉络
——评孙琪《中国艺术精神:话题的提出及其转换》
2014-11-14张茜宋焱
张 茜 宋 焱
传承与坚守:中国艺术精神的脉络——评孙琪《中国艺术精神:话题的提出及其转换》
张 茜 宋 焱
《中国艺术精神:话题的提出及其转换》一书在文化实践和学术空白的呼喊下圆满付梓;通过三代新儒和中西交汇的融通,中国艺术精神的脉络与走向清晰展现;作品点面结合和开放发展的眼光力透纸背。相信作者孙琪完成书稿的心路历程也恰恰是中国艺术精神演进中融通转化且价值坚守的缩影,因为在字里行间,时时流露的是对人的主体性及其价值的追求。
一、文化实践和学术空白的呼喊
现代新儒学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接续孔孟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牲,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吸收、融合西方哲学,并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及其生命精神为宗旨,谋求中国社会和哲学文化现代化的思想理论的学说。名噪一时的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组成了从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的第一代大陆新儒家;20世纪50—70年代,以东方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中心的第二代台湾地区新儒家达到鼎盛;20是80年代以来,杜维明、刘述先等集中在台湾地区和海外的学者,成为第三代海外新儒家。近30年,对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集中在哲学、文化思想层面,而大陆对于美学的研究主要在2 000年以后。从近10年逐步走热的研究中看到,对现代新儒学第一、二代的美学思想做整体梳理、重构的较为集中,对第三代的研究存在空白;对现代新儒学第二代个别成员美学思想的专门研究较为集中,尤其是徐复观,但对于东方美和唐君毅的美学思想关注较少;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研究仅仅集中在徐复观美学思想上面,而忽略了“中国艺术精神”从唐君毅话题提出、到徐复观深入研究,再到海外新儒家的话题转换这一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性和逻辑性的复杂过程。正是这个学术空白,成就了孙琪的专著《中国艺术精神:话题的提出及其转换》。
今天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不仅仅需要经济走向的产业布局,更重要的是对中华文化与时俱进的价值判断以及在此之上的文化自信心和哲学普适性。在当下热情迎接文化产业的同时,更需要厘清中国文化精神的实质,要知其所以然。孙琪站在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从历史的维度、以极为敏锐的学术触角展示了中国艺术精神在三代新儒学研究谱系中的前世今生;从系统的维度、以极为细致的治学方法剖析了中国文化所集中体现的艺术精神在本体问题和价值导向上的多元表现。这种对于社会热点问题主动的担当魄力和阐释能力,显示了一位学者热诚的社会责任和冷静的理性智慧。
二、三代新儒和中西交汇的融通
《中国艺术精神:话题的提出及其转换》全书围绕“中国艺术精神”这样一个问题,从话题提出、话题的深入研究、话题的转换纵向展开,通过近百年三代的新儒学研究成果、采撷不同时期对该问题的哲学认识和文化价值。
(一)中国艺术精神的提出
20世纪上半叶,现代新儒学阵营中的几位学者都提出了“艺术精神”,比如钱穆、东方美。但是真正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正式提出并做明确阐释的,第一人是唐君毅先生。唐君毅于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著及其后几部论著和文章中提出了终身思考的问题“中国文化精神及其价值”。 孙琪从唐君毅的时代背景和师从关系上探讨其“中国艺术精神”提出的社会基础和学术来源,分析其论断用意有三:①突出中国艺术精神之面目以重振民族文化自信;②说明中国艺术精神之价值,进而摄取西方艺术精神以完成自我发展;③通过中国艺术精神及其价值凸显中国文化精神及价值。
接着孙琪庖丁解牛般地对唐君毅的“中国艺术精神”之内涵进行多层面向的解析。首先通过与宗教精神、科学精神的对比,让贯注于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浮出水面,并赋予其统摄政治、伦理、科学的相通和谐的文化底色和为人生、为艺术的生命意义。其次进入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层面,通过中西对比,将中国建筑、书画、文学等艺术作品虚实相生的特质,转化成审美主体的游心寄意;并进一步在儒道二家中找到唐君毅对“游”的定位——“藏、修、息、游”,即心灵的安顿与性情的陶养,而非精神自由超拔的一面。这正是中国艺术精神的独特之处。再次,反观中国人“有容乃大”、“物尽其用”、“轻巧玲珑”、“和谐共处”等方面的人格美,找到中国艺术精神的本质——中国艺术所显发的人的精神。人格完成的结果既是心灵境界的具现,亦是文化精神的显现。最后,通过唐君毅对儒道的同异分析,展现中国艺术精神的充实和空灵之二面,并为这遭人质疑的论断给出四个庇护的理由,即理论划分的而非实践适用的、艺术体验的而非对立类型的、心性人格的而非文艺形式的、道德价值的而非文本自身的原因,使得两种艺术精神生生相续、超拔转化。孙琪从大处着眼区别艺术精神和科学、宗教精神,获取艺术精神的外在表现;从小处探微,展现艺术精神之主体体验、人格本质和儒道分类;真可谓是“游于艺”。
分析了唐君毅之中国艺术精神的里内之后,孙琪沿着唐先生中西比较的哲学视野,将中国艺术精神的哲学基础推演到“重感通之德、尊生化之理、归中和之道”的中国自然宇宙观,进一步从根源解释中国艺术精神的四个多层面向。在此基础上,从心性观的角度,阐释了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隐在呈现:虚灵明觉心。
唐君毅从哲学到艺术的阐释重在体现生命存在和心灵境界,从本体到价值的书写强调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孙琪最终将唐君毅的中国艺术精神落实到唐先生毕生追寻和凸显的人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为其哲学美学思想画上一个完满的圆形。
(二)中国艺术精神的深入研究
1966年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的出版,让中国艺术精神之主体明确呈现、让中国艺术精神系统构建。孙琪认为徐复观多少受到唐君毅提出话题的影响。面对西方当代艺术带来的精神焦虑和华人将中国画附比西方画派的踯躅不前,他通过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以批判现代艺术,并在人性论的关照中延伸艺术精神。区别于唐君毅的直感研究,徐复观明确的方法意识,除了整体的方法和阐释法这样治史的方法外,还专门使用针对艺术研究的追体法。
徐复观阐释中国艺术精神,既有儒道的区分亦有儒道的整合。徐复观对音乐(艺术)本质是“和”的创造性解释,与对道德内涵并非附加于人性之上的仁义之道、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情绪的重新规范,解放了儒学被专制政治绑架的现实,发现了儒家艺术精神。艺术与道德在最深层面的融合,说明道德不是外加在艺术之上的,而是其本身潜在的因素;道德内在的精神情绪与乐(艺术)均“生于人心者也”。在最高处的统一,说明最高的艺术精神与最高的道德可以自然互通。进而“为人生的艺术”、“尽善尽美”,有效地统一了道德与艺术,成为儒家的“大艺术观”。这样的发现已超出艺术的客观意义,将艺术精神还原到人的精神生命里、内化到中国文化中。从人的完整性出发,强调道德的修养内化和艺术的仁义之心,以道解儒,还原、澄清、解放了儒家“仁义之心”的艺术精神。徐复观从西方美学概念“知觉孤立化”、“主客合一”对庄子美学的关键词“虚静”、“物化”进行现代疏释,并用“逍遥游”来印证美的关照中“知觉孤立化”与“主客合一”的体验;用现象学解读庄子的“忘知”、“心斋之心”、“心与物冥”;用庄子的“大情”和艺术形象与情感和想象这两种审美心理对比分析;提出“以虚静为体的知觉可直透物我存在的本质”、“以虚静为体的艺术精神所呈现的物我和谐状态是对生命的复归和完成”,强调了道家“虚静之心”艺术精神的纯粹性。这补充了唐君毅的以充实为主的道德价值之导向。孙琪对徐复观的儒道的区分分别论之、材料翔实、结构清晰,明确地指出了徐复观解放儒家艺术精神的意义和呈现道家艺术精神的贡献。
在论述徐复观儒道艺术精神整合时,孙琪拈出人格修养、工夫、境界、为人生而艺术四个交汇点,同异共在地细细道来。正因为是为人生而艺术,所以才要投入人格修养的工夫,才有艺术境界与道德境界乃至人生境界在最高点上的回归。最终孙琪将徐复观“中国文化乃心的文化”的文化定位作为源泉,涵盖了儒道艺术精神的区别和融通,逻辑论证圆满结束。
孙琪进一步通过“人性—艺术—人性”这一图示,抽象徐复观自上而下,通过以现代艺术危机的反证、构建中国艺术精神的思路。无论“仁义之心”、还是“虚静之心”,都在人生实践中得到统一、实现生命的复归和完成。
(三)中国艺术精神的转换
徐著之后,“中国艺术精神”从现代新儒学转向到整个华语学界,成为一个承接古今中西的重要课题。唐徐二人阐释“中国艺术精神”中存在的些许悖论,诸如纯粹之心何以承担道德价值、道德和艺术何能并列、艺术何以在精神中隐没,成为话题的转换的内在原因。无论是唐君毅的价值论还是徐复观的人性论,第二代新儒家都强调文化价值的立场,而忽视了艺术的本体。孙琪细腻地发现,在话题悖论、时代变迁和现实变化后,“中国艺术精神”已然在第三代新儒家的美学关照中,舍掉了艺术、保留了精神,转化为生态的话题和文学批评的话题。
随着中国地位的提升和中国文化的传播,从新儒家前辈的忧愤中走出的第三代新儒家,用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西方、弘扬传统。海外新儒家杜维明指出这种转向早在熊十力的自然活力论,梁漱溟以调和折中的态度对待自然的论断,还有钱穆、唐君毅、冯友兰对儒家“天人合一”是对全人类最有贡献的概念的观点中出现,并命之为“生态的转向”。 生态美学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杜维明在《孟子思想中的人的观念:中国美学探讨》中指出孟子修身观念比徐复观之具有道德操练的人格修养,更具中国艺术精神的根本。修身包含“大体”和“小体”的共鸣,人首先要实现自身心与身体的和谐,才能与天地合流。杜维明提炼了修身的社会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并在修身的过程中(即自我转化、自我提升、自我超越),引入了诗意的“相遇”和辩证的“听的艺术”,论证修身的审美性和生态精神的根本。人和世界审美的而非认识的、实践的相遇是一种生态精神的呈现,而这种人与自然的互通性和亲切性的审美体验往往是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修养的善果。“听的艺术”不是人的生理听力,而是听的能力。自然有天籁,我辈唯有闭目倾听、虚静感受;只有无言,才能以欣赏的而非主观的姿态融入自然。用现代话语解读“修身”,就是“精神生态”。
海外新儒家刘述先另辟蹊径,从文学的角度入手,寻求艺术、精神、文化的核心。1960年出版的《文学欣赏的灵魂》,怀着有丰富艺术的同情的心灵,在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经典小说的文学批评中,找到了共同本质、不同形式的精神,即“人性的光辉”。
通过对第三代海外新儒杜维明“精神生态”和刘述先“人性的光辉”的论述,孙琪紧紧回溯第一、第二代新儒学成果,寻找三代学者研究路径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指向。对于儒道、古今和中西,三代新儒关于中国艺术精神的成果体现了从分离到融合的转向,对于哲学和艺术的研究方法实现了“隔”到“不隔”转化。在上述转向中,孙琪更为清晰地展现了海外新儒家的坚持,即对于主体和价值的钟爱。人的主体性是任何时代都要考虑的重大问题,人类无法停止对于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
三、点面结合和开放发展的眼光
随着中国文化的国际性传播的增强和后现代西方文化自我批判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美学、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成为一个颇热的研究领域。杜维明对孟子修身观念的“生态精神”的转化,刘述先对不同国家、时代小说的“人性光辉”的提炼,都是对于古典美学文论的现代转型的尝试。孙琪所选择的“中国艺术精神”的脉络和走向的研究,更是关于中国古典美学、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的生动案例。在研究中,孙琪重点阐释两代代表人物的思想流变,同时对其师承关系和这一时期的整体研究也有所铺垫,做到了点面结合、系统有序。
“中国艺术精神”从唐君毅话题提出,到徐复观深入研究,再到海外新儒家的话题转换,经历“通感之德”、“仁义之心”与“虚静之心”的互补,转化为“修身观念的生态精神”和“人性的光辉”。时代的变迁和现实的变化,亟需“中国艺术精神”理论本身的自我调适。孙琪面对这样开放的理论品质,在研究中也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紧密地联系三代学人提出观点的文化境遇,避免泥古不化的定义和矫枉过正的评价。其次,孙琪继承了唐徐两人比较美学的分析方法,在论证中中西兼顾、古今互现,可谓得中国艺术精神之开放品质的真传。再次,该书附录的参考文献相对全面和丰富,三篇学术论文更是展现了孙琪长期以来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深入关注和对当下美学发展的敏锐警觉,可谓得中国艺术精神“通感之德”的底色。
张茜,兰州交通大学艺术学院,主要从事西部影视的研究。宋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学术出版中心(武汉)责任编辑、策划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