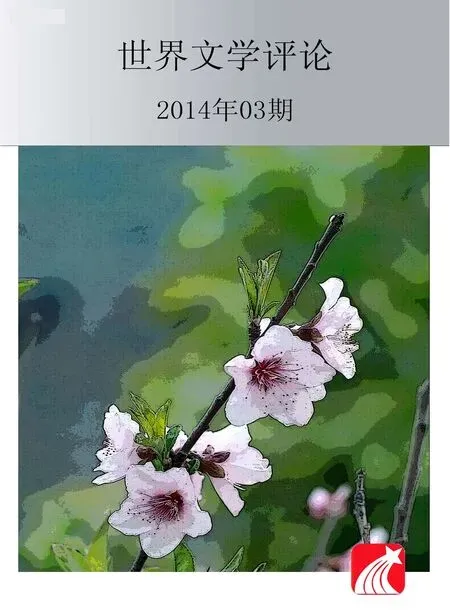城市与文学
——评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
2014-11-14云韬
云 韬
城市与文学——评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
云 韬
理查德·利罕所著的《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以下简称《文学中的城市》)中译本于2009年出版于上海人民出版社,译者是吴子枫先生。这部著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在文学与城市关系的理论研究上的空白。本文就将对这部著作给予初步介绍,以资对国内的文学与城市关系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
一、理论背景概述
理查德·利罕(Richard Lehan Daniel, 1930- )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英文系教授。从他发表的主要著作来看,利罕以研究美国文学为主,兼及现代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文学流派,尤其对美国作家德莱塞和菲茨杰拉德有过深入研究。利罕一直主张重视文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因为美国文学本来就与城市化和现代化密切相关,因此他也比较关注文学和城市的关系,比如他发表的《都市符号和都市文学:文学形式和历史进程》一文。利罕对历史学也很感兴趣,他曾于1990年发表过一篇《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一文,认为存在三种历史观: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认为新历史主义消解历史的结果是造成了三种危险:“时间空间化危险”、太过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语言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割裂。尤其对于第三点即新历史主义造成的作品历史之维的丧失,利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所有小说的发展都可以看成是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小说叙事说明是文化历史变迁的产物。[……]小说产生于中产阶级兴起之时,一个新起城市的商业阶级,不再用传奇的结构去指涉其时代,去歌颂君主、政体或贵族阶级,而转向了以小说的新叙事形式,去歌颂新兴阶级的求爱仪式、婚姻生活、商业运作,并向那些会威胁到他们安全的权力阶层挑战。一个新的阅读阶级创造了对虚构的要求——叙事要求和修辞要求。所以,文学文类的演进和历史的发展是趋于同步的。小说文类走向成熟还和一些“次文类”,即日记、旅游探险、乌托邦文学、讽刺喜剧、古堡小说、乡间小说、成长小说、侦探故事、帝国主义冒险小说、间谍小说、西部故事、硬汉小说、地域小说、科幻小说等相联系。这些叙事的次形式都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将文化理念符码化,而这些文化理念是受制于历史文化变迁的总体模式的。
(王岳川)
这段话与利罕在8年后发表的《文学中的城市》中的观点非常相近。利罕对于新历史主义的反感缘于他对美国当时流行的新批评忽视对作品文化语境的研究,同时他也反对当时文化研究中的精英主义倾向,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和马修·阿诺德等。所以他认为文学作品与产生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可分割,同时,立足于大众的文学作品如德莱塞和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应该受到重视。
以上他对文学与城市关系的思考可说是与其《文学中的城市》的思路一以贯之,这本书可说是对以前文学和城市关系思考的一个总结。《文学中的城市》初版于1998年,这也是据笔者所知利罕的著作中唯一被译为中文的书。利罕的这部作品与当时盛行的城市研究不无关系,那么他是如何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汲取了当时的城市研究和城市文化思想的呢?
随着现代性的进展,西方关于城市/大都会的研究已经受到了很多著名理论家的关注。城市可谓现代性显现的最佳样本。作为空间研究一种的城市研究获得新生,真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以往论者对于时间的关注开始偏向空间。法国列斐伏尔的《城市的权利》(1968)和《空间的生产》(1974)影响很大,认为空间并非如前人认为是自然性的、中性化的、科学化的,而是社会的产物,其中充满了权利与利益斗争的痕迹。福柯在1976年的一个演讲中也认为:19世纪最重要的是时间,而当今应是空间的时代。(包亚明 18)
于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有关空间研究的著作便涌现出来。而空间最具现代性的表现形式——城市,也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对于当代的西方城市研究,按研究内容来看,笔者粗略梳理出几条线索:首先是20世纪城市研究的开创性经典理论,如波德莱尔—西美尔—本雅明系统关注城市中人们的精神状态等经验、韦伯涂尔干马克思对城市的源头即资本主义制度和精神的分析、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等;其次是认为空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和权力斗争的场所,如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研究和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经验,还有福柯的空间权利研究等;再次是美国城市研究中的洛杉矶学派,号称以洛杉矶为典型,研究后现代城市的后都市特征,如迪尔(Michael J.Dear)的《后现代都市状况》(2000)和苏贾的第三空间研究等;再次是城市的信息化和消费性景观,如卡斯特尔的《信息化社会》(1989)和《网络社会的崛起》(1996)、德波的《景观社会》(1967)、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1970)等;最后是全球化和民族志的研究,如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1991)。当然以上分类还有很多不精确和欠妥之处,西方理论家的理论常常是变化万千,想在这里用已有框架来套,难免会挂一漏万。其他还有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沙朗·佐京(Sharon Zukin)和彼得·霍尔(Peter Hall)等都很重要,在此不一一列举。
这种对空间的重视延伸到文学研究领域,再加上视觉文化的兴起,导致了空间文论的兴盛,这也属于城市学研究中的城市文化领域,或也算文学研究与地理学的交叉领域。对于文学的空间背景的重视古往今来并不罕见,这可算是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研究和作者研究的一种,例如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就很重视作品对社会环境的再现性联系,还有弗兰克等著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1952—1981)。(弗兰克)然而利罕等当代西方学者所从事的文学空间学研究却是受了文化研究的影响,认为文学文本和所处环境具有同样的文本性,而且文学与社会并非第二性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是互相影响、互相反映,变动不居的。
利罕的城市理论在西方城市研究中并未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过他的特点在于从文学现代主义及其城市背景出发,其出发点还是文学研究。
二、对《文学中的城市》的分析
这本书分为五编。在第一编“阅读城市/阅读文本”中,利罕梳理了自己的城市观念,提出城市与文学有着相同的文本性,所以可以互相参照。他认为城市有三个发展阶段:商业城市、工业城市和“世界级”城市。新的城市史学家有三种思路:首先是注重现代城市的起源,如斯宾格勒和刘易斯·芒福德;其次强调现代城市的物理法则,如罗伯特·E·帕克和欧内斯特·W·伯吉斯的同心圆观点;最后是关注城市对其居民的影响,特别是城市作为一种心灵状态所带来的后果,如韦伯、涂尔干和西美尔。在第二编“启蒙的遗产”中,他简要介绍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史前史。在第三编“现代主义/都市主义”中,他主要以伦敦和巴黎这两个城市的小说为主体,梳理了现代主义文学在城市发展中的流变过程,这也体现了作家自己对于城市的思考。在第四编“美国再现”中,利罕着重分析了本国的小说,这对科班出身的利罕可谓轻车熟路。在这一编中,他所分析的小说主要面对的都是纽约和西部。这一编又可看到利罕的分析经历了“西部—城市—西部”这样一个循环。在第五编“《荒原》之后”中,他以美国作家品钦为例,表述了后现代小说对城市的反现代想象。在最后一部分“结语——城市的范式:城市过去与城市未来”中,他总结了西方小说与城市共同的三个阶段:“启蒙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与他的历史观是一脉相承的。他还提出自己的与前人如雷蒙·威廉斯的不同之处,即他笔下的城市是一个变化中的而非静态的领域,同时提倡城市的性别研究。最后他宣称:“我们已经从有确定中心的、可描绘的(scriptable)启蒙的伦敦世界,走到非连续的、去中心的、不可描绘的(unscriptable)后现代的洛杉矶世界。”(利罕 383)
这本书运用的理论方法是文化研究与历史主义相结合。其理论特色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点分析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对这本书有着精到的评论,认为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优点在于分析了从启蒙时代的伦敦到后现代洛杉矶的文学中的城市想象,缺点有二:首先是只分析了文学而未涉及其他文化形式;其次是只有抽象的城市分析而没有鲜活的城市记忆。但陈教授的评价有两点不够妥帖:首先,该书分析的小说对象是集中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至于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后现代小说,他分别只有一两章的分析,相对于这些时期西方文学的丰富成就,显然是太少了。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来看,这本书的主体都只能算第三编“现代主义/都市主义”(六章)和第四编“美国再现”(六章)。他注重的是三个阶段“启蒙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中的第二个阶段即“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也与他本人一直关注的文学史领域有关。这使得他的书名《文学中的城市》似乎有点名不副实,似应称为“现代主义小说(兼及诗歌)中的城市”。另外,该书牵涉大量小说和少量诗歌例证,但每篇作品论述得不够深入,似还停留在一般化的观点中。对各国小说分析尤以对美国的分析最见功力。其次,利罕的城市观点还不够深刻和独特,他并没有自己的对于城市的理解,而且从其学术视野来看,他的城市研究还远未涵括当时城市研究的水平。
(二)经典城市理论的城市观
通过研究利罕在该书中对城市历史学的分析(三个方面)和他附在书后的“参考书目”,可以发现利罕的城市观基本上是现代主义式的,他对城市研究的了解只限于笔者在前面梳理的几条线索中的经典理论阶段。因为他的分析对象即现代主义小说的限制,也显现了他的城市观点的倾向。他的书目中甚至都没有提到大名鼎鼎的后现代城市学学者福柯、列斐伏尔和爱德华·W·苏贾。苏贾甚至是利罕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只不过苏贾隶属另一个院系:都市规划系,且为美国城市研究中新兴却势头很猛的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在利罕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苏贾的两部重要著作《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1991)和《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996)已经出版,如此重要的著作甚至都没能进入利罕长达23页的参考书目中。除了利罕在书中提到过的本雅明、西美尔、韦伯、斯宾格勒、鲍德里亚、杰姆逊、勒·柯布西耶和涂尔干,以及他在后记中提到的雷蒙·威廉斯、伯顿·派克、威廉·夏普和纳希尔,他列入参考书目而当今仍活跃的城市理论家及其著作还有: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982),曼纽尔·卡斯特尔《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法文版1972),彼得·霍尔(Peter Hall)《明日的城市》(1988)和《世界城市》(1966),大卫·哈维《意识与都市经验: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历史和理论的研究》(1985)和《资本的都市化》(1985)等。他在书目中列出了鲍德里亚的《类像与仿真》(1981),却不提他影响更大的《消费社会》(1970)和《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同时,利罕还两次提到芝加哥学派罗伯特·E·帕克的城市同心圆学说,的确,利罕在前言中谈到引发自己写作《文学中的城市》的城市学巨著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1961)(更关注城市实体的规划等领域)。在写作的年代,帕克及其芝加哥学派的城市学研究还占有重要地位。
(三)性别意识、大众文化、信息与消费社会和后殖民研究的缺失
利罕重点分析的西方作家中,除了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之外,竟然清一色都是男性作家。好像是已经对自己的这一疏漏有意识一样,利罕在该书的结语部分,在第二节中介绍了城市研究中的性别研究。但是,他的介绍非常简略,只提到了布兰奇·哥凡特(Blanche Gefant)所考察的女性主义对于都市的修正。利罕自己也承认:“至少到最近为止,城市依然被认为是男性而非女性活动的副产品。”利罕认为相对于男性活动的商业区,女性更集中在住宅区和沙龙中。另外,在利罕有限的城市学积累中,并没有包含当时已经影响颇大的两位女性城市学者:沙朗·佐京,拥有重要著作《城市文化》(1995);还有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写有《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1991)。虽然她们并不是从女性主义角度来介入都市研究的。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就表达了对城市的女性化体验,认为女性更为日常化的细致体验使得女性比那些建造和设计它的男人们更能懂得大街的真谛。作为当代文化或文学城市研究的一种,利罕的这本书并未涵盖足够的理论空间,具体表现在性别意识、大众文化、信息与消费社会和后殖民研究的缺失上。不过,这一缺憾,在他的新著《文学现代主义和彼岸世界:幻象的延伸和文本的领土》(2009)中已经得到了部分的修正。这本书的17章中,利罕用了最后的4章分别介绍了后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性别和种族等内容,但此书还是侧重分析文学现代主义。
总之,利罕对文学现代主义所表现出的城市现代性的发展进行了相当全面的历史梳理,如果我们也能从城市研究的角度出发进行北京或上海的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书写,将会是有益的研究。在中国,文学的城市研究也兴盛起来,已有的经典成果莫过于赵园的《北京:城与人》(1991)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1999)。近些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有关上海的城市研究和城市文学研究都进行得如火如荼,著作层出不穷。北京由于相比上海现代性显现稍显滞后,这方面的研究也进展缓慢。但从新世纪以来,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已经开始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和校内课程来推广北京的城市文学研究。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它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凸显出来,我们应该引进更多有关这方面理论的梳理成果,这样才能对我国文学与城市关系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借鉴。
注解【Notes】
[1]《斯各特·菲茨杰拉德和小说工艺品》(F.Scott Fitzgerald and the Craft of Fiction,
1966);《西奥多·德莱塞:其人和其作》(Theodore Dreiser
:His World and His Novels
, 1969);《危险的混合:法国文学存在主义和现代美国小说》(A Dangerous Crossing
:French Literary Existentialism and 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
1973);《名著研究系列——〈了不起的盖茨比〉》(Masterwork Studies Series
—The Great Gatsby
,1989);《了不起的盖茨比:奇才的局限》(The Great Gatsby
:The Limits of Wander
,1990);《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1998);《文学名著导读:嘉莉妹妹》(Literary Masterpieces
:Sister Carrie,
2000);《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转折时代的小说》(Realism and Naturalism
:The Novel in an Age of Transition,
2005);《文学现代主义和彼岸世界:幻象的延伸和文本的领土》(Literary Modernism and Beyond
:The Extended Vision and the Realms of the Text
, 2009)。[2]“其实,讨论文学与城市的关系,除了作家的生活体验,还有思潮的崛起、文体的变异、作品生产及传播机制的形成、拟想读者的制约等,所有这些,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Richard Lehan所著《文学中的城市》,均多少有所涉及。该书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存在的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从‘启蒙时代的伦敦’,一直说到‘后现代的洛杉矶’,既涉及物质城市的发展,更注重文学表现的变迁。作为现代都市人,我们在阅读关于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中成长;正是这一对城市历史的追忆或反省,使我们明白,城市的历史和文学文本的历史,二者之间不可分割。作者讨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学史上的城市,侧重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寓意的分析,也关注生产方式的改变对于文学潮流与文学形式的深刻影响。但因太受‘文学’二字拘牵,毫不涉及对于都市想象来说同样至关重要的绘画、建筑、新闻、出版、戏剧等(即便作为参照系),其笔下的城市形象未免太‘单面向’了。另外,相对于精彩的城市功能抽象分析,‘文学城市’伦敦、巴黎、纽约等的独特魅力没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实在有点可惜。”陈平原:《“五方杂处”说北京》,选自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页。
[3]比如他于2001年和2003年分别开设了“北京文化研究”和“现代都市与现代文学”的专题课,还于2003年与国外机构联合主办了“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的国际学术会议。值得一提的是,他开设的专题课上,所开列的9本重点书目中就有这本《文学中的城市》,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汉译本。
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盲区》,载《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包亚明:《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美]弗兰克:《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秦林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美]爱德华·W·苏贾著:《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美]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云韬,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新时期文论与美学、20世纪中国文论与美学。)
作品【Works C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