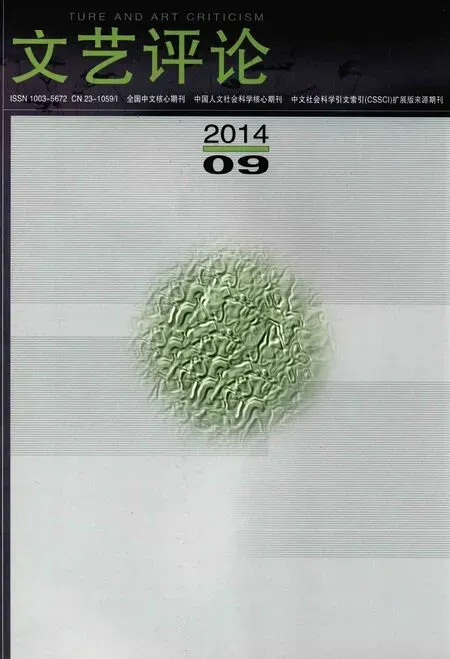“文心”的演绎与寻绎
2014-09-29王晓兵
○王晓兵
一、题释
“文心”的演绎与寻绎,把密切关联的两个课题对接在了一起。从学理层面考量,前者是由文学创作角度切入,探索作家内心奥秘的文本呈现;后者是从接受美学的视野关注读者的价值取向和阐释水平,感悟作家心之所系。作家有了“创作发现”,把独特的意念在心里孵化、孕育,致力于施展文字表现之功,调动各种笔法描摹人事景物,表现情思理趣,使自己的“文心”跃然纸上,按时下的新鲜说法,是予以精彩“演绎”。读者(尤其是批评家)“披情入文”,对作者铺陈在字里行间的文旨诗意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寻绎,关注人物的命运遭际,揣摩作者的谋篇布局,欣赏情思与辞采的互相映发,与作者的心思接触,品味出深藏在书卷里的“文心”,获得审美遇合、对晤之感受。说得雅致一些,此乃“寻绎”。
何谓“文心”?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寻绎作家的文心,是经由文本的通道走进作家心里的过程。脱稿后的文本虽已是独立的存在,但著作者的情思、心结已浇灌在里面。真正会读作品的读者,要解读、要体悟的是作家的本意,要触摸的是他的“本心”。袒露直白的、一目了然的文本阅读,会丧失许多意趣;拨开层层迷雾见到“庐山真面”,既能满足探索者的追求,又能丰富文本的内在意蕴。所以,那些庸常之作,吸引不了我们的目光,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那种人云亦云的套话,或一味猎奇、明显曲解文意的貌似新颖之作,也难入开拓创新之林。
夏丏尊、叶圣陶先生的《文心》有段话说到阅读、写作要重“触发”——“读书贵有新得,作文贵有新味。最重要的是触发的功夫。所谓触发,就是由一件事感悟到其他的事。你读书时对于书中某一句话,觉到与平日所读过的书中某处有关系,是触发;觉到与自己的生活有交涉,得到一种印证,是触发;觉到可以作为将来某种理论说明的例子,是触发。这是就读书说的。对于目前你所经验着的事物,发现旁的意思,这也是触发。这种触发就是作文的好材料”。所以,有触发、能触发,是进入“创意读写”状态的前提条件。
小说家的语言,是神奇的魔杖,能点化出意趣盎然的全新空间。他揉捏语言的泥团,抟出各色人等,灌注进生气,便栩栩有神。他安排情节,设计细节,给环境配置声光色,他是自己小说世界的造物主,内心剧情的编导演,心里有了谱,喊一声“开始”,精彩的戏剧便开演。文字的精灵翔舞到纸面,然后各就各位,等候高明读者的观照、端详,转录到心里。每一部新作的诞生,都经历从无到有的奇妙过程,都是从生活真实向艺术真实飞升,期盼最后能在读者心间留下美的印象,喜怒哀乐、生死歌哭、低回高昂都难忘。
不同风格的作家,他们对于人生万象的演绎各具风采。领略小说中的人与事,能感受作家迥异的创作个性、观察视角和语言风貌。钱先生写《管锥编》、《谈艺录》援引人所未闻的古今中外资料,一条条联翩而出,那是钱氏风格的旁征博引,最诱人、最地道的语言盛宴。《围城》第三章,方鸿渐听褚慎明和苏文纨在客厅里高谈阔论,一个引英国的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另一个引法国人的话,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干男女口吐莲花,未必真懂奥义,这些话语实际是钱钟书安排书中人物作为谈资来卖弄,真正的“围城”意蕴作者会在后面逐层演绎,揭晓。
散文与诗的演绎,也凭靠语言的魔杖点化心灵。读余光中《听听那冷雨》,仿佛也随他撑一把雨伞,“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那淅淅沥沥、点点滴滴敲响在屋瓦上的雨的音乐,触动的是游子对故国的深情思念。恍惚间,想起了戴望舒的《雨巷》:“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视线触着“彳亍”二字,感觉用得极好,对母语字形审美,发现颇像两人撑着伞在雨巷相遇,其中一把伞还歪了一下,让丁香姑娘翩然而去……
二、例说
阿·托尔斯泰曾把“凭借内心的视力来看描绘的对象,来创造作品”看成是“作家的法则”。作家凝聚在对象身上的“内心的视力”,不只是观察力,实际是审视笔下人物性格命运时的思想力和造型力,最后凝结成栩栩传神的“内心视像”。因此,我们寻绎作家的文意“本心”,还要揣想他的心路历程,理解他的材料获取、深度加工和思想形成的来龙去脉,把深刻的内容和“有意味的形式”一并观照。
蔡元培先生为《鲁迅全集》作序时,尊称鲁迅为“新文学开山”者,说“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为快”。因为“环境的触发,时间的经过,必有种种蕴积的思想”,只有通过创作来发抒。他人苦思力索而不易得的“思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鲁迅先生都能凭着天才、实力“很自然地写出来”,“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蔡先生的话说得极精到。引进本文语境,那“蕴积的思想”可以理解成作家要着力表达的“文心”;那“无数法门”,也即作家的文学演绎之精艺。
我们以鲁迅小说《药》的写作为观察点,来寻绎鲁迅“文心”演绎之历程。一个值得发想和索解的问题是:鲁迅当年“弃医从文”的抉择十分坚定,为何在十余年间没有诉诸文学叙事的表达,准确说,小说创作何以晚于杂文呢(鲁迅杂文出手快、下笔狠是著名的)?鲁迅创作的母题是透视国民性问题。鲁迅论及自己小说材料的来源和写作目的时说“多采自病态的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追溯鲁迅思想的原点,一般认为是发端于1906年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书时,看了触目惊心的幻灯片。那血淋淋的杀人场面,包括四周“围着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看客,烙印成鲁迅抹不去的记忆。他由此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鲁迅确信“第一要着”是在改变国民的精神,为此,“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日本学者据此认为,鲁迅获得思想认识的基本素材和各种见闻、经验,是留日期间形成的,这些成为他以后创作的重要根基(见《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第二编第一章)
陈丹青说:“鲁迅落笔,靠的是锐利的想象和内心的剧情。”鲁迅留学日本,心忧华夏故国。他耳闻目睹“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不光有幻灯片上所见的杀头场面,还有1907年夏季徐锡麟、秋瑾的接连被杀。世事愈来愈骇人听闻,这血腥的杀戮,屠场就在鲁迅家乡绍兴街市轩亭口。回国后十年间,鲁迅虽未先用小说叙事来表现它们,然而,他“内心的剧情”却酝酿得愈来愈充分,等着进一步蓄势、演化。他研读域外小说和本国古籍小说,吸取写作经验,锻炼从内容到形式的独特想象,筑着自己的文学梦。在绍兴城府中学(附近就是埋葬男犯和女犯的坟场)任教期间,鲁迅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后来到北京,还间接、直接地参与了《新青年》的部分编务。鲁迅对病态的中国社会及不幸者的观察日臻深入,他所积淀下来的人生故事和人物原型,是可供几十篇小说去刻画的,而且每一篇都设想用新的形制来演绎自己的思想情感。鲁迅沉潜在思想淬炼和形象塑造的创作状态里,为营造自己的小说世界准备着。经长久的蕴积和各种“环境的触发”,最终激情喷涌,迸发为《呐喊》和《彷徨》两本小说集,汇同数不胜数的散文和杂文,蔚为大观。
1918年4月发表的《狂人日记》是鲁迅小说的首次演绎。狂人对大哥说到徐锡麟“被吃”。又说“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狂人所说的城里传闻,虽然是一句话讲一件事,内在关联还不甚分明,但已经透露出基本的写作信息,里面蕴藏着重大的“写作发现”和“创造构想”有待后阶段发掘。鲁迅没让狂人提及秋瑾不会是淡忘,很可能是他想积存着留等后用。一年后写《药》,果然化用这些传闻作了故事胚胎,《狂人》篇也因此与《药》承前启后地有了“互文本”关系。把秋瑾原型转换塑造成夏瑜,完全符合小说家的叙事艺术逻辑和文学演绎技巧。鲁迅在《药》里写轩亭口众看客伸长了脖子看斩首示众一幕,犹如他那个时代的“街头实拍”。鲁迅摄取生活和历史真实演绎成了小说场景,用文字描摹出血腥杀戮的现场,把自己当年在日本看的旧画片里中国民众围观杀人的情景演化成可以让读者目击的文学写真,具有逼近真相、透视本质的作用。
受多年来郁积在心的思想情感推动,小说的悲剧架构呼之欲出。其中微妙的“创作发生学”的心理内况,我们不难把它揣想出来:怎么在犯人和生痨病的人之间建立联系?买“人血馒头”当药“蘸血舐”是个最有可能产生关联的重要设计。两个家庭,两个儿子,两个母亲在墓地相遇,是最得宜的巧妙构思。鲁迅为了表现自己的思想主题,他在结构《药》的小说框架时,敷设明暗双线,从华家到刑场,再到茶馆和坟场的戏剧场景设置,把华、夏两家的悲剧故事组织起来;还通过众茶客议论纷纷,对不出场的夏瑜在狱中的表现作了幕后处理,这是鲁迅间接写人的演绎策略,实际也是请读者参与对人物的塑造,对主题的解读。小说以“药”命名,对题旨探究的意向(究竟什么是救国救民的良药?)已很明显,通过情节演绎和场面调度,读者理解小说主题不会有多少困难。再拓开去寻思,笔者倒是觉得对《药》的结尾还可进一步玩味。按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的说法,这结尾是“最富想象力的高峰”。华老栓买了蘸着革命者鲜血的馒头制药治小栓的痨病,依然无法挽救其夭亡的命运。结局是,华大妈、夏四奶奶都到坟场祭奠儿子,相对默然,气氛凝重,笼罩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悲剧味甚浓。作家并置了两个家庭的悲剧,让我们不禁欷歔,感叹“伤逝”:两个年轻的孩子都失去了生命,白发人送黑发人,真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革命志士考虑国家命运,为人父母更多担忧孩子的存亡,国与民的命运怎样才能真正地生死攸关?此取人性、人道的视角,不只是蹈袭阶级、社会学的解读。不知庶几可贴近“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作家“本心”乎?
有所争议的是夏瑜坟上那个花环,不知谁人所祭献。据鲁迅谈及该小说创作时所说,是为小说添加些“亮色”。也有说是向往革命的年轻人,暗自献上花环表达对先驱的敬意。这样的解读,听起来言之成理,但小说里的人物均无这样行事的可能(夏四奶奶说“这地方有谁来呢……亲戚本家早不来了”)。周作人也说那时乡里百姓吊祭不可能献花圈。依笔者看,这花环就是作者祭献的,是鲁迅采用了“曲笔”演绎法,情不自禁地要表达自己由衷的心意。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演绎”与“寻绎”,《雷雨》是个好例。曹禺在开篇写了四千多字的“序幕”,全剧因此而成为倒叙结构——从飘雪的寒冬,回溯郁热的酷夏(四幕戏,从清晨到子夜,时仅一天),最后再返回开场时的冬季(那是原著的“尾声”)。剧作家一开始就用季节、气温以及教堂医院那间特别的客厅来参与剧情的演绎,带有环境设置和主题隐喻的双重涵义。那摇“慢镜头”的方式,也是曹禺惯用的对于舞台设施琐细说明的手法,他不厌其烦地把门窗、帷幔、壁炉、画轴、地板、桌柜椅凳及摆件都一样样地巡视过去。这里原本是一所旧式公馆,现在改作教堂医院,楼上楼下住着一疯一痴两个老妇人。在过去的日子里,府邸的主人曾先后爱过这两个女人,许多充满温情复又演化为悲情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他陶醉过,享受过,威风过,也愠怒过,颓丧过,无奈岁月荏苒,物是人非,如今他已垂垂老矣。剧作家通过两个修女之间以及姐姐弟弟的对话,来带出发生在这大宅门内的陈年旧事(情情爱爱,恩恩怨怨,包括一夜死三人的悲剧)。只是,那时的观众还不熟悉这样的戏剧叙事和表演所采用的时间流转的方式。即便现代人,也不习惯这样缓慢地去看一出家庭悲剧故事的“前世今生”。更何况,其“序幕”耗时也太过冗长,其“尾声”又那般神秘,于是,接戏的导演把它们都删削了。据曹禺形容,像是“斫去了头尾,只剩下直挺挺的一段躯干”,他为此深表遗憾。
应该指出的是,毕竟也有人孜孜以求地寻绎戏剧大师的“文心”。70年后,王延松导演对曹禺原著的经典意蕴有了独到的阐发,他大幅压缩原剧内容,恢复了“序幕”和“尾声”,还添加了“唱诗班”的形式,使《雷雨》在新世纪的话剧舞台上,演绎出了别致的光彩。
回顾与概述这段作品创作与接受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文心”的演绎,与读者、观众、批评家对其意图的最终寻绎和解读是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的,当然也可能遇到知音而认同。遭遇前一种命运时,诸如“周朴园专制、虚伪”的阶级论、社会学分析等会由此而来。但是,如果全按着剧作家原来的构想在舞台上尽兴演绎呢,也会受到人性论、“宗教至上”说的指摘。
依笔者看来,文本的阐释不应取“非此即彼”的裁断模式。搁笔等待开卷,作家“文心”演绎完毕,评者尽可独抒己见,彰显审美的个性,只要言之成理,甚至可以让原著者也刮目相看。譬如说,“序幕”与“尾声”不必全恢复,可取作者部分原意,在剧情临终时加个简短的“尾声”:老年周朴园以“凭吊”的情怀重返故地,他要缅怀像活化石一样的曾经的爱侣。毁与悔,不仅是两个切肤之痛的词,更是两把尖利的锥,前者真的毁灭了爱,后者则凌迟着老者的心。可以唤起悲,也可唤起悯,悲天悯人于一体么?
曹禺最初的创作基点“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他和自己的笔下人物一起浸入情爱恩怨、生死歌哭的剧情演绎,这完全是受戏剧规定情境和人物性格命运的支配,被“情感的汹涌的流”推着,及至创作完成后的反观和反馈,与前面所经历的过程轨迹也不会全都一致。他曾说要从人物的表面看到其内心,从人物的“此一时”看到“彼一时”。所以,我们要体悟剧作家的良苦用心,也得到《雷雨》的原初构架里去寻绎,包括主要情节的“飓风”刮过后的劫后余生,终场时的余音。
从先前的周公馆变为后来的教会医院这一笔设计来揣度,曹禺确实是把人与住所紧联在一起写着历史化的人生。那我们也不妨对这所老宅悉心体味一番。它是周家的物质外壳和血缘关系的载体,因而也是一个重要角色。三十多年来两代人浸淫其中,由温情抚慰,到悲情不断,大宅门里的故事波澜迭起。这是生活和人性空间的历史存在和必然参与。曹禺曾经想把“雷雨”算作这出戏的第九个角色,那么,这周公馆(十年后的教会医院)就该是第十个角色。30年光阴流逝,一所老宅见证了历史变迁依然默默存在。隐秘与裸露的人性都曾在此时间空间交集点上得到演绎。从作家对剧中人物性格分析及角色特征的说明性文字里,我们可以寻觅到那些能透露心迹的话语。第一幕里,曹禺就通过剧中人的言语,表达了各自对于老屋的意识和情结——周冲同他母亲(繁漪)说起父亲(周朴园)要搬家的事。此后,周萍又说想离开这个“能引起人的无边恶梦似的老房子”;而繁漪却感到“这老房子很怪,我很喜欢它,我总觉得这房子有点灵气,它拉着我,不让我走。”所以,对这所古井深水似的、会闹鬼的老房子,是很有文章可做的。经一番血缘、情欲、利益的交搏,人伦纲常的秩序倾倒,老年周朴园孑然一身,与老宅配衬得晚景凄凉。
《雷雨》“尾声”的设计,考虑观众接受时的情绪调节,增加了调整认知的可能性。剧作家希望观众和批评家不要被这四幕戏感染得过于悲切、沉重,欷歔、哀叹,若能升到上帝的视角来俯瞰人间,拉开“欣赏的距离”,就会从“形而下”看到“形而上”,看一群蠕动在泥沼里的生物是怎样煎熬、挣扎,感悟那纷繁人世背后神秘的命运主宰。这样去看,是否也是揣摩曹禺把剧当诗写的“文心流露”的一种角度呢?
三、衍义
以上研读、探究及表述,不以某派理论为圭臬、某家学说为尺度,而是既注意作家同历史与现实的实证关系,也关注文本内部具体演绎的部分构成要素(语言和形式,开头与结尾,画面与隐喻,等等),并贯彻接收美学的理论原则,重视读者的接受和影响。说得形象一些,好似钟摆一样,从作者一端移向读者一端,来回往复摆动,中间划过的“扇面”,就是文本,是它连接着读写两端,因而,本文是两端加“扇面”的“扫描式”观察述评。
作者的心和读者的心如何互相映照?谁能精确地获知对方的内心感知?把演绎与寻绎的关系放到新阅读时代来看,这个问题的解决仍要经历长期的探索过程。从理想境界来说,“演绎”方和“寻绎”方的信息传递应该是交互的。若按照新的评价模式,从早期的作家创作论、作品的外部和内部研究,到后来的读者理论、接受美学,直至进入文化产业大时代,对于作品的制作、传播和观赏信息的回馈,是要纳入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影响扩散的整个流程来观照的。一方面是追逐创新潮流,另方面是重读经典名著。具有典范意义的大师杰作会被各个时代的读者反复阅读(当然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读,早期的解读意见仅作参考),而产自新媒体、大数据时代的作品,却可能遭遇读众的碎片化快速消费,甚至被海量信息所淹没,得不到确切的反馈。
按照接受美学的理论逻辑,文本中的“未定成分”或“空白”,是可任读者发挥想象的地方。读者的能动作用表现在他虽没参与最初的创作,但他的“阅读修养”和“阅读发现”却可以使文本意义得到阐发而成为新的作品。作品演绎完成,期待着阅读评价,作者的心意不一定全被理解,读者的反应也不会全被作者接受。文本阐释是“既济”与“未济”的反复演进过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的慨叹道出了创作的甘苦以及对知音的期待。“未济”在“既济”之后,正体现了不息运转的动力。知其一,亦知其二;知其表,亦知其里;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知其此一时,也知其彼一时,这种种“知”,是一步步探索作品底蕴的过程性推进。感性品味,知性领悟,让“演绎”者与“寻绎”者对于本体的生命形态与直觉的艺术形式获得通透的理解,读与写两个活动主体之间互通款曲,此能知彼,彼也能知此,这应该是双方都期待的审美感知“视域融合”的高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