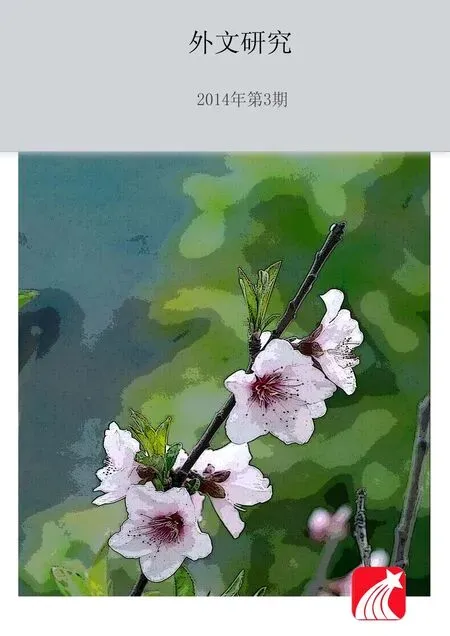更科学地看待语言:符号缺陷与象似表征
2014-09-17上海海事大学刘国辉中国计量学院徐晓燕
上海海事大学 刘国辉 中国计量学院 徐晓燕
1. 引言
人类自从有了自身语言之日起,就希望它能如实地记载周围所发生的一切,而不管这种语言源于神授说、拟声说、生物进化说或拟象说。但真正从研究角度来系统思考这个问题的应是当前的认知语言学,因为20世纪末出现的认知语言学之实质与基础在于体验认知,而体验再现需要语言表征,于是语言的象似性研究被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在国外,Haiman(1985a,1985b)出版的两本书《自然句法》(NaturalSyntax)和《句法象似性》(IconicityinSyntax)系统地对自然语言句法中所存在的象似性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意义相近,形式象似”原则,使得象似性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与此相应,王寅教授的两部著作《论语言符号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与补充》(1999a)和《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2009)把国内的语言象似性研究也推向了一个高潮。那么,语言的象似性描写是否真的如此理想呢?为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从3个方面对其进行再考察:语言符号缺陷、补救策略和语言象似性。这样,我们也许能找到一个对此更科学而合理的认识。
2. 语言符号缺陷
正式讨论语言符号缺陷之前,我们有必要再次正视语言的功绩——语言使人成其为“人”,同时使世界“有序”可知。正如韩宝育(1987)所言,人类思维和认知水平之所以能达到目前这种程度,没有语言的伴随和介入是很难想象的。正因为语言符号的作用,人类才从狭隘的直接感知圈子里解放出来,使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未曾直接体验的东西,表达自己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人类思想和思维水平才达到空前的高度。因为世界原本是孤独的球体,没有语言,也没有人类,后来有了语言,便产生了人类,客观世界通过语言与人类联系起来。人类不再雷同于那些孤独的、寂寞的动物,不再像猿猴模样的祖先那样仅拥有一个狭小的天地。从此,人类在世界上找到了真正的“人”自身。(廖体忠1991)当代文化哲学家卡西尔(1985:42)也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signs)做出条件反射,而人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有意义的“符号”(symbols),于是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因此,希腊人把“人”定义为“会说话的动物”,而把野蛮人称为“barbarian”,意为不会说话、只会吧吧叫唤的生物。(余志鸿 2008)也就是说,人类文明依赖于符号和符号系统,人类的心灵与符号的作用不可分割,即便我们不可以把心灵和这样的作用等同起来。(Morris 1938)既然语言符号有如此成就,能否因此认为这种符号就完美无缺呢?其实不然,因为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经常感到处于“妙不可言、言不尽意、言犹未尽”的状态,这说明语言符号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交际之需,而是存在某种缺陷或不足。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1983)就认为,语言虽是一个有用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也是一个危险的工具,因为语言是从暗示物体具有一种确定、分立和永久的性质开始的,但物理学似乎表明物体并不具备这些性质。比如汉语中有“天上有云彩”、“天上有飞机”、“天上有飞鸟”、“天上有星星”和“天上有月亮”这样的表达,这些表征表面上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中国人一般都能接受或认可,而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它们虽然都使用了相同的表征“天上”,但其中物体所涉及的认知距离,即这些物体与地球表面的垂直距离绝对不等同。那么,究竟有多远的距离?恐怕只是一种直觉意识而已,没人能准确说出来。因此,语言象似性表征不能回避语言这个描写“工具”。对于工具,我们在使用时需持严谨态度,即需要回答:1)工具性质是什么?2)用工具做什么?3)工具是否合适?4)工具功能如何?……等等,因为这些问题若没搞清楚就盲目行动,不仅达不到目的,还可能适得其反。实际上,两个世纪以来(从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算起),几乎所有语言学研究都在围绕语言这个工具是什么和为什么来展开。具体来说,围绕3个同心波转动:语言、符号与社会的关系;语言、人脑与心智的关系;以及语言与其物质媒介载体(即声音、文字和技术处理)的关系。(顾曰国 2010a,2010b)这3种关系涉及语言理据与应用的问题,而理据寻觅的手段之一就是语言象似性,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少(如Haiman 1980,1985a,1985b,2008;Croft 1990;Givón 1985,1991;Simone 1994;Willems & Cuypere 2008;Haspelmath 2008;沈家煊1993;王寅 1999a, 1999b, 2009; 朱永生 2002; 胡壮麟2009),但从语言符号缺陷角度进行探讨者难寻。下面我们具体考察:
第一,先天建构不足。语言符号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历一定的阶段。Steels(2005)认为第一阶段是命名阶段,社区群体需要就一套语言表达习俗达成协议,以使命名成功。这需要三个过程:1)创新(Invention)。若需要一个新名时,说话人能够提出来并能将其与他所需要关注的对象联系起来。2)采纳(Adoption)。当听话人遇到这个新词时,他能够在关注和互动后将其与所指对象联系起来。3)调整(Alignment)。当新名得到认可并运用成功时,应强化这种行为。第二阶段是通过命名来建构范畴,个别物体命名之后需要对一类物体进行不同定位,即区别范畴,以建构此类物体库。这同样需要3个过程:1)创新。当说话人需要一个新范畴时,他能够提出来并增添到已有的范畴库。2)采纳。听话人需要一个新范畴,因为现有语言范畴无法解决。3)调整。跟踪并选择语言中的成功范畴。实际上,最后能成功进入优选范畴的是极少数。这样,语言范畴与非语言范畴呈现不对称性,前者有限,后者无限。也就是说,能用语言表征出来的范畴远低于现实世界所存在的范畴数量和种类。
第二,符号数量及表征手段有限。纵观人类所有的现实语言,若从字母构成看,不过几十个;从语音看,主要有元音、辅音,升调、降调或升降调;从词类看,主要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和感叹词等实词类,介词、连词、冠词和助动词等虚词类;从词汇语义关系看,主要有同义、反义、近义和上下义;从句法结构看,主要有简单句和复杂句/复合句;从句法功能看,主要有陈述句、祈使句、疑问句和感叹句等。若以动词作为参照点,仅就位置而言,名词短语角色的编码只有3种可能的线性序列:
A. ________VERB
B. VERB________
C.________VERB________
(Frajzyngier & Shay 2003)
换言之,语言通过位置来编码动词论元,其最大量就是两个。若真的这样编码论元,只有动词前后两个位置。若只有其中一个位置可以利用,那么论元可以通过位置来编码的也就只有一个。然而,这3个线性序列类型的编码效率是不等同的,在左向或右向语言中默认位置是线性序列编码的唯一可行位置,主要编码动词与名词短语之间的关系。比如英语小句的形式序列就是用来编码主语和宾语语法关系的,若改变这种序列就会使其语法出现问题。如:
(1) a. I’ve told the truth.
b. * I’ve the truth told.
c. * The truth, told I’ve.
d. * Told I’ve the truth.
第三,符号负荷量有限。语言符号之熵作为语言信息量测定值,受到信息处理专家的高度重视。冯志伟(1994)通过研究发现,法语的熵为3.98比特,意大利语的熵为4.00比特,西班牙语的熵为4.01比特,英语的熵为4.03比特,德语的熵为4.10比特,罗马尼亚语的熵为4.12比特,俄语的熵为4.35比特,而汉语的熵则为9.65比特,是拼音文字语言熵的两倍多,可以说独占鳌头。因为每个汉字都是一个图画,在识别上有很高的效率,且每个字都表示一个概念,少数字就能表达大量信息。但当汉语书面语文本中不同汉字的容量扩大到12,370个时,包含在一个汉字中的熵仍为9.65比特,若再进一步扩大文本的汉字容量,这个熵值不会再增加。(冯志伟 1999)也就是说,像汉语这样信息量超大的语言,其负荷量也相当有限,无法展示更多信息,更何况其他语言。
第四,能指与所指错位。彭利元、肖跃田(2009)认为语言符号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物的存在和可以传播的资源,因为语言本身的物质属性,其传播可以在不考虑所指对象与思想蕴涵的条件下直接进行,语言的机械模仿与重复就是这种传播的典型形式。但实际上不可能出现能指与所指的彻底分离,只不过是语言符号逐步脱离它原初的所指对象或思想,导致它们处于一种动态的错位关系(多为隐喻化结果)。为此,Jackendoff(1994: 68-69)认为词性并不能真正表示某种内涵一致的意义,命名物体的任何词都可能是名词,但并非每个名词都命名一个具体物体,如earthquake、concert表活动、行动, redness表性质,location表方位。这样,名词的语法概念无法根据它所命名的实体来界定,即特定实体不必与特定词类一一对应。这也就不难理解英国经验主义大师洛克(1997)在其著作《人类理解论》中所谈到的,语言的缺陷在于其意义不确定性影响观念交流,有碍语言作为记载思想和传达观念的工具的目的。
第五,作为范畴化的抽象系统很难找到其对应实体。也就是说,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已高度抽象化,远离其始源图腾或客体(可能因语言不同而存在度的差异,如意合汉语与形合英语)。许国璋(1986)就提到抽象与具体东西两种对应关系(一是独立于所抽象的具体东西,二是多少依存所抽象的具体东西)对于语言来说都存在,即任何具体东西的毁灭都不会使它相应的抽象东西毁灭,如抽象的“红”不为任何具体的“红”所左右,抽象的“方”也不会为任何具体的“方”所左右。这样,语言符号与实体始终存在一种人为的范畴化距离。
第六,语言符号呈一维线性表征。这种表征使语言不可能共时再现立体、多维的客观世界,即不可能在多维空间展开,因为这种符号只能一个一个地从左至右或从上到下依次进行。正如索绪尔(1980: 106)所言,语言是声音(能指)与意义(所指)的结合,而声音(能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线条性,即能指属听觉性质,只在时间上展开,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a)它体现一个长度;b)这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定,因为它是一条线,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可再现。这就必然导致在“共时”条件下进行或把握的某种事物或活动,若用语言来表征时就会经历一种“历时”的变形处理。如一个精彩的篮球扣篮场面,若我们现场观看,其扣篮那一刹那所发生的全部动作与场景可以一览无余,若用语言把这一场面再现出来,则要变成线性的一一描述,完整的、立体的整体画面不可避免地被分解。
第七,语言系统应变能力有限。客观物质世界可以说瞬间千变万化,并有可能变得面目全非,使我们无法认知。对此,语言系统始终慢半拍,无法及时抓住并描述出来。系统中变化最慢的语法部分更不用说了,即便反应最快的词汇部分有时也难以应对突发的事件,比如当前流行的禽流感最初就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语言表述。
第八,语言符号是客观世界的主观识解。语言所表征的客观世界不是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是经过认知识解处理后的主观世界。从某种程度看,所有自然语言的符号表征就是语言“主观性”(subjectivity)和“主观化”(subjectivization)的结果,因为它体现了:1)说话人的视角(perspective);2)说话人的情感(affect);3)说话人的认识(epistemic modality)(沈家煊 2001)。如:
(2)a. The glass is half full.
b. The glass is half empty.
Tuggy (1980)认为,虽没有绝对的情景来证实某东西处于半满状态是真的,也没办法证实某东西处于半空状态是假的,但从语义看它们肯定是不同的。换言之,真值条件分析可能做出错误的判定,因为两句的同等真值不一定导致完全同义。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从3个不同角度来识解,如图所示(half full与half empty的不同识解):

(a)表征真值条件,将两句的意义进行合并,所有方面也给予同等地位的考虑。而(b)强调杯子中的内容,(c)则凸显未装满的部分,它们都是一种主观识解。根据语义意象,任何将这两句意义分解为同等语义值的处理都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解释当水倒入杯子时的状态,即half full和half empty的分布。因此,可以表征为(3),而无法表征为(4):
(3)She stopped pouring the water out of the pitcher when the glass was half full.
(4)* She stopped pouring the water out of the pitcher when the glass was half empty.
从认知角度看,答案是明显的,因为形容词full和empty针对的是装满和倒空的行为。具体来说,full和empty分别表征装满和倒空行为的终点状态,当杯子被认为在装填时,(3)的half full是绝对可接受的,而(4)的half empty则是不可接受的,即当某东西在装填时,half empty不可能是最终状态。若我们谈论将杯子中的水倒掉一半时,可用half empty,而不是half full。因此,(5)不可接受。
(5)* She stopped pouring the water into the glass when the pitcher was half full.
第九,语言系统是高度整合的,每个层面都不例外。比如句式Jennifer likes that boy的整合就有3种不同方式(牛保义 2011: 114-116):先有动词like和boy的整合,然后like boy与Jennifer整合。前者动词like凸显一个图式性界标,boy凸显一个实体,对动词like凸显的界标做出具体阐释,二者整合为合成结构[LIKE BOY]。后者like boy合在一起凸显一个图式性的射体,名词Jennifer凸显一个实体,对like boy凸显的射体做出具体阐释,二者整合为合成结构[JENNIFER LIKE BOY]。第二种方式是动词like与Jennifer和boy的整合,like同时凸显两个图式性的次结构“界标”和“射体”。名词Jennifer凸显的实体对like凸显的射体做出了具体阐释;名词boy凸显的实体对like凸显的界标做出具体阐释。三者整合为合成结构[JENNIFER LIKE BOY]。还有一种整合方式,先有动词like和名词Jennifer的整合,然后Jennifer like合在一起与boy整合。前者动词like凸显一个图式性射体,名词Jennifer凸显一个实体,对动词like凸显的射体做出具体阐释,二者整合为合成结构[JENNIFER LIKE]。这样,句义建构在句子组构成分义整合基础之上,而每个短语义自身又建构在其构成成分义整合基础之上,直到词及其以下层面。也就是说,句式中每个语法范畴和语义内涵不可能都得到充分展示,只能兑现其中的某个侧面,其他的不得不暂时受到压制,无法激活。
最后,语言的复杂度超越了人的本能。众所周知,一个正常的人先天都会走路,而不需要他人帮助,因为它是人类的生物遗传功能。说话好像我们每天都会,不需要额外地付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语言不是人的一种本能体现,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萨丕尔2005: 3-4),如印度发现与人类隔离的狼孩就不会说人话。那么,人们会问:与人天天相处的其他动物为什么不会说人话?按乔姆斯基的观点,这是人类的语言习得遗传机制(LAD)所致。不过,这只是一种语言潜能,并非语言现实。
以上这些缺陷导致两个直接的严重后果:一是语言与外在客观现实出现距离。表面上,只要有了语言,对客观现实的描写就不会有问题。其实不然,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Plato)就对语言的表达困境提出了看法,认为对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语言是一种粗劣的工具,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把他的理性所体会到的东西付诸语言,都不会写成固定的文字形式。我国古代道家创始人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老子看来,真正的“道”和“名”不能用一般性语言来表达。继承并发展老子道家思想的庄子也说:“道不可闻,闻而非道;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我国当代语言学家钱冠连(1997)在其《汉语文化语用学》中也认为客观世界进入语言世界时,都被打了折扣,因为语言符号有限,不可能与丰富多彩的世界一一对应,语言总是落后于现实。二是语言与内在思维出现距离。语言不仅不能很好地描写客观世界,也无法有效地解决它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以作家的创作过程为例,朱立元(1989)认为在作品的酝酿构思阶段,意象因素压倒语符因素,当还未找到完整而恰当的语符形式时,二者处于分离或部分分离状态。有的作家在酝酿构思阶段同时打腹稿,或进行片断写作,这就有了意象与语符的部分结合。到了动笔写作和修改阶段,艺术思维的语符方面上升到主导地位,这时意象与语符结合得非常紧密,要想把语符从这个思维过程中割裂出来,就等于扼杀意象生命。换言之,作家的文学思维必须将一般的、普遍的语符通过文学化组合,把具体的、独特的意象表现出来,达到“译”象成语之目的。然而,启动思维过程的是思想内容,即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表征,而不是语言,更不是言语。(刘利民1993)作为言语的字、词、句,任何人都不可知觉到(无论是视觉、听觉甚至触觉),但若无语言能力对之予以分解、解释,则不可能转化为思想内容,也不可能激活与之有关的思维过程。
3. 补救策略
语言缺陷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众多因素交融使然。正如王希杰(1994)所言,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演变和发展受到社会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而民族文化和社会因素本身又具有缺陷性、非系统性和不对称性;语言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等级系统,各子系统并非简单对应,而是相互制约;在其演变和发展过程中由简单到复杂和由复杂到简单两条路线同时并存,且相互制约着。面对自然语言的缺陷,人类总是在不停地想办法,如诗人在为“人生最大的痛苦乃是语言的痛苦”的心境下,克服、突破语言的缺陷和交际的不自足性,创造出了不朽的艺术佳句。哲学家从另一条路线上去努力探索克服、消解人类自然语言的缺陷和交际不自足性,创造了人工语言。而语言学家则兼顾诗人和哲学家的努力,在承认人类自然语言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机制的基础之上,力求保持和促进“人—语言—社会”三者的和谐一致,不是征服语言,更不是抛弃语言,而是挖掘语言的巨大潜力。具体来说,主要采取两大补救策略:自救和他救。
语言具有一种自救能力(即自我调节能力,如语言系统内部字、词、句和篇各层次之间的互动照应、转换、增减、替补或整合)。王希杰(1993:8)认为在人类3000多种语言中,有文字的语言是很有限的,规范过的语言是很少的,而且语言的规范化也是很晚才发生的,次数少得可怜,所做的工作又微乎其微。然而,人类一切语言都不是从混乱走向混乱,而是从无序走向有序,即使在社会、语言大变动时期,语言依然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大系统,一定程度的混乱和不规范只不过是语言进一步大发展的伴随物而已。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语言这种自我调节能力在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如语音方面通过变音、语调、重音转移或重复,像汉语中的“妈(mā)、麻(má)、马(mǎ)、骂(mà)”、“长(cháng)短、长(zhǎng)子”、“重(chóng)叠、重(zhòng)任”和“研究(yán jiū)研究、唱(chàng)唱跳(tiào)跳”等,英语中的“′increase (增加,n.)、in′crease (增长,v.)”,“′contract (合同,n.)、con′tract (收缩,v.)”和“′import (进口,n.)、im′port (引进,v.)”等。词汇层面的形态组构,如英语中的“mortal (死的)、immortal (不死或不朽的)、mortify (致死)、mortgage (抵押)、amortize (分期偿还)、moribund (垂死的)”、“curiosity(好奇)、curio(古董)、secure(安全的)、curative(治病的)、accurate(准确的)”、“dictate(口授)、diction(措词)、contradict(矛盾)、predict(预言)、addict(上瘾)”和“illumination(阐明)、luminary(发光体)、luminescence(发光)、luminosity(光明)”等,汉语的“木、林、森,一、二、三,火、炎、焱,日、昌、晶,人、从、众”等。句法层面通过语法隐喻等将同一命题进行不同表征,如“I don’t understand its implication. /I had no idea of its implication. /Its implication was not comprehensible to me. /Its implication was beyond me. /What it implied was not clear to me.”(王逢鑫 1989/1996: 265-266)。语篇层面充分利用重复、排比和拟声词等,如Samuel T. Coleridge的短诗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The ice was here, the ice was there, the ice was all around; it cracked and growled, and roared and howled, like noises in a swound!
与此同时,人类在不停地寻找“他救”的办法,也就是语言符号之外的处理方式(如非语言符号与认知)。韩宝育(1987)认为由于语言符号自身的特点受到两方面限制:一是这种符号系统给我们提供的认知对象是一种粒散语义网络,我们必须凭借其他非语言符号系统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将其转化成一个连续整体;二是我们将自己对世界连续整体的把握用语言符号来表达时,也只能是一种粒散语义网络,且只有人在其非语言符号共存互补作用下才能释读其义,因为人类是用自己整个身体器官来感受世界,无论世界呈现什么状态或采用什么方式联结,都将其转化为各种符号系统加以接收,然后由大脑加以综合,从而实现其认知过程。
其实,人们经常通过非语言符号来解释和表达语言符号之外的种种意图和话语本身的关系,且有些非语言符号可以暂时取代甚至超越语言。随着今天网络时代的到来,交流空间给网友们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表征方式——符号、图片和动画等,这些表征方式可以更直观、形象地传情达意,更加突出和丰富视觉效果。(钱冠连1991)据有关统计,在面对面的交际中,大约70%的“社会含义”是通过体态语来传送的,而语言只负担另外的30%,因为体态语运用可对某些语言符号的真实与否进行检验,如非洲人常用鼓声的高低、长短和节奏的快慢、急缓来表示一定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往往又与自然语言相关联。为此,韩宝育(1987)认为符号系统可能因目的不同而转码,即改变或转换认知内容的存在形式和表达形式。如将一幅画谱写成一支曲子、转换为一段话语或建成一个实物等。反过来,也可以通过语言去认识一幅画、一首乐曲或一座精美建筑。换码后的意义存在方式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存在形式的限制与制约,从而使其意义表达具有该种存在形式的特点。同时,人类认知同样以多种形式和多元方式存在,语言符号只不过以其独特价值存在于人类的认知体系中,它既不是人类认知的唯一途径,也不是人类认知成果存在的唯一形式。也就是说,当非语言符号通过转码获得语言表达时,各种非语言符号系统将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存储有关方面的信息来共同参与认知过程,从而形成对认知对象细密而全面的认识,这种共存互补作用使我们感觉不到语言符号的缺陷。
4. 语言象似性
语言象似性既是一种主观需求,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象似度则没有一个明确的或显性的衡量标准。王德春(2001)认为语言符号是在人的认识和交际过程中用来代表其他事物,接受、存储、改造和传递信息的可感知的物体。最原始的符号是对客体的复制,如猎人按野兽的爪印跟踪猎物,没有图章前用指印作为凭证等,这种符号是复制式的,它们是其与所代表客体相似的复制品,照片和肖像等属于此类。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认识能力的提高,在表示客体时不再仅仅利用与客体有必然联系的符号,即不再仅仅用其复制品标志物或象征物,而开始有意识地用没有必然联系的符号来代表客体。这样,语言符号的意义是概括的、抽象的,不可能是客体的复制,其描写功能自然不得不打折扣,象似度有多高很难断言。通过补救后,语言符号的描写功能虽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和提高,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语言的一些基本特性,如数量、性质与表征方式等。也就是说,这种符号还是人类语言表征能力和认知能力极限范围之内的,没有超越。若超越该范围,那就不是人类语言符号,只有另当别论。众所周知,文学广义上可被视作象似性的,因为文学能以多种方式模仿它所反映的现实(Wales 2001: 193-194),但它离现实仍有相当距离,像卡明斯(e. e. cummings)这样极端人本主义思想的人也不例外,在诗歌创作中随意玩弄字词,字母大小写不按规则,诗歌分行、排列、空格均无常,标点符号用法也与众不同,有的干脆不用。且其漠视语法,把副词当动词、名词、形容词使用或把动词、形容词当名词使用,连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也小写(董衡巽等 1986: 70)。为此,王寅(1999b)强调符号的象似性有一个程度问题,照片与实物的象似度高于绘画,绘画与实物的象似度高于表意符号(如交通标志等),表意符号与实物的象似度高于语言文字,即照片>绘画>语言。不过,象似度再高也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绝对,照片毕竟不能完完全全地反映实物的全部;象似度再低的语言文字也存在象似性现象,其象似性并非指文字形态像镜子一样呈现客观事物,因为文字形态象似性其实是人们认知和内化外在世界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而已。从认知处理上看,象似性的好处在于空间上相邻近的成分若在神经结构上有象似的邻接性,那么神经元的激活就可协同发生,从而缩短处理时间。(沈家煊 1993)
同时,语言象似性考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语言理据的寻觅。而理据则是事物现象所以得名的道理和依据,理据为意义生成提供了原生性动力。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先哲们就开始思考语言文字的理据问题,如公孙龙子在《指物篇》中说:“物莫非物……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在公孙龙子看来,每种事物都有其独特的“指”(即特征),而物的名称就是由这些特征而产生的(王艾录、司富珍2002: 8)。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在争论名称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时,也出现了“唯名论”和“唯实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主张唯名论,认为人们用来表示事物的名称和符号,其形式与它们的所指之间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而是约定俗成的结果。时至今日,当代语言学仍在寻求各种语法规律背后所隐含的理据和动因。国际语言学界目前对语言理据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Radden & Panther (2004)主编的《语言理据研究》(StudiesinLinguisticMotivation),其中涉及语言系统内、外两大理据。内部理据又分5种具体类型:a)内容可能决定形式;b)形式可能决定内容;c)一个语言单位的内容可能决定另一语言单位的内容;d)一个语言单位的形式可能决定另一语言单位的形式;e)一个“语音内容”结合体可能影响另外一个“语音内容”结合体。而外部理据则分为4大类型:a)生态理据;b)种属理据;c)经验理据;d)认知理据。从古代中国、古希腊哲学家关于唯名论和唯实论的辩论,到现代语言学家关于任意性和可论证性的争论,其间虽不断演绎,但语言符号音、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争论的核心问题。(王艾录 2003)近20年来,这种争论更加激烈。从文献资料来看,不论是持任意说的学者还是持象似说的学者,在其论证过程中几乎都会提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前者总围绕该书中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定义及阐释,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为其反驳语言符号象似说寻找最权威的有力证据;而后者则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定义入手,着力寻求语言符号任意性概念的纰漏与不足, 从而为其语言符号象似性学说顺理成章而据理力争。(宋江录 2009)实际上,通过这些争论,事实越辩越清,朱永生(2002)认为在复合词和派生词以及句法层面上的确存在着象似性,但就单个符号而言,任意性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原则。象似性原则应该被看作是对Saussure理论的补充,而不是任意性原则的替代物。胡壮麟(2009)则进一步认为任意论者所谈的符号是语言符号,而象似论者所谈的符号具有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元符号性质;就语言而言,前者着重语音和口述语言,后者还兼及文字和书面语言;就象似性而言,前者承认为数较少的高度拟声性,后者扩展至拟象性和隐喻。总之,语言符号的象似性与任意性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二者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只不过,在不同层面或不同角度上,它们有多少和高低等程度差异,没有绝对的象似性,也不可能有绝对的任意性。
5. 结语
通过以上讨论,笔者认为语言符号的确先天就存在一定的缺陷,虽进行了一些自救和他救努力,但仍然存在不足,因为这些补救策略并非原生性的(一个系统初始的、内在的有机体,具有不可分离性和不可再生性),即补救策略仍无法改变语言符号的量质、线性一维、识解性等特性。因此,语言象似性只是人类语言表征能力和认知能力范围之内的象似性,是一个相对概念。将来某一天人类若能找到一种更有效的多维式、立体式或多维立体交融式语言表征符号,那么语言象似性问题会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但要做到绝对的百分之百象似几乎是一个梦想或奢望。
Croft, W. 1990.TypologyandUniversal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ajzyngier, Z. & E. Shay. 2003.ExplainingLanguageStructurethroughSystemInteractio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Givón, T. 1985. Iconicity, isomorphism and non-arbitrary coding in syntax[A]. J. Haiman (ed.).IconicityinSyntax[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87-219.
Givón, T. 1991. Isomorphism in the grammatical code: Cognitive and biological considerations[J].StudiesinLanguage1: 85-114.
Haiman, J. 1980. The iconicity of grammar: Isomorphism and motivation[J].Language3: 515-540.
Haiman, J. 1985a.NaturalSyntax[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iman, J. 1985b.IconicityinSyntax[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aiman, J. 2008. In defence of iconicity[J].CognitiveLinguistics1: 35-48.
Haspelmath, M. 2008. Frequency vs. iconicity in explaining grammatical asymmetries[J].CognitiveLinguistics1: 1-33.
Jackendoff, R. 1994.PatternsintheMind:LanguageandHumanNature[M]. New York: Basic Books.
Morris, C. W. 1938.FoundationsoftheTheoryofSign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dden, G. & K. U. Panther. 2004.StudiesinLinguisticMotivation[M].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Simone, R. 1994.IconicityinLanguag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Steels, L. 2005.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From lexical to gramma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s[J].ConnectionScience17(3-4): 213-230.
Tuggy, D. 1980. Ethical dative and possessor omissionsí, possessor ascension[A]. J. P. Daly & M. H. Daly (eds.).WorkPapersoftheSummerInstituteofLinguistics,UniversityofNorthDakota(vol. 24)[C].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Huntington Beach, CA. 97-141.
Wales, K. A. 2001.DictionaryofStylistics(2nded.) [K].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Willems, K. & L. De Cuypere. 2008.NaturalnessandIconicityinLanguag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董衡巽等. 1986. 美国文学简史(下册)[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冯志伟. 1994. 汉字的信息量大不利于中文信息处理——再谈汉字的熵[J]. 语言建设(3): 34-35.
冯志伟. 1999. 汉字的极限熵[J]. 中文信息处理(2): 53-56.
顾曰国. 2010a. 当代语言学的波形发展主题一: 语言、符号与社会[J]. 当代语言学(3): 193-219.
顾曰国. 2010b. 当代语言学的波形发展主题二: 语言、人脑与心智[J]. 当代语言学(4): 289-311.
韩宝育. 1987. 语言符号的局限性[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4): 90-91.
胡壮麟. 2009. 对语言象似性和任意性之争的反思[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95-102.
卡西尔. 1985. 人论[M]. 甘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廖体忠. 1991. 语言理据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4): 25-30.
刘利民. 1993.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质疑[J]. 社会科学研究(4): 76-80.
罗 素. 1983. 人类的知识[M]. 张金言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洛 克. 1997. 人类理解论[M]. 关文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牛保义. 2011. 构式语法理论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彭利元, 肖跃田. 2009. 经典“语义三角”辨正[J]. 外语学刊(4): 51-54.
钱冠连. 1991. 语言符号的局限和语用学[J]. 外语学刊(4): 13-19.
钱冠连. 1997. 汉语文化语用学[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萨丕尔. 2005. 语言论[M]. 陆卓元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沈家煊. 1993.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1): 2-8.沈家煊.2001.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4):268-275.
宋江录. 2009. 15年来国内语言符号任意说与象似说的争论焦点及共识[J]. 山东外语教学(5): 33-37.
索绪尔. 1980.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王艾录. 2003. 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6): 1-8.
王艾录, 司富珍. 2002. 语言理据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德春. 2001. 论语言单位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兼评王寅《论语言符号象似性》[J]. 外国语(1): 74-77.
王逢鑫. 1989/1996. 英语意念语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希杰. 1993. 修辞学新论[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王希杰. 1994. 深化对语言的认识,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J]. 语言文字应用(3): 9-15.
王 寅. 1999a. 论语言符号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与补充[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王 寅. 1999b.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象似性[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 51-54.
王 寅. 2009.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许国璋. 1986. 金岳霖论“语言”[J]. 外语教学与研究(3): 1-11.
余志鸿. 2008. 语言观和方法论[J]. 汉语学习(1): 10-18.
朱立元. 1989. 从审美意象到语言文字——试论作家的意象语符思维[J]. 天津社会科学(4): 70-77.
朱永生. 2002. 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J]. 外语教学与研究(1):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