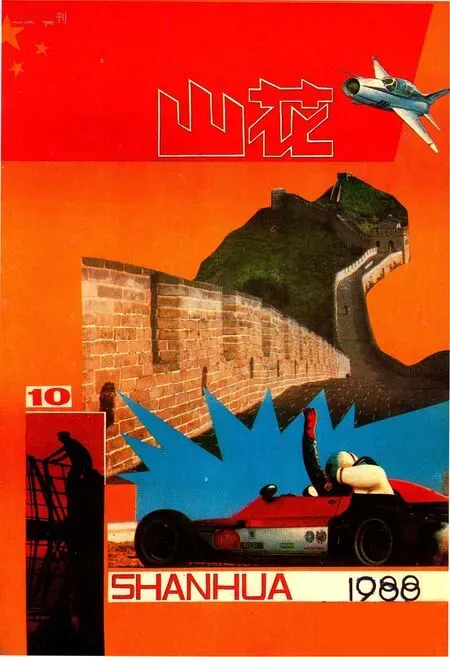探弗吉尼亚·伍尔夫文学创作理论“双性同体”
2014-09-16
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女性主义理论的先驱者,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29年提出文学创作理论“双性同体”,这是对传统男女二元对立观念的解构,同时更彰显出对男性中心的单一标准的抗议,对后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她成长中耳闻目睹的父权制家庭中存在的性别角色经历和不幸遭遇的性侵犯为切入点,透析该理论的成因。
引 言
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开拓者,也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先驱者,她关注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在西方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精神危机日趋严重的历史背景下,在192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出重要的“双性同体”(Androgyny)的文学创作理论:伍尔夫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力量支配,一种是男性的力量,一种是女性的力量,女性往往外柔内刚,男性往往内柔外刚,没有纯粹的男人和女人。“双性同体”才是理想的人格形象,纯粹的男性思维和纯粹的女性思维都不能很好地创作,双性的和谐是文学创作最理想的创作境况。“双性同体”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男女二元对立观念的解构,也显示了对男性中心的单一标准的抗议”,对后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她成长中耳闻目睹的父权制家庭中存在的性别角色经历和不幸遭遇的性侵犯为切入点,透析该理论的成因。
父权制家庭中的性别角色
维多利亚时代所界定的理想女性是居家的、孝顺的、无私的,在经济上不独立的,但在道德上高于男性的虔诚的教徒。这种意识形态剥夺了女性在经济、政治和法律上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当时大多数妇女接受并且实践了父权制为女性设定的这种所谓的女性气质。她们努力使自己成为取悦于男性的“高尚淑女”和“房中天使”,在她们短暂的生命中,她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她们是一切,但唯独不是她们自己,她们是男性的附属品和牺牲品,她们是不具话语权的“第二性”。弗吉尼亚的母亲朱莉娅·达克渥斯不幸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并且堪称“高尚淑女”和“房中天使”中的典范。
1882年1月25日,弗吉尼亚诞生在海德公园门22号,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权制大家庭中。母亲朱莉娅·达克渥斯比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几乎年轻15岁。十口之家,会给一位非常尽心的母亲带来极大的麻烦,这是可想而知的。母亲朱莉娅接受并且实践了传统的女性气质,她是美丽、优雅、温柔、顺从、贞洁、无私的“房中天使”,她严格恪守维多利亚时代的母亲身份,她为人慈善、勇敢地承担着母性的职责:家庭中每个人都要求某种帮助或同情,每个人都能从她那里获得慰藉,大多数情况下她都能营造一个弗吉尼亚所谓的“斯蒂芬的幸福家园”。家中每个人都需要她,可是丈夫最需要她,因此朱莉娅主要是为丈夫而活:他的健康和幸福必须得到保障;必须倾听并分担他在金钱、工作、名望和家庭管理等方面的忧虑;在他们17年的婚姻中,他的性情和需求使得妻子尽管美丽依旧,但却精疲力竭,最终在利他的工作中过度内耗、英年早逝。
1895年5月5日,弗吉尼亚13岁,恰逢青春期初始阶段,不幸遭遇母亲病逝。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在家中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力,但是由于他过度敏感、暴躁易怒的性情,在母亲去世后,使得往昔的“斯蒂芬的幸福家园”变得异常恐怖、阴暗。家中唯有男孩子们可以肆无忌惮、我行我素地生活,而弗吉尼亚和姐姐们却只能噤若寒蝉地苟延残喘。成年后的弗吉尼亚在谈到生命里的那段日子时,再现了一幕幕黑暗的图像:黑色屋子、黑色房间、黑色墙壁,“东方式的阴暗”。这些黑暗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有失去慈母之后的心灵之痛与无所适从,有对反复无常、性情暴戾父亲的深深恐惧,也有对未来生活的不知所措。
父权制家庭中的性侵犯
性是女性一生各个阶段自我界定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女性的生理性别、性倾向、性别角色、性欲望、性感受、感情和记忆等。女性的性反应与女性所处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密切的联系,如女性的年龄、所受的教育等。
弗吉尼亚,一朵艰难生长的小花蕾,还没有绽放就被异父兄长乔治· 达克沃斯毁掉了。爱或者被爱的初次经历可以是迷人的、沮丧的、窘迫的,甚至是乏味的,但不应该是令人恶心的。当爱神扇动着蝙蝠的翅膀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令人作呕的乱伦性欲的形象。
1895年母亲病逝后不久,27岁的异父兄长乔治· 达克沃斯就开始了对13岁的弗吉尼亚的挑逗行为。在人前面目和蔼可亲的兄长,突然在她眼前变成了一只怪兽,变成了她无法抵御的暴君。婚后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海德公园门22号》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处境:“当他(乔治· 达克沃斯)的情欲增长、欲望变得更加猛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不幸的小鱼和一只庞大而骚动的鲸鱼关在同一个水槽里。”据弗吉尼亚未发表的回忆录表明,乔治的乱伦行为持续至1903或1904年父亲去世前。在那个“性是禁忌”的时代里,在集“高尚淑女”和“房中天使”融于一身的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弗吉尼亚耳濡目染,天生对性有关的事情感到害羞,更因受到乔治的恐吓而退缩成了一种终生的、自卫的惊恐姿态,“性冷淡”。
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认为,社会中的男女关系,用两性的生理区别来解释是无效的,二者的区别主要属于心理的范畴,是儿童的社会教化过程造成的。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不是政治的和经济的,而是心理的。
乔治· 达克沃斯是家中享有特权的兄长,天性容易激动,在对弗吉尼亚表示爱意和拥抱时一向感情外露、不负责任;只有非常精明的眼睛才能够察觉出他对妹妹的抚摸和拥抱正逐渐由友爱转变为强烈的淫欲;年幼的妹妹很难判断出应该在哪一点上划出界限,用语言表示拒绝,冒着引起一场痛苦且尴尬的丑闻的危险;要想找个能够倾诉的人就更难了。面对兄长的乱伦行为,她长期保持沉默,归咎于她所受的教育,当时她所受的教育是要保持一种无知的纯洁,也归咎于她本人极度害羞的性格。
性是女性权利的一个重要的生命因素。乔治· 达克沃斯以他的男性身份和男性特权玷污了一朵圣洁的花蕾,严重斫伤了这棵正在生长的幼树,亵渎了花季少女原本绚烂多彩的、纯真的人生梦想,父亲去世后不久,弗吉尼亚再次陷入精神崩溃的痛苦,她进入了一段梦魇的时期,几乎达到了狂乱的极点,她初次尝试自杀。
心理学家认为,自杀是疯狂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些人在过度社会压抑下必然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姿态和话语。弗吉尼亚自幼深受母亲的熏陶和调教,曾经努力使自己成为如同母亲一般的另一个“高尚淑女”和“房中天使”,母亲燃尽自己,英年早逝的伤疤在年幼的女孩心中还未愈合之际,27岁的异父兄长乔治· 达克沃斯趁机向她伸出了魔爪,面对家中性情暴戾的父亲、面对有恃无恐的乱伦兄长,心底无法倾诉的苦楚,当所有不幸狂风暴雨般地接踵而至,天资聪颖、生性敏感的弗吉尼亚在心理承受能力达到崩溃边缘时,自杀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她逃离黑暗、逃离魔爪、奔向自由的唯一的出路。自杀是她在家庭中失去“话语权”后,渴望自我表达、变异的女性话语,自杀式的反抗是她获得自由的极端方式,她是以生命为代价,极力想摆脱来自父权统治的种种压迫。
结束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必然有反抗。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弗吉尼亚·伍尔夫亲历了男权文化对“高尚淑女”和“房中天使”们用心良苦的培养和雕琢,逐渐体会到这是一种男性至上的社会规范。弗吉尼亚·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男女二元对立观念的解构,同时更彰显出对男性中心的单一标准的抗议,也许正是首先来自于家庭里男性霸权的重重压迫唤醒了伍尔夫的女性意识,唤醒了她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地位的思考,唤醒了她对社会中的男女两性关系的深刻反思。“双性同体”理论的提出体现出弗吉尼亚·伍尔夫对男女两性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和远大的社会理想。
[1]Jeanne Schulkind ed. Virginia Woolf: Moments of Being (Unpublishe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M].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2](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田翔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
[3](英)昆汀·贝尔.伍尔夫传[M].萧易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刘秋菊.弗吉尼亚·伍尔夫精神分裂原因的探析[J].作家,2009,(3).
[5]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苏红军,柏棣.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吴庆宏.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女权主义[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8](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9]杨莉馨.20世纪文坛上的英伦百合——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赵思奇.“杀死房中天使”创造女性话语——弗吉尼亚·伍尔夫对维多利亚时代男性霸权的反叛[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4).
[11]甄艳华.解读伍尔夫的两性和谐社会理念[J].外语学刊,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