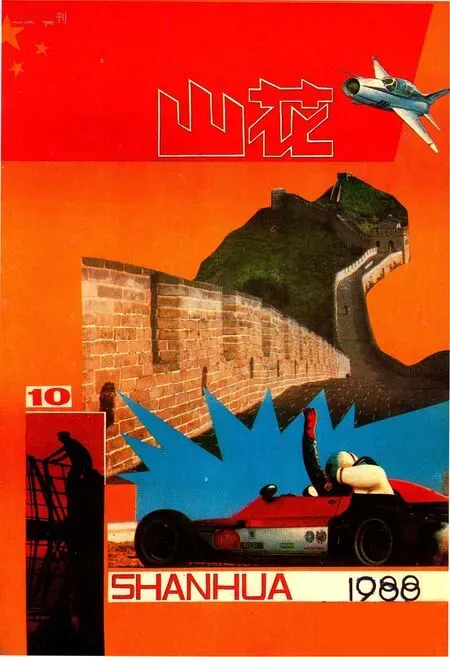砂轮厂
2014-12-02
纪朋飞约的两个人,一男一女,我都不认识。男的彬彬有礼,见面就主动跟我握手。女的则有点自闭的样子,对人不是很热情,握手的时候,只用手尖跟我的手碰了一下(她好像刚摸过冰一样,手是冰凉刺骨的)。据我观察,他们也是今天才第一次碰面,之前并不认识,更没那种男女关系。
男的一边打牌,一边不停地接电话。听上去,每次打他电话的都是同一个人,而且可以确定,是个女人。女的则基本不说话,只是摸牌,出牌。偶尔抬起头,眼风扫过坐她侧面的电话男,虽说显得面无表情,但这样的无表情,不傻的人都看得出来,是一种厌恶。电话男应该不傻,但他真的没感觉到侧面女人对他的厌恶。在没有电话的时候,依然滔滔不绝,好像他不说话,就没法呼吸,会憋死。
你的牌打得好,哈哈。他多次用这个话与桌上的女人搭讪,但对方都没理他。
人就得有个爱好,尤其是女人,没个爱好,哈哈哈,就很麻烦。他说这话时,眼睛看着那个侧面的女人,表明是说给她听的。
但女人还是不接他的话,眼睛只看着自己手上的牌。她的手上戴着一枚醒目的戒指,是不是钻石我没法辨别。
电话男的电话又响了,这次他只跟对方说了一句,在路上了,还等几分钟。然后捂着电话急急忙忙地跑出了包间。
我看了一眼纪朋飞,纪朋飞也在看我,表情有点无奈。我转头看那个女人,她此时依然什么表情也没有。由于电话男的离开,牌局暂停。沉默中,女人从包里掏出一支烟,用精巧的打火机点上,然后,也不看我和纪朋飞,只管自己一口一口地吸着。她抽烟的姿态显示出她是个有阅历的女人。
电话男终于握着电话回来了。他万分抱歉地告诉我们,他要离开一下,也就是说,他不能继续和我们玩了。有点私事要处理,是女人的事情。他冲我和纪朋飞扮了一下鬼脸,意思是这种事情男人都明白的。然后,他急急忙忙地收拾起自己的皮包,说了声对不起,就离开了。
但他突然又倒了回来,没头没脑地问了我一句,你是苏无艳的丈夫吧?我说,曾经是。他意味深长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改天我们聊一聊。我说,好。便看着他夹着皮包有点慌张地离开了包间。
他是谁?我问纪朋飞。
我以为你们认识,所以没介绍。纪朋飞说,他是老艾的朋友,以前也开过酒吧的,现在不知道在干什么。
叫什么名字?
好像是姓陈,名字我忘了。
纪朋飞突然转向那个女人,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女人漠然地摇了摇头。
难道你不是跟他一起的吗?
女人又摇了摇头。见纪朋飞仍然疑惑的样子,她终于开了口,我是敏姐的朋友,是她叫我来的。
纪朋飞打了一下自己的脑门,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对着那女人连说了两声对不起,然后转过来对我说道:
是的,我差点忘了,她是敏姐的朋友,是敏姐帮我们叫过来的。
纪朋飞就是这样的人,出现这种状况我一点不奇怪。我只问他,现在怎么办?走了一个人,还打不打?纪朋飞不马上回答我的问题,却转头去看那女人,意思是,打不打由她说了算。女人抽着烟,依然表情冷漠,对纪朋飞带有询问的目光不置可否,好像打不打都无所谓,与她无关,你们看着办。
我说,我看这样,今天就散了吧,不打了。
这位小姐,你觉得呢?今天就算了,怎么样?纪朋飞问道。
女人说,我无所谓,你们说打就打,不打就不打。不过,请不要叫我小姐。我姓余,多余的余,叫我小余就可以了。
纪朋飞说,牌不打了,但饭还是要吃的。我们去找个地方吃饭,余小姐你看如何?
你们去,我还有事,不奉陪了。
余小姐,你既然是敏姐的朋友,又是为了我们专门过来的,就这样走了,我怎么向敏姐交代?
我也说,反正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就在附近找个吃火锅的地方,怎么样?
余小姐喜欢吃火锅吗?纪朋飞马上转向对方问道。看他那紧张的表情,如果余小姐说不喜欢,他似乎就不打算再活下去了。
不反对。
谢谢余小姐。
请叫我小余。
谢谢小余。
不客气。我喜欢吃火锅。余小姐终于露出了一点微笑。
我们走出茶坊,才发现天色有点特别。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才五点过,六点不到,怎么就暗成这样了呢?纪朋飞也说,是不是要下雨哦?我倒不担心下雨,但对下雨前的这种天气感觉很不好。暗淡的天色中,隐约透出一种番茄红,这天象很不正常。但究竟怎么个不正常,我其实也不懂。
不是要下雨,是要下冰雹。余小姐像是很专业地说道。
我很惊讶,便问,这个样子就是要下冰雹吗?
有可能,但也不一定,我瞎说的。她又笑了一下。
但你的样子不像是瞎说。你一定是有依据的。你是不是在气象部门工作啊?
你觉得我像吗?
很像,而且肯定就是。
要是我告诉你,我不是呢?
哦,不是就算了,我也是瞎猜的。
那好吧,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这女人真就一句话也不说了。而我是希望她能多说点什么的。跟一个基本不说话的女人走在一起,感觉是很压抑的。
这个女人是敏姐叫过来的。”纪朋飞靠过来低声地对着我的耳朵说道。
我知道,刚才她自己已经说了。我本能地偏了一下头,不喜欢他靠得这么近。

王华祥-《纯属虚构》 50×70cm2012
是我让敏姐叫过来的。
我没叫,那自然就是你叫的了。
那你明白了?
明白了。
好,吃火锅我买单。
吃火锅的时候,纪朋飞拼命找出许多话题来跟余小姐套近乎。实在找不到话说的时候,就拿手机出来,念短信里面的荤笑话。但余小姐根本不笑,一次都没笑过,只埋头吃自己的火锅。他又想替余小姐看手相,余小姐却固执地不拿手给他看。
他便说,那我只好就这样跟你说了。
余小姐问他想说什么?
他搓了搓自己的手说,关于你的命相。
余小姐冷笑一声,你看都没看,能说出什么?
他也嘻嘻一笑说,没看你的手但我看了你的脸啊。
余小姐突然把手中的筷子一扔,冒火地说,我看你是不要脸!
一旁的我惊了一下,没想到她这么猛。
接下来,这火锅就吃得很尴尬了。到最后,纪朋飞站起来,走到外面假装接一个电话,接了半天,然后回来说,他有点急事要先走一步,单他已经买了,让我慢慢陪余小姐吃。
我们都没表示什么。等他走了之后,余小姐才开口说话:男人都他妈这样。
我感觉我的脸在发烫,有点挂不住的样子。我问她男人都他妈怎样?
她抬起头来,诧异地看着我,然后说,对不起,我忘了你也是男人。
我是不是男人没关系,我只是好奇,你以为的男人都他妈怎样?
你生气了?好吧,我道歉,我说的男人不包括你。
这无所谓,我没生气。我确实是对你的那句话很好奇,你想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忘了我想说什么了。我忘了,我记性不好,可以吗?
我笑了。我突然意识到,她的话多了起来,而且还那么喜欢饶舌。这时候再看她的脸,她其实称得上漂亮。她脱了外套,露出了里面的吊带装。
我说,可以。
她突然也笑了,说我这个人很真实,不假,不像走掉的那两个男人。
两个男人?
打麻将的时候不是还走掉一个吗?看来你也有健忘症啊,哈哈。
她用这“哈哈”声进一步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就这样聊着,气氛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她告诉我,她其实不是姓多余的余,而是姓于是的于。
不想再打听一下我叫什么名字吗?她又哈哈一笑。
我觉得她开始有点挑逗的意思了。于是,我建议她也喝一点酒。吃火锅的时候她一直推说自己不会喝酒。我说喝酒这种事至少是两个人才会有乐趣。但她说,要喝可以,换个地方喝。
于是,她把我带到了一个酒吧。
我是个很被动的人,比较容易受人摆布。前妻苏无艳就属于那种喜欢摆布人的人。尤其在性方面,她的摆布欲体现得尤其充分。有时候,她规定我们逢单做。过不多久,她又改了规定,逢双做,而且不告诉我理由。她还规定,过了零点以后不能做,下雨打雷不能做,喝了酒不能做,心情不好不能做。这样下来,能做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多了。我可能就是这样开始失眠的。
我泡过不少酒吧,但这个酒吧却让我闻到一种陌生的气息。很特别。怎么个特别我一时还说不出来。笼统地说就是它特别不像酒吧。这感觉把我搞得很拘谨,忽然觉得自己出现在这里就像一个傻瓜。
已自我更正为于小姐的女人对这个酒吧好像很熟悉,所以显得特别自在,一下就变得容光焕发,光彩照人了。她问我要喝什么酒?但我还没回答,她就替我安排了一种酒。你尝尝这个酒,我敢肯定你以前绝对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她的举手投足以及说话的语气都流露出一种奇怪的自信。我有种预感,别看她说得这么神秘,可能等到那个酒送上来后就会发现,那其实是一种很普通的酒。
但我的预感错了。那个酒被装在一只玻璃杯里送上来,看颜色我就认不出是什么酒。在她的注视下,我端起来尝了一口。很特别的味道,的确是我没喝过的。我知道她马上就要问我是什么感受?于是我抢在她的前面问她,这是什么酒?
其实就是啤酒,但你肯定没喝过,因为它已经不是啤酒了,是用特殊方法专门处理过的。你再尝一尝。说着,她自己又喝了一大口。喝了酒之后的她,眼睛和嘴唇都变得格外的湿润。我发现自己有点喜欢上这个女人了。
你想不想跳舞?她问。眼睛热切地看着我,把内心的东西表现得十分直接。
但是,经她这一问,我马上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知道这间酒吧的特别之处在哪里了。这是一间可以跳舞的酒吧。或者说,它就是一个舞厅。这是很明显的啊,但之前我怎么就描述不出来呢?

王华祥-《某日》 110×80cm2012
我略微迟疑了一下,才接受了她的邀请。这不是故意装。在那迟疑的片刻,我还在想别的一些问题。但很快我就决定放弃这些问题,告诫自己不要想太多,眼下只需按本能和直觉行事就行了。于是,我抓住她伸过来的手,离开座位,像旁边那些男女一样,搂抱着开始跳舞了。
你的舞跳得很好。她贴着我的脸这样说道。
我明白此时她说这样的话也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紧张。因为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这根本不像是在跳舞。我们搂抱在一起,连脚步都没有移动过一下,只是随着音乐的节奏做一些轻微的摇摆和晃动。这时候便感觉舞曲长得令人绝望。再这样下去,我真的就要憋不住了。我叮嘱自己,一定得转移一下注意力,以便降低大脑皮层的兴奋度。
这酒吧很特别,我说。想在这个话题上开始转移。
嗯。她只这样简短地回应了一下,并不想顺着我的话题多说点什么。她好像有点醉了,抑或是累了,将整个绵软的身体完全贴在了我的身上。
你,要不要去坐一下?
你想做?好吧。
后来我才知道,她把我说的“坐”理解成“做”了。
你想在哪里做?她问道。
还是去刚才的地方,我们的酒还在那里,没喝完呢。
在那里啊,你想怎么做?
跟她说话的时候,我眼睛一直在看周围那些跳舞的人,感觉很怪异。这里不仅跳舞的人特别多(别的酒吧基本不跳舞),而且跳法很特别,很怪异。男的一般都把自己的手要么按在舞伴的屁股上,要么干脆伸进她们的怀里。舞伴们都穿得很暴露,一律的吊带裙。她们的裙子时常要被其男伴掀起来。男的一律年龄偏大,像我这样的中年男,秃顶的还不少。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哪里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砂轮厂啊。
砂轮厂,即色情舞厅的别称。在这里跳舞,称为跳砂砂舞,简称砂。这里的陪舞小姐被客人们私下叫做砂妹。陪跳一曲十元钱,包场三到五百。由于跳舞时一般都是将身体紧贴在一起做磨砂状,类同砂轮的工作原理,便有了此名。有次我在常去的一个酒吧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自封为“砂皇”的中年男人。是他那天晚上热情地向我介绍砂轮厂,我才知道这座城市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个女性朋友,她们平常都是朝九晚五的机关女,很少知道江湖上的事情。因此,刚开始的时候,这几个笨女人还真以为砂轮厂就是生产砂轮的工厂。当得知真相以后,便一致认为这是个极不健康和道德的场所,并对“砂皇”这个男人顿时起了反感,彼此之间还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没想到,此时此刻自己竟然已神奇般地置身于这个传说中的地方。
你走神了,在想什么呢?她问。
她说得不错,我走神了,以至于刚刚那种紧迫的爆炸感已经没有了。这种生理反应的变化,自然被她感觉到了。
我便笑了起来。我对她说,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
她很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我,什么地方?
砂轮厂。
你才知道?你走神就是在想这个?
是的。
难道你以前没来过?
是的。这是第一次。
不可能。哈,你真土。那么感觉如何?
还好,跟传说中的一样。这样我也放心了。
放心了?你放心什么?
不害怕我们这样抱着的那种后果了。
哪种后果?
你说呢?
你这么文绉绉的,我听不懂。
但我听懂了,你说的那个做是什么意思。是做爱的意思,对吧?
天,开什么玩笑?你以为还会是别的什么意思吗?
我开始以为你说的是坐椅子的坐。
我怎么遇上你这样的笨蛋?
那现在,我们还做吗?
你让我想想。怎么说呢?说真话,你让我有点扫兴了。真的,我现在的感觉,就好像是,算了,我没法形容。你知道吗,你让我尴尬了。
对不起,小于。
不要再说了。不要这样,你让开。今晚就到此为止。不说了,让我走。
她推开我的手,从我的怀里挣脱出来,带着我刚认识她时的那种漠然的表情,去吧台取了自己的包,毫不理会跟在一旁的我,径直往舞厅的出口走去。
外面真的下起了冰雹,我为她担心,急忙在吧台借了一把伞,跟着她跑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