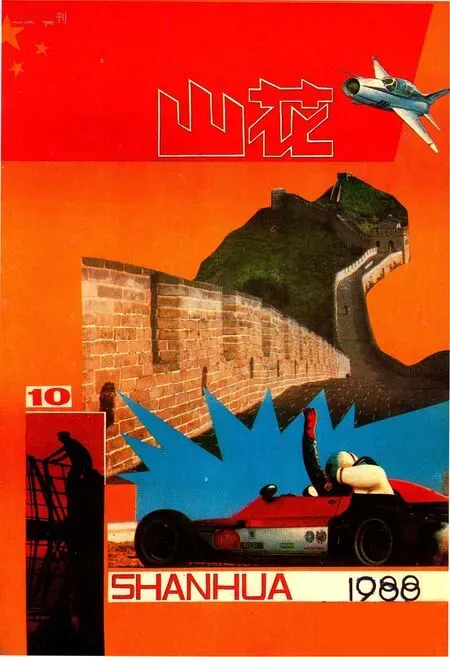生 还
2014-12-02
和P分居之后,我搬回了母亲的老房子。房子在市中心,紧挨着中心广场,小时候别人问我你家在哪里,我就会说,你知道毛主席打车的那个广场吗?几乎所有人都会点头,知道知道,就是伸出手,说起价费五块。我说,我家就在他大拇指的那个方向。时间过得真快,现在的起价费已经八块,下车的时候还要加一块钱的燃油费,毛主席没动,一直站在那里,不过翻修了多次。有一年气候异常,据说是附近的某个烟囱里面有硫,有那么几天,在广场跳舞的女人会突然发现丝袜崩裂,露出光溜溜的大腿。毛主席的大衣也开始掉毛,离远看去,好像患了牛皮癣,因为脸上的皮也掉了几块,所以原先和蔼可亲的笑容也看着诡异了,近于狞笑。而现在,问题解决了,工厂都迁到了市郊,原先的农地上。那熟悉的,凛冽得有些亲切的气味消失了,毛主席换上了新的大衣,看上去比过去壮了一圈,大拇指继续指着我家的方向。
母亲的房子是楼房,有十六层,小区里面一共五栋,紧紧挨着,相互遮住彼此的阳光,因为地皮紧张,当年的设计者看来是颇花了些心思。我家住在七层,厢房,两个卧室朝东,厨房朝北,夏天的上午七点钟左右,会有一片阳光准时落入卧室,照亮我儿时的大半个书柜和一半的地板,叠被的时候能看见颗粒状的灰尘在光束里飘荡。我家的猫咪阿里,这时就会躺在地板上翻滚,让阳光抚摸它的脊背和肚皮。八点钟左右,阳光消失,好像突然间有谁用手拉了一把百叶窗,屋子里马上暗下来,阿里跳上窗台,伸着脖子看着窗外,目送着阳光向另一个窗户走去。我在这里住了十一年,期间父亲去世,原来每年冬天,都是父亲登上椅子,刮掉顶棚角落里的黑霉,父亲死后,这活落到我的身上,我发现,原来黑霉已经深入墙身,无论怎么去刮,都无法消灭,但是像父亲一样,我没有说出这个事实,每年冬天,当母亲递给我一把椅子,我都会登上去,把表面的那层东西刮掉。
在第十二个年头,我与P结婚,搬出了这里。新家在城市的另一头,毗邻水库,阳光大好,只是有些噪音,因为库边有坝,坝上走车,每到夜里,就会有运土石的大车驶过,好像有人在我们头上敲鼓。但是就像人一样,没有一栋房子是十全十美的,总得有些取舍。分居之后,我们商定,房子归她,几年来攒得的书和碟片归我,雇车拉回家。到此为止都很顺利,只是在女儿小Q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我不上法院,一起睡过觉的人去站在法庭的两侧,在我看来是十分难堪的事情,但是通过协商又总是谈不拢。此时的P已经远和过去不同,逻辑缜密,果断决绝。她曾经是一个独立书店的收银,后来书店倒闭,跟着同学卖起了保险。她从不单独见我,每次都是带着父亲母亲哥哥嫂子一众人等,建起一个迷你陪审团。我算了一下,她说,像是在推销一款相当合算的保单,抚养一个孩子,到十八岁,就算十八岁好了,需要大约六十万,你有吗?我说,现在没有,我可以挣。她说,你靠什么挣?你的医保社保,过去都是我替你交的。这时她的哥哥插嘴说,有一次给小Q买感冒药,还用了我的医保卡。在家写了三四年,屁也没有,还当自己是文曲星?我说,我现在是能力弱一些,可是会越来越好的。她把身子向后一靠,停顿一下说,做梦。然后眼泪就流了下来。
老房子有电梯,但是经常出故障,有几次突然从顶楼坠下来,直接把你送到半截腰。里面的人全都摔倒在地,相互倾轧,门突然开了,关上,开了,关上。好像在提醒你,如果你跑得慢,就又会上去了。找了几次维修,说这个老小区,已经没有物业,完全脱管,如果要修理的话,需要大家凑钱,这时大家就都沉默。过去,大家都担心,万一电梯出事,自己在里面怎么办?而此时,大家又都相信,万一电梯出事,自己一定不会在里面。于是依然坐着这部电梯上上下下,各自生活。搬回来之后,阿里就从我的房间搬出去,睡在客厅的旧沙发里,我除了写作,还负责给她喂食,洗澡,换猫砂。而母亲已悄悄把我的房间恢复成我读书时的样子,连小时候的歪脖子台灯都帮我找出来,放在书桌上。她知道我现在写小说,但不知道我具体写的啥,她也知道我笃定以此生活,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放弃。有一次她和我说,小说写得咋样?我说,还行。她说,就是讲个故事,就让人买去?我说,不只是故事,故事和小说不一样。差不多。她说,我想见小Q。我说,她在托儿所,周末我联系一下。她说,小Q满月的时候,挂着我买的小金锁,上面是条小蛇。我说,知道,周末我联系一下。她说,小Q周岁的时候,二十三斤,抱久了,胳膊就酸。我说,妈。她说,如果有一天,我身体不行了,你怎么办?我说,你身体好着呢,以后我伺候你。她说,如果不是你爸死,是我死就好了,你爸喜欢看报纸,还能帮帮你。我说,妈。她说,你忙吧,周末联系一下,我给小Q买了件衣服,都要小了。
因为光线不足,台灯白天也点着,灯泡费得厉害。一天晚上母亲已经睡下,灯泡突然爆了。我把阿里从我膝盖上拿下去,走出门,站在电梯前面。

王华祥-《等待花开》 板面油画 120×80cm2014
电梯停在十五楼,久久没有动弹。我按了几下下行的按钮,完全没有反应。这时突然听见一声巨响,电梯从上面迅速地滑下来,然后紧接着“哐当”一声,显示屏黑了,不知道电梯去了哪里。我等了一会,没有求救声,也没有人拍门板,便准备从楼梯下去。这时电梯门开了一条小缝,一片刀刃从里面伸出来,把电梯门别得更开了一点,露出一只手和一顶红色脑袋。我才发现,原来电梯卡在了六层和七层之间,80%的部分在六层,20%的部分在七层。手把刀扔在走廊里,差点砍在我脚上,然后两只手扒开门板,红色脑袋完全伸出来,带出一个窄小的肩膀。我走过去拽住他的领子,他说,哎我操,要把我勒死了。我赶紧撒手说,那我拽你哪里?他向下一滑,说,大哥,拽头发啊。我抓了一把他的红头发,把他从门缝里拖了出来,门板顺着他的脚尖合上了。他立起来,吐了口吐沫在手上,把头发理了理,原来是像板斧一样,中央挺立,两边露出白花花的脑皮,被我一抓,成了灌木丛。理好之后,他捡起地上的砍刀说,大哥,这电梯老这样吗?我说,是,经常抽风。他说,我刚才以为自己要跌进十八层地狱里了,操,心里“忽悠”一下,一辈子都在心里过了一遍。我说,以后还是尽量用走。刚才抓你,我力气用得不小,你没事儿吧。他说,没事没事,我的头发经常被人抓,一点也不疼。他看了看腋下的刀,又看了看我说,大哥,有报纸吗?我说,没,但是我家就在旁边,可以帮你取。他微微低了低脑袋说,谢了。我回家给他取了一份报纸,某南方报纸的文化版,上面详细报道了一个行为艺术家给人隆胸的事儿,他接过去把刀包好,我看见那个艺术家的试验品裸着上身,弯成一个弧形躺在他的腋窝底下。他朝我伸出手说,东子。他看上去二十一二岁年纪,瘦得厉害,两条腿比擀面杖粗不了多少,一对锁骨好像两根筷子,在领子底下支着。手却挺大,把我握得生疼。我住十五楼,他说,有事可以找我,在走廊喊一声,东子,我就出来了。我说,好。他说,但是得在白天,晚上我都出去。我说,好。他说,我帮人砍人,一次八十。我说,什么?他说,不能砍脸,不能砍手脚,专砍后背,公交车来回,八十。如果顺便砸东西,就是一百五。我说,哦,要是砍脸呢?他说,那就贵了,得细分,看对方是什么人,要砍到什么程度。我说,和脸的大小有关系吗?他乐了,说,有关系,像哥你这种大方脸,就得多费几刀。这时电梯的显示屏亮了,7,悬挂电梯的钢绳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把电梯提到了七楼,门开了。他向我摆摆手,你今天拽我,如果你有事儿,我白送你一次。说完他走进电梯,按下按钮,关上了电梯门。
我走下楼梯,到超市买了一打新灯泡和一包烟,然后去广场走了一圈。毛主席的手底下,一群老人正在跳舞。其中有一个老太太好像是傻了,别人在跳舞,她则冲着大人物拍手,时不时转一个圈。领舞的男人是我母亲的老同学,患癌已有十几年,此时带着漆黑的假发,用力地扭着,鬓角露出白茬。我坐在台阶上,看着他们,想起我那没有阳光的房间,和每天早早睡下的母亲,感觉到一只手摇曳着我,好像要把什么东西从我里面晃出来。这时我兜里的电话响了,是P的号码,我接起来。
“爸爸。”
“小Q,你怎么还没睡觉?”
“爸爸,你先不要说话,我给你讲个故事。”
“讲吧,讲完就去睡觉。”
“有个女孩儿叫桃乐丝,她没有心。”
“再想想。”
“不是不是,不是她没有心,是稻草人没有心,还有一个狮子跟着她们,狮子胆子小,不咬人。”
“然后呢?”
“然后他们找不到家了,想要回家,然后就有一个坏女巫,还有一个好女巫,还有一群小老鼠,还有龙卷风,还有......”
“还有啥?”
“想不起来了,妈妈要洗完澡了,有机会再给你讲。”
“好。”我说。
“爸爸,你是不是也找不到家了?”
我把电话放回兜里,抽着烟继续看老人们跳舞。过了一会,老人们渐渐散了,玩轮滑的孩子们也都走了,然后一个醉汉从中间穿过,领带像蛇一样荡在脖子上,皮鞋踩在砖面,发出不规则的声响。最后广场上空无一人。管理员从岗亭里走出来,开始捡拾人们丢掉的垃圾。他看了看我,和一地的烟蒂,没有说话,从我身边走了过去。走到家门口,我看见了东子,他正在路边的烧烤摊吃肉串,包着刀的报纸摆在桌子上。他看见我了,向我招手,我走过去说,下班了?他说,下班了,吃完串,兜里还能剩下三十几块,去上网。我说,今天去的哪里?他看了看正在翻转肉串的新疆人,说,水果摊。我说,砸了?他说,砸了,老板跑得慢了,耳朵掉了一只,这不怪我。大哥坐下,喝一瓶啤酒。我说,不了,我要去上班。他说,大哥是做啥的?我说,你看呢?他说,出租车司机?KTV少爷?咱俩不会是同行吧?我说,不是,你看我这身板,也干不了你那活。他说,和身板没关系,我这身板,放个屁自己都得晃悠,主要是胆子。我说,对,我就是没胆子,你吃好,我回去了。他说,我在十五楼租的房子,三个月,然后就搬走,一个地方不能老待,有机会一起喝点。我说,好。你是哪里人?他说,城边农村的,地没了,钱都让我哥拿去,我就混到这里来,我们屋有三个人,都和我一样。我说,好,走了。
我听母亲讲过,我们这楼里,住了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昼伏夜出,大都脸色苍白,头发五颜六色,具体做什么不太清楚,但是肯定不是正当事情。他们都有固定女友,一般是KTV的陪唱,或者是洗浴中心的按摩师,工作时间基本吻合,主要是搭个伴,有时候就在楼下大打出手,酒瓶子摔得当当响,几天后,又挎在一起,出去逛街。

王华祥-《等待花开之老区》 板面油画 120×80cm2014
过了一段时间,P打来电话,说实在不行就上法庭,这么拖着不是办法。我说,你是有人了吗?她说,这和你没关系,主要是小Q的问题不能悬着了,我天天睡不着觉。我说,房子都给了你,孩子就给我吧。她说,那房子,早上把人晒个半死,夜里好像在搞阅兵,现在我想脱手都没有下家,你怎么还好意思提房子?我说,你一定是有人了,人家有房子。她说,我是正常人,和你不一样。我说,什么时候有的?她说,你无聊吧。我说,不无聊,你如果有人了,可以再生一个,你年轻,身体也好,小Q当年顺产,第二次生就容易了。我只有小Q,把她拿走,我妈和我都会疯。我听我妈晚上讲梦话,都是给小Q买吃的,小Q你慢点吃啊,她在梦里喊。那头沉默一会,说,不说了,等传票吧。然后把电话挂了。
自从我搬回来之后,好像回到了小时候,母亲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我每天读书写作。唯一的不同的是,母亲的身体不如从前,在走下坡路。有时候她在烧着水,忘记了,去给阿里拌饭,壶就烧漏了,弄得满屋子都是烟。有时候她看着我儿时的班级合影,急得满脸通红,就是想不起坐在中间我那个初中老师的名字,而过去,这些人都好像是她的家人一样,印在她的脑海里。
也许有一天,她会忘记我的名字,但是知道我是谁,不知道她会不会忘记小Q的名字,也许会,也许不会。
我再也没有接到过小Q的电话。
一天上午,我来到十五楼的走廊,里头堆了许多杂物,已经龟裂的酸菜缸,废弃不用的旧沙发,还有变形的儿童车。我喊了一声,东子。没有人回答。我把手拢在嘴边,喊:东子!一扇门推开了一道缝,一个只穿着内裤和胸罩的女孩儿蓬着头发闪出来说,你谁啊,大白天不让人睡觉,操你妈的。这时东子从后面探出头,看了看我,好像琢磨了一下,说,哥,有事?我说,有事。他说,你等一下,咱外面说。不一会儿,他换好衣服出来,我递给他一支烟,帮他点上。他说,说吧,困着呢。我说,想请你做个活。他说,行,八十的还是一百五的?就我一个人,还是给你拉个队形,要哪种?我说,你一个人就够,我钱不多。他说,先说说什么事儿吧,再说别的。我说,我和前妻准备离婚,女儿她不给我。他看了我一眼说,这事儿你得找居委会,上法院也行,找我错了,俩系统。我说,没错,我想请你吓唬吓唬她,让她把女儿给我。他说,这是吓唬的事儿吗?家里的事儿还是关上门办吧,我回去睡觉了。我说,我给一百五。他说,哥,我还没说明白吗?你们两口子的事儿,今天可能来气了,不共戴天了,明天在一块睡一觉,又好了,回头把我折进去。我说,好不了了,这两天传票就到,肯定是陌路。这是五十你先拿着,剩下的事后给你。他看了看钱,说,哥,上次你拽我,我跟你客气客气,你这事儿一百五办不了。我说,就是吓唬吓唬。他说,是,是吓唬吓唬,但是万一出了点岔头,或者没吓唬住,她炸了,我上不上手?一旦动手,这就贵了。而且吓唬了不一定好使,可能倒给她惹急了,你的目的还是没达到,我钱也不能退。我说,你要多少?他说,三百,三百我帮你办。我说,三百我没有,二百吧,各退一步,那一百五回头给你。你别碰她,要是她反抗,你就跑。能跑多远跑多远。他说,跑我会。还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我想了想说,如果她不给,就跟她说,让我跟小Q见一面,我已经很久没看见她了,我妈还给她买了衣服,要小了。他说,价位不变?我说,不变。他说,成,把照片和上班的地方给我,你等信吧。
几天之后,传票到了。我看了看,藏了起来。没有接到P的电话,也没有东子的消息。我过去的一篇小说,毫无征兆地突然发表了,没有任何反响,我把那本杂志包上书皮,放在儿时的台灯底下,没事就拿起来看看。母亲住院了,她开始不认识筷子,不知道那两根竹子是什么,要想好久。每天我都带阿里去医院看她,她还认识阿里,甚至能记得上一次给阿里洗澡是什么时候。
她很久没提起小Q了,只说我小时候的事情。
第二天就要上庭,我再次想起了东子。不知道他见没见过P,但是我确定他肯定没有伤害她,因为我从她朋友那里得知,P正在筹备婚礼,情绪高涨,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早上,我把带回的旧书翻出来,摊在阳台上,迎接那一个小时的阳光,阿里趴在书页间,用手掌洗着脸。我看见远处的大人物用大拇指指着我,好像这么多年,第一次注意到我一样。我再次走上十五楼,敲了敲门,一个中年女人开了门,说,你找谁?我说,我找东子。她说,没有这人。我说,他上个月还住在这儿。她想了想说,我知道了,他们那帮人。我说,我不是找那帮人,我就找东子。她说,他们让老警端了,然后用手指了指楼道里的那口酸菜缸,那里面都是刀。你和他们什么关系?我看了看酸菜缸,说,没什么关系,就是一个楼里住的。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了P的电话,她说,准备好了吗?别迟到。我说,放心吧。她说,你赢不了。我说,知道。但是我去。她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会,说,今天我带小Q去,她要给你背诗。我突然感觉眼眶里面很痒,使劲眨了眨,说,好。她说,你妈给小Q买的衣服也可以带来,如果小了,我给老二穿。我说,好,你知道?她说,你有个邻居来找过我,穿得挺正式,就是头发太傻了,像个洗头的。我说,哦,他还说什么了?她说,没说别的,说他从小就认识你,你现在有出息。也认识你妈,她每天晚上在广场跳舞,他晚上没事就在广场看她们跳舞。我说,一会见吧,完事儿如果有时间的话,别着急回去,让我和小Q多待一会。
晚上回家,我看见一群人站在电梯前面,电梯门开着,里面是一个黑洞,有几个人站在边缘,朝下面望着。我问,怎么了?其中一个人扭回头说,电梯从十六层掉下来,摔烂了。我说,里面有人吗?他看了看我,好像我的问题愚不可及,你什么意思,他说,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