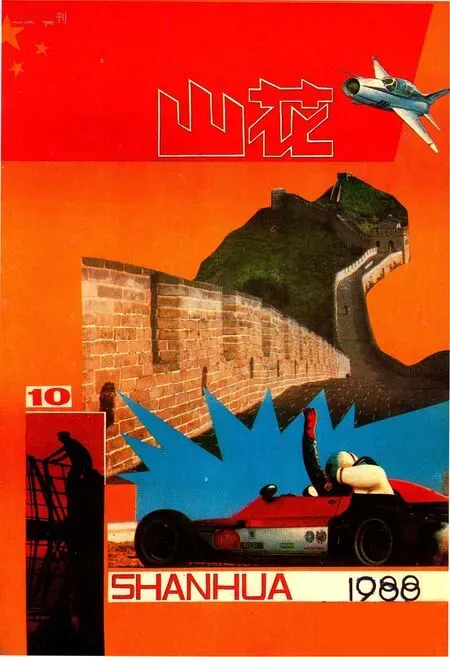两个世界,或一段路
2014-12-02
一
女儿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画画?我想,应该是从她出生后第三天,我岳父给她脚底涂上墨水在白纸上留下人生第一个足印的那一刻开始。在绘画方面,女儿多少还是有点天赋,说这是家族遗传也不为过(鱼的孩子天生会游泳嘛)。过年掸新时,我在墙角发现了女儿多年前偷偷写下的我和她的名字。我想,那几个笔划杂乱的字里面定然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快乐。
因为妻子在家里办了一个书画学馆,女儿打三岁时就开始跟一些大孩子们一起,涂涂抹抹。人之初,心之初。小孩子们的胡言乱语有时可以变成传唱一时的童谣,小孩子们的信笔涂鸦有时也可以变成一幅精妙的漫画或抽象画。童心明明如月,无论怎么看都是好的。我粗粗翻阅过几个学童的作品,他们写的字,大抵如我岳父半溪先生当年所评价的:胆气特别大,而且是怕小不怕大的。他们所作的画,在构图、色彩表达能力上也是出奇地大胆,没有刻意追求变形,反倒有一种不似之似的效果。有一个七岁的学童,画的是京剧脸谱,结果把整张脸画得五官挪位,像个急张飞。那天他刚刚被被爸爸训斥了一顿,心底里还十分憋屈,于是,忽发奇想,在空白处歪歪斜斜地写上五个字:生气的爸爸。这下子,就让败笔变成了生花妙笔。女儿跟我怄气的时候,就会将我画成牛头马面。但她正儿八经坐下来画牛头马面的时候,反倒少了意趣。妻子曾嘱我写一篇谈论儿童画的文章,我却不知道如何着笔。何谓儿童画?《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专门的解释。丰子恺先生曾为儿童画下了这样的定义:儿童画是思想感情特殊而绘画技术未练的一种人所描绘的画。因此,中国画可说是“先练的儿童画”,而儿童画可说是“未练的中国画”。从传统理论来讲,一幅字,我们讲求的是用笔、结体、章法;一幅画讲求的则是构图、色彩、造型三元素。但对小孩子来说,他们画画时通常不会考虑到怎样运用对比、节奏、平衡之类的东西。他们的一勾一划纯然出乎天性,有时会莫名其妙地给我们的审美趣味一记闷棍。有不少书画名家都曾试图让自己的书画艺术回归童趣,惜乎难求。一个人身上的童心,最初的一念之本心,早已是渐行渐远了。
女儿之爱涂抹,是把画画当作游戏的一部分。画不画,两可;画得好不好,不在乎。重要的是,她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有一回,我们家的画室要粉刷一新,妻子让女儿在铺了底漆的墙壁上随意作画。起初,她画得有些拘束,及至放开后,她把自己喜欢的卡通人物和动物都一一画出来,大小比例跟她相等,仿佛唯其如此,才能跟他们够得上平起平坐的朋友。女儿六岁的时候很喜欢看特伟的动画片。尤其是《三个和尚》,她几乎看了上百遍。她一度热衷于画三个和尚,高低胖瘦,画起来特别带劲。有时我说她画的人物身体不成比例,缺这少那,她也置之不理。我有我的想法,她有她的画法,小孩的世界何必跟大人求同?跟大多数孩子一样,女儿不喜欢大人的那种画,仍然喜欢那种变形、夸张的儿童画。我认为很大的东西她画得很小,我认为很小的东西,她倒画得很大。她将小东西变大,或是变得更小,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我甚至不能自以为是地理解为:这就是小中见大或大中见小。女儿的画再丑,我也要厚着脸皮夸她画得好,竖起拇指奉送她两个字:第一。后来女儿画了一朵荷花,就立马跑过来向我讨“第一”;画了向日葵花也要向我讨“第一”。每回都夸她“第一”,女儿就若有所悟地问我,你说荷花第一、向日葵花也是第一,到底哪个是第一?我说,在爸爸的眼里女儿所画的每一朵花都是第一,没有第二。
有一天,女儿画完了一张得意之作,突然问我,像不像?我想,女儿已经长大了。她已经知道一张画像什么就是画得好,不像什么就是不好。
二
女儿及龄,要上小学一年级了。家里的老人听说孩子要“上学堂”,不禁感叹时光流逝。隔壁的阿十太公说,先前的孩子上学堂是要有一种仪式的。儿童发蒙之日,外婆要送来汤圆、猪肝、鲫鱼等十碗菜,俗称“十魁菜”,有讨彩的意思;有些人家更讲究,要请先生用天落水蘸朱砂在孩子的眉心点一下,以示祈福。细说起来,从进学堂写第一个字,到谢师出堂,都有一套完整的仪式。这些仪式虽然简单,却充满了一种庄严的喜悦。后来读到王丽女士一篇谈传统教育的文章,写的是有些学校在孩子入学那天举行了盛大的仪式,颇有复古之风,但我总觉着此举有逞意造作之嫌。
女儿娇小,上学之初却背上了一个大书包,还有拉杆,就像是出远门。我对妻子说,给他买个小点儿的书包吧。妻子却说,你不懂,现在小孩子都是背这么大的书包。我估量了一下,这书包高约两尺,重约十斤。女儿刚刚上学那会儿的体重则是三十七斤。按比例算相当于一个一百四十余斤的人每天背四十斤的东西。
我送女儿去上学时,看见一些高年级的男生都背着一个大书包,从后面望过去,只露出一个小脑袋和两条细弱的小腿,仿佛他们变成了两条腿的书包。我在城里见过一些初中生或高中生的书包,那才叫“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
这些年,读圣贤书读出了菩萨心肠,有些物事,我是不忍目睹的:一匹老马的眼泪,刚刚丧失双亲的孤儿的眼睛,仍然在水中作垂死挣扎的雏鸡,车轮底下压着的血淋淋的细小手臂,被火点燃的无处奔逃的幼鼠。还有就是,瘦弱的孩子背后的书包。
我总是怕女儿不堪负荷,让她把书包里的东西掇一些出来。但女儿说,我背得动。给她减负,她反倒不高兴。在她看来,像那些大孩子一样背着一个大书包似乎是一件荣耀的事。
我当年挎着一个军绿色卡其书包,比现在的书包要小得多,里面没有几本书,有时候连书包都没有背回家。我“背着书包上学堂”的那条路是一条石头路。放学之后我没有径直回家,常常放下书包在野地里撒会儿野。比如捉蝴蝶、掷泥巴、跳水渠、挖荸荠、摘槐豆。快乐俯首可拾。
有一回读报,看见教育局发文,说是孩子们的书包过重,很替孩子们担忧,于是乎作了些硬性规定。书包轻重,也要教育部门发文申明,这真是一件悲哀的事。书包轻重应该是学生自己定的。我们那时候的书包里也就语文、数学,以及薄薄的作业本。有时嫌书包太轻,还要塞几本连环画之类的闲书。我有一位同学,经常在书包里放一块沉甸甸的砖头,这样,他走在路上就不怕被人欺侮了。

王华祥-《等待花开之细细》 板面油画 120×80cm2014
三
女儿读的是柳市一小。这所学校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的祖辈都曾在这里念过书。我自然也不例外。尚记得学校北面有一座小洋楼和碉楼,但现在早已拆除。小学二年级,我就在那栋楼的一楼教室念过书。楼上住着一些老师及其家属,每逢放学时分,便能听到头顶上空传来脚步走动的声音,想必是老师们(或家人)也已回到宿舍,开始做一些洒扫炊汲的家务活了。我们教室边上有一座废园,那里杂草丛生,一片黯默的绿色中夹些不知名野花,或黄或红,但无生气。偶或钻出一只野猫来,趴在窗台上,听老师上课。有人呵斥,它便倏忽不见。偶尔,也有些胆子大些的同学扒开窗户上的木条,从窗台上爬出去,他们在废园里转了一圈就出来了。胆子小的同学讷讷地问他们,里面有什么?他们故作神秘地告诉大家,那里面是一些骷髅和石碑。总之,那块地方虽然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却颇费猜测。过了一年(或者是好几年),有几个民工来到这座废园,竟真的挖出了一些无主尸骨。
以前有个姓陈的老师,高挑个子,年纪不大,每周一总要把学生集中到操场上,而他就模仿伟人站在二楼,对着一个喇叭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宣读教条,无非是不准我们这样,不准我们那样。有些逾规的事,我们不仅没有犯过,连想都没想过。经他一说,我们反倒想试试了。记得大人们时常提起一句毛主席语录:狗屎可能肥田,人屎可能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天性不拘,哪里还管那么多教条?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一位教自然的女老师,她跟我们讲的都是一些清明、浅显的常识,没有什么大道理,“就像是把点心放在低矮的柜子里,让每个孩子都能伸手可及”(布道者穆迪语)。
我们这些男孩子每逢休息时间最常去的地方便是学校南端的“司令台”。这个水泥浇注的台子在六、七十年代专门用于批斗大会,到了八十年代,就用于镇上的公判大会。每逢节日,学校的文艺演出也时常在这里举行。平时,“司令台”就是我们这群男孩子撒野、打架的地方——它总是像一个巨大的磁石那样把我们一个个吸引过去——我们所玩的游戏几乎就是野蛮人的游戏。有一阵子,我们就在台上玩一种淘汰赛。谁被对方推下台,就取消再登台的资格。台子虽然只有四尺多高,但从上面摔下来也是难免要挂点彩的。我有好多回被人从台上推下来,却都安然无事。最后一个站在“司令台”上的男孩子总会受到众人的追捧。有时我想,一个人站在“司令台”上,双手叉腰,再别一把驳壳枪,对台下的人发号施令,想必也是一件很威风的事吧。我曾经站在“司令台”上俯视过众人,但跟平地所见无异,于是乎很扫兴地下来了。我的玩性很大,学习成绩并不理想,人又有几分古怪,所以,老师也懒得理会我。上学的时候,我时常在“司令台”上撒野,一回到家里,关起门来,写我的武侠小说。在老师的眼中,我是一个沉默的坏孩子。
小时候,我因为缺乏“上进心”而被老师晾在一边。这一晾就是好多年。现在,我因为比常人多写了几个字,就被人目为“作家”了。身边也颇有些熟人带着孩子过来,向我请教成才的秘诀,我只是笑而不答。话说得直白了,怕误人子弟。也有些语文老师请我给中学生开一堂文学讲座,我也不好意思拂逆他们的好意,勉强答应下来。在他们的想象中,我小时候应该是那种标准的好学生:言行规矩、读书用功,外示一脸的呆相,内心却溢满聪慧之光……听了我的自述,他们就傻掉了。不会吧,你怎么会是个坏孩子呢?还写武侠,杀气那么重,儿童不宜的……他们震惊、疑惑,于是就从另一个角度向学生们解读我的人生,以正视听。当然,我听了之后也只是微微一笑。我觉得读书不是跑步,而是散步。但在我们的中小学里,读书就是一种集体长跑。大人们的教诲迫使孩子们都齐刷刷地把两眼死死盯住前方的目的地,他们跑得太仓促了,所以忽略了路边的风景。读书的过程缺少了迂回、流连和驻足,它的乐趣自然就少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一个好的学校,它必须是宽容的。它可以容许一些有灵气的小孩子撒点野、搞点小恶作剧、犯点小错误,容许另一些木讷的孩子看着窗外的飞鸟发呆,容许一个嗓门洪亮的孩子像跳大神般跳到桌子上大声朗诵。
四
送女儿上学,喜欢走河边那条小路。右顾,是草坪,一片又一片树荫散陈着凉气;左盼,那就糟糕了,一条大河,浑浊如面汤,且发馊。早晨的时候,颇有些人(老人和妇女)在草地上散步、锻炼。偶尔也有一两个流浪汉蜷缩在石椅上,头上盖着报纸,罗汉般,似睡非睡。如果离上课时间还早,女儿就在那里荡一会儿秋千。两三分钟之后,我们继续赶路。经过一条九曲桥,可以看到几个蓄着白胡子的算命先生坐在桥头的树荫下,一如既往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看着太阳如何把一棵棵树的影子拉长。过了九曲桥,我们照例要穿过一个桥洞。桥洞的墙壁上写着:禁止大小便。但很多人偏偏认准这地方便溺,有时就连一些狗经过这里都要就地撒一泡尿。真是不可思议。人畜粪便混杂在一起,便有了一股奇臭。每回,我们都捏着鼻子快步穿过桥洞,然后吐出一口长气。剩下这段路的旁边就是一些补丁般的平房,墙壁上每隔两三米就写着一个“拆”字。有些脸上涂着厚厚一层脂粉的妇人一大早便坐在巷口,像麻雀似的向外张望。女儿说,这些人一定没有工作,否则不会每天坐在这里。我说,她们坐在这里就是工作。女儿问我她们做什么工作,我没有告诉她。听口音,这些妇人都是外乡人,而且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她们每天七点半左右就过来上班,显得很敬业。她们时常把内衣、内裤晒在各自的巷口作为营业的招牌,眼睛观望着那些操着各路乡谈的客人(当然是男人,其消费群体大半来自于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衣衫不整的外来务工者)。冬天的时候,这些妇人就搬出一方矮凳,坐在那里晒太阳,打毛线衣,有时也把腊肉或鱼干之类的年货拿出来挂在竹竿上;春天的时候,她们也没闲着,就在河边养几只小鸡小鸭什么的。有一阵子,我还时常看见一名面黄肌瘦的少妇抱着一个小孩子,坐在小板凳上,一脸的茫然昧然。有了生意,她就把孩子交给旁边的妇人照料。还有一阵子,我接女儿回家时,偶尔还能看到一个八九岁模样的小女孩跟一个妇人坐在一起吃午饭。也许小女孩压根就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在做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念书的钱是从哪里来。她看到我女儿经过时,很想跟她打个招呼,但她一直不敢开口。她的眼睛很大,很清澈,让我看了十分难受。

王华祥-《等待花开之老任》 板面油画 120×80cm2014
在女儿眼中,我似乎是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上学或放学的路上,她常常向我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譬如:鱼在水里是怎么睡觉的?太阳为什么没有像月亮那样时圆时缺?月亮的另一面是什么样的?“我”出生之前的那个“我”在哪里?我可以作出自以为很“科学”的回答,但我没有告诉她。有些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但永远不需要知道答案。
五
前阵子,女儿要写作文《秋天的田野》。我家屋前屋后,早已没有田野了。驱车去邻镇,也只看见一小畈稻田。没有吃草的牛,也没有供牛吃的大片草地。这些年,一片接一片田野在我眼前消失了,这些都是工业时代过度开发土地资源带来的恶果。在我记忆中,晚稻黄熟的时候,便可以听到左邻右舍磨镰刀的声音。太阳底下,秋收的田野充满了辉煌的宁静。割稻客的身影时而沉入稻浪,时而浮出稻浪。站在田野中央,我仿佛可以感受到大地深处埋藏着一颗庞大而坚固的金黄色核心,它在秋熟时节一圈圈向外扩散——那时候,固然没有像哲学家那样想象大地与苍穹、凡人与诸神合而为一,但我脑子里似乎就有那么一种接近神圣的感觉。
小时候,生长农村,野性未驯。对老师,固然也敬重,但害怕居多。于是,敬而远之。放学之后,喜欢到田野里走一圈。风的形状时常在滚滚稻浪之上呈现,偶尔掠过飞鸟的投影,就像打水漂一般。有时候,田野间吹来的一阵南风比老师的训词更能使人归正,阳光亦足以益智。我外出,相与为伴的,通常是小黑。
小黑是我家的狗。我常常跟小黑在田野中奔跑。听到耳畔响起呼呼的风声就很过瘾。我问大人,为什么狗比人跑得快?大人说,因为狗比你多出两条腿。我纳闷:蜈蚣有那么多条腿,为什么就爬得那么慢?蛇没有腿,靠身体走路,为什么就爬得这么快?这些问题是我后来慢慢琢磨出来的。我一个人游荡的时候总爱琢磨一些事。
偶尔也能在田间看到两条野合的狗。年幼无知,不知道狗也是需要性事的。几个孩子围着两条正打得火热的狗,只觉着有趣。狗在孩子面前也不避嫌。大人来了,就挥舞手中的扁担,试图驱散它们。但它们无处隐避,只是在慌乱间共进共退。那时在我看来,它们粘连的样子有点像鱼和鱼钩:鱼往左,钩也随之往左;鱼往右,钩也随之往右。看样子大人也不忍心拿扁担拆散他们,于是转头问孩子们,你们知道狗在作什么?孩子们都茫然地看了一眼大人,又看了一眼狗。大人转过身来,刮一下某个孩子的小鼻子,笑眯眯地说,回头问你爹娘去。我也见过有位大人教过我们一个法子:若遇两狗粘连不散,就抓一把草木灰撒在它们身上。这样,它们自然就会分开了。我们试过,但不奏效。大人为什么让我们这么做,我至今不得其解。在田间,我曾见过村上的两条狗被大人当场击毙。确切地说,是一条狗(公母不详)被镰刀砍死后,另一条狗尚不得脱,或者是不愿意脱身也有可能,结果也吃了那个杀得性起的大人的一镰刀。后来才晓得,这两条狗的主人是仇家。仇家的狗怎么可以如此不知羞耻地在一起玩?但我也确曾见过两个仇家豢养的鸡鸭在田头一起啄谷、觅虫,端的是一幅和乐图景。一只母鸡给仇家的公鸡生了一窝小鸡也未可知,任谁也不会去管这档子事。但那个大人何以独独不能容忍一条狗跟仇家的狗相好?仇恨,尤其是那种埋进骨子里、流进血液里的仇恨真的是很可怕。

王华祥-《等待花开之老王》 板面油画 120×80cm2014
早稻或晚稻收割之后,田野一片空旷。天和地是完整地合在一起,给人一种无有穷尽的感觉。我们就在那片尚余稻禾残根的土地上追逐着,嬉戏着。在自然之怀里是没有什么规矩可讲的。风一吹,父母和老师的训词早已抛诸脑后,衣裳脏一点、说话粗野一点、举止放肆一点也就全然不在意了。我们的视野所囊括的物事甚少,但天地无比盛大。有一回,有个孩子指着田野的尽头问我们,你可晓得那边是什么?我们都摇了摇头。那个孩子说,田野的尽头就是天,天比地大,我爹说,爷爷就是从这里走过去,在天边消失的。我们不相信,就打算沿着田间的浅涧,向东走去。一路上,我们以飞腿跨过一道又一道浅涧为能事。也有人跨不过去,落进浅涧,溅得一身污泥。我们走了一里地,就看见一条弯曲的小河。河边有一排树,野老模样,在夏风中怡然自得。对岸还是一片田野,隐约可见农舍、路廊、庙宇。但我们见天色已晚,不敢再前行。自从我们发现了这个去处之后,整个夏天,我们便常常结伴出游。那些草木的绿意一直延伸到河心,原本是会教人宁静的,到了我们身上,却激发了几分生辣野性。几个同伴和我齐齐脱光了衣裳,先后跳到河里戏水。这条可称“野水”的河流阻止我们继续向前行走,寻找那个在天边消失的老人。它让我们沉浸其中,由内而外接受一种洗涤。我们在水中撒完了野,就爬上岸各玩各的,有人坐在岸边垂钓,有人玩泥巴,而我通常是独自一人坐在一棵现在早已消失的树下发呆。鸟在我头顶的树枝上,游目四野。整个下午,我什么都没干。有时低下头来,惊讶于一棵树的阴影竟是如此深长。
童年的每一天都是无比漫长的……
那时候,一个人长时间闷在家里的话就会招病。母亲向来不相信红皮书上写着的“用毛泽东思想战胜疾病”那一套鬼话,但她独独相信耶稣的话,而且知道祷告之外还是要给我看病吃药的。我一生病,母亲就得背着我穿过一片辽阔、幽寂的田野去乡村诊所看病。她实在背不动了,就让我下来步行。往往是,我们还没有走到诊所的门口,病就莫名其妙地好了,头不痛了,腿脚也活络了。我后来想,这一路上,若无神助,大约也是田野里吹来的清风、泥土间冒出的青草气息治愈了我的病吧。见我无恙,母亲也开心地笑了,说我像猫狗一样懒贱,越来越好养了。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屋后的田地已经彻底从视野中退出去了。我来到别处的田野,也没有像农民那样一屁股坐在泥土上了。我与泥土始终隔着一张椅子。或者说,是隔着一块薄薄的木板。多年来,竟日长坐,让我坐出了一身的小毛病(三十五岁之后,钙在不断地流失,从头到脚,总有几处会冷不丁地出点问题)。我身上的慢性疾病总是那么顽固地缠绕着我,有时我会忽发奇想,如果我像小时候那样时常去田头转悠一圈,那些疾病是否会一下子被风吹散,被地窍吸走?
也许是这样的吧。
跟我一样,现代人大都寄居商品房,上不见天空,下不接地气,我称之为“汉堡式的生活”。生生不息的楼群日复一日地吞噬我们的天空和土地。向上,我们看不到楼群背后的天空,向下,也看不到楼群背后的地平线。当山与城的天际线被肆意分割之后,我们就很少去关注天空了,我们也从来不会去区分在田野中仰望星空与登楼仰望的感觉是否有什么不同;当我们赖以仰望星空的田野也越来越少之后,我们也就渐渐觉得星空之于我们是可有可无的了。城市越来越大,天空越来越小。我们只有来到广阔的田野中,才能恢复与天地精神的联系。然而,这样的田野在我们这个镇上已经不易觅得了。
有一晚,我驱车闲逛走错了道路,车子误入田间的一条小岔道。前面只有一条机耕路,无法通车,除了倒车,别无出口。我踩下油门时,忽觉胸中滞闷,立马熄火,下车,想出去透透气。我从未见过如此空旷的田野,从未领受过如此清爽的夜风。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汽车闯入这里简直就是一种冒犯。这块被工业文明远远抛在身后的田野,因为无所希求而获得了一种与天空相对应的静和空。静可以让人听到内心的声音,空可以容纳很多东西(这种的空的状态是城市广场所无法替代的)。我感到心神舒畅,索性就沿着机耕路向田野深处走去。站在那里,我能够完整地看到中高周垂呈拱状的星空,那么多星星不拘显隐地闪耀着,让我蓦然想起了小时候第一次走进大教堂的情景。是的,我所置身的田野,就像一个虔诚的信徒,正待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星空则以谦卑的弧状接纳了它,也接纳了渺小如一株野草的我。而我有必要对“无限空间的永久沉默”再度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