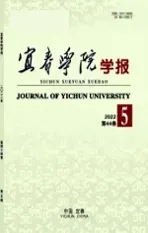先秦两汉诗赋列锦结构模式及其审美特点
2014-08-15吴礼权
吴礼权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
一
“列锦”(或称“名词铺排”[1]),是一种“有意摒弃动词与助词等,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叠加联合在一起,用以叙事、写景、抒情的修辞手法”。[2]作为一种特有的修辞方式,“列锦”植根于汉语之中,鲜明地体现了汉语语法“简易性”、“灵活性”、“复杂性”的特点。[3]“列锦”作为一个辞格被提出来并予以定名,前后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4]但作为一种修辞现象,“列锦”在汉语修辞史上则有悠久的历史。就现存的文学史料来看,列锦的原始用例见于《诗经·国风·草虫》。其开篇二句: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便是最早的列锦修辞文本。
虽然《诗经》所创造的列锦修辞文本并不多,但《诗经·国风·草虫》篇作者所创造的“NP,NP”列锦结构模式,则对两汉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我们对现存先秦两汉诗歌作品的调查分析,发现先秦两汉诗歌中的列锦修辞文本,主要有如下几种结构模式。
(一)以叠字领起的“NP,NP”式列锦
这种结构模式的列锦,由两个“偏正式名词短语”各自成句,形式上并列对峙,但各自意不相属,语法上没有隶属关系 (即彼此不互为语法结构成分)。一般情况下,都可以转换成两个并列的主谓结构的句子。另外,两个“NP”结构的名词短语句都以叠字领起。前文我们说过,就现存文学史料来看,这种结构模式是列锦的最原始的形态,首先出现于《诗经》之中。如:
(1)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诗经·国风·草虫》)
例 (1)“喓喓草虫,趯趯阜螽”,即是以叠字领起的“NP,NP”式列锦。因为这两句居全诗之首,前面没有其他句子,因此它们不可能充当其前面句子的谓语。而它们之后的句
子“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是两个并列的主谓谓语句,主语 (诗中所写的“女子”)都被省略。前句“未见君子”,有动词(“见”)、有宾语(“君子”);后句“忧心忡忡”,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谓语,“忧心”是主语,“忡忡”则是形容词当谓语。可见,“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是个独立的言语文本。而在这个文本内部, “喓喓草虫”与“趯趯阜螽”是一种并列对峙的关系,各自独立成句,在结构上互不充当彼此的语法成分。如果将其转换成一般的主谓句,则是“草虫喓喓,阜螽趯趯”,两个句子在结构与语义上的独立性更加明显。因此,这是一个典型的列锦,是《诗经》创造出的最原始形态的列锦文本。
《诗经》创造于前,汉代诗人踵武其后。在汉代诗歌中,诸如上述《诗经》所创造的以叠字领起的“NP,NP”式列锦,就不再是个别现象了。就现存数量不多的汉代诗歌来看,这种模式的列锦文本就有不少。如:
(2)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汉《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
(3)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汉《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
(4)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汉《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
(5)岧岧山上亭,皎皎云间星。远望使人思,游子恋所生。(汉乐府古辞《长歌行》)
例 (2)“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与《诗经》中“喓喓草虫,趯趯阜螽”一样,也是以叠字领起的“NP,NP”式列锦。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差异只在句式上,一是四言句式,一是五言句式,句法结构没有改变。因为“青青河畔草”与“郁郁园中柳”,都是以名词为中心的偏正词组。前句的中心语是“草”,有两个层次的修饰限定语。第一个层次的修饰限定语是“河畔”,第二个层次的修饰限定语是“青青” (修饰限定“河畔草”)。后句的中心语是“柳”,前面也有两个层次的修饰限定语。第一个层次的修饰限定语是“园中”,第二个层次的修饰限定语是“郁郁”。虽然这两句都是偏正结构的名词性短语形式,但却都是独立成句的。而且两句在语法结构与语意逻辑上是互不隶属的,是一种并列对峙的格局。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两句可以由偏正结构转换成主谓结构,但却基本语意保持不变,即“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可以转换成“河畔草青青,园中柳郁郁”。尽管句法结构有所改变,“青青”与“郁郁”由原来的修饰限定语升格为谓语,但两句所写的内容仍是“草”与“柳”及其生长的状态。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普通句法结构的“河畔草青青,园中柳郁郁”与名词铺排形式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在语义表达上几无差异,但从审美效果来看,则差异大矣。普通句只是告诉读者“草青柳郁、春天已经来到”的事实,而列锦句因为化句子为短语,两个短语句就成为一个构图的整体,画面感特别强。加上两个短语是并列铺排的,这就为易于形成电影“蒙太奇”式的画面组合,从而大大延伸了画面的广度,给人以更多遐想回味的空间,审美价值也就更高。例 (3)至例 (5),情况亦然。
(二)非叠字领起的“NP,NP”式列锦
这种结构模式的列锦,也是由两个“偏正式名词短语”各自成句,形式上并列对峙,但各自意不相属,语法上没有隶属关系 (即彼此不互为语法结构成分)。这种列锦模式,虽也是“NP,NP”结构形式,但不能像叠字领起的“NP,NP”式那样自由转换成两个并列的主谓结构的句子。另外,两个“NP”结构的名词短语句都不以叠字领起。就现存文学史料来看,这种结构模式在先秦时代的《诗经》中还未出现,而是到汉代才零星出现。如:
(6)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炉。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汉·辛延年《羽林郎诗》)
例 (6)“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即是一个以非叠字“NP,NP”式的列锦文本。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列锦文本,是因为这两个句子与它们前后的句子都没有语法结构上的关涉,是独立的。“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炉”居“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之前,但不以之为谓语;“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居“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之后,不以之为主语。而“长裾连理带”与“广袖合欢襦”两句之间,也是彼此无语法上的关涉,呈并列对峙的格局。从语义上说,“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意即“长裾的连理带,广袖的合欢襦”。它们分别是以“连理带”与“合欢襦”为中心语,以偏正结构的形式构句。这一列锦文本,由于是以名词铺排的形式出现,具有一种镜头特写的性质,因而画面感特别强 (后二句“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不是列锦,而是各省略了动词“戴”的普通句),在审美上就有一种特别令人回味的效果。
二
赋究竟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历来都存在争议。但是,主流倾向都认可南朝梁文论家刘勰的见解。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明确指出: “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即认为,赋的远源是《诗经》,近源是《楚辞》,但作为一种文体,则始于战国时代的荀子与宋玉之作。不仅如此,刘勰还在此基础上概括了赋的体裁特点:“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即赋在形式上都以主客对话起首开篇,以铺排声音形貌来夸示文采。现代学者的研究,认为赋除了上述特点外,还有“押韵和不押韵的结合,诗和散文的结合”,[5]指出“赋实是诗和文的结合,在描写上比诗有更多的方便”。[5]又指出:“汉赋有继承屈原抒写情志的,像贾谊赋;继承宋玉的描绘事物再加发展的,有司马相如、扬雄等赋,后者才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品。它也是主客问答,描写情貌,韵散结合,不过规模更大,并且有些赋还有个诗的结尾,象班固的《两都赋》。除了汉的大赋外,还有写物的小赋。到了汉末,又有抒情小赋,象王粲的《登楼赋》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骚体赋。”[5]
在赋的上述发展演变过程中,除了上述诸特点日益突出外,在修辞上还有一种辞格也应运而生,这便是列锦。就现存的汉赋来看,列锦的文本并不很多。概括起来,在结构形式上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NP,NP”式列锦
这种模式的列锦,由两个偏正式名词短语并列构成,每一个偏正式名词短语自成一句,互不充当彼此的语法结构成分。它们与其前后的句子也无语法结构上的关涉,即不充当它们前面句子的谓语或宾语,也不充当其后面句子的主语或定语等。如:
(7)忘忧之馆,垂条之木。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出入风云,去来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黄衣而绛足。蜩螗厉响,蜘蛛吐丝。阶草漠漠,白日迟迟。于嗟细柳,流乱轻丝。君王渊穆其度,御羣英而翫之。小臣瞽聩,与此陈词,于嗟乐兮。(枚乘《柳赋》)
(8)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飰大歠,如汤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尝之乎?(枚乘《七发》)
例 (7)“忘忧之馆,垂条之木”,是两个偏正式名词短语构成的并列句。它们的前面没有其他句子,而它们之后的句子“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则是两个在语法结构上封闭自足的主谓句。前句的主语是“枝”,谓语是“逶迟而含紫”,是描写性的并列短语,写柳树枝条弯曲的形态与枝条绿中透紫的颜色;后句的主语是“叶”,谓语是“萋萋而吐绿”,也是描写性的并列短语,写柳叶嫩绿的形态。可见,“忘忧之馆,垂条之木”在语法结构上是独立的单位,是我们所说的“NP,NP”式列锦。这一列锦文本,从结构形式上看,类似于《诗经》所创造的“NP,NP”模式,但又不以叠字领起。可见,它来源于《诗经》的结构模式,又有自己的创造。从审美效果来看,“忘忧之馆,垂条之木”这一列锦文本,居全赋之首,通过“馆”与“木”的并列铺排,既以特写镜头式的画面呈现出居室与柳树的紧密依存
关系,又突显出柳馆交相辉映的形象,读之给人以丰富的联想与想像,别具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例 (8)“山梁之餐,豢豹之胎”,也是“NP,NP”式名词句铺排,其意是在渲染菜肴的丰盛与珍贵,以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NP,NP,NP,……”式列锦
这种模式的列锦,由若干个偏正式名词短语并列铺排而成,每一个偏正式名词短语自成一句,互不充当彼此的语法结构成分。它们与其前后的句子也无语法结构上的关涉,即不充当它们前面句子的谓语或宾语,也不充当其后面句子的主语或定语等。如:
(9)太子曰:“仆病未能也。”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飰抟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臑,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鱠,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飰大歠,如汤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尝之乎?”(枚乘《七发》)
例 (9)“熊蹯之臑,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鱠,秋黄之苏,白露之茹”,是由六个偏正结构的名词短语并列铺排而成,每个名词短语在上下文语境中都是独立成句的,它们既不充当前句的谓语或宾语,也不充当后句的主语或定语,因此是典型的列锦文本。这一文本,以六个名词句的超常规并列铺排,既突显了表达者所要表达的主旨(强调菜肴的丰盛民珍贵),又别具一种渲染壮势的效果,读之让人有一种浩浩汤汤的痛快感。
(三)“N,N,N,……”式列锦
这种模式的列锦,由若干个表示某些特定事物的专有名词 (二音节)并列铺排而成,每一个专有名词都自成一句,互不充当彼此的语法结构成分。它们与其前后的句子也无语法结构上的关涉,即不充当它们前面句子的谓语或宾语,也不充当其后面句子的主语或定语等。如:
(10)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仍增崖而衡阈,临峻路而启扉。徇以离殿别寝,承以崇台闲馆,焕若列星,紫宫是环。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区宇若兹,不可殚论。增盘业峨,登降炤烂,殊形诡制,每各异观。乘茵步辇,惟所息宴。(班固《西都赋》)
例 (10)“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由八个表示宫殿名称的专有名词并列铺排,属于一个语言单位,与其前后的句子在语法结构上没有关涉。因为它之前的句子“焕若列星,紫宫是环”和它之后的句子“区宇若兹,不可殚论”,都是结构完整的句子。因此,这八个由专有名词并列铺排的名词句,属于典型的列锦。这一列锦文本,以超乎寻常的大量名词句铺排,突显出汉代西都长安宫殿之多的景象,别具一种浩浩汤汤的气势,读之不禁使人顿起一种崇高的美感。
(四)“NP+NP,NP+NP”式列锦
这种模式的列锦,由两个短句并列构成。每个短语内部,则各有两个偏正式名词短语叠加铺排(即“NP+NP”)。从语法结构上看,这两个“NP+NP”结构形式的短句都是各自独立成句的,不与它前后的句子发生语法结构上的关涉。也就是说,它们既不充当其前面句子的谓语或宾语,也不充当其后面句子的主语或定语等。如:
(11)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浮游览观,乃下置酒于虞怀之宫。连廊四注,台城层构,纷纭玄绿。辇道邪交,黄池纡曲。溷章、白鹭,孔鸟、鶤鵠,鵷雏、鵁鶄,翠鬣紫缨。螭龙、德牧,邕邕群鸣。阳鱼腾跃,奋翼振鳞。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叶紫茎。苗松、豫章,条上造天。梧桐、并闾,极望成林。众芳芬郁,乱于五风。(枚乘《七发》)
例 (11)“漃漻薵蓼,蔓草芳苓”,从上下文语境看,是一个独立的言语单位。因为它前面的句子“阳鱼腾跃,奋翼振鳞”是两个并列的结构封闭自足的主谓句,它后面的句子“女桑、河柳,素叶紫茎”则是一个描写性的主谓句, “女桑”、“河柳”是并列主语,“素叶紫茎”是写此两种植物的叶茎颜色。再看“漃漻薵蓼,蔓草芳苓”二句的内部结构形式,都是“NP+NP”,只是前句“漃漻薵蓼”结构稍有变异。“漃漻”,指水清澈的样子。“薵”和“蓼”是两种水生的植物。因此,“漃漻薵蓼”,意思就是“清澈水中的薵和蓼”,也算是“NP+NP”结构。如果作者写成“漃薵漻蓼”,那就完全是“NP+NP”结构式了。后句“蔓草芳苓”, “蔓草”、 “芳苓”都是一种植物,结构上都属于一个名词短语形式,即NP式。由此可见,“漃漻薵蓼,蔓草芳苓”是一个典型的列锦文本。它通过两个“NP+NP”结构的名词短句的并列铺排,将水中之草“薵”、“蓼”与陆上之草“蔓”、“苓”以特写镜头的方式予以呈现,画面感非常强,对比效果也比较明显,读之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另外,从句法结构来看,由于“漃漻薵蓼,蔓草芳苓”与其前后左右正常结构的语句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这就易于打破全赋同构句式铺排所造成的沉闷感,使行文整齐之中有变化,别具一种错综灵动之美。
(五)“NP+NP,NP+NP,NP,NP+NP,”式列锦
这种模式的列锦,结构比较复杂。它由四个短句并列构成。其中三个短语内部,各有两个偏正式名词短语叠加铺排 (即“NP+NP”),另一个短句则由一个偏正式名词短语单独构成。从语法结构上看,这三个“NP+NP”结构的短句和一个“NP”结构的短句都是各自独立成句的,不与它前后的句子发生语法结构上的关涉。也就是说,它们既不充当其前面句子的谓语或宾语,也不充当其后面句子的主语或定语等。如:
(12)于是量径轮,考广袤,经城洫,营郭郛,取殊裁于八都,岂启度于往旧。乃览秦制,跨周法,狭百堵之侧陋,增九筵之迫胁。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闻阖。疏龙首以抗殿,状巍峨以岌嶪。亘雄虹之长梁,结棼橑以相接。蔕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饰华榱与璧珰,流景曜之韡晔。雕楹玉磶,绣栭云楣。三阶重轩,镂槛文(媲换木旁)。右平左域,青琐丹墀。刊层平堂,设切厓隒。坻崿鳞眴,栈齴巉嶮。襄岸夷涂,修路陵险。重门袭固,奸宄是防。仰福帝居,阳曜阴藏。洪钟万钧,猛虡趪趪。负笋业而余怒,乃奋翅而腾骤。(张衡《西京赋》)
例 (12)“雕楹玉磶,绣栭云楣。三阶重轩,镂槛文 (媲换木旁)”,是四个描写汉代西京长安宫殿建筑的名词短句。除第三句是“NP”结构外,其他都是“NP+NP”结构形式,是典型的名词铺排的列锦文本。这一文本通过四组七个名词短语所代表的物象的铺排,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汉代长安宫殿非同寻常的气势,读之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崇高感。
(六)“N+N+N+N,N+N,N+N,N+N,”式列锦
这种模式的列锦,结构更为复杂。它由四个短句并列构成。其中三个短语内部,各有两个表示植物专名的名词叠加铺排 (即“N+N”),另一个短句则由四个单音节名词叠加铺排而成。从语法结构上看,这三个“N+N”结构的短句和一个“N+N+N+N”结构的短句都是各自独立成句的,不与它前后的句子发生语法结构上的关涉。也就是说,它们既不充当其前面句子的谓语或宾语,也不充当其后面句子的主语或定语等。如:
(13)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砆。其东则有蕙圃,蘅兰芷若,芎藭菖蒲,江蓠蘼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司马相如《子虚赋》)
例 (13)“蘅兰芷若,芎藭菖蒲,江蓠蘼芜,诸柘巴苴”,从上下文语境与语法结构分析,是一个独立的言语单位。因为它之前的句子“其东则有蕙圃”,是一个主语、谓语动词等结构成分俱全的封闭自足的主谓句;它之后的句子“其南则有平原广泽”,情况亦然。因此,“蘅兰芷若,芎藭菖蒲,江蓠蘼芜,诸柘巴苴”属于典型的列锦模式。其中,“蘅兰芷若”是“N+N+N+N”结构的名词性短句,因为“蘅 (杜衡)”、 “兰 (香草)”、“芷 (白芷)”、“若 (杜若)”各是一种植物,各以一个单音节名词呈现。“芎藭菖蒲,江蓠蘼芜,诸柘巴苴”三句,则是“N+N”结构的名词性短句,因为“芎藭 (蒿本)”、“菖蒲”、“江蓠 (香草)”、“蘼芜 (蕲芷)”、“诸柘 (甘柘)”、“巴苴 (草名,一名巴蕉)”各代表一种植物,各以两个音节呈现。这一列锦文本,通过四个名词句的并列铺排,将十种香草植物一一呈现,既突显了楚王蕙圃中香草植物之多,又具有一种铺排壮势的效果,读之让人油然而生一种艳羡神往之情。
三
先秦两汉时期,列锦辞格还处于萌芽与发展的初始状态,用例还不多。因此,辞格运用的审美意识还不是很强。就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其审美特点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妙趣天成的自然美
前文我们已经说过,就现存的文学史料来看,列锦的原始用例见于《诗经·国风·草虫》。其开篇二句:“喓喓草虫,趯趯阜螽”,便是最早的列锦修辞文本。这一文本的创造,采用定中结构的“NP”结构形式,先以“喓喓”之声领起,由声及物,引出发出“喓喓”之声的主体“草虫”(即蝗虫,即蝈蝈);再以“趯趯”(跳跃之状)之形象领起,由远及近,引出“阜螽” (蚱蜢)。创意造言没有刻意为之的痕迹,完全是诗人不经意间的妙语天成。因为按照人的思维习惯,总是先听到一种声音,然后再循声去寻找发出声音的物体;总是先远远看到某物活动的朦胧形象,再逼近细看活动的主体 (人或动物)。因此,我们说诗人以“喓喓”居前,“草虫”在后,“趯趯”领起,“阜螽”追补的语序所建构出来的修辞文本“喓喓草虫,趯趯阜螽”,虽然有一种类似现代电影“蒙太奇”手法的画面审美效果,但这种效果乃是妙趣天成,不是人工雕凿出来的美。
《诗经》所创造的列锦文本虽然是诗人不经意间的妙笔,不是刻意而为之,但其妙趣天成的审美效果却成了后代诗人们所热烈追求的境界。因此,在汉代诗歌中,这种以叠字领起、以偏正结构的名词短语形式成句的列锦,就逐渐多了起来。《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不少,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青青河畔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迢迢牵牛星》)、“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等等。汉乐府古辞中也有,如“岧岧山上亭,皎皎云间星。远望使人思,游子恋所生”(《长歌行》)。这些列锦,如果说它们是无意而为之,恐怕很难。相反,说它们是模仿《诗经》“喓喓草虫,趯趯阜螽”的列锦结构形式,则有相当充足的理由。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也可以变换成“河畔草青青,园中柳郁郁”,表意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在审美效果上则有相当大的差异。前者因为是列锦文本,接受上就有一种电影镜头式的特写画面感,给人以更多的联想想象空间,审美价值明显很高。后者则仅是一种简单的描写句,类似于陈述事实的性质,提供给读者的是“春天到了,草绿柳郁”这样一个信息,审美价值就打了折扣。虽然汉人诗歌列锦是有意为之,少点了妙趣天成的审美情趣,但有意以叠字领起的模式,事实上造就了一种听觉上的音乐美,这也是值得重视的。
(二)铺排壮势的崇高美
先秦两汉时期的诗赋中,特别是汉赋中,以大量名词或名词短语超常规集结的形式构成列锦,是一个突出的修辞现象。这种大规模名词句集结的列锦,在接受上有一种铺排壮势的效果,对接受者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视觉与听觉冲击,犹如滚滚江水,一泻千里,不仅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更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怦然心动的崇高感。如班固《西都赋》写汉代西都长安宫殿之多时有这样的笔触:“徇以离殿别寝,承以崇台闲馆,焕若列星,紫宫是环。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区宇若兹,不可殚论”。其中“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是八个宫殿专名的名词句铺排,自成一个言语单位,属于典型的列锦 (因为它之前的句子“焕若列星,紫宫是环”和之后的句子“区宇若兹,不可殚论”,都是语法结构封闭自足的主谓句,与这八个并列铺排的名词没有语法上的关涉)。这一列锦文本,通过八个名词的一气呵成地连续铺排,将大汉王朝的西都长安宫殿林立的景象呼之欲出地呈现于接受者眼前,不仅给人给强烈的视听觉冲击,让人对天朝盛世、大国威仪有一种强烈的印象,一种肃然起敬的崇高感油然产生。又如枚乘《七发》写楚王宫美味佳肴有这样一段文字:“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臑,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鱠,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飰大歠,如汤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尝之乎?”其中,“熊蹯之臑,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鱠,秋黄之苏,白露之茹”,是六个偏正式名词短语并列铺排,它们之前的句子“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和它们之后的句子“兰英之酒,酌以涤口”,都是结构上封闭自足的主谓句。可见,这六个名词句也是列锦文本,它通过大量名词句的集结铺排,强烈地渲染了楚王宫菜肴的丰富与珍稀,读之让人怦然心动,不禁为之神往不已。
(三)错综其文的灵动美
在先秦两汉的诗歌与赋中,都有这种一种现象:在全篇或全段落都以正常语法结构的句子进行铺叙的过程中,不时插入个别名词性短句。这些名词性短句,就是我们所说的列锦文本。由于这些名词性短句在语法结构上与其前后左右的句子都有所不同,这就打破了原来中规中矩的行文模式,使诗文的语言表达显得错综有变化,从而使作品增添了一种灵动之美。如汉·班固《西都赋》中有一段文字云:“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其阴则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灵宫起乎其中。”其中,“竹林果园,芳草甘木”二句在讲法结构上,就与其前后各句不同。它纯以“NP+NP”式的名词铺排而构句,夹在文中,就显得与众不同,别有一种“万绿丛中一点红”的韵味。从整个段落看,整体上的整齐划一与局部的特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遂使语言表达在接受上有了一种错综其文的灵动美。又如汉·辛延年《羽林郎诗》:“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炉。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第一二句和第五六句,从现代语法学来分析,都是主谓结构的正常句 (第二句省略了主语“胡姬”,第五六两句都省略了动词“戴”)。只有三四两句是由“NP”结构的偏正式名词短语单独构句,属于列锦。这一列锦文本,因为结构形式与其前后两句都有不同,遂使整体行文有了变化,从而具有一种错综灵动之美。
四
先秦两汉时期,虽是列锦辞格的萌芽与创始阶段,但其创意造言对后代诗、词、曲、文、小说等各种文体的影响作用则不可小觑。
(一)先秦两汉诗歌列锦的模式虽少,但对后代各种文体中的列锦文本创造却产生了最大最为深远的影响
上文我们说过,先秦两汉时期诗歌中的列锦模式只有两种,一是由《诗经》所创造的“以叠字领起的‘NP,NP’式”,二是是由汉代诗人所创造的“非叠字领起的‘NP,NP’式”。前者虽出于先古诗人的妙笔偶成,是无意识的修辞创造,但却因为其妙趣天成的表达效果,遂成千古以降诗人们一直追求的审美境界。无论是汉代的《古诗十九首》和乐府古辞,还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韵文作品,抑或是唐传奇开始的小说作品,都一直沿用这一最原始的列锦结构模式,至今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后者则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诗歌创作中最主流的列锦模式,初唐诗歌中所创造出来的许多新的列锦结构模式,也是由此而衍变出来的。这与它结构上不再追求以叠字领起而更易于建构有关。正因为如此,它的生命力更加顽强,应用面更广,即使是在现代诗歌、小说、散文中,也仍能时常见到其矫健的身影。
(二)汉赋中列锦辞例虽不多,但结构类型却丰富多彩,对唐传奇开始的小说列锦文本的创造影响深远
从前文所列举的汉赋列锦模式,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汉赋中的列锦并非触目皆是,但却有六种结构类型。就类型的丰富性来说,远远超过比赋更源远流长的诗歌。除了“NP,NP”式与汉代诗歌中“非叠字领起的‘NP,NP’式”相同外,其他五种类型: “NP,NP,NP,……”式、 “N,N,N,……”式、 “NP+NP,NP+NP”式、 “NP+NP,NP+NP,NP,NP+NP”式、“N+N+N+N,N+N,N+N,N+N”式,都是汉赋的创造,在《诗经》与汉代诗歌中都是找不到先例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诗赋两种文体的不同有关。诗有字句结构上的内在规范,不可能像赋那样充分铺排,将大量的名词性短语句超常规地予以集结。从内容上看,汉赋特别是西汉时代的汉大赋,本来就是以“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为旨趣,因而作为“铺采”、“体物”手段之一的列锦手法就有用武之地,结构形式上趋向复杂化也就势所必然。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随着汉大赋的衰落和东汉抒情小赋的兴起,赋中列锦结构的复杂性也随之减弱。这既与赋体形式的变化有关,也与时代风尚有关。
从前面我们所举汉赋列锦的例子来看,汉赋列锦所涉及的内容多是建筑、园林和饮食。以列锦写建筑,意在通过建筑物及其形态特点的铺排,突显大汉王朝的威仪气度;以列锦写园林,多是以铺排的形式展示皇家园林的气派;以列锦写饮食,意在通过丰盛、珍稀的食物罗列,在铺排中呈现出钟鸣鼎食的上层社会生活的奢华程度。汉赋列锦的这一内容特点,在唐传奇中得到了继承。后文我们要讲到的唐传奇喜欢用列锦写建筑物与人物服饰,就是继承汉赋列锦的表现。至于张鷟《游仙窟》中的列锦喜欢铺排宴席食物与闺阁陈设,则更可见出其“铺采摛文”的汉赋列锦烙印。
[1]吴礼权.名词铺排与唐诗创作[C]∥蜕变与开新——古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东吴大学出版,2011.
[2]吴礼权.从〈全唐诗〉所录唐及五代词的考察看“列锦”辞格的发展演变状况[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月刊),2010,(1).
[3]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谭永祥.修辞新格(增订本)[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
[5]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