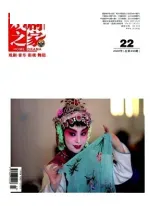坏孩子的天空——美国“X代”导演研究
2014-08-15叶艳琳
叶艳琳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广播电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一、“X代”导演创作历程概述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大批活跃在好莱坞之外的年轻导演,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是1961年出生的斯蒂文· 索德伯格,最年轻的是1971年出生的索菲亚·科波拉。在这二十多年间,他们的作品对美国乃至世界影坛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并且横扫了奥斯卡、戛纳等各大权威电影节,震惊四座,也让不少电影大师瞠目结舌。
1989年的戛纳电影节原本是一届向电影巨匠致敬的盛会,既大张旗鼓地纪念卓别林诞辰一百周年,又以大卫·里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作为开幕影片进行隆重放映。但电影节开幕不久,人们很快就把目光对准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索德伯格带来的影片,他的这部仅花费了120万美元的独立制作影片《性、谎言和录像带》令观众和评委耳目一新,让人们在纪念大师的同时感到了一阵清风。这部探索社会性心理的影片最终打动了评委们,他们把金棕榈大奖戴在了这位年仅26岁的年轻人头上,使他成为电影节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金棕榈获奖者。当年的评委会主席、德国著名导演维姆·文德斯认为这是一部个性鲜明、令人兴奋的影片,它包含着未来电影的冲动与信心。《性、谎言和录像带》为索德伯格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声誉。紧接着,该片在美国获得独立精神奖最佳导演和奥斯卡最佳剧本提名,并且该片在商业上更是获得巨大成功,票房收入高达2500万美元。一时间,《性、谎言和录像带》成了独立制片的典范,再次掀起了人们对独立制片的热潮,而索德伯格也就当然地成了这个群体的旗手。
1992年昆汀·塔伦蒂诺的处女座《落水狗》在圣丹斯电影节上首映,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影片一直彰显的暴力美学也逐渐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紧接着1994年,他的《低俗小说》摘得了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并在奥斯卡、金球和各个世界性电影节上频频获奖,接连击败了《红色》(基耶斯洛夫斯基)、《毒太阳》(米哈尔科夫)、《活着》(张艺谋)等影片。之前,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蓝》捧走了威尼斯的金狮,《白》摘下了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导演银熊奖,这位电影大师原本信心满满地准备实现三连冠,没曾想到却败给了一位31岁的年轻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很是失落,他说:“电影的重要性已经丧失,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电影引领着观众的价值,但现在的观众不知道自己该看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该拍什么了。” 所以有人评价“痞子战胜了大师”,也有人认为“保守的老知识分子电影败给了全新的电影理念”。北京大学的陆绍阳教授认为“评委们确实是有长远的眼光的”。 由此可见,以索德伯格和塔伦蒂诺为首的美国X代导演在世界影坛的闪亮登场也让世界电影人开始对大师的态度从顶礼膜拜转变为冷静审视。
1999年是非凡的一年,有一批游走在好莱坞之外的电影导演集体亮相,这标志着“X世代”电影人的成熟。首当其冲的是这两位刚刚从美国佛罗里达中央大学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丹尼尔·米瑞克和艾德亚多·桑奇兹。他们凭借着一台16mm的DV摄影机和区区3.5万元拍摄的《女巫布莱尔》在1999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放映结束后,艺人娱乐公司立刻宣布将以大约11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女巫布莱尔》的发行权。在《女巫布莱尔》真的走入院线上映时,它之前通过互联网进行的病毒营销产生了巨大效应,而电影开创式的纪录片拍摄手法和代入感极强的情节,让艺人娱乐公司用110万美元换来了亿元回报。;同时,拍摄了引人注目的《异形3》、《七宗罪》、《心理游戏》之后,大卫·芬奇推出了他极具震撼性的影片《搏击俱乐部》。与此同时,山姆·门德斯推出了反映中年危机的《美国美人》,引起社会轰动和好评,拿下5项奥斯卡大奖。
2000年之后,他们的战绩更加显赫。2000年,肯尼斯·龙纳根的社会家庭问题片《你可以依靠我》先是在圣丹斯电影节上一举拿下“大法官奖”和“剧本奖”,继而荣获两项奥斯卡提名。2003年,著名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之女索菲亚·科波拉在《处女之死》之后,又推出了一部风靡海内外的力作《迷失东京》。这部只花了27天拍摄、耗资仅400万美元的小成本影片一经推出即获得包括奥斯卡、金球奖在内的全球多项影评人奖和提名,被誉为“有诗意而具深度的独立电影”。2004年,亚历山大·佩恩在他的《选举》、《公民鲁斯》连连得到好评后,推出影片《杯酒人生》。而拿下奥斯卡最佳剧本改编奖.并获得最佳奥斯卡影片提名。
二、“X代”的命名和由来
“代”概念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电影理论界最伟大的发明。它既不像西方的“流派”,有着共同的美学主张,它比之要粗;也不是简单的编年体,他比之为细。X代是美国人第一次用“代”概念来给一批导演命名,而这个名称原本来源于电影界之外。90年代初美国出版界发现了一个庞大的潜在的读者群,这些读者都是出生在60-70年代,年龄在18-30岁的年青人,总人数约有100万。这些年青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一定的高科技知识。他们的生活深受当代电视文化和其它大众媒介的影响,但也被美国当前日益姜缩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发展的黯淡前景所困扰。这个代表着美国新一代的读者群被商界和广告界称作“X代”。 1991年,加拿大道格拉斯·卡普兰的畅销小说——《X代》,发行35万册,在X代读者群众掀起了一阵狂潮。在上文中提到的这一批从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轰动美国乃至世界影坛的年轻导演恰好和X代读者年纪相仿,并且都成长于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最动荡的80-90年代,同时深受电视、MTV等大众文化的影响,虽然电影风格比较多元化,但都有着同样的精神特质,所以美国学者把这一批导演也命名为“X代”。
三、“X代”电影共同的话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里?
“X代”导演的成长期正好处于美国社会文化生活极具多元化的年代,这样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他们极具个人化的表达。所以“X代”导演没有统一的美学主张,他们的电影风格迥异。或者,换句话说差异化、个人化本身就是“X代”电影最大的特征。在《爱在黎明佛晓时》中,理查德·林克莱特用自然随意的长镜头记录着男女主人公一天之内的漫步闲聊将一个温情、浪漫又略带忧伤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整部影片没有设置任何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完全依靠人物的漫步和语言,从而表现人物情感的微妙变化。在《七宗罪》和《搏击会》中,大卫·芬奇用类似MTV的快速的切换镜头、讽刺辛辣的语言甚至是粗口,直截了当地揭示欲望都市里人们贪婪、虚无的内心。斯蒂文·索德伯格曾经说过“与其它艺术比起来,电影最容易做的事就是打碎时间。”,索德伯格的这句话也代表了很多 “X代”导演的心声。除他之外,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昆汀·塔伦蒂诺。他们的电影《性、谎言、录像带》《水库狗》和《低俗小说》都打破了传统的单线索叙事结构,其中包含的几个小故事被导演打碎并自由拼接。这跟他们深受MTV和广告的影响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山姆·门德斯的《美国美人》却严格地遵循着传统三幕剧的结构,即第一幕抛开引子:男主人公莱斯特偶遇女儿的同学安吉拉,她的美艳让他重新燃起了生命的激情;第二幕发展:莱斯特千方百计靠近安吉拉,终于如愿以偿;第三幕高潮:莱斯特被杀。可以说,“X代”导演把拍电影当成是个人化的行为,因此他们的电影中镌刻着极为强烈的个人风格,但是在多样化和差异化的叙事和视听风格下面涌动着着他们相同的对于电影的精神诉求,他们在电影中集体探讨着一个共同的话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里?,所以他们也被称为“迷失的一代”。
通过电影作品表达对于存在意义和自我价值的困惑,绝不是“X代”导演的专利,但是在美国电影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群导演用极具个性化和情绪化的方式直截了当、毫无保留地去表达这种困惑。这与“X代”导演的出生和成长的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出生于60-70年代,而从60年代末到七、八年代,美国社会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骚乱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十多年的越战让美国耗费了至少二千五百亿美元。尽管军事上美国并未失败,但它表明美国冷战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越战极大地改变了冷战的态势,美国由冷战中的强势一方变为弱势。同时,越战也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和民权问题,使国家处于极度的分裂状态,给美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越南战争也没有得到美国民众的支持,国内的反战运动持续了整整十年。参加战争的年轻人更加认为自己参加了一场无意义的战争,并为此做出了无谓的牺牲,也没有人把他们当做英雄。这期间发生的第二件大事是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被弹劾,国家的威信再次被动摇。伴随着这些的是性解放、民权运动、离婚率的急剧上升、妇女解放运动。前辈们坚守的道德体系到这个时期被彻底颠覆,同时在60年代建立起来的理想主义思潮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到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早期,美国社会以及全世界都变得更加动荡与黑暗,充斥了暴力和死亡,比如盖亚纳狂热教徒集体自杀; 那一时期的精神领袖列农被谋杀;里根总统和意大利教皇被暗杀; 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发动的惨不忍睹的暴力行径。这些事件都在X代导演的心灵深处已经形成了难以愈合的伤疤。进入80年代,大量的新的社会问题出现,旧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比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艾滋病的出现,传统家庭观的崩溃。据统计,从1965到1985年,离婚家庭数从30万增长到120万。于是,“X代”导演集体困惑和迷茫了,他们反反复复地在影片中拷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里?因此他们不会像他们的前辈们一样在电影中探求未来,更不会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因为他们认定自己没有未来。因此,在中国“X代”也被翻译成“未命名的一代”。
据统计“X代”电影人有40%来自于单亲家庭,其中包括昆汀·塔伦蒂诺、山姆·门德斯。这一代的年轻人跟以往几代相比,受到父母及主流教育的影响要少的多。因此,前辈们曾经坚守的家庭观念在这一代人心中崩塌,同时他们也质疑传统的伦理道德。另外,家庭以及国家的动荡、分离导致了他们极缺乏安全感,自我价值极低,所以他们也被称作“被抛弃的一代”。《搏击会》中贯穿始终的男主人公泰勒的旁白句句都道出了“X代”导演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里?”的困惑,比如泰勒曾说到“你的职业不代表你是什么人,你的银行里有多少钱也不能代表你是谁,你驾驶什么车也证明不了什么,不在乎你的钱包有多少钱,不在乎你穿卡其布的衣服,你是这世上无用的东西。”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好莱坞拍摄了《星球大战》等一系列风靡全球的科幻片,“X代”也是这些影片的观众,但是他们的影片却很少去涉及这一题材。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没有未来,他们时常在想“我们该去向哪里?”因此他们在电影中大量触及到死亡和分离。《美国美人》最后莱斯特被杀,《搏击会》最后泰勒先向自己开枪,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挽着他爱的女人玛拉看着夜色里的大楼一座座被炸毁。《低俗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活在危机当中,在一个故事中文森特是杀死别人的凶手,在另一个故事中他却死在别人的枪口下。《爱在黎明拂晓时》中尽管Jesse 和Celine的相识相恋被导演表现地无比浪漫,可是最终还是被迫分离。
“X代”的成长期恰逢80年代美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十年,这一时期被称为“Roaring 80’S”,即“狂热喧闹的八十年代”。因此,在 “X代”电影中,人面临的困境绝非贫穷。主人公大多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富足,他们垂死挣扎的困境是人际关系的疏离和精神世界的贫乏。比如《迷失东京》中的男主人公哈里斯,他是一位明星,住着高级宾馆,有着一个在别人看来非常光鲜的职业。而不为人知的是,在他拍摄威士忌广告时,他像一个木偶一样被摆布。他跟妻子的交流只能通过电话、传真机等生硬的现代通讯方式,客套的几句寒暄也毫无温情可言。女主人公夏洛特的丈夫也事业有成,所以他们过着富足的生活,但是因为丈夫忙于工作,夏洛特感到很孤独。光鲜亮丽富足的生活里边潜藏着的是人际关系的冷漠以及内心的孤独和迷茫。所以男女主人公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东京街头,不知道去向哪里。再比如《美国美人》《性、谎言、录像带》中的两个家庭可以称得上是富足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住着别墅,开着豪华轿车。可是这两个家庭都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精神危机,夫妻之间缺乏交流,家长与孩子之间缺乏交流,各个家庭成员都只是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过客,每个人都渴望交流,可也都没有将家人视作自己的倾诉对象。
自我价值的匮乏以及精神的空虚与迷茫遭遇物质生活的富足之后,人便很容易通过对物欲的无限度膨胀来满足内心的空虚,这便形成了消费时代的群体症候。《搏击会》中,购买曾经是主人公泰勒填补内心空洞的方式,电影中有一场戏是当泰勒走过他的公寓时房间里每件物品的价格依次打在画面上。但是后来,泰勒觉醒了。他高喊“我反对物质主义”,他劝告杰克“别让物质支配你”,他做出了一番惊世骇俗的宣言“广告每天诱惑我们买衣服,于是拼命工作买不需要的东西。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带,没有目的。没有地位,没有大战争,没有经济大恐慌。我们的大战只是心灵之战,我们的恐慌只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从小看电视,相信某天会成为富翁,明星或摇滚明星,但是……我们不会。我们渐渐面对现实,于是非常愤怒。”而《耍酷一族》中的年轻人可以在超级商场里消耗时光。
“X代”感受到的冷漠、孤独、无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排解,于是便在他们的片子中宣泄甚至是爆发。宣泄和爆发的途径不仅仅是无穷无尽的消费,还有充斥着长篇大论以及被渲染到极致的暴力。比如《搏击会》中全片从头到尾都伴随着泰勒的旁白,《爱在黎明佛晓时》男女主人公自始至终都在聊天。再比如《搏击会》中人们在夜晚通过肉搏来获得快感,《低俗小说》中人总是生活在循环往复的暴力中。
人们给昆汀·塔伦蒂诺起了一个绰号叫“好莱坞的坏孩子”,可以说 “X代”是一群坏孩子。因为他们的电影拒绝好莱坞电影的宏大叙事,也颠覆了好莱坞一直坚守的主流价值观。同时,在MTV、广告等流行文化盛行的年代,他们的叛逆又催生出一套和好莱坞电影,专属于“X代”的语言体系。
[1]甄晓菲.大师十年,影迷十年[M].南方周末,2006.
[2]皇甫一川.我需要重新开始——斯蒂文·索德伯格访谈汇编[M].当代电影,2003.
[3]皇甫一川.影坛独行客:斯蒂文·索德伯格[M].当代电影,2003.
[4]周新.Generation X究竟怎么译为好[M].中国翻译,2001.
[5]王立平.美国新一代读者群[M].编辑之友,1995.
[6]Peter Hanson,The Cinema of Generationx: Aritical Study of Films and Directors, McFarland&Company,New York,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