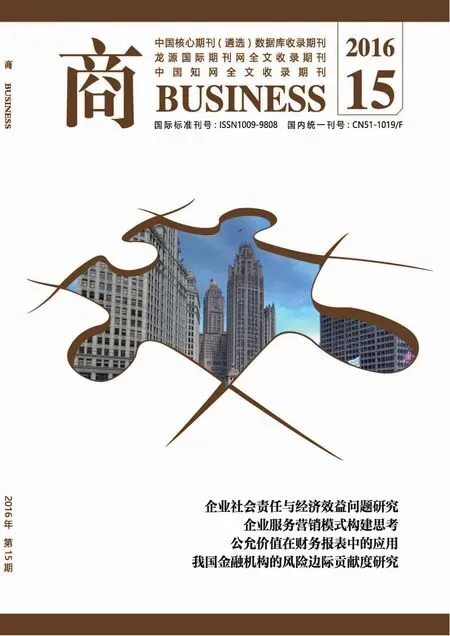苍天水井间的火焰
2014-08-07曾园英初晓慧
曾园英 初晓慧
作者简介:曾园英(1990-),女,湖南邵阳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编辑出版方向,导师张利洁。
初晓慧(1989-),女,山东烟台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广播电视新闻学方向,导师韩亮。
摘要:不同的生存样式造就了不同的文化样式,影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反映了人类不同的生存样式,其中不乏多彩的文化样式呈现。本文通过对余男主演的两部女性电影《惊蛰》《图雅的婚事》进行文本分析,试图解读影视视角下的西北文化传播。两部电影聚焦于西北农村的一片苍茫大地,再现了艰难的生存环境和在此传承千年的厚重文化,人们在这块后象征文化的土壤成长,显现出原始淳朴的生命力。就在这苍天水井之间,电影生动刻画了坚忍勤劳的两位女子,她们不抱怨生活,不放弃生命,成为黄色土地上跳跃的红色火焰。
关键词:影视作品;西部文化;后象征文化;坚忍影视,这个被马歇尔•麦克卢汉称为“拷贝盘上的世界”的电子媒介,将一个世界的图景呈现在另一世界的目光之下。拷贝并非机械串联,而是一个艺术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一个有意义和价值充实的符号体系。“符号既是现实的表征,又为现实提供表征”[1],影视生成于现实之上,升华于意义之中,本身就是精神文化的一种形式,同时又因镜头下的现实景象而表现出文化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族群性。
我国的西北地区不乏镜头的注视,其文化的纷繁性、醇厚性和鲜明性让西部受到不少影视导演的青睐,铸就不少经典之作。画面言语间,将西北各区域极具张力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喷洒出来,催化了维尔托夫口中的“有意义的震撼”。笔者以余男主演的两部女性电影《惊蛰》和《图雅的婚事》为例,进行文本分析,试图解读影视中所呈现的当代西北文化之一角。
电影《惊蛰》和《图雅的婚事》均由王全安执导、余男主演,分别于2004年、2006年上映,在国际国内载誉丰盛。《图雅的婚事》荣获第57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第43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突尼斯迦太基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最佳奖。余男本人凭借《惊蛰》被评为第2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第19届巴黎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凭借《图雅的婚事》被评为第43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第8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女主角、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第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如此重量级的奖项成为两部作品当属“有意义的震撼”之“铁证”,也肯定了唯一的主角余男的“真实”演绎,还反映了作品本身的世界影响力,国际观众更多地会选择通过此类作品了解我国文化,特别是西北文化。因此,研究这两部作品所呈现的西部文化具有代表性意义。
一、叙事线条——一个女人的故事
两部作品关照的对象均是女性,一个是陕北农村里的二妹,一个是内蒙荒漠上的图雅。她们生活在被祖祖辈辈深深打上传统烙印的黄土地上,那个是个后象征文化占主流的局域里,长辈的权威诠释着信仰所在,这本应是寂静得如一潭死水的地方,可是,故事却在某颗小石子不经意地投入中涟漪泛来。
(一)一口棺材引发的故事
《惊蛰》的故事得从关二妹的爷爷说起,爷爷快去世了,为其备置了十年的棺木已陈旧腐朽,家人决定重新做一口棺材,结果因为偷砍树被抓罚款。二妹不愿嫁给能施以援手的章锁,开始了县城打工生活。在历经工作的压抑和男友的背叛后,二妹选择回到家和章锁结婚生子,忍受繁重的农活和酗酒的丈夫。
二妹的故事缘起于一口棺材,为爷爷安身的棺材,即使贫困仍不惜代价办个体面的丧事,就算是搭上二妹的婚事也不足为惜。中国人自古讲究厚葬,入土为安,含笑九泉,这是以孝为先的儒家理念,古有丁忧,甚至卖身葬父,二妹的婚姻也就可以理解了。一口棺材,除暗含孝意,还代表着一种深远的期冀,但愿死者能走得安心,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安好。因此,棺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分量举足轻重,在《惊蛰》中彰显得淋漓尽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二妹作为一名女性在西北农村的地位,由此引发了二妹的离家。
(二)一口水井引发的故事
《图雅的婚事》讲的是巴特尔因日渐干旱的草原而打井,不慎双腿残疾,妻子图雅一人支撑起四口之家。长期的劳碌让图雅腰椎严重错位,并有下肢瘫痪的危险。为不耽误图雅,巴特尔与之离婚,但图雅执意要照顾巴特尔,于是图雅开始艰难地寻找一个能一起照顾前夫的丈夫……
图雅的丈夫因为打一口井而残废,成为图雅的负担,电影伊始就交待了取景点阿拉善这个西北干旱半干旱的地理环境,井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有多么重要,而最后求婚的邻居森格也对图雅说了,“死不了,井就得打”,“我打井是為了留住你”。井,俨然成为生命的曦光所在,人们为寻求一口有水的井付出的代价是重大的。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嫁夫养夫”的故事,导演王全安说,蒙古族可以让他借胆奔放一下。是的,蒙古草原,成为这个故事发生的特定背景,草原儿女的奔放让故事发生得自然,毫不生涩突兀,反倒觉得这就是西北女子的风骨。
两部电影的逻辑生长点——棺材和水井,在影视里是罕见特殊的,但一个关系着死,一个关系着生,这里系着两个西北农村女孩的命运,从此开始对其生存境遇展开叙述。她们同样淳朴不乏倔强,但都为生活所迫,面对自己的婚姻,有过挣扎,触碰家长的逆鳞,但都归于一声叹息,从中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卑微,如同黄沙于无边大地上,随风浮沉,相较于棺材和水井,或许无足轻重,但确实存在着生命的不能承受之轻。
二、物质存在——一幅苍茫的景象
《惊蛰》取景于陕北西北角的定边县,水井、窑洞、炕床、麦秆、白面、白饼子、压面机、拖拉机、大白菜、扑飞的鸡、木电线杆,大红的围巾和上衣、挡风沙的头巾、遮刺眼阳光的墨镜,绣着牡丹花和龙戏珠图纹的衾枕……构成了陕北农村生活的背景。一辆颠簸在黄尘荒野上的白色中巴连接着农村和县城。鱼、电视、巧克力、音乐卡、卫星锅、明星海报、大棚集市、要收费的公共厕所,让这个小县城染有丝缕的现代气息,能与二妹的农村老家形成对比,但并不能抹灭二妹生活之处的偏远落后、苍茫寂寥,反而加深了这种印象。
水井、水罐、奶茶、炕床、灶台、白酒、烤全羊、青花瓷杯、银镯银耳环、厚实的毡靴、宽大的蒙古袍、五颜六色的头巾、挂有成吉思汗画像的蒙古包,草原上的交通工具骆驼和马、摩托车、三轮车、大卡车还有小轿车……这些隶属于生活起居的物质文化,无不影射出阿拉善恶劣的生态环境,一簇簇的骆驼草、成群的绵羊、时有的暴风雪、叶子发黄的沙枣树,无不渗透着蒙古族渊源的历史。文化物质的塑造离不开历史-地理因素的作用力。
两部电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开阔的视野摒去了晦涩压抑,强劲的风沙更添豪放率真,散发出一种粗砺的美感。这里,绿色并不受待见,反而土黄色成为生命的底色,或许鲜有勃勃生机,却仍生生不息,延续着千百年来生产生活的成果,而女主人公常着的红色,如同在这片无言土地上顽强跳动的火焰,执意将生命点亮。
三、精神所依——一座风蚀的雕像
相较而言,精神文化的呈现就有些复杂了,有些是浓墨重彩的特写、长镜头,有些是含沙射影的说唱论及,但有意无意中却能让观众感受到这种精神文化力量的强大和威慑力。
(一)风俗
风俗,正是这种文化迫力的一种演绎,“一种依靠传统力量而是社区分子遵守的标准化的行为方式,是能作用或发生功能的”[2]。风俗在影片中作用力和发生功能大都通过主角经历特殊时刻的一些片段体现出来。
换丧嫁娶是风俗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两部电影中皆是浓重一笔。《惊蛰》中爷爷的葬礼、二妹的婚礼都少不了乡里乡亲的参与,在小小的农村可谓热闹非凡。葬礼上,人们送礼金花圈、敲锣打鼓吹唢呐、参加宴席;送葬时撒冥纸放鞭炮礼花,亲人着孝服戴白布孝帽;葬礼后全家进行扫尘。婚礼上,二妹着红嫁衣,章锁穿黑西装,两位新人走过孩子们欢呼撒彩带的院落,直达端坐在案前的双亲跟前,听人宣布两人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结婚法被授予结婚证书;背景乐是欢快的锣声鼓声唢呐声,一旁还有学生敲打架子鼓,大红灯笼高挂在屋檐下。传统和现代营造起喜庆氛围,却与二妹冰冷的表情格格不入。《图雅的婚事》更是将婚礼推置为影片的高潮。提亲也是婚俗的前奏,电影里,男方家派选几个代表,带着聘礼体面地来到女方家,然后商讨婚事。几经波折,最终才有了一个极富浓郁蒙古风情的婚礼。蒙古族婚礼歌曲由一位老者传唱开来,此起彼伏,从未间断。人们都盛装出席在蒙古帐篷里,图雅和森格身着婚礼袍一杯杯向长辈、主婚人敬酒,正中的火炉生得正旺,只是这样的婚礼没有一丝笑意,唯有泪盈眶。
无论二妹,还是图雅,她们的婚事都是身不由己的,只是长久存活下去的前提,爱情似乎是一个奢望,又怎能企及,甚至都没有了心思去遐想,只求活着,不放弃不抱怨。
(二)声音
声音,这一影视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成为电影中传达西部文化的重要元素。不消说对白内容,语言就带有地方特色,影片让我们耳闻了发音略微低沉,口齿有些含混的西北方言。影片中的歌谣西北味甚浓,韩红深情悠远的《天路》《青藏高原》从播放机里飘荡出来,回响在摩托车扬起的风尘里,飘向远方。悠扬的马头琴和蒙古长调时不时在电影中回旋萦绕,让人仿若置身于苍天般的阿拉善。《惊蛰》里对秦腔有两段单独呈现,一场在室内,一场在露天,沙哑而浑厚的嗓音,带着一股浩然正气,台下一片白帽。
(三)酒
电影中酒多次出现,穿插在故事情节中成为人物形象的补充和某种文化的投射,它既是物质文化的成果,又有精神文化的内涵。人类的行为活动凝结着本身的意向、情绪、价值观,喝酒亦然。西北男子好喝酒这一行为习惯在电影中得到了印证。男人们聚在一起喝酒划拳,二妹的丈夫更是经常酗酒,酒成为枯燥生活的点缀,男人娱乐的必备。在内蒙古草原,酒有了更深层的意义,敬酒成为待客之仪、婚礼之仪,还有白酒刮痧的实用,男人们不仅能喝,女人们也不差,酒,无形中煅造了她们的刚烈性情。
酒,像是人们修行苦难哲学的发明,或麻痹精神,或聊以慰藉,或宣泄情绪,用图雅的话来说是能让人生,也能让人死,用巴尔特的姐姐来说,不喝点酒,不知道日子怎么过的。酒,在电影里超越了本身的含义,成了苦难生活的象征。
电影中所呈现的林林总总的精神文化耐人寻味,因为它从历史的长河流淌而来,在阳光下泛起粼粼波光,仿若一座屹立在那片苍茫大地上的风蚀雕像,有历史沧桑的痕迹,时光雕刻的印记,高大得只能让人敬畏仰望。他靠活的教科书——长者积攒启蒙的力量,在仪式中不断强化,衍化成无形的迫力。在这种精神文化中,有人得到满足,有人得到心安,有人得到快感,也有人感到压抑,感到空虚,感到麻木。
四、井天之间——一个坚忍的女子
所有的文化,最终融汇于人这一生物,人让所有的文化显现生命力。人既是文化产生的主体,又是文化作用的客体。“文化根本是一种‘手段性的现实,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其所采取的方式却远胜于一切对于环境的直接适应。”[3]文明之花也能生长于漫天黄沙的荒芜之地。
在影片描绘的这片苍茫大地上,二妹、图雅生于斯,长于斯,潜移默化地习得文化,她们浸在这条历史的长河之中,除了县城再没去过更远的地方了,生存环境、传统文化作用在她们身上的烙印十足深刻,她们是典型的后象征文化里的人,“未来重复着过去,接受过去的权威”[4]。
她们有着既定的轨道,那是所有生活在那的女子都遵循的路,无数祖辈走出来的毋庸置疑的路,在家干活,接受低水平的文化教育,到一定年龄,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嫁人,在夫家生几个娃娃,养孩子,在农村干农民该干的活儿,在牧区干牧民该干的活儿,就这样一辈子了。
只是,在某个拐角发生了某些意外,然后饶了弯路,实在艰辛得有些不寻常,于是我们见到了影片里的女主人公,唯一的主角。
巧克力、音乐卡,还有毛女口中的“梦巴黎”让二妹萌生了“远方”的念想,她也曾有过想起远方就乌黑发亮的眼眸和天真烂漫的笑容,那一年少时能发出乐曲的心弦。在这个外界看来遥远的小山庄,花样年华的二妹也有自己的远方。关于“远方”的场景电影出现了好几处:她只身一人来到县城打工,开始了远方的第一步;站在高墩上望着远方,男友说,“我们去远方,火车有卧铺”;听说毛女坐火车去了南方,她一脸落寞,却打趣地对儿子说,去英国、去德国,给咱家娶个洋妞;最后在游乐场的电动火车上开始一趟梦幻的旅程,感受奔向远方的悸动……远方,成为二妹永远也到不了的地方,可她把希望放到了下一代,继续这样活下去。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影片标题“惊蛰”这一节气的隐喻意味了。“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这时天气转暖,渐有春雷,是惊醒蛰居动物的日子。此标题隐射了二妹在现代文化触动后的觉醒,但最终现实让她失望了,落寞地回到家接受命运的安排,重复着祖辈的路。
图雅,这个蒙古女汉子要再婚了,可她要找一个愿意跟她一块养前夫的男人,这是唯一的条件。成婚,在这里看上去太沉重了,甚至有些悲壮。一拨又一拨人前来提亲,一次又一次失望而归,直到来了个钻油老板,前夫被送到县城养老院。而当图雅赶到医院看到抢救过来的自杀的前夫,她苦苦压抑的情感得到宣泄,也明言出她的生存之道,“活着不容易,要死早就死了”,死不是本事,活才是。在这里,死有多容易,活就有多艰难,可是图雅却要嫁夫养夫,只为活下来。
电影传播了边远地区女性的生存状态,同时生动刻画了艰难求生的女子,天真烂漫的喂猪姑娘,任劳任怨的能干村妇,策马狂奔的粗壮妇女,皮肤粗糙黝黑的彪悍女子。她们活着从来都不是为自己,也无法单为自己而活,在西北这块安土重迁的土地上,家族是你绕不过去的命运之绳。可是,她们仍活出了样儿来,活在苍天之下,活在水井之上,活得坚忍。“坚忍”这两字有她们对生命的态度,还折射有生存的境地。
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样式之一,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观念体系支配的行为系统。不同的生存样式,如地域、民族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文化样式。影片让我们见识到了西北文化的样式。文化史专家冯天瑜先生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對象化。”透过人物,我们看到了某些价值观念,透过镜头,我们看到了稍纵即逝但斑斓夺目的文化景象,不在别处,就在中国的西北。
参考文献:
[1]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华夏出版社,2005:17.
[2]马陵洛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M].华夏出版社,2001:33.
[3]马陵洛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M].华夏出版社,2001:99.
[4]玛格丽特•米德.代沟[M].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