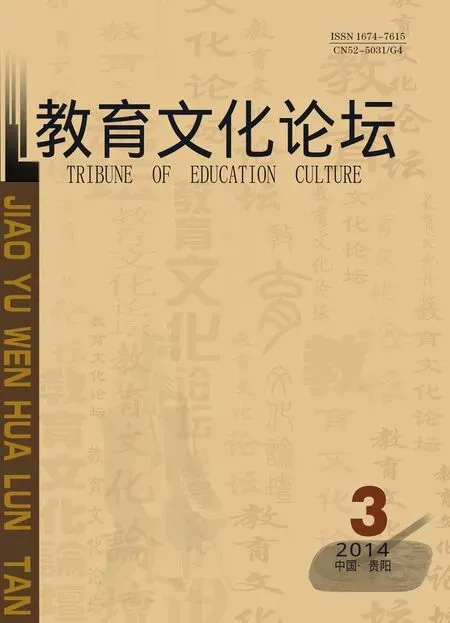影视教学中的社会性别意识解析
——以电影《图雅的婚事》为例
2014-04-17张华
张 华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众所周知,分析影视作品可以从不同视角进入。面对同一部作品,基于不同学理的解读无疑会使作品的内涵更丰富,也能帮助观众(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和创作者的意图。新世纪以来,随着女性学科的蓬勃发展,众多课程门类纷纷引入社会性别概念,为原有的课程注入了新鲜内容。影视作品具有受众多、传播面广泛的特性,笔者认为更可以借鉴这一范畴来分析影片所蕴含的特定的社会文化内容,以此补充电影语言分析的某些不足。教师可根据影视作品的具体内容,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领会隐匿在画面中的社会性别意识。本文以影片《图雅的婚事》(以下简称《图雅》)为例抛砖引玉。
《图雅》曾获第57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影片讲述了一个源于现实的“嫁夫养夫”故事:偏远的内蒙一隅,丈夫巴特尔为了打井而双腿残疾,妻子图雅独自挑起了家庭重担。长期的劳碌致使她腰椎病变,甚至可能下肢瘫痪。为了不再拖累图雅,巴特尔提出离婚。在现实困境面前,图雅同意离婚但坚持要养活巴特尔;办法是带着丈夫再嫁人。由此,图雅开始了周折的择夫再嫁经历。几次不成功的相亲后,图雅最终接受了邻居森格的求婚。然而她并没有从此渡出苦海。婚礼那天,巴特尔和森格当众掐架;图雅的儿子也因受到“两个爸爸”的嘲笑和别人打作一团。坚强的图雅终于忍不住在没人的毡包中失声痛哭起来。
从片名和故事简介不难确知,图雅是影片的核心人物,《图雅》也称得上是部典型的女性题材电影。对大多数观众而言,打动他们的也正是这个蒙古女性的坚强——甚至带点儿强悍,自力和善良。然而从社会性别的理论维度来看,女性题材电影传达的不一定是女性自主意识,反而很有可能是历史以来形成的一种社会性别观念。《图雅》恰恰如此。这一点,需要我们仔细分析影片如何塑造图雅这个人物形象才能说清。
影片在关键事件(图雅腰椎受伤)发生前,用纪录片的方式无序地表现了图雅的生活:饲弄羊群、料理家务,每天往返数十里拉水等等。丈夫残疾后,家庭生活重担全部压在图雅一个人的肩上。她日复一日地做着这些活儿,劳顿至极,靠在床头喝奶茶时都能睡着。她神情沉重地劳作,粗事大气地说话,俨然是一家之主。不过,当再嫁问题提出后,面对“嫁给谁”的选择时,图雅的自主性仿佛水中的倒影,风一吹过就一波一波地晃起来,甚至完全消失。
影片为图雅设计了一道“一女三男”的选择题。对于图雅和丈夫的关系,导演多次陈述,“《图雅》讲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爱情故事,图雅非常非常喜欢巴特尔。”[1]若非生活陷入困境,二人绝不会离婚。几次相亲的场面或许能说明问题。第一批相亲的人来了,图雅单独与他们会面。巴特尔的笛声在另一个空间幽幽响起,引得图雅频频转头。第二个重要的求亲者是宝力尔,图雅夫妇的中学同学,暗恋她十几年,一听说图雅离婚的消息就赶了来。画面中众人团坐,图雅始终挨在丈夫身边,充满依恋或依靠意味。尽管如此,图雅还是带着孩子坐进了宝力尔的小车,安排巴特尔住进福利院,准备开始新生活。影片又是如何处理图雅和宝力尔的关系呢?虽然导演对这个男人的性格阐述只是“很软弱”,但在影片中,成为大老板的宝力尔完全是“有钱人没德行”的活标本。先是企图强行与图雅发生性关系,遭到拒绝;继而为了留下图雅,隐瞒了巴特尔在福利院绝望自杀的消息。从人物设计的角度来说,宝力尔这个形象显然简单化、极端化了,几乎是金钱的化身,成为考量图雅选择的一种因素。
最后一个求婚者是森格,他愿意与图雅共同养活巴特尔。森格曾直言图雅,他知道她最想要的是男人。这种理解成为二人日常接触中的默契。森格以打井的方式来求婚。当他在图雅家门口摆开阵式时,图雅极力反对;然而丈夫说“我们也可以用”,她也就不再多说什么。慢慢地,图雅对森格的态度有了转变,不仅开始为森格等煮奶茶,还决定到井下去看看。很少照镜的图雅在下井之前仔细地对着镜子戴好头巾,特写的脸上隐约浮起她心底的某种情绪。这种情绪一直笼罩着图雅,直至她下到井底,与森格相拥而坐。显然,此时图雅对森格已有了不同于巴特尔的情感,是男女相悦之情。如果在前述相亲戏中的确能看出图雅和丈夫的爱情,到了“井下”,图雅的感情世界已变化了。另一场戏更明确地延续了这种“变化”,就是森格突然消失后又带着打井队和离婚证回来。此前图雅不知内情,以为森格把求婚的事抛于脑后,又跑去找前妻了。影片中,图雅面无表情地出镜,心底里早已波澜动荡了。突然又见森格回来,怒不可遏的图雅说话间与他撕打到一处。二人在地上翻滚着,镜头随着动作渐缓而一点点拉开,最后落在远景、静止画面中:二人停止撕打,相拥而卧。这几场戏表明,影片中图雅作为女性的情欲需求是通过与森格的关系来表现的。然而导演处理得很节制,仅仅“点到”而已,似乎图雅的内心只能罩于“井下”,成为一片被遮蔽的天空。
整个相亲过程中还有几场戏不容忽视。其一,图雅躺在床上和巴特尔商量,要不要嫁给一个“能给孩子辅导功课”的老头,“你说嫁就嫁”,而巴特尔回答“不嫁”,此事就此了结。由此回顾整个相亲过程,不觉令人尴尬:虽然提出“嫁夫养夫”的是图雅,然而“嫁给谁”的决定权却在巴特尔那儿。不论由宝力尔安排去福利院还是森格在家门口打井,都是巴特尔默许的事,实际上是丈夫替图雅应了他们的求婚。不论巴特尔是否是为了图雅考虑,这种“决定权”都令人置疑他和图雅的爱情。图雅的自主性从何谈起?其二,图雅得知巴特尔自杀的消息以后赶回医院,面对躺在病床上的巴特尔,图雅异常激动地把药瓶塞到儿女手中,随后自己也抓起一瓶,说要死一起死。这场戏是整部影片的一段高潮,图雅说完最后一句话 “我们谁也不能死”之后,泣不成声。其三,暴风雪要来了,图雅的儿子放羊还没有回来。图雅骑着骆驼在风雪里狂奔,几番周折,终于找到孩子。她拥抱着孩子弃羊群而去。
有评论者对后两个场景的评价极高,“母爱、母性的平凡与伟大全在这里了”。这种观影效果不仅与演员上乘的表演有关,也和导演对影片的技术处理有关。医院一场戏,一气呵成的长镜头几乎把观众带到了病房现场,让观众直接面对图雅的坚强和脆弱,面对死的痛苦与生的悲惨,观众很难不为所动。雪地寻子的画面几乎被拍成了一张静穆的风情画。当图雅在风雪中找到孩子时,深情悠扬的音乐随之而起,直接表达了导演对一位母亲的礼赞!观众有理由欣赏图雅在此表现出的人格魅力。
然而当我们把这几场戏和前述表现图雅与求婚者关系的主线放在一起时,就会看出问题: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图雅形象是被有意放大了的,导演愿意用一切电影语汇去描述她的坚强、善良、无私、伟大;但当图雅以一个内心有情感欲望的女人身份出现时,导演的表述就很有限也很谨慎,让观众看到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拥抱。说到底,导演是要把图雅塑造成典型的、富于传统光辉的贤妻良母。其中原因何在?
不论放眼于历史还是环视当下,中国都是一个以男权话语为主导的社会,女性形象的美丑善恶均以男权文化为标准来核定。换句话说,像图雅这样的贤妻良母是男性想象中的理想女性,是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中的好女人。严峻的生存问题往往成为考量她(们)是否坚忍和贤良的实验场。比如,图雅的独当一面之后是丈夫残疾、孩子待哺。作为妻子和母亲,当家庭陷入困境时,为了养活一家老少,她应该忍辱负重有所付出。图雅其实并无选择可言,也就无法把其自主性落到实处。如果一定说有,那实际上是一种男性视野中的女性使命感。因而影片中的图雅总是忧郁而疲惫。作为妻子和母亲,她还应该拒绝的金钱的诱惑,也不要考虑自我的欲望和情感需求。这也就注定了,图雅的婚事最终成为一次在贤妻良母之名下牺牲自已的“义举”。因此,影片的环型结构(结尾与开头是同一场戏)在笔者看来意味着图雅的这种生存状态会继续下去*导演用这种结构的意图可能在于表现一种普遍的人的困境,即他所谓超越了文化的界限;然而实际上,这种困境在影片中只落在图雅一个人身上。:终点即起点,图雅的新生活只是过去生活的重复,毫无新意可言;图雅还必须“坚强”地活下去,背负着生存和欲望的双重重担。
或许有观众(读者)会质疑:难道《图雅》表现的不正是一种女性生存困境吗?我们不该籍由影片去关注诸如此类的现实吗?不错,该片所表现的女性生存现状中无疑更值得关注。但令人担忧的问题在于,这既不是导演的创作初衷也不是大多数观众的看点:导演关注的是人在极致环境中的生命力,[2]
绝大多数观众则被影片中“母亲和母性的伟大”而感动和震撼。换言之,被大银幕广而告之的图雅的故事不一定有助于解决女性的现实困境,却一定会把贤妻良母的社会性别观念发扬光大。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尖锐指出,《图雅》并非有关人性的光辉或复杂性的故事,而是一个在人性的水平线之下的故事。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修正主义版的“烈女传”[3]。就此而言,在影视教学中吸纳社会性别视野不仅有研究意义更有现实的必要性。
[1][2] 吴冠平,王全安.图雅的爱情故事——王全安访谈[J].电影艺术,2007(3):66,64.
[3] 崔卫平.带关前夫去结婚[J].视野,2007(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