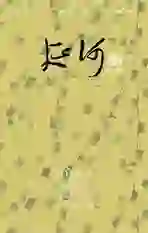乡村物语
2014-07-24马浩
马浩
独轮车
独轮车,家乡人称之为“胶车子”,为何会有此“莫名”的称谓,其中又有隐含了什么样的机巧与故事,至今,我都没弄明白,不堪了了。
世间之事,也许本来就没那么复杂,纯属偶然,就像桑梓,松柏,杨柳……若当初先人把梓名为桑,把柏名为松,把柳名为杨,恐怕而今在人们的意识里,那些树木的形象刚好颠倒过来。这让我想到女儿读小学时,写过的一则日记,她说,“若爸不跟妈妈结婚,我就不是爸爸的女儿,看到别的漂亮女孩坐在爸爸的腿上,我不得气死了。”世间万物似乎都有定数,也就是“道”,当小路上咿呀着手推车的声音,我的目前立马呈现胶车子的形象,这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不由人的。
现在,这种独轮车,基本上是难得一见了,不过,行在崎岖的山经,或漫步在蚰蜒般细长的阡陌,不觉地便会想到胶车子。我想独轮车的发明,于路是不无关系的,过去,乡间道路都是“自发”形成的,就像鲁迅先生所言的那样,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民间还有句大俗语:路要众人踩。众人踩出的小路,便是独轮车的胚胎。
对于家乡人称之为胶车子的独轮车,我相信在其他的地方,一定还有别的不可思议的有趣的叫法,只是孤陋的我所不知罢了。我曾一度想当然地以为,独轮车就是出川九伐中原的诸葛亮发明的,这大概跟我儿时看有关三国的小人书有关,当然,还有我儿时对独轮车的记忆有关。
儿时,最早见过的独轮车,是木头制作的,车轮子是木头的,车身子亦是木头的,车子的主人,是住在村子最东北角的一个孤身老人,老人所居的矮小的茅屋,与村子隔着一段杨树林子,一条细长小路似脐带,连接着村子,忽然哪天,脐带断了,他便会被游离在村子之外了。在我的印象里,老人好像总是推着那辆木头胶车子,穿行在那片杨树林里,车轮压在小路上,咯哒,咯哒地响。老人嘴咬着长长的烟管,似乎很享受这种声响,晃悠悠地走着,有时看他推着车子,如此地惬意,便央求着,试一试,一端起车子,还没走呢,车子便往一边倒去,老人就嘿嘿地发笑。
那时,村子里有独轮车的人家,不在少数,轱辘是钢圈的那种,只是车架子是木头的,轱辘的内带可以充气,车子推起来,轻快,声音也小。田里送粪,收获庄稼,胶车子便派上了用场,尤其在土堰上,路面很狭小,越能显示独轮车的好来,平时,赶集上店,推着胶车子,卖粮食,买回生活所需,独轮车轻快,省去了肩挑手提,那时,推着胶车子赶集,夸张点说,无异于曾经的骑着自行车,而今的开着私家车。
记得小时候赶庙会,父亲推着独轮车,一边厢是我,一边厢是所卖之物,车子一路吱咯着,附和着父亲所讲的故事,满撒在我的记忆里。集市上,父亲把胶车子放在大鼓场的边上,交代我,听大鼓,看车子,买包子给我吃,买小人书给我看。我便老老实实地坐在车帮上,听大鼓,听着听着,人就被说书者带进了书中,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忘记了我屁股下的胶车子。
父亲曾在砖窑厂给人推土,胶车子便成了,父亲赚钱的工具,那时砖窑厂是人工磕坯,木头制作的砖头模具,通常是两个的坯模,力气大者,让人专门制作的,三个坯模。父亲就用胶车子推土,胶车子的两厢各绑一只柳条长筐,按照个人所需推土,一车多少钱,计车。有时,放学有空,我会去帮父亲的忙,用根绳子拴在胶车子的前头,拉纤般,用着力拽。
似乎一转眼,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往,手推车便成了历史的陈迹。手推车,在打小日本时,曾载着物品支援前线,新中国的诞生,独轮车是有过贡献的。有关独轮车支前的故事,有机会专文叙述,在此,不作详谈了。
最近,听说独轮车是个叫奚仲的老乡发明的,是否确凿,我没有去落实。在老家邳州城里,有条路叫奚仲路,这是确定无疑的。若独轮车真的是奚仲发明的,胶车子的叫法,或许隐含着不为人知的故事,亦未可知,如同若干若干若干年之后,人们对着独轮车三个字,发呆。
爆米花机
日前,在乌镇游玩时,在河房边的空地上,见一老者手摇着黑皴皴的爆米花机,泛白的煤烟,顺着爆米花机的四周往外冒着,慢慢飘升,爬向两边的河房,浮在小河的上空,渐渐消散,小桥、流水、石板小巷,古旧的木质房舍,这样的景象,让我回溯到久远的记忆里,仿若是在北宋的汴梁,我清楚,给我如此幻觉的,是那只黑黢黢的爆米花机。
乌镇的那只爆米花机,其实,只是为了应景,让人回顾,怀旧,事实上,这个目的是达到了。有关爆米花机,有着太多的温馨的记忆,一部爆米花机,能爆出一大箩筐的故事,这是这个时代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也是无法体味的乐趣。
爆米花机,呈葫芦状,前首有类似方向盘的圆盘,盘中是块压力表,我一度以为是由看时间的钟表,后面是厚厚地铁盖子。一只烧煤炭的火炉子,一条自制的细长口袋,一头用铁圈固定,一头撒口,爆米花时,把撒口挽个扣。这就是爆米花的全部家当了,哦,还有一只拖着它们的平板车。爆米花者,大约经常与炉火打交道,脸似乎永远都是油黑的,烟熏火燎一般,衣着多藏青色,让你无法猜度他的年龄,他慢悠悠地拖着爆米花机,在乡村的小道上缓步走着,边走边吆喝,爆米花唻,爆米花——悠悠长长的声音,似有古意。
谁家的孩子,听到了吆喝声,闪身探头,远远看着拖着板车的爆米花人,急急忙忙回转身,大声嚷嚷着要爆米花。于是,大人从粮缸里,挖一茶缸玉米,跟在小孩子的身后,哪有爆米花的?说话间,就到了门外,叫声“爆米花的,过来。”
寻一处开阔的地界,把爆米花机,火炉之类的家什卸下来,安顿好,爆米花的坐定在小马扎上,一手摇着机子,一手加着煤炭,青烟缕缕上升,大约是熟能生巧,其闲适的神态,便觉生活有滋味、有情趣,有时我就想,若让忧郁症患者,拖着爆米花机走街串巷爆米花,说不定,爆米花机的一声爆响,没准就把他爆向了生活的怀抱里。看爆米花,惬意非常。爆米花机宛如一块磁铁,纷纷地把小孩子都吸引了过来,随着小孩子,还有那些家长。黑兮兮的爆米花机,在红红的火苗上,滚动着,一会儿红,一会儿黑,在红与黑的交替中,只听一声爆响,一小茶缸的玉米,就能炸一大篮子的玉米花,盆盆的香,酥脆,玉米花的清香足以弥漫半个村庄。
在尚未解决温饱乡村,爆米花是一种奢侈的小零嘴,更奢侈的,是带着甜味的爆米花,在爆米花时,放上几粒糖精,而今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有关爆米花机,还有个关于周恩来总理的桥段。说外国友人来中国访问,在街头见爆米花机爆米花,一小缸装进去,出来就是一大篮子。外国人感慨中国人的聪明。他问周总理,这是什么机械?总理答曰,这是粮食扩大器。每每想到这个桥段,就想笑,民间就是有编故事的高手。
爆米花机,能爆的东西很多,大米、玉米、干的米糕之类等等。在北方的农村,一般都是爆的玉米花,南方的水乡呢,自然多是爆的大米了。地方特色。有关爆米花的小零食,据说最早是在北宋时期。
北方民间有个神话故事,“金豆开花”用以解救龙王为人间降雨。传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这天,人们都要爆玉米花以充金豆花,以期风调雨顺。
宋朝诗人范成大在他的《石湖集》中,曾提及上元节吴中各地爆谷的风俗,并解释说:“炒糯谷以卜,谷名勃娄,北人号糯米花。”《吴郡志·风俗》中记载:“上元,……爆糯谷于釜中,名孛娄,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在新春来临之际宋人用爆米花来卜知一年的吉凶,姑娘们则以此卜问自己的终身大事。宋人把饮食加入文化使之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清诗人赵翼在他著的《檐曝杂记》中,收录一首《爆孛娄诗》:“东入吴门十万家,家家爆谷卜年华。就锅排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红粉美人占喜事,白头老叟问生涯。晓来妆饰诸儿子,数片梅花插鬓斜。”诗人是热爱生活的,看什么都觉的有生趣。
二月二,爆米花的习俗,我知道在老家邳州一带,至今依旧沿袭着。爆米花是用铁锅炒的,柴火,炒时,用淘洗过的沙子去恒温,玉米粒在滚烫的沙子中受热,由表及里,激情澎湃,只听“砰”的一声,一粒玉米开花了,噼噼啪啪,玉米花竞相绽放。至于爆米花机,始于何时,不曾去考证,我有记忆时,它常在乡野中出没,它落地之处,都会弥漫着爆米花诱人的香味。而今,在乡村,拖着爆米花机身影难得一见了,孰料竟在乌镇偶遇,不禁感慨系之。我很怀念。
纸捻子
纸捻子,作为一种包扎绳,在市面似乎是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俗称尼龙匹的塑料制品。商业社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尼龙匹自有自身的优势,不过,站在环保的角度来看,纸捻子显然胜过尼龙匹,况且纸捻子包扎东西,温情,有人情味。
惭愧得很,对于纸捻子,似乎老早就被我埋葬在记忆深处了,所好的是,经过时光的磨洗,始终没有擦洗掉,但又风吹草动,便在忆念里若隐若现。日前,翻阅知堂美文,《关于纸》一文中,纸捻一词抓了我的眼球,不由地走了神。
关于纸捻子,我有着太多温馨的回忆。纸捻子,顾名思义用纸张制作的一种纸质捻子,用普通话讲就是细纸绳,其用途是包扎东西。纸捻子可以说是拓展了纸的用途,纸的发明,利于文化的传播,纸捻子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号称我国的四大发明,其意义自然深广远大。上古,祖先结绳记事,仓颉造字,始以甲骨为“纸”,而后有简牍,韦编三绝,孔子翻阅的便是简牍,后来用了更为轻便的缣帛,穷图匕现,估计那图就是绘画在缣帛上的。1957年陕西省博物馆在西安东郊灞桥附近的一座西汉墓中,发掘出了一批称之为“灞桥纸”的实物,不过,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乃史上公论。
顺笔而下,扯得有点远,好在并非离题万里,说的还是纸,纸捻子的纸。纸捻子所用的纸,俗称桑皮纸,是否真的用桑皮制作的,没有考证,不敢妄论,桑皮纸,色赭黄,比一般的白纸要厚得多,极具韧性,估计这些特点,让它从纸的家族中分家而出。至于如何制作的,实话实说,我不曾得见,我见到它时,是在商店里,团在一起,很安静地坐在水泥的柜台上,在中药铺里,也有它的身影。
来一斤白糖。营业员麻利地在柜台上铺一张赭黄色的草纸,白糖已称好,往纸上一到,雪白的糖,暗黄的纸,竟是如此和谐统一,没来得及多看,营业员便熟练地把白糖包成砖块,随手拉过纸捻子,三绕两绕,便把砖头捆好了,还不忘上边留个扣,方便人拎着。
奶奶的胃不好,常痛,吃中药,村里有位老中医,我常去他家给奶奶抓药,迷你的小称,精巧的圆秤盘,后边一个黑漆的大木柜子,小抽屉里盛着草药,老中医铺好一张张草纸,打开抽屉,抓药,上称,然后,分放在纸上,如此反复着,几味药都抓全了,便扯出纸捻子,一包包扎好,然后再用纸捻子扎总,在上面的药包上放一小片红纸,把药递给我,交代几句,那张红纸片,真暖人。
纸捻子,在生活中不起眼,乃至不起眼到可以忽略,不过,少了它,就会觉得不方便,看来,物各有所用,存在即合理。当然,这是我写此文时的感悟,随便记录于此。
读书的时候,纸自然不可或缺,不想纸捻子也来凑趣,那时,为了节省,我时常买那种白光连纸,自己折叠成十六开,或者三十二开的写字本,折好之后,没有订书机,就用锥子锥眼,用纸捻子订。那时,学校在大队的院子里,教室的隔壁是商店,订本子时,就去商店讨要,那时,觉得去讨要纸捻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笑眯眯地往商店柜台一站,喊声叔叔,营业员叔叔似乎心知肚明,没事时,或者高兴了,便说把本子拿来,我给你契,更多的时候,扯一小团,抛在柜台上,我抓过来就跑,白色的纸,暗黄色的纸捻子作订,看着真悦目。
平时,很少能想到纸捻子的,现在,都提倡无纸化办公,字都在键盘上敲,敲着敲着,数典就忘祖了,一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字,却不会写了。而今,想到了纸捻子,忽然觉得它的好来,不独是让我怀旧,更重要的,纸捻子维系出的人情味,令人怀恋。
石碾
说道石碾,岁月似乎一下子便被拉长了,拉长到我遥不可及的童年。
在一片渚地上,一个大石碾子,每天都安静地蹲在那儿,默默地看着目前的大汪,以及汪周的杂树,尤其是近在咫尺的老柳树,粗矮的树干,烟熏火燎般的黑,千沟万壑的,对于列队在树干上急行军的蚂蚁来说,估计很恰当,也不知那些蚂蚁这么匆忙,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夏日,树冠阴翳,石碾子便在它的阴翳里,蝉声四起,汪水似乎一下子光亮了许多,石碾子也不怕闪了它的眼。
不知从何时始,石碾的碾盘有了场的功能,春日晾晒着咸菜,夏日晒着淖好的马齿苋,秋日是红辣椒的领地,冬天便被勺头菜赖上了。小孩子只有趴在碾盘上,莫名其妙地抠着石棱子的份了。有时,也以石碾为据点,玩捉迷藏,玩打仗。从我记事时起,好像石碾子从来就没有务过正业,估计石碾子也是这么看人的。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它所见的都是些闲人。尤其是夏天,柳阴下坐满了人,打牌的打牌,下象棋的下象棋,闲聊的闲聊,看热闹的人自然也不少,人来了,狗也跟着来了,狗一来,便跷起一条狗腿,在它身上画地图,似乎是想标个到此一游的记号,麻雀也不知哪里来的胆子,居然也飞落在它的头上,叽喳着,大约想寻点吃食,很失望,飞走之前,故意留下粪便,以泄心头不满。闲话的老人,说着说着,就会扯上石碾子。我在老人们的闲话中,才知道石碾子曾有过辉煌的过去。
石碾子的功能,就像乡村里曾时兴一时的轧面机,是那种只有单一粗箩的轧面机。那时,人们吃的面,都是在石碾子上滚压的。尤其是逢节时,闲人不闲石碾子,家家都排队等着压。把淘好晾干的小麦,在石碾子上滚压,粗长的木棍带动着石碾,石碾与碾盘摩擦,小麦便被碾压粉碎了,如此反复地碾压,然后,用细面箩子筛,面粉就这么被加工成了。别说,现在用石碾子碾压面粉,自给自足,绝对安全,没有吊白块之类添加剂,纯天然,无污染,食起来安全放心。
石碾子碾面,可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就不曾见过它的专长发挥。那时,村里已有了轧面机,粗面的,细面的样样都有,先是柴油机带动的,后来是电动的。石碾子自然便没了用武之地,说来也奇,长久闲置的石碾子,苍苔满身,成了不折不扣的老物件,不知何时竟被神圣化了。
小时候,大人是不让小孩子到碾盘玩,说碾盘底下有个黑鱼精,会吃小孩;还说,黑夜里黑鱼精会变成漂亮的姑娘,吸人血。黑鱼精变成美人勾引人,待你靠近她,她一下子变成了,青面獠牙的女鬼,人就被吓死了。无人相伴,我是没有胆子去那里玩的,却偏又好奇,想见一见那个黑鱼精变成的女鬼。有时,伙同多人,在少星无月的黑夜,悄悄地来到汪边,相互借胆还是怕得胆颤,默默地等啊等,只有老柳树枝舞动的风声,偶或鱼拍打水的声响,或有人突然来一嗓子——黑鱼精,于是,大家便嬉笑着作鸟兽散。
村里,有一赵姓人家,人丁不旺,生个男孩,大约为了孩子好养活,请个算命的先生,估计算命先生是天才的诗人,居然让赵姓的男孩认石碾子当干爹。而今,这位干儿子也有40多岁了,也不知还会不会偶尔想到他的干爹。
前些年,回老家时,那个石碾子依旧在,好像没有儿时那么高大了,老柳早就没有了影踪,水汪也缩得簸箕掌般大小了,里面飘满了红红绿绿的塑料袋子,黑黑的水,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村里,几乎见不到人影,都外出打工去了,石碾子冷冷清清的,不知谁家的小孩子走过来,我指着石碾子问他,知道那是什么吗?小孩子摇摇头,笑嘻嘻地走开了,不时地回头看我,很好奇。
铡刀
说起铡刀,我总会想到京剧《铡美案》,还有人民英雄刘胡兰,相信有这种联想的人,不在少数。估计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在铡刀,铡刀已物为役使,迷失自身的本真。铡刀作为一种农具,简单实用,凝结了先人的智慧,乃农业文明的结果。
铡刀,由刀座与铡刀两部分组成。一把带有短柄的柳叶形生铁大刀,短柄有裤,可装细木续以为柄,刀座是一块中间挖槽的长形方木,一般选细密硬朗的材质,耐磨经用,榆木便很有竞争力,把刀的一头固定在底槽里,有把的那头可以上下自由活动。铡刀用的是物理上的杠杆原理。如此看来,理论一旦付诸于实践,就成了赋有生命力的活物。铡刀就是很好的例证。
有关于铡刀的记忆,始于农村的大集体,那时,我还是个孩童,五月的夏风一吹,昨天还泛着青的小麦,一夜间就变作金黄,俗话说,“蚕老一时,麦老一晌”。村头一站,一眼望不到边的金黄,风痕过处,麦浪翻滚。麦浪一词,都叫人用烂了,麦苗青时,碧色的麦浪,麦子黄了,金色的麦浪,觉得一点创意都没有,当你身临其境,便觉得除此,还真的没有比它在合适的词语了。我已好久好久没有这个体验了,不过每每想起如此场景,都会激动不已。
过去,麦收时节号称麦口,靠天吃饭的农人,于季节口中夺食,抢收抢种,小麦上场了,铡刀便在大场上大显身手。小麦收割成一捆捆的,成捆的小麦放在铡刀上铡,麦穗留下来,麦秸丢在一边,这就如同写文章一样,精粹材料,重点突出,那场面热闹非常,握铡刀者,一般都是壮劳力,气力足,手起刀落,绝不拖泥带水,嗤的一声,麦穗头与麦秸腿便身手异处。续得紧铡得快,前仆后继,你来我往,当然,干活时并非鸦雀无语,大家有说有笑,拿这人开心,那人逗乐,有人说一段带着荤腥味的笑话,气氛轻松愉快。没事的时候,我喜欢看大人们铡麦,顺便跟着他们拾二笑,有人便过来打趣我,傻笑什么?你知道说的什么?诡异一笑,大家便跟着哄笑起来。
麦收结束后,铡刀基本就闲置,到冬天方才出山,那就是铡麦草,铡玉米秸之类的草料喂牛。铡草料,一般都在冬日的中午,天气暖融融的,“牛头”搬来了铡刀,饲养员们就在草垛上抱来麦草,铡成一段段的,喂牛时,把铡好的麦草往牛槽里一放,倒上豆沫水,牛便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牛们是不会感谢铡刀的,它们也不知道,铡刀事先已把那些麦草给咬碎了,铡好的麦草,可以填在鞋里,为脚保暖,铡好的麦草堆在牛屋里,家中穷的少被子盖的人不多,可不是没有,夜里就钻进麦草堆里睡觉,夜晚,牛屋里聚满了人,冬日夜长,人们都到牛屋里取暖、闲话,打发漫长的寒夜,我常在那里听人讲故事,尤喜听人讲恐怖的鬼故事,想听,听完了又不敢回家,就特羡慕钻进麦草里睡觉的人。
后来,分田到户,有了脱粒机,有了收割机,铡刀似乎就突然不见了,也不知躲到何处,独自垂泪去了,它或许不知道,它一泪垂,刀面就会生锈,锈迹斑斑,就更没人待见了,生活有时就是这样,有用的常会被人记起。
一天,在中药铺,看到一把铡刀,迷你版的,顿觉亲切,把那小铡刀,切中草药用的,切片、切段……轻巧、灵活,我突然觉得,这才是铡刀的好去处。铡刀,就像一味中草药,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药草香,弥漫在农耕文明的气氛里,疗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