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与无限(上)
2014-05-10;
●[] ;
1 表示与对象性关系
a. 被是所吸收的主体
主体在表示中的卷入,一个从【主体与他者之】切近中显示出来的卷入,并不等于表示之被翻转到了对象的一边,并不等于表示所具有的各项——通过它们在是其所是之中的出现,并通过是其所是【本身】的出现——之在一个共同基础之上的摊开,也不等于表示之被还原为人们称之为主观体验者。*译自Emmanuel Levinas, Autrementqu’êtreou au-delà de l’essence (Phaenomenologica 54,1974, fifth printing 1991,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此为该书第五章。这是最后一章。在本汉语译文中,通常译为“存在/存有”的“Etre”(Being/being)一律译为“是”,通常译为“本质”的“essence”则译为“是其所是”。理由见本译文所附列维纳斯为此书所做之书前总注。“Sens”在本译文中皆译为“意义”,与此相应的“non-sens”译为“非意义”或“无意义”。《法汉词典》中被解释为“意义,意味,意思,含意,涵义”的“signification”,当作者侧重其动词义时我译为“表示”,当其名词义被强调时我处理为“所表示者”。此乃本文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读者应该意识到其与被译为“意义”的“sens”之间的重要区别。在本文中,与“signification”相应的是不见于《法汉词典》的“signifiance”,英译者译为“signifyingness”,在本译文中译为“进行表示”或“表示活动”,以强调其所欲传达的名词之中的动词义。方括号中之文乃译者为补足语义所加,尤其是在“的”字前所加的“所具有”三字。这是由于汉语的“的”一身二任,既表一事物对其他事物之领属,亦表定语对中心语之修饰。于是,本文中反复出现的“无限的荣耀”就既可以被理解为“此荣耀是无限的”,也可以被理解为“无限所具有/拥有之荣耀”。凡此之处,译者皆不厌其烦加以澄清,请读者见谅。不过,我们首先应该回想一下是其所是【这一活动】在对象这边行进的方式:这一活动是通过吸收与对象相对应的主体以及通过战胜——在其“姿态”(geste)之真中——主体的优先地位和主体—对象的对应关系而进行的。
的确,人之能去思想是(être)就意味着,是之出现属于是之行进本身,意味着是所具有的现象性是根本的,而且意味着是绕不开意识,而显现即为着此意识而被形成。然而,如此一来,在真之中以及在真者之真中——亦即,在是其所是(Essence)的出现之中——显示自身的是之是其所是(l’Essencede l’être),就并不是以被揭示之诸项的各种属性的形式而被铭刻下来的,也并不是被铭刻在被揭示之诸项的本质(quiddite)之内的,同时也并不是被铭刻在那聚合了被揭示之诸项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性之中的。但另一方面,真者之真,或其被揭示,或被揭示者之裸体,却也并不接受任何虚假的或真实的“外表”,任何被想象出来的“性格”,那可能会自迎接着被发现者或被揭示者之呈现的意识而来的“外表”或“性格”。*亦即,是意识本身以为被揭示者所可能具有的外表或性格。——译注(此后凡译注即不再一一标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显现不属于是作为是而进行的活动或“游戏”的话,那么显现本身——正如我们刚刚肯定过的——就只会是虚假的外表而已。更有甚者,对象性,或者说,那被揭示于其真相之中的是之是其所是,以某种方式保护着是之展开,使之不会受到那可能会来扰乱是其所是之过程或行进的主观幻觉之投射的影响。对象性与是其所是者承载着的【自身之】是有关。对象性意味着出现者对于其自身之出现的无动于衷。是其所是的现象性,以及那些真实之项的现象性,就好像同时也是此一现象性的附带现象【性】一样。此种无动于衷——亦即,完全不去指涉或参照自身以外之物*此为意译。原文为“Referencepurement negative”。直译可为“纯粹否定性的(或负面的)指涉或参照”,但颇为费解。——乃是系统对于发生在系统之外者的无动于衷。准确地说,是在这样一个系统之外,在这里所发生的非常事件就是知,那并不会影响此一系统——一个被知加以话题化的系统——的知。作为知,主体性使自身从属于对象性这一意义。
现象性——是之是其所是展示自身于真之中——是西方哲学传统永恒的预先假定:是之去是(l’essede l’être)——是其所是者即由此方为是其所是者——乃思想之事,是之去是给思想以可思者,并从一开始就将自身保持在敞开之中。由此说来,在是之中确实有着某种贫困:是被束缚于一异于其自身者,一个被召唤来欢迎其显现的主体。是诉诸为其生活方式所必须的某种接受性,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此乃是其所是的有限性。*有限性还可以被想得更根本一些:从知出发而将有限性想为普遍性的出现。在此,出现只有作为话题化和作为对象性才可能,而普遍性——概念——则只有从否定个体的抽象出发才可能。个体则只有作为可败坏的或有限的才让这一否定有机可乘。——原注由此而来的一个事实就是,除了主体在是其所是的揭示【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意识出于自身的算计而玩的一切游戏都只能成为是之是其所是的遮蔽,亦即,谎言或意识形态,而此种谎言或意识形态的地位则很难被毫无歧义地确定出来。因为谎言或意识形态既可以被解释为是之有限性所产生的纯粹效果,也可以被解释为某种【主观的】狡猾伎俩所产生的效果:柏拉图《小希庇亚篇》中的尤利西斯生在主体——在真面前抹去自身的主体——之“空”中,他跟真【者】耍狡猾伎俩,他比主体所具有的聪明更聪明,聪明到狡黠,聪明到无所不能。*柏拉图的《小希庇亚篇》(参阅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一卷页276—296)是苏格拉底与智者希庇亚对话。苏格拉底想论证故意做错事比并非故意做错事要好。希庇亚认为荷马笔下的尤利西斯精明到能够有意骗人,所以不好。苏格拉底则认为,能够有意骗人的人也是能够了解真相的人,因此比没有能力了解真相因而也不能有意骗人的人更出色。列维纳斯此处的引用似乎只是断章取义:主体通过在真面前抹去自身而让真(实/相)出现。这样的主体是空。此空让企图在真面前耍伎俩的精明的尤利西斯有机可乘,所以说他诞生在此主体所形成的空之中。
b. 服务于系统的主体
但真【本身】之被揭示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视觉现象。如果铭刻在那显示自身的是其所是者的所是(quiddite)之中的并不是这些是其所是者的可见性,以及它们的是其所是【本身】的话,那就是它们的组合,它们的同在,亦即——而这可是某种新颖之事——一者相对于另一者而处的位置,或它们的相对性。在此相对性之中,一者让自身成为一个给另一者的符号,此即一者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表示活动(译案:一者将自身表示给另一者),而这就等于是那些被定了性的本质自身之进入光亮之中(译案:被看见)。所有这些表示/意义或结构之被组合入系统——【亦即,】可理解性——这一组合本身就是揭示。可理解性,或总体的系统性结构,将允许总体出现,并防止总体遭受可能自【对总体之】看而来的【对总体的】改变。*这就犹如已经结构起来的房子框架不会摇晃,而单独树立起来的柱子则容易推动一样。看改变被看者。此一改变的可能是被看者在看中被联系于其他被看者。有结构的总体则使此种改变不太可能。不过【总体】对于来自主体之看的此种无动于衷却并没有被同等条件地保证给【总体中之】诸项、诸结构以及系统,因为实际上一个阴影会遮蔽那被拿到关系之外的诸项(它们是被包含在关系里的),也会遮蔽那被拿到系统之外的或在其之外被撞见的诸关系和诸结构。而系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将诸关系和结构紧紧包住的:在此时刻,仍然孤立的或已经【变得】抽象的关系和结构需要寻找或复归于它们在集合之中的位置;在此时刻,诸关系仍然有待于被装载到系统之中。如果在一个被显现的秩序中,诸结构中之诸项或一系统中之诸成分是作为抽象而待在一起的,那么这一秩序就仍然是晦暗的。而且,尽管它之已被话题化,它仍然会抗拒光亮,而这也就是说,它仍不是充分地对象性的。结构就是某种可理解性,或某种合理性(rationalite),或某种有所表示(signification),而其中之诸项就其本身而言(除非是通过语言那已经是宣教性的观念性)则是无所表示的。*结构是可理解者,是合乎某种理者,或是有所表示者,亦即,是有某种意义者,但结构中之诸项单独来看则无所表示或没有意义。这些单项只在一种条件下可以有意义,那就是被语言命名,亦即,在语言中被说出来。这样,语词本身所已经具有的观念性就会赋予结构中之诸单项某种或某些独立于此结构的意义。在关系中,诸项进入某种失重状态,或者说,受到某种赦免(grace),成了某种被看的透明之物,而它们一旦被分离于关系,就会立即变重,并被遮蔽。于是我们当然就可以在这些单纯地被话题化了的、互相分开的可理解者——假使即便没有那宣教性的逻各斯,亦即,没有现象学,一个现象也还是可能的话——与一个系统的可理解性这一状态之间制造距离,于是我们就可以谈论一个从话题的单纯展示向其可理解性的过渡。我们可以在这从一者向另一者的过渡中分辨出某种犹豫——一点点的时间,某种努力的必要,某种好运或坏运的必要,以便使诸结构可以被装在一起。正是通过这一事件,或通过可理解者本身之内的这一变为开放,我们可以把握主体性,那依然将会是完全从是所具有的可理解性出发而被思考的主体性。是所具有的可理解性永远是没有阴影的正午。在此,主体虽介入其中,但却连自身的粗壮侧影都不投射出来;在此,主体,那溶解自身于诸结构所具有的这一可理解性之中的主体,永无休止地视自身为这一可理解性的服务者,而这一可理解性就等于是之出现本身。而这就是处于其纯粹性之中的理性观照意识(concience theorique rationelle),在此,在真之中出现所具有的清晰性就等于可理解性——【例如,】在好的笛卡尔传统中,那些清晰的观念就仍然从柏拉图那发射着让事物可以理解之光的太阳之处接受照明。但是这一清晰性来自某种安排,这一安排把诸是其所是者或诸时刻以及这些是其所是者的esseipsum(本身之是)整理到系统之中,亦即把它们组合起来。是之出现与诸种成分在结构之中的某种汇聚分不开,与诸结构——是就在这些结构之中行进着——之被装在一起分不开,与这些结构的同时性分不开,亦即,与它们的同在分不开。现在,真与是——真中之是——的这个享有着特权的时间,就是同时代性本身,而是之显现即为再—现。这样,主体就会是一个【进行着】再—现——在这个词所具有的近乎主动的意义上——的力量:主体会将时间上的不均匀在现在之中——在同时发生之中——拉平。在为是服务之中,主体以感觉残留(retention)和感觉预期(protention)把时间性的诸阶段统一到现在之中。*此二现象学术语“retention”与“protention”或有译为“保留”与“预留”者,或有译为“持存”与“预存”者。列维纳斯此处并非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这一对概念。主体因而行动在那四处消散的时间之中;它也作为禀赋记忆的主体,作为记史者而行动,而记史者就是如下之书的作者:在这样的书中,过去的那些失散了的成分,或【未来的】那些仍然在被期待着和恐惧着的成分,在一卷之中接受了同时性。孤立的成分或孤立的结构是不可能展示自身而又不被其无所表示性所遮蔽的。
正因为无所表示的诸成分之被组合到结构之中,以及诸结构之被安排到系统或总体之中包含着风险和耽误,而这就好像某种好运或坏运,也正因为是之有限不仅只在于命运注定了其走向显现的方式,而且也在于其各显现方面被装载到一起时【所可能会有】的波折和危险,所以主体,处于感觉残留、记忆和历史之中的主体,才介入进来,从而加速此种组合,赋予装载以更多的机会,统一诸成分到现在之中,并再—现这些成分。康德(B102-103)将主体的这一自发性——他称之为是在直观之中的纯粹展现——描述为Hinzutun(加合)与Sammeln(聚集)。由此Begreifen(把握,领会),亦即,概念化,就可以被获得,而直观即由于这样的把握或概念化而不再是盲目的。
这样一来,不管它的寻求如何地主动,也不管它有多少自发性,被召唤来寻求这一可理解安排的思想主体都应该被解释为是之是其所是活动所取之道,从而【是之是其所是活动】让自身得以被安排,并因此而得以真实地(vraiment)出现,出现在真实之中。可理解性或有所表示性构成了是之活动本身的一部分,ipsumesse(存在本身)的一部分。于是一切都在同一边,都在是这一边。能够将主体吸收到那把自身交托给主体的是其所是之中来,此一可能恰为是其所是【这一活动】所特有。一切都被关进了是其所是【这一活动】。主体之主体性将始终都在于其在是之前抹去自身,在于以下述方式让是去是:将是之诸结构组合为表示,组合为所说之中的整体命题,组合为一个概括一切的宏大现在,而是就在此之中辉煌地闪耀着。
的确,落到主体头上的这一角色,主体在是之显现中所扮演的角色,使主体成为是之行进方式的一部分。于是,作为那作为事件之是的参与者,主体也显现自身。这一使是得以揭示的功能本身也依次得到了揭示。而这就将会是意识对于自身的意识了。作为是【本身】之时刻/环节,主体作为主体显示自身于自身,并将自身作为对象交给那些关于人的科学。一个必死者——普遍(意义上)的我(Moi)*列维纳斯大写法语人称代词“Moi”——汉语的“我”——之时,他要说的是作为概念的我,普遍的我,或普遍意义上的我。英译将此“Moi”处理为“ego”,即“自我”。汉语中通常也采用“自我”这一译法。但此处不取。列维纳斯本书行文中经常对举大写的“Moi”与小写的“moi”,从而突出普遍意义上的、概念性的“我”与独一无二的、具体的“我”之不同。所以我将此译为“普遍(意义上)的我”。在语境合适时也会译作“大写之我”。——就这样被概念化了。但作为与真正之是有别者,作为与显示自身之是不同者,主体作为主体什么都不是。尽管其有限性,或正因为其有限性,是之是其所是【这一活动本身】就是去包含一切,吸收一切,囚禁一切。除了这一抹去自身于现在(presence)之前,除了这一再现,主体之真诚就并不表示着其他什么了。
c. 作为说而被吸收到所说之中的主体
如果我们只着重于被显现的是其所是之如何被传达给他人,如果我们认为说仅为所说的纯粹传达,那么主体之真诚也不会表示着任何其他什么。显现给他人,以及对于所显现之是的人际的、主体间的一致理解,也可以有一个机会在这一显现之中并且在此是之中扮演一个角色。【在此】主体的真诚将会是其【所发挥的】说这一作用,在此说之中,符号——它们本身并不重要——的发送被从属于所表示者,被从属于所说,而所说则要使自身与那显示自身的是相一致。主体不会独立地是任何表示者——主体所服务的是其所是的真相所表示者——的源头。而谎话则只不过是是之有限性让是付出的代价。通过将那些把是连接起来的是之为是论结构(structures ontologiques)确定下来,一门科学应该能够将是在其esse(去是其之所是)的所有层次上加以总体化。作为主体的主体、自我、他人将会是诸进行表示者(signifiants)以及诸被表示者(signifies),而主体对是之再现则就在此中被实现。
的确,所说可以被理解为先于传达并先于是在主体间的再现。是应该有所表示,亦即,应该显现自身为那已然在沉默的、非人的语言中被唤起者,被那沉默的声音,唤起在GelautdeStille(宁静发出的钟鸣之声)之中,唤起在那在人之前就已在说着的并且庇护着esseipsum(存在本身)的语言之中,而诗则将此语言置入人语。现象本身,在这一仍然很新的意义上,乃是现象学。而实话或谎言,在这一假定【译案:亦即,现象本身是现象学】中,就会在所说中被读到,亦即,当言语——根据传统的语言哲学——表达主体的内在经验之时。让那使诗成为可能的是之唤起在诗中鸣响,就是使一个所说鸣响。所表示者、可理解性和精神将居于显现和同时代性之中,居于梗概(synopsie)之中,居于现在之中,居于是其所是之中,而是其所是乃一现象,亦即,乃一有所表示者,其进程本身就包含着话题化、可见性和所说。任何根本性的、不可组合【为同时性】的不同时都从意义中被排除了。
于是,在再现【活动】之中,主体的心灵即在于能够进行同时化这一天赋,在于能够开始这一天赋,亦即,自由这一天赋,但这一自由是一个被吸收到所说之中的自由,一个不与任何东西相对立的自由。心灵将会是排除了所有创伤的意识,既然是/存在恰为那在一切打击之前就显现自身者,那在知之中减弱了自身之暴力者。
d. 未被吸收到是之中的能应承的主体
一个人是要对其他的人做出应承的——这样的一种局面,亦即,伦理关系,人们习惯于认为乃是从属于一个派生秩序或基于其他之物而建立起来的秩序的伦理关系,在本书中一直都是被作为不可还原者而开始研究的。这一关系被结构为“此一者而为彼一者”(l’un-pour-l’autre)。它在一切终极目的和一切系统之外表示着。当然,就是在系统之中,终极目的也不过是诸种可能的系统化的诸可能原则之一。这一应承是作为一个没有开头的情节而出现的,亦即,是无端的。任何自由,任何在一个现在之中——在某个现在之中,而此现在因而就是可被恢复出来的——所做出的诺约,都不是应承可能会为其反面的某物之正面。*亦即,自由的诺约并非与被动的、不由自主的应承相对。但在同者——那“为了他者”的同者——的【自我】让与之中,也并不包含任何奴役。在应承之中,同者(le Même)或大写之我(le Moi)乃是【单独的】
我(moi),一个作为不可被替换者而被传唤/指派了的、被激起了的我。此我因而也是一个在其最高的被动性中作为独一无二者而被指控者,一个不可能躲避开去而又没有成为不负责任(carence)者的人。*一个纯粹“伦理的”不可能性在“不可能……而没有成为不负责任”、“不可能……而无过错”、“不可能……而无罪”这样的说法中被表达了。如果所涉及的是实在的不可能性,那么应承就只不过是是之为是论层面上的必要性而已。但“纯粹伦理的”不可能性并非仅为是之为是论层面上的不可能性的简单松弛。不负责任,过错,罪,或者,用如今也许更可接受的方式来说,“复杂”——这些可并不只是为了【让】“乖孩子”【知道】的现实。——原注(译案:名词“carence”有“缺乏,缺少;逃避责任,不负责任;无能;缺乏营养;无清偿能力,无支付能力”诸义。作者这里是要说,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被替换下去的,所以我在他者的传唤和指控面前的躲避就使这里缺少了那需要对他者做出应承者,而这正是“carence”,不负责任,成为不负责任。)是,以及主体与对象的相互对应——皆可被辩解为合理,但却都是派生的——这些典范并不适合于表示,亦即,此一者而为彼一者。这个作为此一者而为彼一者的表示确实在所说之中显示出来,但它却是在事后作为被出卖者而显示自身的。而且,作为与那有关于是的所说相陌生者,它显示自身为某种自相矛盾,而正是这一自相矛盾促使柏拉图去【尝试】弑父。*指柏拉图《智者篇》(241d)中来自爱利亚的客人担心自己的话会被认为是对巴门尼德的忤逆。“客人:不过你别认为我正在变成一个杀父母的忤逆者。泰阿泰德:以什么方式?客人:我们发现在为自己辩护时,必须对我们的父亲巴门尼德的论断提出质疑,并且用主要的力量去建立这样的命题:不存在的东西在某些方面具有存在,反过来也一样,存在的东西以某种方式是不存在的。”(汉语译文引自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第38—39页。如果根据本书的译法,最后这句话就是:“不是的东西在某些方面也是,反过来也一样,是的东西也以某种方式不是。”)为了理解A可以是B,不是(neant,无)就必须也是某种是。*这里将“neant”——“无”——译为“不是”,以对应“是”。这也是列维那斯欲表达者:“无”即“不是什么”,或“什么都不是”。作为一切可被话题化之关系的母体,此一者而为彼一者,或表示——意义,可理解性——并不安息(reposer)在是之中。它的焦虑不安(in-quietude)不应该以安(repos)的字眼来翻译。它指引着那超出了是的话语。通过此一者之卷入“此一者而为彼一者”之中,通过此一者之替代彼一者,是所具有的诸基础就被动摇了,或被巩固了。但与那些神话所说的相反,这一动摇或这一巩固并不以任何名义属于是之姿态(geste)。在那些神话中,诸事物与诸是其所是者的起源其实已经是某一历史的结果。这一历史是被称作神的或被赋予了造物赋形之力的某些事物或某些是其所是者所经历的。表示之进行表示并不表现为一种再现,也并不表现为对某一不在的象征性唤起,亦即,并不表现为某种权宜之计,或现在/在场的某种缺失。它也并不表现为竞出高于现在/在场之价,而观念主义就是据此来思考主体性的。在这样的主体性之中,现在重新加入自身,肯定自身,成为【自身与自身的】重合。表示之中当然也有某种竞出高价:此一者在作为应承的“此一者而为彼一者”之中的卷入竞出了高于具有同一性者的那可被再现的统一性之价,但不是通过有所剩余或通过现在之不在,而是通过我(Moi)之独一无二性,通过我之为那独一无二的应承者(repondant)*“Repondant”有“保证人、担保人、保释者”之义。此处译为“应承者”,与本翻译之译“responsabilite”为“应承”一致。,以及我之为独一无二的人质。没有任何别人能够代替此一人质而又不把应承变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角色而已。是与不是(neant)的游戏并不把有所表示/意义(signification)还原为无意义(non-sens)。人质这一状态并非出于选择:如果有选择,主体就会保住它的矜持(quantsoi)及其内部生命中之诸出口,但其主体性,其心灵本身,却是为了他者的,而其独立的姿态本身则就只在于去支持他者——去为他者补(偿)赎(罪)。
因此,在“此一者而为彼一者”中,此一者的卷入不应该被还原为某一单项在一个关系中的那种卷入,某一成分在一个结构中的那种卷入,或某一结构在一个系统中的那种卷入,而系统正是所有形式的西方思想所寻求的安全避风港,或灵魂应该进入的隐退之处。
e. 此一者而为彼一者并非一种诺约
此一者而为彼一者是理论的基础,因为它使关系成为可能,使一个在是之外的点——一个无私之点——成为可能,而这对于一个不想成为纯粹意识形态的真理(verite)来说乃是必要的。但此一者而为彼一者并非人们所理解的“有诺约的主体”。诺约已经预设了一个作为能去担当些什么——无论是事先还是事后——的可能性的理论意识,一种超出了被动性【所具有】的容受性的担当。没有这样一种担当,诺约不就成了一个成分之被单纯地固定在一个机械的或逻辑的决定关系之中,就像一个手指可以被卡在一个齿轮传动系统之中那样吗?作为一个被自由地做出了的或被自由地同意了的决定的结果,作为容受性之被逆转为主动计划(projet)的结果,诺约总是会回指到——我们还有必要再次重复这一点吗——一个有意向的思想,一个担当,一个向某一现在开放的主体,一个再现,一个逻各斯。一个有诺约的意识,如果它不消失在它被抛入其中的系列的干扰之中的话,那就会是在处境之中——那被强加到这一意识之上者乃是已经被衡量者,并形成一个条件和一个处所。在此,通过居住于此条件和此处所之中,此一意识之化身所遭遇的障碍就被“倒转”为自由和源头,而这一障碍之重量则被“倒转”为一个过去。处境之中的意识,以及所有那些取自于其选择的东西,形成一个局面,其中的各项是同时性的或可被同时化的,是被记忆和预见组合到一个过去和未来【所构成】的视域之中的。在此,只是由于其无意义,超出【这个概念】才否定性地具有了意义。
此一者之被卷入“此一者而为彼一者”则以某种方式而全然不同于诺约。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被抛弃在世界之中*这是对海德格尔的“被抛”概念的指涉。,亦即,并不是这样一种形势,一种从一开始就是其自身之翻转的形势。在此种形势之中,我可以安顿下来并且为自己建设一个地方。亦即,这样一种形势,它产生自身并且将自身翻转成为对那被置入聚合之中的杂多的再现。【我们】这里所涉及的则是这样一种表示:在这一表示之中,安顿和再现所具有的意义当然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但这一表示在那尚未及于任何世界之处表示着同者与他者之切近,而在这一切近之中,同者之被卷入他者则表示着同者之为他者所传唤。这一传唤正就是表示之有所表示,或正就是同者之心灵。而由于这一心灵,切近就是我之去接近他者,亦即,就是同者与他者之切近从来也没能足够地近这样一个事实。被传唤者是普遍的我(Moi)或【特定的、独一无二的】我(moi)。我以我的同一性以及我对是之场域的占领而推开和疏远邻人,所以我才总是需要重新建立【与邻人的】和平【关系】。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表明,在这个有所表示者(signifier)之中,在这个“此一者而为彼一者”之中,究竟是什么可以而且必须【将我们】引向知,引向提问,引向“这是关于……的呢?”这一问题,引向那个有关【我们】与是之亲近的明确表述(就好像是乃是已然先在的和隐含的一样)。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表明,在这个有所表示者之中,究竟是什么【把我们】引向是之为是论(ontologie),从而也引向现在,引向那如日中天而毫无阴影的真之显现,引向算计,引向思想,引向安顿,引向制度。然而,无论是这一亲近,还是这些是之步伐,都并不给接近一个基础。【我们】与是的事先亲近并不先于【我与他者的】接近。接近的意义是善——既没有知在内但也没有盲目性在内的,而且超出了是其所是的善。善确实也会在是之为是论中将自身显现为一变形到是其所是之中者,并被还原,不过是其所是却并不能把善完全包含在自身之内。
到目前为止,本书中所做的一切分析都应该可以辩明,拒绝把切近考虑为进行话题化的意向性和开放和是之为是论【所发生】的突变,是有道理的。切近并非是之为是论【所发生】的突变,亦即,并非【是之】事件【所发生】的突变。确实,在【是之】事件中,一切东西都显示自身,哪怕就是被这一显示所出卖也罢。在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中,只有这一事件才被承认为意义(sens)的连贯表述(articulation),亦即,精神的冒险。然而,独立于这一有关意识的唯精神论而被设想的、并被承认为表示或承认为善的切近,却允许善被理解为不同于那需要去被满足(satisfaire)的利他倾向者。因为,表示,或此一者而为彼一者,从来也不是一个足够,而表示这一运动则是往而不返的。善也要被理解为不同于意志所做之决定者,亦即,被理解为不同于意识之行动者。此种行动或开始于那在意识之中有其起源的选择【所具有】的现在之中,或开始于那为居【于是之中】(居是一切起源的语境!)所制约的选择【所具有】的现在之中。善在主体之中,善就是无端本身。作为对他者的自由所做出的应承,善先于内在于我的任何自由,但也先于内在于我的任何暴力,那将会是自由之反面的暴力,因为如果说没有任何人会心甘情愿地好,但也没有人会是受好之奴役者。善(bonte)这一剧情和好(Bien)这一剧情——在意识之外,在是其所是之外——乃是替代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剧情,而那在其被隐藏的真实之中的所说则既在我们面前出卖它,也在我们面前传达它。那从应承出发的我是“为—他者”的,是裸露,是暴露于影响,是纯粹的容受。它不置立自己,不占有自己也不认识/承认自己,它消耗自己,交出自己,去除自己【存身】之所,丢失自己【存身】之处,放逐自己,流放自己于自己之中;然而,就好像它的皮肤本身也还是某种在是之中掩蔽自己的方式那样,它【仍然】被暴露于伤害和侮辱,它清空自身为非处(non-lieu),以至于到了以自己替代他者这一地步,它无法把自己保持在自身之内,除非是在其放逐的痕迹之中。“交出自己(selivrer)”、“消耗自己(seconsumer)”、“放逐自己(s’exile)”这些动词通过其【反身】代词形式所提示的并不是对自己进行反思这一活动,也不是去为自己操心这一活动。它们所提示的其实并非任何活动,而是一种被动性。在【以自己】替代【他人】之中,此种被动性已经超出了是所具有的被动性。就像在自己之放逐的痕迹之中那样在自己之内,而这其实就是将自己从自己之中完全拔出。*西蒙娜·韦依尔(Simone Weil, 1909-1943,法国哲学家,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政治活动家)写道:父啊,把这个身体和这个灵魂从我这儿拿去做成你的东西吧,让我只永恒地存在于这一拿走本身之中。——原注这因而也就是:内在性。内在性根本不是某种处理私人事务的方式。这一没有秘密的内在性是那已然命令了我的过分过度(demesure)的纯粹见证。而此我,以从自己口中拿出面包和将自己的皮肤变为礼物的形式,被给予了他者。
不是诺约描述出了表示,而是表示,作为切近【所包含】的此一者而为彼一者,辩明了所有诺约的道理。
在【我】那与/对邻人的非无差异/有动于衷(non-indifference)——在这里,切近从来都没有足够地近——之中,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difference),以及主体之不可能推卸自身,并没有像在我与他者的关系被理解为是相互的这样一种情况中时那样被抹除。*此处有列维纳斯在此书中屡次使用的双关表达:“indifference”字面上是“difference”——差异——的反面,亦即,“无差异”。但其在法语中约定俗成的意思是“无所谓,不在乎,不感兴趣,漠不关心”。以“non-”对“无差异”加以否定,字面上就成了“非无差异”,引申为“并非漠不关心,并非无动于衷”。我对他者的并非漠不关心或并非无动于衷是由于他者与我的绝对差异。译文中有时采用“并非无动于衷”这样的译法,有时采用“非无差异/有动于衷”这样的译法,以明确表示列维纳斯欲以“non-indifference”传达的这一双关意义。我存在于其中的那对于作为他者之他者的并非无动于衷是对于他人和邻人的并非无动于衷,此一并非无动于衷超出了自愿这一意义上的诺约,因为这一并非无动于衷一直延伸到我之所是(mon port même d’etant)的深处,以至于达到了【以我】替代【他者】这一地步。同时,此一并非无动于衷也处在那尚未及于诺约之处,因为正是它从这一极端的被动性中分离出一个不可推卸自身的和独一无二的主体。应承,或那作为表示的并非无动于衷,在一个独特的意义上是只从自我走向他者的。在作为应承之说——此乃暴露于责任,一个没人能把我替换下去的责任——中,我是独一无二的。【我】与他者之间的和平首先是我之事。并非无动于衷,说,应承,接近:这就是分离出一个要去做出应承的独一无二者,我。我出现的方式就是出庭。我置自己于一不可推卸的传唤【所加之于我】的被动性之中,亦即,我在宾格(accusatif)之中,亦即,我是一己。但却并不是作为普遍的一个特例,一个属于普遍之我(Moi)这一概念的我(moi),而是作为被以【主格】第一人称——我(je)——说出的我,一个在我所属的种类之中只有我这一个的我。当然,在我们目前这个阐述中,此我已经就变成普遍的了,但我却又能够想到一个与此普遍的决裂,以及那始终先于反思的独一无二之我的出现。此反思(以我们在怀疑主义的【一再】被反驳而又一再诞生中所发现的更迭方式)将重新回来把我包括在概念之内,而我则又将重新让自己逃离或将自己拔出。我(moi)的独一无二性,或【主格第一人称之】我(je)的独一无二性,并不在于其独一无二的本性或特质。没有什么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是耐得住概念的,除了那应承【之中】的我。在表示之中,我被作为独一无二者分离出来。那作为应承的说是唯一的方式。只有在这一方式之中,此一者,那不在自身之中隐藏自己,反而在反复发生之中裸露自己的此一者,那在尚未及于其同一性之处以自身替代他人的此一者,才不会让自己在这一【与他人的】关系中增多,却反而使自己作为统一体而在此关系中突出出来。切近所具有的这一“从不足够【地近】”,这一和平所具有的不安,就正是主体之为主体所具有的强烈的独一无二性。那从无条件性所具有的被动性之中——从己之被逐到己家之外这一情况之中——涌现出来的主体是不可能推卸自己的。这一不可推卸性并不是超越/先验主体性所具有的不可推卸性,这一不可推卸性也不是意向性或【人之】向世界的敞开。甚至也都不是向这样一个世界的敞开:此世界漫溢了我,而在此之中,那据说是心醉神迷的主体在独自隐藏着。
切近——并非无动于衷/并非没有差异的差异——应承:不问问题的回应——落在我身上的、成为我之责任的和平所具有的那种直接性——符号之有所表示——(并非从超越/先验主体性出发被理解的!)人之人性——暴露所具有的被动性——被暴露的被动性本身——说,那既不发生在意识之中,也不发生在按照意识或记忆而理解的诺约之中,也并不形成【诸方共在的】局面和同时性的说。*此处直译了列维纳斯的法语表述方式:用波折号连接起来的一系列并不构成完整语句的独立表述,其中每个后面都隐含着一个没有直接写出来的大大的惊叹号。切近乃是先于是其所是并先于死亡的兄弟关系,因而无论是/有与不是/无如何,无论概念如何,它都有意义(sens)。
因此,作为切近的表示乃是主体之潜在诞生。之所以是潜在诞生,正是因为【这一诞生】乃在那尚未及于起源之处,尚未及于主动创始之处,尚未及于一个可以指称出来和可以担当起来的——即使是由记忆指称出来和担当起来的——现在之处。这也是一个时序错置的诞生,因为主体先于自身的现在,主体无始(non-commencement),无端(anarchie)。之所以是潜在诞生,从不现在/在场,从而排除了自身与自身之重合【所具有】的现在,还因为主体是在接触(contact)之中,在感受性之中,在易于受伤性之中,在暴露于他者的凌辱之中。这因而就是一个愈去回应就愈加需要去做出应承的主体,就好像主体与他者之间的距离是随着切近的收紧而成比例地增加一样。主体的潜在诞生发生在没有任何既定诺约的责任之中。这就是兄弟关系,或是并不为了什么的合谋,但【这一关系或合谋】却更为苛求,因为它们收紧自身却并无终极目的,也并无任何终结。主体在无端之没有开始和责任之没有终结/目的(sans-fin)中诞生,它辉煌地增长着,就好像无限正在它之内经过自身/发生(se passer)一样。在主体【受到】的绝对传唤之中,无限被神秘地听到了:在那未及之处和那超出之处。这一声音——无限就这样地在其中被听到——的广度和语气,我们将有必要随后说明。
我们已经多次点到,有一条路从【我与】他者之切近通向是之出现,我们将会回到这一点上来。我们把主体性描述为替代他者,描述为无私或与是其所是的决裂。这一描述引导我们对以是之为是论问题为终极——或首要——问题的论点提出怀疑。*请参考我们题为《是之为是论根本吗?》的研究。《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第56号,1957年,第88—98页。——原注但这一描述真把那仍然还是被这一描述引发出来了的是其所是像驱魔一样地给逐走了吗?作为非人行为(agissement impersonnel),作为从不间断的汩汩之音,作为轻吟低唱的簌簌之声,作为有(li y a),是其所是难道不会吞没那使它得以诞生的表示吗?这一坚持不懈的非人之声难道不正是我们如今所感觉到的那个世界终结的威胁吗?人们冒险将或坚持将“此一者而为彼一者”的表示当做一个受到【条件】限制的或特殊的现象,“是【所具有】的伦理方面”,但我们有必要自问,在“此一者而为彼一者”的表示之中,是否可以听到这样一个声音,它来自于至少也像是之为是论置身于其中的那些视域一样广阔的视域。
2 无限之荣耀
a. 灵感
是之被聚合到现在之中,是之通过感觉残留、记忆和历史而被同时化,通过追想(reminiscence)而被同时化,亦即,【是之被】再现,并不整合那对于相互分开的是其所是者【所做出】的应承。再现并不整合那铭刻在人类的兄弟关系之中的【我】对于他者的应承。人类的兄弟关系并不起始于任何诺约,任何原则,亦即,并不起始于任何可以被回想起来的现在。那将我命令给他人的命令并不将自身显示给我,除了以其幽居【所留下】的痕迹——作为邻人之脸的痕迹——以外,除了以某种退隐【所留下】的痕迹以外。没有任何现实先于这一退隐,而这一退隐则只在我自己的声音——那已经在服从着的声音——中才变为现在,那祭品和礼物的现在。*我在自己的应承之声中将自身作为祭品和礼物献出,所以这一现在是祭品和礼物的现在。在这一无—端面前,在这一无始面前,那使是集合起来的活动就搁浅了。在表示之中,在超出了是及其时间之处,在超越【所具有】的那一不同时性之中,是【所进行】的是其所是的活动就被拆解了。而此超越则是一不可能被转变为内在的超越:那在超出了回忆追想之处的、并且被一个作为黑夜的间隔分离于一切现在的,乃是一个并不进入超越/先验统觉的统一之中的时间。
在我对其他人之应承这一非同寻常的日常性之中,在那对死亡的非同寻常的遗忘或那对死亡的“无视”之中,本书阐述了主体性之所表示者。我对那逃脱了我的自由【之控制】者的应承所表示者乃是超越/先验统觉之统一的失败或变节,是所有行动(acte)【所具有】的源始现实性(actualite)的失败或变节。而行动的源始现实性则是主体之自发性的起源,或是作为自发性的主体的起源。本书阐述了我的被动性,作为此一者而为彼一者的被动性,作为即因此而超越了那被理解为权能和行动的是其所是的被动性。而正因为如此,我的被动性乃是(有所)表示。这是达到了此一者而却作为彼一者之人质这一地步的此一者而为彼一者:在其被召唤出来的同一性之中,此一者是无人可以替换下去的,而且它也不回到自身;在其持身自处之中,它乃是为了他人【而做出】的补(偿)赎(罪);在其“是其所是”之中,它乃是是其所是【这一活动】的例外或替代。此一者而为彼一者并不是此一者之被实体性地转变为彼一者,而是为了彼一者,而这一“为了”是依据表示——尚未被建立在话题之中的表示——所具有的非连续性或不同时性而进行的。当然,在以所说为形式的话题中,表示确实也显示自身,但却似乎立即就陷于话题的圈套之中,陷于同时性和是其所是的圈套之
中。表示与话题并不相适合,但表示却还是得在话题中摊开自身,从而显示自身。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应该视其为“被体验到的表示”。没有什么阻止【我】对他者之应承的那一“非同—寻常”去漂浮在是之为是论的水面之上;不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在超越/先验统觉的统一之中,在现实的并因而是积极主动的综合统一之中,去为应承找到一个位置。此一者和彼一者,那被差异【所具有】的间隔分开的,或被两时之间(entretemps)——应承【所具有】的那一并非无动于衷并不取消此一之间——分开的此一者和彼一者,并不注定要被重新结合到结构的同时性之中去,或被压缩到某种“灵魂状态”之内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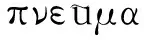
对于笛卡尔来说,灵魂与肉体的结合需要神力的介入,因为笛卡尔将这一结合视为分立之项的集合与同时,并因而根据再现【所具有】的合理性来寻找这一结合。灵魂被他理解为进行话题化的思想。但是,如果从对于另一个人的应承出发来接近在主体之内的心灵,亦即,此一者而为彼一者,那么在主体之内的心灵就是表示或可理解性,或者就是表示活动本身。这是血肉之人所具有的主体性,它处在被带向他者的引渡之中,这一主体性比原因结果链条之中的结果所具有的那种被动性更加被动,因为这一主体性超出了现实性本身,而现实性正是我思所具有的那种统觉的统一。在将自己口中的面包给予他者的这一给予之中,这一主体性是在为了另一者而将自身撕离于自身。这并不是某种无足轻重的形式关系,而是那在其给予的可能性之中被从其是其之所是的努力之中连根拔出的肉体所具有的全部重量。主体的同一性在此显露了/承认了(s’accuser)自身,但却不是通过栖息于自身之上,而是通过一种不安,一种将我逐出我的实体性之内核的不安。
b. 灵感与见证
然而,这一暴露,这一放逐,这一必须待在自身之内的禁令,难道不会倒转入一个位置,并且——就在痛苦本身之中——倒转为自满,一个充满实质与骄傲的自满吗?这一倒转表示着那无法被吸收到主体的被动性之中的主动性的残余。这一残余是自我的最终的实体性,那甚至一直延伸到感受性的易于受伤性之中的实体性。与此同时,或与此相继,这一倒转又义之两可地表示着接近所具有的无限路径。这一路径并非只是一条与邻人逐渐接近的渐进线。超出Sollen(应该)所具有的那种坏的无限,这一路径无限地增长着:一个活的无限,一个随着服从的增加而愈益严格的责任,而那需要穿越的距离则随着接近的愈益变近而愈益不可穿越。直到给予在此将自身表现为悭吝,暴露表现为有所保留,神圣表现为有罪。【这是】没有死亡的生命,或大写的无限,或无限之荣耀所具有的生命,那在是其所是与不是/虚无之外的生命。
因此,为了让作为主体之主体无保留地表示,它向着他者的暴露所具有的那种被动性必须不能立即就被逆转为主动性。这一被动性必须还要接着暴露自身:必须有某种被动性的被动性,必须有——在无限所具有的荣耀之中——这样一种灰烬,一种不会有任何行动重新诞生于其中的灰烬。*作者这里可能影射火凤凰从灰烬中重新诞生的神话,并将他所说的灰烬与之隐含地对立起来。说就是这一被动性的被动性以及这一奉献于他者,这一诚。不是所说——那立即就会把说重新覆盖起来、熄灭下去或吸收进去的所说——之交流,而是将其开放保持为开放的说,不带辩白、没有躲避、也没有托辞的说,交出自身而却并无任何所说之说。这是只说自身之说*“Dire disant le dire meme.”如果不是为了阅读的方便,我会依古汉语风格而将此语译为“说说之说”。作者这里要求我们去想象和思考的正是那说而无所说之说。,但此说却并未将自身话题化,却反而又暴露自身。说因而就是去将暴露这一表示活动本身做成符号:说就是去暴露暴露,而不是将自身作为一个暴露活动而保持在这一暴露之中;说是在暴露自身之中耗尽自身,是通过将自身做成符号而做出符号来,但却又不让自身休息在其作为符号的形象之中。这是被围困的引渡所具有的被动性。在此之中,这一引渡本身——在其确立自身之前*亦即,将自身确立为引渡。这一确立要求着或蕴含着一个确立者,亦即,一个引渡者。如果是这样,我之被引渡给他者就会成为我自己的主动行为。——就被交给了他者。这是在此说本身之说中【发生】的前自反性的反复申说*反复申说或重复意味着回到自身之上。,是“在这儿呢,我”之被说出。此话语不与任何东西同一,而只与那说出自身和交出自身的声音同一,与那进行着表示的声音同一。但虽然是如此地去做出符号,以至于竟然将自身做成了符号,这却并不是一个结结巴巴的语言,就像哑巴的表达那样,或像被囚禁在母语里的外国人的话语那样。此乃语言的极端紧张,此乃切近的那一“为了他者”。切近则是这样的切近,它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甚至于在我的自我同一性中都与我有关。而逻各斯——自语的或对话的逻各斯——则将会已然通过下述方式而松弛了切近的潜能。这些方式就是:将此潜能分散为是【所具有】的诸种可能,以及游戏于意识—无意识、明确—隐含这些对立之间。*那进行话题化的逻各斯,那在自语、对话和信息交换之中说出某一所说的说,以及其所承载的全部文化和历史负荷,皆起源于此前本源之说。之所以前本源是因为,此说早于一切文明,早于【人们的】有所表示的言语之中的一切开始。诚之开启使一切交流和一切话题化将在其中流动的那一层面成为可能。做出符号,以及切近作为进行表示的活动而留下的痕迹,并不会因此而被抹除,而且会在一切语言使用中留下标记。——原注作为被给予了他者的符号,而且已然就是这一给予符号行为本身的符号,亦即,纯粹的表示,切近并不是与他人混为一体。此种混为一体将会是以某种方式休息于化身之中。切近是无间断的表示,是为了他者而不安:一个为了他者而做的回应,不带任何“采取态度”(prise d’attitude)的回应,像“细胞回应刺激”(irritabilite cellulaire,细胞应激性)一样的(回)应承(担),或沉默之不可能,或诚【所激起】之轰动(scandale de la sincerite)。*但另一方面,要在一个语言被客观地言说的世界中,一个我已经与第三者同在的世界中“做出符号”,就必须打穿意义——那被说出来的意义(sens dit)——之墙,从而回到那尚未及于文明之处。因而就有必要以否定前说之说将所有前来损坏符号之裸体的东西去除,把切近所特有的纯说之中的一切被说出来的东西都放到一边。人们不可能毫无暧昧地在黑夜里做出符号。在只说说之前,在做出符号之前,在将自身做成符号之前,人们总得先说点“关于什么”的东西,总得先说点什么东西。——原注
诚并不是说【所具有】的一个特征,反而正是说实现了诚。诚与给予密不可分,因为诚打开了储备*说或诚并不是夸张性的给予。不然的话,给予所见证的无限就只能通过推论来获得了。但这一推论却已经蕴含了无限。——原注,而那进行给予之手即由此取出给予之物,而却没有将任何东西【向他者】隐藏起来的可能:诚,拆解了说在所说之中所经历之异化的诚。在所说之中,在词语的遮盖之下,在字句的无动于衷之中,信息被交流了,心愿被表达了,但应承则被逃避了。没有任何所说与说【所具有】之诚相等,没有任何所说与那先于真者(le Vrai)之真(veracite)相当。此真是接近所具有之真,切近所具有之真,它超出现在。诚因而应该就是无所说之说,是表面上看起来的“为了不说什么而说”,是我做给他人的一个符号,一个有关符号之给予的符号,“就像‘你好’那么简单”,但事实上却是纯粹透明的招认(pure transparence de l’aveu),是对于所欠之债的承认。这一作为对所欠之债的招认的说,难道不正是那先于所有其他形式之说的说吗?作为表示着这一给予本身的符号之给予,跟人打招呼难道不正是这一对于所欠之债的承认吗?诚,表示在其中进行着表示的诚,此一者在其中被毫无保留地暴露给他者的诚,此一者在其中接近彼一者的诚,并不在呼唤(invocation)中穷尽自身,并不在那被理解为纯粹呼唤的、毫无破费的跟人打招呼中穷尽自身。打招呼【这一行为】指示出某个意义,但对于切近所具有的意义和诚——在切近中表示着的诚——所具有的意义来说,这并不是足够的。作为自我的终极实体性的裂变,诚不可能被还原为任何具体的是其所是者层面上的东西,也不可能被还原为任何是之为是论层面上的东西。诚并且就好像是在走向那超出了或者尚未及于一切确定之物(le tout positif)和一切立场(position)之处。诚不是行为,不是活动,也不是随便哪种文化姿态,因为文化姿态以己之被绝对打破为前提。*当语言只被当做一个符号系统时,说并不能被解释为诚。人们总是只从某个已经被说着的语言开始而进入那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而这个被说着的语言并不能还是又由符号系统所构成。各种表示皆在其中被话题化的那一符号系统已然来自于那作为此一者而为彼一者的表示,来自于接近,来自于诚。——原注
c. 诚与无限之荣耀
诚的意义难道不正是在指涉着无限——那就像召唤着说一样地召唤着诚的无限——所具有之荣耀吗?这一荣耀不能出现,因为出现和现在/在场会通过将其限定为一个话题,并通过为其在再现所具有的现在之中指定一个开端,而违背它。作为无限之无限化,这一荣耀来自于过去,一个比那在记忆所及范围之内的、在现在上面排成一线者更加遥远的过去。这一荣耀来自于一个从未被再现过的过去,一个从未呈现过自身的过去,一个即因为如此而不让开端萌生出来的过去。荣耀不可能变成现象而却又并不进入一个与主体——荣耀向之出现的那一主体——的结合,也不可能变成现象而却又并不将自身囚禁在有限和内在之中。作为没有原则、没有开始者,作为无端,荣耀,那使话题炸裂的荣耀,在那尚未及于逻各斯之处表示着主体——休息于自身之上的主体——的引渡,一个将主体引渡到它从未担当起来者那里的引渡。因为,那从不可被再现的过去开始的主体已然敏感于一个刺激,一个从未呈现出自身、但却已然【对主体】进行了震创性打击的刺激。荣耀只是主体所具有的被动性的另一面。在此之中,作为以己代人的主体,作为被命令去做出的那对于最先到来者的应承,作为对于邻人的应承,作为被他者之灵所感者,我——作为同者——被从我在自己之内的那一开始之处撕开,被从我与自身的那一等同那里撕开。无限所具有的荣耀就在这一应承中荣耀着。它不给主体留下任何在其秘密中的避难之处,因为这一秘密会防止主体为他者所萦怀,并且掩盖主体的逃避。荣耀由于主体之出离其阴暗角落“矜持”(quantsoi)而荣耀着。就像是天堂中的灌木丛林,亚当一听到从日出之处传遍整个伊甸园的永恒上帝之声就藏身于其中那样,这些阴暗角落提供了一个摆脱【对主体的】传唤之处。而正是在传唤之中,那位于开始之处的自我所具有的位置,以及起源的可能性本身,被震撼了。无限所具有之荣耀就是那被撵出藏身之地而无处逃避的主体所具有的无端的同一性。这一荣耀就是被引向了诚的自我。这一自我为他者——我要为之做出应承的他者,我要在其面前做出应承的他者——做出符号,那正好就表示着符号之给予的符号。这也就是说,那表示着应承的符号:“在这儿呢,我。”此乃一切所说之前的说,那见证着荣耀的说。这一见证是真实的,但这一真实不能被还原为揭示所具有的那种真实,而且这一见证也并不叙述任何一个显示自身者。这是在那对命令着的荣耀的纯粹服从之中的说,没有任何意向对象之关联的说,是在那从一开始就隶属于“在这儿呢,我”的被动性之中的说,没有任何对话的说。这个随着切近之收紧自身而不断增加的距离——无限所具有之荣耀——就是同者与异者之间的不相等同,就是差异。但这一差异也是同者对于异者的并非无动于衷以及替代。而此替代本身也是一种不与自身相等同,是自身之不被自身所覆盖,是自身之剥夺,是自身之从其认同这一秘密状态中出离,是做给他者的符号,是【表示着】符号之此一给予的符号。而这也就是说,是表示着此一并非无动于衷的符号,表示着此一不可能逃避和不可能被替换下来的符号,表示着此一同一性的符号,此一独一无二性的符号:在这儿呢,我。*作为【表示着】符号之此一表示的符号,一个被给予了【他人】的符号,切近也描绘出了抒情诗的形象性说法:通过将爱告诉所爱者来爱——爱的歌唱,诗的可能性,艺术的可能性。——原注那被在【自我】认同的后面刺激起来的同一性是由于纯粹的挑选而来的同一性。挑选穿过自我这一概念,以便通过他人所具有的那种超乎尺度性而将我传唤到我之上,从而将我撕离于概念,我不停地躲藏于其中的概念,而躲藏于其中是因为我在其中找到了一个未在挑选中被规定的责任的尺度。责任召唤着独一无二的回应,那并未被铭刻在普遍思想之中的回应,被挑选者的无法预料的回应。
这是前起源的、无端的同一性,比所有开端都更加久远。它不是在现在之中到达自身的自我意识,而是向着他人所发之传唤的极度暴露,而此一传唤已经在意识和自由的背后被遵行了。这一传唤是以穿墙撬锁的方式进入我之内的,亦即,这一传唤并不“现出自身”(enparaitre),并且是在被传唤者之说中说话的。我始终已然暴露于那传唤着我之应承的传唤,就像是被置于烈日之下而无荫可庇。在这一烈日之下,那一切秘密的残余,那一切使逃避成为可能的隐含动机的残余,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就在震创产生之处的毫无保留的暴露,那伸给已然打出之手的脸颊,就是作为说之诚,亦即,无限所具有之荣耀的见证。这一荣耀粉碎巨格斯(Gyges)的秘密,粉碎那个去看而却不被看见也不被暴露的主体之秘密,粉碎那个在【自身】内部的主体的秘密。*巨格斯是柏拉图《国家篇》第二卷(359d-360b)中讲到的吕底亚牧人。他无意中得到了一个让他能够隐而不为他人所见而同时又能看见他人的戒指。确认这一戒指有此作用之后,他就装成使者去见国王,勾引了王后,与她合谋杀了国王,霸占了整个王国。希罗多德在其《历史》第一卷第八章中也讲述了这个故事,但与柏拉图讲得有所不同。
d. 见证与语言
主体之为主体,被奉献在另一者的位置之上的主体,从一开始就是替代(并非牺牲者之将自身放在另一者的位置之上,因为这会蕴含着那在作为替代的主体后面的主体性意志所拥有的一个保留区域),但主体先于自由与非自由之别:主体乃(并)非(一处之)处,在此为他者之灵所感也是为他者而补(偿)赎(罪),主体是意识本身会由此而前来进行表示的心灵。心灵并不是来被嫁接到一个实体之上,而是来以一个改变而使这一实体改变。在此改变之中,同一性就被凸显/控诉出来了。替代并不是同情或交感(intropathie)这样的一般心理事件,而是那使设身处地(se-mettre--la-place-d’un-autre)这一悖论性的心理可能性成为可能者。主体(sujet)之主体性,作为那以一切为主之体(être-sujet--tout),乃是前起源的易受感染性,它先于一切自由,并外于一切现在。在宾格(accusatif)的不舒服或无条件之中,在“在这儿呢,我”——作为对于无限所具有之荣耀的服从,对于那将我命令给邻人的荣耀之服从——【这一回应】之中,主体的主体性被凸显/控诉出来(accusee)了。*“在这儿呢我,请差遣我吧。”《以赛亚书》6:8。“在这儿呢我”表示着“请差遣我吧。”——原注(译案:汉译《圣经》此节全文为:“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所有人面前,对于所有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而我尤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卓夫兄弟》中这样写道。*第六卷,II a。——原注主体之主体性,作为被迫害者(persecution)和受折磨者的主体之主体性:此乃反复发生,但此反复发生并非“对于自身之意识”,因为在自我意识中主体将仍然会在一个并非无动于衷之中与自身保持某种距离,将仍然会以某种方式待在自身之中,并且能够盖住自己的脸。这一反复发生并非与自身相重合,亦即,休息,睡眠,或物质性。这是在那尚未及于己本身之处的反复发生,是在那尚未及于对己无动于衷之处的反复发生。这一反复发生正就是对于他人的替代,并且正就是间隙之中的此一者,它没有任何特征,甚至连“此一者之统一”也没有作为一个基本特征而使之【自我】叠合起来的。这是被免除了一切关系、一切游戏的此一者,确确实实地没有任何所处之境,没有任何所居之地,从各方各处也从己本身之中被逐出,对他者说“我”(je)或说“在这儿呢,我”(me voici)。*所以这正是在那尚未及于物化之处的主体性。那些任由我们支配之物栖息在对自身无动于衷的种种物质之中。而那先于此种无动于衷的主体性则是【受】迫害【情况】所具有的被动性。——原注那被迫害【所造成】的震创剥夺了其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的主体性的自我,在没有任何混浊之处的透明之中,在没有任何晦暗地带——有利于逃避的地带——的透明之中,被送回到“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我”是无限之见证,但此见证并不将其所见证者话题化,而这一见证所具有的真实性也并不是再现所具有的真实性,而且也不是证据【的真实性】。【这里】有的只是对于无限的见证,其结构独一无二,例外于是之法则,而且也还原不到再现之上。无限并不向着那见证它的见证者出现。相反,这是属于无限所具有之荣耀的见证。而正是通过见证者之声,无限所具有之荣耀才荣耀着自身。
任何话题——任何现在——对无限都无能为力。而主体就见证着这一无限。在主体之中,同者是为了异者的,所以异者即在同者之中;在主体之中,切近所具有的【同者与异者之间的】差异就随着切近之变得越来越近而被吸收,同时也就正由于这一“吸收”本身而被荣耀地凸显出来,而且这一切近之差异也总是把我更多地凸显/控诉出来;在主体之中,携带着自身之同的同者被越来越多地伸向异者,直至替代,那作为人质的替代,直至补(偿)赎(罪),那最终乃是与同者——在为灵所感之中,在心灵之中——之向着异者的非同寻常的、非同时性的翻转相重合的补(偿)赎(罪)。
在笛卡尔那里,那关于无限的观念居于一个容纳不下这一观念的思想之中。这样一种关于无限的观念表达了荣耀与现在的不成比例,而此不成比例正是【为】灵【所】感【这一情况】本身。处在那超出了我之能力的重压之下,作为那比所有与主动行为相对应的被动性都更加被动的被动性,我的被动性在说中爆发。外在的无限以某种方式变成了在见证【所具有】之诚中的内。荣耀既不作为再现而来影响我,也不作为我将自己置于其前的一个非人的或人性的交谈者而影响我。荣耀在我之说中荣耀着自身,并通过我之口而指挥我。内并不是在我里面的某个秘密之处;内正是这一翻转本身,在此翻转之中,作为无限,那卓越的外,即以它的这一卓越的外在性,以及它的这一不可能被“容纳”和不可能进入话题,而形成了相对于是其所是的例外,并牵涉着我,包围着我,而且还以我自己的声音命令着我。这一命令是由那被命令者的口中发出的。那无限的外变成了“内在的”声音,但这声音却又是见证着内在秘密之裂变的声音,为他人做出符号——表示着符号之给予本身的符号——的声音。曲折之路!克劳戴尔(Claudel)选择了一句葡萄牙谚语作为其《缎鞋》(LeSoulierdeSatin)之题辞。*保尔·克劳戴尔(Paul Claudel, 1868-1955),法国诗人,戏剧家,外交官。曾于1895—1909年间先后在上海、福州和天津担任法国外交官。1895年他从中国写信给法国诗人马拉美说:“中国是一个古老国家,错综复杂,令人目眩。这里的生活还没有遭到精神上的现代病的感染……我厌恶现代文明,而且对它总感到十分陌生。相反,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很自然、正常。”克劳戴尔在文学创作上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Arthur Rimbaud)影响。《缎鞋》(Le Soulier de Satin),其最著名诗剧之一,是以西班牙帝国为背景而展开的对于人性和神性之爱与渴望的深刻探索。这一谚语也正可以在我们以上阐述的意义上来理解:“上帝以弯曲的线条笔直地书写。”
见证,这一让命令在那服从命令者本身之口中响起的方式,这一让命令在一切出现之前、在一切“呈现于主体之前”之前就“揭示自身”的方式,并不是一个“心理奇迹”,而是那无端的无限传达其命令的方式。这并不是巧妙地借助人之传言来揭示自身,并借助人之颂歌来荣耀自身,而是无限在其荣耀之中越过有限的那一方式,或是无限越过自身的那一方式,这样无限就以此一者而为彼一者所具有的那一表示而并不进入话题之是(l’être du theme)中,却表示着【自身】,并且就因此而将自身从虚无中排除出来。见证的无所说之说根据一个不同的情节而进行着表示。这一情节有别于那将自身展开于话题之中的情节,也有别于将意向活动连到意向对象之上、将原因连到结果之上、将可以忆及的过去连到现在之上的情节。这一情节连接于那将自身绝对地分离于其他者,连接于那绝对者。无限之从那寻求将其话题化的思想的分离,从那试图将其保持在所说之中的语言的分离,就是我们称之为他性(illeite)者。*这是列维纳斯自己创造的词:“illeite”由法语代词“il”——他——及拉丁语代词“ille”——他——而来,指被以第三人称——“他/她/它”——称之者的第三人称性,而非指任何特定的第三者或他者。或可译为“第三者性”,或“他之为他”。人们会试图称此情节为宗教的。这一情节并非是以确定性或不确定性这些字眼说出来的,而且也并不栖息在任何肯定神学之上。*肯定神学(theologie positive)与否定神学(theologie negative)相对。前者认为可以正面说出神是什么,后者则认为我们只能说神不是什么。此亦可借佛教说法译为“表诠神学”与“遮诠神学”。
无限在说之中越过自身/发生。而正是在这里,无限让我们将说理解为不可还原为行为或心理态度者,或某种灵魂状态者,或诸思想中之某一思想者,或是之是其所是【这一活动】的一个环节,而人即由此而以不为人所理解的方式使是之是其所是叠合到自身之上。就其本身而言,说就是见证,无论说如何通过语词系统中的所说而进入怎样的后来命运之中。这一系统得自于说,而说却并不是这一系统的口齿不清的童年,也不是说在其中起作用的信息交流的口齿不清的童年。*这里的“说”指的是无所说之说,先于任何所说之说,所以列维纳斯强调此说并非儿童的那种还没有学会清楚地说话、清楚地表达意思并与人交流信息的牙牙学语。当然,人们确实可以表明这一新命运是如何被铭刻在见证之中的。*参见本章第199页(页边码)及其下。——原注但无所说之说,被给予了他人的符号,主体——无限即由之经过/发生——在其中出离于主体之秘密状态的见证,并不是作为信息或表达或反射或症状而被加到某一莫名其妙的有关无限或有关其荣耀的经验之上的。若是这样的话,那就会像是既可以有对于无限的经验,也有不同于荣耀化——亦即,对于邻人的应承——之物。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保持在主体—对象、表示者—被表示者(signifiant-signifie)、说—所说这些对应关系的结构之中的。作为一个被给予了他者的符号,说是诚或真,而荣耀即以此而荣耀着自身。因此,除非通过作为主体的主体,通过【我之】去接近他者这一人性的冒险,通过对他者的替代,通过为他者补【偿】赎【罪】,无限并没有任何荣耀。主体乃是为无限之灵所感的主体,而无限,作为他性(illeite,他之为他),则并不出现,也不成为现在。无限始终已然过去,而且不是话题,不是目的,不是对谈者。无限在荣耀——使主体显现的荣耀——之中荣耀着自身,为的是让无限已然能在由主体实现的无限之荣耀的荣耀化中荣耀着自身。这样一来,一切对应关系结构就都被挫败了。荣耀之实现(glorification,荣耀化)就是说,亦即,就是给予了他者的符号,就是向他者宣布的和平,就是对于他者的应承,那一直达到了替代的应承。*《圣经·以赛亚书》57:19:“这产生话语——口唇之果——者:‘和平,和平,’他说,‘为了更远者也为了更近者的和平。’”——原注(译案:此依列维纳斯法语引文直译。汉译《圣经》此处为:“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与远处的人,也归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
无限越过有限及其越过自身(se passer)*动词“se passe”的词典义是“发生”,但其为列维纳斯所强调的字面意义是“经过/越过自身”。英译本中即将“se passe”译为“passes itself”。列维纳斯此处的排比性措词——越过有限,越过自身——恰表明无限之发生即其越过自身,而其越过自身亦即其发生。无限之为无限即在于,其乃始终越过自身者。的那种方式之有某种伦理意义,并非源于某种为了“伦理经验”而建构“超越基础”的计划。伦理(l’ethique)是这样一个悖论所勾勒出来的领域。一个这样的无限所具有的悖论:它处在与有限的关系之中,但却并没有在这一关系之中停止为无限。*从逻辑上说,如果无限处在与有限的关系之中,这一关系就会限制无限,而无限即不是或不再是无限了。列维纳斯则要求我们想象一个虽与有限相连而却不为有限所限的无限。是为悖论。伦理是先验统觉的原始统一之打破,亦即,是超出经验者。那被见证——而不是被话题化——在做给他人的符号之中的无限所进行的表示从对于他人的应承开始,从为了他者开始,从支撑着一切的主体——那以一切为主之体——开始。作为这样的主体就是为所有的人去忍受痛苦,而且被委以全责却又不必决定是否要去负此全责*“不必决定”这里意味着,没有决定的必要或余地,只能如此而非其他。,一愈加需要负起即愈加荣耀地扩大之责。这是在命令的任何被听到之前的服从。能够在服从本身中不合时间顺序地发现命令,能够从己本身接受命令——这样的可能性,这样的他主他律之翻转为自主自律,就正是无限越过自身/发生的方式。而法律在意识之中的铭刻这一比喻——一个调和了自主自律与他主他律的比喻——则以非常可观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这一比喻是通过一种双重性来调和的:此双重性的不同时性就是表示本身,而此双重性(ambivalence)本身——在现在之中——则是一个义之两可/暧昧(ambiguïte))。命令在服从所具有的那一为他者之中被铭刻乃是一种无端地受到影响。此一影响“像贼一样”穿过绷紧的意识之网溜到我里面。这是使我绝对吃惊的震创。此一命令从未被再现过,因为它从未呈现过自身,即使在那来到记忆之中的过去里面也从未呈现过自身,以至于此一情况竟然会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亦即,是我自己,完全只是我自己,说出了——而且是在事后——这一闻所未闻之责。这是作为例外的双重性,而主体之主体性,其心灵本身,则是为灵所感的可能性。亦即,这样一种可能性:能够是那在我之不知不觉中被吹入我之内者的作者,能够已经接受那我虽是其作者但我却不知其从何而来者。在对于他者的应承之中,我们正就处于【为】灵【所】感这一义之两可/暧昧的核心。那闻所未闻之说就像谜一样地就在无端的回应之中,就在我对他者的应承之中。无限【所留下】的痕迹就是主体之中的这一时而是开始时而是媒介的义之两可/暧昧,而这一义之两可则是伦理使之成为可能的一种不同时的双重性。
e. 见证与先知性预言
我们可以将此翻转称为先知式预言(prophetisme)。*之所以将“prophetisme”译为“先知式预言”,是为了表明此类预言完全不同于基于已有信息而做出的对于未来的预测或预报(prediction)。在此翻转之中,对命令的领会与这一命令——一个由服从这一命令者所给出的命令——所表示者相重合。先知性预言因而就正是灵魂所拥有之心灵本身,亦即同(者)中之异(者),而人的全部精神性因而就是先知式预言。无限并不是在作为话题【而给出】的见证中被宣布的。通过被做成一个给予他者的符号,我发现自己在无所说之说所具有的诚之中,在我的“在这儿呢,我”之中,被撕离于巨格斯(Gyges)的秘密,被“揪着头发”*《圣经·以西结书》8:3.——原注(译案:汉译《圣经》此节全文为:“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异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的偶像的坐位,就是惹动忌邪的。”)从我之晦暗的深处拉出,而且从一开始就处在宾格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被给予了他人的符号之中,我见证着无限。无限并不在其见证的面前,却似乎处于现在之外或处于其“背面”,并且是已然过去了的,是不可取得的,是一个高高在上到不会将自己推向前排的思后之思。*这里“思后之思”或“思想后面的思想”是“arriere-pensee”在此语境中之试译。此组合词在《法汉词典》中只被解释为“不可告人的想法”、“内心的想法”,“私下的盘算”,但这些并不符合这里的语境。英译本此处即译为“a thought behind thoughts”。“在这儿呢我,凭上帝之名,”但【这一回应】却并不把我直接指向他的现在/在场。只是一个“在这儿呢,我”而已!当上帝在这一语句中被首次卷入词语之时,“上帝”这个词还并不在这一语句之中。*在《圣经》的语境里,“在这儿呢,我”是对上帝的回应。这一回应蕴含了那被回应者——上帝,但却没有说出上帝之名。这一语句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说出“我信仰上帝”。去见证上帝恰恰并不是去说出这个非同寻常的词。若是这样,那就好像【上帝的】荣耀是可以栖身于一个话题之中并被作为论题而提出,或可以变成是之去是其所是一样。作为被给予了他者的符号,一个【表示着下述】这一表示本身的符号,“在这儿呢,我”表示着那以上帝的名义而为看着我的人们服务的我*参见《圣经·撒母耳记》17:45:“我以永恒者之名来此。”《以赛亚书》6:8:“在这儿呢我,请差遣我吧。”——原注(译案:汉译《圣经·撒母耳记》此节全文为:“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主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一个除了我的音之声或我的姿之形——亦即,说本身——就再没有任何东西让我去与之认同的我。这一反复发生与回到自己完全相反,与对于自己的意识完全相反。这一反复发生是诚,是己之溢出自身,是己之被“引渡”到邻近之人。见证乃是人性与招供;它是在一切神学之前就做出的;它是福音(kerygme)与祈祷;它是荣耀化与认出/承认(reconnaissance)。所有这些如此展开着的关系——而对于那去把是加以话题化的与真实为友者们而言,以及对于那在是面前抹去自身的主体而言,这又将是多么大的欺骗啊!——所特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亦即,返回乃是在走去之中被勾勒的,呼唤乃是在回应之中被理解的,来自上帝的“鼓动激励”(provocation)就在我的启灵求助(invocation)之中,而感激则已然是对于这样一种感激——那【本身】同时是或轮流是礼物与感激的感激——状态的感激。启示所具有的超越性就存在于“圣显”之在那迎受圣显者的说中到来这一事实里面。那命令我的命令并不给我留下不受惩罚地让正面重新朝上的任何可能,也并不给我们留下从无限之外重新返回的任何可能,就像我们面对一个话题时所能做的那样,亦即,从所表示者回溯表示者,或像我们在一个对话中所能做的那样,亦即,重新在“你”中发现一个是其所是者。正是在先知性预言之中,无限才逃脱了话题化以及对话【所导致】的对象化,并且作为他性而以第三人称进行着表示。但这一“第三”不同于第三个人的那一“第三”,不同于那打断了对另一个人的面对面欢迎的第三者,一个打断了切近或邻人之接近的第三者,而公正即因此第三者而开始。*参见本书第199页以下。——原注
无限将作为脸的“邻人”命令给我,但却并不将自身暴露给我。其命令则随着切近之收紧自身而愈益紧迫。这一命令并不是造成我之回应的原因,甚至也并不是对话中那先于回应的提问。这是我在自己的回应本身之中发现的命令,而我之回应,作为被做给了邻人的符号,作为“在这儿呢,我”,则使我从那不可见状态中出来,从那让我可以躲避自己【所做】之应承的阴影中出来。这一【作为回应的】说属于其所见证的荣耀本身。命令的此种“我不知其自何处”而来,此一并非忆及【往事】(souvenir)的来(venir)*汉语翻译此处无法传达“souvenir”——忆及,回忆——与“venir”——来——之间的意义联系。法语动词“souvenir”源于拉丁语“subvenīre”。后者可拆解为前缀“sub-”(之下,底下)与词根“venire”(来):“来到……之下/底下”即“前来帮助……”,引申为“救出,挽救,保持,维持”等。回忆的作用即是告诉或提醒我们自己某事某物之自何而来,从而挽救并保住一已然逝去者。但无限对我的命令却是一来而我却不知其自何来的命令:我无法通过回忆而忆及其来源。,并非作为一个被改变为——或衰老为——过去之现在的返回的来,以及命令——它超出再现而在我之不知不觉中影响我,“像贼一样溜进我里面”*《圣经·约伯记》4:12.——原注(译案:此处正文中列维纳斯所引法译《圣经·约伯记》之语是根据法文直译的。汉译《圣经》本节为:“我暗暗地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二者有出入。)——的此种非现象状态,我们已将之称为他性。*参见《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一起发现存在》(En decouvrantl’existence avec Husserl et Heidegger)第二版,第201页。——原注此乃这样一个命令之到来:我在听到这一命令之前就已经在服从着它,或者,我在自己的说中听到了/理解着它。此乃令人敬畏的命令,但它却既不约束也不统治,并且将我留在任何一种与命令来源的对应关系之外。任何与对应物的“结构”【关系】都没有被建立,因此那来到我这里的说恰恰就只是我自己的话。权威并不在某一寻视可以去把它作为一个偶像找到或把它作为逻各斯担当起来的地方。*不可被追忆回来的过去是思想所不能忍受的。因此就有了停止(arret)这样一个迫切要求:anankestenai(译案:拉丁语,必要的停止。在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中,我们将一物的原因向回追至另一物。如果没有必要的停止,这一过程将无穷无尽,而认识就不可能完成。在经典的西方哲学和神学中,这一必要的停止停止在第一推动者或上帝之上)。这样,那向着超出了是之处的运动就变成了是之为是论和神学。对于美的偶像崇拜也由此而来。在其【对于世界的】冒昧鲁莽的展示之中,在其【所创造的】雕像的停止不动(arret)之中,在其【形式的】可塑性之中,艺术作品以自身代替了上帝。(参阅我们发表于1948年11月号的Temps modernes上的论文《La realite et son ombre》(实在及其阴影))由于对真相的某种不可抗拒的隐瞒,那不可比较者,不在同一时间者(le dia-chronique),不同时代者(le non-contemporain),就被艺术通过一种欺骗性的、不可思议的图示主义(schematisme)所起的作用而“模仿”了。这样的艺术乃是肖像学。那向着超出了是之处的运动被固定在美之中。神学与艺术“保留”那不可被追忆回来的过去。——原注权威不仅在所有直观之外,而且也在所有话题化之外,甚至也在象征表示(symbolisme)之外。它是铭刻在我里面的“飘忽不定的原因”【所留下】的纯粹痕迹。
对于记忆所拥有的那可被恢复的时间而言,作为在听到命令之前的服从,【为】灵【所】感或先知式预言的不合时间顺序比神谕对未来的预告更具有悖论性。“在他们召唤之前,我就会回应”*《圣经·以赛亚书》65:24.——原注(译案:汉译《圣经》此节全文为:“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一表述应该照其字面来理解。在去接近他人之时,我始终都是晚于“约会”时间而到的。但这一对于要我前去之命令的有独无偶的服从,一个并无对此命令之理解的服从,这一早于再现的服从*亦即,早于对命令的任何再现。一般来说,我需要把听到的命令向我自己再现出来,从而我可以“看到”它,理解它。,这一在所有誓言之前的忠诚,这一发生于诺约之前的应承,就正是异【者】之在同【者】之中,正是【为】灵【所】感或先知式预言,正是无限之越过自身/发生。
无限之荣耀只通过作为表示——作为诚——的此一者而为彼一者而荣耀自身;在我之诚中,无限越过有限;在我之诚中,无限越过自身/发生:这些就是那使伦理这一情节成为首要者,这些就是使语言成为不可被还原为诸种行为中之一种行为者。在使自身作为通过一个语言系统的信息交流而服务于生活者之前,说是见证,是无所说之说,是被给予了他人的符号。那么,又是表示什么的符号呢?是表示同谋关系的符号吗?是表示一个并不为了什么的同谋关系的符号,是表示兄弟关系的符号,是表示切近的符号。只有作为己之敞开,作为向着他者的毫不谨慎的暴露,作为毫无保留的、一直达到了替代的被动性,此一切近才有可能。正因为如此,这才是暴露的暴露,才是说,是不说一语的说,是表示着什么的说,是——作为应承——表示本身,是此一者而为彼一者,是把自身变成了符号的主体之主体性。但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符号只当做是说话的结结巴巴,那就错了,因为它见证着无限之荣耀。
这一见证不能被还原为一个从指示者到被指示者的关系。这样见证就会变成见证之被揭示以及被话题化。见证是应承所具有的无底的被动性,并因此而是诚,是语言的意义,是在语言分散为字词之前、分散为与字词相等的话题之前的语言所具有的意义。话题在所说之中掩盖着说所具有的那像流血的伤口一样的开放性,但即使在其所说之中,见证的痕迹,诚的痕迹或荣耀的痕迹,也并没有被抹去。
我当然可以把被见证了的意义作为一个所说而陈述出来。但这一所说乃一非同寻常之言,唯一的并不把那说出它的说熄灭下去或吸收进去的言,但此言也不能始终停留为简单之言。作为一个惊心动魄的语义事件,上帝这个言词抑制住了他性(Illeite)所造成的颠覆。这样一来,无限所具有之荣耀就将自身关进了一个言词里,并变成了一是。但它又已然在拆解着它的居所并且推翻了所说,而却并未因此而消散为虚无。它向那个让它由此而接受着(而就在此刻,当这一语义冒险在这里被我们话题化之时,它就在接受着)种种属性的系词里投放是。惟其在自身之类型中独一无二*亦即,如果它属于某一类型,那么它是此类型中的唯一者,而这也就是说,它其实并不属于任何类型,或者说,它本身就构成一个不再有任何同类型者的“类型”。,此一所说并不像言词(它既非专有名词,亦非普通名词)那样紧密地结合诸种语法范畴,也不像意义(它乃是被排除于是与不是/无之外的第三者)那样把自身严格地折叠到诸种逻辑规则之中。此一所说从其所见证者获得意义,但话题化活动——通过神学,通过将此一见证的意义引入语言系统之中,引入所说所拥有的秩序之中——又确实会出卖此一见证的意义。但这一过分(abusif)陈述立即就禁止了自身或被禁止了。现在所具有的诸种界限——无限就在其中背叛出卖自身——被打破了,【因为】无限超出了先验统觉之统一的范围,也不可能被组合到现在之中,而且还拒绝被回想。【无限】对于现在和再现的这一否定(negation)在切近、应承和替代所具有的“肯定性”(positivite)中发现了自身与否定/遮诠(negative)神学的诸种命题的不同。对现在/在场的拒绝被转变为我之现在/在场,一个作为现在的我之现在/在场,这也就是说,一个作为礼物而被交给了他者的人质之我的现在/在场。在切近之中,在表示之中,在我之给予【他人以】符号之中,无限已经就通过我对无限的见证而说话了:它在我之诚中说着,在我的无所说之说中说着,在我的先于源头的说中说着。而这一先于源头之说恰恰就是在那接受见证者之口中说出来的。它的表示之让自身被出卖在逻各斯之中只是为了要把自身传到我们面前。此一表示是一个已经在祈祷或亵渎中作为宣教而说出的言词,因而在其陈说之中保存着超越(trancendance)——保存着那超出……之处(au-del)——所具有的那一过度过分所留下的痕迹。
话题化因而是不可避免的,这样表示本身才能被显示出来,但显示乃是去在那哲学开始于其中的智辩(sophisme)之中显示,并在哲学被召唤前来将其还原的出卖之中显示。正因为这些【智辩和出卖的】语词本身所承载的诚之痕迹,这一还原才始终都必须被尝试,而这些语词所承载的诚之痕迹则要归功于作为见证之说。即使当所说在那被建立起来的说与所说的对应关系之中掩盖了说之时,上述情况也依然如此。这一掩盖乃是说始终皆欲将之推翻之说,而这正是说本身之真(veracite)。在那激活了语言之文化键盘的游戏里面,诚或见证通过每一所说皆有的那一义之两可表示着自身,而在所说的义之两可中,在那被传达给他人的信息之深处,那个【同时】也被给予了他人的符号,一个表示着将符号给予他人的符号,也在表示着自身。而这就是一切“凭上帝之名”的语言的震荡回响,是一切语言的【为】灵【所】感或先知式预言。
由于这些义之两可,先知式预言并非跛脚启示的权宜之计。这些义之两可属于无限所具有的荣耀。当然,先知式预言可以具有下述外表,亦即,在他人之间流行的诸种信息。它们源于主体或源于主体所经受的诸种影响,而这些影响首先就是那些自主体本身之生理或自其伤痛或自其成功而来之影响。至于先知式预言何以如此,则是一个谜,一个义之两可,但也是超越和无限【所进行】的统治活动(regime)。在有限愿意为之提供的有关其超越性的证据中,无限会被出卖,并会进入与那会使之现身的主体的结合之中。这样无限就会失去其荣耀。超越必须自己打断【对于】自身之证明。而一旦人们要听取来自超越的信息,超越就必须缄口不言。超越所抱有的大志必须让自身暴露于嘲弄和反驳,直至让人去怀疑在那为之作证的“在这儿呢,我”之中有着一个病态主体——但却正是一个应承于他者的主体!——的一声哭泣或一次口误。这是谜样的双重性(ambivalence)的哭泣或口误,而在此双重性之中则有着一种意义的轮流交替。在说出所说的说之中,有着被陈述出来的所说和是,但也有着见证,有着同者之为异者之灵所感,有着那超出了是其所是之处,有着所说本身之被某种修辞所漫溢,而此种修辞则不仅只是语言【所创造】的幻景,而且也是意义之多出,而意识仅凭自身则将会对此多出无能为力。这里也同时有着【形成】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和神圣谵妄的可能性:一个需要由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来包抄的意识形态;一个需要由哲学来还原的谵妄。而还原则是还原至表示,还原至此一者而为彼一者,还原至我为那在无限之荣耀中的他者所负之使命。而这也就是说,还原至超越,亦即,还原至那超出是其所是之处,而这一超出则同时亦为“是于世界之中”。*“是于世界之中”此处是“être-au-monde”翻译。引号是译者加的。采取这一译法是为了与本书对“être”的译法一致。这一来自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表述在其汉语译本中被译为“在世”。而为此就必须有某种义之两可:意义的某种闪烁不定,而这一意义则不仅只是侥幸的确定性,而且也是一道既不可抹去而又比理想线条的轨迹更加纤细的边界。超越需要那打破先验统觉之统一的不同时性。先验统觉之统一并未成功地把现代人类的时间组合起来,所以轮流地从先知式预言走向语文学,又超越语文学——超越语文学是因为无力否认人类的兄弟性——而走向先知预言性的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