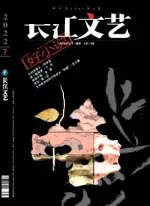止庵:生死命题让人珍惜平凡
2014-04-29范宁
止庵,随笔、传记作家,出版有《周作人传》、《樗下读庄》、《神奇的现实》等二十余种著作。做过医生,当过出版社副总编辑,如今是自由恬淡的笔耕者、读书人。
《庄子·德充符》中有云“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止庵之名便源于此。“‘止是时时告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庵是我想象中读书的所在之处——荒凉里那么一个小草棚子而已。”
止庵行文清淡如茶,无喧哗矫饰,落实细节处见其幽微,情感留白处恰当自然,耐人寻味,却不故作高深。
止庵是一个“藏”在书后面的人。
读书人总有一种气度,他们的生活节奏,有点像闲时读的那本书,书页轻轻翻开,一页一页,可能因为手指的游弋,也可能因为清风的嬉戏,或徐或疾,但不乱从容。
沉浸在书中的生命,就是如此静谧。书卷气缓缓地流泻,周遭的气场,有了阳春的温暖,也有了初秋的清爽。好几次采访止庵先生,电话居多,但仍可感觉到话筒彼端的神情动态:朗笑,因为书;沉吟,因为书;哪怕是倦怠或者困惑,还是因为书。
我觉得,止庵的气度,受到他所喜爱的那些作家的影响,尤其是周作人。周作人对生活艺术的细腻感知,通过不缓不急的文字娓娓道来,这是写作的魅力,也是阅读的快感。看看止庵的新书《惜别》,开篇如此: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生离死别”这句成语。汉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作》:“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乃以“死别”形容“生离”,然而这也只是形容而已,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我在父亲去世后写过下面这段话 :父亲去世给我的真实感觉并不是我送走了他,而是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他送我到一个地方——那也就是他在这世界上的最后时刻——然后他站住了,而我越走越远,渐渐看不见他了。
我的母亲也去世了。
这样的开头不乏信息量,也深具哲思。其实很符合止庵的身份特点。作为读书人,他的文字中也有一份从容雍雅;作为书评人,他的思想里又总有超越感性的理性;作为编著者,他为自己设立的格局,并不在意于一开始就抓住人们的眼球,而是期冀人们随他的节奏,进入他所描绘的思想场景,比如那个父亲与他在人生路上同行的场景,我读了很多次,回味了很多遍,一次次留下的只有感慨和唏嘘,无限。
文字终结处,阅读的节奏戛然而止,而阅读的兴奋却刹不住车,还在继续向前滑行,仿佛蜿蜒而不知所终的流水,逾越了作者所设立的岸线,一路碰撞跌宕,冲刷出属于自己的阅读轨迹——相信每个读书读到深处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作者叙述结束的时候,自己开始演绎后面的情节,于是有浮想,有顿悟,有感叹。
《惜别》这一回,止庵算是从书的后面,走到了前台,把所思所想、所念所恋,摊开了让人看。不过我试图讲述的,是许多止庵们的存在,带给我们的意义。这个意义可以很微小,那就是即便有越来越多的人没有时间或者放弃阅读,但读书带给人们的愉悦之感,并不会随着人数的减少而降低,阅读打开的想象世界,依旧缤纷灿烂;这个意义也可以很宏大,一个喜爱阅读善于沉思的民族和国家,会呈现出怎样的稳重和智慧面貌,足以令人憧憬吧?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惜别”?
一
《惜别》是止庵于母亲故世三年后沉淀而成的生死体悟,它是止庵最私密也最承载个人情感的一部作品。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止庵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母亲,尽孝左右。当年《周作人译文全集》的编辑工作延续逾十载,这期间,止庵也同时经历了母亲的晚年、患病、危重和离世。能够完整地陪伴至亲走完人生最后一段历程,也许是一件幸事,但毫无疑问,如同止庵在书中所写,这也是一种令“人生观甚至都为之动摇”的痛楚。
母亲的病故带给止庵极大的冲击,他形容此后的生活“有如生活在母亲的废墟之上”。因此,在《周作人译文全集》编辑工作结束之后,止庵转而沉入了另外一种阅读与思考的状态。他开始大量地整理和重读许多论及生死的书籍,不限古今,跨越时间和国界之别。就在这时,他也收到了定居美国的姐姐寄来的母亲生前所写的亲笔家书,这些手迹连同母亲留下的日记,让他仿佛再次亲历了母亲的晚年。这促使止庵要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写下来,进入与之前的评书、编书完全不同的创作状态。止庵在《惜别》中这样写道:“有一次去看话剧,忽然悟到:父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一幕结束了;母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二幕结束了;那么现在是第三幕,也就是最后一幕了。”
《惜别》便可说是止庵人生“第三幕”的开启。
范宁(以下简称范):您最近推出了新书《惜别》,这是一本因为母亲病故而缘起的书,也是您自己参悟生死的一部作品。时隔三年才写成,为什么?
止庵(以下简称止):母亲去世的时候,本来没想写这本书。后来之所以动笔,第一是因为她不在之后,我自己写了很多日记,重新读来,她不在的这几年,我对生与死有了很多感想;第二是因为她从前喜欢给我姐姐写信,一周要写一封,我也不知道她们互相写什么。母亲去世之后,我请姐姐把母亲的信托人带回来,才发现有一个纸箱那么多。母亲用A4纸写,很小的字,从一面的左上角写到另一面的右下角,两面密密麻麻写满,粗略数数就有2000多页。她自己以前也记日记,生病之后写了7本日记,后来我把这些信件和日记都读了一遍,更觉得有写成书的意义。
母亲在文字中写的都是日常生活,她熟悉的生活,做饭、集邮、赏花等等,这里面有“生意”——生机勃勃的意蕴,而且我是透过这些文字看这种“生意”,是隔着死看生,就尤其觉得应该动笔记录下什么。2012年,我开始构思这本书怎么写,想清楚了再动笔。
你可能会注意到《惜别》这本书的一些写法,第一章读起来可能有些费劲,其实我是故意这么写的(在《惜别》的第一部分中,止庵写的是“存在与不存在”,从孔子、庄子写到加缪、索尔仁尼琴,还有周作人的译作,仿佛是绕了很大一个圈,将人们落在生与死命题上的视线,带着兜了两千多年。止庵把这比喻成“落下了河流上的一道闸门”)这有点像放下一道闸门,让河流冲击到闸门上,思想才能激起浪花,否则就不会有碰撞。
范:这种写法可能和您过去读书、编书有关系。您之前写过很多书,但不少都是和读书有关,很多本身就是读书笔记。您也有很大的阅读量。所以在写《惜别》的时候,您信手拈来,会将生与死放在一个大环境里观察,而不仅仅从单独的生命入手。
止:这个的确和我过去的阅读,以及做了很多读书笔记有关系。我觉得有两个影响。第一,我编的书里,最多的是周作人的书。周作人的散文传达出一种美学观念,他主张写文章要像朋友在聊天,而不是像在台上演讲。因为如果把写作当成演讲,把读者当成台下的听众,作者本人就会不自觉要调动情绪,而且容易被台下观众所左右,这种情绪往往会脱离真实,变得激昂。朋友聊天就不一样,可以娓娓道来。我觉得周作人解决了一个人写文章的根本问题。
《惜别》写的是情感,我觉得,有七分的情感,写到三四分,就已经足够了,最怕就是七分的情感写到了十分。我作为读者,也最怕读到这样的书。所以我希望写一本能够被读者接受的书。
其二是我喜欢读书,而从古读来,可以读到中国人固有的生死观,从孔子到周作人,其实是有一个传统在的。孔子就不大相信人死后还能存在。我在大学是学医的,对孔子的观点我有共鸣,所以在《惜别》中阐释生死观的时候,我有依据。这并不是我在自说自话,而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就一直有这样的观点。
范:您之前有过很多创作作品。这部书是否延续了过去创作的经验,同时作为专业的创作者、阅读者和编撰者,三者的关系对写这本书,或者说对写作有什么帮助?
止:我以前写了很多诗,后来不写诗了,主要成为一个阅读者。我觉得这里面的变化,是一个从创作到阅读的变化。创作和阅读的差别在哪里?创作比较感性,而阅读比较理性,从创作到阅读,有一个从感性到感悟,到思考的过程,是不断深入的。
我以前写过很多读书随笔,其实就是在思考的层面写作。而现在写《惜别》,这本书里既有感性的部分,也有感悟和思考的部分,感性和理性是揉在一块儿的。我并不是仅仅写我的母亲,写她的一生,我无意把这本书写成一本回忆录,而是试图在所写的内容和读者之间搭一座桥。里面的素材有关我母亲,但是她作为一个普通人,对她的回忆完全构不成一本书,只有感性的回忆是不够的,那么怎么办?我在书里找到了一些情感地标。
就像北京的地标是天安门广场,上海的地标是外滩一样,情感也会有地标。看到这样的地标,所有人都会知道,进入到了一种怎样的情绪中。比如说“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这句诗,这个“门”就是作者崔护的情感地标,看到这扇门,会想起去年今日,这里面有理性的成分,会触发很多读者的同感,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张岱在《西湖梦寻》的序言里面说,因为战乱,眼前的西湖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此时的西湖,也是一种情感的地标。
二
《惜别》中有一处写道:“中秋节。记得一九九八年我们刚搬到望京,没多久就赶上这个节,母亲去超市买了两块月饼,一块是哈密瓜馅的,一块是枣泥馅的。我们原本都不太爱吃月饼,那个晚上一起坐在阳台,边吃边赏月,却待了很久。我从未置身高楼之上看过月亮,乍见简直吃了一惊,真是好圆,好亮。母亲给姐姐的信中描述过她患病前最后一个中秋节的情景:‘方方回去后给我来了电话,说快看窗外的月亮又大又亮……”一件小事,充实而平常,它不是被匆匆度过的时光,而是对亲人有质量的陪伴。
《惜别》写母亲,写生死,都是关乎平凡人的存在状态。止庵越来越认为,相比于平凡,传奇是容易写的,它已具备了好故事的要素,很多时候顺水推舟地作文便是。而平凡生活却不易写出一番况味,倘若没有通透纯明的心,无法诚恳地感知生命,恐怕就会落得庸人自扰。在《惜别》中,藉由母亲的日记书信与止庵的感悟,生活的细节被怀揣出一种实实在在的温度,抚慰人心,也让我们重思:在有限的平凡日子里,我们是否也把每一件小事做得有质量,有滋味,将寻常时光过得“真切而结实”?
范:会不会以《惜别》这本书为触发点,您又回去开始写诗,开始创作?
止:这个可能不太容易。不过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读小说,小说要有好的故事、内容,有很多人都写得很好。但是如果说起写作,我的兴趣点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文学作品要吸引人阅读,写传奇的不少,要写非常之事,总是有一些跌宕起伏的情节。但是我现在关注的却是很多小说家不太关注的部分,那就是平常人的平常事,虽然很普通,但是有意味。
普通的生活,平凡的小事、对话,乍一看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但是细细品味起来,这里面是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寻常人生确实有它自己的魅力,就看我们如何去感悟,用敏锐的感觉去发现。
我读的文学作品里面,福楼拜有一篇小说叫做《一颗纯朴的心》,就是写一个女仆平凡的一生,但它真的是文学史上的一件艺术品。作者写了这么一个东西,把所有的传奇去掉,依然读来非常吸引人。写平凡人生,如果我心中有一个楷模的话,那就是这本《一颗纯朴的心》。
范:平凡的生活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止:假如我们能够永远活下去,这个平凡生活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有意义也体现不出来。就是因为有一个“死”在前面放着,使得我们的“生”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限制,你体会到自己生命有限,可能你会改变态度,这就是“生”的意义。
看看我们一代代的接续吧。我们跟我们的上一代人,或者再上一代人,一代一代人都是先这个人来,然后他存在于下一代人和相关人的记忆之中,然后下一代人和相关人不在了,那个被记忆的人就完全进入黑暗,但是,这个记忆他的人以后又被下一代所记忆。人类就是这样,不断地记忆,不断地遗忘,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很珍重这种关系,我们记住一些人,我们也被后面人所记住,人类连绵不息不断延续下去。
在我的书里引用了一段故事。孔子死了以后,他的学生们在他的坟前守了三年,因为三年时间不短,到了三年以后大家就各自散了,只有子贡又住了三年。在孔子临死之前,孔子病了,人要不行了,他就在唱歌,子贡听了孔子的歌,认为老师快不行了,就赶快去见孔子,见的第一面孔子就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其实子贡是急忙赶去的,但孔子还是觉得自己的学生来晚了。这两段记载,可以看到师生之间的情感——这种情感隔着生死来体会,特别打动我。
范:所以关注平凡,是因为您有一种感觉,觉得“来不及珍重”?
止:是的。我觉得越热爱生活的人越没有办法面对死。说实话,稀里糊涂的人其实是很幸福的,因为你越在意你的生活,你就越觉得来不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
范:我可以明白您的意思。所以您关注那些写日常的文字,是因为生活中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片段,或者是一种感觉,它可能稍纵即逝,也可能会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印象中,隐隐约约,但人很容易对这种感觉着迷。它其实与传奇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只是一种日常的图景,但是就让人沉迷其中,或者能发现些什么。所以对生活我们还是不太敏锐。
止: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如《晚春》、《麦秋》等,说的都是日常的生活,但是就是给人留下一种意蕴悠长的印象。所以,从一种生活态度而言,生活的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生活条件,平常的生活一样可以有“生意”。就像我在《惜别》这本书里写到的,促使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我看到母亲写的一句话,老太太在想,怎么让自己能活得更好一些。为了这句话,老太太的人生从60岁之后开始,去旅游,去种花养草什么的,所以人生从20岁开始和从60岁开始没有太大的区别,在于你是否体会到了生活本身的魅力。
范:您所喜欢的周作人,我觉得就是一个生活家。在他平淡的文字里面,写满的都是对平常生活中的乐趣的感悟。
止:周作人就是一个生活艺术家。
范:那么张爱玲呢?一般认为,张爱玲写的是当年的都市传奇。她是在世俗的生活中写出了那些命运和人性的跌宕起伏。这不就是一种传奇吗?而您又是研究张爱玲的专家,那您所说的生活兴趣点的变化,相对于过去的张爱玲研究,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止:其实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张爱玲的散文,就可以看到她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当然晚年张爱玲过了一种怎样的生活,我们已经很难去还原。但是看看她当年写《重访边城》,写在香港买花布的情形,那种感觉其实是非常生活的,是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发现了人生的乐趣和意义。这些文字是可以体现她的生活态度的。
不妨再举一个例子,鲁迅,他同样也是非常懂生活的一个人啊。作为一个“生活着”的人,鲁迅还有大量的事情,并没有被我们还原。他有很多爱好,喜欢收藏,特别喜欢看电影。在他生命最后一个月的19天里面,鲁迅还看了好几部电影,比如杜布罗夫斯基的片子,看完之后鲁迅还给很多人写信推荐这部电影,说你们赶快去看吧!所以这些人在生活上有非常值得重视的地方。
其实我们文学上的一些经典,比如《红楼梦》、《金瓶梅》,写的就是世俗人生,没有那么多传奇,就是人世中的酸甜苦辣。
范:现在有些作家好像对于情节的跌宕起伏比较看重。
止:是的,不少人喜欢编故事,编离奇的故事。
范:这样的话问题又来了,因为当今中国,纯文学或者说严肃文学这个领域里面,现实主义仍然是最为流行的一种题材,主流而且强势。作家们都那么写实了,难道写的还不是日常生活吗?那么现实主义和日常写实的区别又在哪里?
止:中国文学这三十多年来的两大主流,应该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现实主义走的是实际的路,而现代主义走的则是观念的路。我觉得两者是殊途同归的。的确有很多作家在写现实生活,但是这种现实和日常生活依然不是一回事。
范: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生活,还是具有典型性。它是从一般的生活中萃取、提炼出来的,不能代表日常,是日常中不寻常的地方,它的写实和真正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段差距的?
止:是的,现在日常生活真的很少有人写,因为要写出日常生活中的美妙和情趣来非常难。不过,现实生活不应该把日常生活排斥在外,应该直接地去书写它。
范:您应该也注意到了,湖北也有一批从“新写实”以来就一直驰骋文坛的作家,文学鄂军中的写实能力、写现实的能力和传统都是很强的。他们符合您所认为的书写日常生活吗?
止:湖北确实有一批非常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最有名的当然是方方、刘醒龙、池莉。但是他们关注的依然是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现实,而我所关注的日常生活,和大时代的关系其实是有些脱节的,是一种生活的艺术,某种情况下,其实是和时代保持着一种距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抗。这种日常生活并不能被时代所规定,是在某个大时代中的人,用自己的态度来选择生活,而不是被时代所裹挟。
三
许多人知道止庵其名,乃是缘于他严谨冲淡的书评文章。现下已出版的《沽酌集》《插花地册子》《茶店说书》等十余部作品,均是止庵将自己的读书心得和纵横考究,自然落于笔端的文字集结。而张爱玲的《小团圆》以及周作人相关作品集的编辑过程,都是当年的文化事件,也令止庵“编辑人”的身份为公众所熟知。
范:我做文化记者这几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小团圆》这本书的出版。这几年也出了很多好书,有不少书都形成了一段时间的热度,但是像《小团圆》这样热门的图书,又有销量又有话题性,很多人都在参与的,真的是很少见。您是这本书的编者,您怎么看这种热度?
止:是的,《小团圆》打败了当年所有的图书。而且这是一本作者已经不在了的书,要是作者在,还可以现身说法,有一些宣传的推动。但作者已经去世这么久,还能有一百万册的销量,不能不说《小团圆》是一个异数。
这两年流行民国范儿,但是我觉得这本书的成功还不是民国范儿的影响。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张爱玲是一个文化符号,能够成为标志性的文化符号的作家不多,鲁迅算一个,张爱玲算一个。现在萧红拍成了电影,比较热门,但萧红也难以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文化符号就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容易带来粉丝。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粉丝。粉丝喜欢这个人,但并不一定喜欢她的所有作品或思想,而可能仅仅因为熟悉她的几句话,比如“成名要趁早”等等,开始关注她的生活——《小团圆》这本书,恰恰写的就是张爱玲的生活,满足了粉丝对她的生活的好奇心。第三个原因是张爱玲晚年的长篇小说比较少,而能够承载这么大的话题量和关注度的,大概还是只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都做不到这一点。
还说一件小事,比如安妮宝贝,她就是因为《小团圆》喜欢张爱玲的,但是也只喜欢《小团圆》而已。
范:您之前也参与创办了文学期刊《大方》,安妮宝贝任主编,虽然只有两期就因为客观原因没能继续下去,但是《大方》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于当前文学期刊的生存状态怎么看?
止:我和安妮宝贝本来不认识,因为《大方》成了朋友。我们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做杂志就做好,不能做就不强做。最初对《大方》的期待就是希望能做长久一点。因为阅读率在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身边好多曾经读书的人忽然就不读书或者很少读书了,而曾经不读书的人现在还是不读书。这里面可能文学期刊受到的冲击又是最大的。一个客观的原因是,期刊跟不上阅读的节奏,反而是书出得很快,而期刊能完成应有的任务就已经算表现不错了,这种情况当然是堪忧的。期刊最重要的是有固定的读者,只有有了读者群,期刊才能维持下去。
责任编辑 向 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