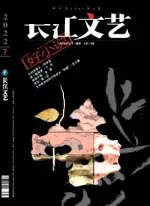观“象”记
2014-04-29占跃海
占跃海
2014年1月,“象内象外——民族风情五人作品展”在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的美术馆开幕,展出了钟孺乾、周乙陶、沈松德、王祥林、罗彬五位艺术家的作品。展览的“象内象外”之名,大抵是试图为五种“形态迥异”的作品提供一个集体性的描述。
此次展览同期,举办了钟孺乾新著《水墨变象》的首发式。钟孺乾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绘画之“象”的研究,此前他的《绘画迹象论》在学界已有颇大影响。《水墨变象》的在场,正好为接近他的画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缘。在几个场合,钟孺乾认真强调他并非一个抽象画家,这对那些喜欢将非写实再现的绘画直接归诸“抽象”一派来认识的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提示。他作品中的“象”,是因水墨的属性而自然变化生发的“变异之象”。这种“象”常驻画中,但不是那么显而易见,钟孺乾常常采取了得心应手的藏匿手法。于是,观众对作品的观赏就无法回避一个寻觅、识别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辗转之间常常会有发现的感动,也有众里寻它千百度却无功而返的失落。《杯酒酡颜》一画便是有趣的例子。这幅画不同于莫兰迪的杯子——那些形体就在观众面前,也不同于罗斯科的那种大色域抽象画——通过色场的磁性效果来吸附观众,《杯酒酡颜》设定了观众参与图像完形的观看距离。这幅画面上只有几条勉强可以围合的或干或湿的粗线,外加几抹酱色笔触。这些线条扭曲摇摆,在题名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将之“投射”成一只濡湿的酒杯。在这颤颤的影迹所构成的画面前,观众悄然成为画家所设定的那个酡颜惺眼的醉客。《是荷非荷有声音》中的墨迹斑点自然坠落晕散,如同天籁雨露滴打青莲,画家试图让驻足者屏息聆听,全面开放感官通道,画家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观众在对传统的再现性绘画的依赖中形成的感官半关闭状态。
据说温日观画墨葡萄,“酒酣兴发,以手泼墨,然后挥写,迅於行草,收拾散落,顷刻而就如神,甚奇特也。”(《农田余话》)古代画家如此这般即兴收拾,渐次成形,钟孺乾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段,但他只收拾一半,另一半需要观众们拓宽视野搜寻经验,象在那里,草草逸笔,曾有不曾有。
而周乙陶的“雪”系列则烘托出一份现代的“荒寒”式崇高。古代文人画的“荒寒”追求反映了这一群体对心灵的萧条澹泊的追求,并落实在空山寂寂的山水图式之中。身处城市的画家将目光投向荒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周乙陶有其特别的选择。他并不采取现场写生的方式来创作作品,而是在绘画开始之前经历一个他人不可参与也难以理解的选择过程。这种图像的选择和阅读,如对一部哲学著作的选择一样谨慎而复杂。他选择的风景图像是萧索而寒冷的,这既与他熟悉的水彩、坦佩拉技法体验中形成的形式需求有关,更是他的文化关怀中的隐隐焦虑不断渗透的结果。我们熟悉他在公开场合的诚挚风趣的一面,却很难读到他在执笔作画时宁静失落的一面,这种失落情怀源于他的哲学阅读和思辨。这个时代的思想贫困和智性荒寒在《雪语》的寂寥中终于寻觅到视觉的隐喻寄托,道路狭窄、土地斑驳的雪域近乎无人区,在远山的映衬下,一排排篱笆或一棵棵树影成为寂寥无言的仪仗队。
周乙陶的水彩、坦佩拉作品中没有这类画种时常展现的技巧花招。他以一种近乎抚摸的方式去描绘每一片区域,并且毫不吝啬地使用白色水彩颜料。作品中的青灰色调、微妙起伏的山地及其坚实的质地效果,也许和他近些年一直密切关注的苗族银饰工艺存在关联。这种青灰凄冷的高原戈壁不同于郁特里罗的孤寂落寞的街巷现实,而是不甘于城市芜杂而选择的沉着隐修。
沈松德的作品则给人以非常明确的清新印象,这与他本人给人的印象相符。他的画很容易被认为是对日本现代画家风格的中国化尝试。待细观画作,发现这些画幅不算小的画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小的十字形笔触纹理。记得未来主义画家巴拉的早期作品《路灯——光的研究》以数不清的V形笔触来处理光线从灯火向四周的散射,最终形成了光束的视觉震荡效果。但沈松德的十字形笔触纹理没有服务于那种强烈的明暗对比和补色对比,而是以节制的、中性的柔和色调组成抒情而富有装饰性的画面,画面上的物象处于凝固的静境中。在一些近作里,画面上的树木、山峦、马匹等物象的轮廓线是以虚线的形式呈现的,它们仿佛厚厚的鞋底上的针脚,与十字形笔触纹理一道,回溯着画家的笔端在作品中漫长而枯燥的行走,这是借助线条的语词一圈一圈、一道一道、从上而下、自左而右、从起点到终点的编织。这种行走与编织过程是极其缓慢的、忘我的、无尘的。与其说这是一种曼妙的女红修辞,不如说是画家面向抒情之光的灵性苦行。另外,沈松德绘画的繁密的笔迹组织丝毫没有回避过去被画家们轻视的“工艺”属性。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极端的写实画家凭借其庸俗的“逼真”优势,以千篇一律的写实绘画技艺取代了古代传承下来的各行工艺绝技,但取代不了工艺制作过程中的恬淡率真和“悟性——物性”一体化的原生体验。
沈松德就是以这种静默的方式来经营他的心灵天地。
在意义上,我认为王祥林的“风”和周乙陶的“雪”是可以相呼应的。王祥林的“风”系列,画的是一些蒸腾云气中半隐半现的马。这种半隐半现的形式让我想起达·芬奇的晕涂法和里希特的模糊图像。当年达·芬奇就是以这种方法赋予形象的轮廓已消融渐隐的效果。这一方法建立在达·芬奇本人对空气的造型价值的认识基础上,空气这种东西可以使轮廓模糊,让物象浸润其中,《蒙娜丽莎》可谓实践范例。王祥林的“风”的模糊性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画面情境幽暗,马影在中下方浮现,其身上的明暗配置凌驾于处理形体结构的意义之上,在朦胧的轮廓的辅助下,实现着黑色空间对马的渗透力量的视觉传达。
王祥林选择的媒介是碳棒素描,而非水墨和油画。干涩的碳棒在相对粗糙的纸本上运行,留下来的碳粉颗粒在服务于形象塑造和空间经营的同时,永远会确证自身在纸张表面的漫延趋势和不可抵挡的覆盖力。这仿佛是疾风作用下的沙尘,隐没这一匹匹模样相同的马。这些马也许在尘风中艰难前行,但它们都朝向左边——这种方向与我们的文字书写方向相反,具有“逆流而上”的意味。
如果说钟孺乾在借“象”虑画,构建中国水墨图像的阐释体系,罗彬则一直在通过古代具有特殊意义指向的仪式或行为惯例(如戏剧)、面具人物来进行水墨叙事。近几年来,他在水墨戏曲人物的基础上尝试一种风格深沉的“傩”系列。这一系列作品改变了以往的那种闲逸懒散的构图,通过对笔致的聚合、堆砌、挤压、重叠的安排来形成画面空间,墨色层次浓郁厚重,沉淀在半透明的纸面上,如岩石般古老。从罗彬的画面上的傩面和尖角装扮形象的特点来看,我认为他画的傩并非全是他一直致力研究的土家族傩仪,也有黔西地区的彝族原始傩舞“撮泰吉”。
“撮泰吉”就是变人戏,即人类刚刚成为人这一时期的戏。出场时一般由6个角色,而为首的是一个叫惹夏阿布的2000多岁的山林老人,他不戴面具,黑衣白须,是智慧的化身。但奇怪的是,罗彬的傩画里,一直没有出现这一无面具的形象。
“智慧老人”的缺席会导致原始傩仪中的远古荒蛮的特征益发显著,罗彬也许试图以此作为契机,在这一与早期人类的生存困境相关的精神活动中注入自己的见地。与他的“戏曲”水墨的清晰形式相比,“傩仪”系列混沌压抑,人物的行径充满未知的力量,这种力量又被一些造型意义不明确的笔墨组织反复加强。原始的神秘至今有多少存留在我们的精神困境和梦魇之中?凝视罗彬的“傩仪”景象会搅起这种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潜意识的悲壮力量,重新调整一直处于机械而疲惫的运转状态的现实心灵的内在布局。
古人云:“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吕氏春秋》)五位画家均已过天命之年,但他们性情稚拙,精神矍铄,和我们这些盲目奔波而焦虑的晚辈相比,显得要年轻许多。他们的年轻包含了一种时光和经历赋予的睿智,在艺术中激发出不断地自问和推陈出新,不拘泥于他们的时代所推行的那些陈规老套。
需要补充的是,在当代艺术中,画家访谈和画家自述似乎非常流行,这是为了摆脱采用新语言表达新观念的过程中遇到的艺术语言的语无伦次和语焉不详的困境。但文字的力量一旦被过度强调,作品本身就可能沦为文字叙述的辅助物,最终导致本末倒置。笔者甘当一个坚持目测意会的欣赏者,支持作品的主体地位,在文字的阐释中力图避免画家的画外言语的介入,但运用这种方式写的这篇“观象记”也潜伏着“占星术”式的危险。不过,倘若观众都能在作品面前凝神慎思而畅想,以上的文字也就可以被置于一旁而不予理会,无所谓它是一种证据充分的论述还是一种荒唐无稽的臆测了。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