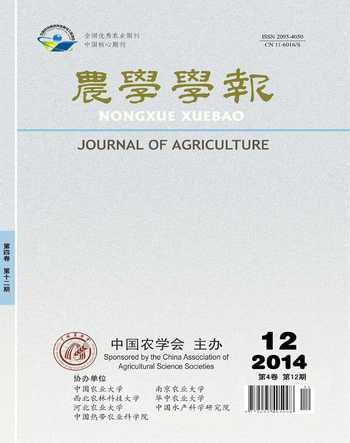论1917年京畿直隶大水灾
2014-04-29赵蓬李三谋
赵蓬 李三谋
摘 要:河北省及其近京地区,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自然灾害,曾严重危及当地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尤其是民国六年(1917年)发生的特大水灾,其破坏力相当之大,百姓罹难极其深重。面对这次惨烈的灾情,北洋政府和民间积极行动起来,想方设法地予以应对,并及时开展和进行了种种减灾救灾的相关活动,一些国际友人也参与其间,取得了相应的效果。为后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1917年;京畿;大水灾
中图分类号:S-09 文献标志码:B 论文编号:2014-0422
Exploration on the Great Flood of 1917 in Beijing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
Zhao Peng, Li Sanmou
(China Agricultural Museum, Beijing 100026, China)
Abstract: There occurred many natural disasters in Beijing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 in ancient time, which seriously endangered the ope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Especially the great flood occurred in 1917 made considerable damage to the area and people suffered a lot. The Northern Warlords Government carried out various kind of disaster relief activities. Many foreign friends offered help too. All the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great flood ar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or us, which is worthy of our study and discussion.
Key words: Flood; Beijing; 1917
1 水災情形
民国六年(1917年),就京畿、直隶一带而言,是历史上令人难以忘怀的大灾之年。这年春夏期间,雨水特少,旱情严重,稼禾长势不良,各处歉收,农产不及常年之半。继而又罹水患,田舍遭淹,旱涝之难交加,犹如雪上加霜,令黎庶苦不堪言。
当年7月下旬,中国华北地区受台风影响,京津冀连降暴雨,太行山、燕山均被雨浪连日笼罩。山洪涨发,洪水泛滥,海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北运河、潮白河等70条河流相继漫溢、决堤。京汉、京奉、津浦铁路受大水冲淹而中断,客涝肆虐,京畿变成泽国。入秋之后(8月底9月初),近京之地又接连遭遇2次台风侵袭,华北之地再次普降超常大雨,一些抢种、补种的秧苗,又一次被毁。就连一些地势较高、没被水淹的农田,也因长期阴雨,日照不足而产量大减。此次漫延河北省及都城北京的大水灾,旷日持久,民间恐慌。其中,直隶省会天津和保定、涿州诸地受灾尤为严重,诸如武清、宝坻、房山、文安、大成、获鹿各县皆为灾情较重之地。地方的农业损失甚为突出,对之,当时的新闻报导:“某乡人来述,略谓连日阴雨,各处水势大见增涨,前次积水尚未退尽,今则而潦忽又暴至,新播麦种半被淹没,明年早秋无望可期。前者洼地被水,芥末未获登进,而高岗肥美之田,实不无多少之收获,乃阴雨不晴,日久未蒙阳光,此类各豆多因积压霉坏,或被潮湿蒸酣,逐渐生芽者亦殊不少。此时即令天晴巫晒。恐亦半成屎土,况复阴雨连连尚无止期耶[1]。”
由于汛情的恶化,致使9月21日南运河在天津良王庄至杨柳青之间右堤溃决13处,洪水向北漫溢。3天后天津市区临时土埝全面溃决,一片汪洋[2]。城内西区、南区全部被淹,水深处竟达丈余。东、北、中区的部分地方也受水淹。日、法、英、德租界仍未能幸免。据《申报》记载:“天津灾情之重为历来所未有,就全境而论,被灾者约占五分之四,灾民约有八十余万人。”有10余万人,被迫逃荒,流离荡析,栖食无所。
时人对省会灾情记到:“洪水滔滔,经杨柳青往河北闸铺天盖地而来,堵救不急,淹灭村庄,吞噬田野,受难灾民在岸边支搭席棚,聚众其中,或从水中扶挈老幼妇女,挟持器物往高处,衣服褴褛,多数小孩身无寸衣,赤身在水中呼唤抢救,惨不忍睹……为五十年来所未有之浩劫。”[3]
据其时的报端文稿讲:正值夜半之时,洪水冲进天津民户,顷刻之间,平地水深数尺。当日市民被水淹毙命者已有二三百人。其逃生者亦皆不及着衣,率以被褥蔽体,衣履完全者甚少。市区街道积水很深,马路均可行船。天津本是华北著名的商业中心,长久以来,与国内其他城市有着广泛贸易。可是由于大水灾的破坏,与外界的水陆交通全部中断,正常的商贸活动已无法进行。秋季2次水灾增加了不少滞津的灾民,如西市大街、广开、谦德庄等地,都是水灾后建起的暂时灾民聚集点。据说,无家可归的“津埠城厢内外男女老幼全数难民”多达55399人,并且“其余被灾后寻亲觅友、租赁房间居住者,不在其内”。[4]那时有一些记者撰文通报:大批灾民涌入天津、北京等地以求庇护。“各乡村避乱来津者不绝于途,所有小学各校业经一律停课,将其房屋安插灾民。”[5]灾民聚集之初,所需生活供应难以组织,相关问题无以解决,一时间,城市运行功能几乎瘫痪,社会秩序滨临失控。其后,随着救助工作的逐步到位,局面才慢慢稍有起色。
河北涿州遭遇水患也相当严重。据当地文献记载:“县境内各河同时漫溢,奔腾冲突,一片汪洋。禾稼荡然无存,而人民之坟墓、庐舍、树木、牲畜付之东流以去者,不可胜计。灾情之重亘古所无。”[6]同样,经济繁庶的石家庄,居民1900多户,受灾1500户,房屋倒塌1万多间,未遭涝浸之民仅为500余户[7]。瓦砾遍地,灾民茫然,悲怆不已。
这年水势之大,难以估量,直隶境内的近河堤堰大都被冲毁,洪涝奔流肆虐。受灾范围遍及河北全省:北自长城张家口,南达临漳、魏县,西至紫荆关,东至山海关,幅员万里,未能幸免。当时的新闻稿声言:“甚哉直隶水灾之酷烈,殆数百年来的未有者乎!由运河而西,永定河而南,凡滏阳、滹沱、大清河之左右数百里内之村庐、田野悉为泽国水乡,而黄河复决于长垣,于是自开、卫、襄、赵、深、定以迄瀛、沧、津、涿、胥占灭顶。全省三千万人,厄于水者二千万,四十六万方里,陷于水者三十余万。”[8]总计被灾面积38950 km2,涉及103个县,1.9万余村庄。房屋被毁8万余处,田亩损失达254800多公顷,受灾人口620万。其中以天津、保定两地受灾最重[9]。四处疮痍,满目凄凉,甚为惨烈。
水患对民间生存形成巨大威胁,灾区饥寒交迫,瘟疫流行,大批因之而破产的农民离乡背井,四处逃荒。而如此人口的锐减,造成了灾区劳动力之不足,乡村生产力之下降。许多村、镇,到第2年春季,按时令需要开展春耕生产时,却有很多农田无人耕种,无奈只能任其荒芜,从而极大地妨碍了京畿、直隶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年度又因粮食产量不足而导致了市场动荡,粮价上涨,民食供应日渐紧张,以至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现象[10]。这次普遍性的地区饥饿,对当地之生灵打击巨大,民众难以抵挡。西洋著作《饥饿地理》曾言:“没有别的灾难能像饥饿那样地伤害和破坏人类的品格”,“饥饿残害人类,不仅在身体方面使身材变小,肌肉萎缩,皮肤损伤,而且影响他的精神,他的心理状况和他的社会行为”[11]。酷烈的饥馁之潮袭来,强躯微支,饿殍遗野。为了活命,民间或杀牛马充饥,或卖儿卖女以换食,并且因饥馁而引发的偷盗现象增多。继而瘟疫兴起,为害更甚。朝野愁云压顶,民情惊恐,民生危急,天地悲泣。
2 灾患原因
此种给京畿、直隶百姓造成巨大损失的水灾,究其原由,虽为天灾,但也有不可忽视的人祸之因素。当年气候异常,北国多次遭遇台风。入汛之后,北京、天津、直隶省内突降暴雨,且持续时间较长,致使数十条河流决口,所有600年来先后筑起的堤坝全被冲毁,京畿一带很快成为泽国。除此自然现象外,还有一些社会的问题介入其中。对此,当时不少有识之士曾指出,此次直隶省几大干河同时为灾,虽由一时之霆雨,实则河底长期淤塞所致。中国北方的燕山、太行山区,古代曾以森林茂盛闻名天下。然而,自明代以后,统治者为营建皇宫和开办冬季取暖炭场,不仅大量砍伐京畿一带的成材树木,而且往往连幼树也大片大片的铲除,地表植被极大破坏。继而在清代和民国初年,又未能真正有效地修复植被,生态环境的恶化没有得到缓解,造成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苟且持续数百年。至民国六年(1917年)时,河北省(直隶省)林草植被已破坏到难以言表的糟糕程度。对之,新闻记者写到:“夫直隶各山之荒芜童秃盛名震于天下,早为各国所共知,泰西各国屡屡派人而来中国,摄照诸山影相持之,为彼国人之戒。” [12]诸多林木既遭严重破坏,山梁泥沙便失去障固之本,随流而下,河道因之而不断淤塞,进而导致决口泛滥,最终酿成了这场大水灾。
针对中国京畿、直隶的这次水患,英国人戴樂仁撰写了《救治直隶水灾计划》一文,阐述了此次洪水发生的缘由后,并着重指出:“京畿各山童童不毛,一遇盛雨则狂流陡下,推岩石、挟泥沙,防止之法,舍多植林木外无他道焉。”[13]揭示了地表植被与水灾之间的利害关系,值得国人注意,理应引起当政者的思考。
据文献记载,明弘治、嘉靖年间,北直隶河道长期淤塞,从前的界河,被永定河挟带的大量泥沙而淤平,漫流之水汇集于界河南侧,形成许多新的淀泊,如任丘和安新的白洋淀、霸州的高桥淀、武清县境的三角淀等,皆为水灾隐患,遇涝则泛滥[14]。境内西靠云中山、大岳山的海河,常因淤塞而漫溢,为害黎民。该河明代成灾81次,清代为灾170次[15]。京师南部的永定河,携带泥沙甚多,明代泛滥19次,清代42次。
清圣祖时,直隶省九龙河入大清河,河道年久淤塞。康熙七年(1668)永定河泛滥,危及京城,民间死伤甚众。“宣武、齐化诸门,流尸往往入城。”[16]雍正初年,士人曾呼吁,直隶各条河流淤积严重,河床不断增高,随时有险情发生。雍正三年:猪龙河“决柴淀口而东,溃蟆蝍口古堤,直冲鄚州,驿路十里,浸为巨泽。”[17]嘉庆六年(1801年),京畿发生水患。嘉庆帝心情沉重地讲:“此次近畿一带地方猝被水患,皆由永定河下游淤塞、冲溃堤工,从前办理河道各员未能认真浚筑所致。……方受畴承办该处漫口时,如果经理妥协,何至本年有漫决之患。”[18]话虽如此讲,但统治者还是得过且过。第2年(1802年),朝廷仍然是在简单地应付河道淤积问题。如颙琰皇帝谕军机大臣等:挑挖淤沙,固为治河不易之法,但永定河南北两岸,长100余里,不便将全河淤沙挑挖净尽。只好“相度形势,裁湾取直,疏通梗塞。”[19]其时不仅挑河不彻底,而且堤防工程也不得力。对之,工部左侍郎那彦宝等奏称:“永定河南北两岸,及三角淀各处土堤,自乾隆五十五年加培后,迄今十有余年,日形卑薄。且经上年异涨,残缺不可胜计。”[20]道光年间,沧州等处的河道长久失修,淤积陈年,士人呼吁无效。光绪十六年(1890年),永定河因陈淤累积而决口,京畿一带房屋庐舍漂没,伤毙人口甚多[21]。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南北军阀争夺各自利益,互相攻伐,根本不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不愿花费较多财力物力去治理河道堤堰。一再承袭前朝之弊,不举河工,任其隐患累积。时人撰文写到:“京畿各河二十余年未经修治,堤防尽行残缺。此次水患,五大河及数十余小河同时并涨,泛滥横流,淹及一百余县,面积之广,所有堤埝无不破坏。人民被灾之后,救死不赡,焉有余力以筹修浚。”[22]《民国日报》记者,也于水灾暴发后指出:长期以来直隶诸山丘大量的水土流失,造成了境内各处河道淤塞,河床添高,其中以淮河、永定河、北运河等五大河流最为严重。政府年久未予修治,因而“盛汛宣泄不畅,遂成巨险。” [23]故而,北洋军阀政府难辞其咎。《大公报》新闻稿,同样把水灾原因归结为河渠浅窄,排洪蓄洪功能差之故。
“兹经调查其水大之原因缘每年伏秋大汛运河水溜狂动辄将千里堤冲刷绝口,灌入文安漥内,本年伏汛西河甚大,预将文安漥灌满,运河水无处容纳,又兼南北运河之水同时暴涨,以致汜滥无归是以淹没津埠多村。”[24]
本来,华北诸多水系以扇状汇集到天津后,形成海河。而河流入海处,地势甚为低下,易生漂淹之患。如此则使得该地不仅要负起本区洪水的宣泄之责,同时也承当了排解海河上游各处洪涝的重任。这年的洪暴势猛,压力过大,防御洪涝之举措又不到位,结果天津不堪重负,而致御洪系统全面崩溃。
防御水灾,或言防汛,是关系到国计民生之要务,不论古今中外,皆是朝野所应关注的大事。尤其是统治者,督饬防汛,责无旁贷。通常要动员官府和社会力量,及时兴办环境保护和修复工程、水利工程(包括水土保持活动),并在汛期运用防洪系统的各种措施,包括守护防洪工程,控制调度洪水流向等,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诸如此类,清政府做得不好,北洋军阀政府则表现更差,犯下了历史上不可饶恕之罪孽。
3 救灾举措
大灾突发,舆论沸腾,救援之声四起。水患之初,京兆尹呈请中央政府赈济。新任民国代总统冯国璋,于9月29日为之特设“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作为应对这次水灾的官方机构。任命已经离任的政府总理兼财政部长熊希龄为督办,专门负责处理水灾善后工作。第2天,冯国璋发布大总统令:让财政部首先动用库银20万元,“交善后处督办熊希龄,会同直隶省长,遴派廉正官绅,分赴灾区,赶办急赈。”[25]由于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经济衰退,财政困难。加之袁世凯复辟又花掉了国帑6000万,国库早已虚弱,遇此灾情,政府捉襟见肘。区区20万元官款,可谓是杯水车薪。不得已,财政部为办理京畿水灾之赈济事务,便向四国银行团及花旗、麦加利、华比等国际银行借款70万两银。10月20日熊希龄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裕中公司签订运河借款合同,向对方协借600万美元,用于水灾善后。紧接着,11月22日财政总长梁启超、善后处督办熊希龄又以“多伦鄂尔及山东、山西之某地常关收人”为担保,向10家日本银行借贷500万日元,用于直隶水灾赈灾[26]。
在拨放帑银和举借外债之余,又因灾发行公债。起初是直隶省长曹锟提出以省税作抵押,向外国银行借债500万元充作河政费用。对此,中央政府表示反对,不予批准。并令其以募集公债的方式,筹集款项,以办理赈务。于是,曹锟以省署的名义发行了直隶省第三次公债,总额数为120万元银元[27]。此外,督办熊希龄、直隶省长曹锟曾数次致函各省官员,要求襄助。一些官僚如广东龙济光等先后筹捐赈款,向灾区散发。
继而开设因利局,发放灾后贷款。那时虽有政府拨款、官僚捐助,但灾民甚众,杯水车薪。因此,督办京畿水灾河工事宜处,发文令各县知事筹设因利局,向灾民贷款。起初设定因利局经费,可“借地方公款,或劝绅商及各慈善团体筹集”,并“选派本地公正绅商经办”,原则上凡本地极为贫乏民户皆可申请借贷,“或定轻息,或特免息”以恤民困[28]。在实际开办业务之后,多处因利局将贷款利息定为一分,这虽不算是轻息。但比民间高利贷低,总算能助民间解决一些燃眉之急。
各社会慈善团体和个人以及海外组织也皆进行了资金捐助活动。在此类活动中,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京直奉水灾義赈会、上海广仁善堂义赈会等组织也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其中,中国红十字会等团体当年10月份在上海募集赈款50万。美国红十字会2次共捐款10万美元作为赈济费用。上海罗叔言先生将家中所存古玩售价2万元,全部捐助灾民。凡此种种义举,到处都有。
同时,北洋政府责令地方衙署及时措办具体的现场救灾实务:善后处督办熊希龄,及时会同京直各级官员尽心筹措,并依靠众多社会团体和绅商帮助,开展了紧急救援和紧急赈务工作。首先,抢救人民生命,迫在眉睫。许多城乡百姓被困水中,其中文安县是此次100多个遭受水害的县份中最为严重的地带。该县的37个村庄被水冲毁,屋址瓦砾无存。剩余的300多个村庄均处在水泊之中。政府下令军方派出士兵,向各区县四处搜救。天津红十字会“亦协力匡助,不避艰险,每日添派救船多艘分赴各村庄逐日救出灾民已达万人。”[29]并送至安全地方予以安置。对于一些留恋故土不愿离开者,则以舟船接济食物。
一边搜救,一边济食、济衣,并简单安置居所。中央动员,多方响应。当时天津督军曹锟筹集大量面粉和小米,预备30个军用巨型铁锅(津城警察厅亦预备8口大锅),进行实地施食,每日动用官粮两万多斤,蒸馒头熬粥,散给受灾的饥民[30]。北京警察厅也在京城开办了六处粥厂,每天早晨前来领粥的难民上千人。同时,京津直隶地方各县衙署,还曾会同乡绅出资筹办了一些零星粥厂,飨惠邻近的灾黎。随着冬季到来,天气转冷,京畿各处人士又募集不少的棉衣,分批赠发给灾民,并临时搭建暖棚让众多丧家失业者其免受冻馁之苦。美国红十字会也在天津搭盖窝棚,安置灾民。上海基督教堂圣公会彼得堂等,捐制棉衣及现金等,托人送往顺直,救济灾民。
在筹置赈款、赈物和简略安排居所的基础上,国家还开展了蠲缓租税、推行平粜、以工代赈等活动:水患当年,中央政府为减轻灾民经济压力和生活负担,曾宣布蠲免一部分重灾区的乡民田赋,并缓征一部分轻灾区的农业租税[31]。同时由于粮价波动,妨碍民生之故,北洋政府倡行平粜,抑制米麦价格,以求从宏观上保障民间的粮食供应。省署命被灾各县知事“邀会绅商筹集资本,择定地点,酌设平粜局”,由“官厅任保护之责,绅商服转输之劳”,“灾民可免冻馁”。[27]另外,京畿水灾善后处特别附设工赈局筹办各级工程,在保定修建的新开路(今西关大街)就是曹锟省长的工赈成果。第2年春,省衙又奉上峰之意,募捐款若干,以工代赈,将残破的刘公堤予以修复,一举两得。北洋政府还应熊希龄之请,允许招募直隶灾民遣往海外服役。
救灾济赈工作是与防疫、防匪结合一起的。水灾之后,常有疫病发生,此次水灾也也不例外。灾后的冬季,患痢疾、热病的人较多。曹锟省长命令警察厅防疫处和境内医院设法预防——控制疫病,清理病源,加强消毒。防疫处协同红十字会加派人手打捞水中尸骸,及时埋葬,并派医务人员赴各处消除秽物,及时诊治疾病。防疫之余,还要防止匪患。那时,有一些人趁灾乱之机劫掠,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鉴此,各租界和警察厅都派出人员,日夜巡护。初期曾击毙了20多名匪徒,后来局面稳定,秩序转好。
开办留养所、慈幼院。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从上海派出蔡吉逢等办赈人员北上,与天津红十字成员分赴天津、保定、徐水、安平、衡水及沧州等灾区,送去赈粮、赈衣和赈款。并帮助不少灾民修复房屋和道路桥梁。还在天津郊区宜兴埠建起了“临时妇孺留养所”,收留了400多名无家可归的妇孺儿童,并给其中幼孩教课。当年督办熊希龄见到有不少灾民儿女遗弃道路或标卖,为此在北京设立了慈幼局2所,共收养灾民的儿女千余人。随后又在香山静宜园建起慈幼院(学校),让无家可归的孩子接受文化教育。
总之,北洋政府施行的各项救灾办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于某种程度上减缓了水灾危害。但是其救灾减灾的力度往往不够,主要是资金的筹集迟缓,且数额较少,难以解决根本性的确问题。当时的中央政权专注于各派系之间的斗争,不能以全部心思地为百姓排憂解难。而且,甚至在赈灾过程中,还曾发生过衙署一再拖延治河经费,官员不尽职守,贻误工程[32],贪污公款,中饱私囊等现象,致使赈济效果大打折扣。
在这次水灾救济活动中,民间绅商和社会团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赈灾工作出力甚多,贡献较大。尤其是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动员广泛,组织有序,表现活跃,行动及时。所属成员,为了难黎,常常走滩过川,爬山越岭,不畏艰险,不辞辛苦地将赈物、赈款送到灾民手中,所作所为,可歌可泣,可敬可贺。
此次灾患,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灾荒一样,广大人民除了取得国家荒政措施的相应支持之外,主要依靠民间的救灾救难、扶危济困、乐善好施、团结互助的传统精神及其行为,及时帮助灾民消减临灾恐惧心理,稳定社会秩序,有效恢复经济,重建家园。如此应对灾荒之行为,如此高尚的民族精神,早已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民族的凝聚力,坚强的战斗力,它战胜了一次次的自然灾害;使国民从灾荒的打击下一次次地站立起来,恢复生产,再现生机,继续向前迈进。
参考文献
[1] 《大公报》1917年10月2日报导.
[2] 赵楠.天津1917年大水灾及其影响探析》[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4).
[3] 《大公报》民国六年(1917)10月9日报导.
[4] 《大公报》1917年10月14日报导.
[5] 王秋华.1917年京直水灾与赈济情况略述[J].北京社会科学,2005(3).
[6] (民国)《涿县志》第3编,经济,实业.
[7] 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济1917年京直水灾述略——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8] 《益世报》民国六年(1917),10月23日.
[9] 刘宏.外国人对1917年天津水灾的救援[J].民国春秋,2001(6).
[10] 赵楠.天津1917年大水灾及其影响探析[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4).
[11] 卡斯特罗.饥饿地理[M].北京:三联书店,1959:63.
[12] 《申报》1918年2月6日报导.
[13] 刘宏.外国人对1917年天津水灾的救援[J].民国春秋,2001(6)
[14] 陈仪.陈学士文集(卷2)直隶河道事宜[M].商务印书馆,1936
[15] 刘宏.海河流域六百年来水灾频发的警示[J].中国减灾,2007(12).
[16] (清)彭孙贻:《客舍余闻》,光绪抄本.
[17] (清)雍正《畿辅通志》,卷45,河渠,猪龙河.
[18] 《清实录·仁宗实录》卷86,嘉庆六年十月庚戌条.
[19] 《清实录·仁宗实录》卷94,嘉庆七年二月壬子条.
[20] 《清实录·仁宗实录》卷94,嘉庆七年二月己巳条.
[21] (清)震钧:《天咫偶闻》.
[22] 《申报》1918年2月22日报导.
[23] 《民国日报》1917年9月28日报导.
[24] 《大公报》1917年8月15日报导.
[25] 周秋光.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26] 《大公报》1917年11月24日报导.
[27]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28]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3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29] 王秋华.1917年京直水灾与赈济情况略述[J].北京社会科学,2005(3).
[30] 池子华,刘玉梅.民国时期河北灾荒防治及成效述论[J].中国农史,2003(4)
[31] 《政府公报》民国六年(1917年)11月24日,第667号,命令.
[32] 《晨钟报》,民国六年(1917年)12月4日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