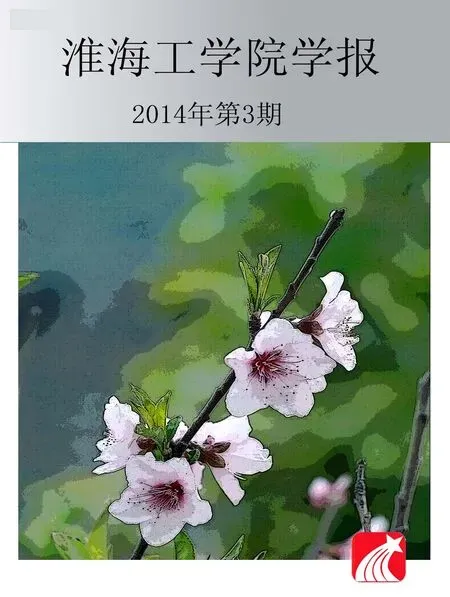灵与肉的生死搏斗
——解析《无名的裘德》中的“本我”和“超我”*
2014-04-17徐苏
徐 苏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外语系,四川 汶川 623002)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是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哈代以诗人的身份进入文坛,以小说家身份闻名,最后又以写诗告别文坛。哈代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是哈代的最后一部小说作品,这部小说一出版便受到了种种非议,哈代也饱受打击,并转而发展自己的诗歌创作。
《无名的裘德》以英国维多利亚后期为故事背景,描述了男主人公裘德和淑的灵魂伴侣的感情以及裘德与艾拉白拉之间充满肉欲的婚姻。正是这一故事题材,深深地震撼了当时的婚姻伦理观,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批评:有些评论家直接将小说改名为“淫秽的裘德”;威尔菲德大教主把这本书当众烧毁,并把书灰寄给哈代;英国许多图书馆也禁止这本书的外借;甚至有读者在《纽约世界》发表文章称“《无名的裘德》是我读过的最坏的一部”,“我看完了这篇故事,把窗户打开,以使空气透进”。
由此可见,《无名的裘德》的出版发行,对当时的社会婚姻伦理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英国公众对婚姻与性、婚姻与道德的激烈讨论。
一、裘德与艾拉白拉:“本我”的肉欲
《无名的裘德》开篇便引用了先知艾司德拉司的一段话:“不错,有许多男子,因为女人而丧失了神志,因为她们而做了奴仆;又有许多男子,因为女人而丧了命,栽了跟头,犯了罪恶……啊,诸位啊,女人既然有这样的本能,那怎么能说女人不厉害呢?”[1]1这便点明了男人容易陷入情欲,犯下错误,这也是裘德失败的原因。
裘德身世悲惨,父母早亡,从小被寄养在老姑太太家,在村民田里做小工赶麻雀。受老师费劳孙的影响,裘德克服困难自学成才,并一心想做一个神学博士,能舒舒服服地住在基督寺。而就在此时,裘德一生中的第一个女人艾拉白拉出现了,并改变了裘德的人生计划,埋下了裘德人生悲剧的种子。
艾拉白拉一出场便是充满了肉欲。为了引起裘德的注意,她将“阉猪身上最特殊的地方”[1]15扔到了正在读书的裘德的耳边,并故意在脸腮上挤出酒窝,用女性对男性不出声的呼唤来诱惑裘德,“他从她的眼睛看到她的嘴唇,从她的嘴唇看到她的胸部,看到她那两只露着的圆胳膊,只见她的胳膊,当时让水泡得湿漉漉的,红一块白一块”[1]19。这是裘德平生第一次感受到的新体验,而这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所有的感觉。
虽然裘德知道艾拉白拉身上缺少和多余的东西都和自己的爱好、性格及理想完全相反,但是他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在艾拉白拉的精心设计与安排下,裘德不得不和她结婚。裘德先前的努力全白费了,最后只落得要把书卖了买口饭锅的地步。
而艾拉白拉嫁给裘德也是有目的的:“把他傻头傻脑的那些书本扔开,把眼光转到实际的工作上,一心一意干自己的本行,那他就很有赚钱的精力,绝不愁给她买不起衣服和帽子。”[1]27
裘德不得不取消了他经过多年思索和努力而制定的完美计划,和艾拉白拉穷苦潦倒地生活。然而婚后的生活无法满足艾拉白拉的欲望,在她感到裘德无法给自己提供充足的物质生活时,她便在杀完猪的第二天留下封信给裘德,然后和父母去了澳洲。
在澳洲,艾拉白拉生下她与裘德的孩子“小时光老人”,并留给父母代养。在未与裘德正式离婚的情况下,艾拉白拉与开酒馆的卡特莱结婚,然而婚后不久便又丧夫。当听说自己孩子“小时光老人”先将自己的兄妹吊死后,自己又自缢时,艾拉白拉“当时好像做出一副理想的凄惨样子而完全没做到”[1]229。
在淑和费劳孙重新结婚后,艾拉白拉灌醉了裘德并和他复婚。婚后,艾拉白拉对生病的裘德产生厌恶,不愿意照顾他。在音乐节那天,艾拉白拉不顾裘德的死活,打扮得光鲜亮丽去参加节日聚会,后来发现裘德已经死在了床上,她毫无同情地抱怨:“真巧啦,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这个时候死。”[1]261接着她又扔下裘德的尸体去找乐子了,后来她想起裘德自己一个人死在床上,法院非检查尸体不可,才回到家请人办后事。
艾拉白拉就是这样一个轻浮而又放荡的女性,她自私自利,无论是和裘德还是开酒馆的卡特莱,都是有着强烈的目的性,不择手段地用肉欲来迷惑男人。从选择裘德到不辞而别,再到后来与裘德的复合,艾拉白拉从未有过自己真正的情感,而只是从自我利益和自我满足出发。于是,艾拉白拉与裘德之间只能是低俗、本能的肉欲。
在保守的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对爱情及情爱的表达都是隐忍、含蓄的,而哈代却创作了这样一个大胆而叛逆的女性形象——艾拉白拉,她大胆追求情爱,为人自私自利,放荡轻浮,缺少道德伦理,毫无妇女道德,与当时社会风尚格格不入。以伦理的角度来看艾拉白拉,她缺少了在道德规范中的责任,“责任在道德规范的整个体系中,是处于最高层次的道德规范。责任是人们主动意识到的义务,它具有良心的成分”[2]187。
从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心理学理论来看,人的心理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另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不能被人意识到的,它包括人的原始的盲目的冲动、各种本能和出生后被压抑的欲望,而这些欲望之所以被压抑,是因为社会道德标准不容许它被满足。当这些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它并不会自动消失,而是慢慢转型,继续活动,追求满足。
正如裘德一样,裘德幼年时便父母双亡,被寄养在老姑太太家,从小缺乏爱,尤其是来自女性的爱,于是当认识艾拉白拉时,他很快便不能自拔,无法控制自己。也是由于从小缺乏家庭温暖,裘德很快便放弃先前的追求,和艾拉白拉成立了家庭。
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和个性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本我”是“快乐原则”,它从不考虑客观现实的环境,它所包含的所有冲动都是无意识的,只追求片刻得到的满足。“本我”中包括“性本能”,或称为爱本能(eros),弗洛伊德称其为“力必多(libido)”[3]284。“本我”是最原始、处在最难接近的底层,但它极端有力量,弗洛伊德把它形容为“巨大的深渊、一口充满沸腾刺激的大锅”[4]。
而艾拉白拉就是当时社会中大胆的“本我”主义者,当她向裘德耳边扔阉猪身上的那个地方的肉时,便是一种本能的、赤裸的勾引;当她把鸡蛋放在胸前孵化,并让裘德摸时,这便是她肉欲的表现。艾拉白拉所追求的,便是这种最原始、最有诱惑的“性本能”。而裘德也不得不让“本我”控制住了自己,虽然知道艾拉白拉和自己不是同一类人,他也觉得不对劲,不知道怎么办好,但此时他却让“本我”控制住了自己,最终和艾拉白拉走到一起,放弃了自己多年来的努力。
在听到淑与费劳孙结婚后的晚上,裘德与艾拉白拉偶遇,在“力必多”的驱动下,裘德和艾拉白拉混在了一起。后来,在听说淑和费劳孙复婚后,裘德便又和艾拉白拉住到了一起,由此可见,艾拉白拉对裘德,或者对所有的男人便是“本我”,是一味追求直接的欲望;而裘德对艾拉白拉也是出于“力必多”的本能,故两人的情感必然会遭到世人的唾骂,“本我”是人格中最低级的。
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大胆描写了一个被当时社会所不容的女性形象——艾拉白拉,她大胆无耻,轻浮放荡,以“本我”为中心,充满肉欲,是当时社会道德伦理的反面人物。而正是这一女性形象,也展现出了社会道德对女性在追求情爱方面的限制,对“本能”的压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而哈代对这一人物也进行了伦理谴责,对她的放荡行为表现出了厌恶之感。
裘德与艾拉白拉的结合是一种典型的“本我”,裘德沉溺于与艾拉白拉的情欲中,即使知道自己的行为荒唐,却无法自拔。一个人如果被本能的情欲所控制,成为没有灵魂的情欲奴隶,就不能做出与人的本性相符合的行为,就无法控制自己,遵守伦理。无论是艾拉白拉还是裘德,都是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本能情欲而背弃了伦理,无法达到正常人格的标准。在《无名的裘德》中,对沉迷于情爱中的裘德和艾拉白拉,哈代从伦理角度进行了谴责。
二、裘德与淑:理性的“超我”
淑是改变裘德一生的第二个女人。裘德在老姑太太那里拿到表妹淑的照片时,她的形象便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形成一种力量,并促使他到基督寺找寻理想。裘德第一次见到淑时,她正在用教堂经文字体刻字,“那位眼睛水汪汪,脚步轻飘飘,年轻、漂亮的女人”,与“充满肉欲”的艾拉白拉形成鲜明对比。裘德与淑见面的环境与裘德与艾拉白拉的截然不同,从而也点明了两类感情的不同。
淑的美是超凡脱俗的,最重要的是她的思想深深吸引着裘德。淑娇小的身体中,隐藏着一股力量,她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勇于追求自己的生活。在教堂做礼拜时,淑买了两个赤身露体的石膏像并抱回宿舍,引起了方德芬小姐的愤怒。在裘德的帮助下,淑到裘德老师费劳孙所在的学校做助手。淑对宗教有着自己的看法,在与裘德讨论《圣经》问题时,淑提出了自己的男女观,认为“男人只从性别上讲,并没有什么好怕的”。
而裘德在与淑讨论知识、讨论人生时,却不得不压制着自己的感情,因为他过去不光彩的婚姻,因为他与艾拉白拉还未正式离婚,根据当时的英国法律,艾拉白拉仍然是裘德名义上和法律上的妻子,所以裘德不能与心爱的淑恋爱和结婚。当听说裘德结过婚的消息时,淑十分气愤,草率地与费劳孙订婚,并到师范学校学习。
淑是一个追求灵魂自由的人,对婚姻有着自己的看法:“只是一种肮脏龌龊的契约,只是为了管理家务、纳捐纳税的实际方便,只是为了子女继承土地财产,以便让外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1]163由于缺乏感情,淑拒绝与费劳孙进行夫妻生活,“履行契约的义务”,淑认为,这件事必须自愿、自发才行。
而从19世纪初期,英国便开始对两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关于婚姻与性的关系,维多利亚时期也有规定,当时在社会中层阶级,作为妻子的规定责任有:第一,服从并满足丈夫的性和其他方面的需求;第二,保证孩子生理和心理上的健康发展;第三,家务劳动(洗衣、打扫卫生等)[5]221。而淑却拒绝这一规定:“人家都说,一个女人,在刚结婚的时候如果有什么厌恶的东西,过了五六年以后,就习惯成自然,觉得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了。不过这种说法,岂不跟说把胳膊或者腿锯掉了并没有什么痛苦一样吗?因为经过相当的时期,用木头腿或者木头手也可以习惯了,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呀!”[1]143
在淑的意识里,婚姻不是一种形式,所以她拒绝在教堂里举行正式婚礼;婚姻更不是一种约束,“一经法律的干涉,那这种热情,是不是就要消灭了哪?”[1]140在淑看来,婚姻的双方既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因为彼此人格是独立的,所以在婚姻中需要相互尊敬和平等对话,并且要给对方一定的空间。
淑不但有着自己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她敢于和当时社会伦理抗争,争取自己的幸福。淑对婚姻有着自己的看法,因此她勇敢地告诉丈夫费劳孙自己的决定:“我不跟你一块儿住,你反对不反对?”“我喜欢你是不错的!但是我认为可不能比喜欢更进一步。”“我原先的意思是说要和裘德一块过去。”[1]160于是,淑便和裘德同居。然而,这在当时社会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当两人在教堂做修缮工作来养家糊口时,人们议论纷纷,两人不得已带着“小时光老人”和他们两个的孩子到处流浪。
可是,后来淑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小时光老人”吊死了自己的兄妹并自缢,淑刚刚出生的孩子也夭折了。饱受打击的淑开始反思自己:“咱们应该永远在职份的祭坛上牺牲自己!但是我过去可老只尽力做于自己合适的事。我完全该受到我挨到的鞭打!我希望一种力量,能把我那邪恶、我那可怕的过失,我那一切罪恶的行为,都给我铲除干净了!”[1]234就这样,淑又回到了费劳孙身边。
淑所处的时代正处于社会急剧变迁的时刻,一方面,传统的维多利亚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新的思想不断涌现。而淑便深受这两种思想的折磨,一方面,淑意识到了女性思想的解放,对恋爱和婚姻有着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她的行为却饱受众人非议,饱受社会伦理的折磨。因此,她用“道德”和“良心”来约束自己,回到了自己丈夫费劳孙的身边。
这便是弗洛伊德的“超我”个性结构,“超我”便是道德的约束,也是人们所说的“良心”。淑回归费劳孙是品德态度中的顺从阶段,她迫于外界的压力和打击,对当时社会道德表现出接纳态度,但是认知和情感体验上却不一致。顺从是品德态度的最低层次。淑的“超我”和“本我”处于直接的冲突中,“超我”力图让淑放弃裘德,回到费劳孙身边,而淑的“本我”却选择和裘德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超我”限制了“本我”的冲动。
三、结语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男主人公裘德的成长为线索,以他一生中与两个女人的感情纠葛为题材,描述了极端的“本我”和“超我”的两种人格特征。
裘德的“自我”便在这两个极端中滑行,从艾拉白拉“本我”的肉欲冲动到淑“超我”的理性情感,最后无法平衡这两个极端而导致悲剧。正如裘德最后反思到:“我试图在这一代就完成的事情,其实需要两三代人来完成。至于淑跟我,我们思想明朗清澈,我们热爱真理,无所畏惧,但是我们这种情况,可完全走在时代的前头!时代还没成熟到我们这种程度啊!”[1]235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行为都需要“超我”的社会道德来约束,如果人一旦只追求“本我”的享受,势必会造成悲剧。
参考文献:
[1] 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M].张谷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 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3] 赵莉如,林方.心理学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
[4] 李汉松.西方心理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5] 玛丽莲·亚隆.老婆的历史[M].许德金,译.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