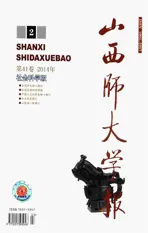论徐复观艺术精神的本质及范畴
2014-04-10朱立国
朱立国,何 静
(1.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 南京 211189;2.安康学院 艺术系,陕西 安康 725000)
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探索,开阔了世人的艺术视界,也引起众多学者对徐复观艺术精神观点的质疑,其中最典型的有两个:以章启群为代表,从老庄哲学本体出发,结合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理解,认为徐复观的艺术精神与老庄哲学是两个系统,不能将中国艺术精神与老庄“道”的哲学思想相比附[1];以李蓓蕾为代表,立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认识,认为徐复观所论的艺术代表了以文人画为主的“纯艺术”,不能代表中国艺术的全部[2]。
徐复观以人性为基础的中国艺术精神研究,加强了理论深度,也的确带来很多疑问:中国艺术精神与老庄“道”的关系怎样?二者如何联系?他的艺术精神能否代表或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艺术?这些问题都影响到对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的理解。
一、艺术与艺术精神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提到的艺术和艺术精神很明显是两个概念,艺术是艺术精神和技巧的结合,徐复观将道与艺术精神相结合,而不是和艺术相比附,他说:“当庄子把道当做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并且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于不识不知之中,曾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3]44。
徐复观所谓的艺术精神实际上是来自于生命体验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体验之所以能与庄子哲学思想相通,在于它们共同的无功利、自由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为自由的人所共有,而非艺术家所独有。徐复观认为庖丁解牛“的精神由此而得到了由技术的解放而来的自由感与充实感,这正是庄子把道落实于精神之上的逍遥游的一个实例”[3]46,而这正是艺术精神在现实的呈现。因为庖丁取消了心与物、手与心的对立,由技术进步达到“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审美效用,这种效用不受对象、环境、工具的限制,处于天人合一的自由境地,所以“是道在人生中实现的情境,也正是艺术精神在人生中呈现时的情境”[3]46。
在徐复观落实庄子哲学于艺术精神的探索中,女偊、梓庆都表现了这种顺应自然、不为物役的无功利的自由状态,这都是非艺术家的艺术精神在现实的落实。所以徐复观把“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中国人生活的艺术精神”并置,章启群就认为“徐复观的著作在关键问题的表达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如果放到这个语境中,这种混乱并不存在。
徐复观认为“由老学、庄学所演变出来的魏晋玄学,它的真实内容与结果,乃是艺术性的生活和艺术上的成就”[4]3。解牛的庖丁、承蜩的佝偻等都把艺术精神落实于艺术性的生活,为何他们没有创造出艺术性的作品?“艺术精神的自觉,既有各种层次之不同,也可以只成为人生中的享受,而不必一定落实为艺术品的创造;因为‘表出’与‘表现’,本是两个阶段的事”[3]44,因为他们缺少艺术家将之“表出”的创作技巧。
中国艺术以写意为优,但徐复观并未否定技术。徐复观认为艺术家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澄汰嗜欲杂欲,以得到精神的纯洁性与超越性,能纯洁便能同时超越;二是专一专注,终始其事,以得到技巧与心相应的熟练。”[3]248在一个艺术家由美的观照到美的创作中,“这中间最重要的是‘终始所学,勿为进退’的勤苦工夫,这才是天才的真实化所必不可少的工夫,其中没有半丝半毫便宜可想”[3]254,这就强调了艺术家修炼技术所必需的勤苦精神。在谈逸品时,徐复观“特强调须先有达到神之工力,再进而为逸,乃不至为偷惰浮浅者所假借,其用意极为笃至”[3]265。这里,不单强调了技术修炼,还对越过“工夫”的投机者提出批评:“仅一副素朴地性情,并不能创造出艺术品来,当然要有技巧的钻仰、澄练。”[3]351“马远们的简淡,实由深于技巧及法度而来。”[3]384在谈院画艺术时,徐复观也同样肯定了它在中国艺术史上的成就,为后期艺术家技术的成熟做了铺垫,影响着梁楷、南宋四家等院画艺术家。
中国自初唐开始为艺术分品,典型的如后来《益州名画录》“逸神妙能”的划分,徐复观对这四类艺术都给予承认,并未因能品艺术更倾向技巧而否定之。因为徐复观认为技巧是达到艺术精神必需的手段,其重要性在于如何超越技巧而达艺术精神。“逸神妙能”的艺术都可以看做艺术家艺术精神的具体化,只是表现程度不同。以庄子最高艺术精神为标的,“逸品”距此目标最近,“能品”距这一精神最远。决定艺术之为艺术的因素在于其所体现的艺术精神,而不是这一精神的表现程度。
但技术终究是为艺术服务的,作为艺术不能仅限于技术层面。“孔子对音乐的学习,是要由技术以深人于技术后面的精神,更进而要把握到此精神具有者的具体人格。”[3]5艺术之为艺术的特点还在于庄子精神的“第二自然”,技术只是为显现“第二自然”服务的,所以“艺术地传神思想,是由作者向对象的深入,因而对于对象的形相所给与于作者的拘限性及其虚伪性得到解脱所得的结果”[3]163。在艺术与艺术精神的关系上,徐复观认为艺术形式有限而艺术精神无限,对艺术的把握,就在于超越有限而追求无限,“由乐器而来之声,虽可以通向此无限的境界;但凡属于‘有’的性质的东西,其自身毕竟是一种限制;所以在究竟义上言,此声对此无限境界而言,依然是一拘限。无声之乐,是在仁的最高境界中,突破了一般艺术性的有限性,而将生命沉浸于美与仁得到统一的无限艺术境界之中。这可以说是在对于被限定的艺术形式的否定中,肯定了最高而完整的艺术精神”[3]28。
所以,徐复观的艺术精神实际是一种无功利、自由的审美心态,“人人皆有艺术精神”[3]44,它是庄子之“道”于人生的落实,艺术精神与创作技巧结合乃成艺术作品。判断艺术作品的是与否在于艺术精神的有与无,艺术作品品次的高与低在于靠近艺术精神的近与远。厘清艺术与艺术精神的关系,是理解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的关键。
二、艺术精神与庄子之道
庄子思想是徐复观艺术精神的基础,“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4]3。将“道”与现实相结合,徐复观称之为“形而中学”,“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加以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辨地形而上的性格。但当庄子把它当作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3]44。
在徐复观的艺术思想中,“道”的范畴要大于艺术精神,“道还有思辨(哲学)的一面,所以仅从名言上说,是远较艺术的范围为广的”[3]44。另外艺术精神与道有层级上的不同,“道的本质是艺术精神,乃就艺术精神最高的意境上说”[3]44。最高的艺术精神才与道相近,与之相对应的艺术才是最高等级的艺术,否则等级就低,价值就不高,这也成为徐复观分析艺术品次的根据。所以不可将道与艺术精神相等同,“道”即“艺术精神”的认识是不对的。
“道”是艺术精神的基础,所以传统艺术与道有着天然的联系,但这不足以说明庄子之”道”的艺术性,于是徐复观又通过三种方式来解释道的艺术性:首先通过艺术精神,其次通过比较“道”与艺术创作的相通性,然后借用西方美学与艺术的关系。三种方式都从外部将二者贯通,未从内部推理得出,由此可见徐复观逻辑推理上的缺失。通过艺术精神以证明道的艺术性在前面已作分析,下面介绍后两种方式。
徐复观用女偊和梓庆两个寓言中修养工夫的一致,以实现道艺的贯通。“从工夫的过程上讲,女偊所说的‘圣人之道’,其内容不外于《人间世》所说的‘心斋’,实同于梓庆所说的‘必齐以静心’。女偊所说的‘外天下’、‘外物’,实同于梓庆所说的‘不敢怀庆赏爵禄’、‘ 不敢怀非誉巧拙’。女偊所说的‘外生’,实同于梓庆所说的‘忘吾有四枝形体’。女偊所说的‘朝彻’,实同于梓庆所说的‘以天合天’。修养的过程及其功效,可以说是完全相同;梓庆由此所成就的是一个‘惊犹鬼神’的乐器,而女偊由此所成就的是一个‘闻道’的圣人、至人、真人、乃至神人。”[3]49对艺术品的加工和圣哲之人的形成,因修养过程的相同而相通。徐复观还用“和”的观念将道与艺相沟通,“庄子所特提出的‘和’的观念,‘和’是‘游’的积极的根据。老、庄的所谓‘一’,若把它从形上的意义落实下来,则只是‘和’的极至。和即是谐和、统一,这是艺术最基本的性格。”[3]58这就看到了道与艺术的共同性格。在谈艺术想象时还用象征性将艺术与哲学相贯通,“庄子的艺术精神,触物皆产生出意味的表象,亦即是产生出第二的新地对象。所以《庄子》书中所叙述的事物,都成为象征的性质;而艺术实际即是象征。”[3]82对于书法成为艺术的具体问题,徐复观亦用类推方法:书法从实用的工具而艺术化,在于性格与绘画相同,再加以使用工具相同,既然绘画是艺术,那么书法亦为艺术。从而他认为当下对“书画同源同法”的理解“把两者本是艺术性格上的关连,误解为历史发生上的关连”。所以,书法因与绘画性格上的相关性而艺术化,庄子哲学与艺术因性格上的相关性也最终艺术化,以此实现了艺术精神与道的贯通。
最后实现道艺贯通的方式是借助西方美学。因为艺术和美学的关系较哲学近,徐复观就是通过“道”与西方美学相比较,认为“道”与西方美学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相似的。利用美学与艺术的关系,以类推方式将庄子的“道”与艺术精神贯通,从而挖掘出庄子哲学的艺术性特征。“我引薛林和左尔格乃至以后还引到其他许多人的艺术思想时,不是说他们的思想,与庄子的思想完全相同;也不表示我是完全赞成每一个人的思想。而只是想指出,西方若干思想家,在穷究美得以成立的历程和根源时,常出现了约略与庄子在某一部分相似相合之点。”[3]47正因为这一相似,徐复观推理出庄子哲学的艺术性特点。
徐复观用左尔格“理念是由艺术家的悟性持向特殊之中,理念由此而成为现在的东西。此时的理念,即成为‘无’,当理念推移向‘无’的瞬间,正是艺术的真正根据之所在”[3]47,契合了庄子对“无”的崇尚。“缪拉认为一切矛盾得到调和的世界,是最高的美。一切艺术作品,是世界的调和的反复。多特罕塔也认为美是矛盾的调和。”[3]58用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暗合了庄子之为“和”的分析。徐复观认为庄子的“和”是“游”的根据,与和谐、统一的艺术性格相契合,从而说明庄子之“道”的艺术性。徐复观还分析了庄子的超越思想,“庄子的超越,是从‘不谴是非’中超越上去,这是面对世俗的是非而‘忘己’‘ 丧我’,于是,在世俗是非之中,即呈现出‘天地精神’而与之往来,这正是‘即自的超越’”[3]89。“即自的超越”之成为艺术精神,徐复观也借助西方美学来说明,“正如卡西勒所说:若如西勒格尔的想法,仅仅是有‘无限’的观念的人,才能成为艺术家,则我们的有限世界,感觉经验世界,便没有美的权利。薛林说:‘美是在有限中看出无限’。”[3]88西方由有限到无限体现的是对美的追求,庄子由第一自然到第二自然的追求与之相似,体现的也是美的精神,只有有此“美的精神”观念之人,才能成为艺术家。
综上,徐复观除了用艺术精神把道和艺相联系,还用类推来阐释庄子哲学的艺术性,这种推理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庄子哲学的艺术性问题,但是逻辑性的欠缺也很明显。所以,人们对徐复观所论“道”与艺术的关系持怀疑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怀疑只能是程度上的深与浅,而不应是关系上的有与无。
三、徐复观的艺术范畴
徐复观强调表现为主的艺术,但也并未否定以技术为工的艺术。首先,如前所述,在对“逸神妙能”各品艺术的研究中,他未否定“能品”的艺术性,只是认为它距离庄子真正的艺术精神稍远。另外,徐复观认为“淡的意境、形相,为庄子所追求的文学的艺术性”[3]349,“淡由玄而出,淡是由有限以通向无限的连结点”[3]353。“淡”是庄子特别强调的艺术精神,徐复观认为,精工的艺术同样体现了“平淡”之美。“董其昌五十以后的平淡,实以五十以前的精工为基础。所以精工、平淡,实系一种发展;并且精工虽不同于平淡,但精神却是相通;所以平淡是韵,精工同样是韵。”[3]392在谈院体画时,他认为:“今日故宫博物院无名的若干宋人画册,就我的看法,多出于画院院史之手;精能之至,亦通神妙,远非许多率易的文人画所能及。”[3]378技是艺的手段,精工是神妙的过程,徐复观肯定精工艺术,认为“精能之至,亦通神妙”。徐复观认为董其昌南北宗的负面影响就有高举“墨戏”投机取巧,一味追求南宗写意之“苟简自便”,从而使绘画日趋浅薄,这说明他并未一味强调平淡与玄远。
对于刚性笔触,徐复观认为:“在‘以天下为沉着’及‘独与天地往来’的精神中,实含有至大至刚之气,以为从沉着中解脱而超升向‘天地精神’的力量。所以,老学、庄学之柔,实以刚大为其基柢。于是,庄子之本来意味之所谓淡,乃是不为沉浊所污染,不为欲望所束缚的精神纯白之姿。在此精神纯白之姿中,刚与柔实形成一个统一。”[3]393刚与柔一样,是在观者与艺术家精神上得以贯通,其前提自然是“艺术精神”的充实。
所以徐复观并未一直强调优美为主的文人画,只要是艺术精神的表达,体现壮美的和精工为主的艺术他同样不排斥,当然还包括对“功利”艺术的认可,那么他是怎么看待艺术的“功利性”呢?
无功利被徐复观看作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对于“成教化、助人伦”的“功利”艺术,徐复观认为:“成教化,是说明艺术在教育上的功用;助人伦,是说明艺术在群体生活中的功用。艺术虽以无用为用;但此无用之用,究其极致,亦必于有意无意之中,汇归于此两大文化目标之上,然后始能完成艺术的本性。……所以彦远这两句话,为艺术指出了它自身最后的归极之地。”[3]227徐复观认为艺术的社会性与真正的艺术性是相通的,“文艺之所以能够成为文艺,必定不是看一二权贵的颜色,而‘必是言当举世之心,动合一国之意’,其根底乃在保持自己的人性,于是个性充实一分,社会性即增加一分”[4]4。艺术的个性与社会性通于性情之正,虽然艺术家并未刻意考虑艺术的社会性,但因艺术家本身的纯粹精神更近于社会的共性,“照中国传统的看法,感情之愈近于纯粹而很少杂有特殊个人利害打算关系在内的,这便愈近于感情的‘原型’,便愈能表达共同人性的某一方面,因而其本身也有其社会的共同性”[4]5。此处纯粹的感情倾向于庄子虚静之心。在“为人生的艺术”中,“诗人是‘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即是诗人先经历了一个把‘一国之意’、‘天下之心’,内在化而形成自己的心,形成自己的个性的历程,于是诗人的心、诗人的个性,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心,不是纯主观的个性,而是经过提炼升华后的社会的心。……于是使读者随诗人之所以悲而悲,随诗人之所以乐而乐,作者的感情和读者的感情,通过作品而融合在一起”[4]2。来自特定时代的艺术家,将他对社会时代性的理解转变为时代的共同意识,这一共同意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精神,能与大众产生共鸣,这样的艺术品在社会上总能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采薇图》还是《流民图》,都是艺术家这一意识的具体化,艺术家抛却社会的沉渣,凝练意识以通于社会,这样的艺术品极具战斗性,无疑是伟大的。
“为人生的艺术”因创作主体的自由与完整,因与对象的主客相融,观者通过艺术品和艺术家作感情上的交流,从而达到“韵外之旨”的意境要求,这和徐复观的“艺术精神”并不矛盾。如果“纯艺术”是通过“无”实现艺术与艺术精神的贯通,那么“为人生的艺术”则是通过“有”来实现艺术精神的要求,前者通过符号讲韵味,后者通过形式讲故事,前者不止于符号,后者亦不止于故事,前者指向作品本身,后者回到社会起点,前者与自然相连,后者与社会相通。同样作为“艺术精神”的表达,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综上,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探索主要基于中国文化,他所谓的艺术精神实际是一种无功利的、自由的审美状态,它为自由的人所共有,将之与特定技巧相结合就形成中国传统艺术。在艺术活动上,他重视于“第一自然”见“第二自然”。徐复观通过类推的方式将艺术与哲学相联系,为中国传统艺术找到终极根据。另外,徐复观的艺术精神既重视艺术的审美性,又强调艺术的社会性,最终归结到与庄子哲学相联系的“艺术精神”。
[1] 章启群.怎样探讨中国艺术精神?[J].北京大学学报,2000,(2).
[2] 赫云,李蓓蕾.论中国传统绘画的文化精神支柱[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44577480100sbhe.html.
[3] 李维武.徐复观文集:第4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4]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