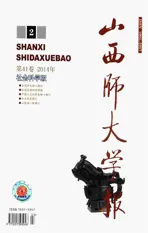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制度之维
2014-04-10罗会德
罗 会 德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思政教研部, 上海 201620)
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并发挥作用,它必须依托一定的制度基础才能切实发挥道德教化、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效能。尤其是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各种道德价值观念并存,相互冲突,而要使一种核心价值观真正在社会中确立起来,能够为人们所认同接受,并自觉履行遵守,就必须按照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进行制度设计,使大众的道德始终得到制度道德的规约和关怀。
一、现代社会制度是价值观培育的工具性基础
制度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保证,也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由人们所制定的具有普遍性的、以激励和约束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和规则体系。在人类社会文明史上虽然各种社会基本制度都是按照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体系建立的,但只有当统治阶级建立起符合自己价值标准的社会基本制度之后,其价值观念体系才能成为在全社会占统治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核心价值。“制度中蕴涵着文化基因,是人们的伦理关系、价值关系及其评判尺度的现实凝聚物。”[1]192社会基本制度直接决定着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着人们各自的政治、经济地位,因而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直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制约作用。
首先,现代社会制度为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刚性保障。一般而言,制度与价值观的形成存在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任何制度都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形成的,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确立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总是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价值观构成了制度的内在精神和品格。“意识上的变革——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2]527“社会价值的改变——即意识形态的变革——是制度变革的主要因素。”[3]69另一方面,制度一旦形成,又对人的价值判断起引导和规范作用,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保障和支持。例如,政治制度的价值在于使政治的价值理念获得具体的落实。政治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是,“价值规定了行为的总方向。然而,价值并不告诉个人在既定的情境中干些什么;价值太一般了”[4]145。因此,“价值通过合法与社会系统结构联系的主要参照基点是制度化”,“价值系统自身不会自动地‘实现’,而要通过有关的控制来维系。在这方面要依靠制度化、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一连串的全部机制。”[4]141从国外经验来看,多数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建设都以制度安排作保障,以保证行为的规范性、过程的持续性和结果的可靠性。
其次,现代社会制度为核心价值观培育确立了可能性空间。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保存其历史性,又要培育新的特质。制度通过把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进步思想观念具体化、固定化,通过反复训练,使人们逐步接受某一制度所提倡的价值观念,并将其由外在的他律转化为内在的自律,形成适应现实生活世界的新的符号系统,这也就是新的价值观的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吸收各种已有文明成果和社会发展中涌现的新鲜文化元素,不断创新,营造新的文明体系的过程。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柔性的社会特质,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刚性社会制度的规范、引导和灌输。现代社会制度本身也促进新的价值观特质的生成,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实践养成,而且要靠制度机制加以保障、固化和“定型化”,需要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制度建设的良性互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制度保障
“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路径,并且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框架,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5]429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需要优先考虑其制度基础。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制度是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结构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需要创新和完善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制度。
(一)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经济机制。唯物史观认为,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意识形态的产生和性质,经济的变革决定意识形态的变革。对此,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591—592人类整个思想发展史证明,人们的精神生产及其价值观念将随着物质生产的变化而变化。根据这个原理,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辩证关系,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我国的经济变革联系起来,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现实联系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性互动,不能脱离经济的发展而空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令人欣慰和自豪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但是“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7]244经济建设的确取得巨大成就,但未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越来越多,譬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很低;环境、资源瓶颈制约越来越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统筹发展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还十分明显,等等。这些社会现实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许多任务还远未完成,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邓小平所言:“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8]225
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9]544削弱或消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切入,把经济建设摆在中心位置,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最根本任务,努力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经验支持。
(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政治法律机制。任何社会要使其主流价值观得到广泛认同并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就必须使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及司法行政等很好地体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我们所要培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反映,更应在具体制度的设计安排、政策法规中得到充分体现。所以,我们必须以制度安排为依托,综合调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各种手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体现到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和社会管理之中,使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鼓励与惩罚有机结合,形成有效的法律支持、政策保证和机制保障,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10]326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指出:“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律本身都促成对其自身神圣性的信念。它以各种方式要求人们的服从,不但付诸他们物质的、客观的、有限的和合理的利益,而且还向他们对超越社会功利的真理、正义的信仰呼吁,也就是说,以一种不同于流行的现世主义和工具主义理论的方式确立法的神圣性。”[11]44美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也极具洞见地指出:“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情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12]315由此可见,公民的法律情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法的神圣性的意识和观念,对法的“宗教”情怀和信仰,是全部法治建立、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保障,是法治本身之存在及其具有效力的“合法性”根据。这种对于任何法治都必不可少的情感和信仰,只有通过不断的公民意识教育才能形成。法治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法的神圣化的过程,即法的神圣性通过对公民进行法治的精神性信仰教育而内化为公民的内心信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的神圣性被强化,其价值蕴涵也得到了极大提高。
社会主义法律通过一系列的规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要求的具体内容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形成了一个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框架和规则,并通过各种组织制度的结合构成社会中的制度调节和法律调节,强化了个体的集体意识和道德意识,保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取得实效。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部门在制定政策和法规时,还存在维护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倾向,有些还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出现具体政策与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积极健康的导向作用。因此,要尽快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政策、法律的规定,同时用法律的权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三)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社会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密切相关。首先,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建构过程来看,虽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是以制度化的形式由国家来推行,但这一价值观的产生又是各领域的理论工作者、专家、学者在论辩中集思广益的结果。社会建设所具备的价值整合功能,能有效凝聚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促进作为规范性社会思想共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确立。其次,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而言,除了借助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外,亦离不开群众的积极参与。正确的价值体系只有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理解掌握并转化为社会的群体意识,才能为人们所自觉遵守。再次,借助于包括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等具体制度(体制)建设及社会事业的发展,可以有效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协调各方面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的身心和谐,利于“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的营造。因此,社会建设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社会基础保障。
长期以来,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教育、解疑释惑的工作者,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工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宣传、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党和政府在加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社会建设。这些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奠定了基础。但也应当承认,我国的社会建设诸方面的发展还有许多不足,如教育发展中,城乡间、东西部间的发展还不均衡;尤其是社会不同群体间受教育的公平性还存有问题;在社会保障方面,住房问题、医疗保障问题、养老问题等,群众还不十分满意。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成员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与积极支持。
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社会保障,需要着眼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建立健全人才管理机制、工作平台和课题研究机制,整合研究力量,优化资源配置,努力打造高水平的资源共享的宣传思想工作新平台,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和宣传。二是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当前,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制度保障,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注重制度的整体设计,协调推进制度与文化建设。要在总结以往制度改革经验与教训、把握制度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对制度改革的步骤、方式、整体布局做到科学规划。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意义,因为一切理念、设想、措施等最终是以制度的形式存在,只有通过制度才能得到规范、公正、长久的实行。另外,在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文化建设,因为制度的土壤是文化,制度的根基是文化。[13]
二是要把握制度改革的时机,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发展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作为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的思想内核;大力倡导和谐的思想观念,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通过对和谐的肯定评价和相应的奖惩褒贬,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以及法律规范、行为准则,以指导和约束各种社会行为。
三是要以实效性为检验标准,不断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解决制度供给方面问题的同时,还要解决制度的适应性、实践性问题,即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提高制度的质量和水平,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实际效果。好的制度,来源于集体的智慧,来源于丰富的实践。一项制度安排的选择与供给,只有体现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利益,才能最终得到认可和实施。因此,在制定制度时,就应当坚持公开原则,把制度的制定过程置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主体的广泛参与之中,经过反复征求意见,集中民智,达成共识,使形成的制度真正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实践证明,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成本最小的资源,制度建设每前进一小步,人类文明就会前进一大步。在现实社会实践中,只有找到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质规定和符合我国国情的有效实现形式,并通过一系列科学合理的具体政策、法规、制度和措施,正确地调节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落到实处,使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地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各种现实利益,也才能为人民群众理解、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1] 鲁鹏.制度与发展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 (冰)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M].吴经邦,李耀,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 (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梁向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5] 曾小华.文化、制度与社会变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田海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12] (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M].董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3] 陈秀梅,于亚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路径[N].河北日报,2007-05-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