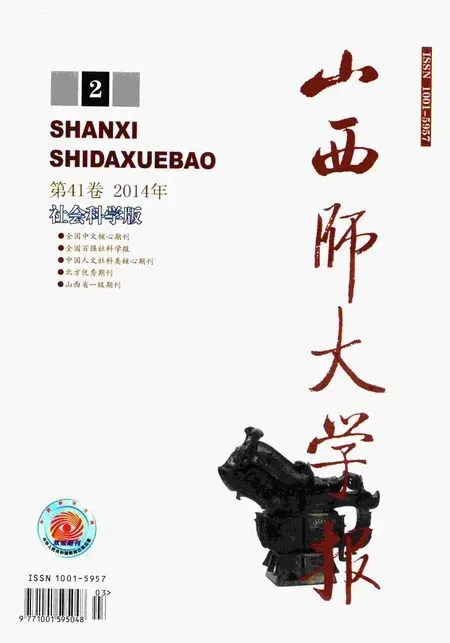社会经济转型与代际关系变动
2014-04-10冯华超钟涨宝
冯华超,钟涨宝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武汉 430070)
费孝通在论述中西文化差异时将中国的代际关系概括为“反馈模式”,而将西方的代际关系概括为“接力模式”,认为二者的不同在于赡养父母在西方并不是子女的义务。[1]李银河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指出,反馈关系和接力关系二者之间的区别,应当说不仅仅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区别,而是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区别。她论断的依据是,当西方处于农业社会阶段时,也存在代际之间的反馈关系,而在中国现阶段的文化中,反馈关系正在让位于接力关系。传统社会反馈关系存在的基础在于农民经济基本上还属于非货币经济范畴,老年赡养成为子女的绝对责任,在这种非货币经济造就的养老方式之上形成的美德就是孝道。而到了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农民经济由非货币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家庭养老方式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转变,反馈关系就可能为接力关系所取代。[2]207—212
现代化理论认为,在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扩展式的家庭关系纽带将被弱化,传统的家庭形式将变得更为松散,个人与扩大亲属制度相联系的义务关系同时被削弱。[3]但是我国家庭关系深受地方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影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家庭没有失去它独特的作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家庭关系随现代化的进程而减弱[4],传统的家庭团结力量延续使得家庭凝聚力超越了现代化的作用[5]。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产生了大规模的社会流动,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以及代际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经济转型在给代际关系产生影响的同时,也赋予了代际关系以“问题性”的意义所带来的经济转型与代际关系的变动。
一些学者将代际关系的变化归结为国家推行的制度变革的结果,即外部力量的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农村社会的介入主导了乡村代际关系的变动。[5][6]250而另一些学者则质疑这种国家政治决定论,贺雪峰就认为,建国以后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虽然有所变动,但是集体经济制度本身的特点和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尊老爱幼、父慈子孝的借用和倡导仍然使代际关系保持相对平衡,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代际关系逐渐失衡。[7]Jack M.Potter也认为,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并没有改变传统的的包括代际关系在内的基本亲属关系结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建设运动却使得传统的亲属关系结构渐渐解体。[8]显然,他们认为是经济转型而不是国家导致了乡村社会代际关系的根本变化。具体来说,社会经济的转型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代际交换的社会化程度加深
代际关系可以划分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微观层面的代际关系主要涉及家庭内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关系,而宏观层面的代际关系则涉及社会上老一代、中一代与年青一代之间的关系。[9]在传统社会,代际关系仅仅涉及家庭内部,代际之间的资源分配和交换、情感的交流和沟通以及道德义务的意识与承担等,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亲子之间,中国的孝道规范和社会结构更加强调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威,强调子女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以维护子女和父母的和谐关系为准则。而在广泛的社会层面,资源的分配和交换、情感的交流和沟通以及道德义务的意识与承担等关系和问题并不存在,或者只有在涉及公共财产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和分配时才会得以显现。因此,传统社会的代际关系主要体现在家庭内部,以孝道规范等来调节代际之间资源的分配和共享,而在社会层面,仅仅体现在尊老敬老的道德伦理上,并不能调节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和共享。
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个人所拥有的资源逐渐超出了家庭的范围,包括家庭内部的资源,也涉及更广泛的来自社会方面的支持。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个体在生命周期阶段的资源转移,也越来越多地对职业发展和社会支持产生需求,代际关系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10]在西方国家,由于养老基本社会化,家庭内的代际交换财富流向偏重于从老人向年轻人的“向下流”方向,国家和社会承担了大量的责任。在我国,代际之间的资源交换主要以家庭内的交换系统为主,公共部门交换系统的转移和市场交换系统的转移较少,但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口老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加深以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预计公共部门交换系统的转移和市场交换系统的转移的份额会逐渐增加,而家庭内的交换系统的转移会逐渐减少。[11]因此,可以说社会经济转型推动了代际关系的社会化过程,使得代际之间的资源获取方式开始由家庭转向社会,并更多地依赖社会,家庭的养老功能开始外移。
(二)养老经济支付能力提高
在我国,工业化水平提高的直接目的和后果就是人民能够共同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工业化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从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来说,无论是家庭中父母的收入还是子女的收入,都有助于提高家庭中老年人的保障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经济支付能力。[12]老年人有了收入,可以提高自身生活的独立性,可以从外购买养老服务,这不但减少了对子女的依赖,也减轻了子女的负担,从而大大提高了家庭养老保障水平,家庭各成员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需求。另一方面,老年人有了收入,就有了一定的资源与其子女可以相互提供多种形式的协助和支持,这为持续的合作和义务提供了稳固的结构性支持,有助于代际之间建立和谐、良好的关系。但是康彩芳认为,人们收入水平的增长,消费以及商品性支出的增加将改变农村老年人供养以实物支付为主的传统方式,当子女对老年人的供养逐渐向以货币支出为主转变的时候,就使得老年人的经济供养来源对市场的依赖性加大,缺乏稳定性并隐藏着各种风险,养老的质量和水平也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13]
(三)养老保障水平提高
农业社会,国家无力负担庞大的养老保障,而是将责任托付于家庭,并对家庭养老予以合理化、规范化,这样,在国家和社会的保障水平较低的时代,就只能通过家庭内部的赡养来解决养老问题。而进入到工业社会,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覆盖面广、层次较高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始逐步建立。但是,养老的社会保障政策却给代际关系带来正向和负向的影响:一方面,国家社会保障政策的推行将削弱实际上已经存在的非正式保障安排的基础,优越的保障政策代替家庭向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服务,就将家庭的责任推向一边,弱化了代际之间的相关性。[14]张航空等通过上海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老人养老金的增加,代际经济支持会被养老金挤出,但是这种挤出是有限度的,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不会被全部挤出,也许是由于国家在这个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支持减少,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更多地成为一种象征性行为。[15]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保障政策的供给使得老年人在能够保障最低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可以与子女进行各种形式的协助和支持,与子女之间的给予或接受的互惠程度会更大,越能够为持续性的合作和义务提供稳固的结构性支持,有助于加深亲情,增大代际之间的亲近机会。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政策与家庭责任的负向关系,但在家庭内部,却有助于增大代际之间的亲情和互爱。怀默霆通过对保定和台湾家庭中的赡养义务的对比发现:1950年代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惯例为老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使得他们不必依赖子女。虽然子女提供的是辅助性的赡养,但社会主义的惯例使得多数子女乐于住在父母身边,随时可以并乐于提供代际支持,代际交换更为平衡,父母对于所获得的子女的赡养以及子女所表现出来的孝敬程度都表示满意,但是1994年制度保障的惯例发生变化,使得老年人的晚年安全感受到了威胁。[16]
(四)全民的教育程度提升
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全民的受教育年限和程度提升。李帅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教育发展水平的高低会引起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变化[17],而代际关系的和谐程度,与各代人的教育程度是密切相关的。文化教育程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代际关系产生了影响[18]181—187:从宏观层面来看,文化教育程度的高低对老年人的心理自信程度和老年人对自己与社会各层面的代际关系评价有很大影响。文化教育程度高的老人自认为能融入社会的自信度较强,这些老年人的代际关系比较好,能够和社会各层面的代际相融共处,而文化教育程度低的老人则缺乏各代之间相融的条件基础,不易融入社会。另一方面,老年人文化教育程度越低,对各方面的要求则相对越低,容易产生满足感,而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对衡量社会关心老年人的标准越高,关注的内容也比较广泛,很难达到这类老年人的意愿水平。从微观层面来讲,文化教育程度决定着每一代人对问题的看法以及处理问题的方法,还与经济独立性有一定的关联。一般地,教育水平高的人考虑问题比较周到,处理代际问题更加理性,家庭代际关系问题处理得也比较好,经济上也相对独立,相互依赖程度较低,代际之间也能够相互尊重,关系比较密切。而文化水平较低的老年人收入相对较少,生活经济来源主要依赖子女,自信心不够,容易把自己视为家庭的负担,在家行事比较谨慎,唯恐惹子女不高兴,从而产生代际矛盾。[19]
(五)父母对家庭控制力下降
农业社会,农耕劳作是绝大多数家庭成员的职业,人们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和生活,在家长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集中收获并以实物形式体现大家共同的劳动成果。人们实行同居共财的生产方式,生产和消费都是以家计的形式进行,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传统社会赋予家长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也就赋予了家长最高的权威。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封闭的社会决定了在家庭老年人的赡养中强调的是子女的绝对责任和义务,父母对子女有较大的控制权。此外,由于生产和生活经验是由年老一代传递给年轻一代的,老年父母即使在年老力衰不能再参加生产劳动时,凭借其丰富的生产经验和人生阅历仍可以对子孙后代的生产和生活进行指导和监督[20],这也使得亲子两代之间的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21]。吴小英则进一步指出了其原因,她认为这种原始的、封闭的文化只能在整体性和复制性的系统中依靠长辈对后辈的控制形式延续下去,“长老统治”下的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正因为长辈牢牢掌握着资源、权力和财产,使得代际之间的冲突和隔膜被掩盖在老年人的控制和权威之下,因而表现得较为和谐。[22]
然而,进入到工业社会以后,代际文化传递的模式逐渐发生变动。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知识的不断更新使得许多过去的经验过时,失去了传承的价值,老年父母无法再对子代的生产工作和生活进行具体的指导,在生产生活上的优势与权威逐渐消亡,其地位和社会经济价值都急剧下降,对家庭的控制力也随之下降。[21]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外流规模加大,流动不仅提供了子女独立于父母的机会,也使得子女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和对居住地的选择。父母对家庭内资源的控制权削弱,这不仅包括失去了对子女经济收入的控制力,还可能包括对子女婚姻控制力的下降。随着家庭收入格局的改变,父辈对子辈的控制逐渐减弱,家庭内部的成员关系也从过去的“主从性人际关系”逐步向“平权性人际关系”转化。[23]12—21肖倩认为代际权力关系的变化导致代际回报原则的变化,对代际之间的赡养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24]当子代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方面不必完全依靠父辈和家庭的传承和支持,而可以依靠个人的努力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取得成功时,代际关系容易变得松散疏远。[25]此外,当子辈独立性越来越强,父辈的权威日益消失,代际关系不仅受到空间上日益分割的影响,还受到利益离心化的影响。[26]
(六)人口迁移和外流带来的影响
城市化过程中产生了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收入“剪刀差”,在巨大经济利益的刺激和诱导下,大量人口离开家乡流动到距离较远的、收入比较高的地区。古德认为,现代化进程中离开家庭和土地,使得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模式,老年人在传统联合型家庭生活的可能性减小。而代际支持资源减少最终会导致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降低,这将对缺乏固定收入保障和社区服务支持的老年人产生深远的影响。[19]此外,人口外流减少了子女和老年父母共同居住的可能性,子女对老年父母生活照料增加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家庭对老年人的持续供养能力可能发生变化。宋璐等认为,缺乏自身资源的老年母亲并没有从子女外出带来的经济收入增加中获得比老年父亲更大的收益,老年父母只好付出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以增强子女的养老能力,巩固与子女的养老契约而得到补偿性回报,这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使得他们的福利和健康状况恶化。[27]。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对核心家庭和个人价值的关注会淡化迁移者的“孝”的观念,在城市生活越久的人更加关注独立和平等,他们自身思想意识的转变会导致他们传统的赡养责任不断弱化,最终影响到他们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也使得老年人自身的养老观念发生转变。[27]31因此,传统的老年学理论认为,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外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家庭结构和居住距离的变化,这直接和间接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因此城市化进程是不利于老年人的。[26]
Mason则认为,虽然人口迁移可能会侵蚀家庭代际支持,但人口外流所带来的人均收入的提高可能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的福利状况,使他们通过个人财富的累计或收入转移获得更高程度的经济独立,还可能从富裕的子女那里得到更多经济资助。[28]年轻一代也会更加注重独立和平等,可能会接受西方赡养老人的一些观念,使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平等、和谐。[29]宋璐等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使子女对老年父母经济支持增加的可能性上升,而且子女外出降低了子女间以及子女与老年父母间产生摩擦的可能性,赡养老年父母的责任分工在留守和外出的子女之间进一步明确,提高了其对老年父母增加情感支持的可能性,促进了代际间的感情亲近程度。[19]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从家庭成员的外迁中获益,Adi在印尼爪哇的调查发现,有一部分家庭的经济状况在其成员外出之后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因为这些移民在外的收入还不足以抵消他们的外出成本和在外花销,更没有能力为家庭和老人谋福利。[30]43
(七)女儿参与养老
传统父系家族制度中,男子参与收入和地位高的工作,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妇女从事无收入的劳动,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不大,评价一个妇女的主要标准在于她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儿子的能力。在注重宗法血缘关系的传统家庭中,妇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继承家业的权利,此外,妇女不但不能给家庭挣得更多财富,在出嫁的时候还需要娘家出嫁妆。受传统家庭结构的影响,父权体系切断了妇女在婚后与其娘家的紧密联系,其对娘家的回馈也特别少。因此,传统社会妇女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较小,没有继承娘家财产的权力,也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唐灿等将继承财产的权利和赡养的义务相联系,认为女儿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是以不承担赡养责任为补偿性代价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女性身份和归属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女儿在出嫁前身份处于暂时的性质,在父系家族中没有地位和权力,是家族的附属成员,出嫁后就成为“泼出去的水”,而且在出嫁后女性也是所在家庭的附属,经济上并不独立,也就没有能力对父母进行回报。[31]
进入到工业社会,社会生产和劳动越来越社会化,生产技术和工具的改进解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外出就业,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社会化劳动的参与使得广大妇女有了自己的经济收入,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增加,这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提供了一个摆脱社会性别劳动分工的良机。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和传统劳动分工社会性别差异的缩小,可能会改变中国传统的主要依靠儿子的养老方式。[27]48已有研究证实,虽然儿子仍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但一个趋势是女儿在养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1]。女性外出就业对老年父母经济支持增加的可能性大于外出儿子增加的可能性,外出促使儿子和女儿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工缩小;外出女儿对老年父母情感支持增加的可能性大于外出儿子增加的可能性,代际情感支持的性别分工进一步扩大。[19]。由此可见,女儿参与养老成为老年人家庭养老理性化的选择[32]。
(八)代际支持行为逐渐理性化
在传统社会,父母抚育子女在老年的时候得到子女的反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自然的代际亲情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运行已带有明显的市场经济特征,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交往行为介入了理性化的因素[33]151,关系越亲密,越有可能被用来实现功利目标[34]。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村庄社区的生活意义系统被消费文化塑型,使得村民以在消费竞赛中不断获取“尊严感”和“自我实现感”作为生存的动力。在这种持续进行的、强调物质利益的角逐中,他们通过向父辈的索取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继而舍弃了对于老人的责任和义务。[35]朱静辉通过对安徽薛村的个案研究,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代际之间的关系逐渐理性化,虽然老人仍旧以长时间的道德感情的互惠模式来考虑与子辈之间的关系,子辈却愈发用理性方式考量代际关系,更加注重经济物质上的交换,赡养动机不是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恩情,而是与市场交换类似的有来有往的给予方式。[36]阎云翔认为,国家在公共生活的退出,使得新兴的市场经济、消费主义抢夺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农村出现大量的“无功德个人”,他们强调个人享受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无视对他人的义务和责任,在代际关系中,如果父母对子女不好或者没有尽到责任,子女就有理由减少对父母相应的责任,代与代之间的相互报答必须有不断的有来有往才能维持下去。[6]255—266目前,大量的研究也证实了代际关系中人们的行为逐渐理性化,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逐渐淡化,代际支持必须有所交换才能得以维持。[21]
综上所述,代际关系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现象,它总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仅仅将研究的视角和问题局限在一个有限的方面,而对代际关系所嵌入的外部宏观社会环境缺乏关注是不够的。20世纪后半期,我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转型,代际交换的社会化程度加深,养老经济支持能力和保障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父母对家庭的控制力下降,人口外流一定程度拉大了亲子在地理和社会上的差距,人们的家庭伦理观念变化,代际支持行为逐渐理性化,种种因素使得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我国社会的转型并非简单的由计划经济体制直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而是呈现出两种经济体制的社会机制的共生。[37]而转型期的代际关系特别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共生,从而出现与假定的现代化模式不一致而显示出符合传统的特征,这使得我国的代际关系要比西方社会更加复杂。社会经济转型是代际关系变动的外在宏观背景,也提供了一个考察代际关系的视角,转型的复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代际关系的变动也无规律可循。有学者推断,当子辈代际支持行为越来越理性化,父母的思想意识会提高,他们会降低对子女孝道的预期,这样两代人在责任和义务分割方面将会有更多的理性和计算,这样的结果就使代际之间的平衡关系在经历一段时期的平衡之后,将会重新达成新的均衡,但是这是一种类似接力的平衡,相对理性及较少奉献。[38]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仍有待验证,就全国范围来看,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仍是主要的养老方式,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城市,尽管大部分老人有维持经济独立的能力,但是子女的支持仍是养老的重要方式之一,绝大多数人仍将赡养父母视为自己的责任,代际之间无论是分开居住还是住在一起,仍旧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在农村,广大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仍旧要靠子女来提供,在子女外出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帮助子女带孩子、做家务等来支持子女,子女对老人也有经济和情感上的反馈,而且,城乡一个普遍的趋势是女儿参与养老,给父母的支持和帮助越来越大。因此,对于代际关系研究,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前提: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现代化的市场交换逻辑日益深入中国人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内心,子女的支持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代际之间的差异、冲突、互惠可能是多种力量作用下彼此较量和妥协的体现。
[1]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6).
[2] 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3] WJ Good.家庭[M].魏章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 边馥琴,约翰·罗根.中美家庭代际关系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2).
[5] 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J].中国学术,2001,(4).
[6]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M].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7] 贺雪峰.农村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J].江海学刊,2008,(4).
[8] Potter SH, Potter JM.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9] 王树新,马金.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代际关系新走向[J].人口与经济,2002,(4).
[10] 吴 帆,李建民.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代际关系[J].学海,2010,(1).
[11] 于学军.中国人口老化与代际交换[J].人口学刊,1995,(6).
[12] 丁士军.经济发展与转型对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影响[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4).
[13] 康彩芳.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变迁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7.
[14] 徐征,齐明珠.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如何建立正向的代际关系[J].人口与经济,2003,(3).
[15] 张航空,孙磊.代际经济支持、养老金和挤出效应——以上海市为例[J].人口与展,2011,(2).
[16] 怀默霆.中国家庭中的赡养义务:现代化悖论[J].中国学术,2001,(4).
[17] 李帅,毛蒋兴,侯刘起.我国文盲率与经济及教育发展水平关系实证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2,(11).
[18] 王树新.社会变革与代际关系研究[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3.
[19] 宋璐,李树茁.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20] 靳小怡,李树茁.中国社会转型期老年人生活状况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21] 刘桂莉.眼泪为什么往下流?──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倾斜问题探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22] 吴小英.代际冲突与青年话语的变迁[J].青年研究,2006,(8).
[23] 沈崇麟,杨善华,李东山.世纪之交的城乡家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4] 肖倩.农村家庭养老问题与代际权力关系变迁——基于赣中南农村的调查[J].人口与发展,2010,(6).
[25] 周祝平,等.城市化加速和体制转轨背景下的代际关系研究[J].中国老龄研究,2004,(3).
[26] 张文娟,李树茁.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4,(8).
[27] 宋璐,李树茁.当代农村家庭养老性别分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8] Moson K. Family change and support of the elderly in Asia:What do we know?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1992,(3).
[29] Yuan F.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Chinese elderly in families and society. Aging China:Family, economic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ransition”. In JH Schulz and DD Friedman(eds.)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1987.
[30] 王萍,李树茁.农村家庭养老的变迁和老年人的健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1] 唐灿,马春华,石金群.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浙东农村家庭亲子关系的性别考察[J].社会学研究,2009,(6).
[32] 高建新,李树茁,左冬梅.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子女养老分工影响研究[J].南方人口,2012,(2).
[33] 潘鸿雁.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4] 李沛良.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题.载北京大学社会学所.东亚社会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5] 袁松.消费文化、面子竞争与农村的孝道衰落──以打工经济中的顾村为例[J].西北人口,2009,(4).
[36] 朱静辉.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与老年人赡养——以安徽薛村为个案的考察[J].西北人口,2010,(3).
[37] 刘平.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7,(1).
[38] 贺雪峰.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从“操心”说起[J].古今农业,2007,(4).